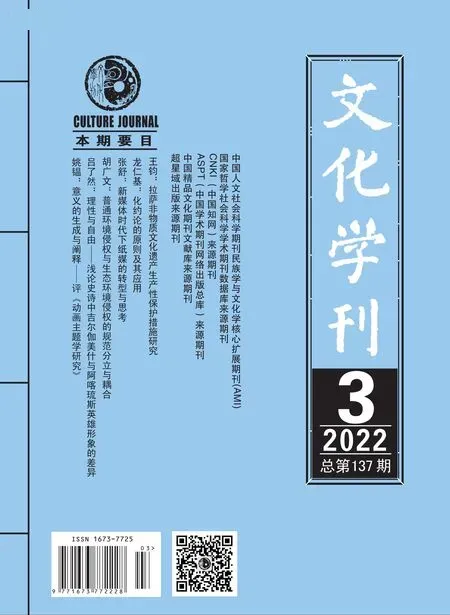王阳明诗歌中“风”意象探微
杨薏冉 卓光平
王阳明诗歌中的自然意象随处可见,“风”意象便是其中的典型,作者赋予“风”不同的丰富内蕴,既有直接饰有情感色彩的“风”,又有与其他气象名词搭配而成的“风”。一代圣哲如此钟爱风,与“风”意象的独特性有着密切的关联,“风和人的情感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异质同构关系,概括来说,人类的情感思绪如风一般无形无影而又丰富多样。”[1]造物之风穿梭牧野与广厦,内心之风游离佛禅与政务。造物之风能够进阶内心之风,与风自身的可视性差可感性强的特点有很大关联,更是与王阳明注重内心体认的心性相契合。本文从王阳明诗歌中的“风”意象着手,感受王阳明在不同视角下对外物之风的情感变化,体悟“风”意象喻指的王阳明的情、志、心,进而得出王阳明看似观“风”记“风”实则审视自身的结论,由此展现普通情思与儒、道、佛三教思想融合的通达境界与物我合一的圆融境界。
一、以风传情:文士笔下的“风”
风来去无影且变幻万端,世间各处无所不往,王阳明诗歌中的“风”多表现自己的人生起伏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无常,呈现出景明则喜与物暗则悲的两面状态,由此体现王阳明常从普通文人墨客的角度感受外物之风。“景明”与“物暗”指的是造物之变化,喜与悲指的不仅是文士笔下“风”的状态,更是诗人的“情”。其中喜包括游赏玩乐之喜与仕途顺利之喜;悲则包括怀古伤今之悲与生活境遇之悲。
文士笔下的“风”可承载王阳明的喜,其中游赏玩乐之喜占喜之大成。弘治十六年(1503),王阳明前往杭州西湖疗养,写下“溪风欲雨吟堤树,春水新添没渚蒲”[2]26(《西湖醉中谩书》),“溪风”即溪谷吹来的风,王阳明在此地漫游名胜、饮酒赋诗,溪风带给他的不仅是温和的触感,更有愉悦舒适的情感体验。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上疏失败,不幸被贬谪下狱,文士之风一度披上迁客之悲,而在两年后的浙东四明山游历中,此时的诗人相较于贬谪初期,对于自然万物的初始感受已经有了积极的转变,“风回碧树秋声早,雨过丹岩夕照明”[2]61(《杖锡道中用张宪使韵》),“碧树”“丹岩”都是代表盎然生机的景物,更有前文“山鸟欢呼”“山花含笑”等欢悦的群像,这里的“风”带给诗人的不再是寒冷的体感,而是充满着生活希望的温存之感。除了游赏玩乐之喜,文士之“风”中蕴含的喜还体现在仕途顺利之中。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发起福建漳南之战,这是他军事生涯的首次战役。取得大捷后王阳明写下“数峰斜日旌旗远,一道春风鼓角扬”[2]149(《丁丑二月征漳寇进兵长汀道中有感》),“春风”意象便是王阳明凯旋之时欢欣心情的恰当映射。
文士笔下的“风”除了呈现景明则喜之状,亦展现出物暗则悲之形。风不受时空拘束,可承载王阳明怀古伤今之悲。他在弘治十一年(1498)写下“落日凄风结晚愁,归云半掩春湖碧”[3]1697(《游秦望用壁间韵》),“凄风”一词展现了王阳明登秦望山的复杂心理,除却登高望远时惯有的指点江山、奋发有为的高昂进取精神,此处还有将秦皇断碑与禹迹进行比较后的吊古黯然情思,“凄风”可谓触发了王阳明对科举落第、朝政飘摇的心忧之情[4]。王阳明游历焦山次邃庵时,写下“势挟惊风振孤石,气喷浊浪摇空城”[3]1748(《游焦山次邃庵韵》),“惊风”的侵蚀是当地名胜瘗鹤铭脱落沉江的重要原因,同时风之惊也是王阳明伤古情思的外化表现。
又因风常与霜、雪、雨等其他天气状况组成恶劣天气,使得“风”意象常成为一种不稳定的环境烘托[5],因此文士笔下的“风”亦可寄托王阳明生活境遇的波折之悲。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为南京言官戴铣直言上疏,惨遭下狱贬谪的下场,这一人生坎坷使王阳明触及生活的下限,对于“风”的书写也从前期耽迷任侠骑射下的来去无由转向仕途失意后的沉郁蕴藉。“深谷多凄风,霜露沾衣湿”[2]137(《采薪二首(其一)》)展现了王阳明初抵贵州龙场驿后的生活境遇,“凄风”一词喻示了他坎坷的生活境遇。综上可观,“情”外化为“风”且“风”饱含“情”,王阳明从文士角度写下的“风”意象实则是他面对不同生活经历与人生境遇时的情感表现。
二、以风表志:儒者笔下的“风”
诗人笔下的“风”意象除了呈现普通情思之外,还展露了诗人之志,由此体现出王阳明不仅是一位具有普通情思的文士,还是一位积极入世的儒者。从儒者角度审视外在之风,其笔下的“风”意象多豪迈激越,投射出王阳明坚贞正直的品质、积极进取的追求与治学兴儒的祈愿。
风常有扫尘埃之效,尘埃存于世亦存于心,王阳明借“风”扫除心灵的浮埃,从而展现自身正直坚贞的品质。“载拜西北风,为我扫浮霭”[2]21(《双峰》)是王阳明在1501年游历九华山时写下的,“浮霭”指诗人在刑部任主事期间发现一些冤假错案后产生的满腹心事,能扫浮霭的“西北风”喻示了王阳明对真理与公正的诉求。
除了扫尘埃之效,风亦有破浪的喷薄力量。疾风排云而上,展现了王阳明积极进取的追求。1507年,王阳明赴谪居地时,曾因遭遇刘瑾暗算而心生遁隐之心,后在荒寺老道的启发下坚定了渡过难关的信心,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经历此般磨难后的王阳明变得愈加坚定。他写下“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2]117(《泛海》),王阳明形容自己手拿锡杖、身驾天风,在月光下穿越三万里海涛。这里的“风”意象一扫狱中的积郁,变得气势磅礴,其实风并没有大变,只是诗人对风的阐释发生了变化。结束谪居生活,王阳明回故里探寻山水奥妙。在此期间他常有对时局、自身命运的隐忧,但更多的是渴望建功立业、复兴儒学的雄心伟志,这也暗示了诗人较少沉溺个人情思。“云根奇怪起双峰,惯历风霜几万冬”[2]58(《双笋石赞》),这首诗是诗人从四明白水前往钓台山所作,在两地所作的几首诗中都提及“风”,但游历四明时诗人提及的“风寒”“风雨寒”与在钓台山时吟诵的“惯历风霜”是截然不同的,四明山的寒风尚停留在迁客之悲的层面,而此处的带霜之“风”则喻示了周遭的磨难,“惯”字与磨难结合反射出王阳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并且该诗中诗人以石笋双峰托物言志,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建功立业的雄心。
儒者笔下的“风”除了喻示坚贞品性与进取精神,还用来表达王阳明治学以兴儒的祈愿,例如“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风不化山石顽”[2]71(《琅琊山中三首(其一)》),结合前文“六经散地”“丛棘被道”的儒学现状,可以推想“山石”正是象征了儒道式微的时局,而意图化山石的“春风”则是象征了王阳明复兴儒学的祈愿。“难化”却仍要化,折射出王阳明治学兴儒的坚定意志。由上可观,王阳明虽喜自然之风,但不意味着他沉溺自然,他常以山水点化门生,在天地灵秀间积蓄力量、研磨心性,寻觅真正的儒者之“风”,这时的“风”不仅寄托了王阳明的普通情思,亦彰显了其坚贞心性的重塑与入世情怀的复苏,是王阳明之志的外化表现。
三、以风述心:逸者笔下的“风”
王阳明诗歌中的“风”意象不仅具象化展现了诗人的情与志,还喻示了诗人的心之向往与心之升华,在“幽谷风”“高风”“长风”等诸多意象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向往隐逸之境,追慕圆融之界,由此可观王阳明不仅是一位托风传情的文人墨客与借风表志的入世儒者,他还是一位以风述心的隐逸之士。从一位旷达超脱的文人角度捕捉到的“风”意象多寄托王阳明的出世之思与圆融心性。
风不仅能游走于高堂广厦,其亦能于牧野山林留痕,故“风”可寄寓王阳明出世隐居之思。王阳明在贬谪贵州龙场驿的途中两次前往常德,“惟余洞口桃花树,笑倚东风自岁年”[3]1707(《晚泊沅江》)便写于此时。这里的“东风”意象承载了诗人物是人非的感慨与出世隐居的思索。王阳明在常德桃花源盘桓多时,对八仙往来、桃川仙源、道教丛林这些充满隐逸气息的景点与“多淳朴少宦情”的民风十分向往。人世倥偬,但桃花却一直盛开在“东风”里,这触动了王阳明出世归隐之思。
逸者笔下的“风”除了具有清新超脱的特点,还具有澄明平和的特点,澄明通透乃是心定之状,何以心定?正是因为王阳明将佛教的“无我之境”融入儒家的“孔颜之乐”,达到了普通情思、入世热忱与道、佛灵醒相交合的圆融化境。弘治十一年(1498),王阳明登秦望山,写下《游秦望用壁间韵》,篇始王阳明怀古伤今的普通情思已在文士笔下的“风”中展现,而王阳明何以成大家?正是因为他不会沉溺在个人情思的窠臼,而是常用圆融变通的智慧来指引自己走出困顿,在格取外物的同时体悟到一种澄澈自得的心灵境界,篇末“夜深风雨过溪来,小榻寒灯卧僧屋”[3]1697(《游秦望用壁间韵》),夜来的风已经无法引起诗人的心湖波动,只余“小榻寒灯”的澄明莹澈之境。正德八年(1513),王阳明借滁州琅琊山的优美环境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讲学活动,山水人文之灵秀激发了诗人的超然情思,他写下“草露不辞芒屦湿,松风偏与葛衣轻”[2]78(《龙潭夜坐》),王阳明认为“松风”是轻盈的,物轻盈源于心轻盈,这时的诗人已在滁州经历了对心学未来的彷徨与聚众讲学的充实,并悟出了“静坐以悟”的心学之法,他对于心学以及人生之理有了进一步的思索,松风吹拂之下的心境过而不滞、空明澄澈,充满圆活的智慧。逸者笔下的“风”中蕴含的圆融心性在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在绍兴家中赋闲讲学的诗歌中达到至臻之境:圆月夜王阳明与众弟子喝酒赋诗,写下“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2]200(《夜坐》),与歌声同存的“清风”意象自在超然,曾经戎马倥偬、宦海沉浮的王阳明,如今清风高歌,内心是何其的恬淡逍遥,联系颈联表述的心外无物之理,不难看出这时的王阳明做到了入世与出世的合一,已达自足之境。总而观之,王阳明从逸者角度下审视自然,心底深处的隐居之愿得以浮现,澄明平和的圆融智慧得以迸发,故而看似记“风”实则述“心”。
四、结语
文士笔下的“风”、儒者笔下的“风”及逸者笔下的“风”展现的是王阳明从不同视角对外在之风的三重审视,这三重审视看似并无关联,但实则相互贯通:从王阳明自身理论建设来看,“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可见逸者部分的“不动之心”是一个基础。王阳明虽强调“致良知”“不为外物所累”,却并不认为人应当“毫无感知”,其仍主张依从自然本性,当喜则喜,当悲则悲,由此便有文士笔下的“风”。不仅如此,孔颜之乐的圆融境界在很多“景明”诗中亦有呈现,“逸者”部分一旦涉及官场的黑暗,就容易回归文士的自然性情中去,由此可见文士笔下的“风”与逸者笔下的“风”是紧密贯通的。王阳明看似达观随寓,文士之“风”随波于外在变化,但实则是自身统摄外物,“人生不努力,草木同衰残”,他将天地万物皆纳入自身,不断扩大自身心性的内涵与张力,这也是他看似心随境迁却积极入世的心理基础[6],这个心理基础打破了文士之“风”与儒者之“风”之间的壁垒;王阳明认为养心并不是要“沈空守寂”,而是要经得住事的磨炼,才能成就圣贤的事业[7],由此儒者之“风”与逸者之“风”亦可贯通,消除相互壁垒的三重“风”展现了王阳明将普通情思与儒道佛三教思想合一的通达境界。同时可以将王阳明从三重身份落笔的“风”合称为文学之“风”,文学之“风”是外在之风经过王阳明内心投射思考后的产物,故而王阳明从不同身份落笔的“风”可以对应为他作为文学之人的不同部分:文士笔下的“风”即王阳明的情,儒者笔下的“风”是王阳明的志,逸者笔下的“风”实则是王阳明的心。情、志、心相辅相成、三位一体,贯通成为王阳明大写的“人”,王阳明看似在观风,实际上是在观己身,由此外在之风进阶为内心之“风”,达到物我合一的圆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