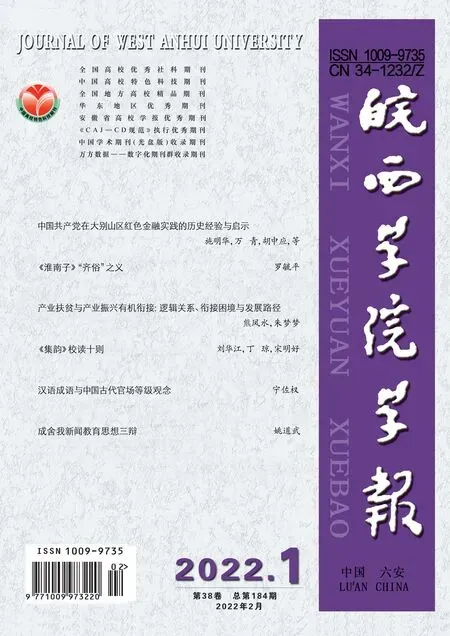精神分析视域下《萨宁》之解读
曹雨轩,张 蕾
(1.安徽大学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长篇小说《萨宁》是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代表作,自问世以来受到无数批判,其中主人公萨宁这一人物形象被认为是消极可耻的。高尔基曾在《个人的毁灭》一文中对萨宁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批判:“如今由精神贫困的人们组成的画廊被阿志巴绥夫(即阿尔志跋绥夫——引者注)的沙宁(即萨宁——引者注)可耻地完成了。”[1](P79)与此同时,也有文学批评家挖掘出萨宁这一形象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如沃罗夫斯基认为,萨宁这一人物形象蕴含着平民知识分子对服务于被压迫阶级传统的反叛。国内对《萨宁》的研究数量稀少,有从叙事层面的研究,如陈爱香对《萨宁》的复调叙事手法进行了探析:“《萨宁》这本小说中融合了多种主体意识:既描述了肉欲主义者兽性极度膨胀的悲哀,也呈现了革命主义者理想破灭后的精神迷惘,同时还揭示了自由主义者的极端个性主义。”[2]她还通过将萨宁形象还原到革命文化语境中,解读出了“作者阿尔志跋绥夫在《萨宁》中展开了一场反思革命知识分子‘民粹主义’精神的话语叙事”[3]。有从思想层面的研究,如贾冬梅结合作家的人生经历分析了小说中蕴含的对于死亡这一永恒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李暖分析了《萨宁》中的自然主义思想意蕴:“将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置于社会秩序之上,通过‘力’之角逐,深刻地揭示了世纪之交俄国社会的全民自杀风潮和个性觉醒。”[4]这些研究为萨宁形象的不断丰富提供了多维度的思考,但目前学界很少有从精神分析角度出发对《萨宁》所进行的相关分析。
本文在肯定萨宁形象积极意义的基础上,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相关理论,将着眼点置于《萨宁》中两个主要人物的相互关系上,进而挖掘出人物关系设定背后的深意所在。萨宁是一个纵欲主义者,他坦诚地追求欲望的满足,不以任何传统道德标准约束自己。尤里则是19世纪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具有崇高的理想、自命不凡,同时又因革命的接连失败而陷入迷茫。萨宁与尤里在小说中有多次思想、行为的交锋,二人的关系是敌对的。那么,作者为何要塑造两个截然相反而又相互博弈的主人公呢?为解决这一问题,将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萨宁、尤里截然不同的人格结构,之后,再运用弗洛伊德的文艺观分析两个人物形象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反映的作家内心的思想斗争,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分析作家塑造人物关系的深层原因和目的。
一、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与文艺观
潜意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划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部分。意识即自身能够察觉到的心理活动,前意识是能够被唤起并可以进入清醒意识中的潜意识,它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中介机制。前意识的内容可以进入到意识中去,前意识既与意识相关,又与潜意识关联,它使潜意识中的内容有可能进入到意识中去,其更重要的作用是阻止潜意识进入意识,控制着充满本能冲动的潜意识,使其不能变为前意识和意识。潜意识是被压抑的欲望、感受、记忆、本能冲动的储存库,具有原始、野蛮的特点,其虽然被前意识压抑,但并未消失,而是从深层控制人的心理和行为,成为人一切行为动机的源泉,潜意识是人的心理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潜意识并非弗洛伊德首创,然而弗洛伊德却是第一位认为潜意识比意识更加重要的心理学家,他认为潜意识中蕴含着人类真正的精神现实。
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将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组成的心理结构表述为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的人格结构。“本我”代表人与生俱来的冲动、欲望,尤其是性冲动,它依照“快乐原则”行事,追求欲望的满足而忽视道德的约束;“超我”是人格结构中最上层的部分,是道德化、理想化的自我,按照“至善原则”行事,是在人发育成长进程中社会、父母奖赏惩罚权威的内化,职能是以高尚的道德、良心指导“自我”压抑“本我”的原始欲望和冲动,是人格结构中努力追求完美理想的部分;“自我”处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它按照“现实原则”行事,不断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灵活”“识时务”。“自我”要压抑来自“本我”的本能冲动和欲望,同时还要按照现实原则调节“超我”对完美的追求。健康的人格通常是人格结构中的“自我”部分大于“本我”和“超我”部分,能够灵活地适应社会规则,并调节自身心理状态。当人格结构中的“本我”所占比例最大时,人会纵欲,与社会格格不入;当人格结构中的“超我”所占比例最大时,人会变得过于刻板,并且社会化过强,内心充满冲突和争斗。
除人格结构的相关理论外,弗洛伊德的文艺观同样是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庞杂。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并非单指生殖行为,而是将其泛化为对一切器官快意的欲望。弗洛伊德认为文学作品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性欲”的升华,他用“泛性论”来解释文艺创作的起源和本质,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作家创作的动力。显然,弗洛伊德的文艺观有一定的局限性,其过分夸大“性欲”即人本能欲望的作用,忽视了社会历史环境的重要影响,未能充分解释文艺创作的本质。但是,弗洛伊德将文艺创作与白日梦同归于幻想的替代性满足的观点符合文艺作品的重要特征,在今日仍有其可取之处。本文将运用弗洛伊德“创作与白日梦”的观点对小说《萨宁》进行分析。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与白日梦的幻想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梦表现的是人的被压抑的欲望,而文艺也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升华,具有梦境的象征意义。其次,梦的显现内容与潜在思想之间的关系犹如文学作品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它们是通过伪装或象征手段来表现其意义的。文学与梦实质上都是一种替代物,是一种具有充分价值的精神现象。再次,释梦的方法与文学批评类似,都是为了发现并揭示其中的‘潜在’意义”[5](P48)。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源于潜意识内受到压抑的欲望和冲动,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是一种替代性满足。“文学作品总是表现艺术家自己的幻想,是‘内心生活的外表化’。艺术家‘自我’就是‘每一场白日梦和每一篇故事的主角’。”[6](P360)他还指出,作家通过观察自身,将“他自己精神生活中冲突的思想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体现”[7](P145),从而通过文学创作不断调试自我。
二、萨宁与尤里:截然相反的人格结构
萨宁是以“本我”为主导的人格,在小说开端,作家叙述了萨宁的成长经历:“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就是人和自然最初冲突的影响下形成性格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弗拉基米尔·萨宁却是在家庭之外度过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监督过他,没有任何一只手管教过他,这个人的灵魂是自由自在地形成的,就像旷野里的一棵树。”[8](P1)“超我”是社会、父母赏罚权威的内化,显然,在萨宁的成长过程中,这样的权威是不存在的,这导致萨宁人格结构中“超我”的缺失。萨宁以“本我”为主导的人格体现在心理活动、外在行为等方方面面。首先最直接地体现在萨宁对待两性关系的态度上。萨宁对待两性关系随心纵欲,认为其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体验,人应当遵从本能的欲望,享受幸福。萨宁刚一回乡,就对自己的亲妹妹丽达·萨宁娜产生了违背伦理的情感,对此他非但没有感到羞耻,反而大方地表露。萨宁认为,这种情感是正常的,他顺应了“本我”中最原始的欲望。在丽达与扎鲁丁未婚先孕心情沮丧时,萨宁试图劝说丽达摆脱社会传统道德标准的束缚,以“他身上仅有的好东西就是美貌,可他的美貌已经被你足足享用过了”[8](P186)为由安慰丽达。萨宁认为,丽达与扎鲁丁不体面的恋情不过是青春、充沛的丽达对于本能欲望的享受罢了,丽达不应为此感到羞愧,甚至在以后可以给更多人这样的幸福。
萨宁还被卡尔萨维娜的美貌迷住,在明知她与尤里交好的情况下仍诱骗了她,事情发生后,他试图劝卡尔萨维娜卸下名誉的重担,享受原始的、没有禁忌和顾虑的幸福,全身心地沉浸在所能获得的快感中。由此可见,萨宁的人格是以“本我”为主导的,不受道德准则的约束。这也体现在他对人生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在与扎鲁丁的谈话中,萨宁毫不避讳地提道:毫不掩饰自己欲望的坏蛋是完全真诚的、自然的,享乐就是人生的目的。在一次郊外野餐时,萨宁因人们对于醉鬼的不喜感到诧异,他认为醉鬼的生活是合理的,因为醉鬼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为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害羞。在扎鲁丁要求与萨宁决斗时,萨宁轻描淡写地拒绝了这一在俄罗斯传统中习以为常的行为,原因仅仅是萨宁的“本我”不想死,也不想杀死扎鲁丁。
萨宁对充满道德说教的基督教感到厌恶,他人格中没有“至善原则”的位置,他对自身没有道德的要求,而是顺应和听从“本我”在自然生活中所产生的欲望的呼唤。“生活的每一时刻都要给出自己新的话语……应该去倾听和理解这样的新话语,不要事先给自己划定尺度和界限”[8](P242),由此可见,萨宁人格中的“本我”远远大于“超我”。他不用道德标准约束自己,而是注重生命体验,追求人类最原始欲望的满足。
尤里是小说中另一位主人公,阿尔志跋绥夫在作品中描写尤里的篇幅仅次于萨宁。尤里是传统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代表,拥有与萨宁完全相反的人格,在尤里的人格结构中,“超我”占据主导地位。在小说开端,参加革命失败的尤里返回家乡,他高傲忧郁而又自命不凡,同时崇尚禁欲,对自身有着极高的道德追求,每做一件事都要认真思考对错,从不向生活索取任何东西。在作家的叙述中,尤里和萨宁对卡尔维萨娜的感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都是本能的性冲动。萨宁自然地接受和顺应了这一冲动,尤里却试图给自己和卡尔维萨娜的感情赋予某种高尚的意义,强迫性地说服自己相信卡尔维萨娜是高尚优雅的,因此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是至高无上的。在正常不逾矩的感情互动中,尤里为自己套上了道德的枷锁。他认为自己对卡尔维萨娜的冲动是庸俗的,向卡尔维萨娜索吻是庸俗的,与卡尔维萨娜结婚也是庸俗的。尤里因自己与卡尔维萨娜的感情而自我批判,认为自己应该是高尚、骄傲的,不应与普通小市民一样,为庸俗的事情感到快乐。尤里以强迫性的心理状态抵抗欲望对自己的侵蚀,认为自己不应被欲望主宰,应杜绝庸俗的欲望。萨宁的种种举动与尤里恰恰相反,萨宁主张人应当尽力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自然真诚的。
显然,在尤里的人格结构中,“超我”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尤里始终以一个伟大高尚和智慧、理想化的“超我”要求“自我”,对自己的每个行为都进行审视和批判,思考它们是否高尚,一旦发现自己的行为带有普通庸俗的成分,便会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尤里精神痛苦的另一来源在于思维中对自我的高度评价与现实中所参与的政治活动接连碰壁的矛盾。尤里是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因政治活动接连失败返回家乡。他巨大的精神痛苦由自身人格结构中的“超我”与“本我”的矛盾所造成,“一个人越是抑制他对外界的攻击性,他越是会在自我理想中变得苛刻——也就是好斗”[9](P221)。对于外界,尤里的态度蕴含着民粹主义传统,是禁欲和克制的,这种克制使他的“超我”愈加强大,强大的“超我”对尤里进行了苛刻的约束,使其无法容忍“本我”的欲望。尤里的“自我”不够强大,无法调和“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他的形象总是带着一些刻板、强迫症的色彩。在与萨宁的志同道合者——伊万诺夫辩论的过程中,伊万诺夫“像尤里这样的人是毫无用处的,他们不敢向生活索取属于他们的东西”[8](P399)的观点让尤里理想的“超我”受到强烈的冲击。尤里想要追求幸福,却不甘心沦为庸俗的“小市民”。最终,尤里思索无果,“更为痛苦的是,他意识到所有那些关于功勋的理想都是儿戏而已”[2]。软弱无助的尤里不堪精神内耗,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尤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纠结矛盾的,他因理想落空而自杀,在开枪后却因想活下去的强烈的本能冲动而幻想枪坏了,并大喊着叫医生,这一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三、萨宁与尤里的博弈:时代的困惑
在《萨宁》中,尤里与萨宁的关系是敌对和博弈的,二人的冲突贯穿整部小说。在作家的叙述中,萨宁与尤里是互相厌恶的,二人在思想方式、生活态度以及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矛盾。作家正是通过塑造两个人物之间的思想、行为交锋来呈现自己内心的思想冲突,“同萨宁一样,阿尔志跋绥夫在矛盾中思考着人生。作家始终站在理性的角度去看待社会,他作品中的矛盾是对社会真实面貌的反映”[10]。两位主人公的思想、行为交锋体现在文中的一系列对话和事件中。尤里认为,人必须高于生活,萨宁则顺应生活本来的面貌,认为人不可能高于生活,而是应当满足自己的愿望。萨宁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好奇心,对每个人都颇为感兴趣,喜欢同新来的人见面。而尤里则因强大的“超我”而骄傲、自命不凡,认为自己不能趋于平庸,同时觉得周围大部分人都是庸俗的,像自己一样有趣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尤里对周围人的态度始终保持冷淡。在小说第九章,尤里认为,萨宁对喝酒的喜悦显得庸俗做作,“他便厌恶地转过了身”[8](P81),而与萨宁志同道合的伊万诺夫却调侃道,还好自己没有成为尤里这样的人。尤里对萨宁的存在感到不自在、不愉快,他觉得自己所有的方法在对付萨宁时似乎全部不管用了,在面对萨宁时,尤里觉得“似乎自己是站在光滑的冰面上去推倒一堵墙”[8](P225)。
在关于世界观与书单的争论中,尤里的观点是传统的,认为人应当通过阅读伟大的书籍来塑造自己的价值观。萨宁则认为尤里的看法无聊而幼稚,他认为一个人的世界观应该来自生活本身,由与生活的互动和反馈构成,书籍不过是世界很小的组成部分,人不应以刻板的标准要求自己。扎鲁丁固执地要求与萨宁决斗,萨宁对决斗的传统感到不屑,多次拒绝未果后,萨宁将扎鲁丁打伤以摆脱纠缠。在尤里眼中,萨宁粗暴的行为如野兽般卑鄙,而在萨宁眼中,他看透了决斗无聊的本质,认为自己的行为不过是为了结束扎鲁丁无休止的要求。在与卡尔维萨娜的对话中,萨宁说出了他对尤里的评价:“像所有终结的东西一样,他吸收了时代的所有精华,那些精华却毒害了他,直至心灵的深处……”[8](P379)在故事结尾,尤里因萨宁支持者伊万诺夫对自己高尚生活方式的鄙视所造成的思想困境而自杀,萨宁却在葬礼上扬言:“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傻瓜,仅此而已!”[8](P418)。由此可见,作家塑造的两个主人公的关系是互相敌视的,他们拥有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且都认为自己的观点高于对方。尤里与萨宁是两个具有鲜明冲突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两人集中了各自所代表群体的典型特征。尤里是传统民粹主义者的代表,而萨宁的形象则带有个人主义、“超人”哲学以及摒弃道德约束、回归个体本真状态的自然主义色彩。根据弗洛伊德“作者精神生活中的冲突和思想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体现”的观点,能够得出结论,作家对尤里与萨宁博弈和敌对关系的描写其实是其内心两种思想斗争的反映。
阿尔志跋绥夫内心的思想冲突和斗争与其所处的世纪之交社会背景息息相关。《萨宁》创作于1902年,作家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俄国知识分子空前彷徨的年代。俄国的封建农奴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对农奴制的废除并不彻底,封建农奴制仍然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阻碍。亚历山大二世所实行的改革在俄国社会引起了一阵民主主义思潮,然而这并未引起沙皇政府的重视,民主运动遭到镇压。俄国青年知识分子对沙皇政府的失望,以及对俄国社会改革迫切的愿望,促使他们放弃对沙皇政府的期待,转而向群众寻求希望。“到民间去”运动成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进步青年行动的指南,他们以去民间感化群众为己任,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被称作民粹派,这一时期他们广泛活跃于俄罗斯政治舞台。然而,由于封建皇权思想根深蒂固,民粹派缺乏群众基础,“当他们揭露地主的剥削时,农民能够理解。但是当他们指出专制制度的罪恶时,农民根本不明白其中的道理”[11](P300),因此遭到沙皇政府的无情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将俄国知识分子带入空前彷徨绝望的境地。亚历山大二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是坚定的封建专制制度维护者,力图将俄国带回1861年改革前的状态。由此,封建农奴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西方先进的哲学思想源源不断地传入俄国,使青年知识分子对俄国社会前景的思索受到巨大的影响。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阿尔志跋绥夫的思想无疑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像世纪之交的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对俄国的现状倍感悲观绝望。民粹主义运动失败后,俄国社会曾掀起一阵“自杀风潮”,这种因理想无法实现而追求毁灭的倾向在《萨宁》中的尤里、索罗维伊契克等人身上有所体现。另一方面,作家深受尼采“超人”哲学和施蒂纳追求本真利己主义的“唯一者”哲学的影响,这体现在对萨宁这一极端个人主义“超人”形象的塑造中。
萨宁与尤里皆是世纪之交俄国社会矛盾加剧、知识分子空前彷徨的典型社会背景下的典型人物,他们身上分别融合了各自群体的典型特征。二人的敌对与博弈实际上反映的是俄国社会充满困惑的青年知识分子两种思想的斗争。而到底应该选择哪一条路,作家已经在萨宁与尤里博弈的过程与结局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尤里对萨宁的话感到不自在、不愉快,觉得自己所有的方法在对付萨宁时似乎全部不管用了,在面对萨宁时,尤里觉得自己“是站在光滑的冰面上去推倒一堵墙”[8](P225)。在故事的结尾,尤里因思想困境而自杀,萨宁在葬礼上扬言“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傻瓜,仅此而已”[8](P418);在小说的结尾,“萨宁就像是迎着太阳在大地上步行”[8](P429)。这样的结局蕴含着作家对统治俄国思想界将近半个世纪的充满禁欲主义、理想主义以及自我牺牲精神的民粹主义的深刻反思。作家对尤里、萨宁不同结局的描绘,背后蕴含着其对于自身思想斗争给出的答案——对民粹主义的反思和对个人主义哲学、无政府主义哲学的希冀。
尤里与萨宁的博弈实际上是阿尔志跋绥夫内心思想斗争的反映,这种思想斗争蕴含着作家对俄国社会道路的探索。通过对尤里与萨宁不同结局的设定,作家已为俄国社会的出路找到了新出口——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风靡俄国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道德信仰、远大理想和禁欲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反思,以及用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超人”哲学解救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困境的初步尝试。
四、结语
在长篇小说《萨宁》中,同名主人公萨宁与尤里拥有截然相反的人格结构,两人有过多次思想和行为的交锋。尤里与萨宁的博弈,其实是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内心思想冲突和时代困惑的反映。作家通过塑造相互敌对的人物关系发出了时代之问:革命失败了,俄国社会该何去何从?又从二者不同的人生结局对俄国社会的发展前景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通过尤里自杀、萨宁拥有未来的博弈结局,表达了对充满自我牺牲精神、道德信仰、远大理想、禁欲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反思,同时也表达了自身对解救知识分子精神困境和俄国社会困境的思索,用个人主义哲学冲破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的束缚,在民粹主义的实践多次失败后寻找新的出路:将对“超我”的极致追求转移到对“本我”的尊重和释放上来。通过分析两位主人公截然相反的人格结构和敌对关系背后的深刻内涵,可见在世纪之交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作家对国家前途命运和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这为《萨宁》这部作品赋予了深重的时代意义与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