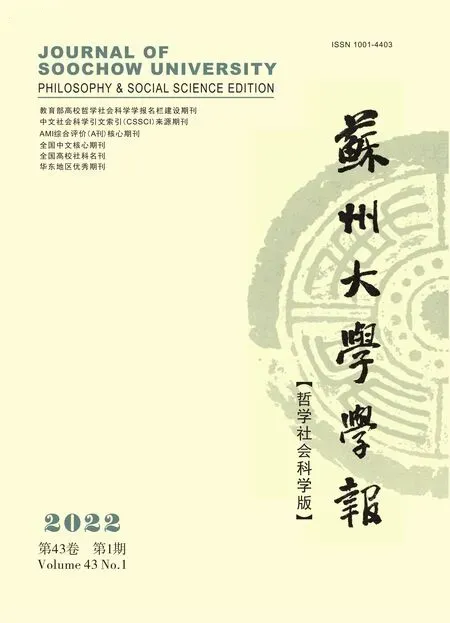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新法兰克福学派”与德国哲学
李哲罕
(浙江大学 哲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一
在经历过被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称为“德国的浩劫”的纳粹运动(1933年至1945年)之后,不仅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而且整个旧欧洲都彻底崩溃了。为旧欧洲陪葬的还有之前几个世纪以来作为其荣耀的启蒙和现代性规划。启蒙和现代性规划被认为是这种崩溃的结果还是原因,可否与之进行有效切割,则是本文试图厘清的主要问题之一。至少可以首先承认的是,“德国哲学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与之相关联的启蒙和现代性危机的一个表现,因为两者是发生在同一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不过这之中更为复杂的机理则需要下文进一步剖析。
像英国政治学家霍布豪斯曾说在投向伦敦的炸弹呼啸而下的声音中听到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回响,抑或像在北非战死的德国青年士兵的背包中发现了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都让人们无法否认德国哲学传统与那段扭曲的历史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过,正如当代德国哲学史家路德维希·西普所指出的“人们宣称的思想史的效应链大多都经不起一种更精确的检验”①(1)①路德维希·西普:《德国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张东辉译,谢地坤、朱葆伟、汉斯·菲格主编,《东西方哲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若将现实政治因素简单地归咎于哲学思想是非常成问题的;同理,若将哲学思想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外在的现实政治因素也是非常片面的。“德国哲学的危机”的确有其外在和内在的双重原因:外在原因就是现实政治所导致的德国哲学传统因勾连于纳粹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而被视为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甚至是有危害性的,或者因为战争的失败导致相较盎格鲁-萨克逊的哲学传统失去了话语权等;而内在原因则是在启蒙和现代性危机之后,研究范式的转换使得德国哲学失去了原先存在的土壤,本身的发展之路已经越走越窄,或者按照非常典型的哈贝马斯式的说法就是耗竭了启蒙运动和乌托邦的潜能。不过,对哲学史略加考察可以发现,其实启蒙和现代性的危机早在叔本华、尼采和胡塞尔时代就已经被预示或意识到,乃至尝试解决了。分析哲学、实证主义科学在那个时代的兴起本身就预示了问题所在,传统意义上的(德国)哲学家们只能在一个被限定的(甚至说是日益收缩)范围内开展工作。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德国两次战败)大大加速了这场严重危机。在此背景下,各门具体学科的发展是哲学——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德国哲学——遭遇危机的部分原因,也是部分结果或表现。不过,若对德国哲学的当代发展趋势有所考察就会发现,虽然“德国哲学的危机”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其背后所潜藏的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危机,更是德国学者对越走越狭隘的德国哲学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更张。
喷混植生技术在当前岩石边坡生态治理中起着无以替代的作用,但是现在国内所掌握的喷混植生技术还不完善,有许多技术难题需要攻关。主要是:
正如康德关于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一样,德国哲学传统中的哲学家们普遍认为物理事实与社会事实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以及分别适用两种不同的逻辑(即“精确科学”与“精神科学”之二分),因此需要从不同的取径(研究方法)去理解。即使之中有寻求哲学统一性的倾向,这种“统一性”也是基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两者差异性的统一性。就此可以得出的初步论点就是他们在研究对象上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同分析哲学、实证主义科学相区分或切割。这也正像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所指出的:“我正在批判的——这也是我‘逆向地’理解这两位作者(哈贝马斯和塞拉斯——笔者注)时所对准的目标——是这样的假设:我们首先必须按照与理解物理事实同样的方式理解社会事实。”①(2)①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罗亚玲、应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如上文所论述的,研究对象的不同也暗含着取径的不同。在德国哲学传统视域中,哲学是一门关于规范性的学科,这就要求哲学区别于事实性的实证研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哲学传统忽视事实性问题,而是他们倾向于对事实性问题加以反思与批判以求得规范性。许多现当代德国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是如何在与自身原先传统进行有效切割之后继续保持一种传统德国哲学式的反思与批判的潜能。这种反思与批判不仅是为了应对分析哲学、实证主义科学的挑战,而且也是德国哲学传统所认为的一种“做哲学”的方式。就像雷蒙·盖斯所言的批判理论对实证主义一以贯之进行批评的原因是:“批判理论是一种给人们带来某种知识的反思性理论,该知识能内在地产生启蒙与解放……实证主义可以被看成是‘对反思的否定’。”②(3)②雷蒙·盖斯:《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汤云、杨顺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14页。译文中的“批评理论”被改为了“批判理论”。换言之,反思与批判并不仅仅是一种否定性的方式而已,它其实也内在地蕴含着一种肯定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即它在德国哲学传统的语境内还被视为对人类认识与实践两者奠定可能的基础,更是人类达致真实自由体验的可能途径,而这同时也恰恰是克服启蒙和现代性危机与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关键。在德国哲学传统中,从德国古典哲学、浪漫派、现象学-存在主义到批判理论这一系列关于思维和存在及其之间关系的恢弘画卷中所展现出来的正是一种人类思力的充分表达。路德维希·西普曾总结说:“批判能够产生进一步的意义,这种意义在德国传统中至少从黑格尔延伸到了批判理论。”③(4)③路德维希·西普:《德国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张东辉译,谢地坤、朱葆伟、汉斯·菲格主编:《东西方哲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0页。
合作学习的有效性是指学生在合作的状态下,相互协作、克服困难,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为了让合作学习有效性在语文课堂中得到真实的发挥,需要认清当前出现的课堂秩序较差、教师定位不准确、学生主导能力有限等问题,以建立和谐有序的课堂秩序为前提,积极提高教师的设计合作水平和学生自主合作的能力,以使学生在语文课堂中的综合素质有显著提升。
正是受到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物哲学思想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个大部分德国人在精神上都有些迷茫和不知所措的年代,哈贝马斯和韦尔默等年轻一代的哲学家们开始了对德国哲学的重建和改造工作。他们的这种重建和改造工作甚至也指向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即他们试图通过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思想注入一种民主与法治框架下的“规范性基础”以期克服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为代表的那种陷入未来指向性匮乏的内在理论困境。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这种‘规范性的基础’除了为否定性的‘批判’提供基础之外,同时也为建设性的‘实践’提供依据”①(8)①童世骏:《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序言第5页。,哈贝马斯和韦尔默在这里其实以共享一个关于(在民主与法治框架下的)主体间的“诠释-实践循环”的方式来理解与实现动力学与规范性基础问题。主要根据哈贝马斯和韦尔默等人理论中存在的一个朝着政治哲学与语言哲学的理论转向,他们也可以被称为“新法兰克福学派”②(9)②应奇:《新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之再出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29日。,而这种“新法兰克福学派”的提法与学界既有的对“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代际划分与研究互为补充而非互相冲突。③(10)③参见王凤才:《“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群体剖析:从霍克海默到弗斯特(上)》,《南国学术》2015年第1期,第158-176页。
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德国的语境内——也就是西奥多·阿多诺认为写诗是残酷的“奥斯维辛之后”,按照韦尔默的说法则是,“狭义而言,奥斯维辛的罪行就是启蒙运动的完成和自我毁灭的时刻”①(5)①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290、290-291页。——就对之前德国哲学传统的批判性发展而言,在一种去除了政治上负面影响以及反启蒙和反现代性的一面之后保留德国哲学“本真性”的处境下,即使不能完全说是唯一的,“法兰克福学派”至少也是其中最为核心和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理论姿态。这里不得不援引韦尔默对其博士导师阿多诺的评价:“从对于联邦共和国的文化影响上说,阿多诺不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批评家和哲学评论家,他还是在反动政治的损害后恢复德国文化传统的本真性,并使之进入在道德上受到困扰、其认同被动摇的战后一代人意识之中的第一人……阿多诺再一次使德国人用不着在智识上、道德上和美学上仇视康德、黑格尔、巴赫、贝多芬、歌德或荷尔德林。”②(6)②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290、290-291页。正是经历了这样一种涅槃,德国哲学才可以再次审视与正视自身之前的传统,以及打开更为宽阔的视域。当然,也正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大多持有左派政治立场、具有犹太人身份、参与抵抗纳粹的活动和流亡海外,才使得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哲学的重建工作具有道德上的充分的正当性与说服力。这种正当性与说服力使得他们不仅可以调用那些被19世纪以来日益狭隘的德国民族主义所封杀、遮蔽或遗忘的德国哲学资源,而且还可以直面那些因涉及纳粹而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哲学资源。换言之,他们从正反两方面进入了德国哲学的“本真性”。如上文所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奥斯维辛”使得德国哲学传统可以在与其伴生的各种反启蒙和反现代性的路线做出有效的切割之后,于内部继续修正和挖掘启蒙和现代性规划的进路,这或许也是克服“德国哲学的危机”和实现德国哲学(以及启蒙和现代性规划)重建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出于“新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继往开来的特征,他们要求自身能够对传统进行充分的反思与批判,而非全然回到自身的传统中去。对自身传统进行充分的反思和批判不仅是他们的理论立场,而且也是他们的理论方法所内在要求的。正如韦尔默所指出:“事实证明,批判理论是这样一种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一方面有可能分析德国文化传统的那些反动的、压迫性的和敌视文化的方面,而且比任何其他的立场更准确地这样做;另一方面有可能揭示同一传统的颠覆性的、启蒙的和普遍主义的特征。我要指出的是,批判理论是战后德国能够想象的与法西斯主义彻底决裂,而又不必与德国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一个人自身的文化传统类似地彻底决裂的惟一理论立场”③(7)③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290、290-291页。。
这里的问题其实涉及这种德国哲学式的反思与批判的潜能在和其自身原先的传统进行有效切割之后的新语境下是否可能实现,抑或是何以可能实现。或者可以说问题是启蒙和现代性规划是否还可以——经过转化之后——继续发展下去,以及从其内部挖掘出一种积极的面向。在德国哲学传统中,他们一直与原初的启蒙和现代性规划——这并非是出自德国的原生性观念,而是外来的——保持着距离,不过除去各种反启蒙和反现代性思想之外,更应该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在面对各种反启蒙和反现代性思想挑战的时候试图对启蒙和现代性规划本身进行修正与挖掘。德国哲学传统不应该如一般观点所认为的那样被视为启蒙和现代性规划的挑战者,也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关联物,而是内在的批判性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可惜这一进路被其从19世纪以来更为强烈的反启蒙与反现代性思想这条脉络所遮蔽,因此也一直为人们所忽视。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零点时刻”,宣告了德国哲学中启蒙和现代性的一面可以摆脱与自己伴生的反启蒙和反现代性思想的那一面,进而可以尝试重新恢复其原先的理论定位,也即在内部继续修正和挖掘启蒙与现代性规划的进路。
鉴于公司当前的发展规模,采取适合公司操作的关键绩效指标法,在明确公司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的前提下着重研究影响知识型员工绩效的关键因素,将公司目标进行分解后以确立部门目标,并最终形成员工个人工作目标。
此外,相较于总是处理严肃主题以及热衷参与具体政治论战的哈贝马斯,韦尔默在研究兴趣上更为接近传统意义上书斋式的和博雅的阿多诺。①(19)①格奥尔格·洛曼:《民主和人权的变奏曲——纪念哲学家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李哲罕译,方博校,《哲学分析》2020年第5期,第177-183页。上述与哈贝马斯(以及阿佩尔)之间的理论分歧预示了韦尔默更为接近阿多诺式的文学与美学进路(韦尔默在柏林自由大学担任的就是诠释学与美学的教席,甚至他还是主要由诗人与作家等组成的国际笔会PEN的成员)。他不仅在早年的科学与艺术等的关系研究中一再援引阿多诺的论述,而且在他晚年的著作《关于音乐和对话的探寻》(VersuchüberMusikundSprache)中对“无调音乐”(atonale Musik)的研究也不禁让人联想起曾在维也纳跟随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学习过的阿多诺。②(20)②Albrecht Wellmer.Versuch über Musik und Sprache.München:Carl Hanser Verlag,2009.阿多诺被认为代表与体现了纳粹上台之前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这座工商业大城市富裕的德国-犹太中上层所特有的才情和品味,不过这早已随着“德国的浩劫”而成了明日黄花。早年曾参与过韦尔默组织的讨论班的马格德堡大学荣休实践哲学教授格奥尔格·洛曼在谈及为何会有韦尔默这种类型的学者时,他不禁感叹韦尔默属于那种旧时代的德国大学教授,具有完全自主研究的空间去充分实现自己的理论志趣。③(21)格奥尔格·洛曼:《民主和人权的变奏曲——纪念哲学家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李哲罕译,方博校,《哲学分析》2020年第5期,第177-183页。可以说,韦尔默留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其学术作品及观点,更是其人格所透显出来的自由和格调。
三
按照韦尔默的观点,对话伦理学并不能预设一种先验的前提,也不能预设一个必然的结论,而是需要承认各种偶然性和非理性的存在,这也正是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换之处。这点就像韦尔默所说的:“尽管对偶然性的承认为民主的和自由主义的原则以及以它们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制度提供了新的论证,它依然是对偶然性的承认。然而,偶然性是无法消除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和自由主义的原则就缺乏好的论证;毋宁说它表明了在这些原则的建制化、保持活力和转化成一种伦理生活形式方面存在着偶然性的因素。”⑤(17)⑤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35-136、339、339页。和哈贝马斯一样,韦尔默也主张一种后习俗的伦理生活(post-conventional ethical life),而这正是基于对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俗成的伦理生活的反思,而并非直接接受或取用俗成的伦理生活的实质性内容。不过和哈贝马斯不同的是,韦尔默强调了其中的历史偶然性:“虽然对于形成个人的和共同体的认同来说,特定的传统、历史和事业常常都是重要的,认同的这些特定的基础并不能成为一种民主的和自由主义的伦理生活形式的实质核心。只要这种伦理生活形式要求对差异、‘他律’的承认,它就同时要求对特定的传统、历史和事业保持一种反思的距离。换句话说,它要求承认偶然性。”⑥(18)⑥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35-136、339、339页。韦尔默就此将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和多元主义(亦或是社群主义)有效地关联了起来,而这使韦尔默可以更好地论证与捍卫少数族群的权益。
“新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在更为复杂的晚期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处境下,以一种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内的主体间交往方式来实现德国哲学所重视的反思与批判潜能。正如一般观点所认为的,以哈贝马斯和韦尔默等人为代表的“新法兰克福学派”相较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为代表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发生了一种语言学转向以及一种政治哲学转向。这种所谓的转向表达的只是一种进一步的发展和延续。这里涉及韦尔默和哈贝马斯关于交往和言语的许多更为细致和技术性而非原则性的讨论,而这也正是两人之间争论最为集中的地方,⑤(12)⑤Jürgen Habermas.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s:Five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ve Reason.Ciaran Cronin trans.Cambridge:Polity,2018,pp.27-30.但他们之间这种“家族内部”的差异终究只是表现在以同样的思维态度在相同的理论旨趣中融入更多需要被处理的“主题”而已。出生年龄只相差四岁的哈贝马斯和韦尔默两人亦师亦友:两人不仅在哲学方法上具有相关性或相似性,而且共享了许多价值观念,追求同一事业。根据对联邦德国知识分子的代际研究可知,哈贝马斯和韦尔默的年龄让他们一方面免于直接参与纳粹的罪行,另一方面又要在成年时直面纳粹的罪行(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纽伦堡审判”告诉了他们纳粹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在政治立场上,他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经历了“去纳粹化”和“再教育”、1968年共同抵制左派激进大学生运动,一直到共同参与联邦德国民主生活中“宪政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重建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争取民主人权的斗争。两人在此过程中无不体现出同时抵制右翼保守派和左翼激进派的一致性。在学术观点上,他们都坚持结合民主法治和语言交往的批判理论,但是其中的具体观点略有分歧。就与哈贝马斯的异同,韦尔默曾坦言:“我的立场在诸多方面都与尤尔根·哈贝马斯相近,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我从他那里受益良多;虽然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我也与哈贝马斯存在分歧……从根本上说,我与哈贝马斯的分歧既与‘概念建筑术’问题有关,也与构想民主‘包容’的理想终点的可能性有关。这也意味着我把现代世界中的民主构想为有待于具体的人民在他们置身的特定历史情境中历久弥新地‘创制’和改善的一种谋划。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文章中,我与哈贝马斯共享的是对于道德普遍主义的承诺,对于一种反帝国主义的民主的世界秩序的承诺,以及对于捍卫现代世界中的普遍人权的承诺。”①(13)①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35-136、339、339页。韦尔默与哈贝马斯最为主要的分歧在于韦尔默并不像哈贝马斯以及“新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位主要成员卡尔-奥托·阿佩尔一样认为在证成和真理之间存在一种一致的必然关系(先验性),进而可以从这种必然关系出发来产生和确保一种关于主体间言谈所能达成共识的道德普遍主义,而是认为需要通过——经验的、科学的(认知的)、道德的、审美的或诠释学的等——多重意义或领域的区分和统一去理解世界以及实践。②(14)②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7、118页。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当然并不否认这多重意义或领域的区分以及它们的重要性,只是韦尔默认为他们所寻求的统一或还原这些多重意义或领域的方式是成问题的。正如韦尔默自己指出与他们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的分歧时说:“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克服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引入一种语言学上的普遍的‘规范’有效性要求的概念,这种要求和真实的有效性要求与真诚的有效性要求一起构成了言语行为本身。然而,我并不认为这种‘形式语用学的’区分能够导致‘有效性领域’——即科学的领域、道德的领域和艺术的领域——以及相应的论证模式之间的区分……在我们的生活中,合理性、话语形式和实践形式的不同风格总是已经相互联系在一起,相互预设,允许并常常要求从一种风格转换到另一种风格。”③(15)③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35-136、339、339页。换言之,韦尔默所追求的即“在多种理性的范围内对单一理性的扬弃”④(16)④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7、118页。。韦尔默在这里不仅构成了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而且也出于同样的理由构成了对以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为代表的对话伦理学的批判。
如上文所述的,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物对之前传统的批判性继受,使得在下一个世代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的哈贝马斯和韦尔默等人可以不带偏见、不背包袱和以相当正面的形式去处理之前的德国哲学传统中的智识资源,诸如就康德、黑格尔、青年黑格尔学派、马克思、韦伯、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等的讨论。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新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并未受到19世纪以来德国哲学传统中经常性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影响,所以他们还可以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容纳与处理更多之前并未得到德国哲学传统足够重视的或者被认为是“非德国的”成分。当然,这里所谓“非德国的”成分不仅是指来自其他哲学传统的智识资源,而且也包括在扭曲的民族主义历史被遮蔽与压制的德国哲学传统原本具有的其他面向。大体而言,上述这些成分不仅包括民主、法治、人权等实践哲学的成分,而且也包括语言分析等理论哲学的成分,这两部分正是我们所讨论的“新法兰克福学派”的两大支柱。“新法兰克福学派”在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对德国哲学的重建和改造,而且是对分析哲学与实证主义科学以及各种后现代思潮大行其道的当代语境内,我们依旧可以坚持通过反思与批判以实现启蒙和现代性规划的努力。正如韦尔默评价其授课资格论文导师哈贝马斯时所说,“哈贝马斯的主要成就在于为批判理论恢复了历史的视界,开启了历史可能性的视野”④(11)④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也即他们通过“交往理性”或“交往行动”重新开启了之前启蒙运动和乌托邦所未完成的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继续这个之前被中断了的进程。
辅助系统是船舶轮机内部重要构成部分,在进行船舶轮机检查时,要将该系统作为重点检查对象,以便在辅助系统正常工作下,为轮机功能发挥提供保障。辅助系统以供给系统为主,能起到储存和供应油料的作用。待使用的船舶油料可储存在系统内。在船舶航行过程中,油料经过燃油管道传输到船舶,是保证船舶航行任务有效完成的关键。这一系统的缺陷,体现在滑油舱缺陷、燃油舱缺陷以及运输管道缺陷等方面,在检验时应加大这方面的检查,确定缺陷产生原因并提出具体应对措施。例如,当燃油舱和滑油舱之间缺少有效的隔离措施时,这两种油会混合在一起,从而出现船舶轮机运行故障,不能支持船舶良好航行。
四
图宾根大学哲学教授曼弗雷德·弗兰克2015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哀叹德国古典哲学在目下德国范围内的全面衰退,不过他调侃人们还是可以到中国或巴西去学习德国古典哲学的。④(22)④Manfred Frank.Hegel Wohnt hier nicht mehr:die Kontinentale Philosophie Verschwindet aus Europa.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15-09-23.在目下德国大学中许多教席被偏向英美风格分析哲学的学者所占据的时候,两位具有德国哲学研究背景的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和让-吕克·南希还是在2016年于柏林关于德国哲学所做的一场对话中重申了德国哲学之意义。⑤(23)⑤Alain Badiou,Jean-Luc Nancy.German Philosophy:A Dialogue.Jan Völker(ed.).Richard Lambert(tran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8.
德国哲学之于中国哲学界是“最为熟悉的他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虽然我们一直热衷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但其实缺乏一种全面系统和深入反思的态度。就全面系统而言,我们倾向于选择这些“星丛”(Konstellation)中最为闪亮的甚至最为时兴的那些人物,而忽视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哲学家;换言之,这些选择的理由或标准多少是有些外在的。就深入反思而言,我们对他们的智识背景以及理论定位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不能真切地理解他们焦虑所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实则是充满“任意性”的。在这种“任意性”的支配下,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产生一定的偏差不仅是难免的,甚至是必然的。
国内学界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加以接受或批判,但是并不能十分真切地理解他们在整个(德国)哲学传统中的定位及其重要意义,以及在“法兰克福学派”这个标签之下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生发性。我们还是亟需深入了解“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代际之间、同一代际的不同个体之间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同与异。在此可以引用韦尔默相对中肯的说法:“‘法兰克福学派’也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项集体的和合作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要复兴和发展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⑥(24)⑥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页。
不论是上面讨论的哈贝马斯和韦尔默的观点,还是嗣后阿克塞尔·霍耐特的“承认”和雷纳·弗斯特的“证成”,都被认为在“德国特色”方面稍显不足,但是“新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是以一种“不那么德国的”方式有效转换和实现了德国哲学中反思和批判的潜能,而且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准确地说是重新实现了——德国哲学和其他哲学有效交往的开放性。可以说,“新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意义正是为之前自19世纪以来越走越狭窄的德国哲学传统之路打开了一种新的和可能的视野和空间。在融入和整合更多其他哲学传统资源的情况下,德国哲学才能走出原先的自我限制从而更好地实现自身反思和批判的潜能,以及进一步在现代性或后现代社会中实现启蒙和现代性规划。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