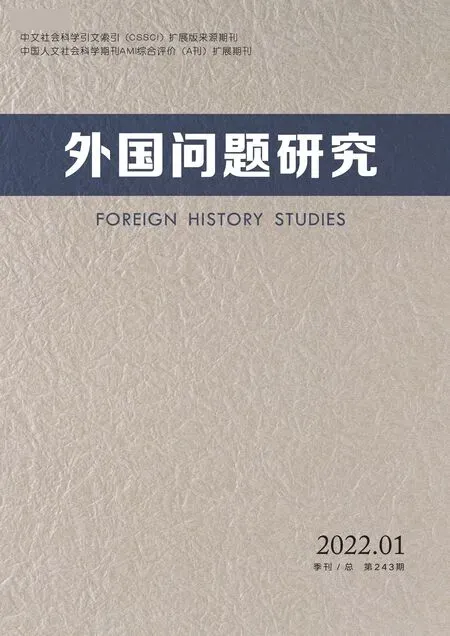诺曼征服与中世纪英国智识生活的复兴
孙逸凡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5)
1066年诺曼底大公威廉征服英格兰是中世纪欧洲的焦点事件,为期20年的武装征服改变了英国的历史,给它的社会、文化发展带去了深刻变化。如何评价诺曼征服对英国带来的影响是中世纪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学者们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主要关注诺曼征服在英国民族历史、文化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E.A.弗里曼在其六卷本巨著《诺曼征服的因与果》中强调英国历史的连续性,认为诺曼征服的作用不过是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诸多粗糙的社会风俗、传统加以精炼以适应新的时代。与弗里曼不同,以J.H.罗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更加强调征服运动在历史中造成的断裂性,认为英国连贯的政治传统始于诺曼征服,需要从诺曼底、法国寻找它的源头。(1)相关学术争论可参见R. Allen. Brown, The Norman Conques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7, 1967,pp.109-130; Majorie Chibnall, The Debateon Norman Conques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Press,1999;刘铭: 《诺曼征服及其对英国文明的影响》,《英国研究》2020年第11辑。20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出发,在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民族语言等方面揭示出征服造成的深刻变化,同时这些变化当中源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本土元素也逐渐为人知晓。(2)例如早先学者们断言英国封建制度源自诺曼征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征服并没有立刻给政治制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更多是渐进式的。C. Warren. “Hollister, The Norman Conquest and the Genesis of English Feudal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 1961, pp.641-663.
在诺曼征服对中世纪英国智识文化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认知经历类似的发展历程。以大卫·楼勒斯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修道文化的连续性,他们将本笃修道院中围绕礼拜仪式展开的读经、解经等传统智识活动,与世俗学校里依靠逻辑、辩证法工具进行的新兴智识活动严格区别开来,认为诺曼底修道文化是陈旧的中世纪早期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修道文化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诺曼征服并未将欧洲大陆新的思想风潮带到英国,也没有改变当地智识活动的发展方向。(3)David Dom Knowles,The Monastic Order in England, London: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495.萨恩森认为,由于欧洲大陆风行的以世俗学校为中心,注重思辨的智识活动并未在英吉利海峡另一边流行,英国在12世纪文艺复兴浪潮中更多贡献的是如历史写作这类诞生于传统修道生活的知识产品。R.W.Southern,“The Place of England in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History,Vol. 45, No.155, 1960, pp.201-216.然而后来的学者则更加强调修道院与世俗学校两种智识传统在诺曼征服前后的相互影响(cross-fertilization),认为征服活动将欧洲大陆新的文化注入英国,给岛上的本土修道文化带去了较大的变动。(4)Marjorie Chibnall, The Anglo-Norman England,1066-1166,London:Balckwell,1986,p.214.笔者以为,在11世纪欧洲大陆文化复苏的历史背景下,欧洲新兴的世俗智识风潮与新一轮修道改革运动在诺曼底相汇,二者结合形成了一种更注重学习的修道文化,并通过诺曼征服这一中介移植到了海峡对岸,带动了英国智识生活的复兴,为后者在12世纪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文化复兴”背景下的诺曼底修道院
幸运的是,欧洲各地文化凋敝的背后埋藏了复兴的种子。自11世纪开始,在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北部、日耳曼的南部及西部,以修道院、主教堂学校为中心的智识活动稳步发展。拉丁古典文化遗产以及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传统的“七艺”(文法、逻辑、修辞、音乐、算术、几何、天文)以及医学和法学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欧洲各地涌现众多学术活动活跃的文化中心,也出现了阿贝拉尔、马莫斯伯里的威廉、圣伯纳德、安瑟伦等以学问闻名于世的教士、僧侣。后世学者将这场发生于中世纪的文化大繁荣称作“12世纪文艺复兴”。(10)学术界一般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时间范围限定在1050—1215年,因此这一时期又有“漫长的12世纪”(The Long Twelfth-Century)之称,John Van Engen, ed., European Transformations The Long Twelfth Centur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12,p.4. 近年相关论述可见,Alex J. Novikoff,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A Reader, Toronto: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7; 李腾:《“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发展史:从让-雅克·安培到查尔斯·哈斯金斯》,《世界历史》2018年第3期。
在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中,意大利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由于在地理位置上毗邻拜占庭与阿拉伯世界,意大利能够从这两个地区源源不断地获取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遗产。康斯坦丁(Constantinus Africanus)在11世纪将阿拉伯的一些重要医学典籍翻译成拉丁文传入意大利,意大利的萨莱诺(Salerno)是远近闻名的医学研究中心。随着《学说汇编》《民法大全》等一系列罗马法律典籍被重新发现,学者们开始聚集在城市中围绕这些法律文本进行研究。这类智识活动催生出了法学研究学校,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由伊内留斯(Irnerius)教授法学课程带动发展起来的博洛尼亚大学。(11)有关11世纪意大利法学研究活动的论述,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47—152页。与此同时,源自加洛林时期的主教座堂学校在法兰克、德意志地区逐渐复苏。这类学校旨在为教俗两界培养管理人才,向学生提供圣经与世俗教育,其课程大量使用拉丁古典文学遗产培养学生个人的德行而带有明显的世俗化特征。在教学组织上,主教座堂学校以老师和学生的私人关系为主,当时的科隆、列日、兰斯、沙特尔、施派尔、班贝克等地都因学者的名声吸引各地学生前往求学而成为著名的智识活动中心。(12)C. Stephen Jaeger, The Envy of Angels: Cathedral Schools and Social Ideals in Medieval Europe, 950-1200, p.53.
11世纪以来,商贸往来的发展促进了欧洲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随着学者的流动,意大利、法兰克等地文化发展的成果逐渐扩展到了欧洲北部的诺曼底。未来两地文化重要的传播人贝克的兰弗兰克(Lanfranc of Bec)便出生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帕维亚(Pavia)。他曾在提供人文教育以及法学专业教育的学校中学习,精通罗马法,曾是帕维亚当地出色的辩护律师,对中世纪“七艺”的相关学问都有涉猎。帕维亚所处的意大利北部地区自10世纪以来便与诺曼底有着密切的联系。出于现实统治的需要,诺曼底的统治者从10世纪开始在领地内大力推动修道组织的发展,他们寻求从法兰克与意大利北部地区邀请学者前往诺曼底帮助修道院建设,兰弗兰克便是在11世纪初来到了诺曼底的贝克修道院修行,并很快被任命为修道院副院长。(13)H. E. J. Cowdrey, Lanfranc Scholar, Monk, and Archbisho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9.
兰弗兰克在任职期间将对同袍的责任与自己深厚精湛的学识、潜心向学的态度结合在了一起,为修道院营造出良好的智识环境。按照本笃会规的要求,修道院的负责人是僧侣在修道生活上的领路人,须利用言传与身教两种方式对门徒们施以教化。(14)一方面,修道院负责人要更多地用身体力行而非言语,为所有人指出何为善与神圣;另一方面,对可堪教化之人要用言语让其明白主的诫命,对迟钝固执之徒则要用榜样的力量对其进行感召。米歇尔·普契卡:《本笃会规评注》(上),杜海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57—58页。兰弗兰克像众多本笃修道院领袖一样,严格利用会规指导自己的生活。唯一的不同在于他是位精通世俗学问的新潮学者,其并未因修道放弃对学问的追求,而是将学术重心逐渐转移到圣经研究上。在担任修道院长副手的18年里,他将最新的逻辑、辩证法学问融入神圣知识的学习中,撰写了大量系统而简洁的圣经评注。同时他还参与了与贝伦加尔的神学论争,从“形式”与“质料”的概念出发,利用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工具批判了贝伦加尔的圣餐理论,捍卫了教廷的正统学说。(15)R. W. Southern, SaintAnselm: A Portrait in a Landsca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1990, p.45.兰弗兰克的这些学术活动不仅为修道院成员的圣经学习提供了养料,同时也以学者的身体力行为僧侣们提供了可供效法的典范,带动了整个修道院的学习氛围。
除了自身的榜样作用,兰弗兰克最重要的贡献是其在修道院中开设的学校。有别于传统克吕尼修道院只接受修道人士的做法,贝克的这座学校几乎对所有立志于学习的人开放。学校里提供世俗人文教育与宗教课程,内容包含传统的七艺,经文诵读、释义,教父作品的研读。僧侣们每天除了做礼拜仪式与祈祷外,将大量精力花在学习上。贝克修道院中智识活动明显受到了11世纪以来神学中兴起的思辨风潮的影响,修道院学校中除了阅读、冥想等传统学习方式外,精通辩证法的老师们会利用古希腊哲人惯用的对谈(dialogue)、争论(disputation)这类知识助产术来帮助学生理解问题。在学习具体的神学问题时,学生常常会围绕讲授者抛出的核心议题提出自己的论点,并通过辩论的方式让各自不同的思想进行交锋、碰撞。随后讲授人对各方提出的论据进行一番考量后作出结论,同时也对各方的论点进行回应,知识便在一来一回的争论中源源不断地产生。(16)Alex J. Novikoff,The Medieval Culture of Disputation: Pedagogy,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3, pp.40-41.
学校的开放性与浓厚的学习氛围以及兰弗兰克本人的名望,使贝克修道院很快成为阿尔卑斯山以北远近闻名的智识活动据点,从法兰西、加斯科尼、不列颠、弗兰德斯等地慕名来听课、求学之人络绎不绝。(17)Thomas Forester tr,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us Vitalis, Vol. 2, London: H. G. Bohn, 1854, p.40.在这些学生中,既有僧侣、教士,也有世俗界的显贵子女。例如,教皇尼古拉斯二世从意大利送来不少年轻的学生在此进修,出身诺曼底贵族的罗伯特二世也曾有过贝克的学习经历。(18)Sally N.Vaugh,“Lanfranc, Anselm and the School of Bec: In Search of the Students of Bec,”MarcA.Meyer, The Culture of Christendom, London and Rio Grande: The Hambledon Press,1993,p.169.
贝克修道院学校的盛况是以世俗学校为代表的智识风潮向修道生活渗透的结果。随着有世俗教育背景的学者在各修道院间的人事流动,这股智识运动的影响也被散播到诺曼底各地。诺曼征服前,兰弗兰克受大公任命前往卡昂担任圣艾蒂安修道院的院长,随即将贝克的管理经验运用到新修道院的建设中。他在修道院外建立了一所学校,与贝克一样都接收俗界学生,为他们提供神学与世俗教育。(19)David Spear, “The School of Caen Revisited”, The Haskins Society Journal: Study in Medieval History, Vol. 4,1992, pp.55-66.曾在沙特尔时师从著名神学家富尔伯特(FulbertofChartres)的吉拉德受诺曼底大公的邀请,前往圣旺德里耶修道院主持工作。后来鲁昂的大主教马芮利乌斯(Maurilius)在进入诺曼底修道院前也曾在列日、哈贝尔施塔特的世俗学校有过学习任教的经历。尽管因个人带来的智识活动的兴盛容易因学者的离去而衰落,但他们确实为日后的教俗两界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有以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吉伯特(Guibert of Nogent)为代表的神学家;也有艾德玛(Eadmer of Canterbury)、奥斯本(Osbern of Canterbury)、哥瑟林(Goscelin of Saint-Bertin)等史学家。据统计,12世纪拥有贝克修道院学校教育背景的学者大概有30多位,而且不少学生后来在基督教系统中身居高位。(20)从贝克修道院中共走出1位教皇,1位意大利红衣主教,5位英格兰大主教,两位教皇特使,11位主教与数十位修道院院长。Sally N. Vaugh,“Lanfranc, Anselm and the School of Bec: In Search of the Students of Bec,” p.179.这些人才在随后的诺曼征服运动中,也会如他们的老师一样将智识的火种散播到英格兰岛上。
对于一级模糊变换,首先确定各指标突出影响程度系数,Λ1={3,2,1},Λ2={1,3,7,5},Λ3={3,3,5,2,3,3},最后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最终评价结果,综合评价结果见表6,且均满足最大隶属度有效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诺曼底修道文化的复兴不是单独一两个学者的功劳。11世纪中叶基督教学者对待“知识”“学习”的态度上的转变,以及这股思想潮流背后修道生活的革新,为诺曼底智识生活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而持久的推力。
二、基督教学者对待知识的态度的转变与诺曼底修道生活的变革
在早期基督教学者的思想中,知识与信仰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一方面,在拉丁古典文学等知识上投注过多的精力在正统教徒看来显然有损信仰的纯洁;另一方面,基督教学者想要更好地宣扬基督信仰,在与异教的论战中维护主的荣光,同样离不开修辞学、演说术等世俗知识的帮助。圣本笃的修道理想中,修道生活只有一个超越性的目的——寻求与上帝的联合,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不值得去关心。僧侣学者始终对过分追求知识带来的危险持警惕态度。(21)Jean Leclercq, The love of Learning and the Desire for God:The Study of Monastic Culture, New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05.他们认为,僧侣如果将精力放在对纯粹知识的学习上,费尽心思去讨论各式各样复杂、多变的学术问题,会打破内心平静纯朴(simplicity)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僧侣追求至善,寻求与上帝联合的前提保障。一旦被打破,僧侣就无法达成修道生活的终极目标。因此,修道生活中对知识的学习始终要服从于追寻上帝的目标。在道德上,人们越是依赖世俗的学问去解释、理解问题,利用辩证法的工具去探究信仰,就越会“自我膨胀”,在心理上放弃本笃修道主义宣扬的谦卑态度,犯下傲慢之罪。(22)Jean Leclercq, The Love of Learning and the Desire for God:The Study of Monastic Culture, pp.206-207.
在对知识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警惕的同时,僧侣学者又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肯定了知识的价值。比德就对拉丁古典修辞学的宗教价值持积极态度。《圣经·撒母耳记》记载了扫罗与其子约拿带领人民与非利士人作战的事迹。故事中约拿违背了其父斋戒的誓言吃了树林中的蜂蜜,但却因此明目击杀了更多敌人。比德认为,拉丁古典学术亦如这树林中的蜂蜜,浅尝辄止不但没有坏处,还有益于信仰的增进。约拿对非利士人的意外战绩归功于蜂蜜,亚他那修在尼西亚会议上能够击败阿里乌斯派,亦与其在古典修辞学上的功力有关。(23)Roger Ray,“Bede and Cicero,” Michael Lapidge,ed, Anglo-Saxon England,Vol.16, 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pp.1-15.以西塞罗、昆体良、维吉尔等拉丁古典学者为代表的修辞学、演说术,在比德眼中是价值中立可以被修士们利用的知识工具。
中世纪的基督教学者好似拿着平衡棒在走钢丝的艺人,需要在信仰与知识的张力中寻找平衡。他们渴求用知识填充自己的精神世界,但稍有不慎对纯粹知识的追求就会使其堕入道德尴尬的境地。罗马帝国末期著名的教会学者哲罗姆曾因痴迷拉丁古典文学而做过一个梦。梦中他被押解到天堂中接受审判,天使控诉他是西塞罗的门徒而非上帝的追随者。梦醒过后,哲罗姆立刻发誓再也不看任何拉丁古典文献。(24)Charles Mierowtr, The Letters of St.Jerome, Vol.1, NewYork: Newman Press,1963, p.166.一个人如果过多地追求俗世的智慧,对自己的知识、智力过于自信,就是犯了傲慢的原罪。然而,一名成功的学者定然是对学习与知识抱有极高热情的人。学者个人强烈的求知欲与他的信仰经常会产生冲突。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在他的《忏悔录》中细数了自己早年犯下的罪行,为自己在幼年沉迷于维吉尔、狄多(Dido)等拉丁古典文学作品感到深深地愧疚。(25)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页。但矛盾的是,恰恰是奥古斯丁口中这些“荒诞不经的文字”对他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世纪英国僧侣学者奥德海伦在坎特伯雷进修时,曾因痴迷于研习罗马法无法回修道院庆祝圣诞专门在节日来临之际给地方主教写信致歉的事例,多少也体现了学习与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26)M. R. James: Two Ancient English Scholars: St Aldhelm and William of Malmesbury, Glasgow:Jackson, Wylie & Co, 1931,p.14.
知识与信仰的关系在11世纪的文化复兴浪潮中得到了改善。10世纪末,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在法兰西北部被重新发现,并在11—12世纪迅速传播到圣米歇尔山、沙特尔等地的宗教学校中。(27)R. W. Southern, Saint Anselm, A Portrait in a Landsca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8.古希腊逻辑、辩证法学说在欧洲重见天日,标志着七艺中与思辨有关的逻辑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修士开始使用新发现的辩证法工具来研究、探讨信仰问题,修道院中寻求知识的风气也越发浓厚。在这种背景下,知识与信仰的冲突必须得到解决。兰弗兰克的学生安瑟伦在此时提出“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的口号,试图调和理性与虔信间的紧张关系。他认为,单纯的信是一种消极的信仰,为了更好地信,信徒必须积极地利用知识和理性工具来研究、分析它。我们对信仰理解越深,就越能增进对上帝的信仰。知识、理性与信仰在安瑟伦这里不再对立,僧侣们对理性和知识的追求不但不会贬损信仰,反会成为他们修道路上的良好助力。
安瑟伦的这个口号代表了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在知识问题上的转向。僧侣学者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汲取知识的养分,学习与创造知识并非修道生活附产品,它们有成为修道者主业的资格。在史家的记载中,当时贝克修道院学校的学生“是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知识的学习之中,是那样急切地想要解决神学问题,编纂教化文章,以至于他们人人都像是哲学家”。(28)Thomas Forester tr,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us Vitalis, Vol. 2,p.68.在日常礼拜活动之余,他们急切地利用新的知识工具去探究三位一体、真理、自由意志、撒旦的堕落、上帝为何创造人类等问题。
在安瑟伦等学者对知识态度转变的背后,此时期诺曼底修道院在制度层面也发生了有利于智识活动开展的改变。在兰弗兰克的时代,诺曼底大公理查德二世邀请意大利僧侣沃尔皮亚诺的威廉(William of Volpiano)前往费康(Fécamp)主持修道院建设。这位熟悉几何学与医术,精通音律和建筑艺术的僧侣将克吕尼修道主义引入诺曼底,促使此地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1035—1066年)里涌现出25座新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在组织架构上仿照当时的克吕尼修道院的结构,形成了一个效忠于大公并以费康为中心的修道组织网络。理论上,克吕尼修道改革促使修士将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冗长、烦琐且僵化的祷告仪式中,让修道生活变得对智识活动更加不友好。但现实中,诺曼底公爵政治上的强势让这些修道院的日常运转较少受到外界干预。威廉等宗教领袖能够依照自己的志趣改造修道规则,使得诺曼底的修道院相互之间保持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的同时享受充分的组织自由。在此背景下,此时段的诺曼底修道院在礼拜仪式等制度上能够看出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它对修道以外的事务有较高的包容性,不会因追寻超脱而对此世采取弃绝的态度,无论是拉丁古典作者的世俗文章,还是地中海地区的艺术风格在修道院中都能拥有一席之地,这就为智识活动的开展留下了空间。(29)Chrysogonus Waddell,“The Reform of the Liturgy from a Renaissance Perspective,” Robert L.Benson, Giles Constable, ed., 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pp.101-104.其次,延长礼拜让僧侣们得以名正言顺地取消会规中的手工劳作戒律,因为如果劳动是为了应对懒惰(sloth)这一灵魂之敌,现在完全以用虔诚的礼拜仪式、神圣阅读、抄写经文等活动代替它,由此僧侣们开展学习活动便有了正当的理由。(30)后世如奥德利克·维塔利斯,马莫斯伯里的威廉等修道院学者都曾提到过自己用撰写历史度过闲暇时光。Marjorie Chibnall, The World of Orderic Vitalis: Norman Monks and Norman Knights,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1984, p.66.再者,礼拜仪式的延长客观上导致修道院对圣经、圣徒传记等工具性文本的需求暴增,迫使修道院或修建自己独立的缮写室拷贝手稿,或求助于其他修道院图书馆的馆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院内智识活动的发展。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征服英格兰前夜的诺曼底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修道文化。这些新建的修道院一方面遵循克吕尼修道主义理想,严格遵守本笃修道戒律,使修道生活的运转变得井然有序;另一方面,它们更加重视知识获取对信仰生活的助益作用,对纯粹的智识活动更加宽容、开放。僧侣们在礼拜读经之余可以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对知识的追求上,形成一种学习氛围浓厚的修道生活,同时也带动了地区文化的繁荣。在当时,费康、贝克、阿弗朗什、卡昂和鲁昂等大修道院都建有学校,吸引全欧洲的学生前来学习。(31)Anne Lawrance,“Anglo-Norman Book Production,” David Bates,Anne Curry, ed.,England and Normandy in the Middle Age, London:The Hambledon Press,1994, p.81.即便是没有知名学者驻扎的普通修道院,也都普遍具备开展知识学习的良好条件。它们从建立伊始就配有图书馆和缮写室,专职的缮写员将各地搜罗而来的图书进行抄写、复制以满足僧侣们日益增长的知识需求。11世纪中叶诺曼底各主要修道院的藏书量飞速增长。这些书籍不仅数量多且种类繁杂,基本涵盖了礼拜用书以外中世纪流行的绝大多数图书门类。(32)11世纪,费康图书馆内书籍数量多到僧侣们需要专门制作书籍目录来帮助记录。具体的个案研究参见Branch Betty, The Development of Script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 Manuscripts of the Norman Abbey of Fécamp,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lassical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1974.修道院内藏书的增长绝非僧侣们附庸风雅的结果,现存抄本缺乏华丽装饰的现实与安瑟伦等学者告诫缮写员注重抄本准确性,忽略书籍装饰的劝言提醒我们,僧侣们抄写手稿时注重的是知识本身,书籍增多反映了学习活动的内在需求,是修道院智识生活繁荣的绝佳见证。(33)Jenny Weston,“Manuscript and Book Production at Le Bec,” Benjamin Pohl,Laura L. Gathagan, ed., A Companion to the Abbey of Le Bec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2018, pp.156-157.诺曼征服前,诺曼底诸修道院内的生活应当如菲利普(Philip of Harveng)所说的那般,在那里,“公正的人们服从于上帝的旨意,全身心地投入到唱诗、静思、祈祷、阅读之中。这种真诚的信仰净化了人的灵智,使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加简单、高效。”(34)Jean Leclercq, The Love of Learning and the Desire for God:The Study of Monastic Culture, p.198.
三、诺曼征服与英国智识生活的复兴
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来看,是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带动了英国智识生活的复兴。1066年初,诺曼底大公威廉一世挑战英国国王爱德华之兄哈罗德的王位继承权,领兵入侵英格兰。黑斯廷一役威廉大获全胜,哈罗德战死,诺曼人逐渐占领了整个英格兰。
在诺曼人的征服过程中,英国本土基督教组织因参与抵抗对外来征服者产生较大威胁。为稳固统治,诺曼人在征服后开始有计划的用外来教士取代本土人士担任教会组织中的要职。深得威廉大公信任的兰弗兰克在英格兰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职;约克的大主教职位落入了威廉的牧师托马斯(Thomas of Bayeux)之手。1073年,英格兰全境15个主教职位有8位诺曼人,4位洛塔林人(Lotharingian),2位英格兰本地人和1位意大利人,到威廉去世之时英国本土出身的主教只剩下了一位。(35)Frank Barlow, The English Church 1066—1154, London and NewYork:Longman,1979, p.57.征服者在英格兰的“诺曼化”政策不仅限于高级教士,各地方修道院的院长职位也是其意图控制的目标。据统计,1066年英格兰岛上共有35所修道院,其中4座大教堂修道院(坎特伯雷、温彻斯特、伍斯特、谢伯恩)里的2座——坎特伯雷与温彻斯特的修道院长分别是兰弗兰克与另外一位诺曼人沃克林(Walkelin),副院长则分别来自贝克与法国的圣图安。另外16所修道院在征服者威廉统治期间一共发生了24次人事任免,绝大部分都是任命诺曼人当修道院长,这其中来自贝克与卡昂这两座兰弗兰克曾经待过的修道院的就有15人。(36)David Dom Knowles, The Monastic Order in England, p.112.
修道院领袖的置换不仅意味着宗教组织对统治者的忠诚度有了保证,也为岛上修道院文化的复兴带来了契机。彼时诺曼底的僧侣早已习惯了戒律严苛、学术氛围浓厚的修道生活。他们进入英格兰后发现当地修道院纪律松弛,智识活动匮乏,僧侣们的文化水平极为低下,仿佛置身于文化与知识的孤岛。兰弗兰克曾对教皇将其派往英格兰任职表示不满,认为岛上文化一片荒芜,自己成天只能与野蛮人为伍,“忍受各种各样的麻烦与精神上的不适。”(37)Helen Clover and Margaret Gibson, ed., The letters of Lanfranc,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pp.30-33.这一时期从诺曼底来到岛上任职的修道院长都有过类似的抱怨。圣埃尔班修道院的院长保罗称自己的几位本土前任是“缺乏教养的傻瓜”;阿宾顿修道院瓦林以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是“粗俗之人”为由,禁止僧侣庆祝纪念本土圣徒的节日。(38)S.J.Ridyard, “CondignaVeneratio:Post-Conquest Attitudes to the Saints of the Anglo-Saxons,” R.Allen Brown ed., Anglo-Norman Studies IX, Woodbridge:The Boydell Press,1987, p.194.这些声音或多或少反映了诺曼征服之初英格兰文化贫乏的状态与外来“和尚”试图改变修道院糟糕现状的意愿。
新到任的修道院领袖在掌权后开始着手改善修道院的文化环境。他们自己的修道院在半个世纪以前同样声名不显,因此在如何振兴修道院文化发展方面有着现成的经验,可以依照前人的做法在英格兰展开书籍的抄录、搜罗工作。(39)提瑞(Thierry)花了8年时间在抄写员的帮助下为诺曼底的圣埃夫鲁修道院(St.Evroul)收集了大量的书籍,为僧侣知识生活的展开提供了保障。Thomas Forester tr,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usVitalis, Vol.2, pp.48-51.他们与诺曼底修道院的组织联系在英格兰与欧洲大陆之间构成了一张繁忙的文化交流网络,使岛上的修道院可以依靠欧洲大陆的文化资源反哺自身。这些外来僧侣前往英格兰任职时都有抄写员陪同,在后者的帮助下能够制作各类拉丁文作品的缮写室很快便在修道院中建立起来。(40)在阿宾顿修道院,修道院长莱纳德随行有一位来自久米埃日的抄写员;松兰(Scolland)在前往圣奥古斯丁修道院任职时,至少有一位来自圣米歇尔山抄写员陪伴;而在耶稣教堂修道院,兰弗兰克身边也带有两位诺曼人抄写员助手。A. Lawrance, “Anglo-Norman Book Production,” D. Bates, eds., England and Normandy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Rio Grande:The Hamblemdon Press,1994, pp.79-94.修道院长们利用原生修道院的组织人脉,向海峡对岸讨要抄本搜罗书籍。坐镇坎特伯雷的安瑟伦向自己原先待过的贝克修道院去信,讨要一些教父著作的抄本;兰弗兰克还曾要求诺曼底的僧侣们将自己落在贝克的保罗书信评注带到岛上来。在11世纪后半叶,英格兰各地的修道院普遍都开展了类似的书籍收罗工作。12世纪史家马莫斯伯里的威廉曾经回忆,在他幼年时来自久米埃日的修道院长戈德福里(Godfrey of Malmesburg)为修道院图书馆搜集、抄写了大量书籍。在圣埃尔班,那位曾嘲笑自己的前任没文化的修道院长保罗为图书馆找寻到28部书。圣卡利勒夫的威廉给杜勒姆修道院搜罗了50多部书。(41)David Dom Knowles, The Monastic Order in England, p.523.
诺曼征服后跨越海峡的宗教网络不仅给英格兰带来数量可观的书籍、抄本,同时也为两岸学者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1066年后英国与大陆日益密切的文化联系,使许多大型修道院可以非常方便地从欧洲的学校中聘请学者来自己修道院学校任教,彼时也会有精通教会法、罗马法等新兴学问的欧洲学者被邀请到岛上讲学,协助征服后岛上教会的改革工作。马莫斯伯里的修道院长瓦林就曾邀请当时巴黎大学著名的神学家、语法学家亚历山大·尼卡姆来执掌修道院学校,来自意大利博洛尼亚的法学家维卡利尤斯受大主教西奥博尔德之邀前往牛津讲学,成为英国史上首位罗马法教师。(42)J. J. G. Alexander, M. T. Gibsoned, Medieval Learning and Literature, Eassay presented to Richard William Hunt,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76, p.258.这一时期圣奥尔本斯、伯里圣埃德蒙德修道院的学校内也曾出现大陆学者的身影。这些学者的到来,不仅丰富了本土学校的课程内容,也让以文学为主导的修道院智识传统能够不断接触到欧陆新兴的思想潮流,为文化事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诺曼修道院长们推动的文化复兴运动不只集中在少数大型修道院,而是一个由点到面向各地扩散的过程。诺曼征服在英国创造了一个相对统一、稳定的政治环境,使那些未能享受到第一波文化发展成果的修道院,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派僧侣造访其他本土修道院讨要抄本、书籍。在基督教“好客”(hospitality)价值观的影响下,这些奔着文化交流目的去的“陌生人”绝少被当地修道院拒之门外。(43)福音书中强调,友善而慷慨地对待旅客是获得救赎的必要条件。本笃修道院会规中也对妥善款待访客做了具体的要求。在俗世层面,热情地接待访客能为修道院赢得良好的公共声誉,也可能因为客人的好感而带来实际的物质收益。参见马太福音24:34—40,米歇尔·普契卡:《本笃会规评注》(下),杜海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599页。关于好客价值观的论述,见Julie Kerr, Monastic Hospitality: The Benedictines in England, c.1070-c.1250,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7, pp.23-37.外来寻书的僧侣只要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就能从图书馆中借到书稿。在阿宾顿修道院,图书管理员没有权力将馆藏图书私自出售或赠予他人,但只要押上与图书等价或超出其价值的事物,外人就能够从他手中将书借走。在艾恩汉姆修道院只要有合适的价格,管理员甚至可以将馆内图书直接出售。而按照伊夫舍姆修道院的规矩,任何人在付出相应抵押之后都能够在图书馆中借走图书。当时英格兰境内除了西多会之外,绝大多数奉守本笃修道规则的修道院都有图书外借的习惯。(44)R. Graham, “The Intellectual Influence of English Monasticism between the Tenth and the Twelfth Centuries,” Trana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o.17, 1903, pp.23-65.受益于这种友好的社会氛围,知识与文化以书籍抄本为载体得以在英国修道组织内部频繁地流动,距离海岸线较远的修道院能够通过本土修道院内部的交流网络分享文化资源,诺曼征服在智识生活上带来的影响因此向英格兰各地辐射。
诺曼人推行的搜集、抄写图书政策与文化交流活动,在他们与后人的不懈坚持下在12世纪迎来丰收。英格兰的修道与智识生活在比德之后再一次走向繁荣。这最直观地体现在诺曼征服后岛上修道院藏书情况的改变。对比征服前,英格兰修道院的藏书量在黑斯廷斯战役结束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有了长足的增长。伯里圣埃德蒙德修道院在诺曼征服之前没有专门的缮写室,图书馆中只有圣经文本和赞美诗集等基本的礼拜用书。自法兰西人鲍德温担任修道院长开始,图书馆书籍收藏情况逐渐有了改观。1081年修道院建成了独立的缮写室,僧侣们有了读经专用的书籍。12世纪圣萨巴的安瑟伦(Anselm of St Saba)担任修道院长期间,有大量早期教父与中世纪神学家的著作在缮写室被抄录收入图书馆,修道院长本人也曾多次前往意大利,带回维吉尔、塞涅卡、普林尼等拉丁古典作家的众多书籍。(45)R. M. Thomson, “The library of Bury St.Edmunds Abbey in the Eleven and Twelfth Centuries,”Speculum,No.4, 1972,pp.627-628.
伯里圣埃德蒙德修道院藏书在诺曼征服后的变化情况可以反映这一时期英格兰藏书的整体发展趋势。达拉谟(Durham)、埃塞特(Exeter)、罗彻斯特(Rochester)、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等修道院的藏书量在此时都经历了一个大致相同的增长。在英国现存的文献抄本中,属于11世纪后半叶的有56本,到11世纪末有107本,随后到了160本,到12世纪初这个数字到了182本,最后在到1130年左右又翻了将近一倍达到302本。(46)Richard Gameson, “English Book Collections in the lat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 Symeon’s Durham and Its Context,” David. Rollason, eds, Symeon of Durham Historian of Durham and the North, Stamford: Shaun Tyas,1998,pp.232-233.书籍抄本这种程度的激增在中世纪实属罕见,以至于后世学者将12世纪称作“英国图书生产史上最伟大的时期”。(47)Rodney M. Thomson,“England and 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Past & Present, No.101 (Nov. 1983), p.15.
英国修道院的藏书在量上飞速增长的同时,藏书类型对比征服前也有明显改变,具体表现为礼拜仪式用书以外图书数量的显著增加。这一时期属于异教文学的拉丁古典作品在英国大量出现,拉昂的安瑟伦(Anselm of Laon)、沙特尔的伊福(Ivo of Chartres)等当代神学家的著作也经常出现在修道院藏书之中,有些新增的古典抄本甚至此前从未在岛上流传。(48)Richard Gameson, “English Book Collections in the Lat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 Symeon’s Durham and its Context,” p.243.总体上,现存该时期抄本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基督教教父的作品,数量占抄本总数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后教父时代的神学作品;再下来是圣经、福音书、诗篇等礼拜仪式的基本用书;最后是各类历史著作和圣徒传记。(49)Richard Gameson, “English Book Collections in the Lat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 Symeon’s Durham and its Context,” pp.235-237.
非工具性图书在总藏书中的占比提升与征服后新的修道生活直接相关,是智识活动活跃的重要指征。如前所述,纯粹的修道理想本与单纯的智识活动存在紧张关系。修道生活的核心是诵读经文与礼拜仪式,只需拥有经文和其他简单的祈祷用书即可维持,其他书籍并非必需品,只能算是日常修行的补充。此时修道院中拉丁教父的著作以及后教父时代的神学作品的抄本数量远远多于礼拜仪式书籍的现象表明,修道院中的学术活动在诺曼征服后日益活跃,僧侣们在修道之余有大量的时间研读各类神学著作与拉丁古典文学作品,使得院内对学术书籍的需要超出了对礼拜仪式书籍的需求。这种环境培养出了一批喜好追寻纯粹知识的僧侣,他们如史家马莫斯伯里的威廉一般,将一生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对古罗马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研习工作中,并用学习成果反哺宗教写作,为古典文献在中世纪的保存与传播做出了较大贡献。(50)Rodney M. Thomson,“England and 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Past & Present, No.101 (Nov. 1983), pp.11-13.显然,诺曼征服后英国修道院的生活正在逐渐向海峡对面那些学习氛围浓厚的“姊妹”修道院靠拢。
修道院内藏书不断增长,智识活动日益活跃之时,英国整体的文化教育环境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改善。与征服前诺曼底的情况类似,此时英国的知识生产与传承活动开始依托修道院向全社会扩展。修道院在征服后仍然为立志修道的儿童与俗人提供传统的语法、修辞教育,如坎特伯雷、圣奥尔本斯等大型修道组织也能适应时代要求,让学生接受法学、神学等新学问的滋养。(51)Nicholas Orme, Medieval Schools: From Roman Britain to Renaissance Englan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55.在修道院之外,英国境内由南到北绝大多数主教座堂所在的城镇中都建有世俗学校,这些学校由修道组织或世俗教会赞助,在授课内容上更多聚焦于教会法与神学领域,为修道院、教会和政府源源不断地输送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才。即便当人们离开宗教与政治中心城市,他们仍旧能在科尔切斯特、丹维奇、沃里克等重要的商贸据点与港口找到可以提供文化教育的学校。(52)Nicholas Orme, Medieval Schools: From Roman Britain to Renaissance England, pp.192-193.这些学校在14世纪之前虽未能如同时期欧洲学校那样独立发展,但确实让僧侣以外的群体获得了更多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
英国的智识环境在诺曼征服后具体呈现出怎样的状况?或许我们可以从12世纪记述亚瑟王传说的伪史《不列颠诸王史》一书早期的流通情况中管窥一二。该伪史成书于12世纪30年代,一经问世便靠其内容与文笔而广受欢迎,很快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收获大量读者,随后又被翻译成各地的方言融入法国、西班牙、威尔士等地的文学故事中。(53)SinEchard,“The Latin Reception of the De gestisBritonum,” Joshua Byron Smith and Georgia Henley, ed., A Companion to Geoffrey of Monmouth,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2020,pp.209-234.有趣的是,在《不列颠诸王史》广泛的读者群中包括了一小批同时代的本土史家,他们在书籍问世不久就在各地读到了相关抄本。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早在1135年之前就已经获悉了该书部分内容,亨廷顿的亨利在1139年前往罗马的路上于贝克修道院内看到它的早期版本,稍晚些出生的12世纪史家也都曾获得过此书的抄本。(54)Jaakko Tahkokallio,“Early Manuscript Dissemination,” Joshua Byron Smith and Georgia Henley, ed.,A Companion to Geoffrey of Monmouth,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2020, pp.155-180.这些“专业读者”对这部同辈人的作品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亨廷顿的亨利因为它填补了英国早期历史的空白而对其大加赞善;威尔士的杰拉德则对其持怀疑态度,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写了个笑话嘲讽它的真实性;纽堡的威廉则从比德的权威论述和宗教常识两个层面对《不列颠诸王史》的叙事真实性展开批判。这些史家的行为很难被称作是“学术共同体”的自觉。但一本描述英国古代历史的书籍能在问世后就被大量复制并在欧洲各地快速流通,同时代相关领域的学人在众多赞赏声中有能力辨别书中的虚构内容,并从学理上对其进行理性批判,这件事本身即证明当时的智识环境繁荣而活跃。
结 语
在诺曼征服后的数十年,复兴了的修道院智识生活终于结出硕果。12世纪的英国涌现出安瑟伦、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等中世纪最为重要的学者,也有马莫斯伯里的威廉、伍斯特的约翰、坎特伯雷的艾德玛这样优秀的史家,在拉丁古典文学、自然科学、语法学领域都有一定的建树,同时见证了中世纪英国书籍生产的大繁荣。(55)R. W. Southern,“The Place of England in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History,Vol. 45, No.155, 1960, pp.201-216.这些英国文化复兴的代表人物多数是在本笃会受教、成长、生活的僧侣;部分学者虽是在欧洲大陆接受的经院哲学训练,但其早年的教育与后来主要的写作活动都与英国文化环境脱不开干系。从学术潮流上,不同于欧陆流行的主教座堂学校和辩证法学问,英国此时的智识活动更多集中在历史书写、经文评注及整理、研习拉丁古典文学遗产等领域,这些知识文化的形式源自修道院的古老传统,但在“精神与方法”上却体现出新的理性化思潮的影响。(56)J. 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64页。这些迹象表明,英国文化在12世纪取得的成就不是欧洲文化的简单移植,也非单纯的本土文化复兴,它植根于诺曼征服后新兴的修道生活,是11世纪以来欧陆新的智识潮流与修道组织改革运动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