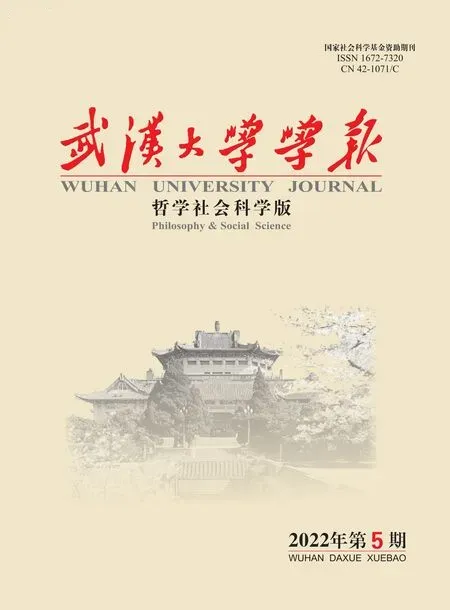西汉后期的文人与环境之关系
——以扬雄的述作经历为中心
侯文学
西汉后期是学术(经学)与文学、地方与京师(宫廷)诸文化奏出交响乐章的重要历史时期①本文所指的西汉后期,主要指元、成、哀、平四帝统治时期,即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至孺子居摄三年(8年)[1](P10-11)。。但既有研究受限于主题或材料,无论是于地域视角的考察还是共时性的整体研究,都忽略了文人流动带来的种种变化。有些问题还有待解决,比如:地方文化与京师(宫廷)文化有何差异,当文人由地方流向京师之后,带来述作上的哪些变化,变化的条件与动因何在?
扬雄是西汉末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人。他由蜀入京的经历,勾连了地方与京师(宫廷)。他各个时期都有述作且留存至今,为我们考察地方与京师(宫廷)文化对文人及其创作的影响提供了生动的个案。可以说,如果要考察西汉后期的上述问题,扬雄是资料相对完整的可资前后比较的唯一文人。而在既有的扬雄研究中,很少有人追问他知识的生成过程,追问他的辞赋及《太玄》《法言》《方言》的著作条件与述作之间的差异及背后的原因。
以神话传说与历史人物助成文思、表达观念,是扬雄述作最突出的现象。本文将以他的经历与述作中的人物为线索,将可以编年的扬雄西汉后期述作中所涉及的人物(包括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全部摘出,予以讨论,梳理其知识、观念的形成与变化等诸多问题。《核灵赋》的写作时间无从判断,且只有不相连属的数句残句,故不予讨论。扬雄作于新莽时期的《元后诔》《剧秦美新》是其第三阶段述作的延续,为了保证扬雄研究的完整性,也一并纳入讨论。
扬雄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居蜀时期;第二阶段,初入京师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门下史至承明殿待诏时期;第三阶段,为郎与石室观书时期。每一个阶段的述作形式与内容都与外在环境的变化关联密切。本文将细致梳理扬雄生平与述作的细节及其与环境的关联,还原西汉后期的文学与文化生态,追索当时文人①东汉王充的《论衡·书虚》《超奇》等篇对“文人”概念使用较多,李春青对此予以总结:“大抵能够遣词造句,布局谋篇而成文章者,均可涵盖在内。”[2](P197)本文对“文人”的理解同此。与环境的关系,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比较的基点。
一、居蜀时期:地方文人的知识结构与价值追求
扬雄居蜀时期的材料保存极少。《汉书·扬雄传》开篇说“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3](P3513),但后面追溯其家世时却又说他的先祖扬季“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3](P3513)。对此,任乃强解释说:“盖郫与成都紧连。雄实长、读于成都,有别业,为跨籍也。”[4](P541)任先生的推断是有道理的,《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间接谈到扬雄年轻时在成都问学于严君平的经历:“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杨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3](P3056)。而《汉书》本传关于其作《反离骚》之后“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3](P3515)的举动的叙述,则留下他早年活动于岷山之阳的郫县的线索[5](P158)。
现存扬雄居蜀时期的作品有《蜀王本纪》《蜀都赋》《反离骚》。《蜀都赋》并非一般论者所论定的汉代散体赋“曲终奏雅”的劝讽结构,全篇都以热情的笔调铺陈蜀都的形势物产、历史由来、风俗人情。开篇“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弥望,郁乎青葱,沃野千里”[5](P1)云云,将蜀地历史追溯到禹的时代。赋文通过禹的治水敷土传说,将蜀文化与华夏文明勾连,也为蜀地的千里沃野、丰饶物产寻找了一个人文的依据与起点。赋文在铺叙蜀人自己的历史时,言及的人物有蚕丛、杜宇、鼈灵:“王基既夷,蜀侯尚丛。”[5](P21)“昔天地降生杜鄠密促之君,则荆上亡尸之相。”[5](P35)丛,即蚕丛。据扬雄《蜀王本纪》,蚕丛是蜀人最先称王者。杜鄠,即杜宇;亡尸之相,指鼈灵。《蜀王本纪》载,杜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百余岁后,有荆人鼈灵之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5](P246)。望帝以鼈灵为相,命其出外治水,自己则与鼈灵妻通。后望帝惭愧,乃禅位于鼈灵。赋文将杜鄠、鼈灵并提,显然不以其德行缺失为意,反而强调其“天地降生”的神异。赋文写蜀地饮食、歌舞、游猎等风俗,其中涉及的具体人物有有伊、罗儒、吴公、郤公:“乃使有伊之徒,调夫五味”“罗儒吟,吴公连”“若其游怠鱼弋,郤公之徒,相与如平阳”[5](P31,36,40)。有伊,即伊尹,传说中他是善调美味的高手。枚乘《七发》:“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6](P637)罗儒、吴公盖为善歌者的代称。这儿的歌舞,曲调是不避郑卫之音的《凄秋》《阳春》[5](P36),歌舞者“眺朱颜,离绛唇”[5](P36),作者关注的是歌舞极具感染力的那方面,根本不在意歌舞的内容与儒家经学教义相违。郤公,亦见于左思《蜀都赋》,刘逵注:“豪侠也。”[6](P97)郤公等蜀地豪侠的游猎活动,成为扬雄笔下成都的一道风景。上述人物,或有道德缺失,或有长技,而其所持长技满足的是人的声色犬马一类欲望,作者于此津津乐道,并无儒家经学道德立场的批判。
《蜀王本纪》中出现的蜀地历史人物更多,除了蚕丛、杜宇,还有柏濩、鱼凫、尧、舜、卢保、开明尚、禹、启、老子等。对于蚕丛等蜀地先王,扬雄记录了他们的成仙传说。请看有代表性的几例: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5](P244)
望帝以鼈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鼈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鼈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鼈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鼈灵即位,号曰开明帝。[5](P246)
望帝去时,子䳏鸣,故蜀人悲子䳏鸣而思望帝。[5](P246)
这些记载中透出蜀人对于怪力乱神之事的兴趣与信仰。如果说《蜀王本纪》是扬雄在蜀地文献传说基础上整理而成,具有地方文献整理的性质,那么《蜀都赋》中与之相同的杜宇、鼈灵的叙事则显示出扬雄此时的为文旨趣有与之相合的一面——对于神怪之事相当有兴趣。
《反离骚》开篇叙述作者家世、先祖中有声名者,言之以表明自己有资格凭吊屈原。文中其他人物有重华、宓妃、瑶台之佚女、彭咸等人。其中,有6 处(8 人次)是撮《离骚》文意而述及,至如阳侯(波涛之神)、渔父等2处则是取资于屈原《九章》与托名屈原的《渔父》。另外,《反离骚》还指出屈原的行为是“资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赖”[5](P161),认为屈原应该学习孔子:“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5](P171)又批评屈原“弃由聃之所珍”而一味效法彭咸。娵娃,指孟娵和吴娃,古代的两个美女。二人并称见枚乘《七发》:“使先施、徵舒、阳文、段干、吴娃、闾娵、傅予之徒,杂裾垂髾,目窕心与,揄流波,杂杜若,蒙清尘,被兰泽,嬿服而御。”[6](P638-639)“仲尼之去鲁”见于《孟子·尽心下》:“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7](P329)由聃,指许由与老聃,二人在《庄子》中多次出现,以珍视生命著称。扬雄以之为乱世取法的对象,表明对于生命的珍视态度。上述人物以出自屈原《离骚》为多,这与本文的“摭《离骚》文而反之”的构思有关[3](P3515)。
上述神话传说与历史人物,多来自蜀地文献或民间口耳相传的传说,以及在蜀地流传的屈原、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也有《孟子》一类少量儒家文献。这些话语资源是扬雄抒情的语料,也折射其居蜀时期知识的主要来源。据《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论》,扬雄曾师从严君平,后者精于占筮技术与《易》《老子》《庄子》。扬雄从严君平处获得关于老庄的知识,即在《反离骚》等作品中获得呈现,至如其观摩严君平占筮而得的《易》类知识与相关思考,还要等到他入京作《太玄》才表现出来。据扬雄《答刘歆书》,他早期的著述还有《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成都城四隅铭》(今皆不传)等。《文选·甘泉赋》李周翰注还提到他早年作《绵竹颂》(今佚)。从篇名来看,其关注点在家乡的本土文化,且颇有应地方州郡县府之命(请)而作的痕迹。《答刘歆书》又说“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5](P264),这似乎说明,这几篇亡佚的作品,与司马相如赋颇类。征之以《蜀都赋》,实然。综上可以结论:早年居蜀时期的扬雄的知识主要是关于蜀地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易》、老庄、辞赋的,另有少量方言知识的积累[5](P263-264)。这里面既有他个人的兴趣与偏得,也有地域文化的影响。扬雄自陈“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3](P3514)的全部意蕴盖尽于此。此期的扬雄还热衷于鬼神仙怪一类不经之言,崇尚隐士保身全命的价值取向。《蜀王本纪》为编纂的地方历史文献,《蜀都赋》《反离骚》等是辞赋作品,在汉人的知识结构中,前者属于六艺春秋类,后者属于诗赋类,但从人物摄取来看,扬雄没有刻意区分两类著述的价值取向,很多与儒家经学价值取向相悖的人物受到肯定,显示其早期赋作不受经义道德牵绊的价值取向。
论者论及扬雄早年的教育,往往据文献记载的文翁化蜀的影响以及东汉蜀地的经学盛况来讨论扬雄所生活的西汉后期的蜀地经学,并推论扬雄早年“必然接受过较为严格的儒家教育”[8](P54)。但据《汉书·循吏传》,文翁的兴学举措发生在景帝末年,彼时儒家经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还没有确立,“经师犹乏,博士决不限于五经传记”[9](P194)。文翁立学官与蜀地的经学兴起不能并提。另《汉书·平帝纪》载,平帝元始三年夏,“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3](P355)。由此强制性的要求可推知,直到西汉将终,郡国的经学教育也并非处处发达,郡国官学中经师一人的配置尚需下诏落实,何谈五经的教育呢!蜀地地方官学或高于此,但也应相去不远。至于整个西汉蜀地私学的授经情况,也并不见载于史籍。彼时另一个事实是:“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而载也。”[10](P88)由下节所引在蜀曾为学官“僮子”的何武入京师太学习《易》经历推知,西汉中后期蜀郡的官学所授大概是《易》学。回到扬雄身上,由其现存早期文章述作所涉文献知识来看,并不出上面所论。扬雄晚年写给刘歆的书信曾回顾早年的学习状况说,彼时“于五经之训所不解”[5](P263-264),就未必是谦言。与此相应的是,《易》以外的儒家经典之学,在扬雄现存的居蜀时期作品中还没有多少痕迹。即便是最易入赋的《诗》的辞、义,在《蜀都赋》《反离骚》中也还不见踪影。
相较于蜀地经学资源的有限,京师可谓经师宿儒云集,除了最高学府太学有专门的博士授经,一些明习经学的官员也广收徒众,如习《春秋》的翟方进身为议郎,与同学胡常各有生徒,为身处京师的士子提供了许多习经的方便。生长京师的文人也因此更容易博通经典。与扬雄同期的文人刘歆自幼生长京师,贵为楚元王后裔,可谓京师贵族文人的代表,史载他“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3](P1967),又以能“诵读诗赋”,受到成帝的欣赏[3](P4019),则缘于京师浓郁的经学氛围与其家相对丰富的藏书及父亲刘向的引导。刘歆这种深厚的学养使他得以年纪轻轻就受诏参与父亲刘向主持的中秘校书活动[3](P1967)。与刘歆相比,谷永可以说是京师中层出身的文人代表,他的父亲谷吉于初元四年(前45年)以卫司马身份出使匈奴,被郅支单于杀害。自幼丧父的谷永少年时代即“为长安小史,后博学经书”,建昭(前38—前34年)年间,御史大夫繁延寿就闻其名,推举他为太常丞[3](P3443)。谷永的博学经书的收获,则与京师地区经学大师云集教授的氛围关联更为密切。
二、从门下史到待诏:身份的转变与知识的激增
武帝、宣帝好辞赋,士人或以此受到重视,仅蜀地作家就有司马相如、王褒由作赋步入仕途。这自然引发士人们创作辞赋的热情,也成为后世史家所乐道的西汉中后期的文化政策的一个方面。武帝以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3](P212),经学渐趋昌明。元、成好儒,多“征用儒生”[3](P298)。宣帝时名儒夏侯胜就常对学生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3](P3159)基于韦贤、韦玄成父子“以明经历位至丞相”的现实,其家乡邹鲁一带为生谣谚:“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3](P3107)。但在扬雄的家乡,似乎司马相如、王褒等人以辞赋为荣阶的榜样力量更为强大,所以出蜀前后的扬雄以“文似相如”为追求[3](P3522),也因此受到权门与帝王的重视。
论者大都能够据汉代选官制度,判断扬雄“以平民身份入官,必须有所请托”[8](P58),却因缺乏直接材料,无法推知细节。史书的间接记载却提示了被人忽视的若干线索,这就是长扬雄一辈的蜀人何武。
《汉书·何武传》载:“何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也。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娄蒙瑞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召见武等于宣室”[3](P3481),后“(何)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与翟方进交志相友。光禄勋举四行,迁为鄠令,坐法免归。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3](P3481-3482)。据此知何武是扬雄的同乡,两人经历相似,都是生在郫县,少年以后至成都求学。何武在宣帝神爵、五凤之间(假定是神爵四年、五凤元年,即公元前58年、前57年)时年十四五岁,那么他的生年则是公元前72年或前71年,长扬雄十八九岁。何武从太学学成之后,因成绩优异,先是为郎,又被任为鄠县县令。之后,又免官回乡,居乡期间颇有声望。何武何时回乡,我们不得而知。但据本传,何武居乡“久之,太仆王音举武贤良方正,征对策,拜为谏大夫,迁扬州刺史”[3](P3482)。《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载王音在河平三年(前26年)至阳朔二年(前23年)之间任太仆[3](P827,829-830),时扬雄28岁至31岁。《何武传》又载,何武乡居时,因兄弟何显与市啬夫发生矛盾,何武向太守建议,召市啬夫求商为卒史,并由此收获“州里闻之皆服”的声望[3](P3482)。可知免官后的何武在成都很有影响力,与官府保持密切往来。由此我们不难想到,居乡期间的何武应该知晓当地文名颇盛的郫县同乡扬雄。何武入京为谏大夫期间,向时(阳朔三年至永始二年)任大司马车骑将军的王音推荐扬雄[3](P830-831,834-835),在时间上刚好吻合。那么接下来30余岁的扬雄获知于王音[11](P851),“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3](P3583)。
奇怪的是,基于扬雄《自序》写成的《汉书·扬雄传》正文[3](P3583),并无王音、何武之名。这当如何理解呢?《汉书》给出了答案。《何武传》记载了何武与王莽的交恶:哀帝即位,疏远王氏,“后有诏举大常,莽私从武求举,武不敢举”[3](P3487);王氏重新得势后,“莽风有司劾奏武、公孙禄互相称举,皆免”[3](P3487);平帝元始三年(3年),何武遭诬陷,“大理正槛车征武,武自杀”[3](P3488)。据《王莽传》知,元始年间及稍后的孺子婴时,正是王莽筹措代汉的时期,其权势如日中天,故王莽能挟私报复何武,迫其自杀。扬雄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创作了《法言》[8](P181-183)。《扬雄传》所转录的《自序》提到《法言》的目录,知《自序》的写作又在《法言》完成之后,其规避与何武有关的信息,甚至不提及王音,当有避祸的考虑。
扬雄晚年的《答刘歆书》也回避了他与王氏的瓜葛,说其先前所作《县邸铭》《王佴颂》等文,是因同乡杨庄在成帝身边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5](P264)。因为成帝的鼓励,扬雄继续以司马相如为学习和模范的对象。扬雄在这一阶段创作的作品主要有《甘泉》《河东》《羽猎》三赋[3](P3522-3553,3583)。此三赋因与《长杨赋》创作时间较近,自《汉书·扬雄传》以来,学者们多将此四赋并提,视为一个整体。但四赋风格并不相同。具体而言,前三赋的结构、手法相似度较高,《长杨赋》自成一格,原因在于其间扬雄身份的转变①熊良智据《汉书·赵充国传》《段会宗传》《西域传》等文献所载西羌有警的具体事实,系《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于永始四年(前13年),《长杨赋》于元延元年(前12年)。我们认同熊先生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扬雄为郎的时间当在元延元年初。故本文将《赵充国颂》《长杨赋》放在第三部分即扬雄为郎与石室观书阶段予以讨论。。我们看《甘泉》等三赋。
三赋的题材不同,但结构一致,都是不假问对的直陈式。铺写帝王出行仪仗构成三赋的重点,这是司马相如以来以天子为中心的赋作布局特点。就写法而言,则是广泛摄入神话与传说人物用为帝王随行人员的比喻,关注点在人物的艺能与力量,以显示帝王出行的排场与威仪。就作者而言,则是满足对于天子仪仗的夸饰之趣。如《甘泉赋》写天子前往甘泉宫的仪仗:“八神奔而警跸兮,振殷辚而军装。”[5](P46)《河东赋》写天子往河东汾阴:“羲和司日,颜伦奉舆。”[5](P74)《羽猎赋》写天子往上林羽猎:“贲、育之伦,蒙盾负羽。”“蚩尤并毂,蒙公先驱。”“飞廉、云师,吸嚊潚率。”[5](P92,96)写天子的威德所及也是类似的手法:“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5](P62)“秦神下詟,跖魂负沴;河灵矍踢,爪华蹈衰。”[5](P74)“叱风伯于南北兮,呵雨师于西东。”[5](P78)
因题材不同,三篇赋作又各有铺陈的重心,但借神话与历史传说人物以为比喻夸饰则又是必不可少的手法。三赋涉及神话中的神怪33人,历史传说人物42人。其中《甘泉赋》神怪16人,历史传说人物11人;《河东赋》神怪9 人,历史传说人物11 人;《羽猎赋》神怪8 人,历史传说人物20 人。我们同样关注的是,扬雄从何处得来关于这些神怪与历史传说人物的知识的?时间久远,文献散佚严重,已不能完全指实,但结合前人注释,可以知道大概的情形。《甘泉赋》出现的神怪与历史传说人物见于司马相如《大人赋》者计有5人:獝狂②当即《大人赋》中的矞皇。獝、矞古通用。狂、皇俱可通“往”。、玄冥、征侨(即征伯侨)、西王母、玉女;见于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者1人:偓佺;见于《离骚》者3人:虙妃(即宓妃)、巫咸、帝阍。另有一些神灵与传说人物,如倕、蚩尤、泰壹、般、王尔、皋陶、伊尹等,散见于《庄子》《九章》《山海经》《尚书》《吕氏春秋》《孟子》《墨子》《韩非子》《淮南子》《史记》等。他如招摇、泰阴、堪舆、壁垒等,后世注家也不能明其出处。仅就已知的部分看,《甘泉赋》中的神灵与历史传说人物以取资《大人赋》为多。《河东赋》中的神灵与历史传说人物也以出自《大人赋》者为多,如风伯、雨师、钩芒(句芒)、蓐收、玄冥、祝融,也旁及《离骚》《尚书》《史记》《韩诗外传》等文献,如羲和、颜伦(颜沦)、秦神(怒特)、河灵(河神)等。他如晋文公、介子推、大禹、虞舜、唐尧,并见《九章》《左传》《史记》《尚书》等。另有一些历史人物则隐含在地名当中,如南巢、垓下、彭城、岐等。据《史记》,夏桀无道,汤放桀于南巢;项羽败于垓下,都于彭城;公刘居豳;太王居岐。作者由地及人,引出这些历史上的圣主贤臣与昏暴之君,以供帝王省思。《羽猎赋》中的神灵与历史传说人物如飞廉、云师、虙妃,俱出《离骚》。他如望舒、屈原、彭胥(彭咸与伍子胥)、贲育(孟贲和夏育)等,以出自《离骚》《九章》为主,也有《孟子》《七发》《韩诗外传》《史记》等文献。
综上,扬雄《甘泉》等三赋神灵与历史传说人物以出自司马相如《大人赋》《天子游猎赋》及屈原作品为多,其次是《尚书》《孟子》《山海经》《韩诗外传》《韩诗内传》《淮南子》《史记》等文献。三赋相对于早期的《蜀都赋》《反离骚》,变化较为明显。从摄入人物的数量与来源看,三赋出现人物更多,且知识来源复杂,分别出自六艺经传、前人辞赋作品、传说、史书。从人物对于构篇的作用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古代的圣王贤臣,关注点在其功业与德行,用为当今天子圣明、求索贤才的比喻;天地间的神怪异物,关注点在其技艺与力量,用为天子壮观仪仗与参与狩猎的勇士的比喻,表明天子驱遣天地、无所不能的威力;同情与摒弃的对象,用以颂扬天子的德行。三赋对于天地间的神怪异物,相当一部分是正面取用的态度,这与居蜀时所作《蜀都赋》类似。此期扬雄的神话传说与历史知识大增。三赋对于《诗》《书》等经典颇有涉猎,尤其是对于《诗》的辞、义等的取用,多达9次[12](P332-356),这在此后的作品中较为常见,却是扬雄现存居蜀时期的作品所没有的现象。那么,何以会发生上述变化呢?
扬雄经历与环境的变化提供了答案线索。《汉书·扬雄传》:“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3](P3522)承明之庭即承明殿。扬雄是在待诏承明殿期间写作了《甘泉》等三赋。承明殿是当时奉诏文人的主要著述之所,《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13](P58)班固《两都赋》:“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周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14](P1341)意思是说,承明殿、金马门是文人们奉诏著书立说的地方,他们还负责校理秘书。可见,承明殿、金马门也是宫中的藏书之所。我们有理由相信,奉诏作赋的扬雄,此间有机会阅读承明殿的藏书,以更好地完成他的创作。这些书籍成为他骋辞赋作的重要知识来源。扬雄三篇赋作知识承载量较大,作者所以能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完成三篇大赋,其承明殿待诏身份所带来的阅读殿中藏书的方便,是不能忽视的因素。面对“壮好经书”“精于《诗》《书》”又爱好辞赋的成帝[3](P301,1950),身处以帝王之趣为核心的宫廷文学氛围,文人作赋语涉经典、引经以助文,是势之必然。
未央宫的承明殿与金马门是西汉中后期待诏文人的主要汇聚之所,也是最富艺术气息的述作空间。一些来自全国各地有一技之长的被征召者,在获得正式职官之前,要以待诏的身份展示才技。这些人所擅才华各异,史载武帝时吾丘寿王以善棋艺(格五)待诏,宣帝时赵定、龙德以善琴待诏[3](P2794,1711)。《汉志·诸子略》纵横家还列了武帝时的“《待诏金马聊苍》三篇”[3](P1739)。用我们今天的话语说,在承明殿、金马门的待诏者大概涵盖了当时各个学科的拔尖人才。他们的才技多转化为文字述作,并呈现出广博的特色。承明殿、金马门的藏书类型,当与这些待诏者所擅的方面有所关联。上引班固《两都赋》赋写西都长安的文化盛事,就特别拈出在承明殿、金马门著作的文人们的述作风格是“元元本本,周见洽闻”。而擅长辞赋的待诏者的数量大概是最多的,如枚皋、王褒、张子侨、华龙、冯商等。经“待诏”的身份入仕也几乎成了西汉中后期擅长辞赋者的入仕传统。
赋是高品位的文学样式,需要大量的博物学、神话学与历史学等知识充实其中,以满足赋体本身的铺陈夸饰之趣。获取这些知识在今天不为难事,但在书缺简脱与文献载体或笨重或贵重的西汉,却需要一定的机遇。以辞赋见长的扬雄出蜀入京,待诏承明殿奉旨创作,待诏群体历史形成的艺术氛围、承明殿丰富的藏书助成了他的骋辞能力,《甘泉》《河东》《羽猎》三赋即因之而成,三赋既满足了帝王的辞赋趣味,也成为赋史的经典。
三、为郎与石室观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的价值凝定
史载扬雄奏《羽猎赋》后,由待诏拜为郎官[3](P3583)。这是为多数研究者所忽略的扬雄经历的重大转变。经学通明是西汉后期郎吏群体的主要素质,而这些经学通明的郎官又是后来高官的重要来源。这些大部分时间都身居宫廷当值的士子,人数众多,朝夕相处(每工作五日,才能有一日休假,出宫归家)[15](P265),互相之间交流议论的机会自然很多。身处其中的扬雄不可能无动于衷。对于献赋得官的出身、作赋类俳倡的待遇未免耿耿于怀,也让他感受到自己青年时期学问的偏颇,发愤去读“圣哲之书”也是必然的选择[3](P3514)。其《答刘歆书》说他在“为郎之岁”上奏成帝:“少不得学,而心好沉博绝丽之文,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徭,得肆心广意,以自克就。”[5](P264)成帝嘉许他的志愿,“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5](P264)。石室,指石渠阁,阁中多藏秘书,一般官员不得借观,故汉史有“泄秘书”获罪的记载[3](P796-797)。石渠阁还是西汉宣帝以后博士校订经书、辩论经义的最重要的所在,经典类藏书自然可观。扬雄要去石渠阁观书,读经的立意显然。相对于石渠阁藏书,承明殿的藏书质量与数量是很逊色的。石渠阁至迟在王莽时废为铸币场所,彼时中秘图书大概都转置天禄阁[16]。因此,后来扬雄又去“校书天禄阁”[3](P3584),与“观书石室”的初衷并无不同。可以说,石室观书并藉以立言成名是扬雄人生最后阶段的主要事业。
扬雄具体入石室观书的时间不得而知。但据《答刘歆书》,在他为郎的当年,上奏成帝,请求入石室观书,成帝痛快答允。可知扬雄为郎之年,便入石室读书,这也是学者们比较一致的意见。前言《赵充国颂》与《长杨赋》创作时间相仿,都是初入石室观书的作品。《太玄》《解嘲》《解难》《太玄赋》《上疏谏勿许单于朝》《逐贫赋》《法言》《琴清英》《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包括作于新莽时期的《剧秦美新》《元后诔》)则是他入石室观书颇有一段时日之后的著述[8](P347-354),在大体的创作时间的判断上,学者们并无争议。自得到成帝的支持,扬雄似乎就一直延续着在中秘读书、校书的生涯。此期政局变化剧烈,哀帝揽政,平帝继立,稍后王莽居摄,继而新朝建立,这些变化固然在扬雄的著述中留下影迹,但没有动摇他的价值体系。
(一)初入石室的价值转向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是《长杨赋》《赵充国颂》。《长杨赋》设为主客问答,概述汉、匈关系,赋予成帝猎长杨以历史的依据,现实的理由。赋开篇用封豕、窫窳、凿齿等凶神怪兽来比拟形容暴秦与六国残害士民、将高祖起兵笼罩在“上帝眷顾”的天命之下。除此以外,全篇出现的都是历史人物,如“躬服节俭,绨衣不敝”[5](P122)的汉文帝,任命卫青、霍去病“砰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5](P124)的汉武帝。赋文写文帝突出其节俭,写武帝突出其出击匈奴、南越、羌僰等四夷的赫赫武功,目的是为当今天子的行为寻找前代圣王依据,所以下文说当今天子:“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5](P129)非但如此,当今天子还取法三王、五帝:“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5](P129)可谓德业至隆。赋文最后指出,那些反对习马长杨的人如不见咫尺的盲者,缺乏“离娄烛千里之隅”的长远之见[5](P129)。
此赋是扬雄初入石室观书的作品,但身份与环境的变化已经在创作中有所体现。将此赋与《甘泉》《河东》《羽猎》三赋对比能明显看到这种差异。《甘泉》等三赋都有表现天子出行的场面,表现手法也相似,即用天地之间的神怪来铺陈天子仪仗。强调神灵的神性与力量,至于其善恶等道德因素则不在考量之内。《长杨赋》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借猎长杨之事说明对待匈奴的策略。此赋纯以铺陈汉初以来的历史事实(此事实经过作者的筛选)取胜,显示出相当的历史厚度与人文理性。虽然《文选》将其归类为“田猎”,但赋写田猎的笔墨并不多,与《天子游猎赋》《羽猎赋》有较大不同。相对于前三赋,此赋历史人物摄入较多,达10人,神怪较少,仅4人。即便是取用《淮南子·本经训》中的封豕、窫窳、凿齿等怪兽,但作者明确提示是用为比喻,目的是强调六国与秦政的残暴(神怪的力量与失德捆绑在一起)。与《甘泉》等三赋直接用为天子仪仗的比喻(只取其勇力),还是有所不同。这种改变不乏作家创新求变的考虑,也与彼时作者为郎的身份、视野与为文旨趣的变化有关。
与《长杨赋》创作时间相近的《赵充国颂》,思路与风格均与《长杨赋》相似:“明灵惟宣,戎有先零……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5](P293)引古证今,表明宣帝时的将军赵充国的武功乃是接续周宣王时期的名臣方叔、召虎的事业。从人物摄取看,作者主要取鉴于《诗》,将赵充国置于儒家经典政治的框架下予以刻画。这说明为郎之后的扬雄对于文章的儒家经学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有了相当的关注与认同。
(二)观书立言中的不遇之感与《易》、老宽慰
扬雄读中秘书若干年后,撰成《太玄赋》《解嘲》《解难》,纯粹抒写个人怀抱。三篇作品都与其仿《易》而作的《太玄》有关①扬雄仿《易》而作《太玄》,受当时京师重《易》氛围的影响。刘向、刘歆校书,成《七略》,班固据以成《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便以《易》为引领,视其为五经之原。。颇令他自负的《太玄》与官位的卑微给扬雄造成心理冲击,三篇作品就是作者的自解之词。《太玄赋》中,作者自陈从《易》与《老子》体认了人生损益无常、祸福相依的道理,认为应该学习许由、老聃“执玄静于中谷”[5](P141)。他设想出一个自由的近乎游仙的境界来使“执玄静于中谷”的心境具象化,主人公驱遣众仙灵,先是“纳傿、禄于江淮兮,揖松、乔于华岳”,又“役青要与承戈兮,舞冯夷以作乐。听素女之清声兮,观宓妃之妙曲”,继而“载羡门与俪游”[5](P141-142)。与此境界构成反对的,则是在世俗网罗中挣扎的古今人物:“斯、错位极,离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鱼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饿首山兮。断迹属娄,何足称兮。”[5](P144)作者并不认同他们的选择,表示“我异于此,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5](P144)。《易》的思想与道家价值观念给予扬雄以安慰,道家人物老子也成为他师法的对象。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文献看,这些人物或已见于扬雄早期作品,或见于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或来自《山海经》等神怪之书,或见于《史记》等历史文献,或见于儒家经典文献,或来自当时流行的仙话传说。这些人物从作者态度说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作者学习师法的对象,如许由、老聃;一组是消遣交游的对象,如赤松、王乔、宓妃等,他们都是传说中的仙人,主人公或与他们交友,或欣赏他们的才艺;一组是他否定的对象,如李斯、晁错、屈原、伍子胥等,作者认为他们虽然“智若渊兮”,但都死于非命,不值得效仿。
与《太玄赋》颇耽于人仙娱戏的想象的笔法不同,《解嘲》《解难》则完全就历史人物来书写怀抱。《解嘲》的作因在于“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3](P3565-3566)。文仿东方朔《答客难》的体式,以“客嘲扬子”独守《太玄》而“为官之拓落”起笔,随后借“扬子”之口开列出一系列历史人物的遭际,用以说明时移势易、彼我异时的道理。《解嘲》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有范雎、颜阖、驺衍、孟轲、稷、契、皋陶、伊尹等53人。文中人物及其事迹多见于《史记》《庄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先秦汉初典籍,而以《史记》及诸子书为主。
扬雄对于这些人物的看法值得注意。他肯定人物的才能,驺衍、孟轲并提,以明战国君主以得士人为务;又用稷、契、皋陶、伊尹、晏婴、管仲来说明当时人的自我认同与期许的情况;再用比干、箕子、微子、伯夷、姜太公、伍子胥、范雎、蔡泽等人事例,说明士人有才能则得任用及君主得士则国强的道理。他先直接排列出有能之士的名字,指出他们才能的落实之处,说明时移势易,当今无事之时不需人才的现实环境。接下来写“上世之士”管仲、傅说、侯嬴、姜太公、孔子、虞卿、小臣稷、驺衍等人出身的卑微、君主不拘一格的拔擢,以为当今天子、地方官不用人才的对比。文末又出列范雎、蔡泽、刘敬、叔孙通、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事迹,指出他们的“为可为于可为之时”,所以成就事业。对于这些人才智的肯定态度贯穿全文。至于穰侯、唐举、臾跗、扁鹊、卓文君、细君等人则是叙及上述历史人物连带而及的人物,不是扬雄关注的重心。总体来看,扬雄关注历史人物的才智与他们所处的时机,并不涉及人物的道德境界。这就与早期赋类作品对人物取用保持了前后一贯的视角。
据《汉书·扬雄传》,《解难》之作是因为《太玄》作成,“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的情形[3](P3575),扬雄遂作此文以自我纾解。文章先以伏羲作《易》,文王附爻、孔子错象、彖辞,说明宏文必艰深的道理,又进一步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獿人与匠石的故事、师旷故事、孔子作《春秋》事、老聃的名言等来说明宏文必然少有解者,《太玄》非庸人所能知。最后作者在老子的遗言中找到安慰:“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5](P201-202)熟悉先秦两汉典籍者都知道,这些人物故事分别见于《淮南子》《庄子》《吕氏春秋》《孟子》等文献。
二《解》涉及的历史人物较多,相关知识主要是来自《史记》与诸子书。《史记》在西汉后期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并不易得。如《汉书·叙传》《东平思王刘宇传》均载,东平王刘宇贵为宣帝之子,但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即《史记》),成帝却要征求大将军王凤的意见,因为王凤反对,刘宇失意而归。扬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选择诸子书与《史记》来阅读,与他最初入石室选择经书来读一样,是外在环境的鼓舞与推动。《史记》为他的《解嘲》之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同样是抒写不遇之感,东方朔以才辩取胜,扬雄则以知识的密集出脱前者的樊篱。
这方面的阅读也刺激了思想进一步变化的扬雄后来写作《法言》。《汉书》本传谈到扬雄作《法言》的目的:“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3](P3580)《史记》与诸子书既是扬雄《解嘲》等设辞类作品的资料来源,也是他以圣人继承人自居时批判的对象。
(三)儒家经学价值取向的提纯与述作表现
与《太玄》《解嘲》《解难》三文相反,此后的《法言》全以儒家经学伦理道德尺度评价历史人物。很多《解嘲》等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在《法言》中都受到道德的鞭挞。《法言》中涉及的人物236个,都是以历史人物的形象出场。从关涉事件判断,《法言》中人物的文献出处主要是《史记》《诗》《尚书》《春秋》经传、《易传》《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庄子》《邹子》《老子》《说苑》《楚汉春秋》《子思》以及当代史料和俗议,而以《史记》为最。依扬雄态度,这些人物可以分为六组:
第一组是《法言》肯定的人物,主要是早期儒家所推重的道德楷模,如尧、舜、禹、汤、皋陶、箕子、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渊、孟子等;另有一些则以淡薄寡欲、洁身自好著称,如严遵、郑子真等,这与《论语》的立场相接;还有一些偏有一行的人物,如荀息、程婴、公孙杵臼、蔺相如等;或是近世社稷之臣与名卿良将,如张良、陈平、周勃、周亚夫、卫青、霍去病等。第二组为《法言》部分否定者,同时也指出其可取之处。如老子,取其论道德,否定其“搥提仁义,绝灭礼学”[17](P114);庄子,取其“少欲”,否定其无视“君臣之义”;邹衍,取其“自持”,否定其“无知于天地之间”“迂而不信”[17](P135,280)。第三组为部分否定者,但没有明确指出其可取之处,如叔孙通、晁错、东方朔等。这些人大概在世俗评价中享有较高声誉,《法言》则在前人基础上指出其不足。第四组以否定为主者,如杨朱,批评他“荡而不法”;申不害、韩非,批评二人“险而无化”。他如公孙龙、伍子胥、文种、羿、逢蒙、王良、蚩尤、王翦、要离、聂政、荆轲、张仪、苏秦、夏育、孟贲,蒙恬等,也都蒙受严厉的批评。第五组是作者评判理想人物、理想事物的衬托,没有直接否定,似乎也不以为意,如丹圭、猗顿等。第六组为叙其事而不置可否者,如扁鹊、落下闳等。
从阅读范围看,扬雄此时对于经史著作、诸子书有了广泛的阅读,所以能够站在儒家经学立场上,品评诸子,责其缺失。从价值取向看,《法言》主要接续了《论语》的价值观品评古今人物。第一组人物自不待言;第二组中的人物如庄子、邹衍、老子,《法言》只是肯定他们与儒家经学伦理相合的部分,或者是对儒家经学伦理顺应、完善的部分。对于第三、四组人物的批评否定,也主要立足于他们对儒家伦理的违背。与《论语》价值观稍有差异的是,扬雄格外称许善于保身全命者,如范蠡,扬雄既批评他不强谏而使其君“诎社稷之灵而童仆”[17](P330),又肯定他能够适时隐遁,赞以“肥矣哉”;对于屈原,则慨叹他“如玉如莹,爰变丹青”[17](P57),其实是对屈原自沉殒身的含蓄批评。
其中,第四组人物最值得人们注意。这一组很多人物也出现于《反离骚》《甘泉赋》《太玄赋》《解嘲》等辞赋类作品,但《法言》与这几篇辞赋类作品对上述人物的关注点却呈现较大差异。扬雄在《法言》中不否认这些人物偏有一才,但将这些才能置于伦理道德及保身全命的框架之下予以观照,其“才”便成为陨性伤身、戕害他人的助力,不足称道。如《渊骞》篇先提出“君子绝德,小人绝力”的命题[17](P418),然后具体出列绝力者的名单与行事,“秦悼武、乌获、任鄙,扛鼎、抃牛”[17](P418)。将这些人一并视为“绝力”的“小人”。与此态度类似,有人向他请教如何评价孟贲、夏育,他回应“育、贲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17](P491)。再如他给张仪、苏秦定性为“诈人”,评价说“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17](P448)。《法言》将被司马迁及俗议所肯定的古代与近代人物置于儒家经典道德秩序中评判,是作者接受经学价值的充分体现。
由此我们看到,在《法言》里,儒家伦理道德与保身全命成为衡平人物的主要标尺,才艺不具有独立价值,只要人物存在伦理道德缺陷,或在保身全命方面有所不足,就成为否定的对象。因此,那些在《甘泉》等三赋中被圣王驱遣的勇士神怪,在《解嘲》中被作者用以平衡自己的有才能但遭遇不幸的士人,在《法言》中几乎都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鞭挞。《羽猎赋》中伍子胥还是他同情与肯定的对象,并用以称颂成帝“鞭洛水之虙妃,饷屈原与彭胥”[5](P106),寄托他对于帝王求贤的讽谏。《解嘲》肯定伍子胥、范蠡和文种的才能以及三人对于吴、越的贡献,说“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粤伯”[5](P182)。在《法言》的观念世界里,扬雄则侧重开掘伍子胥“俾吴作乱,破楚、入郢、鞭尸、藉馆”的行为,指责他“不由德”[17](P330)。《蜀都赋》中豪侠“郤公之徒”还是蜀地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法言》却转而批判游侠,认为他们是“窃国灵”者。
与《法言》的创作约略同时的《上疏谏勿许单于朝》《逐贫赋》《琴清英》《州箴》《官箴》及作于新莽时期的《剧秦美新》《元后诔》等文章涉及人物136人,且都是历史人物,或者是西汉时期的学者文人所理解的历史人物(如少典,据《史记·五帝本纪》,是黄帝之父),神灵全部退场①有些人物,既有神话色彩,又有历史影迹,扬雄在这些作品中立足于后者来取用。。这几篇作品涉及的历史人物除跖、曹沫等少数人以外,都没有超过《法言》所论,从关涉事件判断,人物的文献来源主要是《尚书》《左传》《史记》《论语》《孟子》《诗》等六经经传、信史②按,《论语》《孟子》在汉代都被视为辅翼经书的“传”,如《汉书·扬雄传》谓扬雄以为“传莫大于《论语》”,《汉书》《说文》引《孟子》也都称“传曰”。,或《史记》以后的近代史料。其评判人物也秉持儒家道德规范,与《法言》的尺度一致。如《卫尉箴》:“曹子摽剑,遂成其诈。轲挟匕首,而卫人不寤。”[5](P366)《太仆箴》:“昔有淫羿,驰骋忘归。”[5](P370)《廷尉箴》:“昔在蚩尤,爰作淫刑。”[5](P373)《上林苑令箴》:“昔在帝羿,共田径游。”[5](P401)对于曹沫、荆轲,揭其挟君行刺;对于后羿,责其荒于田猎;对于蚩尤,发其制作淫刑。这些行为都违背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受到扬雄的批评与否定。
扬雄人生最后阶段所作的《州箴》《官箴》等奉制制作之文或应用文,或用以补阙朝政,或是表明他的德治理想,则只就六经与信史范围索取人物,对于人物态度,与《法言》保持一致。由扬雄人生不同阶段作品对于人物的选择(类型、关注点)可以看出,他对于怪力乱神的兴趣渐趋减弱,对于伦理政教的信仰逐渐攀升,表现在文类的选择上,就是想象的文学逐渐退场,伦理政治的说教应用之文成为他后期关注的重心。受环境影响并充分利用了环境方便的扬雄的述作由辞赋而儒学,终于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驱逐了神话,摒弃了与儒家对立的才、艺的独立价值,进入了儒家的理想国。他也不再是那个初入京师时“于五经之训所不解”的蜀地才子,并在身后赢得了与刘向父子齐名的评价:“(谷)永于经书,汎为疏达,与杜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浃如刘向父子及扬雄也。”[3](P3472)
将扬雄与西汉后期的其他文人的述作合观,会发现这些述作主要以“六艺”为宗,对六经作各方面的阐释、引申,其次便是辞赋,另有个别偏于实际的技术应用之作。我们看《汉书·艺文志》的归类就可一目了然③其他不具名或不明时代的述作也不排除有个别作于此期,另有《汉志》未录者(比如未录支持我们的结论的刘歆的述作),即便将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也不妨碍我们得出上述结论。。根据《汉书》中各方面的信息可以判断《汉志》中成于元帝至孺子婴时期文人述作有:《孟氏京房》11 篇、《灾异孟氏京房》66 篇、五鹿充宗《略说》3 篇、《京氏段嘉》12 篇(以上为《六艺略》之《易》类),刘向《五行传记》11卷、许商《五行传记》1篇、刘向《稽疑》1篇(以上为《六艺略》之《书》类),《王禹记》24篇(为《六艺略》之乐类),冯商所续《太史公》7篇(为《六艺略》之《春秋》类),《鲁安昌侯说》21篇、《鲁王骏说》20篇(以上为《六艺略》之《论语》类),《安昌侯说》1篇(《六艺略》之《孝经》类),《急就》1篇、《元尚》1篇、《训纂》1篇、《别字》13篇(即扬雄《方言》)、《苍颉传》1篇、扬雄《苍颉训纂》1篇、杜林《苍颉训纂》1篇、杜林《苍颉故》1篇(以上为《六艺略》之小学类);刘向所序67篇(班固自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扬雄所序38篇(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以上为《诸子略》儒家类),《氾胜之》18篇(班固自注:“成帝时为议郎。”)(为《诸子略》农家类),河内太守徐明赋3篇、给事黄门侍郎李息赋9篇、淮阳宪王赋2篇、扬雄赋12篇、待诏冯商赋9篇、博士弟子杜参赋2篇、车郎张丰赋3篇(班固自注:“张子侨子。”)(以上为《诗赋略》赋类),《许商算术》26卷、《杜忠算术》16卷(以上为《数术略》历谱类)[3](P1703-1766)。其中,《六艺略》占据了绝对数量(20种),其次是《诗赋略》中的赋类(7种),《诸子略》儒家类(2种),《数术略》历谱类(约2种。按,《杜忠算术》列在《许商算术》之后,也视为同时或稍后之作),农家类(1种)。按照汉人的理解,儒家类乃是羽翼六经之作,所谓“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者[3](P1728),可以与《六艺略》归并,概称儒家经学。这些经学述作者或供职内廷,或任职外朝,用文字共同演绎了西汉后期宫廷文人奉行的最高价值。
四、皇权与经学的双重规制:西汉后期文人生态
西汉自武帝以后,皇权在各方面得到强化,京师吸引力大增。士人流动方向也改变了早期较为分散的状态而以京师为主。扬雄家乡的先贤司马相如、王褒的经历最为典型地反映了此期的风气转变。这是西汉中期的大致情形。西汉后期士人流动仍以京师为主要去向,但彼时的文化环境与西汉中期存在较大差异。扬雄的述作转向就是这一差异的具体体现。
两汉地域文化特征鲜明。虽然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但经学的普及是个漫长的过程。直到经学史家所标举的“经学极盛”的西汉后期,蜀地经学仍然不甚发达。扬雄现存在蜀期间的述作几乎不涉五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地的文化样态,表明此时蜀地辞赋创作之风颇盛,司马相如等人开创的辞赋传统,直到西汉后期仍然蔚为风气。《汉书·地理志下》谈到蜀地文化时也主要立足于对此地辞赋传统的解释:“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3](P1645)这是东汉前期的班固对刚刚逝去的西汉史的总体印象,所据当更为充分。
通经与献赋是汉代文人踏进仕途的两条主要路径。如果说辞赋是西汉中后期蜀地重要传统,那么齐鲁之地则以经术(学)为盛。《汉书·地理志下》就说齐地“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3](P1661),又说鲁地虽因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3](P1663)。好学的对象,在儒家语境中,自然指向儒家之道。所谓“多至卿相”,指的是韦贤(鲁国邹人)、夏侯胜(东平人)、王吉(琅邪皋虞人)、贡禹(琅邪人)、匡衡(东海承人)等通明经学而至高官者。京师则以统治的需要与帝王的趣味显示其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并开出孝廉、待诏、公府辟除等名目,用为地方文人奔赴京师进入王庭的通道。就现有文献看,“待诏”是辞赋家成为天子近臣的主要通路。
同样是归趋京师,西汉后期扬雄的经历与武、宣时期的司马相如、王褒却有不可不辨的细微差异。后面两个人都是有人直接向天子推荐,天子直接征召,扬雄则是入京先被王音召为门下史,并因王音的推荐,得为承明殿待诏。扬雄这一经历反映了西汉成帝以后皇权下移王氏的情形。彼时王氏家族以太后(成帝母王政君)之故,分享了较多天子的威权,一时英俊如谷永、李寻、刘歆、杜邺、杜钦、班斿、班稚等莫不与之交好,或附之以求进。王氏家族成为平民与天子之间的“通行证”。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王氏长期左右政局,但西汉后期并没有形成以王氏为核心的文人创作群体,也没有出现对王氏歌功颂德的赋颂作品。同样是外戚专政,西汉后期与东汉中期以后(文人歌颂外戚窦氏、梁氏)又有所不同。
扬雄的述作以“为郎”为分界,前后期述作类型与价值取向发生较大变化。郎官文化群体与扬雄所面对的宫廷图书资源是促成其转变的环境与条件。人数众多的郎官是西汉宫廷最重要的知识群体,文化群体。帝王的需求与趣味主导以郎官群体为主的宫廷文化的风向。西汉后期元、成二帝在位时间较长,对西汉后期的宫廷文化氛围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一方面,元、成二帝都是文艺爱好者,史载元帝为太子时,曾经因为爱妾离世而“苦忽忽善忘,不乐”[3](P2829),他的父亲宣帝便令王褒为他诵读奇文,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3](P2829)。成帝也“性宽而好文辞”[3](P3465),彼时周围也聚集了一批辞赋作家。另一方面,元、成二帝以重儒学好五经著称。在经学与辞赋之间,前者的地位重于后者。至于哀帝则但行儒政,不重辞赋;平帝以后,政出王莽,更重经学。这就与武、宣时期宫廷文人生态有了较大不同。武、宣二帝均好辞赋,在武帝周围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著名辞赋作家群,宣帝先是征召能够诵读楚辞的九江被公,后又让有文才的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又征召“有轶材”的王褒。当有人以为辞赋乃淫靡不急的小事时,宣帝坦然为辞赋开解:“‘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3](P2829)相比于武、宣,元、成二帝的态度就显得消极被动,缺少相应的立场表述。
武帝确立了经学的意识形态地位,但无论是外朝官员还是身边的郎官构成仍然十分驳杂。如名臣主父偃、徐乐、严安、桑弘羊、卜式、李广、苏武、张骞、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霍光、张安世等人,都曾为郎,却都不以经学立身。武帝之道,宣帝承之。武、宣之间,还是王道与霸道并用,诚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3](P277)。反映在用人上,就是不拘一格。西汉后期的郎官固然也有如扬雄这般擅长辞赋或其他才艺者,但通明经学者却占较大比重。以作为常行定制的举孝廉和博士弟子射策甲科两种为例,据严耕望《两汉书列传人(及附传)除郎补吏表》统计,西汉武帝至宣帝时举孝廉为郎者4人(严表误将冯野王计入,此排除野王),元成至汉末7人;武帝至宣帝时博士弟子射策甲科为郎者2 人,元成至汉末3 人,另有召信臣在宣元之际,不能明确时间上的具体归属[18](P328-334)。举孝廉与明经关系密切。又据黄留珠《西汉孝廉》的统计,《汉书》载西汉孝廉16人,明言有“明经”“治(受)某经”类学历者11人,有先明经后举孝廉为郎者9人[19](P106-108)。可见,孝廉之选,主要还是考察其经学修养。如此,则西汉后期的郎官群体的经学素养要略胜武宣之际。这些都还是依据得以进入史书记载的名臣得出的结论。而为研究教育制度者所熟知的是,西汉后期专门修习经学的博士弟子扩招较多,相对于武帝时员额50 人,昭帝时100 人,宣帝末增为200 人,元帝时至少扩招至1000人,射策甲科为郎者所占比重自然更大,而这些人“为郎”是制度的规定。若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西汉后期郎吏群体通经者的比例会更高。扬雄《解嘲》“策非甲科,行非孝廉”[5](P188)的慨叹,乃是基于彼时内廷群体对于这两种出身之人的重视而发。彼时内廷的经学之盛也可想而知了。
就辞赋家出路而言,宣帝时王褒仅因为辞赋才能,便被擢为谏大夫,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谏大夫“秩比八百石”[3](P727);而以“能属文”受到成帝青睐的刘歆,最初也与扬雄经历相似,“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3](P1967)。黄门郎,即给事黄门的侍郎,秩比四百石而已。郎官成为元成时期纯粹的辞赋家仕禄的顶点。以经学为出身或兼明经学者的擢升却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出自“博士经学”系统的何武、翟方进,前者位至大司空,后者位至丞相;长于文辞的刘向、刘歆父子得以升迁,则主要得益于其“郎官经学”[20](P95)系统的出身。王褒早逝不论,武帝时司马相如以辞赋家终身,没有转向经学研究,成帝以后扬雄悔赋,转向儒家经学的述作,除了个人的才性等因素,生态环境的不同是不能忽视的原因。
西汉后期的郎官文化群体特征大致有二:第一,以明经者为主,若就形成的氛围而言,自然是以经学讨论为主,所擅以明经为上。第二,以广学、博通为风尚,非如彼时太学博士的“章句”经学拘牵于一家一派之学。刘向、刘歆父子以其身处政治中枢又统领中秘校书的权力与方便,相继引领此风气[20](P255-266)。扬雄“好博览”的性格与“不为章句”的学术取径正与此风尚相契。就郎官群体的便利条件而言,置于未央宫之北的石渠阁、天禄阁藏有彼时帝国质量最高、数量最巨的图书。这些图书对于朝廷之外的士子而言,是稀缺的资源。说到此,我们便不能忽视当时书籍流通的情况。
那是一个书籍复制全靠抄写的时代。简帛等载体或笨重或贵重,再加上一些书籍在流通方面的限制,对于一般士子而言,很多书籍并不容易获得。博览群书对于一般人而言,是比较奢侈的事。西汉待诏、郎官是主要的文学侍从群体,奉诏写作是其义务,义务背后也有方便条件可资利用,这就是宫廷藏书。《史记·太史公自序》谈到汉初至武帝时图书事业的发展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21](P4026)可见,西汉太史所藏之书(与太常、博士所藏之书俱称外书)数量就已经十分可观。中秘藏书(或称中书、内书)更不待言。那些富有才华、饱读经籍的承明殿待诏、金马门待诏、郎官们可以阅读的主要是中书。善于著作之士,利用这个方便条件,奉诏为文、著书。翻开《汉书·艺文志》我们注意到许多著述出自服务于宫廷的待诏、郎官(或有出入宫廷方便职事近似于郎官、待诏者)之手,虽然不能说这些作者都是借助宫廷藏书完成了立言的事业,但如此身份相似的庞大的述作群体却不难让我们看到其中的密切关联。即便是刘向、刘歆父子,贵为皇族,家中已有丰富的藏书,也还是借助宫廷藏书的便利,完成了《说苑》《新序》《列女传》《洪范五行传论》《七略》等相关著述,对于扬雄等平民知识分子而言,这些累积的精神财富更是何等重要!
中秘藏书在西汉后期对于文人而言尤其珍贵。王葆玹据《汉书》的相关记载得出的结论:“诸子书在汉昭帝时尚是贤良文学所依据的典籍,在汉宣帝时尚由于朝廷奉行‘霸王道杂之’的政策而得以流行,而到汉成帝时,却成了‘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的文献,是‘不宜在诸侯王’的禁书,可见当时的朝廷弥漫着‘独尊儒术’的气氛。”[22](P230)这也直接导致“经学之外的文化资源,甚至一些经学资源,就以文化遗产的形态封存在皇家图书馆里”[20](P234)。这些中秘书籍因为政令的限制,文本复制的困难,西汉后期即便是外廷官员也没有机会涉猎。唯有出入内廷,方有阅读的可能。仅由扬雄《法言》所涉人事来看,他是广泛阅读了诸子书、太史公书的。而这些书,是他后期立言的基础材料。
与此相关的是扬雄等内廷文人学者的经学“学派”问题。自晚清以来,学界讨论汉代经学,一直囿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二分法,并以此为框架对汉代文人学者予以定性,但结论并不一致,或依据扬雄对于孔子的评述等认为《法言》“体现了古文经学的精神”[23](P260),或认为他所受主要是今文经学,理据之一便是扬雄所称赞的楚人龚胜乃“古文经立学官的主要反对者之一”[8](P79)。但如果考虑到门户之见仅在博士经学系统中存在,内廷郎官的修习并无此限,这个二分法就失去了解释的效力。就扬雄、刘向等人的述作看,他们的学术没有局限于一经一家之学,而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有所主张与建构。博通是西汉后期郎官经学的氛围,也是身处其中的述作者的追求与特色,丰富的中秘藏书为其提供了智识资源。扬雄与刘向、刘歆父子因为身处相同的学术环境,拥有相近的学术旨趣与学术追求,他们也一并在身后获得了“洽浃”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