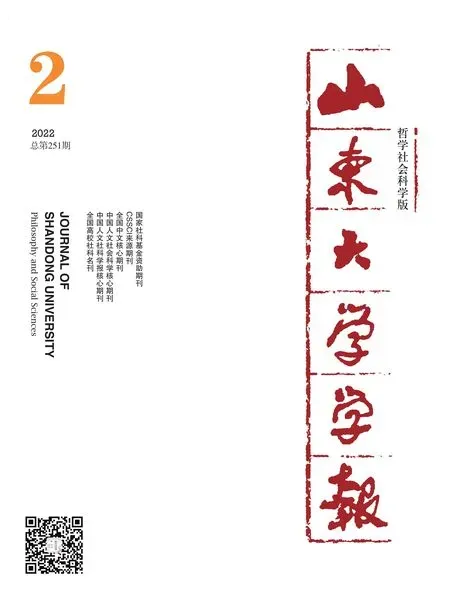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共情修辞路径
李 克 朱虹宇
在秉持人本主义原则的国际传播领域中,情感是重要且隐蔽的因素,即使正式程度较高的外交场合也无法完全抛却情感而只关注所谓“理性”。所以,以人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更需要严肃对待情感。
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获得受众认同并推动全球参与构建共同体的必经之路。受众国家及其情感的多元化,促使传播者脱离传统传播框架,在满布情感波动的新环境中寻找相应的传播模式。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要传播者,中国从来不是单纯、单向的说服者,而是始终秉持“以人为本”和“以仁为本”态度的传播者、始终携带情感关怀的受众共情者。将共情融入传播行为,以共情修辞为路径,提升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并引导其诉诸实际行动,是符合当前人本主义传播环境的因应之策,也是尊重受众情感的新型传播模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过程中,应当有效利用共情修辞的思维框架与修辞实践模式,推进修辞者与受众的情感联结,从而实现由情感同向到理念认同。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模式:修辞传播

修辞是关于如何获得受众“认同”(identification)的学问,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中,他国的观念认同与行动反馈是传播目标。此时,修辞与传播之间形成“体”与“用”的关系。“各类传播主体适时、适当、适度的修辞性干预”(3)刘肖、董子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的“时度效”研究》,《中国出版》2017年第11期。是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把握好修辞与传播的角色平衡与融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重要保障。

“修辞为体,传播为用”可适当消解修辞与传播的学理矛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可以借鉴并运用的一种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模式,已经逐渐从传统的“劝服型”向“认同型”转变,致力于引导国际社会产生观念认同与行为呼应(4)李畅、万婷:《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的视像化建构理路研究》,《新闻界》2019年第8期。,具有了以“认同”为核心、以唤起改变为目的的修辞性质,主要传播内容也被修辞化为修辞文本。修辞通过传播呈现并发挥效用,传播力与创新力的高低则直接影响修辞行为的有效性与持续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带有政治传播学的特点,目标是“促进不同的利益集团达成信仰互文、政治协商、社会共识”(5)胡范铸、胡亦名:《政治传播语言学的逻辑起点》,《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所以会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与受众,存在相当多的困难。另外,传播过程中任何一种阐发与表述都不会具有全球普适性,适应具体情境与受众态度而不断调整修辞文本,可为传播的有效性提供强有力保障。曾有学者强调说,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既有“我说你听”的互动,“让我们所说的,能够被国际社会听到、听清、听懂”(6)白丽娜:《中国各省市形象在西方网络世界的传播——基于英、汉两种语言媒介和网络前三页检索的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也包括“听懂”之后的认同与行动。我们认为,修辞传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国际社会的基本路径,进行先修辞后传播的内涵与外延构建,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高效传播。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基础:共同情感
(一)国际传播,情感先行
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心的国际传播中,受众自身的政策、利益等因素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我们需要从具体情境出发,寻找能为所有受众共享并具有较强传播感染力的因素,从而真正调动起受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的‘行动’需要共通的‘知识’,利益的‘调和’需要文化的‘理解’”(7)胡范铸、张虹倩、周萍:《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一个基于“文化治理”视域的分析框架》,《文化艺术研究》2021年第1期。,而文化的理解又离不开情感的参与。归根结底,情感是庞杂的受众群体共同拥有的特质。
情感是人类的共有属性和人际交流的基本要素,其“传导性、感化性和联动性聚焦了诉诸情感的普遍性”(8)詹小美、赵晓营:《记忆仪式沉浸化:共同体意识传播的情感动员》,《民族学刊》2021年第1期。,贯穿于人际交往的全过程。在以人际交往为前提的团体、组织甚至国际交往中,情感可成为重大事件的触发因素,因为它“不仅是社会现实的一种构成成分,同时也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源泉参与社会进程与分层系统的生产实践”(9)刘涛:《情感抗争:表演式抗争的情感框架与道德语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5期。。关于情感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法国蒙泰涅研究所特别顾问莫伊西曾这样说道:“情感很关键。情感影响到人们的态度,影响到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行为”(10)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5页。。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过程中,情感能否被唤起、能否影响并践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有相关的国家行为,是传播活动成功的前提。
情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中的作用应受到高度重视。对此,国内学者王锡苓、谢诗琦在设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评价体系时曾将“情感倾向”和“姿态平等”分别设定为舆论引导和引导方式下的三级指标(11)王锡苓、谢诗琦:《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评价体系的构建》,《现代传播》2020年第7期。,肯定了情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重视并需要发挥情感对受众的影响。当然,国情、国家利益、政策、外交原则等的不同会导致受众身份的不同,而国家行为与其身份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无形中强化了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12)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第170页。。
利益是国际社会的永恒话题,是国际交往的首要考虑因素,但情感却因其人本主义特质成为以“人的交往”为基础的“国的交往”的深层次行为逻辑之一。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情感的表达总是在审慎考量后由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人或机构代为发声。不同的国家会具有不同的国家现实,不同的国家现实会催生不同的国家情感。情感多元化会给前期的修辞过程与后期的传播过程带来不确定因素,从而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带来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寻找的是构建以“情感的沟通和共鸣”为基础的“情感共同体”(13)胡范铸:《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第97页。的可能性,以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命运同体,情感同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与共同情感的结合(15)张虹倩、胡范铸:《全球治理视域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及孔子学院建设:问题、因由与对策》,《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其中共同情感就是重要的情感交叉点,是建立情感共同体的必要因素。因此,我们提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过程中,着眼于如何发掘共同情感并建立情感共同体,推动修辞者和受众在拥有同向情感的基础上探讨关于人类发展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建设关涉全人类福祉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访问日期:2021年3月28日。,没有国家能够独立于该共同体。诸多国家之间虽然存在不易调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冲突,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各国仍然存在值得共同努力并将从中获益的发展目标。而各国对同一目标的追求能够激发起共同的渴望与情感,以此为根基的共同体建设关注到每个国家的情感需求,符合人本主义原则,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更持久的发展动力。如果我们能够促使国际社会秉持相同或相似的目标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那么各国的情感即使无法完全同步,也已处于有可能被影响的积极状态,并由此显现出传播行为的显著成效。
(三)积极共情,适切传播
全球共同体“是一个人类命运视角的共情性概念”(17)李怀亮:《从全球化时代到全球共同体时代》,《现代传播》2020年第6期。。共情是对他者情感的关注与代入,也是对他者情感类别与来源、自身情感类别与来源的全方位认识。共情对情感与认知的整合,适当平衡了情感的主观性倾向,是合乎“情”与“理”的思维模式与行事指导。当前,包含情感维度与认知维度的共情概念已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人本主义时代能够有效激活行动的活跃因素。在修辞传播中,共情是连接传播者与受众的重要纽带,一国范围内的传播活动是否能够达到理想效果,就在于传播者的共情能否激发受众的共情,实现以心换心、以情换情的目的。对此,曾有国内学者提出要在共情传播视角下探讨中国形象的内涵、意义和路径问题(18)赵新利:《共情传播视角下可爱中国形象塑造的路径探析》,《现代传播》2021年第9期。,所以我们在国际社会中也同样需要智慧地调用共情资源,从而促成有效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国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但彼此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所以如何对待差异将会极大影响国际交往的走向。在急遽演变的世界格局中,“如果要从抵触走向认同,则必须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进‘互惠性理解’”(19)周翔:《“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建构——概念再造、语境重置与方式转换》,《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7期。,而文化的差异将会带来几乎无法完全调和的思想和情感冲突,解决之道只有“求同存异”。从情感视角来看,情感“不仅为政治思想提供动机,而且还确定政治判断中必须使用的价值尺度”(20)刘晶:《政治视觉修辞的概念维度与阐释框架》,《浙江学刊》2021年第1期。。更准确地说,共情更应被视为价值尺度,因为情感带有即时性和冲动性等特点,共情的认知维度可弥补情感的短暂、易变等特性。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可从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视角观察对方的心理与现实处境,从而达成全面的认知理解。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受众代表不同的情感载体,对其情感的正确认知是确立修辞传播原则的依据。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21)陈寿:《三国志》,武汉:崇文书局,2009年,第137页。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是为建设共同体而消解多元性,而是试图在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具体层面上传播共同体理念,推动受众施行有助于人类共同发展的行为。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时代,主客观结合的视角已成为当前政治性修辞传播的刚性需求,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对共情的依赖程度愈加显著。中国作为率先提出并积极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家,更应承担起共情的发起者、践行者与传递者的责任,营造和谐的传播氛围,获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国的认同与支持。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路径:共情修辞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视域下的共情修辞内涵

共情修辞概念把共情作为修辞行为的起点,致力于实现修辞实践的人本化,其具体内涵是:“在修辞目的的驱动下,修辞者有意识地使自己进入对受众的共情状态,在能力范围之内达成与受众情感的时间同步和类别同向,并能够清楚判断受众和自身情感类型及来源,区分受众和自我表征,随后设定并施行修辞策略,这一修辞运作机制可被称为共情修辞”(25)李克、朱虹宇:《“共情修辞”的学理渊源与机制构建》,《当代修辞学》2021年第4期。。共情修辞以人本主义的发展及受众情感的多元趋向为背景,正逐渐形成学理化和学科化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全方位认同已经不再符合修辞者期待的当下,共情为我们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
共情修辞始终受到共情的牵引。修辞者的共情能力虽然各异,且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质的提升,但其共情意识足以触动修辞者的情感并改变其随后的修辞行为。在进行修辞选择之前,修辞者会率先了解受众的情感及产生原因,凭借自身的修辞能力和外部修辞资源,构造符合修辞目的的修辞表达方式。共情修辞与广义修辞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它对受众情感的关注和对修辞者共情行为的施为要求。共情修辞的出现并不是共情与修辞的因缘际会,而是衍生于深厚的学理渊源和社会关怀。从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角度来看,共情修辞挑战了国际传播中修辞者对情感的隐晦态度,将“人”及“人性”置于重要地位,其内涵与特征均彰显出明显的人本主义修辞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先进的关于人类发展的理念,根植于人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各个方面,影响并映射于民族、国家以及国际间的交流等团体行为。共情修辞的出现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对其理解与实践都离不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在修辞目的层面,共情修辞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目的;在受众层面,修辞者在实施修辞行为之前,根据受众情感进行认知建设和情感铺垫,沿袭了传统修辞实践中对受众的关注,并将关注点聚焦于极易引发修辞效果波动的情感层面,对有效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实践意义。传播的目的在于激起行动并生发改变。在国际话语传播中,中国以共情者的身份从情感和认知上向受众靠拢,在保持自身立场不被对方“同化”的前提下作出修辞选择,不论从人本主义的伦理道德还是从讲求利益的国际交往角度来看,都有助于激起受众的主动认同和行为呼应。
(二)共情修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适配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方式随着国际形势与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共情修辞与蕴含共同体理念的人类整体传播学的契合,与人类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的衔接,对外界误解的消除等,都说明该修辞模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具有适配性。长远来看,在符合基本伦理道德与人本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共情修辞将弱化国际传播的博弈性,为缓解国际交流中的冲突提供一条可行性思路。
1.共情修辞符合人类整体传播学的传播意旨。人类整体传播学认为,传播研究应该“回到‘人’的本质维度”(26)邵培仁、陈江柳:《人类整体传播学: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传播研究》,《现代传播》2019年第7期。,“充分挖掘人类多元文明体系当中被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激发能够产生全人类共鸣的朴素情感……诠释好人类文明多样性交融协调、和合共生的真谛”(27)邵培仁、陈江柳:《人类整体传播学: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传播研究》,《现代传播》2019年第7期。。不论是“共同价值”还是“激发全人类共鸣的朴素情感”,它们都强调了人性中固有的共情因素。只有在传播过程中达至理智、全面、深刻的共情,才能诠释新时代传播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也才能切实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中的人本主义温度。共情修辞将共情融于修辞行为,引导、激发修辞者内化并充分运用共情这一重要因素。共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只有在修辞传播中有机糅合,人类整体传播学的宏大学科视角才会落地生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所需的学理依据也才能真正得到夯实。
2.共情修辞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统一。形式与内容契合,能够避免“表里不一”的修辞传播窘境,也是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助力。从内容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类社会的互联互通、人类文明的共建共享”(28)肖玉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之维》,《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在生态、社会和文明等现实层面实现统一,需要以情感的趋同为前提。当各国对人类共同的未来怀有同样的情感寄托时,会逐步达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心理认同并诉诸实践。依此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讲求具体层面的和谐统一,同时注重基于情感的共情融通。从形式上看,共情修辞体现出明显的人本主义关怀。虽然目前的修辞伦理已逐渐将修辞的“善恶”之分消解,共情修辞却在修辞者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的伦理倾向和价值判断。共情修辞行为源于共情思维模式,自然沿袭了共情的人本主义属性以及对被共情者情感的先导式关注。当修辞者与受众位于某个情感交叉点,而且修辞者能够以此为原点并依据修辞目的拓展共情认知,将会形成修辞者与受众在具体方面的情感共同体;另外,修辞者还会加入带有理性色彩的认知共情,以此平衡主观倾向。可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过程中,共情修辞的传播方式迎合了传播内容对情感的重视,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契合。
3.共情修辞在伦理上有助于消除外界对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误解。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涵具有人文关怀特征,但是该特征并非“不言自明”,外界的误解依然存在,这种误解体现于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情感反应。例如戴博(Robert Daly)认为,“中国正试图通过渐进及和平方式,必要情况下使用强制手段,来成为‘亚洲仁慈的霸权国家’”(29)高望来:《美国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及中国应对之策》,《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8期。,其中“仁慈”与“霸权”的矛盾内涵暗示着对中国的怀疑与抵触情感,一旦情感基调确立,随后的言论、政策及行为等都会受其影响。共情修辞施行之前对受众情感的研判,影响甚至决定着具体的修辞选择。当我们能够精确了解受众是在何种情感类型的基础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误解,继而以改变情感为切入点,改变受众的认知与行为,将有助于消除误解,引导生成基于现实的合理的情感、认知和行为。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中的共情修辞实践路径

1.修辞目的的确立以共情为前提。在伯克看来,“人们的任何行为总是带有某种目的”(32)转引自邓志勇:《修辞理论与修辞哲学——关于修辞学泰斗肯尼思·伯克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而修辞目的又可分为普遍和特殊两个层面。“通过优化设计言语以更好、更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33)胡习之:《修辞的目的和修辞的核心原则》,《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是具有广泛适用性的修辞目的,所有修辞实践都是为了追求如何高效达成交际目的,而具体修辞实践涉及的则是依据修辞情境确立的特殊修辞目的。修辞活动受修辞者的观点或修辞情境驱动而产生依附点,在一个修辞事件闭环内,修辞目的并不随着修辞活动的发展而改变。可以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情修辞传播过程中,修辞目的为传播活动奠定基调,而共情首先体现在修辞目的的确立上。
通过共情修辞视角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已经将修辞目的聚焦:宏观层面上,对受众作共情性了解,并以自身修辞能力为上限,作出符合共情性了解的修辞行为;微观层面上,以共情修辞的修辞模式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受众正确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诉诸行动。共情修辞模式将引导修辞者确立更契合受众情感状态与需求的具体目标,为修辞事件把握方向。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面向全球其他国家的活动,但是宏观目标并不能成为引导受众行为的唯一指导,仍需依据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团体的特点及情感需求,将宏观目标切分为可行的具体目标,所以此前的共情了解和修辞规划尤为重要。另外,具有人本主义特色的共情修辞在对受众进行共情了解后会放弃最初设定的修辞目的,重新开始新一轮的修辞活动。以共情修辞视角重新审视具有不同情感需求的受众后,修辞者可在宏观目的不变的前提下更换具体执行目的。如对待美国和对待巴基斯坦的修辞目的并不相同,对美国进行修辞传播时我们致力于纠正他们对中国的不实看法,通过人格诉诸和逻辑诉诸激起受众的积极情感;在对巴基斯坦进行修辞传播时我们则致力于建立友好关系,以实质性成果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价值。
2.修辞话语内容的设计以共情为基点。除客观反映真实事件的描述性语言之外,布局谋篇和文体两个环节会将零散的话语内容串联成有可能产生修辞反响的文本,它们也是话语内容的重要部分。依据共情修辞的运行机制,共情外显于修辞话语而内化于修辞目的,即修辞者率先达成与受众的共情,继而生产出带有共情色彩的修辞话语。中国是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要执行者,也是共情修辞过程中的共情者。当代表国家的修辞者在共情的思维框架下向外界传播修辞话语时,受众所听所感所想都在一定程度上被修辞者融入修辞文本。此时我们认为,共情修辞行为将以修辞者的共情为起点,以受众的共情为终点,情感闭环的完成主要依靠共情修辞话语。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所作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详细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及发展蓝图。该演讲凝聚着大国气魄与担当,成为通过精准、适切话语进行传播的成功案例。演讲以近百年间全球面临的挑战为起点,展现当下人类整体情感状态并对此作出回应。习近平总书记说道:“这100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然而,这项任务至今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要顺应人民呼声,接过历史接力棒,继续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奋勇向前。”(34)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1-01/01/c_1126936802.htm, 访问日期:2021年4月10日。可以看出,前两句话是对“人类愿望”及“任务”的理性认知,也是对受众情感的客观推理,认知共情成为表述共情修辞话语的铺垫;第三句中的“我们要顺应人民呼声”则是对人民情感需求与现实需求的话语呼应,“接力棒”和“马拉松”的隐喻显示了和平与发展任务的不间断性、合作性及长远性、艰难性,也是修辞者担当与决心的修辞呈现,微观层面的共情修辞表述由此完成。
3.修辞话语呈现方式皆以共情为依托。话语呈现方式是修辞态度的载体,是话语内容的表现形式,常常以语境和分析目的的改变而改变。话语表达方式(35)喻国明:《传播语法的改变与话语方式的革命——在纪念〈新闻透视〉开播20周年论坛上的演讲》,《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话语表述方式(36)王丹、孙敬鑫:《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当代世界》2018年第6期。、话语表现方式(37)李畅、万婷:《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的视像化建构理路研究》,《新闻界》2019年第8期。、话语宣传方式(38)章剑锋:《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话语方式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9期。都属于话语呈现方式,而“方式”的范畴也从“严肃、单调……亲切、活泼的文风”(39)周翔:《“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建构——概念再造、语境重置与方式转换》,《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7期。的文体学概念延伸到“陈情说理相结合”(40)王丹、孙敬鑫:《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当代世界》2018年第6期。的叙事学概念,甚至包括“视觉手段”等“形象化的表现方式”(41)李畅、万婷:《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的视像化建构理路研究》,《新闻界》2019年第8期。。本研究论及的话语呈现方式主要指语气、语调、手势、站姿、文本排列及多模态等一切有助于凸显话语内容、收到话语效果的方式,其作用在于辅助修辞者通过修辞话语的呈现达成修辞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过程中的共情修辞主体部分为话语内容的产生,但话语呈现方式则可直接影响传播效果,是修辞传播过程的最后一关。
共情修辞的话语呈现方式与传统修辞传播的话语呈现方式并无二致,即呈现方式本身并不会因为共情因素的加入而改变,但共情修辞的思维模式会影响修辞者对呈现方式的选择。在意识到受众的情感偏于兴奋或激动时,修辞者可选择含有相同或相似情感的呈现方式,通过情感同向与受众成为“情绪共同体”。相反,当受众的情感偏向于不同或反感时,修辞者则不宜以同类情感呈现修辞内容,可通过认知共情的思维模式,明确受众情感的由来,并在掌握必要信息后决定是否采用带有情感色彩的呈现方式。
话语呈现方式对演讲类修辞文本的影响较为显著,这也正是演讲被当作修辞分析重点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2019年10月22日,CGTN通过YouTube发布了一段题为“China proposes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的视频,包括了“一带一路”的背景、提出、践行、发展、挑战、机遇及发展前景等内容。视频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被提出的部分皆使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声录音,这种呈现方式极大地提升了视频的权威性及震撼性;而以“国家形象和声望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代言人”(42)周亭:《作为国家形象符号的领导人形象传播——以白宫网对奥巴马的形象塑造为例》,《现代传播》2013年第6期。的国家领导人为触发点,有助于推动其他国家建立对中国的信任与认同。从共情角度来看,运用国家领导人原声这一呈现方式不仅与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对话方式相契合,也拉近了与国内受众的距离,有助于激发受众的爱国情感。另外,该视频在快慢节奏的把握、政治场景与其他场景的切换等方面也显示出视频制作者对国内及国外受众情感和认知的考量,体现出修辞传播的宏旨,在话语呈现方式上做出了积极努力。
在以对话为主要修辞形式的情境中,话语方式更能明显表现出修辞者对受众的态度及隐藏于话语方式背后的多种影响因素。2021年3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安克雷奇举行了一场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该对话不仅是一次捍卫国家利益的沟通,也是一场激烈异常的国际级别的政治修辞事件。两国代表都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对话前提,但中方的态度强于美方,这在杨洁篪的对话姿态与语气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阐述中国发展、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等问题时,杨洁篪语气坚定平缓,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有助于夯实其爱国情感和民族自信心,而对修辞受众——美国来说,则是对其高傲甚至敌对情感的打压;在指责美国有关民主治理、国际安全等方面的不足时,杨洁篪表现得极为愤慨,他通过特殊的语气、音调等话语呈现方式,表达了中国对美国扰乱社会秩序行为的不满,对受众产生了情感震慑。杨洁篪的话语呈现方式虽然并未与受众的情感同步或同向,但中方对受众情感的了解及产生原因已然掌握,即通过认知共情对受众情感有了前期观察与客观预设,因此修辞行为依然属于共情修辞范畴。总之,共情修辞并不是鼓励修辞者一味迎合受众的修辞喜好、使自身情感与受众完全相同,而是在深刻认识受众情感的基础上,依据自身修辞目的选择适当的呈现方式。
四、结语
在国际社会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属于博弈性地获取阐释该理念的话语权。“权力的争夺不仅仅是在经济和利益的物质层面,不局限于取得物质利益的支配权,在更深的层面是追求精神领域的支配权。”(43)刘淼、金林南:《权力实践与政治象征》,《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作为传播理念与实践模式,“修辞为体,传播为用”的修辞传播模式是获得受众观念认同和行动呼应的助推力;以受众情感状态为切入点的共情修辞,则是符合时代和平发展潮流的修辞传播路径。共情修辞强调依据修辞情境、综合感性与理性认识来设计修辞话语,以严肃的国际交往场合为情感坚守阵地,在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同时发扬人本主义精神,由内而外地表露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所秉持的全球意识。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过程中,我们或可使用共情修辞的思维框架和实践模式,推动其他国家与中国在和平、友好的修辞情境中达成沟通与合作,以情感渴望和现实需求为引擎,激发实际行动,共同构建情感和命运共同体。本文从理论层面阐述了这种实践的可行性,但仍需对大量的、不同修辞情境中的实例加以详细验证,这将成为我们今后的研究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