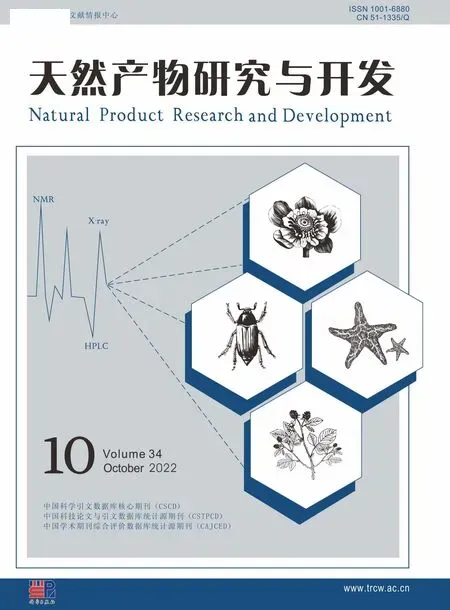基于肠道菌群探讨多糖干预2型糖尿病的研究进展
唐志雁,袁平川,3,柳春燕,3,王国栋,3*
1皖南医学院药学院药物研发中心;2安徽省多糖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徽省皖南地区植物药活性物质筛选与再评价工程实验室;3活性生物大分子研究安徽省重点实验室,芜湖 241002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为糖尿病中较常见的一种类型,以高血糖为主要特征,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如未及时治疗控制,往往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威胁着人类身体健康,研究发现其发病与氧化应激、胰岛素抵抗、炎症反应等因素密切相关,但具体机制尚未明确[1,2]。随着T2DM患病率持续上升,人们对其研究也不断地深入,普遍认为肠道菌群失调是T2DM的重要危险因素[3]。肠道菌群失调可引起全身慢性低水平炎症,进而导致肥胖和胰岛素抵抗,且T2DM患者肠道菌群结构和分布与正常人明显不同,这是由于肠道微生态中各种微生物丰度的变化所致[4,5]。
多糖是由十个及以上单糖通过糖苷键结合成的高分子化合物,其单糖组成或相同或不同,分子结构复杂且庞大,并拥有着丰富的自然界资源,安全性高,毒副作用小,具有诸多药理活性,例如降血糖、抗氧化、抗炎、抗肿瘤以及免疫调节等[6-9]。其中,多糖在降血糖方面表现出较好的效果,如黄连多糖能明显改善T2DM大鼠的空腹血糖水平且具有良好的降脂效果[10]。尽管不同多糖之间降血糖的机制可能存在差异,或同时存在多种机制,但主要是在修复胰岛细胞、增加胰岛素含量、增加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关键酶活性、增加肝糖原合成以及调节肠道菌群等方面发挥作用[8]。多糖与肠道菌群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已成为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多糖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维持肠道微生物之间的结构稳定,预防肠道功能异常,从而调节糖代谢紊乱[11]。而且肠道菌群也可以将多糖代谢利用,增加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s)含量、改善肠道酸性环境、促进拟杆菌等有益菌生长、为肠道和肝脏提供能量、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增加胰岛素敏感性以及改善胰岛素抵抗等。本文查阅近几年相关的文献并进行整理,对肠道菌群于T2DM的影响、多糖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对T2DM发生发展的影响进行综述,为T2DM与肠道菌群之间机制研究以及开发治疗T2DM的活性多糖提供思路,并为T2DM的治疗提供更多安全有效的选择。
1 肠道菌群与2型糖尿病
人类肠道共生着大量微生物群,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千差万别,种类可达1000多种,其数量和多样性可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可以调节宿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12,13]。人们普遍认为肠道微生物区系在维持宿主健康和诱发多种疾病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例如,肠道微生物区系可以帮助宿主获取能量。相比之下,肠道微生物区系失调可能与许多疾病有关,包括炎症性肠道疾病、结直肠癌,以及肠外疾病,比如糖尿病。饮食被广泛认为是影响人体肠道微生物区系组成和功能的主要因素。例如,富含非淀粉、不可消化的多糖和膳食纤维的饮食主要是通过降低Firmicutes(厚壁菌门)与Bacteroidetes(拟杆菌门)之间的比例来影响肠道微生物区系[14]。
肠道菌群的变化与T2DM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表明,移植到无菌小鼠体内的T2DM小鼠的粪便细菌引起了糖尿病样改变[15],相反,将正常小鼠的粪便细菌移植到db/db小鼠体内可以改善新陈代谢[16]。T2DM患者肠道菌群结构和分布与正常人明显不同,这是由于肠道微生态中各种微生物丰度的变化所致。对动物模型的比较分析表明,糖尿病小鼠的Lactobacillus(乳酸杆菌)比例高于正常小鼠[17]。此外,正常人肠道微生态中的Bifidobacterias(双歧杆菌)水平较高[18],相比之下,T2DM患者肠道菌群中的丁酸产生菌、Lactobacillus和AkkermansiaMuciniphila(嗜粘蛋白-阿克曼氏菌)的组成有较大差异[19]。
肠道菌群影响T2DM的机制可能包括影响肠道激素、食欲、能量消耗以及炎症反应等,作用媒介主要包括SCFAs、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胆汁酸(bile acids,BAs)以及支链氨基酸(branched-chain amino acids,BCAAs)。肠道微生物可通过发酵食物残渣中的碳水化合物产生SCFAs来改善结肠中的酸性环境,抑制有害细菌的生长,从而预防肠功能异常。且SCFAs已被证明能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s,HDACs)在糖尿病中发挥抗炎作用[20]。同时,肠道微生物群能够产生许多可诱导外周组织炎症的物质,如肽聚糖和LPS,这些物质在从肠腔进入血液时会引起胰岛素抵抗和T2DM[21-23]。在人体肠道中,Bacillus-pumilus(短小芽孢杆菌)和普通类杆菌能够促进BCAAs的生物合成,但它们缺乏运输系统,不能将产生的BCAAs转运到细菌细胞中,从而导致血清BCAAs水平增加和胰岛素抵抗[24]。其他的肠道菌群作用媒介还包括、吲哚、神经递质等。
1.1 肠道菌群影响短链脂肪酸(SCFAs)含量
SCFAs可通过一系列与食欲调节、能量消耗、葡萄糖稳态和免疫调节相关的组织特异性机制直接调节宿主代谢健康,在为结肠上皮提供能量、抑制致病性肠道细菌以及调节糖脂质代谢和免疫系统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微生物肠源性SCFAs含量的增加被认为是有益于健康的[25,26]。SCFAs主要包括乙酸、丙酸和丁酸,作为肠道菌群的发酵产物,现有研究表明,SCFAs可以调节血糖和调节肠道功能[27,28]。其中,丁酸盐是结肠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已被发现可以增加线粒体活性,预防代谢性内毒素血症,且可抑制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6(IL-6)等促炎因子的分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具有抗炎潜力,增强肠道屏障功能[29]。另外,乙酸盐可用作胆固醇或脂肪酸前体,丙酸是糖异生的底物[30]。SCFAs可以通过上调肌肉和肝脏中的蛋白激酶信号来改善胰岛素敏性。SCFAs还可通过与G蛋白偶联受体结合,促进胃肠激肽YY(peptide-YY,PYY)、胰高血糖素-1分泌(glucagon-like peptide-1,GLP-1),从而促进胰岛素分泌[31]。而肠道菌群的紊乱可能会影响体内SCFAs的合成以及代谢,使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以及胰岛素分泌紊乱,从而导致T2DM发生。
1.2 肠道菌群影响脂多糖(LPS)分泌
LPS作为革兰氏阴性细菌细胞壁中的一种主要成分,是炎症中的主要致病因子[32]。TLR4和NF-κB信号通路是LPS介导的信号传导通路中重要的下游信号通路,TLR4受体可识别并结合LPS,进而激活NF-κB信号通路,从而诱导TNF-α、IL-1、IL-6等促炎因子的释放,导致炎症的发生和加重胰岛素抵抗[33]。表明LPS以及炎症因子在T2DM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而肠道菌群的紊乱会导致大量的LPS以及其他炎症因子的释放,引发慢性持续性炎症与胰岛素抵抗,进而导致T2DM的发生发展。
1.3 肠道菌群影响支链氨基酸(BCAAs)的合成
BCAAs是指α碳上含有支链的氨基酸,即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研究发现,体内BCAAs水平会影响血液中胰岛素的敏感性[34]。Horiuchi等[35]发现减少小鼠食物中的蛋白含量时会使其胰岛素分泌降低,而在饮食中补充BCAAs(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后则可改善小鼠胰岛素分泌并使其达到正常水平。此外,过高水平的BCAAs可能会引起胰岛素抵抗,高水平的BCAAs尤其是亮氨酸可作为上游的营养信号持续激活mTOR通路,抑制转录因子Kruppel样因子15(Kruppel-like factor 15,KLF15)的表达,而KLF15是葡萄糖、脂质、胆汁酸以及氨基酸代谢的重要调节因子,可使胰岛素敏感性增强,糖原合成增多[36,37]。体内BCAAs的合成与肠道菌群密切相关,且体内BCAAs及其代谢物的水平也影响着肠道菌群的变化[38]。因此,肠道菌群可通过影响BCAAs的水平代谢来影响胰岛素敏感性等,对于T2DM的发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3 肠道菌群影响胆汁酸(BAs)信号通路
BAs是在肝细胞中产生的胆固醇分解代谢产物,合成后,BAs与一种氨基酸结合并分泌到胆汁中,被回肠末端的肠细胞主动重吸收,并通过门静脉到达肝细胞,在那里被吸收和循环。然而,一部分BAs逃逸回肠吸收,被肠道微生物修饰,随后通过在结肠中的被动扩散吸收,因此,在肝脏、胆汁和肠道中都存在高水平的BAs[39]。BAs主要激活法尼醇X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FXR),次级胆汁酸主要激活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G protein-coupled bile acid receptor 1,TGR5),在调节全身糖脂代谢以及改善胰岛素抵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0]。同时维持肠道内屏障结构的通透性和完整性,减少促炎因子的释放。BAs的产生和代谢需要肠道菌群的参与,且在肠道菌群的作用下,BAs信号增强,肠道优势菌群的变化会减弱FRX和TGR5的激活,导致糖脂代谢紊乱,可能会导致T2DM的发生发展[31]
2 多糖调节肠道菌群对T2DM的影响
2.1 多糖调节肠道菌群
多糖是一种丰富的天然产物,其来源包括药用植物、谷物、水果、蔬菜、食用菌和药用食品,具有抗糖尿病的潜力[41]。按不同来源可分为动物多糖、植物多糖以及微生物多糖。尽管多糖难以被胃肠道酶吸收和加工,但其作为每天摄入碳水化合物的重要来源,被认为是能影响肠道微生物区系种群和代谢的益生元。未消化的多糖进入大肠,在那里它们被肠道微生物进一步降解和发酵[42,43]。多糖可以影响肠道微生物区系的结构和功能,并通过重塑肠道微生态或肠道内稳态对人体健康起到调节作用[44]。例如,Ding等[45]发现枸杞多糖可以促进SCFAs的产生,调节肠道微生物区系的组成,增加Bacteroidtes、Lactobacillus和Clostridium(梭状杆菌)的相对丰度,这些与免疫调节特性呈正相关。另外,有研究发现壳聚糖可以通过降低Firmicutes与Bacteroidetes之间的比例来降低结肠的炎症水平,从而改善宿主的肠道健康[46]。鱿鱼墨汁多糖能降低化疗损伤小鼠结肠中的促炎性细菌的比例,如Ruminococcus(瘤胃球菌)、Bilophila(嗜胆菌属)、Oscillospira(颤螺菌属)、Dorea(加德纳菌)和Mucispirillum(黏液螺旋菌属)等,特别是Mucispirillum,它能在结肠黏膜破坏初期快速成长,导致炎性疾病的发生[47]。
2.2 肠道菌群代谢利用多糖的机制
肠道微生物区系包含许多编码各种碳水化合物活性酶的基因,而这些酶在人类基因组中几乎不存在[48]。因此,多糖在体内的消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肠道内的微生物,大部分未被消化的多糖通过胃肠道到达结肠,由肠道菌群通过碳水化合物活性酶类(CAZymes)以及相关的糖结合蛋白将多糖降解利用[49]。例如,Ai等[50]发现鲍鱼多糖不会在消化液中被降解,可以安全到达远端肠道,由Bifidobacterias和Bacteroidtes发酵利用。降解多糖产生的代谢产物如寡糖、SCFAs以及一些其他的次级代谢产物,一方面可以为宿主以及肠道菌群提供能量来源,另一方面还可以影响肠道环境,如调节肠道pH、促进有益菌生长、抑制有害菌等[42]。
成人肠道微生物区系主要由Firmicutes和Bacteroidetes两大类杆菌组成[51],而肠道中复杂碳水化合物的降解利用主要是由Bacteroidetes来完成的,其拥有编码了糖结合蛋白(SGBPs)、CAZymes和转运蛋白系统的多糖利用位点(Puls),能够将多糖降解为单糖以及一些其他的小分子糖类化合物。在Puls中,SGBPs将多糖募集到细胞外膜,通过外膜上的特异性内切糖苷水解酶或多糖裂解酶将多糖分解生成低聚糖,然后经由TonB依赖转运蛋白或SGBP复合物穿过外膜。一旦到达周质,独特的寡糖特征就可作为目标聚糖的代理,并与跨内膜传感器或调节器结合从而诱导Puls表达。最后,由外源CAZymes(其数量反映了同源多糖连接的复杂性)作用产生单糖/双糖,通过内膜运输进入代谢途径[52]。
2.3 多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影响2型糖尿病
2.3.1 动物多糖调节肠道菌群影响T2DM
动物多糖作为多糖大家庭的一员,来源分布广泛,几乎存在于所有动物的器官中,包括糖原、甲壳素、肝素、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以及硫酸角质素等,具有降血糖、调节血脂、抗肿瘤以及抗炎等作用[53]。
有研究发现动物多糖可通过影响肠道菌群的结构组成以及参与SCFAs代谢等途径影响机体的代谢,Ma等[54]研究了牡蛎多糖的消化以及益生特性,发现其可以增加结肠SCFAs的合成,调节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和多样性,特别是增加有益细菌的丰度,如Bacteroides、Prevotella(普雷沃氏菌)和Faecalibacterium(普拉梭菌)。继而改善胰岛素抵抗、增加胰岛素敏感性。
Zhao等[55]发现海参多糖能明显改善T2DM大鼠糖耐量异常,调节血脂和激素水平,且可通过降低T2DM大鼠肠道内Furmicutes、Proteobacteria(变形菌门)、Spirochaetes(螺旋体门)和Actinobacteria(放线菌门)等条件致病菌,增加Bacteroidetes、Cyanobacteria(蓝细菌)以及TM7等有益菌的比例,有效地优化T2DM大鼠肠道微生物区系的组成,增加SCFAs的产生,从而改善T2DM大鼠的症状。
2.3.2 植物多糖调节肠道菌群影响T2DM
植物多糖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和保健功效,通常被认为是药食两用植物中的天然活性大分子[56]。近年来,越来越多具有降血糖活性的植物多糖从植物中被分离出来,经过研究,很多植物多糖都能通过影响体内肠道菌群来参与T2DM的发生发展。
Li等[57]发现羊栖菜(Sargassumfusiforme)多糖联合小剂量阿卡波糖,对大鼠空腹血糖、TC和TG等有着良好的控制效果,可明显减轻大鼠T2DM症状以及改善胰岛素抵抗,且调节了肠道菌群的组成,显著恢复了其肠道菌群的有益成分,包括Bacteroides、Lachnospira(毛螺菌属)、Bifidobacterium在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并使Escherichia(大肠杆菌)、Shigella(志贺杆菌)等致病菌减少,其机制可能是增加SCFAs的生成来发挥作用。Jia等[58]研究发现羊栖菜(Hizikiafusifarme)多糖单独使用亦可恢复T2DM大鼠肠道菌群的有益组成,相关分析表明糖尿病的改善与其干预肠道菌群的改变密切相关。
青钱柳多糖能治疗T2DM,但其不能被人体直接消化吸收。Yao等[59]研究发现通过青钱柳多糖治疗后的T2DM大鼠血糖水平降低,糖耐量和血脂指标改善,且肠道菌群有明显的变化,包括Ruminococcus_bromii、Anaerotruncus_colihominis、Clostridium_methylpentosum和Intestinimonas_butyriciproducens等11种菌属均增加,而这些菌属均为体内SCFAs的产生菌,另外,青钱柳多糖可显著刺激SCFAs受体GPR41、GPR43和GPR109a,并伴有GLP-1和PYY表达上调,这可能是青钱柳多糖治疗T2DM的一种机制。
Wu等[60]建立T2DM小鼠模型,研究了南瓜多糖降糖降脂作用以及与肠道微生物调节相关的潜在机制,结果表明,南瓜多糖治疗后,T2DM小鼠的空腹血糖值、胰岛素抵抗和血脂水平降低,南瓜多糖增加了T2DM小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增加了可产生包括丁酸在内的SCFAs产生菌的丰度,增加体内SCFAs的含量,减少了包括Clostridium、Thermoanaerobe、Symbioticbacteria(共生菌)、Deinococcus(异常球菌)、Vibriohaematococcus、Proteusgamma、Corio等在内的有害菌,明显改善了小鼠的T2DM症状。
丹参是一种常用的中药,对于糖尿病合并慢性心脏病患者有着良好的疗效,从丹参中提取出的丹参多糖能改善T2DM大鼠的胰岛素抵抗[61]。Wang等[62]发现丹参多糖能改善高脂喂养的小鼠肠道Cyanobacteria的丰度,而Cyanobacteria的丰度与体内LPS的分泌和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此外,补充丹参多糖还能提高小鼠体内乙酸和丁酸等SCFAs的浓度。
菊粉是植物中一种储备性多糖,为一种功能性成分,已被用于动物和人体研究的各种功效研究中,它被回肠末端的肠道微生物群修饰,以发挥其益生元作用,促进良好的消化健康,影响脂质代谢,改善免疫系统和炎症性疾病,并在保持血糖和胰岛素为最佳水平方面起到有益的作用[63,64]。Li等[65]对关于菊粉对于不同时期T2DM小鼠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膳食菊粉可通过抑制炎症和调节肠道微生物区系,缓解T2DM的不同阶段,结果显示,经过菊粉干预的T2DM小鼠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脂等指标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作用,IL-6和TNF-α等炎症因子减少,肠道微生物区系测序分析门水平和属水平的结果显示,菊粉处理的T2DM小鼠Cyanobacteria和Bacteroides数量增加,Mucispirillum和Ruminiclostridium-6数量下降,而呈现下降趋势的这两种菌均具有促炎作用,提示菊粉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逆转促炎作用并减轻小鼠的T2DM。
2.3.3 微生物多糖调节肠道菌群影响T2DM
微生物多糖主要来源于真菌、细菌和藻类等,包括胞外多糖、胞壁多糖以及胞内多糖。其因无毒安全、生产周期短、易于分离纯化等特点研究较多,逐渐成为植物和动物等多糖以外的另一个研究热点。
灵芝属于担子菌纲多孔菌科真菌,包括多糖、三萜、甾醇等化学成分[66]。灵芝多糖作为微生物多糖,可调节肠道菌群,Chen等[67]发现灵芝多糖能改善T2DM大鼠体内Blautia(布鲁菌),Dehalobacterium(嗜盐杆菌)、Parabacteroides和Bacteroides含量较低的情况,并能降低潜在致病菌Aerococcus(气球菌)、Ruminococcus、Corynebactrium(棒状杆菌)以及Proteus的相对丰度,使T2DM大鼠肠道微生物区系恢复到正常水平,恢复肠道细菌群落紊乱的氨基酸代谢、碳水化合物代谢、炎性物质代谢和核酸代谢,且可与宿主的代谢产物相互作用来实现其抗糖尿病作用。
灰树花常被用作食用和药用真菌,以β-葡聚糖为主的灰树花多糖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灰树花多糖分解产生的鼠李糖、岩藻糖、甘露糖和半乳糖等可被肠道菌群利用来产生SCFAs,改变肠道菌群组成[68,69]。Guo等[70]研究了灰树花多糖对于T2DM小鼠的降糖降脂效果以及肠道菌群的影响,结果显示,灰树花多糖能明显改善T2DM小鼠的空腹血糖值以及糖耐量,显示出了较好的降糖效果,相比于糖尿病组小鼠,多糖给药组小鼠的Roseburia(罗氏菌属)、Lachnoclostridium(酪酸杆菌)、Lachnospiraceae-NK4AB6-group和Alistipes(另枝菌属)数量增加且伴随着SCFAs含量的增加,相反,Enterococcus(肠球菌)、Aerococcus、Streptococcus(链球菌)和Staphylococcus(葡萄球菌)等菌群数量降低。
桑黄是一种广受欢迎的药用蘑菇,含有多糖、三萜以及呋喃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具有降血糖、抗炎和抗肿瘤等众多药理活性[71]。Liu等[72]研究了桑黄多糖和肠道微生物区系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于T2DM的影响,发现桑黄多糖可通过增加SCFAs产生菌的数量来增加SCFAs的水平以维持肠道屏障功能,降低血液中脂多糖含量,从而有助于减轻全身炎症反应,逆转胰岛素抵抗,这些SCFAs产生菌包括Lachnospiraceae-NK4A136、Lachnospiraceae-UCG-006、Roseburia、Prevotella9、Blautia、Ruminiclostridium-9、Eubacterium_xylanophilum、Anaerotruncus(厌氧球菌)以及Oscillibacter(颤螺菌属),同时也降低了Escherichia等可促进LPS分泌的菌属。
3 小结与展望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严重影响着人类生命健康,发病机制复杂,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研究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肠道菌群影响着体内SCFAs生成、胆汁酸和支链氨基酸代谢以及内毒素的分泌,在T2DM复杂机制研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发展能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治疗T2DM的天然药物是当前趋势。多糖安全且毒副作用小,具有良好的益生元效应和血糖调控作用[8,41]。多糖影响体内肠道菌群的结构,其所改变的菌群类型并不固定,但大多都是通过增加有益菌的含量,如Bacteroides、丁酸产生菌;减少Shigella、Escherichia等有害菌;并增加SCFAs的含量,影响包括LPS在内等物质的代谢,从而改善T2DM引起的肠道内生态紊乱,这对于缓解并治疗T2DM有着重要的意义。
尽管多糖在调控血糖和维持肠道菌群方面表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但目前多糖的研究与开发仍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多糖结构复杂不均一,关于多糖化学结构的表征颇具挑战性,难以明确构效关系,体内代谢研究也较为匮乏,不同来源的多糖分离难度不一且质量难以控制。并且,肠道菌群种类繁多,不同来源多糖对肠道菌群结构组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此外,目前多糖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的研究多数仅限于动物实验层面。因此,基于肠道菌群研究多糖对T2DM的作用,首先需要明确多糖的结构及质量控制标准,在此基础上,明确多糖的构效关系,深入探讨多糖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扩大多糖的临床应用范围,可为开发维持肠道稳态、防治T2DM的活性多糖提供新思路以及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