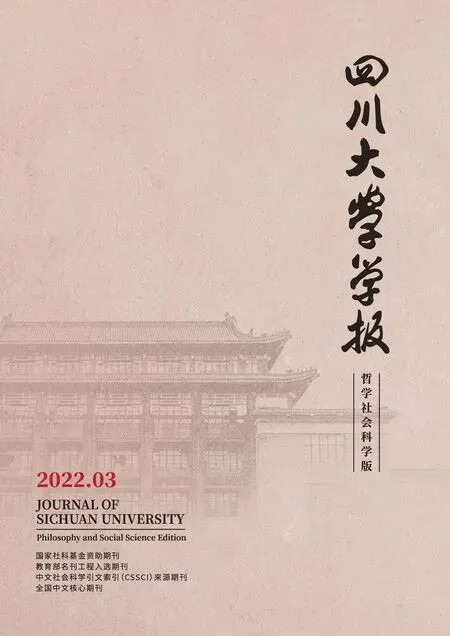陆象山的解经法
何 俊
近年来,随着宋明理学研究的深入,被标签化为“六经注我”的陆象山,其“我注六经”的经学研究与经学思想日渐受到学者关注。(1)象山缺少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这样重要的解经著作,故专题研究他的经学并不多,近年来受经学研究的重视而多有关注,包括硕博士生的论文选题。最新的研究可参见向世陵:《陆九渊〈春秋〉“讲义”的经学思辨》,《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1期;许家星:《吾之深信者〈书〉——从〈尚书〉之论管窥象山学的经学底色》,《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5期;以及收入欧阳祯人主编:《心学史上的一座丰碑——陆象山诞辰880周年纪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中的相关论文,其中与本文关系重要者是《陆象山心学与周易研究》《陆象山的认识论研究》二栏目的诸篇相关论文。我已就象山的“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关系,以及象山“我注六经”的原则与标准进行了分析,(2)参见何俊:《陆象山的“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5期。本文试图对象山的解经方法做进一步的讨论。
考虑到解经的具体方法常常体现在具体的解经中,因此本文对象山解经法的说明也将结合他的经解来进行。由于象山的解经著述主要针对《易》与《春秋》,而《易》学与《春秋》学是象山经学的重要成果,涉及思想内容,为了不枝蔓开去,故本文主要结合象山对其他经典的解释,尤以《论语》《孟子》为主。当然,这些经典的解释同样反映了象山的思想,尤其是对《孟子》的诠释几乎融入到象山的全部思想之中,而本文举例仅聚焦于方法的说明,其中的思想则点到为止。
一、先立乎其大者
通常,方法与结果总是结合为一体的。只是,并非所有人都对自己选择的方法与路径有高度自觉,或者自始至终绝无疑虑与修正,相反,往往是确信与质疑共生共长。但是,对于象山而言,方法与路径不仅是高度自觉的,而且对于自己的创新是充满自信,从无疑虑与修正的,因此象山的方法与路径其实已构成他思想的重要部分;至于他的方法与路径所带来的结果,象山也都有明确设定,并且从不动摇。具体到经学,象山坚信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是准确无疑的,他的“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只是“自明而后明人”“先觉觉后觉”的不同而已。在这点上,他甚至认为《论语》也是存有问题的,即所谓“《论语》中多有无头柄的说话”。(3)《陆九渊集》卷三十四,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5页。他对《论语》中所录有子的话语基本否定,便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还讲:
观《春秋》《易》《诗》《书》经圣人手,则知编《论语》者亦有病。(4)《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434页。
《论语》虽然不是直接的注经著述,却是孔子与弟子们围绕“六经”展开的对话,因此《论语》可以被视为注经的著述,这点至少在宋儒那里是毫无疑义的。“四书”为“六经”之阶梯,就是佐证。但在象山看来,“编《论语》者亦有病”,后世的注经著述自然更在其次。
比较而言,象山对《孝经》的评价似乎更高些。象山曰:
《孝经》十八章,孔子于践履实地上说出,非虚言也。(5)《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415页。朱熹对《孝经》的看法大不同,他在《孝经刊误》中指出:“窃尝考之,传文固多附会,而经文亦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至或以为孔子之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这里的“或以为”未必是专指象山,但可窥知象山在对待经典的方式上,与朱熹有很大的不同。《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六,《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05页。
联系到象山对《论语》所记颜回言行的高度认同,大致也可确认,以践履为指向的实学正是象山发明本心的基本维度,(6)参见何俊:《本心与实学——兼论象山对心学谱系的疏证》,《哲学研究》2022年第2期。而“六经”的注释,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都是次要的,甚至是舍本求末的。
当然,象山完全清楚,“六经”既成,注经便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性存在,必须面对。象山曰:
书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经既作,传注日繁,其势然也。苟得其实,本末始终,较然甚明。知所先后,则是非邪正知所择矣。虽多且繁,非以为病,只以为益。不得其实而蔽于其末,则非以为益,只以为病。(7)《陆九渊集》卷二十,第245页。
因此,关键在于“得其实”“知先后”。象山之学以本心确立为本;本心既立,则不废传注,传注“虽多且繁,非以为病,只以为益”。
然而,要做到这点很难。这个难,来自两个层面。表层上,科举对士人的负面影响已成为严重的弊病,即象山所谓“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驯致其弊,于今已剧”。(8)《陆九渊集》卷十九,第237页。深层上,人们对科举带来的弊病有所警惕与反省,追慕“前辈议论”,激发起“为学之志”,却又陷溺于“乡学”的忽悠之中。两者相较,后者的危害更具隐蔽性。象山曰:
今时士人读书,其志在于学场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间好事者,因书册见前辈议论,起为学之志者,亦岂能专纯?不专心致志,则所谓乡学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
面对这样的现状,象山不愿有丝毫妥协,故标示“先立乎其大者”。象山曰:
私意是举世所溺,平生所习岂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学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惧,深思痛省,决去世俗之习,如弃秽恶,如避寇仇,则此心之灵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习,如见晛之雪,虽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谓之知至,乃谓之先立乎其大者。(9)《陆九渊集》卷十五,第196页。
由于用猛药治重症,致使象山着意于与时流反向而行,如他所讲,“今之论学者只务添人底,自家只是减他底,此所以不同”。(10)《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401页。因此,象山的解经法遂不为人所关注。
二、大纲提掇来,细细理会去
象山解经首重把握主旨。这一方法既适用于整部经典也适用于一段经文的解读。象山曰:
三百篇之诗《周南》为首,《周南》之诗《关雎》为首。《关雎》之诗好善而已。(11)《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407页。
这是对整部《诗》的主旨把握。象山从最显见的结构入手,落脚却是主旨。《诗》以《关雎》为首,而《关雎》的诗义在“好善”,这便意味着读《诗》都宜在这一主旨的引导下体会。
再看象山对一段经文主旨的把握:
“所谓诚其意者,无自欺也”一段,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故反复言之。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恶,非出于勉强也。自欺是欺其心,慎独即不自欺。诚者自成,而道自道也,自欺不可谓无人知。十目所视,士手所指,其严若此。(12)《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418页。
“诚意”一段是否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以及三百篇《诗》的主旨是否就是“好善”,这无疑是可以争论的,但象山以此来主导自己对经典的注释,却是他在意的方法。在象山看来,把握主旨,乃是解经的根本,如果忽视根本,解经再精细,都不外是舍本逐末。
象山曰:
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树木观之,则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概使其本常重,不为末所累。然今世论学者却不悦此。(13)《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407页。
这虽是讲“教人”,其实也适用于解经,因为解经原本就是自明而明人的教人工作。
把握主旨,“使其本常重,不为末所累”,当然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所谓“《尚书》一部,只是说德,而知德者实难”。(14)《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431页。从技术的层面讲,把握主旨需要注意正反两方面的问题。正面的问题是要准确把握文本中的一些有思想意涵而后人不易理解的关键用语。象山举例曰: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首尾文义。中间“所恶于智者”至“智亦大矣”,文义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据某所见,当以《庄子》“去智与故”解之。观《庄子》中有此“故”字,则知古人言语文字必常有此字。(15)《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415页。《庄子·外篇·刻意》原文系“去知与故”,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注:“《管子·心术篇》:‘去智与故。’此用其语。”
孟子以为天下言性,“故而已矣”,这一对“故”字的准确理解,涉及对孟子整段文义的把握,象山引《庄子》“去智与故”,便是对此关键文字作出了合理性的思想诠释。
反面的问题主要是对经文的阐释,应克制炫耀博学的欲望与诊治好论的毛病。象山曰:
《孟子》揠苗一段,大概治助长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论辞语之病,然此等不讲明,终是为心之累。(16)《陆九渊集》卷五,第66页。
《孟子·公孙丑上》此段,以一则寓言来反向说明孟子养气之道的一个关键点——“勿助长”。什么是“勿助长”?为什么必须“勿助长”?如何“治助长之病”?这些既是颇费思量的理论问题,也是行之不易的践履问题。孟子善喻,他以一则揠苗助长的寓言非常形象地将上述问题讲清楚了。这则寓言只有40余字,可谓精练又精彩。但在象山看来,如真知“治助长之病”,“亦不必引用耘苗”,否则反而染上“好论辞语之病”。这当然不全是针对孟子,更是针对宋人的经解讲学。然而,何以要如此干净简洁,以至于如此妙喻也要归入“好论辞语之病”呢?象山接着讲:
一处不稳当,他时引起无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议论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刚毅木讷近仁,而曾子之鲁乃能传夫子之道。
可知症结不在妙喻本身,而在因为妙喻而容易转入好论辞语,从而忘了“勿助长”的主旨。这种毛病尤其容易发生在“英爽、能作文、好议论者”身上,孟子自然就是这样的英才。孟子尚不能完全避免“好议论”之讥,更何况不能望其项背的寻常书生。故象山一则就经验层面宣称,“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少”;再则就经文本身阐扬,“所以刚毅木讷近仁,而曾子之鲁乃能传夫子之道”。
象山当然不反对辨明主旨,他把对主旨的辨明作为“知”看待,而“知”又是前置性的前提。所以象山在此信的最后指出:
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费力驱除。真知之,却只说得“勿忘”两字。所以要讲论者,乃是辨明其未知处耳。
毫无疑问,象山所谓“真知”,便是与本心的契合;而本心契合,自然也就明理,通体皆是道义。如此,“病自去矣,亦不待费力驱除”。
由此亦可知,解经的把握主旨固然属于“知”的范畴,其实在象山那里是涵摄“行”的。只是后来王阳明昌明的“知行合一”,象山并未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专门提出,于是象山的这一思想有所遮蔽罢了。指出这一点,一方面自然表明阳明思想在此问题上的更进一层,或更具理论的自觉,另一方面也须看到象山思想中内含知行合一的观念。而且,在象山这里,这也许根本不属于需要专门加以疏证的问题,因为在象山的论述中,无处不内含这一精神。尤须指出的是,象山为了强调知对于行的涵摄,在经文有所冲突时,甚至完全以此立场来注解。引一例以见之,如《语录》载:
夫子曰:“由!知德者鲜矣。”要知德。皋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后乃言曰:“载采采。”事固不可不观,然毕竟是末。自养者亦须养德,养人亦然。自知者亦须知德,知人亦然。不于其德而徒绳检于其行,行与事之间,将使人作伪。(17)《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466页。相近解读,别有记载,见《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403页。
象山解《论语·卫灵公》中的孔子论断,以申明“知德”为主旨。但这一解释与《尚书·皋陶谟》皋陶所强调的“行有九德”“载采采”似有所冲突,后者强调的是德不在知,而见之于行,应该以所行之事为九德之验。象山依其对“知德”为主旨的确认,以为“事固不可不观,然毕竟是末”,因为“不于其德而徒绳检于其行,行与事之间,将使人作伪”,如果拘执于行事以验德,作伪的情况是很多的,也是很容易发生的,甚至当事人也自以为真诚而不以为作伪。因此,“知德”是根本。
把握主旨,是象山解经的切入口,仅此自然不算解经的完工,甚至不能说是已完成了主旨的把握,因为主旨固然如诗眼之于诗,尽显一诗之精神,但须贯通全部,才足以真正为主旨。象山曰:
大纲提掇来,细细理会去,如鱼龙游于江海之中,沛然无碍。(18)《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434页。
因此,在把握主旨以后,“细细理会去”,便是把握主旨的具体化。只有做到了“细细理会去”,才可能“如鱼龙游于江海之中,沛然无碍”,否则把握主旨便只能是空话。
大纲与细目之间的关系,不可固执于纲目的体例。且以象山对《诗》《书》的解读为例。前文讨论本心部分时,曾反复论及,在象山看来,经典记录呈现的是古人的实践活动,而道理隐含于其中。就此而论,《诗》《书》堪称“六经”的基础。象山对这两部经典都非常重视,前引论《诗》是一佐证;对《书》则更甚,曾言“吾之深信者《书》”。(19)《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403页。
象山对《诗》《书》的纲目关系有全然不同的判识,他讲:
《大雅》是纲,《小雅》是目,《尚书》纲目皆具。(20)《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434页。
为什么《诗》有纲目之别,而《书》纲目具于一篇之中?纲与目在象山这里,是否有内涵上的区别?象山曰:
《诗·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大雅》虽是言小事,亦主于道,《小雅》虽是言大事,亦主于事。此所以为《大雅》《小雅》之辨。(21)《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404页。
据此可知,纲与目的区别在“言道”与“言事”。言道简明直截,可以为纲;言事交待原委,宜置于目。只是,《诗》原本是形象的艺术表达,无疑与事相有关,但象山着意指出仍有“言道”与“言事”的重心不同。把握主旨,自然应针对主旨,故作此区分与点示,对于解经无疑是关键性的方法。
与《大雅》《小雅》的“言道”与“言事”相分有别,“《尚书》纲目皆具”,这便意味着,《书》虽然全是史事记录,但事与理合一,解读便不可只作故事看,而须由事见其理。象山尝曰:
韩文有作文蹊径,《尚书》亦成篇,不如此。(22)《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466页。
这一比较耐人寻味。象山所指是什么?韩文是宋学之前导,其关键在文以载道。只是韩文为道而作文,其中便有所谓的作文方法,亦即“蹊径”。《尚书》并非有意要为道,而是本心所发活动的实录;同时,虽是活动,却通体皆是道义,故它各篇自成篇章,无须什么雕琢,自然也无所谓“作文蹊径”。对经典的纲目有此判明,根本的方法有了保证,“细细理会去”,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三、须当理会他所以立言之意
象山解经的第二个基本方法,用他解读《孟子》的话,就是“须当理会他所以立言之意”。(23)《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445页。粗看,理会立言之意与前述的把握主旨,似乎所同胜过所异。然而细加体会,两者虽然目标是一致的,但就解经的方法而论,实有不可忽视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二。一是把握主旨可以被认为是普遍意义上的解经方法,举凡解经都须秉持这一方法;理会立言之意,更在于具体语境中的体会。二是经典所记并非全是立言,许多是记事,对事的分析与对言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事的背后是道理,故把握主旨是由事而见理,言则更多涉及语境,理会立言之意在方法上须重在体会语境。
在《语录》中,象山通过答门人李伯敏问——如何践行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而延伸到如何读《孟子》与解《孟子》。前者在第一章中曾引及,后者在上一章中亦引及,但象山与李伯敏后续的答问,对《孟子》的解释非常细致,而且据此得出“须当理会他所以立言之意”的方法。故下文便以此为例,体会象山此解经方法的运用。(24)详见《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444-445页。下文随引分析,不另细注。需说明的是,象山对《孟子》的解释同样也是在示门人以读书法,但他这里示门生的读书法是通过对经典的解释来呈现的,且重在解经;只不过象山此处的解经不是书之以笔,而是说之以言。
李伯敏问象山,如何践行孟子所谓“尽心”?如何区别孟子讲的性、才、心、情?象山回答,四者“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如强作分别,便“只是解字”了。接着便有连续三个问答,涉及如何具体地解释《孟子》。
第一个问答,李伯敏问性、才、心、情“莫是同出而异名”?这显然是对象山前面所答——四者“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有所不满,故进一步追问。所谓“同出而异名”,无疑涉及“解字”。象山虽不满解字,但伯敏的追问表明,即便在象山门下,解字亦是解经不可回避的。象山的回答详尽,先答以理会立言之意的基本方法,然后以具体文本的解释作示范。
(1)不须得说,说着便不是,将来只是腾口说,为人不为己。(2)若理会得自家实处,他日自明。(3)若必欲说时,则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4)此盖随吾友而言,其实不须如此。(5)只是要尽去为心之累者,如吾友适意时,即今便是。
在(3)对伯敏的追问作了明确的回答之后,象山紧跟着以(4)作补充,强调(3)只是应对伯敏的追问,只是特定语境中的回应,不能作为标准的解释。换言之,解经的基本方法就是不落于文字,要体会具体语境。不过,象山并未直接说“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不能作为标准解释,而是说“其实不须如此”,也就是(1)开始就申明的“不须得说”。然而,为什么“不须得说”?象山的理由有二。其一是(1)所讲的“说着便不是”。这等于间接讲,“说着”便须借助具体文字,便被限定了,便不能作为标准的解释。其二就是这样的解释属于“为人不为己”,以及(2)所表达的“他日自明”。至于(5)则转致尽心工夫了,已溢出单纯的解经方法。
再看象山的具体文本解释。他以“牛山之木”章为例:
“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义上。“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此岂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说及,初不须分别。所以令吾友读此者,盖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
此章孟子言及“山之性”“人之情”,象山以为这并非孟子在界定性、情,而只是“偶然说及”,是特定语境中的表达。因此解释经典时,不宜纠缠这样的言语,“初不须分别”。象山接着讲:
“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盖人之良心为斧斤所害,夜间方得歇息。若夜间得息时,则平旦好恶与常人甚相远。惟旦昼所为,梏亡不止,到后来夜间亦不能得息,梦寐颠倒,思虑纷乱,以致沦为禽兽。人见其如此,以为未尝有才焉,此岂人之情也哉?只与理会实处,就心上理会。……圣贤急于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说与人,如何泥得?若老兄与别人说,定是说如何样是心,如何样是性、情与才。如此分明说得好,刬地不干我事,须是血脉骨髓理会实处始得。凡读书皆如此。
此段对性、情的“偶然说及”做进一步的论证。象山通过对“日夜之所息”的解释,说明孟子因“牛山之木尝美”而引发议论,才牵出了人之情、有才无才的问题。《孟子》此章的主旨在仁义,情、性、心、才都只是孟子阐扬仁义主旨时,因其语境而“偶然说及”。如果注释此章,“定是说如何样是心,如何样是性、情与才”,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如此分明说得好,刬地不干我事”。虽然这个“不干我事”也溢出解经方法,而进入尽心的践履问题,但是象山此结论,终究是建立在一大段的论证上,也就是基于他对孟子此章的语境分析上的。
如果说,上一解答对语境的体会是指出孟子的论述风格与语气,那么接着的第二个问答,语境则转为对话。李伯敏“又问养气一段”,象山曰:
此尤当求血脉,只要理会“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当吾友适意时,别事不理会时,便是“浩然”。“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盖孟子当时与告子说。告子之意:“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门别派,将来也会成,只是终不自然。孟子出于子思,则是涵养成就者,故曰“是集义所生者”,集义只是积善。“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若行事不当于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辟告子。
象山指出孟子论养气一段,全是针对告子而发。孟子讲“浩然”“集义所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皆所以辟告子”。而告子的问题“是外面硬把捉的”,这样的路径虽然“将来也会成,只是终不自然”,故孟子所谓“养气”是要从心里内生出来,即前引对李伯敏所言自家适意时便是尽心。象山的解释是否正确,另当别论,此处重在由此指出象山的解经方法,即语境还原的第二种类型。
第三个问答,“又问养勇异同”。象山曰:
此只是比并。北宫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施舍用心在内,正如孟子“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宫又似子夏。谓之似者,盖用心内外相似,非真可及也。
在这一问答中,象山对于孟子的语境还原,则是指出孟子论述中所运用的比较法。象山对比较方法的体会与运用,可谓得心应手。他先指出北宫与施舍是一对比,以此标示用心之内外的不同;继而又引入曾子与子夏,分别对应施舍与北宫。这样的解释显然更贴近一层。若只是指出北宫与施舍的比较,由于北宫与施舍的材料甚少,以此说明用心之内外,不一定非常有效;而引入曾子与子夏,对于熟读《论语》的士子,无疑更形象亲近,进而由此及彼,对北宫与施舍的理解便会得以增强。象山充分意识到这样的引入对比,只是一个点示,如果拘泥于此,真把施舍与北宫看作曾子与子夏,则又犯了语障,故紧跟着说明,“谓之似者,盖用心内外相似,非真可及也”。
经此三个问答,象山最后总结:
孟子之言,大抵皆因当时之人处己太卑,而视圣人太高。不惟处己太卑,而亦以此处人,如“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之语可见。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尝不同。如“未尝有才焉”之类,皆以谓才乃圣贤所有,我之所无,不敢承当着。故孟子说此乃人人都有,自为斧斤所害,所以沦胥为禽兽。若能涵养此心,便是圣贤。读《孟子》须当理会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非常清楚,如果不能还原语境,只在文字表面求解释,是不可能把握经典之“立言之意”的,而不能真正理会立言之意,所谓注释经典便只是无益的沉溺章句。
四、子直将尽信乎?抑其间有拣择
象山解经的第三个基本方法,可以概之为质疑拣择法。把握主旨、语境还原,预设的前提是对经典的确信无疑,总体上可以视为对经典的诠释。质疑拣择法在广义上,当然也是对经典的诠释,但显然是放弃了经典确信无疑的预设前提。且看《语录》一段记载:
伯敏尝有诗云:“纷纷枝叶谩推寻,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无弦陶靖节,个中三叹有遗音。”先生肯之。呈所编《语录》,先生云:“编得也是,但言语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时说话有不必录者,盖急于晓人,或未能一一无病。”时朱季绎、杨子直、程敦蒙先在坐,先生问子直学问何所据?云:“信圣人之言。”先生云:“且如一部《礼记》,凡‘子曰’皆圣人言也。子直将尽信乎?抑其间有拣择。”子直无语。先生云:“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得?若使其拣择,却非信圣人之言也。”(25)《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445-446页。
这则语录可分作两截看,后半截是提出质疑拣择法,前半截则可视作质疑拣择法的理据性伏笔。后半截针对杨子直的“信圣人之言”,象山以商量的语气进行讨论,以质疑的语句进行阐释,“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得”?即全信圣人之言是不可取的,而应“间有拣择”。“间有拣择”是最终的取舍,前提是经过了“如何都信得”的质疑。因此,质疑与拣择实是合二为一的过程。
前半截所以视为后半截的理据性伏笔,不仅是因为质疑拣择法是由李伯敏呈所编《语录》而引起的话题,而且是因为象山对《语录》的看法,内含他对经典解释采取质疑拣择法的理据。象山虽然肯定李伯敏《语录》编得好,但又强调“言语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言语微有病”,是因为“兼一时说话有不必录者,盖急于晓人,或未能一一无病”。这样的文本,由于记录者是语境中人,自存自然毫无问题,甚至会有极大的亲切感。但是对于非语境中人,尤其是后人,时过境迁,言语形式已发生变化,言语中的毛病就可能成为语障,甚至产生误导。象山对于语录的警惕是一贯的,他强调书写较之语录更可靠。然而,即便是书写文本,同样也属于特定语境,“言语微有病”的问题是无法彻底避免的。概言之,圣人之言不可尽信,实是具有充分理据的。象山更强调:
自古圣人亦因往之言,师友之言,乃能有进。况非圣人,岂有自任私知而能进学者?然往哲之言,因时乘理,其指不一。方册所载,又有正伪、纯疵,若不能择,则是泛观。欲取决于师友,师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当否,若不能择,则是泛从。泛观泛从,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用不溃于成。欲取其一而从之,则又安知非私意偏说。子莫执中,孟子尚以为执一废百。执一废百,岂为善学?后之学者顾何以处此。(26)《陆九渊集》卷二十一,第263页。此段文字,卷三十四亦录,基本一致,见《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411-412页。
“后之学者顾何以处此”,简明地讲,就是质疑拣择法又应当如何具体操作呢?
象山解释经典的质疑拣择法,就其实际运用而言,不可一概而论。比如,象山曰:
《系辞》首篇二句可疑,盖近于推测之辞。
吾之深信者《书》,然《易系》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处深可信。(27)《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403页。
对《书》,象山深信之;对《易经·系辞》,有可疑处,也有可深信处。其间,象山自然有他或深信或质疑、或取或舍的理据,比如他讲《系辞》首篇二句“盖近于推测之辞”是理据;但是有些理据于当下的判断中并没有指明,如上引对“默而成之”语的深信。
如何进一步确认象山对此方法的运用?窃以为或宜二径并进。其一,从象山心学的基本宗旨与方法来确认。象山立学宗旨在自立本心,本心既立,无论临事与论学,本心自然就能洞见道理,或信或疑,或取或舍,当下即是。象山曰:
古者十五入大学,《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言大学指归。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入大学标的。格物致知是下手处。《中庸》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读书亲师友是学,思则在己,问与辨皆须在人。(28)《陆九渊集》卷二十一,第262-263页。此段引文前引论读书法,见《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411页。
象山对《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阐明扣其主旨,“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入大学标的。格物致知是下手处”;而格物之方则援引《中庸》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但是,象山的结论是,“读书亲师友是学,思则在己,问与辨皆须在人”。思的具体形式,可以是自己内在的思考,也可以呈现为外在的问与辨。问与辨,就是质疑与拣择。故其所谓“皆须在人”,亦即“在己”。因此,自立本心是贯彻质疑拣择法的根本,这是可以确认的。但是,仅此终究不够具体。故在明确此路径的同时,宜细观象山具体的经说,作为掌握象山解经质疑拣择法的另一路径。上引《学说》其实已是一例,再举象山的《论语说》《孟子说》,以见具体。
先看《论语说》。象山在《论语说》中曾解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而以前三句为重。释“志于道”,象山以“道者,天下万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也”破题;接着,象山指出,君臣父子各有其道,“惟圣人惟能备道”,常人固然不能备道,但也不能尽亡其道。然后,象山转出他的立论:
民之于道,系乎上之教;士之于道,由乎己之学。然无志则不能学,不学则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学,所以为学者在乎志。
得出这个结论后,象山又拣择孔子的两句话与孟子的一句话,佐证他的结论。
释“据于德”。象山先标示“圣人之全德”,然后引《皋陶谟》之九德说,指出德之在人不可求全责备,虽一德亦不必求全,即便“有微善小美之可取而近于一者,亦其德也”,所谓“据于德”,便是据徽善小美,“日积日进,日著日盛,日广日大矣”。
释“依于仁”。象山开宗明义,“仁,人心也”。然后引孔门弟子进行分析,指出圣人能“尽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然亦岂皆顽然而不仁”?圣人与常人在人心上的差别,不在仁之有无,而仅在完备与不足。仁之在人,“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灵,而不能泯灭者也”。故当“依于仁”。
释“游于艺”。象山解得很简单,以为“艺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习者也”。(29)以上引《论语说》出自《陆九渊集》卷二十一,第263-265页。游于艺,固无害于道、德、仁,相反,三者于艺中而有可见者。
整篇解说,除“游于艺”外,其余三句,象山都拣择相关经典文句或人物事迹,以佐证自己的立论。象山的立论全由自己的本心所发,并不玄远高妙,而是平易亲切,常人亦足以接受。象山曰:
古人皆是明实理,做实事。
因叹学者之难得云:“我与学者说话,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势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30)《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396、404页。
这其实也正是象山质疑拣择解经方法的具体运用。
再看《孟子说》。这里仅取开篇释“志壹动气”为例。象山曰:
“志壹动气”,此不待论,独“气壹动志”,未能使人无疑。孟子复以蹶趋动心明之,则可以无疑矣。壹者,专一也。志固为气之帅,然至于气之专壹,则亦能动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无暴其气”也。居处饮食,适节宣之宜,视听言动,严邪正之辨,皆无暴其气之工也。(31)《陆九渊集》卷二十一,第265页。
“志壹动气”与“气壹动志”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象山指出,“志固为气之帅”,因此“志壹动气,此不待论”;但孟子同时强调“气壹动志”,如果不加说明,则“未能使人无疑”,因为气原本就是流动不居的,它的专一与否,又如何能够摇动志的坚固呢?象山指出,“孟子复以蹶趋动心明之,则可以无疑矣”。孟子在言“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之后,紧跟着追加了一句说明:“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指出蹶趋虽是气的流变,但足以摇动其心,故而摇动心志。因此,“气壹动志”便“可以无疑矣”。由此而知,象山的质疑拣择法,其质疑绝非为疑而疑,其拣择也绝非为信而信,疑与信皆依本心而见实理为准。象山曰:
人心有消杀不得处,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牵义,牵枝引蔓,牵今引古,为证为靠。(32)《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458页。
换言之,依循本心,正是去除私意。凡人心私意消杀不了,一切引经据典,都只是“牵枝引蔓”,以今人古人之言语作外在的证据与依靠,而这正是解经之弊病。
综而观之,象山以高度自觉与自信,通过把握主旨、还原语境、质疑拣择三个环节,构成自成一体的解经方法。其中细分,把握主旨又可谓是目标,还原语境与质疑拣择则是更具体的方法。总体而言,象山的解经法虽然也沿用汉唐经注的训诂章句,但只将其作为初级手段,他的解经根本上是作义理的阐明,这也是他以把握主旨为目标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象山的解经法已完全跳出经学的窠臼,而进入分析批判的理学形态。就此而论,由于象山的解经法与其读书法一样,(33)象山的读书法另稿专论。完全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来展开的,因此,象山的还原语境与质疑拣择作为理学的解释学,可类比西方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与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诠释学之间的思想转移,(34)参见傅永军:《从哲学诠释学到批判诠释学》,杨乃乔主编:《比较经学:中国经学诠释学传统与西方诠释学传统的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31-743页。以彰显象山解经法的思想意义。一方面,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是用历史主义对抗客观主义,就此而论,象山解经法的还原语境可谓相似。象山所挑战的是汉唐经学,乃至朱熹的经典注释学,因为朱熹的经典注释学正是在充分吸收汉唐经学基础上,以追求客观主义为表征的。(35)钱穆尝指出朱子融义理于训诂的注经特点,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80页。另一方面,伽达默尔在以历史主义对抗客观主义的同时,又过度张扬了传统、权威、成见的影响力和合法性,从而为哈贝马斯所不满,进而提出交往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批判理论采用重建而非历史的方法,批判性地借用各种竞争的理论和历史先例,而这种借用的基础自然是从主体出发,进而在主体与各种理论与史实之间建构起主体间性。(36)除前注外,哈贝马斯交往批判理论及其性质的简约介绍,可参见詹姆斯·戈登·芬利森:《哈贝马斯》第二章,邵志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无疑,象山解经法中的质疑拣择也多少具有相似的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