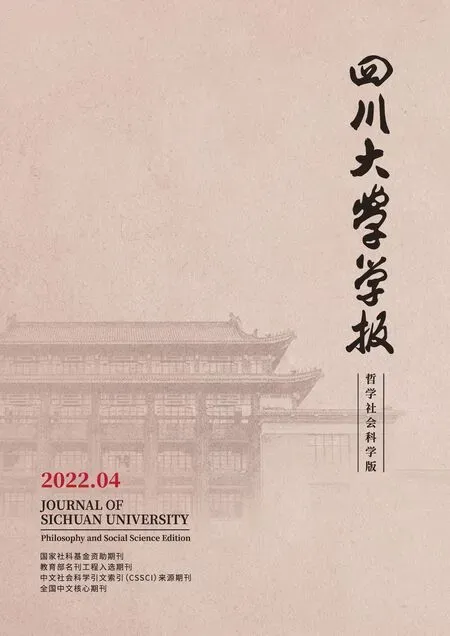晚明诗学中的主体质素论述及其演生过程
——从李贽的“二十分识”到公安派的尚趣重学
杨遇青
古典诗学中的作家论有两种主要趋势:一是儒家的作家论,以《尚书》的“诗言志”和《诗大序》的“吟咏情性”为核心,认为诗是主体情志的呈现。此一观点衍生出发愤抒情说、缘情说等,构筑了古典诗学的理论基石;二是以佛道两家“无我”或“性空”为内涵,强调审美主体的虚灵不昧。(1)参见黄卓越《晚明性灵说的佛学渊源》(《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普慧《慧远的禅智论与东晋南北朝的美虚静说》(《文艺研究》1998年第5期)等。明中叶以来,随着阳明心学的发展,主体性问题占据了文学思想的中心。王守仁说:“心之虚明灵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2)王守仁:《传习录》卷二《与顾东桥书》,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7页。袁中道说:“虚灵之性圆,而全潮在我矣。”(3)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二十《论性》,钱伯城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50页。随着心本体或良知主体在士大夫中得以广泛讨论并深入人心,“作者在文学世界中的位置”(4)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93页。被推至文学思想的前沿。一方面,文学主体的童心、性灵及至情等本源性问题,得到了深入省察和自觉体证;另一方面,对识、才、学、胆、趣等主体质素的发微,也丰富了关于作家精神世界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晚明李贽和公安派的作家论是在心学思潮与佛教复兴的双重影响下,对言志说与虚灵说的综合发展。从李贽到袁宏道、袁中道的诗学论述中,作为本源性的童心、性灵与作为质素论的识、才、学、胆、趣之间体用相即互补,深入辨析其中有关作家主体质素的论述,可以深化对童心说、性灵说的理解,拓展我们对晚明士大夫的生命内涵和文学世界的认知。本文即尝试通过探讨这一主体质素学说的生成与发展逻辑,以展现晚明性灵诗学不断拓展的文学内涵及其主体性意义。
一、李贽三要素说及思想渊源
所谓“作者是谁”的问题,既有本源性回答,也有描述性回答。如果说童心与性灵是对作者问题的本源性省察,那么李贽有关才、胆、识的论述则是描述性的。他在《二十分识》中系统讨论了才胆识的关系问题: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
万历二十年(1592),李贽流寓武昌,“时闻灵、夏兵变,因发愤感叹于高阳,遂有《二十分识》与《因记往事》之说”,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对高阳酒徒郦食其、海上巨寇林道乾等人的才胆识予以积极评价。其所谓“才胆识”指涉颇广,“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5)以上引文参见李贽:《焚书》(《焚书 续焚书》合印本)卷四《二十分识》、卷二《复麻城人书》、卷四《二十分识》,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5、68、155页。左东岭认为:“李贽此处所言之才胆识显然并非专指文学作家而发,同时亦兼指学道乃至治国治家。但李贽又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政治、哲学与文学间确实存有差异。”(6)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第197页。李贽的确把才胆识的标准运用于“处世”(政治)、“参禅学道”(哲学)和“出词落笔”(文学)三种论域。他反躬自察,以为“余谓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在“处世”方面,他把自己描述为洞明世道但不愿苟且的人;在“参禅学道”方面,声称自己识见逊于佛陀,至于当世名家大概并不在其法眼之中;在“出词落笔”方面,则才胆识皆臻于圆满。此际,李贽正批点《西厢记》《水浒传》,自称“《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7)以上引文参见李贽:《焚书》卷四《二十分识》,第155页;《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第34页。并先后写成《童心说》《忠义水浒传序》等宏文,在文学批评上形成了独立的观点,心态极为自负。(8)许建中在《李贽思想演变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4-275页)中指出,“李贽于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开始批点《西厢记》《水浒传》,到万历二十年夏,仍在抄批《水浒传》”;“万历十九年十二月正在批点《西厢记》《琵琶记》,那么批点完此两剧后,因有所感于《西厢记》而写《童心说》,其时间当在第二年(万历二十年)初”。袁中道《游居杮录》(《珂雪斋集》卷九,第1315页)记载其批点《水浒传》的情形:“记万历壬辰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
李贽的才、胆、识三要素脱胎于刘知几的“史有三长”。刘知几曾云:“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9)《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刘知几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522页。李贽认为刘知几于“才、学二字发得明彻,论识处尚未具也”。(10)李贽:《藏书》卷四十一《刘知几传》所附按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06页。与“史有三长”相比,李贽的才胆识三要素说在指涉范围与具体内容上均有较大不同。首先,刘知几的批评对象是史家,而李贽所论包括从孔子、释迦以下乃至海盗之属,具有普遍意义;刘知几所论是史家的学术素养,而李贽所论包括士大夫“处世”“参禅学道”及“出词落笔”诸层面,认为同一主体在不同层面上具有的个体潜能是有差别的,唯有在专擅的领域才有可能出类拔萃,“出词为经,落笔惊人”。其次,李贽的论述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特质:一是去学问化。他在成于万历十八年的《童心说》中就说:“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11)李贽:《焚书》卷三,第98页。认为从闻见道理开始,学者逐渐茅塞其心,异化为假人,以“天下之至文”与多读书识义理背道而驰。二是尚胆。与刘知几相比,李贽易“学”为“胆”,第一次把“胆”提升为主体素质的关键要素。“放胆为文”使得李贽的文章通脱颖锐,为古文发展辟一新境。(12)参见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5-28页。三是重视“识”的根本意义。鉴于刘知几于“论识处尚未具也”,李贽尤其强调识的作用,认为“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
李贽的所谓“识”,首先是强调行为主体独具只眼的洞察力。如他认为“蜀之谯周,以识胜者也。姜伯约以胆胜而无识,故事不成而身死;费祎以才胜而识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观英杰作用之大略矣”;论顾恺之与周瑜“二公皆盛有识见、有才料、有胆气,智仁勇三事皆备”,认为二人一者善藏,一者善发,“皆具只眼”,故在处世上游刃有余。其次是认为识见在“出词落笔”中起到主导作用。如他论班固说:“班氏文才甚美,其于孝武以前人物尽依司马氏之旧,又甚有见,但不宜更添论赞于后也。何也?论赞须具旷古只眼,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刘向亦文儒也,然筋骨胜,肝肠胜,人品不同,故见识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13)以上引文参见李贽:《焚书》卷四《二十分识》、卷二《与友朋书》、卷五《读史·贾谊》,第155、57、201页。在李贽看来,班固有二十分才,但识见不济,刘向之识见在班氏之上,而唯有司马迁是“具旷古只眼”者,为真英雄、真豪杰。
文学主体的识见问题,可以上溯到江西诗派和严羽。黄庭坚论诗认为:“学者要先以识为主,如禅家所谓正法眼者,真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而严羽在此基础上提出“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并认为“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出第一义”。(14)以上引文参见张健:《沧浪诗话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6、65、7页。所谓“正法眼”,原指禅家对“正法”或“第一义”的辨别抉择能力,而此处则应指“通过阅读各家的大量作品培养起来的一种揣摩、辨别的能力”,(15)郁沅:《严羽诗禅说析辨》,《学术月刊》1980年第7期。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识见”。严羽认为,历代诗歌皆有不同的体制、家数或言语,“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晩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因而,作为诗学批评主体的“识”,主要功能是“辨”,即“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眩于旁门小法”,“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已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16)以上引文参见张健:《沧浪诗话校笺》,第497、483-493页。
无论是黄庭坚或严羽都把这种作为文学鉴别力的“识”与禅家的“正法眼”联系起来,对此唐顺之的阐述更别开生面。他认为,“千古作家别自有正法眼藏在”,“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与此”。在这里,唐顺之对作者的主体性的涵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为它并非“以眉发相山川”,而是以“精神相山川”,这就超越了文法层面的“揣摩、辨别能力”,而关注到作者的“真精神和千古不可磨灭之见”。(17)以上引文参见唐顺之:《与两湖书》《答茅鹿门知县二》《答茅鹿门知县》《答茅鹿门知县二》,《唐顺之集》,马信美、黄毅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2、294-295、293、295页。如果说黄庭坚与严羽的“以识为主”是指“识辨诗作差异和优劣的能力”,(18)郁沅:《严羽诗禅说析辨》,《学术月刊》1980年第7期。那么唐顺之则把这种外向型的文学鉴别力转化为内在型的真精神与真识见,而这无疑是心学语境下对主体精神的肯定。
李贽的学术也源于王学左派,尤其受“龙溪、近溪二大老”(19)李贽:《焚书》卷二《答庄纯夫书》,第55页。影响较大。王学重在“识自本心”(20)吴震编校:《王畿集》卷四《留都会纪》,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89页,“识得本体”,(21)罗汝芳:《近溪子集》卷射(三),方祖猷等编校:《罗汝芳集》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也重视本体之流行,如罗汝芳以为“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气力,又有大大识见,就此安心乐意而居天下之广居,明目张胆而行天下之达道”,但他也认为这种襟期、气力、识见可以“致广大”,却“未尽精微也”。(22)罗汝芳:《近溪子集》卷乐(二),《罗汝芳集》上,第62页。李贽的主体性论述,经过了心学的过滤,以“童心”为本源,以“才胆识”为主体潜能的展开,构成了内容充实的人物批评话语体系。他不仅运用“才胆识”的标准评骘历史人物的“英杰作用”,也以此评价杨继盛的奏疏:“若论此疏,直是具二十分识,二十分胆,二十分才矣,当是卓老对手。”(23)《李卓吾批评杨椒山集》,《三异人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3册,济南:齐鲁出版社,1997年,第336页。又以此勉励朋友,如认为袁宏道“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汉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此处的“担荷此一事”,专指参禅学道的“入微一路”,这是说袁宏道在禅学上勇猛精进,不同凡响。(24)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第756页。还以此来品鉴文学形象,如他眉批《西厢记》“拷红”说:“红娘真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城不克,宜于莺莺城下乞盟也哉!”(25)转引自许建平:《李贽思想演变史》,第276页。在才、胆、识三要素的相互关系上,李贽既主张“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也认为才与胆亦可以支撑识见的发明,如他评价席书说:“然有识而才不充,胆不足,则亦未敢遽排众好,夺时论,而遂归依龙场,以驿臣为师也。”(26)李贽:《续焚书》卷三《读史汇》,第87页。认为识见在主体质素诸要素中具有统领作用。
在三要素中,李贽于识与胆尤其自负,自谓:“天幸生我心眼,开卷便见人,便见其人终始之概。夫读书论艺,古多有之,或见皮面,或见体肤,或见血脉,或见筋骨,然至骨极矣。纵自谓能洞五脏,其实尚未刺骨也。”又言:“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27)李贽:《焚书》卷六《读书乐并引》,第226页。袁中道曾将李贽与苏轼相比,充分肯定其文章中的胆识:“龙湖先生,今之子瞻也,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28)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二十《龙湖遗墨小序》,第474页。当代研究者也都肯定了李贽的胆识,如左东岭认为“李贽的确无法与东坡汪洋恣肆、挥洒自如的过人才气相比。但在目光的敏锐和冲决传统的勇气上,苏轼显然又抵不过卓吾。”(29)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第199页。陈平原则充分地肯定李贽的“放胆为文”,认为文胆基于眼光:“李贽的读书,特有眼光,别出手眼,经常能发千古之覆。读史如此,论事也如此。”(30)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第20页。
综上,从严羽的“以识为主”到李贽的“唯识为难”,是对作家主体性论述的重要转进。在此过程中,“识见”由外向型鉴识力转向内在型的主体潜能,从诗文鉴识发展为面向修道、处世和出词落笔诸层面的主体质素论述。这一转进受到禅学与心学的影响不小,它是宋代以来“转向内在”(31)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的文化转型中的一环,也是阳明心学发展的一种逻辑结果。
二、公安派的“五要素”说及其“唯趣”说的意义
万历十九年,袁宏道曾赴龙湖访李贽,从游三月有余。袁中道对此有过评说:“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32)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第756页。次年五月二十九日,袁中道也到武昌向李贽问学,相处一月多。转年,公安三袁又联袂访李贽于麻城,谈道问学,逗留十余日。李贽也很推重袁氏兄弟,以为“伯也稳实,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33)以上引文参见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第756页。关于三袁与李贽交往之事实,可参见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及戴红贤《三袁与李贽会晤时间及地点考辨》(《长江学术》第六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等。
在公安三袁中,袁宏道最为颖锐,而袁中道与李贽交往最多,在武昌时,又甫值李贽《二十分识》脱稿,所以他对才胆识之说了然于心。袁宏道去世后,袁中道在为其所撰《行状》(1610)中综合了李贽的三要素说与袁宏道的诗学实践,总结出写作主体的五要素:
总之发源既异,而其别于人者五:上下千古,不作逐块观场之见,脱肤见骨,遗迹得神,此其识别也;天生妙姿,不镂而工,不饰而文,如天孙织锦,园客抽丝,此其才别也;上至经史百家,入眼注心,无不冥会,旁及玉简金叠,皆采其菁华,任意驱使,此其学别也;随其意之所欲言,以求自适,而毁誉是非,一切不问,怒鬼嗔人,开天辟地,此其胆别也;远性逸情,潇潇洒洒,别有一种异致,若山光水色,可见而不可即,此其趣别也。有此五者,然后唾雾皆具三昧,岂与逐逐文字者较工拙哉!(34)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第758页。
袁中道所归纳的“五要素”,在理论上以性灵说为依据。他认为袁宏道在吴县辞官(1597)后,诗文“俱从灵源中溢出,别开心眼,了不与世匠相似”,其“别于人者五”,根植于“发源既异”。此处的“发源”,无疑指向袁宏道的“性灵”。袁宏道在吴县辞官前一年写下《叙小修诗》,以为“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35)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明确了写作中的性灵主体。以此“发源”,他在诗文创作中表现出“了不与世匠相似”的五种特质,所以五要素也可以视为性灵说的基本内涵。在创作上,以袁宏道漫游吴越时所作《解脱集》为依据。袁宏道从吴县辞官后,漫游吴越六个月,诗文辑为《解脱集》。这不仅意味着他从官场的桎梏中获得了解脱,也是其由儒入佛的一种明志。袁中道在《行状》中说其兄“走吴越,访故人陶周望诸公,同览西湖、天目之胜,观五泄瀑布,登黄山、齐云,恋恋烟岚,如饥渴之于饮食。时心闲意逸,人境皆绝。先生与石篑诸公商证日益玄奥。……两人递相取益,而间发为诗文,俱从灵源中溢出,别开心眼”。(36)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第756页。可见,吴越山水的熏陶与友人的“商证”都是袁宏道打开灵源的重要因缘。在内容上,则以李贽的才胆识说为依据。虽然袁中道说其兄诗文在五方面“了不与世匠相似”,但李贽显然不在“世匠”之列。袁中道正是在李贽的“才胆识”三要素上,增加了“学”与“趣”,构成了性灵主体的五要素说。
从童心说到性灵说,从写作主体的三要素到五要素,文献史实和思想脉络至为清楚。但从童心到性灵,到底有何不同,有何发展?却未必是不言自明的。相对于李贽的三要素说,袁中道的五要素说增加了“学别”与“趣别”二种。从性灵主体的要素分析入手,即从“趣”与“学”入手,无疑是解释这种发展逻辑的关键处。从时序上看,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于吴县任上提出“独抒性灵”后,随即在次年漫游吴越时所作的《叙陈正甫〈会心集〉》中,明确表述了其“唯趣”的观点: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37)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第463页。
所谓“趣”有皮毛与实质之分,书画、古董鉴赏、焚香品茗以至禅悦,“这些都是趣的皮毛,而趣之要,是神情”,(38)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44-745页。“神情”体现为闲适雅致的生活情趣,也是诗文中映现出来的审美趣味。
如果回到“唯趣”说被提出的万历二十五年,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这种“神情”具体地理解为春山鸟鸣、弹琴绿荫之象外之象的一种折光。袁宏道写作《叙陈正甫〈会心集〉》是在他漫游吴越、纵览天目之后,赴歙县欲登齐云前夕。(39)钱伯城笺云:“陈正甫时任徽州知府,宏道此文当是作越、歙之游时在歙县所作。”袁宏道在《伯修》中说:“因便道之新安,为陈正甫所留,纵谈三日。”(《袁宏道集笺校》,第464、492页)当然,也可能是他从徽州返杭后补作。在此期间,他“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吴,山行殆二千余里”,“看花西湖,访道天目,往返吴越间四阅月。足之所踏,几千余里;目之所见,几百余山”,“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谭,无一谭不畅”,这种游赏活动无疑对他的诗文创作有积极影响,而此际也正是其山水小品和诗歌创作最具活力的时期,他不无夸张地说自己“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40)以上引文参见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吴敦之》《赵无锡》《伯修》,第505、494、492页。江盈科为《解脱集》所作序中也说:“中郎所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动静之性,无不描画如生。譬之写照,他人貌皮肤,君貌神情。”(41)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三《解脱集序二》,第1691页。山水亦有喜怒动静之性,此即山水之“神情”。由此说袁宏道的“趣”主要得之于吴越山水的灵气,应当并不为过。而此种灵气,得之于西湖为多。袁宏道漫游吴越以西湖为中心:“浪迹四阅月,过西湖凡三次。初次遊湖,次则从五泄归,再次则从白岳归也。湖上昭庆五宿,法相、天竺各一宿。”这期间,他“每将暮,则出藕花居,棹小舟看山间夕岚。月夜则登湖心亭,过第四桥、水仙庙,从堤上步而归”。(42)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湖上杂叙》,第438页。山间夕岚,湖上月色,为其小品文增添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氤氲气息。他在《西湖二》中写道: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43)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第423页。
他的此类小品文可视作对“趣”的诗性描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正是前文所及其“唯趣”观中的“山上之色,水中之味”;“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是为“花中之光”;“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是为“女中之态”。乃至“安可为俗士道哉”一句,亦含有“唯会心者知之”的意味。所以作者领悟到“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
在此基础上,袁宏道把这种得之于山水的灵感用于诗文批评。如他在万历二十五年写信给钱象先说:“扇头诸绝,鲜妍如花,淡冶如秋,葱翠如山之色,明媚若水之光。”(44)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钱象先》,第497页。这是将他对钱氏所赠绝句审美感受亦形容为如花如秋、如山色水光,一言以蔽之,是说诗中充溢着“趣”。如果说“趣”是一种在物质形态之中又超越物质形态的“神情”,那么它首先是袁宏道寓目所见的“花态柳情,山容水意”,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间的山水之神情。这种“山水之神情”通过文学书写,转化成为作品中的那种“宁静淡远韵味”和“悠然闲适之趣”。
然而,能否就此把“性灵”直接理解成一种山水之趣?从袁中道认为“远性逸情,潇潇洒洒,别有一种异致,若山光水色,可见而不可即,此其趣别也”的表述可知,“山光水色”只是对“趣”的一种拟喻,“趣”本质上是主体的“远性逸情”。万历二十五年秋,袁中道在真州见到从西湖归来的袁宏道,对其《解脱集》的诗文新变很是讶异,以为“彼文人彫刻剪镂,宁不烂漫,岂知造物天然,色色皆新,春风吹而百草生,阳和至而万卉芳哉”。在袁中道眼中其兄此期的诗文如“造物天然”,色色皆充盈着生命活力。此后,他又把袁宏道的诗文成就置于诗史中予以确认,认为宋元以来,诗文芜烂,“徒取形似,无关神骨”,袁宏道起而振之,“而诗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为寒氛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竞皆鲜敷;如流泉壅闭,日归腐败,而一加疏瀹,波澜掀舞,淋漓秀润。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45)以上引文参见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九《解脱集序》、卷十一《中郎先生全集序》,第452、522页。袁中道其实采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隐喻:“名卉”需要“杲日”,所谓“春风吹而百草生,阳和至而万卉芳”,指山水在心灵之光映射中才能生趣焕然;而“流泉”需要“疏瀹”,则是说心灵需要从“闻见道理”的壅闭中加以“疏瀹”,才能“鲜敷”“淋漓”。显然,他是把袁宏道诗文之“色色皆新”,归之于“心灵无涯”。
事实上,袁宏道《解脱集》之新变不仅得力于“山川之奇”,也得力于其在佛学上的精进。袁中道在《解脱集序》中说:“及我大兄休沐南归(1592),始相启以无生之学。自是以后,研精道妙,目无邪视,耳无乱听,梦醒相禅,不离参求,每于稠人之中,如颠如狂,如愚如痴。五六年间大有所契,得广长舌,纵横无碍,偶然执笔,如水东注。既解官吴会,于时尘境乍离,心情甚适。山川之奇,已相发挥;朋友之缘,亦既凑和。游览多暇,一以文字为佛事。山情水性,花容石貌,微言玄旨,嘻语谑辞,口能如心,笔又如口,行间既久,遂以成书。”(46)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九,第451页。这段文字是袁中道对《解脱集》诗文意义的抉微,所谓“山情水性,花容石貌”不过是“一以文字作佛事”。由此,我们应当在“一以文字作佛事”的语境中对山水之趣的实义做进一步的诠释。
袁宏道曾说:“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像,不师先辈。”(47)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之十八《叙〈竹林集〉》,第700页。所谓“师物”即“师森罗万像”,那么“师心”与“师物”又是何种关系?亦即,主体性的“远性逸情”与自然山水的“森罗万像”是何种关系?法藏《妄尽还源观》中说:“经云:‘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印。’言一法者,所谓一心也。是心即摄一切世间出间法,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48)石峻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册,第99页。简言之,心与象之关系,即是性与相、理与事的关系。“一心”为理,“森罗万象”为事,一心与森罗万象不一不异,理事无碍,此即华严宗的“理事圆融观”。这一观念在后来的佛教发展中成为共识,如禅宗的马祖道一说:“三界唯心,森罗万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菩提道果,亦复如是。”(49)普济:《五灯会元》卷三,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8页。袁宏道写作《叙陈正甫〈会心集〉》的前一年(1596)曾写信给陈正甫说:“《华严经》以事事无碍为极,则往日所谈皆理也。一行作守,头头是事,寻得些子道理。看来世间,毕竟没有理,只是事,一件事是一个活阎罗。若事事无碍,便十方大地,处处无阎罗矣,又有何法可修,何悟可顿耶?”这是说他在吴作令,事事执着,不能放下,而按照华严宗教义,事事无碍,又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他又在《德山麈谈》中说:“儒者但知我为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事事物物,则我安在哉?如因色方有眼见,若无日月灯山河大地等,则无眼见矣。”(50)以上引文参见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六、四十四,第265、1289页。可见在袁宏道看来,“事事物物皆我”,以此类推,“山光即是佛光,鸟性即是佛性,悉表真如;潭影无非佛影,人心无非佛心,尽归般若”。(51)屠隆:《重建破山寺碑》,《常熟县破山兴福寺志》卷三,《程嘉燧全集》下册,沈习康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3页。潭影人心皆是一法之所印,山光鸟性皆为一心之所现。正如袁宏道所说:“性一而已,相惟百千。离百求一,一亦不成;离相言性,性复何有?”(52)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八《八识略说叙》,第702页。眼见为色,离相无性,森象万象即性海之洪澜,空诸所有方能尽揽千山万水于襟怀之中。袁宏道以华严禅的眼光看山水,则山光水态无非性灵,可见他不愧为“千古具眼人”。(53)藕益智旭《评点西方合论序》云:“中郎年少,风流洒落,亦为缁素所忽。试读彼《西方合论》,可复忽乎?呜呼,今人不具看书眼,何怪乎以耳为目也哉!”参见《净土十要》,于海波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34页。
从童心说到性灵说,文人的主体性规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李贽万历二十年的才胆识说重视写作主体的独立识见与批判能力,其所谓绝假纯真的童心,是以识为本,以才与胆为用,对人世间一切闻见道理假人假事加以判断和口诛笔伐。袁宏道万历二十五年的唯趣说则集中表现为“闲情逸性”,其性灵说中作为主体的“性”,指向“事事物物皆我”的一心之性,此即山水自然之神情,是“一心”与“森罗万象”的理事圆融、交相辉映;而“灵”则是他获得解脱之后的闲适神情在自然山水上的映射。从官场的“事障”与闻见道理的“理障”中逃离,在自然山水和对禅意的回归中,袁宏道发现了自然之灵趣与人性的奥秘。
三、性灵诗学的学问化转向与“学道有韵”
袁中道以为《解脱集》不但体现出袁宏道的才胆识趣,也体现出了他对学问的融会。而性灵主体五要素说,理应是对袁宏道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或思想的归纳,但至少从《叙陈正甫〈会心集〉》看,袁宏道其时并不那么重视学问,在其“趣”与“学”之间反而呈现出明显的紧张关系: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袁宏道这里的“趣”与李贽的“童心”之间的关联性至为明白。李贽反对闻见道理,推崇童心,袁宏道也以童子“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且为“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认为老学究“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去趣愈远,无法参透生命真趣。这是李贽与袁宏道共通的人生经验,也是《解脱集》写作的前提。此前,袁宏道在其性灵说的宣言《叙小修诗》中已说:“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竿草》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54)以上引文参见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四,第463、188页。在他看来,“真人”的基本内涵是“无闻无识”,从“闻见道理”中解脱出来,才能有“任性而发”的真声。可见,袁宏道所主张的是一种主体精神上的“童趣”,他不仅要从世俗官场中解脱出来,也要从精神上的“闻见道理”中解脱出来。
显然,从李贽的《童心说》(1590)《二十分识》(1592)到袁宏道的《叙小修诗》(1595)《叙陈正甫〈会心集〉》(1597),贯穿着对闻见道理的排斥和对童心天趣的认同。但从李贽《二十分识》中的三要素说到袁中道所总结的五要素说,袁氏兄弟对李贽的作家主体论述有了较大发展。这之中,除上述“趣别”外,袁宏道还从“经史百家”“玉简金叠”里采其菁华,认为“此其学别也”。那么,如何理解所谓“学别”?亦即,袁宏道的“学问”与他所排斥的“闻见知识”差异何在?
事实上,把“学问”二字植入公安派的诗学经验中是性灵诗学的重要拓展,而这种拓展在袁宏道入京谒选教职以后变得明朗起来。唯趣说产生在袁宏道万历二十五年漫游吴越之际,故他对童心天趣的自觉阐发与“山光水色”的熏陶不无关系,也确实是“趣得之自然者多,得之学问者少”。但在万历二十六年,袁宏道出任顺天府教授,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都主要是在顺天府和国子监担任教职。在此期间他对读书和治学显示出更加积极态度,不仅集中地阅读了宋人别集,还致力于欧苏文集的批点,并经常在致友朋的书信中分享其读书体验,如“邸中无事,日与永叔、坡公作对”;“近日始遍阅宋人诗文”;“生在此甚闲适,得一意观书。学中又有《廿一史》及古名人集可读,穷官不须借书,尤是快事。近日最得意,无如批点欧、苏二公文集”。经过系统阅读,他重新发现了苏诗的价值,认为“苏,诗之神也”,“苏公之诗,出世入世,粗言细语,总归玄奥,怳惚变怪,无非情实。盖其才力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绝千古”,认为苏轼的诗虽不如李、杜二公遒逸,但才、学、识兼备,“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他还以“才高”与“学博”衡鉴当世名流,如认为徐祯卿、王世贞“才亦高,学亦博,使昌谷不中道夭,元美不中于鳞之毒,所就当不止此”。(55)以上引文参见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一《答梅客生开府》《答陶石篑》《与李龙湖》《答梅客生开府》《与李龙湖》、卷十八《叙姜陆二公同适稿》,第734、743、750、734、750、696页。
袁宏道对学问的肯定,与其作为教授和助教的身份不无关系。一则他“邸中无事”,既无如作吴令时之苦窘,亦不复如漫游吴越时的放浪形骸;二则他“一意观书”,特别对欧苏文集的研究,让他对宋人学问有了更深切的体认。做学问本是教授生涯的题中之义,从中他也获得了乐趣,如其言“近日坐尊经阁,与弟子谈时艺,乐亦不减。阁中有廿一史、十三经及他书甚多,穷官不必买书,是第一快活事”;在看到“门人某等留心学问,其为文根理而发,无浮词险语”时,也表示“是可喜也”,并为弟子总结举业中“险”“表”“贷”三种浮词险语,指出文与学的关系,认为“文之不正,在于士不知学。圣贤之学惟在心性。今试问诸举业者,何谓心,何谓性,如中国人语海外事,茫然莫知所置对矣。焉知学?既不知学,于是圣贤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响见,有如射覆”,而解决的办法是“士当教之知圣学耳,知学则知文矣”。(56)以上引文参见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一《答梅客生》、卷十八《叙〈四子稿〉》,第745、697页。在袁宏道看来,举子业须知学,而“圣贤之学,唯在心性”,无论是“根理而发”的举子业,还是“任性而发”的真诗,都不能离此本源。
做学问须读书,对此袁宏道说:“近日始学读书,尽心观欧九、老苏、曾子固、陈同甫、陆务观诸公文集,每读一篇,心悸口呿,自以为未尝识字。”(57)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答王以明》,第772页。这里的“未识字”典出其导师李贽和座师焦竑。焦竑曾记录李贽在南京聚友讲学时所说,“宏甫曰:‘君辈以高科登仕籍,岂不读书!但苦未识字,须一讲耳。’或怪问其故。宏甫曰:‘《论语》《大学》岂非君所尝读?然《论语》开卷便是一学字,《大学》开卷便是大学二字。此三字吾敢道君未识得,何也?此事须有证验始可。’”(58)焦竑:《焦氏笔乘》卷四“读书不识字”条,李剑雄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3页,李贽以为“学”字要彻上彻下,始是识得,“大学”二字要证得行得,始是真解;而袁宏道亦以举子业“义本浅也而艰深其词”,“词本芜也而雕绘其字”,“理本荒也,而剽窃二氏之皮肤,如贫无担石之人,指富家之囷以夸示乡里也”,认为学问没有本源,则文章如衣饰相矜,徒有其表。此时他不但指出“当知读书亦是难事”,且“习久,渐惯苦读。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处,辄叫号跳跃,如渴鹿之奔泉也”。(59)以上引文参见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八《叙〈四子稿〉》、卷二十二《答王以明》,第697-698、772页。
在北京问学读书的两年多,袁宏道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万历二十六年,陶望龄写信给袁宗道说:“近日看《宗镜录》,可疑处甚多,即如‘三界唯心,一切惟识’二语,三岁孩儿说得,八十岁翁行不得。”袁宏道读后哂之,复书说:“既云唯心,一切好恶境界,皆是自心现量也,更何须问行与不行?”(60)以上引文参见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一《答陶石篑》,第735-736页。此时,他坚执“唯心”一语,不重“行与不行”。但万历二十七年,他写信给陈正甫说:“古人云‘行起解绝’,弟辈未免落入解坑,所以但知无声无臭之圆顿,而不知洒扫应对之皆圆顿也。”又作《答陶石篑》说:“妙喜与李参政书,初入门人不可不观。书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久为魔所摄。’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经论中可证者甚多。姑言其近者:四卷《楞伽》,达摩印宗之书也;龙树《智度论》、马鸣《起信论》,二祖师续佛慧灯之书也;《万善同归》六卷,永明和尚救宗门之弊之书也。兄试看此书,与近时毛道所谈之禅,同耶否耶?”(61)以上引文参见《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二《答陈正甫》《答陶石篑》,第775、790页。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他撰成《西方合论》,并在序言中说:“余十年学道,堕此狂病,后因触机,薄有省发,遂简尘劳,皈心净土。礼诵之暇,取龙树、天台、长者、永明等论,细心披读,忽尔疑豁。既深信净土,复悟诸大菩萨差别之行。如贫儿得伏藏中金,喜不自释。”(62)石峻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8册,第312页。万历二十八年春初,他又致信李贽说:“世人学道日进,而仆日退,近益学作下下根行。孔子曰:‘下学而上达。’枣柏曰:‘其知弥高,其行弥下。’始知古德教人修行持戒,即是向上事。彼言性言心,言玄言妙者,皆虚见惑人,所谓驴橛马桩者也。”(63)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二《李龙湖》,第792页。袁宏道从万历十九年龙湖问道以来,至此已近“十年”。他开始全面反省狂禅,晦言心性,走向实修实证的“下下根行”。
综上,万历二十七年前后,即在北京担任顺天府教授和国子监助教期间,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发生了关键性的进展。从以前的一切现成,不重功夫,转向重实证实修的“下下根行”,与此同时,他的文学思想也开始凸显读书和学问的意义。那么,重学问的袁宏道是否仍坚持对“闻见道理”的批判,或者他能否在天趣与学问之间能达到平衡?答案是肯定的。
万历三十五年,袁宏道在《寿存斋张公七十序》中发展了唯趣说,把它解释为“学道有致”的韵致说:
山有色,岚是也;水有文,波是也;学道有致,韵是也。山无岚则枯,水无波则腐,学道无韵则老学究而已。昔夫子之贤回也以乐,而其与曾点也以童冠咏歌。夫乐与咏歌,固学道人之波澜色泽也。……大都士之有韵者,理必入微,而理又不可以得韵,故叫跳反掷者,稚子之韵也;嬉笑怒骂者,醉人之韵也。醉者无心,稚子亦无心,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由斯以观:理者,是非之窟宅,而韵者大解脱之场也。(64)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四,第1541-1542页。
这段文字并非讨论文学的专论,但对童心和趣无疑有重新阐释。“士之韵”如山之岚、水之波,是童心的洋溢。稚子的叫跳反掷、醉人的嬉笑怒骂,都是理无所托的“自然之韵”。与唯趣说一样,他仍然沿用了童子拟人和山水拟象,也认为韵致“得之自然者多,得之学问者少”。其重要的发展在于把“韵”解释为“学道人之波澜色泽”,即一方面将学道者“一一绳之于理”,而“理又不可以得韵”,所以世上不乏“学道无韵”的老学究;另一方面又以世之有韵者“理必入微”,能体证到至人无己、无心是道的妙处,从而“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袁宏道以童子、醉人无心,故“理无所托”而有“自然之韵”;又以颜回之乐、曾点之咏歌为从心所欲而韵致不绝。他这里的“韵”是趣的深化,如果说“趣”源于童心与自然山水相看两不厌的冥会,“韵”则是学道人对无心是道的生命本相的自觉把握。
在文学批评史上,严羽提出“盛唐诸公唯在兴趣”,“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一兴趣说与袁宏道的“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有异曲同工之妙。严羽也重视别材别趣与读书穷理的辩证关系,认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所至”。(65)以上引文参见张健:《沧浪诗话校笺》,第157、129页。但严羽所讲的兴趣,主要“指诗歌艺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所引起的人的审美趣味”,(66)张少康:《论〈沧浪诗话〉》,《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这一审美批评立足于言、意关系。兴趣是言外之意,即一唱三叹之音。而袁宏道所讲的“世人所难得者唯趣”,首先是一种对作者的批评,指向“童子”“山林之人”“愚不肖”和“年长官大”者的人生趣味,以童子的“不知有趣”为最上乘。可以说,严羽的“镜花水月”偏重于作品中所表现的悠远的韵味,而袁宏道的“山容水态”本质上是指作者的“闲情逸性”;严羽的兴趣说是师古的,专门用来概括盛唐诗歌的美学特征,而袁宏道“师森罗万像,不师先辈”,森象万象不仅指涉山水,也包括辨说书画、涉猎古董、烧香煮茶等“皮毛”,更指向会心者从象中领会到的“神情”;严羽读书穷理是用来为诗人助“兴”的,而袁宏道的读书穷理是用来修道的。总之,严羽是以艺术为中心的批评家,而袁宏道是以诗人为中心的表现者,所以其理论被概括为“性灵”,性灵是主体自内而外的“趣”与“韵”。
四、余 论
袁中道以李贽的才胆识作为基础,把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五年从童心说发展而来的唯趣说和万历二十七年以来重学问的面向综合起来,形成了性灵派的诗人主体质素的五要素说。从重识到尚趣、重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袁宏道文学思想和李贽的联系与发展,一方面他继承了李贽的童心与才胆识的主体论述,另一方面,他更重视得之于自然的天趣与得之于读书求道的韵致。从历时性上看,尚趣与重学问构成了性灵说发展的两个阶段。
袁宏道的思想发展既基于其自身学养的提升,也出于他与李贽在个性上的差异,这在性灵说的主体论述中表现为其对“胆”的忽视。虽然袁中道说,袁宏道“随其意之所欲言,以求自适,而毁誉是非,一切不问,怒鬼嗔人,开天辟地,此其胆别也”,但其“胆别”不过表现为“自适”和“一切不问”,与李贽的“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相勘,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闲情逸性”。袁中道也明确表示对李贽“不能学有五”,其一便是“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怯弱,随人俯仰”。(67)以上引文参见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七《李温陵传》,第725页。可见在胆力方面,不论是袁宏道还是袁中道,与李贽相去甚远。但在识见方面,特别是在“参禅学道”上,袁宏道则颇为自负:“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勍敌,唯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炼衲子,久参禅伯,败于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68)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张幼于》,第503页。万历二十七年以后,袁宏道全面反省狂禅,走向更稳实的“下下根行”,与李贽的向上一路的思想形态已经有了较大的距离。李贽作为自觉的异端思想家,更重视主体在识力和胆力上的能量,偏重于对“闻见道理”的批判;与李贽相比,袁宏道缺少“出世处世”的批判锋芒,基本上属于有识无胆的类型,因而他更钟情于山水与生活中的适性与自得,偏向于“闲情逸性”的表达,归宿于读书求道的人文体验。或者说童心的实现需要写作主体才胆识的支撑,而性灵则源于“得之自然”的天趣和“学道有致”的韵味。
此后,叶燮也更是明确地把文学要素分为“在物者”——“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和“在我者”——“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此心之神明”。叶燮在李贽三要素的基础上增设了“力”,认为“唯力大而才能坚”,并且以“《三百篇》而后,唯杜甫之诗,其力能与天地相终始”,这些都可以视为对李贽学说在“出词落笔”层面上的延展,但与袁宏道的唯趣说相去甚远。简言之,叶燮的思维是分析的,他明晰地划分了创作中我与物、能与所、主与客的关系,提出“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69)以上引文参见叶燮:《原诗》(《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合印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7-28、24页。而袁宏道的唯趣说则是理事圆融的,强调森罗万象无非一心之所印,山容水态无非神情之摇曳,“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70)江盈科:《敝箧集序》,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三,第1685页。李贽说:“心即是境,境即是心,原是破不得的,惟见了源头,自然不待分梳而了了在前矣。”(71)李贽:《续焚书》卷一《复陶石篑》,第8页。袁宏道关心的是“见了源头”,叶燮关心的是文章之生成,他用主客对立的思辨逻辑,破了性灵诗学中心境一体的主体灵性。就此而言,李贽与袁宏道虽然在主体论述上有不少差异,但他们对主体性的本质省察是连续的,对主体性的要素分析一脉相承。把李贽与袁宏道的主体论述置于严羽与叶燮之间,我们不难发现,万历二十年至三十年间的确是主体精神鲜明而踔厉奋发的年代。
——以黄麻士绅纠葛为中心的讨论
——《李贽学谱(附焦竑学谱)》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