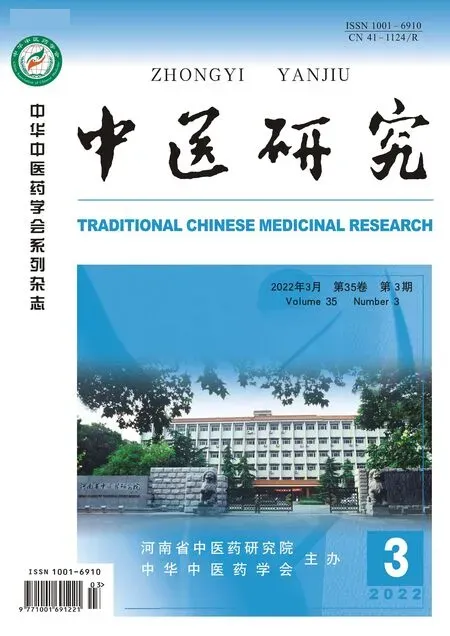国医大师张磊运用丹栀逍遥散治疗慢性胆囊炎经验 *
张勤生,吴明阳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2)
国医大师张磊是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二部一局第二批师承制导师,国家“十五”攻关“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课题名老中医,主编《张磊医学全书集》《张磊临证心得集》《张磊医案医话集》《<产鉴>注释》《<产鉴>新解》等书。他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崇尚致中和平,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在70余年的教学和临床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动、和、平”学术思想,创立了具有临证特色的八法,临床擅长以经典理论为指导治疗内、外、妇、儿科疾病,尤善诊治内科疑难杂病。笔者有幸跟随张老身侧学习,获益匪浅。现将张老运用丹栀逍遥散治疗慢性胆囊炎的经验介绍如下,以飨同道。
1 西医学对慢性胆囊炎的认识
慢性胆囊炎(chronic cholecystitis,CC)是由于胆囊结石、慢性感染等多种原因引起的胆囊壁持续、反复发作的慢性炎症,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病、多发病。该病患者常表现为右上腹胀痛、隐痛,或右上腹有轻度压痛及叩击痛,疼痛可放射至肩背部,伴恶心、嗳气、食欲不振等消化不良症状,尤在饱食后或进食肥甘油腻食物后出现[1]。慢性胆囊炎可根据胆囊内是否伴有结石分为慢性结石性胆囊炎和慢性非结石性胆囊炎。慢性胆囊炎的诊断可通过患者病史、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确诊。影像学检查包括腹部B超、CT、MRI等,其中腹部B超是最常用、最有价值的检查,超声下可见胆囊体积大小、胆囊壁厚度、胆囊内结石及胆囊收缩情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呈现多元化的改变,高胆固醇饮食、脂质代谢障碍等与胆囊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密切相关[2]。西医治疗症状轻、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患者以饮食调整为主,配合利胆药物对症治疗;针对反复发作或症状重、伴有胆囊结石者,可行手术治疗。然而,以上治疗不能完全根除该病,患者病情仍易反复发作,迁延难愈,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因此,临床上越来越重视该病的治疗。
2 中医学对慢性胆囊炎的认识
中医学根据该病的症状及表现将其归于“胁痛”“胆胀”范畴[3]。该病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如《灵枢·胀论》曰:“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灵枢·五邪》云:“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描述了该病的病名以及临床常见的症状如胁下胀痛、口干苦、善太息等,指出该病发生与外邪、肝胆病变、瘀血等因素有关。清代《医宗金鉴》曰:“其两侧自腋而下,至肋骨之尽处,统名曰胁。”明确了胁部为腋以下至十二肋骨部位的统称。中医药疗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理论,在诊治CC方面具有整体观、个体化用药、辨证论治等优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治疗胆囊炎、胆石症的疗效显著,其临床疗效越来越被肯定[4-7]。
3 中医学对慢性胆囊炎的病因病机认识
根据CC的临床表现,可将其归为中医学“胁痛”“胆胀”等范畴。根据该病的临床特征表现,历代医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阐述,不断地促进和完善中医学对该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和诊治。
3.1 湿热郁阻,气滞而痛
《证治汇补·胁痛》云:“湿热郁火,劳役房色而病者,间亦有之。”指出湿热蕴结可导致胁痛。湿热可因外感而致,亦可因脾胃损伤。脾失健运则化生湿热,循经而结于肝胆,导致肝胆失于疏泄,气机郁滞,不通则痛,发为胁痛。
3.2 脏腑失和,瘀阻而痛
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黄病诸候》中言:“气水饮停滞结聚成癖,因热气相搏,则郁蒸不散,故胁下满痛,而身发黄。”认为脏腑功能失调导致的气滞、水饮停滞、瘀血是胁痛发病的重要病理因素;各种病理产物导致气机郁滞而化热,郁热不得宣散,出现胁胀痛、身发黄等症。
3.3 情志失调,肝郁而痛
《济生方·胁痛评治》载:“夫胁痛之病……多因疲极嗔怒,悲哀烦恼,谋虑惊忧,致伤肝脏。肝脏既伤,积气攻注,攻于左则左胁痛,攻于右则右胁痛。”《金匮翼·胁痛统论》曰:“肝郁胁痛者,悲哀恼怒,郁伤肝气。”情志不舒,长期悲忧、过于恼怒、多思善虑伤及肝气,气机郁滞,滞于两胁下,导致胁痛发生;气郁日久,既可化热,又易致血行不畅,气郁化火、气滞血瘀均可导致胁痛加重,并易变生他病。
3.4 瘀血阻络,不通则痛
瘀血由气滞而致,亦有因外伤跌扑闪挫所致,外伤导致脉络损伤,离经之血溢于脉外,留滞胁下,瘀阻胁络,发生胁痛。瘀血所致胁痛,刺痛明显,触之痛甚,如《类证治裁·胁痛》言:“血瘀者,跌仆闪挫,恶血停留,按之痛甚。”
3.5 体虚失养,不荣则痛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云:“凡房劳过度,肾虚羸弱之人,多有胸胁间隐隐作痛,此肝肾精虚。”指出因房劳过度或素体肾虚体弱之人,因肾精亏虚,肾水不能涵养肝木,肝阴不足,肝络失于濡养,不荣则痛,发为胸胁间隐隐作痛。
综上所述,该病病因多为感受外邪、饮食失宜、情志不畅、劳逸失调、素体虚弱等多种因素导致气机郁滞或肝络失养而发病;病位在胆腑,病性虚实夹杂,病变涉及肝、脾、胃、肾等多个脏腑;病机为气滞、湿热、瘀血、砂石、虫积等阻滞于内,导致肝胆失于疏泄,胆汁瘀积,胆腑不通,发为胁痛。
4 丹栀逍遥散方药解析与研究
4.1 丹栀逍遥散的方药分析
张老所用丹栀逍遥散出自明代薛己的《内科摘要》,该方是在宋代陈师文等编写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名方逍遥散的基础上加牡丹皮、栀子而成。原方有疏肝解郁、养血健脾之效,主治“血虚劳倦,五心烦热,肢体疼痛,头目昏重,心忪颊赤,口燥咽干,发热盗汗,减食嗜卧;及血热相搏,月水不调,脐腹胀痛,寒热如疟;又疗室女血弱阴虚,荣卫不和,痰嗽潮热,肌体羸瘦,渐成骨蒸”;加入牡丹皮、栀子后,具有疏肝解郁健脾兼清郁热之效,主治“肝脾血虚发热,或潮热,晡热,或自汗盗汗,或头痛,目涩,或怔忡不宁,或颊赤口干,或月经不调,或肚腹作痛,或小腹重坠,水道涩痛,或肿痛出脓,内热作渴”。方中柴胡条达肝木,疏肝解郁;当归、芍药既可养血柔肝、滋养肝木,又能防止柴胡升散之过;白术、茯苓、甘草健脾益气,使脾土强健、气血生化有源;薄荷佐助柴胡,疏肝郁,散郁热;生姜可辛散郁滞之气;牡丹皮入肝胆血分,清泻血中伏火;栀子通行三焦,清热利湿,泻火除烦。诸药合用,以水涵木,培土荣木,以遂肝木之条达。
4.2 古代医家对逍遥散及丹栀逍遥散的分析研究
宋代《圣济总录·产后虚热》记载,逍遥散可用于“治产后亡阴血虚,心烦自汗,精神昏冒,心忪颊赤,口燥咽干,发热头痛,或寒热如疟”。当时,该方被认为是一首治疗妇人虚劳有热的方剂。明代薛己在《女科撮要》中多用丹栀逍遥散治疗妇科疾病,如产后大便不通、产后咳嗽、阴疮、阴口不闭、月经不调、痛经、闭经、保胎、热入血室等。明代赵献可在《医贯·郁病论》中论述郁证言:“以一方治其木郁,而诸郁皆因而愈。一方者何?逍遥散是也。”又曰:“推而伤风、伤寒、伤湿,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郁看,以逍遥散加减出入,无不获效。”由此将逍遥散列为治疗木郁之首剂。清代江笔花的《笔花医镜》言:“女科除外感内伤外,不外血虚与肝郁,所以治疗女科病,四物、逍遥二方,首当考虑。”将逍遥散为妇科病的首选方之一。清代汪昂在《医方集解》中对该方进行论述,曰:“疏逆和中,诸证自已,所以有逍遥之名。”并将逍遥散归入和解剂,凡需和解之疾病,皆可考虑逍遥散治之。逍遥散的运用范围由此扩大。清代张秉成在《成方便读》中解读丹栀逍遥散,曰:“肝属木……喜条达,必须水以涵之,土以培之之,然后得遂其生长之意。若七情内伤,或六淫外束,犯之则木郁而病变多矣。此方以当归、白芍之养血,以涵其肝;苓、术、甘草之补土,以培其本;柴胡、薄荷、煨生姜惧系辛散气升之物,以顺肝之性,而使之不郁,如是则六淫七情之邪皆治而前证岂有不愈者哉。”《删补名医方论》曰:“肝性急善怒,其气上行则顺,下行则郁,郁则火动而诸病生矣,故发于上,则头眩耳鸣而或为目赤,发于中,则胸满胁痛而或作吞酸,发于下,则少腹疼疝而或溲溺不利,发于外,则寒热往来似疟非疟,凡此诸证,何莫非肝郁之象乎,而肝木之所以郁,其说有二:一为土虚不能升木也,一为血少不能养肝也……若内热外热盛者,加丹皮解肌热,炒栀清内热,此加味逍遥散之义也。”
综上所述,古代医家对逍遥散在组方及运用的认识不断深入,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主治病证、病机不断地扩充和完善,这也促使了丹栀逍遥散的形成,以及逍遥散的不断加减变化如黑逍遥散、辛芷逍遥散、荆防逍遥散、桃红逍遥散等。
4.3 现代医家对丹栀逍遥散的分析研究
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认为,以逍遥散为基本方治疗肝硬化既能调肝健脾,又能养血,这可能与其能改善肝脏功能有一定关系。蒲辅周先生采用丹栀逍遥散治疗肝郁证高血压病、胸膜炎及颈淋巴结核,依病分别加入决明子、夏枯草、珍珠母,或青皮、郁金,或合用消瘰丸等,疗效显著。刘渡舟认为,苦寒之药非治肝郁化火之证,丹栀逍遥散之用惟在调达肝气、顺其性而治之,符合“木郁达之”之法,主治肝郁血虚、化火生热之证,临证用此方加减治疗部分奇难杂证,效果显著。国医大师王绵之认为,逍遥散具有调整肝郁、血虚、脾虚三个方面功能的作用。逍遥散在后世的发展,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加味逍遥散,即原方加入牡丹皮和栀子,以治疗血热相搏、月经不调。《方剂学》以丹栀逍遥散治疗肝郁血虚证,内有郁热证,其方证为“潮热晡热,烦躁易怒,或自汗盗汗,或头痛目涩,或颊赤口干,或月经不调,少腹胀痛,或小便涩痛,舌红苔薄黄,脉弦虚数”“两胁作痛,头痛目眩,口燥咽干,神疲食少,或月经不调,乳房胀痛,脉弦而虚”。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不断进展,丹栀逍遥散在治疗脑卒中后抑郁、乳腺癌、高血压病、眼科疾病等方面的作用不断被证实[8-11]。
4.4 国医大师张磊对丹栀逍遥散的认识
张老认为,本方重在条达肝木,并能调营血,扶中土,兼清郁热,是解郁之良剂。肝脏最刚,具有升发之性,一旦怫郁,则易化火,火旺克金,木旺克土。因此,丹栀逍遥散于调养中又寓疏通条达,再清郁热,使肝木以遂其性,则诸病得消。《黄帝内经》云:“木郁则达之,遂其曲直之性。”此之谓也。该方常用剂量如下:柴胡、当归、茯苓、白术、牡丹皮、栀子各10 g,白芍15 g,薄荷3 g,甘草6 g。本方适用于肝郁化火证,临床症见情志不畅、抑郁、焦虑、胁肋胀痛、月经不调、经期乳房胀痛、少腹胀痛、身热、盗汗、口干渴、食欲差、心烦急躁、失眠、多梦、大便干、小便黄、舌质红、苔白腻或黄厚腻、脉沉滞或弦滑或滑数,主治病证涉及习惯性流产、遗尿、失眠、慢性胆囊炎、抑郁症、焦虑症、不明原因疼痛等[12-16]。
5 病案举例
患者,女,44岁,2013年5月10日初诊。主诉:反复右胁部胀痛2年余。患者2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胁胀痛,曾自行服用西药、中成药及中药汤剂(具体不详),病情时好时差。现症:右胁部胀痛,睡眠差,早醒,情绪不佳,易焦虑,头晕,左侧耳鸣,乏力,易感疲劳,纳可,小便正常,大便干,月经后期,舌质暗红,苔黄、稍厚腻,脉沉滞。辅助检查示:①胆结石;②幽门螺杆菌(+);③乳腺增生;④总胆红素及间接胆红素增高。西医诊断:①慢性胆囊炎;②胆结石。中医诊断:①胁痛;②胆石症。中医辨证:肝郁化火证。治则:疏肝解郁,清泻郁热。方予丹栀逍遥散加减,处方:柴胡、当归、茯苓、制香附、浙贝母、牡丹皮、栀子各10 g,生白芍、蒲公英、山楂炭各15 g,红花、甘草各6 g,薄荷(后下)3 g。7剂,1剂/d,水煎服。2013年8月23日二诊:症状有改善,仍易抑郁,月经基本正常,但经前胁胀痛明显,经期小腹胀痛、双下肢痛、右胁连及后背胀痛,头晕、耳鸣减轻,偶有胃脘痛,纳可,睡眠如前,无口干苦,心悸,面部黄斑、色暗,二便正常,舌质暗,苔黄、厚腻,脉细滞。处方1:柴胡、当归、茯苓、制香附、桑叶、竹茹、丝瓜络、知母、牡丹皮、栀子各10 g,黄柏、香橼、甘草各6 g,生白芍、蒲公英15 g,薄荷(后下)3 g。20剂,非经期服用。处方2:醋延胡索、山楂炭、炙甘草各15 g,当归、制香附各10 g,生白芍30 g。5剂,经期服用。2014年3月5日三诊:右胁疼痛基本消失,仍有抑郁、焦虑感,偶感乏力疲倦,时有泛酸,纳可,睡眠较前好转,二便调,舌质淡红,苔白、稍厚,脉细滞。辅助检查示:幽门螺杆菌阴性,肝功能正常。处方:柴胡、当归、茯苓、制香附、牡丹皮、栀子10 g,生白芍15 g,百合30 g,甘草6 g,薄荷(后下)3 g。继服20剂。2018年5月11日四诊:诸症基本消失,稍有抑郁、焦虑感,偶有乏力、多梦,余无不适。三诊方再服10剂。随访3个月,病情稳定。
按 患者以右胁部胀痛为主症,平素因琐事而易导致情绪不稳,长期情志不舒导致肝失疏泄,气机不畅,肝气郁结,形成气郁,气滞则易致胸胁部胀痛;滞于右胁部,发为右胁胀痛;滞于胸部,发为乳房胀痛;滞于少腹,则少腹胀痛、经行不畅、痛经。气郁日久而化火,热扰动心神,可见心烦、失眠、多梦;热易伤津,可见大便干、舌苔黄。肝木郁而犯脾土,脾失健运,气血生化不足,可见头晕、乏力、耳鸣、易感疲劳、脉沉滞等。张老遵“木郁则达之,遂其曲直之性”之宗旨,以丹栀逍遥散条达肝木,调养营血,培补中土,兼清郁热,以遂肝木条达之性。该方具有疏肝健脾、清散郁热的功效,实属“和”法之用[17-18]。肝木疏通条达,气机通畅,郁滞渐消,肝木既达,脾土得以复健,气血有生化之源,气血可复,则诸症悉除,疗效显著。
6 小 结
丹栀逍遥散是治疗肝郁化火证的一首经典方剂,临床疗效确切,诊治疾病十分广泛。随着历代医家对其方药配伍、主治病证的研究不断深入,目前该方的主治病证可涉及妇科、消化科、神经科、风湿免疫科、耳鼻咽喉科等疾病属肝郁化火证者[19-24]。张老认为,丹栀逍遥散是解郁之良方,其功用为疏肝健脾、清散郁热,补不恋邪,清泻而不伤正,实属“和”法之用。张老在中医学经典理论的指导下,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以“木郁则达之,遂其曲直之性”为准则,采用丹栀逍遥散治疗慢性胆囊炎,以达肝木之郁,培补中土,兼清郁热,寓疏中有养、养中有清,故获良效。张老强调,情志致病,木土壅滞,症状繁多,壅滞日久可变生多种病理产物,因此,临证用方还需辨清病情,切中病机,方能取效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