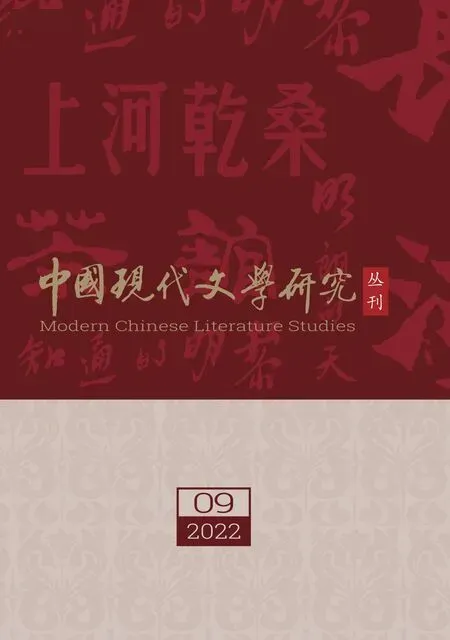“近未来”书写的审美形态及其对科幻小说的观念变革※
——郝景芳小说论
刘永春
内容提要:郝景芳的小说创作以独特的“近未来”书写连接社会现实与未来,形成了对中国科幻新浪潮小说形态与观念的新超越。在叙事上,郝景芳小说的“近未来”书写主要塑造贴近现实的叙事场景、生活内容;在主题上,其对(后)人性的思考充满历史意识,对社会现实充满反思意识;在观念上,郝景芳小说减少了类型化特征,推动科幻文学与雅文学有机融合。郝景芳小说以其具有鲜明特色的“近未来”书写创造了新的审美形态,对科幻小说的理论观念进行了变革。
历史、现实、未来,是科幻小说与传统主流文学共同面对的叙事境域,但科幻小说更需要,更善于,更集中于勾画中国社会从现实走向未来的路径及其后果,未来性场景的建构与塑造乃是科幻小说的先天职责。值得注意的是,自1999年开始的中国科幻新浪潮中,大多数科幻作家关注的乃是“远未来”,甚至是整个宇宙尺度之下遥远的人类未来。整个人类文明、中国社会乃至某个现实地域怎样逐渐从现实过渡到未来,则是大多数科幻作家有意回避的。在“硬科幻”作为总体特征,技术主义作为显性面貌的路径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的未来性”与“未来的现实性”两个维度均未得到有效展开,科幻新浪潮处理的仍然是传统主题,虽然各个面貌不同但总体主旨更接近于主流文学的宏大叙事模式。在此背景下出现的郝景芳小说显示出了不同的路径与方法,其结论也与科幻新浪潮的主要作家们有着重要分判。与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硬科幻”“远未来”写作风格不同,①朱颖琦、刘延霞:《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科学叙事艺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郝景芳以独特的“近未来”书写确立了自己的诗学立场,尤其是努力超越启蒙主题与宏大叙事,形成了属于自己主题领域与叙事模式,从而与中国科幻新浪潮建构起了对话关系。因其“近未来”书写,郝景芳在文体和观念两个方面对中国科幻小说都形成了变革性的突破。
一 “近未来”书写及其产生背景
美籍韩裔学者朱瑞瑛(Seo-Young Chu)对科幻文学做出的描述性定义广为人知:“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摹仿性话语(mimetic discourse),它再现的对象是非想象性的,尽管它在认知上也是陌生化的。”②Seo-Young Chu: Do Metaphors Dream of Literal Sleep? A Science-Fiction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转引自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09页。在这个定义模式中,以“陌生化的”“摹仿性话语”“再现”“非想象性”的现实是科幻小说的本质特征与存在方式。换言之,科幻小说建立在已知的各种社会现实基础上,与传统主流文学的区别仅仅在于,其表现社会现实的方式是“摹仿性”和“陌生化”的。如果进一步推究,即使在“摹仿性”与“陌生化”两个维度,科幻小说与传统主流文学仍然是相通的,或许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此种定义方式已经内含了科幻文学接近传统主流文学的最重要路径。
科幻文学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陆士谔的《新中国》等文本无不成为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装置。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科幻第三次浪潮在对社会现实进行话语呈现方面的尝试与成功同样引人瞩目。刘慈欣的《中国2185》被视为此次浪潮的滥觞之作,其中的“华夏共和国”集中了刘慈欣复杂多元的文化政治想象;王晋康的《转生的巨人》《蚁生》以多层隐喻的形式隐晦地表达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忧思;韩松的短篇小说《再生砖》《我的祖国不做梦》(未发表)、长篇小说《地铁》《高铁》《轨道》三部曲与《医院》《驱魔》《亡灵》三部曲等作品无不将现实忧思转化为层层意象覆盖之下的诡异诗学,将中国的现实忧患与未来可能等命题作为小说最核心的话语场域。在此基础上,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在现实反思与未来想象之间产生出了越来越多的经典文本,以“韩慈康”(韩松、刘慈欣、王晋康)为代表的科幻作家们逐渐建构起了对“中国必将崛起”的文化信心与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神话”的文化解构两种相辅相成的书写模式。
“尖锐的社会批评意识”与宏大叙事中的未来想象两种看似矛盾的主题、姿态、路径糅合成为绵延二十余年的科幻新浪潮的主要诗学特征。在其催化之下,“硬科幻”成为首选和常态,批判现实但不纠缠现实,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不盲目乐观的文化立场导致以“韩慈康”为代表的作家们更多将叙事笔触伸向遥远的未来。这种模式既是中国科幻传统的进化结果,也来源于民族国家想象的核心主题;既可以形成现实反思与未来书写间的叙事张力,也可以与意识形态之间同时保持距离与合作;既可以便利地呈现“技术的权力”与“权力的技术”,也可以形成跌宕起伏、婉转多姿的人类命运图景。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所引起的极大关注来源于这种总体性的诗学背景及其形成的接受视域,但也存在诸多重要差异。小说中三个空间的折叠与轮换映射出未来人类的人群分布与阶级界限,尤其是将“空间”本身视作未来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成为城市生态结构分析的基本手段。老刀的穿越过程更像是一次各阶级生活状态展示,其自身身份成为社会剖析的一把利刃。“老刀短暂的穿越之旅,本质上更是一次自身身份符号的验证过程。他的身上始终贴加着第三空间底层工人的符码和烙印。”①霍国安:《论郝景芳〈北京折叠〉的空间叙事艺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小说中逼迫老刀铤而走险的故事起点却是女儿糖糖的入园难问题。这个“救救孩子”式的诉求以老刀父子两代人的垃圾分类工职业作为背景,也是整个叙事的逻辑起点,寄希望于孩子将来能改变自己所属社会空间和族群身份。在主题层面,小说将七环以内的北京划分为三个空间结构,以此来探讨“近未来”社会中科技发展所导致的失业问题。现实北京与未来北京在这种焦虑里顺利实现合体,现实反思透过未来想象得到了有效释放。
郝景芳是最为关注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当代中国科幻作家之一。人类与人工智能(AI)的对立与交融是其连接当下现实与“近未来”人类场景,探索(后)人性,建构后人类美学的主要叙事路径。弥漫在郝景芳小说中“近未来”世界的本体性特征主要有两个:“孤独”“彼岸”。对于郝景芳来说,面对“近未来”时的“孤独”既是个体性、审美性的,也是普遍性、哲学性的,既来源于“未来的现实性”也来源于“现实的未来性”。这种“孤独”气质虽然遍布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但在郝景芳这里则具有更强烈的主体性,甚至构成其叙事结构的最核心动力与最显在特征。在一个以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对立交融作为主要特征的“近未来”之中,(个体与群体意义上的)“人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这样的时刻,世界兼具现实性与未来性,人类本身作为世界的建造者/建造结果,同时也在体验着这种“边缘”处境中的“孤独”——在时间意义上,“近过去”与“近未来”的裂变促使人性产生变异;在空间意义上,个体命运与人类命运的纠结使得个体自我的内涵与外延都产生了重大变化。因而,郝景芳十分准确地意识到这种“最孤独的孤独”在整个人类历史与文明这一科幻文学最宏大的叙事尺度上具有界碑性的意义,其具体形态表现为“出世和异化”。可见,“孤独”“出世”“异化”这些常见的世俗伦理范畴在郝景芳小说里自然而然地转变成为在整个人类文明尺度上思考如何连接“现实的未来性”与“未来的现实性”的有效途径,也成为郝景芳在小说中建构“近未来”的主要方式。
二 “近未来”书写的诗学特征
与传统的“硬科幻”相比,“近未来”书写更侧重对现实的结构分析与人性反思,虽然这种解构多是通过“未来的现实性”进入“现实的未来性”,但其与现实和未来的时空距离、文化距离都极大缩小,甚至努力弥合两者间的缝隙,使得郝景芳小说中的现实与未来往往成为硬币的两面,彼此依存,共生共长。
与现实世界差距很小的故事场景是郝景芳“近未来”叙事的外在特征。郝景芳较少历时性地表现大时段的宇宙演化史,而更多将小说情节设置在某个较近的时空之中。《北京折叠》中的北京除了三个空间的轮番折叠之外几乎就是现实北京的镜面投影,作者为了增强“未来的现实性”还特意写了从父亲到老刀的职业传承。“城一代”的父亲与“城二代”的老刀的命运形成强烈的互文结构与隐喻空间,共同指向当下中国那如疾驶的火车一般的城市化进程。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在三个空间之间,在虚无与意义之间,老刀的命运折射了社会底层在后人类时代必然面对的“卑微生活”,同时也指向现实世界里业已存在的阶层固化与底层窘境。一个并不遥远的北京及其城市面貌使得这篇小说在主题层面同时指向未来与现实两个方向。《北京折叠》在现实与未来的互相隐喻之中达成了微妙的平衡,使得整篇小说的主旨从个体命运上升为群体命运,老刀的遭遇才同时具有了“孤独的历史”与“历史的孤独”两个层面的丰富意义。
与现实生活差距很小的生活内容是郝景芳“近未来”叙事的主要表现形态。她极少表现长时间跨度、大宇宙视野或者高科技远景,相反,其小说中的“近未来”充满现实感,人物形象的生活方式与行为逻辑与现实世界并无太大差异,其情节结构与性格塑造手法与传统文学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这固然与郝景芳擅长中短篇写作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来源于其对科幻文学的理解与追求。在郝景芳的理解中,自己作品属于“无类型文学”,介于纯文学(或主流文学)与科幻文学(或奇幻文学)之间。她将自己的叙事场景大量放置在“近未来”的日常性生活形态之中,对“远未来”的高科技进行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则不是她的目标。“近未来”叙事的树干与枝叶紧靠现实之根、人性之根,只能以日常性作为主要形式。郝景芳极力论证优秀的作品都是“将现实放在虚幻的大框架下”,由此而产生的“虚幻现实可以让现实以更纯净的方式凸显出来。虚幻的意义在于抽象,将事物和事情的关系用抽象表现,从而使其特征更加纯粹”。①郝景芳:《去远方·前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在现实与未来的关系上,郝景芳显然是以未来为手段,以现实为本位的,未来是现实的投影而不是现实的变形与夸张。“近未来”场景的实质仍然在于其对当下现实的深刻呈现,惟其如此,郝景芳理解中的“虚幻现实”才能成为科幻小说的核心要素。荒诞的想象仅仅是郝景芳反思社会现实的路径与形式,现实本身的荒诞才是小说的反思对象。
对郝景芳而言,科幻文学主要是“再现”的,而不是“表现”的,因而其“隐喻”或者“抽象”也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的,从而也就不再是宏大叙事的。在硬科幻、高科技、宇宙尺度当道的时代,郝景芳在“情节化”与“意象化”中更倾向于后者。显然,这些构成郝景芳小说主要场景与核心目标的“抽象的意象”更多的来自于其对社会现实的深切体认与对人性结构的复杂辨析,更多的来自于“尖锐的社会批评意识”。因此,郝景芳将现实与未来进行叙事连接的路径与“韩慈康”等主流科幻作家存在着重要的观念分歧与路径差异。其对人类主体(性)的哲学基础与建构方法自然也有较大差异。
三 “近未来”书写的诗学意义
对于科幻小说而言,如何处理未来与现实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着力于“远未来”的“韩慈康”,还是执着于“近未来”的郝景芳,其共同美学任务皆是建立一个融“现实的未来性”与“未来的现实性”于一体的叙事构架。郝景芳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不断尝试通过“近未来”贴近现实生活中的人性,贴近人类面临的最切近与最切身的挑战,以此重构科幻小说与社会现实的审美关系。尤其是,郝景芳以此来确认自己对科幻小说的类型定位、功能定位、价值定位,确立自身与中国科幻新浪潮的承续与变革关系,确证自身的审美立场、叙事模式与历史属性。因此,可以从进入未来的角度与方式、想象未来的依据与模式、塑造人物的层次与方法等方面来理解郝景芳所建构的“近未来”书写所具有的诗学意义及其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观念的创造性转换。
“近未来”书写使得郝景芳小说超越了简单的故事层面,进一步深入社会现实与(后)人性之中,其主题空间往往曲折幽深且充满思辨色彩。在此情况下,外星技术的炫目多彩、故事走向的诡异多变、星际战争的残酷惨烈等因素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甚至,郝景芳在小说中有意回避这些科幻传统中常见的情节模式。人类甚至后人类在面对社会现实与智能技术时的孤独无助与自我反思才是其小说的主题重心。在此意义上,郝景芳小说接续了中国科幻新浪潮的人文主义色彩与哲学高度,却将小说叙事深深移植到更具现实性的土壤之中,以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切入“现实的未来性”,通过(后)人性分析与现实反思的完形作用最终获取“未来的现实性”。
从人类时代到智能时代,从人类到后人类,从人性到后人性,郝景芳特别关注过渡过程的起点、动力、特征、结果、意义等方面的问题。这部分小说可以视作郝景芳的“问题小说”。《弦歌》里的陈君在地球人类准备与月球上的钢铁人同归于尽的历史性时刻却对人性中总是习惯于屈服的特征做出了深刻反思。“人活在大地上,充满劳绩,却诗意地栖居。这话说得太抒情。人往往是带着睡意栖居的,醒来也仍在睡。当梦魇来临被惊醒之后,人们用自我催眠的办法继续睡去。睡去比醒来好过得多,睡去之后,生活的一切都可以容忍。惊恐可以容忍,屈服可以容忍,限制的自由也可以容忍。”①郝景芳:《弦歌》,《孤独深处》,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2页。从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出发,郝景芳看到的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过度“容忍”,是将主体性主动交付给更强大的主宰者从而获得暂时的“限制的自由”。郝景芳小说着力书写的不是未来性的场景与情节,而是充满思辨性的、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以及由此展开的对人性与后人性的深入反思。
郝景芳小说中的另一种主题类型则是直接的现实反思,小说集《长生塔》中的作品最为典型。这些作品中的高科技因素都只是时代背景,而后人类时代的社会现实及其对(后)人性造成的巨大影响才是小说着力展开的叙事视界。在文体类型上,这些小说已经不再属于科幻小说范畴,变成了带有科幻因素的非科幻文本。《长生塔》中除了不断长高的那座长生塔,其余的情节都围绕着乡村的拆迁展开,由此书写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命运悲剧。长生塔只有象征意义,与人物命运、故事走向以及主题内蕴都没有关系。长生塔是人性欲望的外化,它的不停生长代表的则是人类欲望的无休无止。小说集《长生塔》及其中的作品,对郝景芳的创作而言,意味着潜藏在以往作品中的现实反思倾向与主题从文本深处浮现了出来,强烈的社会关注淡化了科幻色彩,脱去了类型文学的外在形态,转而向传统的主流文学靠拢。尤其是,明显的底层叙事特征与反思立场,辅之以沉重的思辨性叙事风格,郝景芳小说与经典的科幻叙事已经渐行渐远。
“近未来”书写使得郝景芳小说超越了经典科幻小说的叙事模式与文体特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体类型。郝景芳在科幻小说中熔铸了自己独特的小说观念,在形成自己独特的文本形态的同时也建构起了与“韩慈康”迥异的观念形态。因此,郝景芳的“近未来”书写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而言具有叙事与观念上的双重变革意义。
首先,郝景芳的“近未来”书写采用了从现实进入未来的独特角度与方式。经典的科幻叙事往往从宏大的时代背景和技术背景开始,人物及其生活往往是某个特定未来时空的注脚。郝景芳通常直接进入小说的情节与人物中去,直接展开小说的精神分析与存在追问。在《北京折叠》开始的那一刻,“清晨四点五十分,老刀穿过熙熙攘攘的步行街,去找彭蠡”①郝景芳:《北京折叠》,《孤独深处》,第1页。。此后,小说进入老刀的日常生活场景,直到后面才介绍了折叠城市的运作方式。这并不仅仅是叙事层面的技术问题,而且关系到作者对小说叙事的整体把握,涉及小说主题的设定,更来自于作者对科技与人文关系的衡量与选择。这样的叙事模式更接近传统主流文学处理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方式,其中的人文精神与哲学意识也就更加充盈流荡。
其次,郝景芳通过“近未来”书写改变了经典科幻小说重故事,轻人物,重传奇,轻心理,重场面,轻细节的常见特征,转而以细腻深入的人物刻画塑造饱含情绪特征与个性色彩的立体、丰润、自足的人物形象。“远未来”书写由于需要覆盖更高、更远的时空尺度,其叙事节奏往往需要保持较快的频率,其叙事单元里所需要的人物数量往往远超传统文学。“近未来”书写则可以从容地展开情节,塑造人物。郝景芳小说关注的多数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在无望的抵抗中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价值,因而其心理世界往往显得沉滞凝重。《永生医院》里的钱睿得知自己也是克隆人的事实时,人物心理的突然转变构成了小说最大的戏剧性之所在。小说写了他三次激烈的情绪反应,到了最后一次:“钱睿疯狂地摇头,他觉得自己的神经快要错乱了,心中大骇,他本能地后退,拒绝,他不想听,还想回到从未听说过这个消息的时间里。他无法理解自己听到的消息。怎么突然之间,他就成了那个他想要揭穿的身份?”②郝景芳:《永生医院》,《长生塔》,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6页。这段心理描写既符合钱睿克隆人的身份特征,也在情节最激烈转折的关节点上对小说主题产生了重要的呈现作用,在小说中是必不可少的精彩部分。人物形象塑造,是郝景芳小说的重心,而“问题”与“个性”则是触发点,科幻是为故事服务的。这些观念都具体落实到了其小说创作实践中,形成了郝景芳小说独特的叙事模式。
最后,“近未来”书写使得郝景芳小说呈现为“问题导向”,而非“故事导向”。这种“问题小说”模式能够有效地连接现实与未来,为科幻文学创造了新的文体观念和结构形态。“《北京折叠》与其说是科幻,不如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社会隐喻:顶层操控规则,中层高节奏工作,而底层的穷人,将连被剥削的价值都不再会有。”①杜丽花:《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阶层区隔——基于〈北京折叠〉哲学反思》,《改革与开放》2016年第22期。《长生塔》对拆迁问题,《永生医院》对克隆人问题,《生死域》对生命本身的价值问题,《积极砖块》对社会的单向化与制度化问题的思考,都不可谓不深刻。此外,郝景芳对人类/后人类与人工智能之关系的思考也是当前中国科幻作家中用力最多的。这个主题倾向集中反映在其小说集《人之彼岸》的六篇“科幻故事”和两篇“非科幻思考”中。从具体问题出发,指向人性深处,而非从某种民族性叙事模式、某种启蒙/反启蒙观念出发走进流行的宏大叙事,这种反抗硬科幻的非技术主义路线是郝景芳小说“近未来”书写的核心形态与倾向,也是其小说诗学的核心特征。正是这种观念形态使得郝景芳小说与中国科幻新浪潮形成了最大的审美区隔。
郝景芳小说“既有向下的对当下社会民生与人们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又有向上的在哲学和文化领域对世界和宇宙进行纵深的探索与追问,这两种写作方式交叉并行,共同构成了郝景芳科幻小说的独特内涵与图式”②孙涛:《孤独深处的对抗与求索——评郝景芳科幻小说集〈孤独深处〉》,《百家评论》2017年第4期。。独特的“近未来”书写是郝景芳将两种路径结合起来的具体方式。郝景芳小说的突破性意义不仅在于其“近未来”书写创造的细节性景观、人物塑造深度与叙事结构形态,更在于其对科幻小说观念的突破,对科幻小说反思人性、反思社会问题的功能的深度确认。在此意义上,郝景芳使得科幻小说减少了类型化特征,向着雅文学传统进一步靠拢。尤其是其小说中对“现实的未来性”与“未来的现实性”诸种问题的思考与雅文学中的精英意识有着相似的精神结构与呈现方式。可以认为,郝景芳的小说创作在当代科幻文学由俗入雅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最核心的推动力量。
结 语
不管具体表述怎样变化,郝景芳的小说创作始终紧紧围绕中国社会如何从现实过渡到未来这个主题,不断从“现实的未来性”与“未来的现实性”两个维度建构自己的诗学路径,其小说不断想象与刻绘的“近未来”图景,“后人类美学”与“类主体”镜像则是其与中国科幻新浪潮中大多数作家的最鲜明差异。只有在这个维度上,其小说创作内部的历时性变迁与共时性拓展,其小说诗学的难以归类,其小说的想象冲动与现实执念等问题才可以得到合理解释。更重要的是,在处理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关系这一整体性、贯穿性主题的时候,郝景芳并没有遵循简单的进化规律,从不将未来简单视作现实的替代与新生,也从未将现实视作未来的记忆与阻力。相反,她的小说总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合理的逻辑关系、技术路线与价值更替,她将现实与未来视作互相连接的两个文本,彼此对照,互相生成。与“韩慈康”等相比,郝景芳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尤为执着,也更为有效、动人。
对于科幻文学要尽力贴近现实这种倾向,郝景芳是有着清楚认识的,在比较中外科幻文学的差异时,她认为:“从内容上看,国外的科幻小说一方面与科学前沿结合得更紧,另一方面有很深的读者基础,作者在创造新世界、新空间的时候可以更加大胆创新。而国内还是那些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小说读者面才会广一点。”①李苑:《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幻文学》,《光明日报》2016年8月9日第11版。可见,“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小说”是郝景芳自觉的叙事追求与审美理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汹涌奔腾的中国科幻新浪潮背景下,郝景芳在科幻小说的叙事模式、主题空间、诗学观念、价值立场等方面都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与突破,既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体形态,也使得科幻文学渐渐脱离其类型化、理念化、技术化的叙事样态与观念范式,将科幻文学的由俗入雅向前推动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