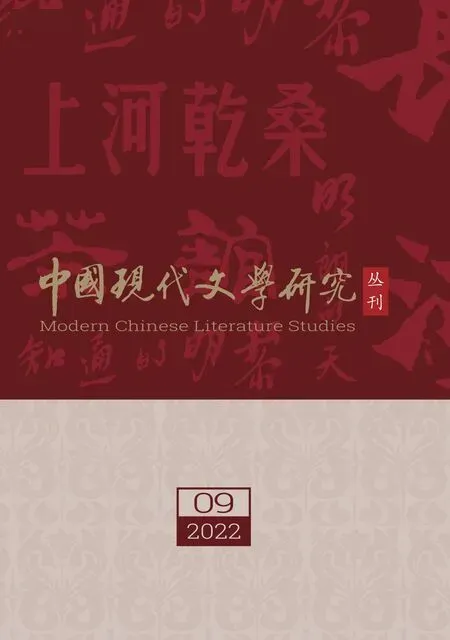2005年版《鲁迅全集》日记卷正文勘误
朱文健
内容提要:所有版本的《鲁迅日记》和所有版本的《鲁迅全集》日记卷正文部分都有不少讹误,2005年版依然如此。这些讹误既有编排上的失误,也有鲁迅日记手稿本身存在的笔误未被发现并校改。该文在理解、保持编排原则的基础上对所有编排的错误逐一进行校改,又结合相关资料对鲁迅日记手稿的错误逐一进行辨析和纠正。
在现代作家全集中,《鲁迅全集》版本多,编校质量相对较高。随着研究的深入及史料的发掘,新的研究成果又不断使得《鲁迅全集》新版本更准确、完善、可靠。2005年版《鲁迅全集》是目前通行的权威版本,但这一版本依然存在不少错讹。①笔者发现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不同印次之间也存在差异,因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2005年版2016年第6次印刷本为校改底本。笔者发现,仅以日记卷的正文而言,就有较多编排上的失误,也有不少日记手稿原文的笔误未被发现。这些错误无疑会影响读者对鲁迅日记的研读与理解,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全面、完整的校改。
一 对编排失误的纠正
鲁迅日记手稿原文存在很多笔误,《鲁迅全集》日记卷对此的编辑原则是:“手稿中的笔误,以下列方式订正:误字(包括颠倒),加[]号,排仿宋体;漏字,加〔〕号,排仿宋体;衍字,加〖〗号,不变字体;存疑,用[?]号;个别西文或日文讹误则径予订正,不作标示。”①见《鲁迅全集》第15卷卷首“说明”。
(一)误字编排
由编辑规则可知,在校正鲁迅手稿原有的误字时,须“加[]号,排仿宋体”。而核校鲁迅日记手稿原文后,笔者发现下列误字均被直接校正而未遵循此原则,不妥当,应予改正。
1913年1月8日:“晚得二弟信,一月四日发(1)。”编号应处理为“(一[1])”。
1913年5月21日的“《陶庵梦忆》”应处理为“《陶庵梦意[忆]》”。
1913年9月12日:“下午得二弟信,五日发(9)。”编号应处理为“(九[9])”。
1913年11月22日的“《郡斋读书志》”应处理为“《郡齐[斋]读书志》”。类似的情况还有四处,应一并处理:1916年4月15日“青云阁步云齐[斋]”,9月6日“震古齐[斋]”,1917年12月30日“端匋齐[斋]”,1918年2月24日“德古齐[斋]”。
1914年3月8日的“四日发(16)”,编号应处理为“(十六[16])”。
1921年9月30日的“季巿赠《越缦堂日记》一部”正确,但应处理为“季巿购[赠]”。
1925年2月11日的“夜伏园来”正确,但应处理为“衣[夜]伏园来”。
此外,对鲁迅日记手稿原文误字的校改,还有一些不到位之处:
1924年2月16日:“晚寄胡适之信并百卅[卄]回本《水浒传》一部。”括号文字“卄”是对手稿原文“丗”的校改,不妥,应为“卅[廿]”。
(二)漏字编排
在对鲁迅手稿遗漏的文字进行添补时,须“加〔〕号,排仿宋体”。而核校日记手稿后,笔者发现下列漏字均被直接增补而未遵循此原则,应予改正。
1920年9月24日的“戴螺舲”应处理为“戴螺〔舲〕”。
1926年8月22日的“李遇安”应处理为“李遇〔安〕”。
1928年5月26日的“得小峰信”应处理为“得小峰〔信〕”。
1933年1月28日的“夜蕴如及三弟来”应为“夜蕴如及〔三〕弟来”。
1934年3月19日的“晚三弟来并为取得《四部丛刊》续编二种共三本”应处理为“晚三弟来并为〔取得〕《四部丛刊》续编二种共三本”。
1935年3月22日的“罗清桢”应处理为“罗〔清〕桢”。
(三)简化字编排
鲁迅日记手稿中有很多古字,编辑对此的原则是:“手稿中的古字,除必要保存者外,都已改为现行通用字。”①见《鲁迅全集》第15卷卷首“说明”。而笔者核校鲁迅日记手稿原文后,发现《鲁迅全集》日记卷对鲁迅原稿某些字的简化不妥当或有误。
某些字不能或不需简化却被简化,如:
1918年7月13日的“粘”字,原稿为“黏”,现仍通用,应保留。
1920年12月26日、1923年1月7日、1933年3月21日、1936年1月17日、7月1日五处的“桔”字,原稿均为“橘”。“橘”曾被要求简化为“桔”,后该要求又被废除,故应将这五处的“桔”恢复为“橘”。
某些字应简化而未简化,如:
1916年1月29日的“緟出”和1919年3月3日的“无复緟者”,这两处的“緟”都意指“重复”,应简化为“重”。
1929年5月23日的“蒐罗”应按惯例简化为“搜罗”。
1934年1月6日的“鉤沈”应按惯例简化为“钩沉”。
对某些字的简化有误或不妥,如:
1913年2月2日、3月30日、4月6日的“王(君)懋熔”,手稿原文最后一字均为“鎔”。由1993年发布的《关于“鎔”字使用问题的批复》及2019年版《通用规范汉字表》可知,“鎔”字应处理为“镕”。故这三处都应作此处理。
1915年9月12日及30日的“流沙队简”,手稿原文第三字均为“隊”。该字既可直接简化为“队”,也可先视作“墜”的本字再简化为“坠”,此处当然应该取后者。故应处理为“流沙坠简”。
(四)标点不妥或有误
鲁迅日记手稿并无标点,自1959年版《鲁迅日记》起,编者对其进行标点,其后各版均作此处理。2005年版《鲁迅全集》日记卷是标点本,但笔者发现其中部分内容的标点违背统一的编辑惯例,故依次校改于下。
1912年11月17日“元《阎仲彬惠山复隐图》”,据原书,应改为“《元阎仲彬惠山复隐图》”。
1913年4月19日“叶氏《观古堂汇刻书并所著书》一部”,据原书,应改为“叶氏《观古堂汇刻书》并《所著书》一部”。
1914年1月18日的“《江苏江宁乡土教科书》”,据原书,应改为“江苏、江宁《乡土教科书》”。
1914年9月17日“《十八空百广百论合刻》一本”,应按惯例改为“《十八空、百、广百论》合刻一本”。
1915年7月7日“《同州舍利塔额》一枚”,应改为“《同州舍利塔》额一枚”
1915年12月5日“《关胜颂德碑》,《比丘道造象记》拓本各一枚”,逗号应改为顿号。
1916年1月2日“《吴谷朗碑》”,“吴”指三国孙吴,应在书名号外。
1916年1月13日“《吴葛祚碑》”,“吴”指三国孙吴,应在书名号外。
1916年2月27日“《魏珍碑》”,“魏”指北魏,应在书名号外。
1916年5月7日:“又买《吹角坝摩厓》一枚,二元;《朱鲔室画象》十五枚;杂山东残画象四枚,五元;杂六朝小造象十六枚,三元……”由本日书账可知,朱鲔石室画象十五枚是四元,杂汉画象四枚是一元,即它们的总价为“五元”。故正文应处理为“《朱鲔室画象》十五枚,杂山东残画象四枚,五元”。
1916年5月14日和1923年11月25日的“《魏三体石经》”,“魏”指三国曹魏,应在书名号外。
1917年5月6日“《隶释》、《隶续》附汪本《隶释刊误》”,据原书,应改为“《隶释》、《隶续》附《〈汪本隶释〉刊误》”。
1918年7月9日的“《汉黄肠石题刻》”,“汉”指汉代,应在书名号外。
1921年1月26日:“买得《元勰墓志》,《元详墓志》各一枚,共二元。”应处理为“买得《元勰墓志》、《元详墓志》各一枚”。
(五)未按惯例作日文化处理
鲁迅记载了一些日文用语,也购买了很多日文书,为示区别,日记卷编者都作日文化处理。笔者发现下列内容未作此处理或处理不当,应按惯例校正。
1918年7月31日的“引换”是日语,应处理为“引換”。
1921年11月29日的“《现代》杂志”和12月31日的“《現代》杂志”是同一本日文杂志,应统一为“《現代》杂志”。
1926年4月17日的“《支那游記》”应处理为“《支那遊記》”。
1928年12月27日的“《板画の作り方》”应处理为“《板 の作り方》”。
1929年7月22日的“《观光纪游》”应处理为“《観光紀遊》”。
1932年5月2日的“《友达》”应处理为“《友達》”。
1932年5月6日、30日的“《古东多卍》”应处理为“《古東多卍》”。
1933年1月9日、12日的“《鲁迅全集》”是日译本,应为“《魯迅全集》”。
1933年9月21日的“《猟人日记》”应处理为“《猟人日記》”。
1934年7月12日的“《陣中の竖琴》”应处理为“《陣中の豎琴》”。
1935年11月8日的“《越天乐》”是日文书,应处理为“《越天楽》”。
(六)体例不统一
鲁迅手稿有些用字习惯并不统一,而日记卷编者对此的处理规则是:若无误,则保留;若有误,则统一为正确的字。下列内容不符合此规则,当改。
1912年7月16日的“六十元”,按惯例,应保持原稿的“六十圆”。
1912年11月17日的“文征明”和1914年11月29日的“文徵明”,手稿原文均为“文徵明”,可统一处理为“文徵明”。
1912年11月17日的“仇十洲”和1914年11月29日的“仇十州”,应统一处理为“仇十洲”。
1913年1月2日:“午后寄二弟信(一)。”应保持原稿的“(弌)”。
1913年12月19日的“上午寄东京羽太家家信”和1917年10月20日的“午后得东京羽太家〖家〗信”,这两处的原稿都是“羽太家家信”,而编者只按惯例校改了后者,却遗漏了前者,应统一。
此外,鲁迅每年日记都有相应的书账手稿,第15卷目录将书账原样抄录,无误;而第16卷目录却处理为“附书账”,既与手稿原文不同,也未统一体例。
(七)误改手稿原字
1912年11月17日的“《王小梅人物册》”,手稿为“《王小某人物册》”。查该书可知其题名与手稿相同,将“某”改为“梅”有误,应还原。
1915年9月19日的“《郑厂所藏泥封[封泥]》”,10月7日的“《郑厂所臧泥封[封泥]》”,手稿最后两字均为“泥封”。查该书可知其题名与手稿相同,将“泥封”校改为“封泥”有误,应还原。
1916年1月22日的“晋立《太公吕望表》”,手稿原文为“晋立《大公吕望表》”。查鲁迅对该拓片的录碑手稿,可知碑文就是“大公”①见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第23卷《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碑铭(中)》,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2页。,日记手稿所记正确,将“大公”直接校改为“太公”有误,应还原。
1916年2月19日的“《讳昜墓志》”,手稿原文第二字为“”。查鲁迅对该拓片的录碑手稿,可知原碑确实为“”,而该字即为“堕”。②见《鲁迅大全集》第28卷《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墓志(下)》,第267~268页。故本处应处理为“《讳堕墓志》”。
1918年6月4日的“券三十六元”,手稿原文为“券丗六元”,而鲁迅习惯将“卅”写成“丗”,故本处应按惯例处理为“券卅六元”。
(八)误看或误排手稿原字
1914年1月12日的“上午寄二弟书〖书〗籍二包”,手稿原初为“上午寄二书弟书籍二包”,后鲁迅对前一个“书”字画上小圆圈,表示删去此字。故原稿就是“上午寄二弟书籍二包”,无误,保留即可。
1915年4月1日的“上午得二第信”,手稿为“二弟”,当改正。
1925年4月27日的“静衣”,手稿原文为“静农”,当改正。
1927年4月21日和23日的“龚玨”,手稿原文均为“龚珏”。据查,此人是一位画家,曾与孙福熙、艾青同船赴法国学画。1932年3月10日病逝于巴黎,稍后的两篇纪念文章都说明他的名字就是“龚珏”。①苔:《画家龚珏逝世》,《南华文艺》第1卷第7、8号合刊,1932年4月16日;陈醉云:《艺术家之死——悼我们的故友龚珏》,《南华文艺》第1卷第9、10号合刊,1932年5月16日。故鲁迅原稿无误。
1933年5月18日“晚大雨一阵”,1934年8月15日“下午雨一陈”,1935年8月10日“午后复雨一陈即晴”,这三处的手稿原文依次为“一陈”“一陣”“一陣”,应按惯例处理为“一陈”“一阵”“一阵”。
1936年7月10日:“内山夫人之父自宇治来,赠海婴五色豆、综合花火合一合,赠以荔枝一筐。”手稿原文为“各一合”。“五色豆”和“综合花火”都是日本宇治市的特产,但前者为食物而后者为烟花,不可能合装一盒。故本处应保持手稿原样,处理为“各一合”。
(九)遗漏手稿原字
1912年10月31日,11月4日、9日、13日上标有阿拉伯数字“1、2、3、4”,11月1日、6日、10日、15日上标有汉字数字“壹、弍、弎、四”。经考察,这是鲁迅对信件最早的编号,前者与11月16日的“晚得二弟并二弟妇信,十一日发(5)”相连,后者与11月17日的“寄二弟信并银五十元(五)”相连。编者不查,未解其意,径直将这些信件编号删去,不妥。笔者认为,可按惯例将这些编号放在其本日书信后。
1912年12月8日:“午后寄二弟信(十),《古学汇刊》第一、二编共四册。”手稿原文中“古学汇刊”前有“又”字,应补上。
1920年7月31日:“无事。”手稿原初为“晴星期休息无事”,后来鲁迅发现该日并非星期日,就用加圆圈的方式将“晴星期休息”删去。但随后他又加粗“晴”字的笔画,将圆圈隐去以保留该字。故本处应处理为“晴。无事。”
(十)校勘底本质量不佳
笔者曾请教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日记卷编者,得知他们在编辑、校勘时所用的手稿底本都是1951年版影印本,遇有疑问则查阅鲁迅日记原稿。而受限于印刷技术,1951年版手稿影印本存在不少讹漏,导致编辑也产生了相应的问题:一是遗漏手稿原字,编者就以补字符号“〔〕”进行校改,而本无须校改;二是遗漏手稿的删字符号——字上小圆圈或字右两点,编者就以衍字符号“〖〗”进行校改或存疑符号“[?]”表存疑,而本可直接删去;三是遗漏手稿原有的换位符号——字右小竖线,编者就以“[]”改正颠倒,而实际上无须校改;四是漏印或衍印手稿的笔画,编者也以“[]”改正,而实际上无须校改。笔者以文物出版社1979—1983年《鲁迅手稿全集·日记》核校后,发现下列情况。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了《鲁迅手稿丛编》,但其质量反不如文物版,故不取;另外,最新版《鲁迅手稿全集》78卷本已编好,但尚未面世,故本文无从核校。
第一类,手稿原有,无须用补字符号:1913年9月16日“晚小雨〔一〕陈即止”,1914年7月4日“共七角二分〔一〕厘”,1920年12月2日“《惠究道通造象》〔一〕枚”,1925年5月26日“下午雨〔一〕陈即霁”。
第二类,手稿已删,可直接删去,无须用衍字或存疑符号:1914年6月28日“文明书局印行黄[?]《炭画》约言一分”,8月8日“买〖唐〗、宋、明《高僧传》各一部”,1915年8月25日“晴,〖无〗上午雨”,1924年3月7日“夜世界语〖送〗校送来一月上半及二月下半之薪水泉共十五元”,1926年2月27日“〖星〗晴”。
第三类,手稿已换位,无须再用符号将其颠倒:1913年8月16日“午后往璃琉[琉璃]厂”,1918年2月23日“《青新[新青]年》一册”,1925年11月23日“午访韦素园,其在[在其]寓午饭”,1936年8月5日“下午岛津[津岛]女士来”。
第四类,手稿无误,无须校改:1913年3月30日“三[二]十四”,1929年6月18日“今关大[天]彭”,1933年12月21日“《故宫自[日]历》”。
二 原稿笔误未校改之处正误
鲁迅日记手稿正文部分仍有不少“误字”及“漏字”一直未被发现并校改。而要证明这些确实为笔误并对其进行校正,需要坚实、充分和有效的证据,也需要科学的校改方法。
(一)误字
鲁迅日记手稿中还有一些误字,一直未被发现并予以校改,现笔者将其依次订正如下:
1914年1月13日:“得二弟所寄书籍四包,计《初学记》四册,《笠泽丛书》一册……”由周作人本年1月9日、鲁迅1915年4月28日、周作人1915年5月2日日记及鲁迅此期间书账可知,此处“《笠泽丛书》”的“一册”为“二册”之误,应处理为“《笠泽丛书》一[二]册”。
1914年7月11日:“又往有正书局买阿含部经典十一种共五册,六角四分……”由该日的详细书账可知,“六角四分”为“六角四厘”之误,应处理为“六角四分[厘]”。
1915年2月15日:“午寄二弟信,又还《会稽书集》样本二叶(十)。”由鲁迅该月10日、19日日记可知,此处的“(十)”为“(十一)”之误,应处理为“(十[十一])”。
1916年3月16日:“夜写《法显传》讫,都一万二千九百余字,十三日毕。”这份抄稿仍存,实际共13900余字。①据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2函第6册《法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故本处应处理为“一万二[三]千九百余字”。
1917年11月10日:“往留黎厂德古斋买汉画象拓本二种,一元,拓活洛氏旧臧,近买与欧人,有字,伪刻。”本处有两个错误:“拓活洛”为“托活洛”之误,是晚清大收藏家端方的姓氏,从鲁迅的录碑手稿可知他对此很清楚;端方在1911年镇压四川保路运动时去世,故“买与”也有误。笔者又查得鲁迅藏有两份汉代“白杨树邨画象”拓本,且还在其中一份的背面写有题签:“托活洛氏旧藏,近卖与欧人,有字,伪刻”②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藏拓本全集Ⅰ·汉画像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正是本日所购,可证这两处确有误,故应处理为“拓[托]活洛氏旧臧,近买[卖]与欧人”。
1919年7月26日:“为二弟及眷属租定间壁王氏房四大间,付泉卅三元。”8月10日:“寓间壁王宅内。”由本年周作人8月10日日记“下午移居间壁曹姓家外院”①《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中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鲁迅8月13日致钱玄同信手稿原文将“间壁王宅”改为“间壁曹宅”②鲁迅:《19190813致钱玄同》手稿,《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1册,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65页。可知,这两处所记的“王氏房”“王宅”有误,应分别处理为“王[曹]氏房”和“王[曹]宅”。
1921年2月5日:“午后往留黎厂买《霍君神道》一枚……《樊敬贤造象》并阴二枚,共泉六元。”由该日的详细书账可知,购书总价“六元”为“五元”之误,应处理为“六[五]元”。
1925年8月8日:“得培良信,八月廿日衡阳发。”“八月”有误。本年,尚钺7月6日从开封致鲁迅信手稿曾说:“培良去了。培良去时曾做了一首诗,想先生也已看过了……”③见张杰编著《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鲁迅7月4日记载:“上午得培良信,二日郑州发。”由此可判断:向培良6月底7月初离开河南开封,7月2日在郑州时给鲁迅发一信,其后到达湖南衡阳时又给鲁迅发一信。故本处的“八月”为“七月”之误,应处理为“八[七]月”。
1928年4月25日的“《美術全集》19”及1930年5月30日的“《世界美術全集》(一五)”所记册数“19”“一五”均有误:第一,“《美術全集》”和“《世界美術全集》”是同一套日本画册;④见《鲁迅全集》第17卷“书刊注释”,第475、503页。第二,这两处正文所记册数都与各自对应的书账不同,前者书账所记为“美術全集第16一本”,后者书账所记为“世界美術全集(14)一本”;第三,这套书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共36册⑤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三集,1959年版,“日文书部分”第79页。;第四,由鲁迅1930年10月30日日记“午后往内山书店取《世界美術全集》(三十六)一本,于是全书完”可知,他完整购买了该书整套;第五,查鲁迅历年购书书账可知,他另在1928年8月21日购买了该书第19册,在1930年7月21日购买了该书第15册,时间恰好分别在本处两条正文所记之后,而册数却重合,必有误记;第六,只有取本处两条的书账册数才能既无冲突,也恰好满足鲁迅所购该书1~36册齐全这个事实。综上可知,本处两条正文所记册数都有误,应分别改为“19[16]”和“(一五[一四])”。
(二)漏字
鲁迅日记偶或漏写某些文字或信件编号,编者会按惯例将这些漏字增补。但笔者发现仍有漏字未得到增补,这既违背编辑惯例又容易造成误解,应补上。
漏字应增补:1914年11月28日的“有正局”应增补为“有正〔书〕局”。1917年10月4日:“下午宋迈来笺并《藤阴杂记》二部”,应在“下午”后增补“〔得〕”。1920年1月16日的“尉娘墓志”不妥,本日书账是“尉富娘残墓志”,多一“富”字。而国家图书馆“碑帖菁华”收录该墓志,题名为《尉富娘墓志》,且碑文第二行写明“女郎姓尉,字富娘”。故书账所记正确而正文有遗漏,应增补为“尉〔富〕娘墓志”。1920年12月31日:“往留黎厂买《三体石经残石》一枚,杂造象四种五枚,一元。”从正文看,鲁迅买这些拓片共花“一元”。但由书账可知,鲁迅买“三体石经残石一枚”和“杂造象四种五枚”各花一元,总价是二元。故正文的“一元”应增补为:“〔各〕一元”。1927年7月3日的“广雅局”应增补为“广雅〔书〕局”。1932年6月25日的“光华局”应增补为“光华〔书〕局”。1933年5月5日的“高桥齿医院”应增补为“高桥齿〔科〕医院”。1934年12月16日的“寄母信”应增补为“寄母〔亲〕信”。
信件编号应增补:1912年11月27日:“晚得二弟、二弟妇及三弟信,二十二日发。”应增补为“二十二日发〔(7)〕”。1917年4月7日:“上午得三弟信,二日发。”应处理为“二日发〔(一)〕”。1918年6月26日:“寄二弟信,附与二弟及三弟妇笺,又以孙先生介绍拓专函二封。”应在句尾增补编号,处理为“〔(七十五)〕”。
刊误并非具较高创造性、能代表学术前沿的研究,但却是研究基础而必不可缺。本文即是这样的一篇刊误文章。因所见有限、所识非广,难免会有遗漏与舛误,期待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