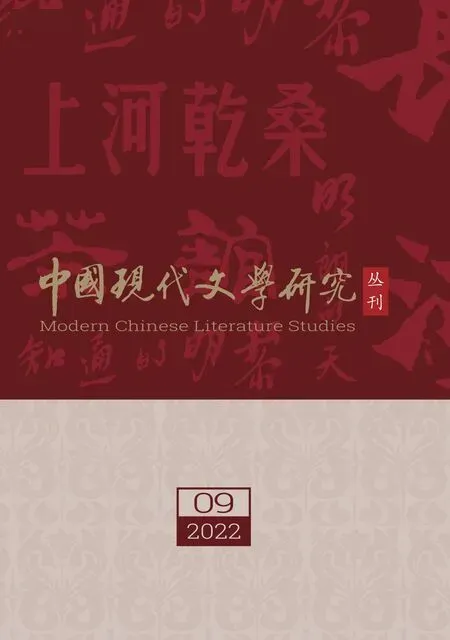重建宏大叙事:路径、策略及其症候性问题
——以胡学文《有生》为例
王金胜 初晓涵
内容提要:《有生》在宏阔时空跨度中,以空间化和伦理化方式构造情境化叙事,在日常微观世界中重建生活的整体性。小说以生命视角观照人、历史和世界,将其构造为自然性、人性与神性的统一。小说以祖奶为人物和叙述者,将历史与现实转换为个人记忆和个人体验,显示着作家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内向性”的继承,以及在当下某种文化共识作用下的转换。《有生》显示了当下文学在经历“语言学”和“后现代”转向之后重建宏大叙事的路径、策略和可能性,以及重构中国叙事的现代性和总体性宏大叙事所需思考的问题。
宏大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重要精神和美学追求。史诗性是衡量一个作家成就高低和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向往长篇小说宏伟目标的小说家,心目中必定得有一个‘总体性故事’”①程光炜:《心思细密的小说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宏大叙事是“形式”,更是“内容”甚或“价值”。鉴于宏大叙事、史诗与中国历史、时代、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联,宏大叙事始终处于建构、解构和重构之中的“敏感性”。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文化政治语境中民族文化复兴的诉求,强化了中国文化和文学主体意识的自觉。因此,新世纪兴起的宏大叙事热潮,除了中国文学内部的嬗变调整,更隐含中国/世界的双向互动视野、机制。
一 借历史的“情境化”重建生活整体性
从时间上看,《有生》有着广阔的时间跨度。小说从清末写起,直至当下,跨越近代、现代、当代,具有宏大的历史时间架构。清末皇帝的登基,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慈禧西逃,军阀混战,日寇入侵,伪蒙疆政府成立,“饥饿年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20世纪中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时间节点,浮现在叙事流程中,影响着人物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命运走向。历史时间的跨度,成就《有生》以祖奶为中心人物和线索人物的女性命运史、家族史性质。从空间上看,小说叙述围绕祖奶的行迹展开。祖奶和她的父母从河南一路北上,逃荒流浪,最终在荒寒的塞外之地——棋盘镇宋庄安家落户,繁衍生息。成年后的祖奶,传承黄师傅衣钵,四处接生,足迹遍及棋盘镇、张北县、张家口等地。这成就了《有生》开放的空间视野。《有生》在时间与空间的交织联系中,描画了一幅乱世流民图,一幅民间众生栖息生活图景,同时,也讲述了百年历史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史、情感史和生命史。《有生》在用小说形式讲述历史的意义上,是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甚至是喧嚣动荡、让人不安的;在图景描画意义上看,小说又是平稳的、静态的,甚至是沉默的、静谧的。《有生》采用鲜活的“情境化写作”方式,形成一个密实鲜活的“微观世界”,将历史个人化、生活化,使大历史成为个人生活史。历史现场转换为生活现场,回到历史现场即返回生活现场。伦理关系超越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成为《有生》最核心的人物关系。
《有生》的“情境化写作”最大限度地去除了被社会学思路和意识形态主宰的经典宏大叙事模式,将历史做“时间化”的中性处理,现代性的历史成为“前现代性”时间和恒常不变的空间。《有生》关注被大历史和宏大叙事湮没、忽略和无法收纳归置的“无声的”的个人、群体,注重乡土微观历史的细节还原,使历史走向普通寻常的“自然”的生活世界。通过这一世界的人物、家庭、家族和村庄市镇的勾连和转换,通过与人物之间的心灵默契,勾画其心理深度,传达具有“乡土性”的历史意识。
相对于大历史、宏大叙事之“变”,《有生》青睐的是“恒常”与“不变”。体现“恒常”“不变”的是“生”——生存、生活和生命之“道”。古语云,道不外饮食男女、应事接物。在百姓繁杂琐细的生活、交往等常人凡事中,隐藏着传统哲学、伦理纲常的深刻哲理,在大众自身的生活和历史中包含着历史的奥秘和“生”之奥义。
将历史做空间化和伦理化处理,以生命视角观照历史,建构生活的总体性,是《有生》区别于1990年代以来风行的日常生活审美的关键点。
首先,《有生》将历史时间化、空间化,并不意味着时间的断裂和空间的隔离。在时间维度上,小说将时间处理为一种生活、人性和生命的绵延,每一段时间、每一个时间点都牵连整体,传达重建生活整体性的诉求。从小处说,乱世中生命的死亡和无常不仅强化了“生”之意志,更催生了绵延不绝的生育。人们处于生存苦境和焦虑不安中,却也生生不已。从大处说,时间的绵延体现着中国文化“生生之谓易”的生命精神和生命超越诉求。
在空间维度上,小说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营造了一个具有鲜明生活实感和生命质感的空间。历史之“变”化为四时交替,时令变化,日升日落。在这个世界中,人与物相亲,物与人共存。置身这一世界中的人是自然性、人性与神性的统一。祖奶则是人的整体性的体现。
其次,祖奶是世俗的存在,在历史和现实中有着自己的无奈和尴尬。她自认是一个“半死不活的寻常人”,却被周围的人奉若神明。她四处接生、开方治病,被奉为观音弟子,却对女儿李桃的不育无能为力,亦无力阻止其自杀。她接生了众多生命,却无法主宰自己被安置的命运。同时,祖奶也代表超越世俗理性的终极性质的关怀,承载着处于生活和生命困境中的人们的希望。祖奶虽为凡人,却代表着一种崇高的生命理想和信念。世人对祖奶崇拜,实质上是一种生命超越诉求,寄托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生》通过祖奶形象,展现了一种看似淡然却竭力对抗和超越历史与时间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祖奶形象中寄寓的生命超越意向,并非指向神仙、菩萨式的不可验证的终极,而是落到具体的经验性的此岸“世界”,回到现实生活本身,回到日常事物或“此在”。
最后,人的内心生活的整体化。生活的整体性必然包含人的内心生活的整体性。《有生》设定的终极在“人”。这个“人”是生活之人、生命之人,同时也是更高意义上的存在之人。生命是生活的支柱和灵魂,是整体性生活的必然构成。生活包括物质性生活和精神性生活,是生命存在和展示自身的根基、舞台。在通过祖奶回忆写出的“历史”中,人们衣食无着,以生育婴孩显示生命的意志。战乱年代祖奶甘冒风险四处接生,写的不仅是人们的生育愿望和生命意志,也是接生者的神圣的生命信仰。在物质生活宽裕的“现实”中,人们却陷入彼此间的隔膜、矛盾,困于精神的匮乏和空虚。小说以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和伦理关系为纽带塑造人物,设定人物关系,强调一种拥有爱、仁慈、仁义、道义的合乎人性的生活。
二 回归个体生命的“历史”
《有生》叙事重心不在于揭示特定时代和历史“真相”。但“历史”并未在小说中彻底消失,它从清朝末年一直延伸到当下的市场经济社会。《有生》虽未将个人置于历史的巨流和漩涡中,书写生命/历史的碰撞与激荡,但历史却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个人命运。《有生》借“历史”为生命赋形赋意,同时也借“生命”重塑历史面貌精神,但“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的整体变化并不在《有生》的焦点处,而只是作为生命活动的背景和环境得到侧面表现”①桫椤:《生命因为仁慈和坚韧而神圣——评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小说在以生命为切口进入这一较长时段历史时,将历史生活化也生命化了。只要生活在延伸,生命在绵延,历史就不会消失,它只是隐匿于常态生活之下和个人生命之中。“历史”与“生命”在《有生》中既缠绕纠结,又疏离游移。历史改变个体生命的生活轨迹和命运,却无力主宰生命的全部;生命个体虽无力对抗乃至改变历史,却又有游离于历史之外的自然性,甚至会重构和丰富历史。生命个体“非历史性”的一面,潜在地构成了反历史主义叙事倾向。
这个文学世界的“构造者”是祖奶,连接生命世界和历史世界的也是祖奶。她与百年中国历史同步而行,也如同这段历史一样,历经坎坷和曲折。即便遭受动荡历史和无常命运的折磨和捉弄,她却始终坚守接生的职责,坚守生命信仰,承担着人类繁衍的使命。她游走于历史缝隙之间,也处于激荡的历史之外。
《有生》中世间小民在普遍的生存状态和一般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历史”中饱受贫困、饥饿、死亡威胁的人物,还有“现实”中被隔膜、孤独、抑郁、烦躁困扰的“现实”人物,都是被困于灰暗、贫瘠而无意义的生活的“蝼蚁般的存在”。他们无奈地与历史周旋,承受着生存和生活之重。生存生活之重,意味着生存生活的匮乏和沉陷,也迫使人贴近大地这一生命本源。
三 由“个人记忆”重述历史
《有生》的“历史”叙事是通过祖奶的“个人回忆”完成的,“历史”在此成为“个人记忆”。如果说历史建构的是一种族群性记忆、公共性记忆,那么“个人记忆”能否有效履行这一职能?《有生》中的百年历史是谁的记忆,何人何事进入记忆、值得记忆,记忆由谁言说,如何言说?“祖奶”的身份设定、形象塑造和叙述者身份的设置至关重要,是进入上述问题的起点和关键。“祖奶”是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也是历史的讲述者;既是小说中心人物,又是主叙述者。祖奶的出身、经历、生活观、价值观,以及她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有生》历史叙事的底色、气质和小说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表征。
首先,“祖奶”视角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祖奶作为主人公和叙述者,是两个世界——历史与生命,外部与内部,自我与他人——的中介,在这两个世界之中穿行,也游离于两个世界之外。特殊的人物/叙述者把两个世界统一了起来,传达了两个世界的感受。在个体生命与内部的世界中,作家通过胸襟博大开阔的祖奶建构的“普遍性”视角,自如地处理复杂多变的历史与现实,彼世界成为此世界自我情思投射和浸染的“意象化”对象。同时,被祖奶讲述的历史、外部和他人的世界,既是一个被普遍性“观照”的自我肯定性的世界,又是一个被这一讲述中断(打断)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否定性”世界。所谓肯定性是指小说中由“生”——生育、接生、生存、生活、生命等——生发和生长出来的希望、期冀、关于生活和生存的深一层的意义;所谓否定性既指充满暴力、无常和死亡的“历史”,也指灰暗、无意义、期待摆脱和救赎的“现实”。肯定性与否定性的共存并生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突破了“普遍性”讲述语法的限约,呈现出令“普遍性”难以接受的尖锐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其次,历史中“祖奶”的尴尬无力与叙述者“祖奶”的自由、敞开。祖奶既是一个世俗性存在,又代表着终极价值。作为人性和道德标杆,她仿佛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朱先生。他们都曾经历过历史,遭逢历史暴力,后者甚至干预、改变历史;但后来他们同样被历史/时间放逐,成为“历史之外”的人物;较之朱先生尚能编撰县志铭刻历史,发出历史预言,晚年的祖奶则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神圣“偶像”。正是在“偶像”意义上,祖奶获得了众多善男信女的崇奉、膜拜,这有违祖奶初衷,却无力改变众人想法和自己被安置的命运。
吊诡的是,也正是在崇高神圣的意义上,祖奶的“个人回忆”便具有了“普遍性”。《有生》中的“历史”借个体生命的讲述获得了个体/族群/人类多重意义上的“生命”普遍性。作为感性生命个体的“祖奶”的回忆/体验视角,使其讲述偏离了历史轨道,撬动和偏移了既定“知识化”(启蒙的与革命的意识形态)视角。当作为“历史”叙述者时,祖奶身经百年历史却无力言说宏大历史,对于她来说,历史只是个人、家庭经历过的及耳闻目睹的惨烈事件的创伤记忆。当作为“现实”叙述者时,她只能通过听觉和视觉来间接“感知”现实,更多的现实是通过如花、毛根等视角性人物,以及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得以揭示。而在第三人称讲述中,鉴于祖奶(视角)的全知性、权威性,小说叙事兼有了个人化/整体性双重质地。这是由特殊性开出的普遍性,由尴尬无力的现实生存和生活中发掘的生命自由,由个人化叙事中生长出来的宏大叙事。
作为人物和叙述者,“祖奶”倾听和讲述了几乎所有人的故事。历史与现实,经过祖奶感官的“过滤”,被个人化、生命化乃至感觉化了。《有生》的全部叙事都与祖奶、与她的感觉有关,也与她历经世事沧桑的感受和体悟有关。“历史”和“现实”在个人生命化的视角中,被情境化为颇具抒情意味的日常人性景观。在小说中,一方面是具体的、直接的生活场景和细节,另一方面是个体生命的感觉、感受及由此营造出的氛围和情调;一方面是历史迅速而无声地逝去,如同祖奶和她接生的众多生命一样,另一方面是生活和生命的无限绵延和充满复杂纠葛的现世生活本身。
历史/现实在这里碎片化了,生活、生命也被分割为片段的“个人故事”。《有生》具有先锋小说的气质、手法和新历史小说的基质、视角。《有生》中不存在整体性历史,生命个体亦不像莫言《红高粱》《丰乳肥臀》、陈忠实《白鹿原》中的人物那样与历史博弈缠斗,其叙事呈现为主体弥散、精神乏力后的碎片化拼贴。
但《有生》却在生命的衰颓中发现和挖掘生命的繁衍生息,且历史的逝去又以生命的形式得以救赎。绵延的生命之流重构历史,也复活了历史。卧榻不起的祖奶,既是历史的神游者,也是当下的感受者和领受者。如此一来,通过祖奶,零散的碎片之间便建立起历史/现实的生命联系。《有生》将“后现代”碎片重新聚合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历史故事,完成了一个以物理时空和心理时空交错的带有后现代弥散性特征的形式修辞,讲述现代故事的“叙事”实践。
最后,“祖奶”视角与单纯/混沌意蕴及其美学形态的生产。小说通过生命/历史的结构性关系设置,生产了一种基于生存、生活和生命的文化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虽受历史的影响,却存身于历史与生命、主流与非主流文化区隔之外,呈现出一种未被历史及其话语所完全同化和宰制的,难以完全分辨的模糊状态。这一文化形态的非观念性、非概念性,决定了其无所不在的弥漫性和渗透性。
《有生》在悠久的乡村生存历史、独特的地域景观和丰富鲜活的人情事物之外,多有风情风物风俗的描绘,以此构成叙事内容,营造情境、氛围。风物习俗、民间知识、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乃至象征性符号的无所不在的弥漫性,造就了一个多重价值共存共生的叙事空间。同时,历史“情境化”和“微环境”设置,以经验性、感性和生活性祛除了某种主导理论话语如启蒙、革命和现代化的规定,使《有生》成为一个以“生”为神魂,尚未完全被现代性话语宰制和整合的的审美空间。这是一个“生”的、“俗”的、“民”的世界,它不是国族或个体的镜像,却能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更远方的人们提供另一种可能的文化和意义空间。
四 “内在性”与充满“忧郁”的超越
1990年代作家的现实洞察力转向对日常生活审美的聚焦,以观念化为基础,谋求理想性、超越性的宏大叙事呈明显衰微之势。文学的“主体”和“本体”急剧向曾经被历史压抑的“世俗”“生活”维度回落并走向另一个极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重现宏大叙事热潮,内含重建历史主体性和文学精神高度、灵魂深度的超越性意识。众多作家以长篇小说文体在“世界”视野中关注“本土”,从“传统”中寻求建构现代国族主体的资源,力图超越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孤独”个体认同,重建具有时代全景性和历史整体性的文学和文化政治视野。自1980年代至今,先后经历了人、个人、纯文学、私人化、日常化、世俗化等话语洗礼之后,尤其是在反本质、反中心、反深度的后现代历史观的颠覆性影响下,重构整体性、统一性的宏大历史图景,是否必要,何以可能,如何可能?作家的思考和选择见仁见智。
新世纪文学延续1990年代解构宏大叙事元话语的兴趣,也在新的历史契机时代语境中寻找重构的可能路径。胡学文一直想写一部“表现家族百年的长篇小说”①胡学文:《我和祖奶——后记》,《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941、941~942页。,《有生》构思与写作长达七八年之久,其宏大叙事之热情和抱负可见一斑。②2 胡学文:《我和祖奶——后记》,《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941、941~942页。《有生》蕴含“讲述故事的年代”的认知和情感结构,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化共识”。
表面上,小说聚焦普通民众,将百年历史分解为具有民间性、日常性和世俗性色彩的个人故事,同时借助伦理关系、情感关系,连接更为广泛的人群。《有生》将潜藏在民众生活和生命无意识深处的能量发掘出来,使之由弥漫状态而凝聚成形,重建基于生命深度、广度和生活本相的深度模式—— 一种新的意义上的总体性。祖奶不仅是在历史宏大进程中的个体生命,也代表了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风貌和秉性气质的生命群体。这一群体,不管其阶级归属、身份如何,还是其他面目出现的无声的、沉默的、零散的个人,共同构成一个民族的“原型”和象征,成为某种深层集体无意识或民族文化心理的映照和召唤下的充满生命力量和大地诗意的族群形象。
从解构宏大叙事角度看,《有生》散发着一种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命存在论本体气质;从宏大叙事重构的价值向度看,小说则深含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某种历史意识和理想主义色调。《有生》不仅在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内部展示了文学如何重构民族总体性的问题,也在现时代与世界双重视域中,思考历史与现实、时代,总体性与个体性主体如何重塑的命题,体现了一种在时代和世界视野中理解历史与传统的意识自觉。
《有生》蕴含强烈的生命意识,强调主体内在性和自身的无限性,沉潜于主体自我意识世界。《有生》在主体(以“内宇宙”为内核的主体论)和叙事(以“纯文学”为想象目标的本体论)两个相关维度上,体现了一种198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文学“内在性”的突出。在这种写作观念中,内在性与个体、个性、情感的肯定,与心灵存在的饱满及个人主体对于自身潜能的信念相联系,也与崇高的愿望(生命的崇高意识)、宏大叙事意图和总体性美学诉求相关联,是人类灵魂相通的隐蔽而坚实的根基。因此,“内在性”沟通、联结普适性,甚至本身便是普适性。这是《有生》以“内在性”在历史/现实的映照中讲述“家族百年”历史的基本路径,其目的则在将普遍性、普适性维度置于民族史诗形式内部,以“生命史诗”超越和重构“民族史诗”。基于此,小说放弃“民族史诗”常用的家族架构而采用“伞状结构”(实为“拟家族”结构的叙事外化)。这一改变带有的不仅是令作者“欣喜若狂”的结构创新,更重要的结果是,取消了人物之间的血缘关系,降低祖奶与其他人物仅仅是接生与被接生、崇拜与被崇拜的关系,极大降低二者的关联度;其他人物相互之间关联度相应降低。
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对束缚和异化生命的历史和理性的反抗,那么《有生》生命意识的强化则更属历史和理性的顺应性生产:暴力、无常的历史催生人们的生育欲望,淬炼了祖奶的生命信仰,此谓生命作为“历史”的顺应性生产;相对于1980年代小说如莫言《红高粱》、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将生命视为欲望机器,在本能欲望层面上释放“生命”的解构性、颠覆性能量,《有生》则通过道德、秩序、理性、信仰等介质使之成为一种积极的、有序的建构性精神力量,此谓生命作为“理性”的顺应性生产。精神代替了欲望,理性驱逐了非理性,历史意志重新定义了生命意志。
因此,尽管《有生》延续了1980年代以来文学的“内向性”,却又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以某种“文化共识”转换了“内向性”,小说以内在于这个时代的方式超越历史。它以阻断“历史”,祛除知识“中介”的方式返回经验性讲述。生命蕴含着超历史超时代的绵延性崇高,却也显示了其外在于历史的忧郁、孤独、焦虑乃至庸常。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现时代建构宏大叙事的矛盾或难题:如何处理个体与总体、内在与外在、个人与历史、文学与历史之关系。从历史叙事层面看,则是作为经验的历史、作为文本的历史与作为话语的历史,三者孰轻孰重,如何选择、谋思及处理其间关系的问题。换言之,则是在经历“叙事学”和“后现代”转向之后,如何重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总体性宏大叙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