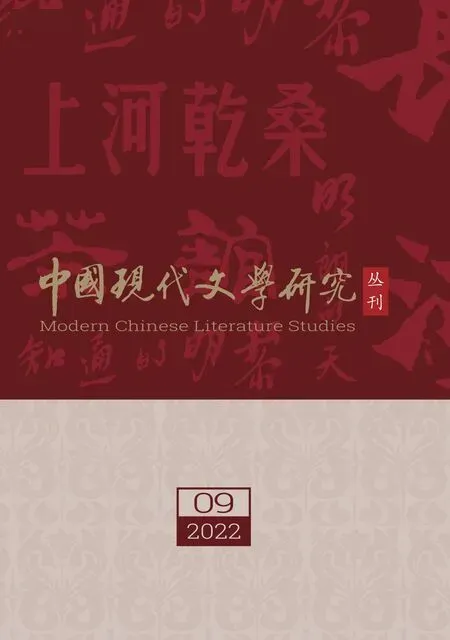“本事”向“故事”转化中的史与诗
——从《宗月大师》看老舍向民族传统的精神回归
李 笑
内容提要:《宗月大师》寄寓了老舍对自我命运与文化人格的重新体认,按时间线索展开“我”与宗月的交往始终,“我”的求学历程与他的生活变迁互为映照,所刻写的几个时间节点均内含着“我”向新的生活和新的自我的进阶。在此意义上,通过考索现代佛教期刊等文献中的宗月行迹,回到其特定的生活与工作现场,分析老舍与宗月二人在人格修行、苦干意识、躬身实践等方面更为深远的精神联系。同时,重读老舍对宗月及其相关的原型人物的遮蔽与改写,不仅可以体察他在“本事”与“故事”、“私意”与“诗意”之间的编织,亦有助于思考身处抗战文化语境中的老舍通过“灵的文学”路径向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归。
1944年1月23日,老舍在成都《华西日报·每周文艺》副刊发表散文《宗月大师》①目前《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卷所收录的《宗月大师》,文末标注的刊载来源为1940年1月23日《华西日报·每周文艺》,属错讹,实为1944年1月23日。。这篇纪实性的回忆文章在追念北平僧人宗月大师的同时,展开自我童年及其成长经历的重述,两条线索互为表里,寄寓着老舍对自我命运与文化人格的重新体认。如今,作为老舍散文名篇的《宗月大师》被人提及的同时,依然停留在文学造像的层面。我们虽然知道宗月大师是北京城内的一位僧人,满洲贵族出身,时常以“善人”的形象出现在老舍的自传体文本中,特别是与童年老舍的“上学”事件紧密关联,然而,作为“僧人”,他僧腊几何,出家前有过怎样的经历,出家后建树过怎样的功德,老舍与宗月的交往除了老舍自己在文章中描述的之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老舍的虚构文学创作中有哪些重要的“宗月”元素等等问题还需要研究者予以进一步的发掘与考证。本人近期从现代佛教期刊等出版物中搜寻到有关宗月大师生平事迹的大量文字撰述,拟对这些文献进行爬梳、整理和诠释,探索老舍对宗月及其相关的原型人物如何“遮蔽”与“改写”并形成新的艺术合力,从而为重新解读老舍的思想人格及小说创作建立一个新的参照。
一 宗月大师身世考述
1928年9月2日,宗月升座鹫峰寺住持,9月20日《佛宝旬刊》刊载了北平僧界同人对宗月的祝词贺联等,而同期由主编刘显亮、好友魏悟澄等撰写的《现继席鹫峰寺住持宗月大师略史》、宗月本人撰写的《鸣谢鼎惠》等,基本可以梳理出其身世情形及家族变迁。
宗月大师,北平世家刘氏子,俗名刘德绪,号寿绵,清内务府旗籍,官部曹。刘家三代历任粤海道道台,负责清代广州海关贸易,家资丰厚,祖居北京西直门横桥迤北,号称“粤海刘家”。刘德绪生于光绪六年,即1880年。至于卒年,宗月的同门师弟悟性法师在其自传《散金碎玉集》中明确写道,民国三十年旧历九月初九(1941年10月28日),现明和尚圆寂,宗月为其举行接三送三仪式后,端坐而逝①悟性法师:《散金碎玉集》,第15页。此书无版权页,应为寺庙自行刊印。。因此,宗月的生卒时间应是1880年和1941年。
宗月少时曾拜京城文举人杨公全为师,后娶其长女杨木槿为妻,育有四女一子,长子贵霖,长女振华,次女振亚,三女振中,义女振志。宗月未出家之前以“守圆居士”自居,且于1910年前后在北平有“刘善人”之称,与妻子儿女尽心一切社会救济事业,念佛茹素多年,直到1925年前后随弘慈广济寺现明和尚出家为僧,法名悟天,法号宗月,是年45岁。至于宗月为何在45岁时选择弃俗出家,悟性曾言及此事:“(宗月)因中年丧子,看破红尘,乃率全家毅然皈依佛门,一生专修净土,一心念佛。”②悟性法师:《散金碎玉集》,第15页。此书无版权页,应为寺庙自行刊印。宗月在其子丧期结束后,常有出世之念,具体受戒时间不详,笔者推测最晚1925年。因《佛宝旬刊》第48期曾刊载宗月亲撰的《悟纯沙弥往生略传》,为其外甥悟纯作传。悟纯跟随宗月左右近三年,遇有佛事,无不随喜,奔走终日。1925年春悟纯罹患胃病,诸法治疗无效后,依现明和尚剃度受沙弥戒,刘显亮曾提及宗月和尚“常率已圆寂沙弥悟纯接引临终念佛者数十人,每见瑞相至,沙弥悟纯圆寂时,亦由和尚接引共见瑞相云”①刘显亮等撰:《现继席鹫峰寺住持宗月大师略史》,《佛宝旬刊》1928年第51期。。也就是说,宗月于1925年为悟纯接引时已在广济寺正式出家受戒。宗月拜师现明和尚,既是出于佛缘使然,亦感念同道兴学办学、启发民德的宏愿支撑,不仅赞助广济寺开办弘法利生事业,同时还曾兼任广济寺监院、广济寺佛事学习堂讲员、广济寺一切慈济事业临时代表主任等职务,出资出力,不辞劳瘁,为近代北京的佛教振兴事业承担着切实可行的工作。
宗月出家时“率全眷尽数皈依”。其实,宗月携眷属皈依佛教并非一时冲动,皈依之前家中即设专门的佛堂院,客厅供奉三大世、观音像等,以学佛诵经为日课,平时也会召集亲友后学到家中共参佛道,这种礼佛家风一直保持多年。同时,其子女均接受现代高等教育,偏于实业与师范专业,这也与宗月希望后辈致力于兴学利生的宏愿有直接关系。
20世纪上半叶,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在北平一共开展过三次寺院登记,用以了解寺院的来历与沿革,以便规范各庙行为,督促其施行慈善救济等事。1928年10月内政部拟具《寺庙登记条例》,次年1月再次核准颁布《寺庙管理条例》,可能是北京建市后的第一次寺庙登记,共登记寺庙1631座,详细记录了寺庙的庙名、庙址、建立年代、庙产情况、管理状况、法物情形等。1936年内政部再次公布《寺庙登记规则》,预计之后每10年登记一次,1947年7月为最后一次登记,因遭战祸人祸侵扰,寺院仅剩728座。据北京市档案馆于20世纪90年代对这三次寺庙登记材料的整理,宗月于1928年住持的鹫峰寺,“不动产土地东至西十五丈一尺六寸,南至北二十二丈三尺,房屋六十二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住持管理,除各殿堂供奉佛像外,其余房间暂借给北平佛经流通处。庙内法物有佛像七十尊,画像一尊,礼器十九件,乐器十二件,法器七件”。②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由北京市馆藏档案《北平警察局档案》,1928—1929,档号J181-15,属不开放档案。除此之外,鹫峰寺下院大悲庵亦在宗月管理之下,1938年,宗月住持永寿观音庵,位于西直门内大茶叶胡同,“本庵残破异常,本住持新接收次第整理修补”①《北平特别市社会局寺庙情形调查表(按宗派的分类)》,1938,北京市馆藏档案,《北平市社会局档案》,档号J2-8-1226。。中国近现代宗教文化在北京非常昌盛,古刹林立千余所,但从庙产面积、佛宝法物等方面来看,鹫峰寺绝非香火旺盛之处,更何况下属塔院又仅供香客歇息及僧人备葬,更是寥落。像宗月这样出身富庶而半路出家的僧人,散财利生本是其修佛方式之一,并不为庙产积累,也无意要做高僧大德。
二 老舍人格思想中的宗月影响
作为僧人,宗月并未跻身中国近代名僧大德之列,也未留下传世的佛学著作。然而,在宗月的僧侣生活中,白话写作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佛教有“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之说,主张道传,不必以诗示人,但清末民初的佛教文学家都非常重视通俗文体与白话文学的影响,希望佛教由丛林走向社会,由寺庙走向人间,希望现代佛教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一道发挥国民启蒙的作用。
据黄夏年主编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第33卷所录,宗月曾接任并主笔北平《佛宝旬刊》,从1928年5月2日第37期至1929年8月22日第84期,共48期,旬刊,每月10号发行,募捐办报,不对外出售,仅赠阅给寺庙、佛学院、念佛堂等宏法机关,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刊,再未复刊。《佛宝旬刊》栏目设置包括佛学开蒙、佛学浅解、彰善要闻、慈航随笔、僧界公案、论说、喻言、诗歌、通讯等,维持一年半之久,在国府南迁之后的北平已属不易,且风行海内。翻检《佛宝旬刊》,宗月的新诗创作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兼具语言与体式上的革新。从体裁看,以口语为主,通俗明了,三言、五言、七言相间排列,句式灵活而不拘一格,适宜民间传诵。就题材言,大致诗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诗偈直接表达佛法妙理,另一类是以日常生活入诗,透露着人间烟火的温润。此外,宗月常常以组诗的形式摹写周遭的贫民群体,钦敬这一群体遭逢苦难之后的尊严修持。
在宗月修行的年代里,白话文学已经成为文学的正宗,佛教文学界也涌现出了不少用白话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显现出了佛教文化在五四新文化影响下向现代性的发展。宗月不是文学家,也无意于做一个文学家,他用白话写作,只是看重白话在广宣流布中能起到的普及作用。但他对新的书写方式的诚心接受和娴熟运用,体现了他追随时代前进的个人眼光与恢宏气度,这一点或许也是作为新文学家的老舍对宗月抱持亲切感的原因之一吧。
1928年北平学务局儿童图书馆因经济困难停办,宗月在其旧基上因陋就简将之改组为慈航图书馆,之后不久,又在慈航图书馆内设置慈航小学,召集恤嫠会中的孤儿弱女入学受教。“贫儿”老舍正是在清末庙产兴学的社会风潮中进入学堂,宗月引领老舍就读的第一所私塾正是设于寺庙中的改良学校,礼佛向善的氛围伴随着老舍度过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1909年夏,老舍在宗月帮助下转入西直门崇寿寺内城第四学区私立第二小学堂(后称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初小三年级,直到1911年冬离开。1913年2月,老舍考入祖家街市立第三中学,半年后因贫辍学,投考北京师范学校,直至1918年6月毕业。
老舍自述,与宗月过往最密的时期是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此一时期老舍之于宗月散财赈济的救世策略处于“人情”与“理智”的矛盾之间。宗月倾尽全力以赴慈善,老舍敬畏他的“真诚”,同时目睹他的一步步破产,对此怜惜而又无奈,转而对自我人生做出更为主动积极的抉择,并未像宗月子女一样成为彻底的佛教信徒。这种保留态度本身也是主导其以偏于“人情”而非“理智”的一面看待底层贫民群体,是老舍文化人格与精神信仰构成及演化的重要质素。
在实践意义上,多年跟随宗月出入于寺院、粥厂、孤儿院、感化院等,所积累的感性体验与经验渗透到老舍个人的气质、情绪、心理等深层意识结构中,建立起个体生命与贫民群体的一种情感连接,同时积淀了老舍创作中所需要的材源与写作动力。王富仁先生曾言:“一个贫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忘掉自己所出身的那个阶层的人们的痛苦和绝望,但自知自己是没有力量拯救那里的人们的,于是一生向我们赔着小心,几乎是用乞求和谄媚的眼光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给那个世界的人们多一点爱,多一点真诚的同情和理解。我认为,这就是老舍一生所经历的精神的炼狱。”①王富仁:《平民文化与中国文化特质——作为城市贫民作家的老舍之精神历程》,《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处于五四启蒙时代的老舍与鲁迅都面临“揭出病苦”的使命与责任,只是老舍将目光投向城市贫民之时,重在其经济的困境而非精神的愚昧,重在金钱杠杆对于各种情感关系的撬动,由此带出一系列最终只能以“混”为哲学的人物,如《月牙儿》中的母与女,《我这一辈子》中的父与子,《骆驼祥子》中的车夫老马与小马,后者世袭着前者的“贫”与“苦”以及由此带来的“恶”,一个有着天然缺陷而又无力逃脱的苦迫世间。老舍当然无力为此提供疗救的“药方”,他也只能通过现代教育这一渠道摆脱贫民阶层跨向知识阶层,然后通过小说写作为底层代言发声,为我们提供一种尽量可靠的底层叙事,同时制造了一个哀悯众生、慈悲为怀的出家人视角。
谭桂林曾指出,老舍在情感上亲近佛教,正是宗月所表现出的大慈大悲、舍己度世的菩萨行观念在其精神发展与人格建构中的深刻影响。①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宗月大师》发表时正是老舍南下抗战并苦苦支撑“文协”的第七年,老舍对宗月所作的评价也正是他自己在抗战八年中的工作状态写照。对于“文协”事务的勉励维持,当然存在抗战所激发出的国民意识与民族意识构成,但更多内在于老舍自身信仰中对于“做事”的一种自觉执行,对于“牺牲”“舍己”信念的先在认同,由此将机械的、消磨意志的事务性工作转化为一种灌注热情、情感、心性的行动实践,无意之间也为流亡个体提供了一种身心安顿之感。这样一种新的“工作伦理”远非现代科层体制中的“做官”所能比附。
三 老舍创作中的“宗月”元素
《宗月大师》作为典型的非虚构文本,按照时间线索勾勒出宗月的家世、修行、去世,同时展开“我”与“宗月大师”的交往始终,“我”的求学历程与“他”的生活变迁互为映照,作者在追悼北平善人宗月的同时,流露出如师如父般的感恩情愫。宗月大师直接关联着老舍的“上学”事件,成为老舍书写自传文学《正红旗下》时必然加入的重要一笔。《正红旗下》并未完成,但从目前所呈现出来的样貌来看,“定大爷”这一角色的地位并不简单,定大爷(定禄),从其身份、样貌、性格、家世及其经历等看,是以宗月为原型。②鉴于老舍在北京求学期间与宗月过往甚密,参与到宗月的慈善事业办理过程中,与其亲友及同道应大多相识,定大爷取“定”姓,可能与宗月的挚友定君保有关。
老舍写作《四世同堂》时,宗月已圆寂,但他还是在小说中为其加入了篇幅不多却饱含深情的一笔,历史地融入了宗教的、诗意的成分。小说安排钱诗人隐居在北平城西的一座破庙,并结识明月和尚,借明月的僧人身份陆续将瑞宣、瑞全、高第、白巡长等人拉进寺庙,油印传单、递送情报、编辑地下报刊——明月所在的破庙无形中成为北平沦陷后的抗敌阵地,佛寺作为戒杀之地成为杀敌保国的隐喻空间,这样的叙事安排可看作老舍对明月(宗月)的一份致敬。
老舍与宗月一家的相识交往,除了恩情,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恋情。1944年4月,重庆进步文化界为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举行纪念活动,由此产生的纪念文字大多围绕着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做文章,唯独挚友罗常培《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一文,在兼顾这一写作任务的同时旁逸出更多的私人交情,并披露了一个“秘密”,即“《微神》,就是他自己初恋的影儿”。大致原委如下:“有一晚我从骡马市赶回北城,路过教育会想进去看看他,顺便也叫车夫歇歇腿,恰巧他有写给我的一封信还没有发,信里有一首咏梅花诗,字里行间表现着内心的苦闷。(恕我日记沦陷北平,原诗已经背不出来了!)从这首诗谈起,他告诉了我儿时所眷恋的对象和当时情感动荡的状况,我还一度自告奋勇地去伐柯,到了儿因为那位小姐的父亲当了和尚,累得女儿也做了带发修行的优婆夷!”①罗常培:《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罗常培文集》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涉及私人私事,罗常培心有顾虑而说得隐微其辞。但基本情感事实可以落实,特别是小说《微神》写到“我”毕业后荣升小学校长,“她”发来的祝贺信笺上印着一枝梅花,这一情节便是对罗常培所看到的“咏梅花诗”的明确交代。
从仅存的这些迹象看,罗常培所言老舍眷恋的对象应是宗月长女刘振华。关于她确切的生平详情,据现有资料,她与老舍同为1899年生人,毕业于师范学校,1925年前后随父皈依佛教,法名悟莹,在家修行之余任小学教员。其余线索仅有:第51期《佛宝旬刊附张》庆祝宗月升座住持时,发心捐印资人中,宗月的四个女儿在列,包括“刘悟莹”;1929年鹫峰寺念佛堂清众师圆寂时,“刘悟莹居士助洋一元”。②宗月:《鸣谢助道功德》,《佛宝旬刊》1928年第51期。在这之外,笔者无意中发现201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八旗子弟》一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都在描写刘振华。③《八旗子弟》一书采用“刘惠华”,为刘振华皈依之后,由万善寺法师所赐名。《八旗子弟》的作者陈君安作为刘振华的表弟,儿时两家相交甚好,直到1960年深秋陈君安被“下放”至黑龙江萨尔图,与刘振华失去联系。老舍与刘振华的“初恋”是否真有其事,暂不可考,也不必细考。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刘小姐确实追随父亲出家念佛,而老舍与刘小姐儿时相识直到赴英任教后断了联系,痴情多年,回国后,宗月已率全家皈依,这段感情算是缘分已尽。
基于以上的情感背景,《微神》可以说是一个半真实的故事,更是一个经典的症候性文本①除《微神》外,老舍在济南、青岛时期尚有新诗《微笑》、散文《无题(因为没有故事)》等,均属于作家对这段情感的个人式回望,以“化实入虚”的象征结构自剖心事。,内含着老舍内心深处不忍明言的情感潜流。表面上看,《微神》中的“她”似乎可以归入老舍的底层女性系列,但其独特之处在于,文本内外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反向书写:现实中的刘小姐出家为尼弃绝了爱情,将流年青春付与青灯古佛;小说中的“她”沦为暗娼却将爱情视为宗教。神女/妓女、圣洁/失贞、清修/纵欲、安详/狂笑参差对照,这样的有意改写或者说颠覆性的再创作,使得小说的虚构早已脱离了现实材料的拘囿,成为老舍对早年爱情苦闷的一次爆发。故事最终被导向一种“破坏性重述”,将作家多年前的心事再次撕开一道口子,“她”在重逢之时的大段告白当然不可能是真实的刘振华之语,而是“我”的心理真实。这也正是一个男性作家的落网,小说中流露着知识分子男性对沉沦女性的怜悯与残忍,属于现代小说家所特有的消解神圣爱情的方式。
《微神》发表时正值老舍长女舒济出生不到满月,小说家初得小女,小说中的“她”却因打胎而死,或者说“她”不得不死,这样略显残忍的想象与安排是否是老舍对这段情愫的告别与哀悼?作为一次怀旧的复发,老舍借助多重意象的联结使得《微神》从“私意”走向“诗意”。小说前半部分所浮现的海棠花、小绿拖鞋、她的脚、她的笑等,承担着对往昔美好情愫的怀旧;后半部分,两人在多年后的重逢场面,“她”那种深情的爱与无奈的怨,正是作家心造的幻影,或者说是对现实中遁入空门的刘小姐心里的想象,将出家念佛一事隐藏,改写为家道中落后沦为娼妓的结局。这样的遮蔽与改写,表面上是反向结构,实则改写是由遮蔽部分激发而成。老舍用自己的方式译解了自己的过去,通过“她”对于爱情近乎偏执的疯狂,以及最后的“死”,在双重置换中完成了对这段情感的追悼。
老舍在长篇小说《选民》(即《文博士》)直接将唐孝诚的大女儿取名“唐振华”,且唐家也有大花园,家中三子一女,似乎是宗月家庭成员构成的翻版。《微神》中的爱情意象如海棠花、小绿拖鞋、她的脚、她的笑,师范学校毕业的小学教师身份等,原样复现在唐振华身上,遗憾的是,这篇未竟之作来不及透露唐振华后续的发展与结局,但16小节的篇幅已经为这一女性形象定了正面轮廓,而且明显流露出作者对这一角色的倾心与偏爱。“安详”一词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用来形容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女性似乎格格不入,却与其原型人物相称。
结 语
老舍早年受宗月影响,青年时期受基督教洗礼①老舍于1922年夏在北京缸瓦市伦敦教会接受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在业余时间参加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试图将基督教中国化以服务社会改造,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而非将之作为宗教信仰。他认同和推许基督教文化精神中的平等、博爱、人道主义,以期更好地改造社会,而在深层心理以及情感倾向上更接近佛教文化。,此后一段较长的时间老舍小说的创作主题都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自我缠绕。抗战期间,迁居重庆的老舍多次前往位于北碚缙云寺的汉藏教理院,与佛界友人交谈。1940年9月,老舍受太虚法师之邀参观汉藏教理院,演讲《灵的文学与佛教》。②徐慧文:《老舍演讲佚文〈灵的文学与佛教〉续考与补正》,《东岳论丛》2016年第9期。演讲中虽然将基督精神与佛教文化并举,但老舍将但丁《神曲》中的地狱书写归因于东方佛教的影响,进而提到“肉体”、“灵魂”与“抗战”的关系。此外,老舍还对现代佛教僧侣寄予了深厚的期望。大约四年之后,老舍写作《宗月大师》,这篇散文应该联系《灵的文学与佛教》这一演讲和《四世同堂》等抗战文学的创作来理解。首先,老舍对现代僧人人格建设与抗战建国之间的关系有所期待,宗月大师就是他向现代僧人人格建设提供的一个楷模。其次,《宗月大师》一文深情地表示自己正是在宗月的言行中懂得了帮助别人的意义,这种追溯式的判断无疑可以视为老舍在战时流亡生涯中对自我人格的一种寻根。最后,老舍祈望宗月成佛后“以佛心引领我向善”。这是老舍对未来自我人格发展的一种期待,是发自内心的对宗月式的人格力量的景仰,对这种佛性人格在国民精神建设中的作用的肯定。《宗月大师》显现的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回归,在《四世同堂》这种民族史诗性的长篇巨制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所以,《宗月大师》对老舍的人格建构和创作发展而言,既是本事,也是故事,在本事向故事的诗意转化中,闪射着个人心史的熠熠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