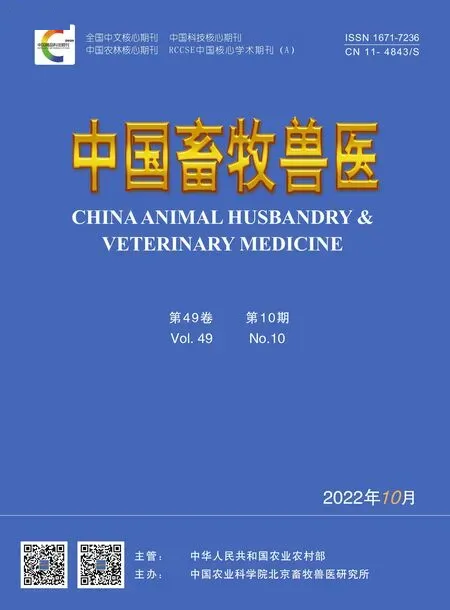半乳糖凝集素1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鹿茸再生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李勋胜,史婉婉,邢宝瑞,周 珏,李春义,孙红梅
(1.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长春 130022;2.长春科技学院,长春 130600)
半乳糖凝集素(galectins,GALs)是一类通过碳水化合物识别域(carbohydrate recognition domain,CRD)结合β-半乳糖苷的动物凝集素[1]。目前,发现的半乳糖凝集素已达15种,根据结构特征,将其分为三大类:①原型,含有1个可以二聚的CRD;②串联重复型,包含由2个短肽连接的CRD;③嵌合型,1个CRD和1个胶原蛋白样重复结构域[2-4]。半乳糖凝集素在动物体内广泛分布,不仅存在于细胞内的各种部位(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也可通过非经典途径在细胞外分泌,沉积于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中或与细胞膜结合[5-7],它们没有特定的个体受体,但每一种都能与含有适当寡糖的细胞表面或细胞外基质糖蛋白结合。1975年在电鳗的电器官中发现动物体内的第一种半乳糖凝集素,最初被称为电凝集素(electrolectin),即如今的半乳糖凝集素1(galectin-1,GAL-1)[8]。GAL-1属于半乳糖凝集素家族的原型成员,是发现最早、研究最深入的半乳糖凝集素。以下主要介绍了GAL-1的蛋白结构、生物学功能,阐述了其在鹿茸再生过程中的作用,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以期为更深入研究GAL-1蛋白的功能及其在鹿茸再生过程中的调节机制提供参考。
1 GAL-1的生物学功能
1.1 GAL-1的基本特征
GAL-1是由位于染色体22q13.1上的GAL-1基因编码,4个外显子通过剪切组装成600 bp的转录本编码135个氨基酸[9]。GAL-1的折叠由2个反向平行的β-片组成,2个β片分别由5和6个相邻的β-链构成。GAL-1在溶液中通常以二聚体的形式存在,每个单体的N-端和C-端位于二聚体界面,而聚糖结合位点位于二聚体的相对两端。二聚体的完整性主要是通过疏水核心的相互作用来维持,疏水核心是由2个亚基的Leu4、Ala6、Ile128、Val131和Phe133疏水侧链组成。另外,2个亚基的Val5、Ser7、Val131、Lys129和Phe133残基骨架建立起了氢键网络[10]。GAL-1序列中6个半胱氨酸残基的存在使其进入细胞后快速氧化形成二硫键限制了GAL-1的聚糖结合活性。然而,一旦与膜表面受体结合后,即可保持稳定的结构继续发挥作用。所以,根据氧化还原条件的不同,GAL-1可以为单体(氧化状态)或同源二聚体(还原状态)的形式存在[11]。半乳糖凝集素的CRD识别来自细胞表面受体和细胞外蛋白聚糖上的N-乙酰乳糖胺残基,如整合素、白细胞唾液素(leukosialin,CD43)、白细胞共同抗原(leukocyte common antigen,CD45)、纤连蛋白、黏蛋白和层黏连蛋白,因此,GAL-1与细胞增殖、黏附、迁移、存活和信号传导等关键细胞过程有关[12]。二聚的GAL-1可以与细胞膜上多种糖蛋白建立细胞表面的微型区域,这些微型区域在细胞表面起到介导信号的作用,并通过控制内吞作用决定受体的稳定性[13]。例如,二聚GAL-1能够通过与整合素受体相互作用来控制同型肿瘤细胞的黏附,或者通过识别细胞外基质蛋白上的多糖(如层黏连蛋白或纤连蛋白)来控制细胞的迁移和侵袭[14]。所以,GAL-1的表达或功能失调通常与疾病有关,最明显的是炎症性疾病和癌症,另外GAL-1表达的增加与许多癌症的低存活率相关,这是由于GAL-1能够抑制抗肿瘤免疫反应,诱导肿瘤内血管生成和促进肿瘤转移[15-17]。
1.2 GAL-1在细胞增殖中的双向调节作用
Wells等[18]纯化了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mouse embryo fibroblasts,MEFs)分泌的具有细胞抑制活性的蛋白,随后根据胰蛋白酶消化多肽后的氨基酸序列克隆了该蛋白的cDNA,并将这种蛋白命名为小鼠β半乳糖苷结合蛋白(mouse β-galactoside binding protein,mGBP),即如今的小鼠GAL-1蛋白。Wells等[18]在不同细胞周期的MEFs中添加重组GAL-1蛋白会导致细胞阻滞在G2期,而在G0期MEFs中添加GAL-1重组蛋白会抑制血清对细胞的刺激作用,阻止其重新进入细胞周期。中和单克隆抗体进一步证实了内源性GAL-1蛋白的细胞抑制活性,在处于G0期的细胞中添加这种抗体可以恢复血清的刺激作用,细胞重新进入细胞周期[18]。进一步研究发现,用GAL-1处理3种致癌潜能不同的人乳腺细胞系发现,在所有细胞系中GAL-1在细胞进入G2期之前诱导了细胞周期阻滞[19]。GAL-1还可以通过调节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TCR)信号通路和抑制白介素2(interleukin-2,IL-2)的产生来抑制新鲜分离的小鼠胸腺细胞的增殖[20]。然而,GAL-1不直接作用于细胞周期的调控,有证据显示,GAL-1需要与α5β1整合素相互作用,进而抑制RAS-MEK-ERK信号通路和细胞周期依赖性蛋白激酶抑制因子(cyclin-dependent kinase inhibitor 1B,p27)的连续转录诱导以达到抑制细胞增殖的作用[21]。Fischer等[21]确定了p27蛋白启动子中的2个特异蛋白1(specificity protein 1,SP1)的结合位点,它们是GAL-1反应的关键位点,RAS-MEK-ERK信号通路被抑制后,SP1的苏氨酸磷酸化减少,增加SP1的活化及其与特异性序列的DNA结合,从而导致p27的转录上调。此外,GAL-1诱导细胞周期依赖性蛋白激酶抑制因子1A(cyclin-dependent kinase inhibitor 1A,p21)转录,选择性地提高p27蛋白的稳定性,GAL-1介导的p27和p21的积累抑制了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2(cyclin-dependent kinase,CDK2)的活性,最终导致细胞周期阻滞和生长抑制[21]。Lee等[22]在小鼠胚胎干细胞(mouse embryonic stem cells,MESCs)的研究中却得出不同的结论,GAL-1诱导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和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磷酸化从而抑制p27蛋白,促进细胞周期蛋白的表达从而诱导MESCs的DNA合成。在胰腺星状细胞(pancreatic stellate cells,PSCs)中,GAL-1通过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κB,NF-κB)、c-Jun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和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ERK)通路的激活协同促进趋化因子的产生和诱导细胞增殖[23]。此外,GAL-1还可以促进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NSCs)的增殖[24]。由此可见,GAL-1在细胞增殖中可以起到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这种看似矛盾的促进和抑制,高度依赖于细胞类型和细胞激活状态,也可能受到单体与二聚体不同形式或细胞内与细胞外形式相对分布的影响。GAL-1对细胞生长的调节还表现出2种特性:双向调节作用和细胞类型特异性。Adams等[25]研究显示,高剂量的GAL-1具有独立于自身的糖结合活性,抑制细胞的增殖;低剂量的GAL-1具有诱导细胞增殖的作用,但易受乳糖抑制。在早期造血细胞中同样证明了这一点,高剂量的GAL-1(10 μg/mL)显著降低造血祖细胞的生长,这种抑制作用并不会被乳糖阻断,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凝集素的β-半乳糖苷结合位点;相比之下,低浓度的GAL-1(10 ng/mL)增加了粒细胞-巨噬细胞和红细胞集落的形成[26]。上述数据表明,GAL-1具有独立于自身糖结合活性的生长抑制位点,为确认β-半乳糖苷结合和生长抑制位点的独立存在。Hirabayashi等[27]通过创建β-半乳糖苷结合活性缺失或降低的GAL-1突变体,并验证它们的生长抑制作用,三级结构的测定和诱变研究结果表明,His45、Asn47、Arg49、Trp69、Glu72和Arg74参与或影响糖的结合。Zhang等[28]通过定点突变对GAL-1负责生长抑制活性的位点进行定位,其中包括1个表面环(残基25~30)和2个内部β-链,与糖结合位点明显不同。Yasumitsu等[29]从美国牛蛙中分离得到高纯度的GAL-1,其对人早幼粒急性白血病细胞(HL-60)、单核细胞人白血病细胞(U937)和人慢性髓原白血病细胞(K562)等均有明显抑制作用,但对人结肠癌细胞(Colo 201)和小鼠乳腺肿瘤细胞(FM3A)均无抑制作用。重组人GAL-1蛋白抑制肝细胞瘤和骨肉瘤细胞的生长效果显著,而抑制HeLa细胞的生长则不明显[30]。然而,GAL-1具体如何实现细胞增殖的双向调节和细胞类型的选择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1.3 GAL-1与血管生成
GAL-1在诱导血管生成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GAL-1缺失的妊娠小鼠中,由于胎盘的血管化不足而造成胎儿生长延迟[31]。最近的研究显示,GAL-1也是肿瘤内血管生成的关键参与者,如在小鼠模型中,肿瘤细胞可以通过分泌GAL-1刺激肿瘤内血管的生成,与之相反,GAL-1敲除小鼠中,不同肿瘤模型中的血管生成均受到阻碍[32],且肿瘤内皮细胞还可以摄取外源的GAL-1,刺激其增殖和迁移[32]。用GAL-1抗体可以抑制小鼠体内异常血管生成,促进肿瘤消退[33]。此外,在肝癌、高级别浆液性癌、胃癌、胶质母瘤和多发性骨髓瘤中,GAL-1表达都与微血管面积呈正相关[32,34-37]。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结合酪氨酸激酶细胞受体(receptor protein tyrosine kinase,RPTKs)调控了大部分内皮反应,如内皮细胞(endothelial cellls,ECs)的增殖、迁移和成管[38]。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VEGFR2)作为VEGF的主要受体,具有更强的促血管生成活性,比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1(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s-1,VEGFR-1)具有更高的酪氨酸激酶活性[39]。在视网膜病变中,GAL-1直接或间接地导致VEGFR2的磷酸化上调,缺失GAL-1可抑制脉络膜新生血管生成,同时抑制VEGFR2及下游分子的表达[40]。嵌合于VEGFR1/2中充当诱饵受体的阻断剂—阿普西柏(aflibercept),利用与GAL-1更高的亲和力,与GAL-1的受体竞争性结合,可抑制GAL-1诱导的血管生成作用[41]。Hsieh等[42]指出,在口腔鳞状细胞癌相关内皮细胞中,GAL-1并不直接与VEGFRs结合,而是通过识别ECs上的糖基化受体神经毡蛋白-1(neuropilin-1,NRP1)促使VEGFR2的磷酸化上调,NRP1/VEGFR2介导的MAPK/SAPK1/JNK信号通路被激活,以增强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GAL-1似乎是独立于VEGF诱导血管生成的信号。肿瘤中VEGF的靶向治疗,包括封锁VEGF-A信号、抗VEG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或受体酪氨酸激酶(receptor tyrosine kinase,RTK)抑制剂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43]。但抗VEGF难愈性肿瘤会释放替代VEGF的血管生成信号,具有VEGF抗性的肿瘤中的GAL-1处于高表达状态,最终肿瘤会重新生长。肿瘤内皮细胞表面糖基选择性调节GAL-1的结合,GAL-1在识别VEFGR2上的N-聚糖后激活VEGF样信号[44-45]。因此,抗GAL-1与抗VEGF治疗联合使用可作为一种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策略。
1.4 GAL-1与免疫抑制
活化的T细胞分泌GAL-1(静息期的CD8+T细胞几乎不表达,活化的CD4+、CD8+T细胞均表达),重组GAL-1蛋白可以将细胞周期阻滞在S期和G2/M期,抑制抗原诱导的T细胞增殖[46]。另外,GAL-1上调活化的T细胞膜Ⅱ型干扰素受体(IFN-γR)α和β链的表达,这使活化的T细胞对IFN-γ诱导的凋亡敏感[47]。研究证明,GAL-1通过识别末端半乳糖残基β-1,4连接到N-乙酰乳糖胺(LacNAc),LacNAc存在于不同的细胞受体中,包括CD43、CD45、早期激活抗原(early activation antigen CD69,CD69)和前B细胞受体(pre-B cell receptor,pre-BCR)等,诱导活化的T细胞凋亡[48-50]。GAL-1有作为CD8+T细胞的自分泌负生长因子的作用,可能是效应T细胞通过分泌GAL-1抑制自身增殖或阻止幼稚T细胞进一步诱导,确保在抗原被清除后免疫反应适当下降。如在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中,CD8+T细胞则表达GAL-1抑制炎症反应[51]。大鼠在约束应力的刺激下,GAL-1在脾脏和胸腺中累积,通过调节CD45免疫反应性淋巴细胞影响脾脏和胸腺的免疫耐受,代表预防心理或生理应激的新机制[52]。提示GAL-1在超敏反应的控制治疗中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多种类型的肿瘤细胞通过分泌GAL-1抑制免疫反应,创造免疫逃逸的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黑色素瘤共培养体系上清中的GAL-1分泌水平与小鼠和人类黑素瘤细胞系中肿瘤诱导的T细胞死亡程度相关,将GAL-1抑制后,共培养的T淋巴细胞的活性则得到恢复[53]。在小鼠黑色素瘤模型中,靶向抑制GAL-1可增强辅助性T细胞1(helper T cell-1,Th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以获得肿瘤排斥反应[54]。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中,GAL-1过表达与浸润的T细胞数量呈负相关,并且GAL-1高表达也标志着预后不良[55]。此外,在神经母细胞瘤中,GAL-1作为免疫抑制因子直接诱导T细胞的凋亡和抑制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的成熟[56]。人胰腺星状细胞分泌的GAL-1诱导T细胞凋亡,促进Th2细胞因子极化,有利于胰腺肿瘤的发展与转移。在恶性外周神经鞘肿瘤中,敲除GAL-1抑制趋化因子受体4(chemokine C-X-C receptor 4,CXCR4)和Ras通路,诱导肿瘤细胞死亡[57]。在胶质瘤细胞中阻断GAL-1的表达,导致肿瘤中聚集Gr-1+、CD11b+骨髓细胞和NK1.1+自然杀伤性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从而损害肿瘤的生长,表明GAL-1对不同的先天免疫细胞和适应性免疫细胞具有多重抑制作用[58]。
2 GAL-1在鹿茸再生过程中的作用
2.1 GAL-1与鹿茸再生
鹿茸是迄今为止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唯一可以周期性完全再生的哺乳动物附属器官,它已经成为再生医学研究的理想生物医学模型[59-60]。鹿茸的再生是指包括软骨、皮肤、血管以及神经等组织在几个月内以远超普通细胞甚至癌细胞的生长速度下实现完全再生[61]。鹿茸再生是基于鹿茸干细胞增殖的过程。近年来,对鹿茸干细胞的定性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生茸区骨膜干细胞(antlerogenic periosteum cells,APCs)和角柄骨膜干细胞(pedicle periosteum cells,PPCs)被鉴定为一种特殊的间充质干细胞,鹿茸干细胞APC、PPC不仅具有间充质干细胞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胚胎干细胞特性,可被诱导成为多种不同类型的细胞[62]。胚胎干细胞关键标记物CD9抗原(CD9 antigen,CD9)、八聚体结合转录因子4(octamer-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4,Oct-4)、同源盒蛋白NANOG(homeobox protein NANOG,NANOG)、myc-原癌基因蛋白(myc proto-oncogene protein,myc)和SRY相关高迁移率族盒蛋白2(SRY-related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protein 2,SOX2)等多能基因均可在鹿茸干细胞中检测到,证明鹿茸干细胞具有强大的分化潜力[63]。
研究显示,GAL-1在鹿茸干细胞中的过表达,与多能基因相互作用,可能参与了鹿茸的再生过程。与鹿脸部骨膜细胞(face periosteum cells,FPCs)相比,GAL-1在APC和PPC中分别上调15和20倍[64]。此外,GAL-1在APC、PPC中通过14-3-3信号通路与多能基因NANOG、N-myc原癌基因蛋白(N-myc proto-oncogene protein,MYCN)和SMAD同源物4(mothers against decapentaplegic homolog 4,SMAD4)相互作用共同调控了鹿茸干细胞的分化[64]。
在脊椎动物中,激活先天免疫是对损伤的早期应答,这一过程很可能与再生程序相关。然而,免疫过程中瘢痕的形成中断了再生程序,在阻止再生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如何抑制瘢痕的产生以激发再生的潜力一直是免疫与再生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鹿角脱落后,伤口暴露,血液流出,在正常机体中,免疫细胞会被大量激活,促使瘢痕产生。然而,事实却是鹿角脱落后的伤口快速愈合,并没有感染发炎。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鹿茸干细胞课题组提取鹿茸生长期(二杠茸)与鹿角脱落后的血液进行GAL-1含量检测,发现相较于鹿茸生长期,在鹿角脱落后,血液中GAL-1含量更高,初步推测血液中高浓度的GAL-1抑制了免疫细胞的活化与增殖,促使机体免疫响应降低(尚未发表)。赵志峰[65]通过RNAi技术抑制APC中GAL-1的表达,与外周血淋巴细胞共培养可以促进淋巴细胞的增殖,说明GAL-1是梅花鹿免疫调控中的关键因子。鹿茸中GAL-1可能与多能基因共同调控鹿茸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并通过调节不同时期GAL-1的表达,抑制机体免疫水平,参与鹿茸再生过程,具体的调节机制值得进一步探索。
2.2 GAL-1与鹿茸神经再生
鹿茸中含有丰富的神经系统,具有很强的空间位置感,对痛觉和不连续的触摸非常敏感。神经对于鹿茸的发生与再生并非必需的,如切断生茸区的感觉神经并未终止角柄的发育与初角茸的生长,但被切断神经的鹿茸均出现发育不良与形态畸形[66]。说明神经在鹿茸再生过程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营养作用与塑形。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鹿茸神经的再生除了鹿茸快速生长延长带来的机械牵拉,其旁分泌因子可能对鹿茸神经生长起主要调节作用[67]。GAL-1可以通过旁分泌的形式促进轴突再生活性[68]。在小鼠生长过程中,GAL-1表达于背根神经节的感觉神经元以及一些脊髓运动神经元。当感觉神经元达到生长目标时,GAL-1会相对降低,但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说明GAL-1可能有助于神经的生长[69-71]。GAL-1的碳水化合物结合活性也是促进成年小鼠神经祖细胞增殖所必需的[24]。Horie等[72]从非洲绿猴肾成纤维细胞(CSO1)中分离出一种能增强轴突再生的因子,后来被鉴定为GAL-1。因为GAL-1在坐骨神经、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元再生过程中都有表达,它可能调节轴索断裂后周围神经的初始轴突生长。GAL-1抗体应用于体内和体外均强烈抑制轴突再生[72],提示GAL-1可能在鹿茸神经的快速延伸及鹿角脱落后断端再生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
2.3 GAL-1与鹿茸软骨内血管形成
GAL-1在生理或病理状态都具有促进血管生成的特性。同样,在鹿茸中也需要大量血管生长,鹿茸血管的发生主要是为满足角柄发育及鹿茸快速生长所需的营养代谢需求。来源于浅层颞颥动脉的血管上行并分支至鹿茸顶部构成鹿茸顶部生长点的血管网,在这期间,皮下血管层动脉经过分支并深入鹿茸内部组织,并在上行至鹿茸顶部过程中分支逐渐增多[73]。这些分支在鹿茸内部逐渐变成静脉,将血液经前软骨层、软骨层和骨层导入鹿茸基部,其密集的血管分布满足了鹿茸快速生长期(2 cm/d)的营养物质需要[73-75]。这也造就了鹿茸的一个独特之处——能够快速自我修复和再生血管化软骨。与之相比,普通软骨具有很强的的抗压和抗撞击的能力,但内部并没有血管分布,因此几乎丧失了自我修复能力[76]。研究发现,血管化软骨并非鹿茸组织的固有特性,异种移植后并未产生含血管的软骨[77]。Li等[78]通过在皮肤和角柄骨膜之间插入不通透膜阻止了鹿茸血管的再生。为确定是细胞间相互接触还是通过游离小分子物质诱导的再生,在皮肤与骨膜之间插入半通透性薄膜(0.45 μm孔径),结果发现血管和神经均实现部分再生,明确了游离小分子物质参与角柄骨膜诱导血管的再生,同时也说明了游离小分子物质诱导软骨内血管生成的可能性,而GAL-1在其中可能发挥了调节作用。
如前所述,在小鼠妊娠期发育过程中缺乏GAL-1会因血管化不足而导致发育延迟[31]。敲除小鼠GAL-1或其抗体的应用,可以抑制体内病理血管生成[32-33]。在多种肿瘤中,GAL-1的表达也与肿瘤内血管的表面积呈正相关。在鹿茸中,不仅鹿茸干细胞过表达GAL-1,在鹿茸的前软骨区和软骨区也广泛表达GAL-1,而这也是鹿茸血管生成的区域。GAL-1作用受体VEGFR2,在鹿茸皮肤及软骨区大量表达,GAL-1使VEGFR2磷酸化上调,激活VEGFRs下游通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成血管作用[79]。在过度增殖的组织中需要大量耗氧,如肿瘤组织,缺氧是其重要的生物学特征。在鹿茸快速生长过程中,GAL-1则可能是其内部缺氧与血管生成的偶联因子。缺氧诱导因子1a(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HIF-1a)可以直接结合到GAL-1启动子区域的缺氧反应元件,诱导其表达[80]。缺氧状态下也可以通过非HIF-1a依赖机制促进GAL-1的表达。在视网膜色素上皮(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RPE)细胞中,缺氧诱导VEGFR1的配体胎盘生长因子(placental growth factor,PlGF)激活Akt/p38/MAPK通路,上调GAL-1增强子区域的激活蛋白1(acvator protein-1,AP-1)亚基磷酸化,上调GAL-1的转录水平[80]。缺氧还可激活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依赖性NF-κB通路,诱导内源性GAL-1与ECs表面的N-聚糖直接相互作用,促进血管生成[81]。总之,GAL-1在鹿茸干细胞中高表达,包括在鹿茸内部组织的广泛分布,可能通过分泌作用与血管内皮细胞结合,在诱导血管快速延伸及软骨内血管生成等方面起到关键的促进作用。
3 小 结
作者探讨了GAL-1生物学功能以及与鹿茸再生过程相关的最新进展。GAL-1在血管生成、免疫抑制、细胞增殖和凋亡等方面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凸显了GAL-1在机体发育和维持正常生理功能中的重要性。此外,GAL-1通过促进肿瘤内异常血管生成和抑制免疫细胞的增殖和活化,以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转移已得到多方面证实。但就目前而言,仍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如在增殖试验中,添加相同生物类型的GAL-1蛋白对细胞的增殖可能是促进或是抑制,也取决于剂量和细胞类型,但具体的分子机制仍待进一步研究。GAL-1参与调节的生物学功能与鹿茸再生过程高度相关,而GAL-1在多种组织类型中的过表达被视为恶性肿瘤进展的标志物。与肿瘤组织相比,在生长更迅速的鹿茸中,GAL-1高表达但鹿茸组织却并未癌变,其中的调控机制仍不清楚。GAL-1在鹿茸中的功能研究以及鹿茸在高表达癌症标志物并维持极速生长的条件下却不发生组织癌变的调控机制值得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究,这可能是癌症治疗、破解鹿茸再生机制和再生医学难题的关键突破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