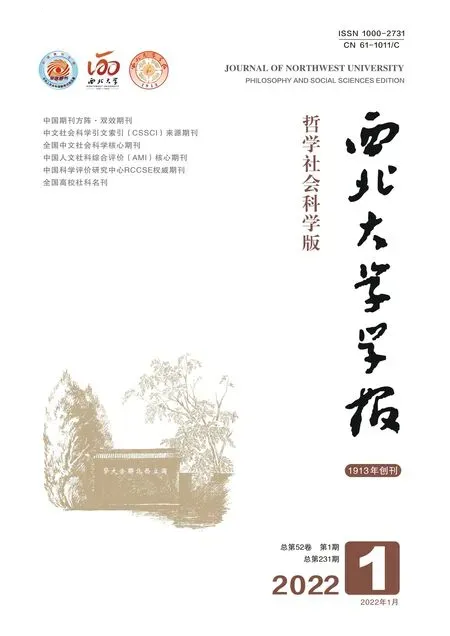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符号属性
——洛塞-郎蒂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及方法
张 碧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作为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意大利学者费鲁奇奥·洛塞-郎蒂(Ferrucio Rossi-Landi)在国际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界享有盛誉。洛塞-郎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立场,以现代符号学为重要方法,在欧美学界开创了极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学界,关于洛塞-郎蒂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及相关思想的介绍和研究基本处于缺失状态。鉴于国内这一研究现状,本文拟对洛塞-郎蒂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和方法依据,在商品交换活动、语言哲学等诸多领域所展开的符号学批评及理论建构进行详尽分析和阐述。
一、商品交换活动中的语言符号特征
在其诸多著作中,马克思曾明确地将商品活动视为一种符号现象:“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1]110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曾从符号学角度对商品活动加以考察,“商品的价值也必定取得一个在质上可以和商品区别的存在,并且在实际交换中,这种可分离性必定变成实际的分离……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字母,是它自身价值的单纯符号”[2]85,从而将商品交换活动看做以符号为基本单位的意义交流活动。可见,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至为重要的理论体系,商品交换理论渗透着十分丰富的符号学思想。恰由于此,洛塞-郎蒂意识到,马克思的商品交换理论,所处理的实际正是一个庞大的符号系统,一如洛塞-朗蒂的学生苏珊·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等人所言:“马克思将商品作为信息加以分析,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商品语言’(language of commodities)和‘商品奥秘’(commodity’s arcanum)的解释上。”[3]187
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商品交换的过程体现出了鲜明的信息交换的特征,正如意大利符号学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所言:“商品间的交换应被视为符号现象(semiotic phenomenon)。”[4]24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艾柯援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论述了商品交换活动中的符号现象及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艾柯此处的论述引用了洛塞-郎蒂的相关观点,而他对商品交换活动的符号价值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到了洛塞-郎蒂的影响,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关于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探讨上,洛塞-郎蒂的论述是颇具代表性的。在洛塞-郎蒂的诸多论述中,往往试图用语言学或符号学知识来考量和分析商品交换活动的诸多属性:“我们可以从符号学角度,权且将社会过程中‘货品(以商品的形式)的生产和流通’和‘句子(以语言信息的形式)的生产和流通’视为同一事物,并加以结合”[5]5,在他看来,商品的交换在使用价值层面进行的同时,也涉及交易人之间置于商品之上关于商品的意识的彼此交易,这样,两个商品在被交易时,与之相关的某些具体信息即符号或所谓“语言信息”也便完成了交换,亦即实现了商品交换活动中特有的符号表意(1)关于洛塞-郎蒂就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符号特征、劳动生产的整体性等问题所发表的论述,参见张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符号批评的范式转换》,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除洛塞-郎蒂外,包括戈德里耶等在内的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同样对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过深入探讨参见张碧《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人类学方法的嬗变》,载于《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年第4期。。
然而,洛塞-郎蒂认为,并非所有商品在交换过程中都同时遵循这两类交换形式,因此,无法从不同商品类型的交换过程中抽象出一种统一范式,原因在于不同商品的制造是基于“不同的目的”,且“适应于其他的需求”[5]61的,也就是说,某些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其符号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物质性间的交换过程可能并不同时进行,而是可能存在彼此相互弱化的情况。例如,某些商品的商品价值本身便主要体现为符号价值,在从生产到消费的诸多环节中,完全是围绕着符号价值来进行的,这种情况在广告宣传品中最为常见。在关于广告宣传品的物质性部分的生产得以展开的同时,其符号价值虽附着于广告的物质性媒介层面,却成为该商品几乎所有价值的体现。此处,洛塞-郎蒂显然意识到了这类商品的符号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某种对立性质,从符号学原理讲,可以理解为符号的在场对其物质性的忽略,或曰,符号价值的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物质性的使用价值,“任何符号物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移动,因此,绝大部分物都是偏移程度不一的表意使用体”[6]28,换言之,在广告宣传品这类商品形式中,符号价值遮蔽了使用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伴随着符号价值的兴起和使用价值的式微,社会生产和交换体系日益呈现出某种符号化的社会景观。洛塞-郎蒂此处的认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符号化倾向,从而极大地响应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左翼思想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文化符号化状态的批判思潮。
当然,洛塞-郎蒂在关于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之间关系的论述上,可能过于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未能指出如下事实,即某些商品类型往往在维系原有的使用价值的情况下,还能够产生某些与使用价值没有直接联系的符号价值,同时,却使得两者间的关系并行不悖。例如,子女赠送给父亲的烟斗,便既有使用价值,亦即用它来吸烟丝,同时,也相应地具有由使用价值引起的符号意义之外的其他象征价值,例如表达“对父亲的拳拳之爱”,等等。在这些情况中,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显然可以同时发生并存在。当然,对于以社会批判为主要价值立场的洛塞-郎蒂而言,似乎无暇顾及这种关于社会文化表意机制细节的思考。
二、“自然符号”的社会内涵及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
作为在人类社会中起基本作用的文化体系,符号自身的属性和特征业已得到了思想界的诸多探讨。学界往往遵循不同的逻辑范畴,对符号进行不同维度的探讨。马克思本人虽并未对符号现象自身的属性、范畴及特性进行系统讨论,但其论述其实在不同角度上,暗含了关于符号现象自然性、社会性等诸多品质的潜在性思考,对此,洛塞-郎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大多数符号必须以某种物质形式作为符码的媒介,在使符码得到接受者的感知和阐释时,也往往使符号自身的物质媒介性引起人类的感知。然而,作为以物质为媒介的符号,其媒介既可能是天然生成,也可能是经由人工制造而成,因此洛塞-郎蒂将符号分为“自然符号”与“社会符号”两种类型。此前,关于这两种符号类型分类的方式,学界的界定往往是:前者的物质载体产生于自然,经由人类的符号分节(articulation)性阐释而成为符号(2)“articulation”一词在符号学中具有不同内涵,本文中主要涉及“分节”和“发出”两种内涵。关于“分节”,可参阅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3至97页。;后者则完全是根据人类的特定需求而被制造和应用的。洛塞-郎蒂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角度,对这种认识做出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在《巴黎手稿》中进行过“人化的自然”这一著名论述,认为人类生存于其中的、作为对象世界的环境,是经过人类的劳动实践加工之后的产物。根据这种认识,自然材料在得到人类的实践加工后,也随之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洛塞-郎蒂看来,经由社会实践加工的自然材料,也便在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相应地附带了某种符号意义,随之成为所谓自然符号。
美国符号学家托马斯·西比奥克(Thomas Sebeok)曾提出,动物虽与人类一样,在交往过程中能够使用符号来进行彼此沟通,但严格地讲,这种符号属于遵循“刺激-接受”模式的“信号”形式[7]12。如果人类和动物的符号形式全然一样,那么对于人类而言,符号也便与动物的单一交际模式一样,成为一种生理性本能;人类与动物在制造符号的能力方面,也便不存在差异,人类对自然的“人化”实践也随之失去了意义。因此,洛塞-郎蒂提出,人类的符号系统的形成,是人类在逐渐摆脱其自然属性、使之具有社会属性之后,在人性方面的再次升华,“在人类实现劳动分工、并由此具有了使用和交换的能力后,在这两者之间的辩证性出现时,人类的纯粹自然性的进化,便带上了‘二次进化’的过程”[5]12。这种认识,显然是对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关于“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著名论断的延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认识从马克思主义“自然的人化”角度,对符号的社会属性进行了再次强调。由此可见,洛塞-郎蒂更多的是从人类社会诸多活动的角度来界定符号的,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种“自然的人化”作用,所谓“自然符号”,便同样应被视为人类在实践过程当中根据其特定的内在尺度,将主体意志投射于对象之后的产物,因此在本质上,“自然符号”与“社会符号”一样,在本质上属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和产品,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则仅仅体现于工艺水平的高低上。
洛塞-郎蒂认为,在马克思关于符号现象的论述中,事实上涉及非语言(non-verbal)符号和语言(verbal)符号两种符号类型。前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交换的论述中有所体现,后者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人类语言符号现象的论述相关。按照马克思的这种关于语言符号的观念及前述关于“自然的人化”的论述,那么可以由此判断,无论是非语言符号抑或语言符号,都像洛塞-郎蒂所界定的那样,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产物,也便因具有社会属性而属于社会符号的范畴。对这两种符号类型的关系,洛塞-郎蒂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强调了两者所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洛塞-郎蒂的界定方式中,语言符号是由人类的语言、文字所构成的符号系统,非语言符号则包括除语言符号外,人类的肢体语言以及其他所有经过人类实践活动改造而成的符号系统形式,例如政治活动、司法活动,尤其是经济市场中的商品交换活动,都是明显的非语言符号系统[8]66-67。洛塞-郎蒂认为,语言符号的符号价值或功能在表意实践方面更加纯粹,亦即除基本表意功能外,不发挥其他使用价值或功能;相应地,非语言符号则除了发挥一般符号的表意、交际功能外,还可能因其载体的物质属性而发挥某些实际使用功能或用途。尽管两种符号类型在表意方式、符码形式、符号载体等方面存在质的差异,然而由于都与人类行为有关,因此在洛塞-郎蒂看来,两者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即它们都可以被统摄到某种有机性(organic)范畴之内,能够通过某种外在环境的中介和协调作用而实现相互转换,其中,语言符号最为典型,原因在于,一旦语言由说话者说出后,便可能相应地引发对外界环境的影响,并由此逐渐形成某种持续影响外在环境的非语言符号体系,例如体现语言符号中的观念意识的图画、艺术品,等等,“它们能够构成一种普遍化、超个体的体系”[5]20。换言之,两种不同类型的符号形式,能够由具体的媒介方式而实现形式的转换。
同时,洛塞-郎蒂认为,两种符号形式往往遵循某种共有的语法关系,因此,两者之间在通过语义链所表述出的语法结构方面,具有异质同构性。作为语言符号而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语言的发出(articulation)当然是主体意识通过语法规范而实现的表达,而非语言符号则同样能够从某种观念意识出发,显示出与语言符号的语法关系的一致性,尤其是就作为非语言符号的劳动过程而言,更是这种人类的观念意识及其语法特性的体现。
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人类往往能够在思维中预先设定某种可能加以展开的行动模式,“认识超越于现实本身,把现实纳入可能性和必然性的范围之内”[9]52。洛塞-郎蒂同样认为,人类思维能够预先构思出某种行动模式,但与皮亚杰不同的是,在洛塞-郎蒂看来,人类的劳动,往往是其自身出于对某种具体的社会需求、劳动欲望的现实逻辑的判断并在其作用的促动下,在意识中所形成的语法观念或符号意识的外化的产物,而这种观念和符号意识由人类的客观社会活动决定并形成。显然,这种基于唯物主义的认识方式,与皮亚杰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认识有很大差异。例如,在制造一把锄头前,人类在特定的社会生产需求和意图的建构作用下,在心理世界形成了这样一种符号意识:应当制造一个工具,用它来锄地、刨去多余的杂草等。此处,工具作为一个施动者,通过锄地这一行动,形成了某种效果,或达到了除去杂草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其意识中,这个工具,即锄头,能够作为主语,通过谓语“锄”,作用于宾语“地”,由此体现出“锄头锄地”这样一个完整的语义链条。因此,人类能够在其意识中形成遵循“主”(锄头)“谓”(锄)“宾”(地)的句法结构,并以此既作为“锄头锄地”的话语语义逻辑,又将其作为判断和决定锄头用途的基本行动逻辑,亦即作为其从事劳动实践的具体指示方式(3)在某些语言中,宾语在谓语之前,但这不影响主、谓、宾语间的逻辑关系。。这样,“锄头锄地”这一实践活动,便显示出人类从高级别思维维度来审视与锄头相关的话语及实际活动的语义链,“它们形成了某种真实关系,构成了一种话语(一种相互连接的句子的群体)”[5]22。人类思维作为这种语义链的“元语言”,是描述、解释和生成这种劳动行为的语法的内在“语言结构”。显然,洛塞-郎蒂此处将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归纳为索绪尔所述的、且深藏于人类意识中的横组合关系:“我们正是在所有语义关系的基础上,在物的层面,来判断话语的模式。”[5]23也由此通过人类生产活动所遵从的语法结构,论述了非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可能具有的转换关系。
当然,洛塞-郎蒂也意识到,对某些话语而言,不同对象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成立的,例如“锄头锄钢铁”这句话在现实逻辑上是不成立的,那么,人类思维便会根据这一现实逻辑,判断这一话语形成了一种不符合现实的伪命题。这样,这一话语及其认识也便无法从现实的逻辑层面,使人类在思维中形成相应的语法观念。总之,洛塞-郎蒂此处将现实中的行为逻辑,作为思维中判断话语逻辑的基础,从而体现出了鲜明的唯物主义原则。
三、劳动与人工制品的符号学意义
洛塞-郎蒂注意到,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劳动”(work)这一概念主要在以下两个意义上被使用:第一,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实践性改造;第二,工人制造产品的过程。尤其在《巴黎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性地接受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劳动对于人类社会的本质作用,并以此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特征。在马克思的论述基础上,洛塞-郎蒂看到了这一概念极为复杂的其他内涵,并对“劳动”做了十分细致的分析。
在洛塞-郎蒂看来,劳动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activity),但并非所有人类活动都属于劳动的范畴。洛塞-郎蒂借黑格尔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提出所谓“活动”只是人类为满足一般欲望或需求的行为,且在追求这种欲望的过程中,并未将其裹挟着主体意志与目的行动作用于对象之上,亦即仅仅使产品带上主体关于工具用途的最基本的符号意识。然而,“劳动”则不仅是劳动者将其意志、目的投射于对象的体现,而且能够使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将自身的价值尺度投射于劳动对象之上,使自身的人性品质通过这一对象而得到某种升华,“活动是一种没有产品出现的耗费(expenditure);劳动则指向某种目标”[5]37,在劳动过程中,人类能够将自己的主观认识、价值观念等,按照某种特定的规划方式——亦即马克思所说的“内在的尺度”作用于对象,这便是劳动的本质,也是人类超越一般现象并实现本质对象化的体现。在洛塞-郎蒂看来,劳动的过程,也是主体将自身的某种审美品质通过劳动对象而加以符号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的国民经济学理论中,“产品”(product)恰指代人类从事劳动或社会生产活动的成果形式。当然,洛塞-郎蒂并未直接沿用这一概念,而是使用了人工制品(artefact)这一术语(4)洛塞-郎蒂有时根据语境的需要,以“器具”(utensil)等表述来指称这一概念。,以此指代人类对自然物进行劳动加工之后的产物。自然物受到人类劳动活动的加工,即成为人工制品;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劳动加工的人工制品,往往带有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投射于其上的主体性价值尺度。根据洛塞-郎蒂的论述,人工制品在被制造的过程中,人类业已将自己的制造意图赋予了这件制品,从上述皮亚杰心理学角度来解释,洛塞-郎蒂认为人类的心理认知结构能够预先对某种事物及行动做出规划,其中亦包括对人工制品基本属性及用途的构思与规划,同时,劳动者更是将其特有的价值意义、也是符号意义投射在这件制品之上。因此,人工制品的符号特征体现在:在作为劳动的被制造过程中,人工制品携带了生产制造者特有的主观意图和价值维度。例如,一截木头有可能被刻制为木雕,或被制作成拐杖,那么它恰是制造者在某种预先设定的意义图式的引导下,对木头进行加工后的产物。这段木雕或拐杖,既是实用性的生活器具,同时作为人类劳动的产物,也带上了劳动制造者投射于其上的某种主观审美性价值维度。
在洛塞-郎蒂看来,作为符号体系的语言同样属于人工制品范畴。从人类学角度讲,人类的声音本具有自然属性,然而,人类必须通过彼此之间声音的交流,而逐渐使其生产活动群体化、社会化。这样,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日益进步和复杂化,在这个过程中,也必然不断地给自己的声音加上更多其他音响因素,使其易于表达愈加复杂的社会意义,“声音对象存在于自然之中……它作为材料,不断加入到此前产品的复杂的生产过程之中”[5]33,因此,在人类社会中,大部分声音都是人类为实现某种交际活动,而从其心理意识结构和价值尺度出发,特意为其自然声音赋予某种意义和价值后,并经过不断地加工和修缮,而制造出的一种复杂的表意工具。在文学创作或其他诉诸语言符号的活动中,语言文字往往更是人类表达特定情感或思想内涵的制造品,其人工制品的属性也便更加明显,这也解释了马克思将文学创作视为生产活动的原因。由此可见,洛塞-郎蒂不仅将语言视为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交流工具,同时在他看来,语言符号体系自身就是人类依据其主观意志和价值尺度,对现实对象进行符号化加工与改造之后的产物,也便当然成为经过人类劳动过程后而生产出的人工制品结晶。
总之,洛塞-郎蒂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劳动及人工制品等概念的发生及属性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在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实践中美学属性的论述做了一定的延伸性探讨。
四、对劳动过程的符号学考察
人类的劳动过程是一个由诸多阶段构成的整体行为,而在洛塞-郎蒂看来,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同样体现出某种符号特征。洛塞-郎蒂的另一位学生、意大利学者奥古斯托·庞齐奥(Augusto Ponzio)指出,洛塞-郎蒂在对生产过程各阶段之间关系的分析中所运用的符号学方法,是其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独到贡献[10]190-191。洛塞-郎蒂关于劳动阶段关系的符号学分析,体现为对其系统性特征等方面的探讨。
马克思将人类的一般劳动过程分为若干个阶段。洛塞-郎蒂通过对诸多阶段的分析,认为至少应该包含这样几个因素:劳动时所使用的材料、劳动工具、劳动者、劳动过程、劳动目的和劳动产品[5]39。洛塞-郎蒂认为,由于劳动过程是由诸多劳动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性活动,因此在劳动过程中,诸多劳动环节的展开,也是劳动信息的产生、发送和接收的过程。正如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将符号信息的一般传播模式描述为“发送者、语境、信息、接触、符码和接收者”[11]175,洛塞-郎蒂认为,上述几个方面,也从劳动信息的角度,勾勒出了社会劳动过程的一般情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分析方式将劳动的诸阶段置于一个整体系统之中,试图以整体视域来判断每个部分的价值意义。显然,这种观点带有某种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系统论特征。
总而言之,对于各个阶段而言,每个阶段都是整个劳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一旦它们共同构成这一整体,则每个部分将失去其相对的独立属性,而必须被置于这一劳动情境的整体中,方能获得其价值:“所有劳动情境都构成了一种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组成部分都失去了各自的原有特征,亦即辩证性地‘降了格’(degrade)。”[5]40这种观点,从符号学角度强调了劳动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有机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特征,换言之,在劳动过程中,诸多劳动环节带上了整体结构中的符号特性,彼此处于某种协调性机制之中。同时,洛塞-郎蒂却又提出,“劳动者自身能够发挥材料、或劳动工具、或劳动目的、或不同劳动的产品的功能”[5]40,将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要素的功能视为同等的生产要素。这种观点从劳动过程的整体性来审视劳动者,将劳动者视为生产活动的一分子,明显带有某种系统论的认识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表述在事实上进一步表达了洛塞-郎蒂的如下观点:诸多劳动者,以其各自的劳动方式,在共同构成某种劳动情境的同时,每个劳动者也在这种劳动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在劳动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功能、扮演的生产角色,不断将其从事的工作内化为自己在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position),亦即在意识或无意识的过程中,对其自身在生产活动、乃至社会活动中的角色及功能进行了自我确证。相对于马克思所描述和阐释的劳动者的“异化”状态,洛塞-郎蒂更加强调劳动者在现代社会中结构化、体系化的生产活动中所具有的功能化、符号化的人性状况,由此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进行了独到论述,也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主题传统。
五、结 语
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批评往往通过对社会文化文本的深入剖析,发掘其中所具有的隐喻含义。与之不同的是,洛塞-郎蒂则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包括商品交换活动、劳动等人类实践活动中所包含的符号功能进行深入分析,并对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等符号类型及其关系进行细致考察。这种认识,不再是将符号学视为一种简单的方法论工具,而是试图从符号现象角度,探讨附着于诸多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表意过程。洛塞-郎蒂的研究,试图在符号活动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间架起桥梁,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进,同时也极大地开阔了符号学及语言哲学的探讨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