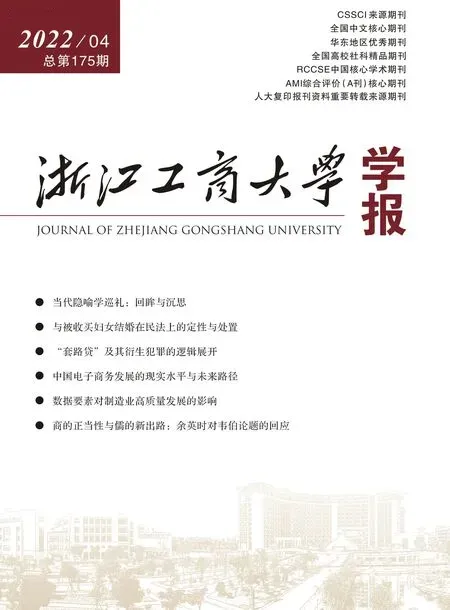商的正当性与儒的新出路: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
王小章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余英时先生去世后,笔者拿出历年零星购置的他的一些著作又翻了翻,特别是重温了他回应“韦伯论题”的一些篇章。重温引出了一点新的感悟: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一方面是对论题的一种承接,即延续了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世俗经济活动之关系的讨论,并对韦伯关于儒教伦理的观点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是对论题的一种转换,即在对这个论题的讨论中,转变了韦伯的关怀,或者说,引出了一个在韦伯那里所没有的新的关怀,那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学及其担纲者“士”(“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的命运和出路,这自然也是余英时毕生治学的一个核心主题或者说关切。
一、 “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
此处所谓的“韦伯论题”,指的是韦伯最初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而后在关于中国宗教、古代犹太教、古代印度教等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的一个问题,因此,它虽然包涵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问题,却不仅仅限于这个问题,而应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为宗教伦理与世俗经济活动的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韦伯自己为他的比较研究计划所拟的题目较好地表达了“韦伯论题”的意涵。不过,这个题目对于我们更全面地领会、发掘“韦伯论题”的意涵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误导,即更容易使我们从宗教伦理如何作用于世俗经济活动这个方向来理解韦伯的研究,而忽略从另一方向来领会蕴含在韦伯研究中的一个意图,即为现代世俗经济活动,特别是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寻求伦理正当性。
长久以来,学界确实主要是从新教伦理如何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角度来认识理解韦伯论题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这一论题的正面展开,而关于中国宗教、古代印度教、犹太教之经济伦理的研究则是对于唯有新教伦理才能生发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反面论证。从总体上看,这种理解应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作为一项科学的比较研究工程,韦伯关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研究确实主要措意于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现代理性资本主义之精神的历史起源问题,换言之,他肯定,清教,特别是加尔文教的世界观催生了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哺育了近代理性职业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1]141不过,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蕴含在韦伯论题中的另一面相。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寻找宗教伦理上的起源,从另一角度看,实则也就是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至少是曾经承载的伦理精神,就是追寻作为一种世俗经济活动的理性资本主义的伦理正当性。因此,揭示新教伦理如何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实际上,韦伯本人也曾明确认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是“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而不能仅仅被看作只是一个要么“漠视伦理”,要么“理应受到谴责”,但又不可避免而只能“被容忍”的单纯事实[1]41。就此而言,对于韦伯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除了从新教伦理如何催生资本主义精神这个维度来解读,还应该从“经济行为之伦理意涵”的维度来领会。
韦伯指出,“在‘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这样一种意义上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其最重要的敌手,就是对待经济活动的“传统主义”态度[1]41。“传统主义”的态度将工作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苦难,从事它只是为了维持一种适当的生活水平,在此前提下人们往往宁愿少做事而不愿多赚钱,同时也不愿采用和适应新的更高效的工作方式;传统主义的经济态度一方面在天主教的伦理观下将追逐利润、金钱看作道德上可疑的品行,认为有利息的借贷在道德上是不允许的,只能为非天主教徒所使用,另一方面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贪婪、肆无忌惮的占有、寡廉鲜耻的投机冒险等又随处可见;此外,传统的态度一方面因对金钱利润怀有一种罪恶感从而导致获利者在宗教活动或公共节日上不吝开销,以图缓和上帝的愤怒或邻里被冒犯的情感,另一方面经济收入的多余部分则被无节制地花费在个人的享乐或炫耀消费上面。与“传统主义”对于经济活动的态度截然相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态度则把工作本身视为一种美德和义务,勤勉是一种高尚的、令人尊敬的品质;它不仅认为有利息的借贷是允许的,而且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职业。一方面,它决绝地摈弃传统主义对待利润、财富的态度,认为:“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1]127;另一方面,它又使理性的职业人(入世苦行的清教徒)将自己看作“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代”[1]133,若非为了上帝的荣耀,他无权以任何非理性的方式花费哪怕一分钱。概括地说,通过与传统主义态度的比较,韦伯实际上从“如何赚钱”(拒斥一切非理性、不道德、不合法的途径,坚持以和平的、合法的、理性的方式来获取和积聚财富)、“如何看待赚钱”(以正当的手段挣钱,赚钱是一项在道德上正当的、应该的、必需的事业,是“天职”)、如何花钱(作为受托管理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的人,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要有所交代,除非为扩大财富而投资,除非为荣耀上帝,其他的非必要的开支都是不正当的)三个层面,揭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下,世俗之经济行为的伦理意涵。[2]由此,韦伯一方面彰显了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下世俗职业之“内在的准则”[3]104有别于传统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则追寻到了这种世俗经济行为的伦理正当性:“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至于遭到非议,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1]135,137-138。
值得一提的是,韦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的这番追索,恰恰是在这种伦理精神已经隐遁剥落的背景下展开的。许多人都熟悉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尾处所发出的悲凉浩叹:“清教徒想在一项职业中工作;而我们的工作则是出于被迫。”韦伯所置身于其中的现实是,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运行已经走上例行化的道路,深受“工具理性”的宰制,另一方面,“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如此发展的前景,很有可能将是“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1]142-143。而要避免这种情景,唯有为资本主义重新注入一种伦理精神。因此,韦伯的这番追索,在竭力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学术话语之下,潜藏着一个隐秘的意图,即要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但是,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韦伯力求“在新教的历史中追求一种当代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中所缺少的精神尊严。但韦伯对历史的追寻是一种徒劳无功的胜利。他发现了他所寻找的精神,但是他无法把它带到现在。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度量那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讽刺性的鸿沟,并提醒那些倾听他的听众说,在以前,这种精神曾经是存在过的”[4]104。
二、 近世儒学与商人精神: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
韦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联系(用他的话说,即“选择性亲和”)的研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和所谓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儒家伦理和现代经济发展或者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而对韦伯在《中国宗教》中所提出的观点提出质疑。余英时即是这些重新思考和质疑者中的一位重要代表。在1985年发表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立足于中国两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中唐以后宗教的入世转向和16世纪以来商业的重大发展,他提出了一个自称为“韦伯式”(Weberian)的问题:“中国儒、释、道三教的伦理观念对明清的商业发展是否曾发生过推动的作用?”[5]219,213也即,上述的两个历史事实,是否有着重大的关联?由此,余英时一方面承接了韦伯的论题,另一方面则在这一论题的讨论中质疑了韦伯的结论:“在《中国宗教》,他(韦伯)所问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他承认中国有‘理性主义’,当然更肯定儒家的入世性格,但是中国的‘理性’与‘入世’,在他看来,都和基督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派不同。所以从思想根源上着眼,他断定中国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精神’。……我(余英时)所特别感兴趣的则是下面这个问题: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是否如韦伯所说的,和新教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不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我的答案恰好与韦伯相反。”[5]221-222
需要指出的是,余英时虽然质疑韦伯关于中国宗教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观点,但是,在下面这个基本立场上则是与韦伯一致的,那就是反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单因素决定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是一个涉及到制度性、技术性等许多因素的异常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绝不是诸如新教伦理这样单一的精神因素所促成的。因此,如同韦伯从来没有认为新教伦理是促使资本主义兴起的唯一力量,余英时通过对中国近世宗教伦理的考察尽管得出了“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但也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中国本来可以自发地走向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换言之,如同韦伯“仅仅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1]143,余英时也是在这一前提下,承接韦伯的论题,尝试性地探究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特别是儒家思想)和商人精神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揭示新教伦理如何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乃是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同样也体现为一体两面。从一个方面或方向,余英时通过梳理考察中唐以后佛教(特别是禅宗)、道教的入世转向,特别是儒家伦理的新发展,力图论证说明,中国的宗教伦理恰好是符合“入世苦行”的形态的(也就是韦伯认为基督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才有的伦理精神),进而,又考察了明代王学试图扭转儒学与社会下层脱节的努力。从另一个方面或方向,即世俗商业活动的伦理意涵的方面,余英时把在韦伯那里实际上作为这个论题的潜在的或者说作为一条副线存在的面相强化为一个凸显的正面论说的内容。通过对明清儒家之“治生”论的叙说,通过对士商关系、儒商关系之变化,以及商人伦理、“贾道”等的分说梳理,余英时多方位地揭示、说明了明清之际“中国商人的精神”,或者说,商人自己的“意识形态”,既分析了勤俭、诚信等经商之道及其与儒家伦理之影响的关系,也说明了在士商、儒(学)商(业)互动中,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俗世商业活动之伦理意义的获得,伦理正当性的提升:商人不再是四民之末,商业也不再仅仅是孳孳为利的“市井小人之事”(陆游语),而是同样可以立功立德行仁义的大事业。
如何看待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以及在这一“韦伯式”问题的探讨中得出的“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应该肯定,他的工作,对于纠正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的误读,特别是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工作伦理,尤其是明清儒家士人对于商业、商人的新态度,不无消翳去蔽的启发;而他把世俗商业活动的伦理意涵这一在韦伯那里作为副线存在的面相强化为一个凸显的正面论说的内容而展开的考察,对于一直以来在所谓“士农工商”的模式下不假思索地以为从商在传统社会始终只是属于“市井小人之事”的末流的陈见,更具纠偏匡正之意义。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余英时所得出的“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也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同样是确凿的呢?笔者认为还不能那样看。
这里首先要说明,“商人精神”实际上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这不仅仅是指两者在内涵上可能存在的区别(比如,从“治生”论的角度把经商挣钱看作人格独立和其他事业的前提或基础,是否等同于清教职业人为赚钱而赚钱的精神?即使是“商人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于经商所怀有的诸如“创业垂统”之类超越性动机[5]325-326,是否能与清教徒职业人的“天职观”同等看待?),更是指两者在社会成员的广覆度上存在的差异。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乃是一个社会整体的精神,它普遍地存在、体现于全体职业人身上,既作为一种伦理约束着又作为一种内在动力推动着职业人的现实行动;而余英时所说的商人精神则显然没有这样的广覆性,它只体现在社会中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即从商者的身上。
明了了余英时所说的“商人精神”与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也就可以进一步来说明何以笔者认为余英时的考察分析尚不足以证明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一般来讲,一种伦理思想要转化为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的、对其现实行动既有约束作用又有动力作用的精神,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接触和接受这种伦理的人们的普遍性;其二,这种伦理对于接受了它的人们是否具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约束力。对于第一点,应该说余英时实际上也注意到了中国宗教特别是儒学与韦伯所分析的西方宗教的区别。尽管明代的王学曾努力改变儒学与社会下层民众脱节的问题,但是,儒学与下层民众的结合显然不能跟西方宗教与信徒之结合相比。余英时指出,基督教各派都有严密的教会组织,通过种种经常性的组织活动,教会对教徒信仰的控制力量是非常强的。一般来说,只要知道某一地区的人们属于某个教派,便能大致断定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包含着哪些具体的教义。也即,教派(如加尔文教)的教义能够普遍地流布影响于全体民众。但中国的情况与此全然不同。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组织,佛道两教虽有寺规与宗派,但与信徒之间的关系根本不能与西方的教会相提并论;儒家在这方面更不必说,典籍中的思想没有通向普通百姓的渠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通常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可能接触到儒学著作与儒家思想,而且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正接受其道德观念[5]224-225。至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识字的广大普通民众,在缺乏像西方的教会组织这样有力的观念、教义传播手段的情况下,则很难接触到孔孟程朱陆王等儒学典籍的思想,更遑论接受其观念。质言之,中国社会中接触和接受余英时所分析的儒家伦理的成员的普遍性与西方社会中接触和接受韦伯所分析揭示的新教伦理的成员的普遍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新儒家的工作伦理确曾产生过现实影响,这种影响也局限于一个并不大的群体,也就是余英时所分析考察的商人群体。
一种伦理思想转化为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的、对其现实行动既有约束又有动力作用的精神的另一个条件,是这种伦理对于接受了它的人们是否具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约束力。在这一点上,余英时似乎没有完全注意到韦伯之论述分析中所包含的“心理学解释”路径,进而在其关于近世宗教与商人精神的分析中与韦伯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实际上跑在了两股道上。韦伯指出,加尔文的“预选说”杜绝了灵魂得救的一切现世途径,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是,迫使每一个信徒都为自己是否被“选中”而深感焦虑,而上帝则绝不给人任何是否获得恩宠的外在标志,于是,信徒的这种焦虑便终其一生处于无穷无尽之中。怎么办?既然没有任何外在标志证明预定的一切,那就只有靠信仰了。按照加尔文的训诫,每个信徒都有责任坚信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而这种信仰的有效性就表现为增加上帝的荣耀,即恪尽“天职”。由于由“预选说”带来的焦虑无穷无尽,通过恪尽“天职”来缓解这种焦虑的心理动力也就永不消退。正如一位知名的韦伯研究者指出的:“韦伯所强调的始终是因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心理约束力对于日常实际行为所产生的作用,而不是新教教义或伦理规范本身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分析,并不是在具体地探讨各种合理化因素或成分是如何由此产生,也不是讨论哪一条教义中包含了有利于经济行为发展的内容。相反,他分析的是,普遍的一种信仰如何在通过教义的变革后,成了普遍适应经济理性主义要求的内在动力。换句话说,并不是‘先定论’带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合理化,而是‘先定论’造成的心理约束力驱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受了合理化要求。”[6]69而余英时的工作,恰恰是检讨中国宗教特别是儒家伦理的“哪一条教义中包含了有利于经济行为发展的内容”。确实,鉴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即使是读过一些孔孟程朱的人,也无法判断其受到了其中哪些道德观念的影响,甚至不能判定其是否受到任何实际的影响,因此,他以历史学家的素养通过对儒商互动、对明清商人言行的考察,努力以经验证据来显示近世商人所受的儒家伦理的影响。但也仅仅是显示了近世儒家与士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看待久已存在的商业及其从业者,后者则从前者那里获得了新的意义或者说新的正当性来源,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关注的历史变化,但是,这与清教徒们在上面所说的那种伴随终生的深切焦虑感或者说心理约束力驱使下全身心地投入世俗职业生活,从而把整个世俗世界变成了一个修道院的情形,显然是不同的。对此,一项关于明清商人职业身份认同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该研究将明清商人的职业身份认同分为价值型和工具型两类,每类可分为A、B两小类。四类认同中,唯有“价值型A”才是对商业完全认同,将经商、积累财富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和途径。其余三类,则要么虽然对从商基本认同,但心下总觉得从商是“迫不得已”,是“眼前的苟且”,业儒才是“诗和远方”(价值型B);要么将从商单纯看作谋生的工具和手段,虽然也没觉得低贱,但终究只是满足世俗的目的(工具型A);要么更进一步将经商行贾看作是丈夫贱行(工具型B)。而历史资料显示,明清商人中,绝大部分持有的是工具型的身份认同,至于持“价值型A”身份认同的,则是少之又少,不超过商人总数的17%[7]。
三、 儒学与儒士的现代出路: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转换
如上所述,通过承接韦伯的论题,一方面,余英时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化,即近世儒家与士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看待商业及其从业者,后者则从前者那里获得了新的意义或者说新的正当性来源,并开始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他想以此证明“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的努力,则并不能说完全成功。不过,笔者同时注意到,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既是对论题的一种承接,同时也包含着对论题的一种论述方向的转换。韦伯的论述,一方面是探寻现代理性资本主义之精神的历史起源;另一方面也是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伦理意涵,并且,作为一个“隐秘的意图”,希望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余英时的论述,则在努力说明近世儒学与商人精神的关系以承接韦伯的论题的同时,表现出一个与韦伯并不同向的关怀,那就是儒学与儒士的新出路。换言之,韦伯关心的是,如何避免那“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宗教禁欲主义支持的“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堕入“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境地,而余英时更为关切的,则是在明清时期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何处才是儒学和儒士得以安身立命之所?
明代以前,从政一直是儒家士人唯一理想的人生正途,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而政治自然也一直是儒学最基本的托命之所,所谓“得君行道”。但这种情况到了明代开始出现变化。在写于1986年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余英时即指出,王阳明试图完成程朱理学所没有完成的任务,即儒家与社会下层的结合。而“新儒家伦理在向社会下层渗透的过程中,首先碰到的便是商人阶层,因为16世纪已是商人非常活跃的时代了。‘士’可不可以从事商业活动?这个问题早在朱子时代便已出现,但尚不十分迫切,到了明代,‘治生’在士阶层中已成一个严重问题”[5]290。十年以后,余英时又写了《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在该长文中,探寻儒学与儒士之新出路的意图就更加明显了。我们知道,儒学从来便是主张入世的,因此所谓“儒学转向”并不是从“出世”到“入世”的转变,而是“入世”之具体方向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从原先单一的政治取向转为社会取向,而社会取向在当时的实质所指即商业取向。余英时注意到,16世纪在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士商合流。一方面,商人的精神生活开始“士大夫化”,商人开始打破2000年来士大夫对于精神领域的独霸之局,转而毫不犹豫地肯定自己的社会存在和价值。另一方面,在商人“士大夫化”的同时,士大夫也开始“商人化”,“贾而士行”与“士而贾行”(或“商而士”和“士而商”)本是在当时同时出现的词汇,士大夫“商人化”在当时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社会现象[5]178-179。这也就是所谓“儒学”“儒士”之“转向”的主要所指。换言之,除了政治之外,商业成了儒学、儒士新的安身立命之地,新的出路。
余英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一转变,即商业何以成为儒学、儒士之新出路的原因。第一,明代的科举名额(包括贡生、举人和进士)并未随人口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小,16世纪即有“士而成功也十之一,商而成功也十之九”的说法,这促使不少士人放弃举业而投身商业[5]164。第二,商人“自足”世界的形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价值观念的改变是很缓慢的,明清时期无疑还有大批商人企羡士的地位,另外,由于商业的兴盛,其吸引力与日俱增,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商不如士的关键在于从社会承认、政治表彰所获得的荣誉,但从明代中晚期开始,商人也可以通过热心公益之举而获得这种荣誉了,这无疑大大提升了商的地位。总之,16世纪以后,商人已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自足”、足以安身立命的世界,这一方面使得一些本已在商的人们宁愿守其本业而不愿踏入高风险的仕途,另一方面也吸引一些士人“弃儒从商”,并在“士商异术而同心”“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下以商行道[5]174-178。第三,明代专制皇权对士人与商人的压迫。明代自太祖开始,便对“士”抱着很深的敌视态度。而自16世纪以降,明代专制皇权的最大特色就是宦官在皇帝的默许下广泛滥用权力,结果是不但朝廷与士阶层互相异化,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商人阶层的权益,这反过来促使士人和商人的抱团联合,相互支援,即“士商合流”[5]188-192[8]89-91。所有这些因素,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了儒学和儒士在十六世纪以后的转向,王阳明从早年之未脱宋儒“得君行道”的意识,到所谓“龙场顿悟”后转向“觉民行道”便是此转向一个典型表征:“‘觉民行道’是十六世纪以来文化、社会大变迁的一个有机部分,其源头则在于因市场旺盛而卷起的士商合流。”[8]93到了晚清,特别是1905年废止科举制度以后,这种转向就进一步直接体现为现代知识人——他们是“士”的现代传人——的“实业救国”意识和精神了。
如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追索是在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学术话语之下展开的,余英时对于儒学、儒士由政向商之转向的探究也是在“价值中立”的话语下展开的,即这一探究本身是一项经验性的考察,而不是规范性的求索。但需要指出的是,同样如同韦伯在科学学术话语之下潜藏着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的意图,余英时的研究同样也包含着一个要为儒学和儒士(及其现代传人现代知识人)寻求和指出新的托命安身之所的、具有价值意向性的动机。而如果联系余英时其他一些文字,那么,这一意向可以说要远比韦伯表现得明显。关于儒学,在1988年的《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中,余英时提出,旧制度崩溃以后,儒学与制度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如果儒学不甘成为游魂而仍想‘借尸还魂’,那么何处去找这个‘尸’”[9]264?在写于1995年的《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中,他又指出,儒家思想与传统建制分手以后,尚未找到现代的传播方式,为此,“近年来我曾对儒家究竟怎样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的问题曾反复思索。我所得的基本看法是,儒家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惟有如此儒家似乎才有可能避开建制而重新发生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9]254。十年之后,在《价值荒原上的儒家幽灵》一文中他又一次提到:“在这个价值荒原上如何把儒家价值重新整顿起来,和现代社会系统进行有机配合,最后使它们能进入多数人的识田之中,这实在是一个艰巨无比的大工程”[9]268。可以说,对儒学或儒家之现代出路的探求在余英时那里是一以贯之的。而与此紧密相连,实际上可以说是同为一体的,就是对“士”的新出路的探求。在《士与中国文化》的自序中,余英时自陈:“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把‘士’看作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所以,‘士’可以是‘官僚’,然而,他的功能有时则不尽限于‘官僚’”[10]128。也即,“士”的作用可以在政治领域,但并不限于政治领域。16年后,在该书的新版自序中,余英时又进一步指出:“‘士志于道’——这是孔子最早为‘士’所立下的规定。用现代话说,‘道’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但这套价值系统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以求其实现的;唯有如此,‘天下无道’才能有可能变为‘天下有道’”[10]134。问题是,明清以来,得君行道已越来越成为士人的一个行不通的死胡同,而清末的废科举更是断绝了士人从政的传统通道,并且士人本身经此也“终于变成了现代知识人”,但是,“‘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10]135那么,当“得君行道”之路完全断裂之后,何处才是作为“士”的现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践行其道的场所呢?至此,隐含于余英时对于儒学、儒士由政向商之转变的探究之下的动机,应该说不言自明了。
通过转换“韦伯论题”的论述方向,余英时考察了在明清时期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许多儒家士人弃儒从商的现象,如上所述,在这一历史考察的背后,隐含着一个为儒学、儒士,特别是为作为儒士后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在科举废止从而“得君行道”之途从根本上断绝之后寻求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的意图。至此,就本文的论旨而言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不过,在打住之前,我们不妨再回到韦伯一下。事实上,对于韦伯来说,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寻求伦理正当性,归根结底是为投身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现代职业人寻求生命的价值依托,从而不至于堕入“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境地,或“为万物皆空的神咒所吞噬”[11]103,进而更在这种世俗职业实践中成就积极的“人格”或“自我”[12]。早在《“道德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一文中,韦伯就指出,在现代世界中,要成就一种“人格”,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工作’,不论这项工作(及其派生的‘时间要求’)可能是什么。”还说:“每一项职业都有其‘内在的准则’,并应据此来执行。在履行其工作职责时,一个人应当全力以赴,排除任何与之不严格适合的行为——尤其是他自己的好恶。有影响的人格并不会通过试图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对每件事情都提出‘个人感受’来显示其自身”[3]104。显然,韦伯在此是在一种更加一般的意义上将“职业”与现代世界中“人格”的成就或者说自我实践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一个人具体投身何种职业,是“以学术为业”,还是“以政治为业”,抑或是“以商为业”并无根本的不同,关键在于你能否将自己从事的职业视作“天职”,并恪守其“内在的准则”,如能,则每一种职业都是安身立命之所。因此,在这个涉及“人生归宿”的层面上,对于韦伯来说,只存在一个现代知识人如何“以学术为业”的问题,而不存在如何去寻求求知本身以外的安身立命之所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层面上,“为知识而知识”与“为挣钱而挣钱”是等值的,都属于各自“为自己选择生命的守护神”。而由此反观余英时的为现代知识人寻求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我们是否可以隐隐感受到从中折射出来的中西知识人之不同的精神世界呢?质言之,对于西方知识人而言,求知本身足以构成一个自足的、可以托付生命意义的精神世界,而对于中国知识人来说,虽然其老祖宗曾言“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但实际上很少真正把求知问道本身认作生命意义的根本寄托,而总是“别有怀抱”。而这种区别,无疑又反过来折射出中西(宗教)伦理精神的不同,或者说,与中西(宗教)伦理精神的不同紧密相关:西方宗教(尤其是清教)从根本上是拒斥、否定现世的,其伦理与现世之间是一种“巨大的、激烈的紧张对立”,世俗生活从根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宗教对现世所取的是“宰制”的态度,[13]310入世禁欲主义的“入世”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始终在天国,“道”或终极的意义只能实现在彼岸世界,而不可能在世俗世界;赋予求知活动本身以意义自足性的,正是对超越的彼岸世界的信仰,或者,这种信仰的现代余绪。中国的伦理精神与此不同,儒教对这个世俗世界采取的是“肯定和适应”的伦理[13]312,“道”或生命的意义就在这个世界中,并且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实现,所不同者,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中的哪个领域去实现,哪个领域容许“道”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