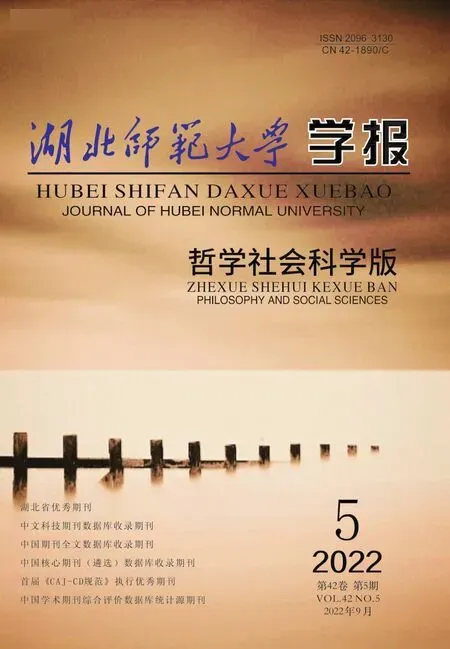四象论与中国意象理论的现代转型建构
——来自胡塞尔和郑板桥的双重启示
曾仲权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浙江大学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笔者在撰写硕士论文《身体美学的现象学研究》[1](p36)时曾提出四象论并用以研究读图时代的身体审美现象[2],在此过程中,笔者就发现四象论可以用来研究和阐释意象,可以成为中国意象理论现代转型的理论创新范式。
在此,笔者先从视觉意象理论的维度阐发四象论的理论内涵,后续再将四象论从视觉意象理论发展到一般意象理论。叶朗先生曾在《美学原理》中认为意象可以从感官感觉角度进行分类,也就是说意象包含视觉意象、听觉意象、触觉意象、嗅觉意象、味觉意象,而其中,视觉意象则是意象的主要类型。朱光潜先生对此就说道:“所谓意象,原不必全由视觉产生,各种感觉器官都可以产生意象。不过多数人形成意象,以来自视觉者为最丰富,在欣赏诗或创造诗时,视觉意象也最为重要。”[3](p58)因此,四象论在视觉意象理论中能寻得突破,必将对整个意象理论的现代转型带来实质性的推动。
而四象论突破的契机在于结合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想象意识理论和郑板桥的画竹论,依据人类视觉意向经验的差异,将视觉意象分为本象、直象、间象、想象,同时通过想象的纽结点与西方的想象理论思想传统相打通,沿着宗白华先生的道路,将康德思想特别是康德的想象理论吸收进四象论的理论建构之中,以此深化意象理论探讨。
一、胡塞尔现象学图像意识理论和想象意识理论启示下的四象论
所谓四象论,是笔者在研究读图时代的身体审美现象时吸收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提出的现象学理论,四象论是以本象、直象、间象、想象概念为基础,在胡塞尔现象学意向性的可视见维度下朝向事情本身、做意向性还原的理论。本象指的是非形而上学的人或物的本源性的意向性整体,属于胡塞尔的图像主体范畴,若用于指人则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言的此在。直象指的是人的视觉所感知的象,是睁眼即意向的象。间象指的是在直象中的象中之象,如镜子成象、电影电视图像、照片甚至水中反射所成之象,通常需要在知觉作用下才能和直象予以区分。一张照片在直象中只是一张纸,但其上的图画则属于间象,对于他的把握需要借助于知觉以和直象相区分。间象属于胡塞尔图像客体范畴。想象指的是暂时弃视觉不用呈现于脑海中的象,多在回忆、思考、想象中产生,所谓暂时弃视觉不用是指不拘泥于当下在场的视觉意向经验,而以人当下或以往的视觉意向经验为基础唤起对于不在场的人、事物、事件等的回忆、思考和想象。四象论中的四象是意向经验中的意向对象,具有对象性(objectivity[4])。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视觉意象就是奠基于人的视觉意向经验中的图像意识。从四象论对视觉意象进行研究,必须吸收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胡塞尔曾在研究图像意识时提出了图像意识理论,将图像意识中的图像分为图像主体、图像事物、图像客体,是一个三层图像意识理论。胡塞尔说道:
“我们有三个对象:1)物理图像(Das physischeBild),由帆布、由大理石等制成的事物。2) 代现或映像的对象(Das repräsentierende oder abbildendeObjekt),以及 3)被代现或被映像的对象(das repräsentierte oder abgebildete Objekt)。对于后者,我们更愿意简单地称之为图像主体(Bildsujet)。第一个是物理图像(Das physische Bild[5]),第二个是代现性图像或图像客体(Bildobjekt)。当然,这是代现图像,不是物理图像事物(des physischen Bilddinges)的一部分或一面。”[6](s18-20)。
胡塞尔也将物理图像称为图像事物,倪梁康先生将其译为图像事物。正如前文所说,胡塞尔图像事物与图像客体的区分与四象论中直象与间象的区分有部分类似。图像事物突出图像意识中相关事物的物理质地、物理属性,如纸张、亚麻布、线条、客观颜色分布。在四象论中属于直接呈现的视觉意向经验,即直象的范围。图像客体相较于图像事物,则突出图像客体基于与图像主体的相似性,对图像主体的代现(Das repräsentierende)。而四象论中的间象除了包含胡塞尔图像意识理论中图像客体的相似性特征之外,更为重要的差异在于突出视觉意向经验呈现的间接性,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视觉意向经验的考察范围,使其不局限于人类创造的关涉图像意识的艺术作品,如胡塞尔主要分析的绘画、钢版画、雕刻等。水中倒影、镜中成象、光滑的事物表面反射成象、视频图像、电视电影图像等俱在间象所关涉的视觉意向经验范围,人对于间象的把握需要与在直象中所呈现的事物的物理质地、物理属性相区分。本象相较于图像本体而言更具有现象学的意义,本象强调视觉意向经验的整体性。而胡塞尔的图像主体则突出被图像客体代现的主题或主体。任何事物的本象在视觉意向经验,甚至或者说意向经验上具有无限丰富的整体性,它的实现或者切近只能通过想象综合直象、间象和视觉意向经验得到部分程度的切近或实现。笔者在硕士论文中,用借鉴自胡塞尔图像意识理论发展而来的四象论分析身体和身体审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合了胡塞尔的论证思路。因为胡塞尔在提出了三层图像意识理论之后紧接着就举了三维身体的例子,只不过它所例举的显现在眼前的三维身体是作为艺术创造物的身体,即马背上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雕像,以此强调图像事物与图像客体的区分。同时提及了小孩照片与小孩本人的差异,以此凸显依托于相似性的图像客体与被代现的图像主体的不同[6](s18-20)。
需要注意的是,在胡塞尔图像意识理论中,图像意识只具有图像本体、图像事物、图像客体的三层结构,而四象论具有本象、直象、间象、想象四层结构。相较于四象论而言,图像意识理论缺乏想象层。以致于有的学者认为胡塞尔“图像理论完全忽略了想象问题的这个基本事实”[7](p51)。就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而言,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是按照倪梁康先生的看法,胡塞尔是将整个图像意识理解为想象,并视之为想象的当下化的具体形式[8](p93)。这种看法在胡塞尔原文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文本证据,“而且从一开始它就归属于想象性理解的本质”[6](s18-20)。据此,可以认为胡塞尔继承了西方的想象理论传统,将图像意识理论作为想象当下化现象学的具体形态来看待。
但是,胡塞尔后来,以作为内在图像的幻象,对想象的当下化现象学的想象形态进行了具体的讨论,这对于丰富四象论的想象层内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倪梁康先生认为,Phantasie应该直接译为想象[8](p356)。不过,笔者在胡塞尔现象学文本的具体阅读中发现,这种翻译在特定的地方会引起名词概念的混淆,特别是在Phantasie和Imagination同时出现的时候。在笔者看来,Phantasie应该翻译为幻象,它是想象当下化现象学的具体形式,“如果应该用属于想象的幻象(derPhantasie von Imagination)来谈论”[6](s63-64)。
作为内在图像的幻象是想象的具体形式,是想象意识的产物。胡塞尔在论述中揭示了幻象所关涉的想象意识具有类似于图像意识的双层结构,即幻象图像(das Phantasiebild,也即幻象客体(das phantasierteObjekt))、图像主体(das Bildsujet)。在想象意识中,幻象图像和图像主体共同构成幻象表象(Phantasievorstellung)[6](s23-24),它们是在幻象立义中产生的。幻想图像是呈现在想象意识中现实并不存在的内在图像,而图像主体则是被幻象图像所展示的客体。幻象图像和图像主体的关系,也是基于相似性的图像代现关系,胡塞尔将其称为内在图像代现。胡塞尔以想象柏林城堡进行说明,“我想象(stelle vor)柏林城堡,即,我表象性地使它成为图像,图像悬在我面前,但我并不是指图像。……在不是城堡本身的图像中,但是我看着城堡,将图像对象化,类似于城堡,现在我的意指不仅指向图像客体本身,而且指向它所代现的东西,相似物。”[6](s24)在胡塞尔看来,想象意识即是内在图像意识,想象意识中的图像客体绝不是图像意识理论中有其物理图像属性的图像客体,它是不具有现实存在特性的幻象图像,想象中的作为幻象图像的柏林城堡,不是作为外在图像的柏林城堡。在胡塞尔将幻象作为内在图像来看待的同时,则将图像意识理论所涉及到的图像作为外在图像来看待。幻象图像与图像主体之间的内在图像的代现关系和图像客体与图像主体之间的外在图像代现关系除了具有基于相似性的代现机制的共性特征之外,胡塞尔还强调了其特殊性,即符号代现关系。
胡塞尔将基于相似性的代现关系分为两类,内在代现关系和符号代现关系。胡塞尔认为,图像意识理论所涉及到的图像客体和图像主体的代现关系,是以内在图像的形式内在代现的起作用。正如前文所言,内在图像其实就是胡塞尔所说的想象。这也就意味着,事实上,在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中仍然摆脱不了想象意识的参与。虽然胡塞尔隐约地意识到这一点,但胡塞尔在图像意识理论中并没有明确设立与图像客体、图像主体、图像事物并列的想象层。而对于想象意识理论来说,胡塞尔明确指出想象意识所关涉的图像是内在图像,存在两种内在图像:一种完全外在的超越的图像,没有直接的现实根基,如对于半人半兽的怪物的想象。另一种则是基于相似性的符号代现所呈现的图像所传达的想象意识。“就内在图像而言,在其中,我们实际看到了想象意识(imaginative Bewusstsein)。但是,由此,我们区分为两种:一种外在的、超越的图像,另一种依赖于相似性的代现方式,它归属于通过符号代现的系列,或者至少属于用符号传达的想象意识。”[6](s50-54)对于后者,事实上,需要作为相似性符号代现基础的图像客体来引发。胡塞尔以照片、作为目录内容的艺术作品集、象形文字[6](s35-36)、拉斐尔的麦当娜版画[6](s35-36)等进行了说明。胡塞尔认为这些图像客体只是作为符号引发人对于不在场事物的记忆,不在场的事物以内在图像的形式,也即幻想表象中的幻想图像显现出来。当然,胡塞尔在这里主要强调这些照片之类的图像作所引发的符号代现的记忆功能。它根本上存在于幻象图像对图像主体的符号代现关系中。
但是,胡塞尔的分析呈现出一些困境,一方面,从他所举的照片例子来看,图像意识理论所关涉的照片与想象意识理论所关涉的照片的观看方式并不能截然有效的区分。胡塞尔强调,照片如果不是作为某人本人来看待,而是作为对某人的记忆来看待,则是基于符号代现对某人的记忆想象。“一张照片也可以以相似的方式回忆起这个人,就像一个符号可以回忆起所表明之物一样”[6](s50-54)。这种对待照片的方式会引发幻想表象中的幻想图像,产生想象,而幻想图像就是典型的内在图像,尽管胡塞尔在这种观看方式中侧重于强调照片之类的图像客体作为记忆符号所引起的对图像主体的符号代现关系。事实上,从时间上看,严格来说,照片一旦诞生,即成为过去某个时间节点的原印象滞留。任何的照片都是对过去某人、某物的回忆式呈现。将照片作为某人本人来看待的图像意识观看,与将照片作为对某人的记忆、回忆的符号来看待的想象意识观看并不能有效区分开来。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说,图像意识理论中图像客体对图像主体的展示也关涉内在图像。按照胡塞尔的论述,图像客体以一种内在图像起作用的内在代现关系展现图像主体。[6](s35-36)如果说,在胡塞尔那里,内在图像关涉想象,那么,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并不能与想象意识理论完全切分,二者存在有机的关联。
既然,胡塞尔的分析存在一些困境,而解决的方法在四象论看来,即是建立想象层,从视觉意向经验的进路将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和想象意识理论进行整合。从四象论角度,将图像主体归入到本象,将图像客体归入到间象,将图像事物所关涉的表象归入到直象,切实地看到,被归入本象的图像主体的现象学呈现,是通过直象、间象,并最终由想象实施综合、统一而完成。这样,一方面,在面对图像时,将图像意识的观看方式和想象意识的观看方式结合起来,运用四象论中的想象对经由图像客体联想到图像主体现象学过程进行描述,无论是图像客体以内在图像代现图像主体,还是图像客体以符号代现方式激发幻象表象的幻想图像建立对于图像主体的回忆,都包含在四象论所建立的想象之中。以此,就能够运用“奥卡姆剃刀”减少不符合现象学事实、过于冗杂琐碎的术语分析。如果琐碎术语分析能揭橥现象学的真理,则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过于繁琐的无效区分违背现象学的事实,则需要被矫正。另一方面,运用四象论中的想象对图像主体具体的现象学呈现过程进行描述,既强化和承认了图像意识是想象当下化现象学的具体形式,又在图像意识理论具体分析中不排斥想象意识的分析,将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和想意识理论结合起来,建立完整的视觉意向经验的现象学理论。
诚如前文所说,四象论中的想象是暂时弃视觉不用呈现于脑海中的象,多在回忆、思考、想象中产生,所谓暂时弃视觉不用,是强调与直象、间象的视觉意向经验的区分,而不是说完全弃视觉意向经验不用,它强调的是不拘泥于当下在场的视觉意向经验,而以人当下或以往的视觉意向经验为基础唤起对于不在场的人、事物、事件等的回忆、思考和想象。在现象学情境中,想象可能是当下的直象、间象所触发唤起的对过往不在场的人和事的意向经验(在视觉意象理论的研究中强调过往的视觉意向经验)的回忆、思考和想象。由此,四象论的想象定义与西方思想中认为想象是对不在场事物的表象的传统定义结合了起来。“对缺席的感性事物生产感知的能力被称为想象或想象力”[9](p54),“想象是在直观中再现一个不在场的对象的能力”[10](s151)。从而,四象论所建立的想象层,不仅能全面描述视觉意向经验的现象学状况,而且与西方的想象理论传统的结合起来,这为四象论应用于中国意象理论的现代转型研究,深化意象理论的探讨,将西方最深刻的思想引入到意象理论的现代转型中来提供了理论的契机,提供了理论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表面看来,上文主要侧重于现象学论述,与意象理论无关,其实不然。综合借鉴胡塞尔图像意识理论乃至想象意识理论所建构的四象论,应运于中国意象理论的现代转型研究,其理论结合突破的契机在于:中国传统的视觉意象理论的集大成形态——郑板桥的画竹论。
二、四象论与郑板桥的画竹论的契机——四象论:中国意象理论的现代转型的突破契机
郑板桥的画竹论是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中用来探讨意象的经典文献材料,前辈学者如叶朗、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等都引用和研究过郑板桥的画竹论,但是罕有人看到其中所蕴藏的中国意象理论,特别是视觉意象理论现代转型的契机。通过综合借鉴自胡塞尔图像意识理论和想象意识理论发展而来的四象论烛照,笔者试发掘郑板桥画竹论与四象论的契合,展现四象论的阐释效力,以此将四象论作为中国意象理论现代转型理论建构形态。
郑板桥说道: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霜气皆浮动于疏枝密枝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非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11](p1173-1174)
郑板桥画竹论是他在谈论画竹的绘画艺术,也即图像艺术时提出的论点。毫无疑问,画竹作为图像艺术,关涉人的视觉意向经验,与现象学中的图像意识和想象意识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四象论看来,眼中之竹处于四象论中的直象层次,是画家所获得的现实中竹的视觉意向经验,胸中之竹处于四象论中的想象层次,是画家通过综合在直象中所获得眼中之竹的视觉意向经验在大脑(“胸中”[12])形成的关于竹的想象视觉意向经验,手中之竹则处于四象论中的间象层次,是画家通过综合在直象中所获得的眼中之竹的视觉意向经验和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竹的想象视觉意向经验在物理载体(胡塞尔所说的图像事物)上进行创作所生成的作为绘画的图像,而产生的视觉意向经验。郑板桥突出地强调了手中之竹相较于眼中之竹和胸中之竹的重要差异,其实质是凸显手中之竹在绘画艺术需经由艺术家的创作而最终生成。从四象论角度看,即使强调作为间象的手中之竹,其视觉意向经验,也即其视觉意象,并不是现成的,而是动态生成的,需对作为直象的眼中之竹和作为想象的胸中之竹进行综合,经过艺术创作动态生成。
叶朗看到了这一点:
“郑板桥这段话概括了艺术创造的完整过释:这个过程包括了两个飞跃:一个是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的飞跃;一个是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飞跃。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这是审美意象的生成,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画家进入操作阶段,也就是运用技巧、工具和材料制成一个物理的存在,这仍然是审美意象的生成,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造过程”[13](p248)。
不过,叶朗继承了朱光潜关于物本身(物甲)和物的形象(物乙)[14](p43)的观点,朱光潜认为,“这个“物”〔姑简称物乙)不同于原来产生形象的那个“物”(姑简称物甲),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14](p43)朱光潜的观点其实是在主客二分认识论框架下承认存在纯粹客观存在的与人无关的事物及其属性,并将其与主观认识中的事物相区分的观点。叶朗继承了这种观点,认为郑板桥的画竹论与意象相关的仅是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而将眼中之竹排除在意象之外,视为物的表象。“朱光潜在这里用的‘意象’的概念相当于我们一般说的‘表象’,即郑板桥说的‘眼中之竹’,而他说的‘诗的境界’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意象’,也即郑板桥说的‘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13](p56)在叶朗看来“眼中之竹”不过是朱光潜所说的“物甲”,“物甲是自然物”[14](p43),“物甲是自然存在的,纯粹客观的”[14](p47),不属于意象。这就将郑板桥画竹论本身所提供的中国视觉意象理论乃至中国意象理论完整建构的契机阉割掉了。事实上,眼中之竹也仍然属于意象范畴,因为绝然与主观无涉的纯粹客观存在是不存在的,而且对人来说是没有意义。其实,即便在认识论哲学阶段,洛克就认为,人所认识到的事物(自然事物或人)是“一般实体”(substance in general),它可能是单一观念(simple ideas)也可能是复合观念(complex ideas)构成的,其基础皆在于事物呈现在人的感官感觉中的属性(sensible qualities),包括颜色、温度、密度等[15](p277-302)。事物的审美属性(味道、声音、颜色)等正属于洛克所说的一般实体的次要属性[15](p117-118),是在人的感官感觉和主观意识中所呈现出来的属性。人们所认识到的事物,即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事物,早就是打上主观烙印,是与主体相关的属性和表象。仅就眼中之竹的颜色而言,就是一般实体的次要属性,因此,即便从认识论哲学家洛克的观点来看,眼中之竹绝也不是外在于人纯粹客观存在的自然物、物本身(物甲)。而叶朗遵从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将眼中之竹作为物本身(物甲)的表象排除在意象范畴之外,是一种理论阉割,与其所强调的现象学立场[13](p71)相乖背。现象学所强调的正是人与世界的有机关联,叶朗继承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将眼中之竹排除在意象之外,不仅不是现象学的态度,而且还有机械“反映”[14](p44)论的嫌疑。因为朱光潜就认为“蔡仪同志的基本毛病就在没有足够地重视这里所说的分别,把自然‘物’和经过美感反映之后的‘物的形象’,混为一事。”[14](p44)这或许不是蔡仪的毛病,恰恰可能是朱光潜和叶朗的毛病所在。将物甲(物本身、自然物)和物乙(物的形象)区分开来,将眼中之竹排除在意象之外,使得朱光潜和叶朗的论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朱光潜说“我们常可以看出内在情趣常和外来意象相融合而相互影响。如欣赏自然风景”[3](p54)。自然风景正是“眼中之竹”式的自然物,也即朱光潜所说的物甲(物本身)。但是,在这里,作为自然物的自然风景(物甲)又变成外来意象了。同样,对于叶朗而言,既然眼中之竹不是意象,那么在叶朗《美在意象》或《美学原理》中关于自然美的意象讨论就存在问题[13](p178-202),因为既然眼中之竹不是意象,那么现实中直观到的自然山水皆不是意象,那么对自然美的欣赏只要待在家里通过看山水画想象,或者从风景区回来闭上眼睛想象即可,而不必在风景区持续睁眼饱览名山大川。事实也的确如此,叶朗将“眼中之竹”排除在意象之外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自然美是见于自然物、自然风景。用郑板桥的术语,就是‘胸中之竹’”[13](p181)。按照叶朗的观点,只有在审美意象: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中才能展开审美鉴赏活动,眼中之竹只不过是物本身的表象而不是物的形象,因而不是意象。这种对郑板桥画竹论的偏狭理解所形成的意象解释,与审美活动的现实状况不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也会推论出荒谬的结论,更阉割了郑板桥画竹论丰富的意象内涵。
应该来说,郑板桥画竹论呈现出来的是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层次的视觉意象层次结构,从四象论的角度看,他们分别呈现在直象、想象、间象的视觉经验之中。郑板桥突出了手中之竹经由画家创作的动态生成过程,它是画家综合眼中之竹与胸中之竹进行审美创作的结果。“落笔倏作变相”[11](p1173-1174),指出了手中之竹与眼中之竹差异,手中之竹与眼中之竹存在相似性,但是就艺术而言,特别是中国古代写意的绘画艺术而言,并不强调完全逼真的相似性,承认艺术创作所存在的创造性变化。而“意在笔先”[11](p1173-1174)则展现出了胸中之竹对手中之竹生成的意向性指引。也即是说,胸中之竹的想象在手中之竹的间象生成中,会成为具有意向性奠基意义的“蓝图”。但是终究,通过画家的创作所最终生成的手中之竹与胸中之竹又有所不同。
有趣的是,郑板桥的画竹论呈现出来的视觉意象层次和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层次都是三层。从四象论角度看,郑板桥画竹论的眼中之竹、手中之竹、胸中之竹分别对应和呈现在直象、间象、想象中;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中的图像事物、图像客体、图像本体分别对应和呈现在直象、间象、本象中。相较于四象论,胡塞尔的图像主体只凸显其作为图像客体代现对象的主题地位,没有如同四象论一样强调本象是人或事物所关涉的意向经验的整体性、完满性和丰富性。人的意识意向性在某个时间节点,基于某种视域、某个视角只能部分当下化把握意向对象的部分意向经验特性,而意向对象的其余部分的意向经验则需要通过滞留性记忆、想象、前摄得以当下化把握。本象是现象学意向经验在意识中呈现的完整状态,是人只能切近但永远不能完全实现的,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无论是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乃至他的想象意识理论,还是郑板桥的画竹论都没有提出或者真正触及到这一意向经验层次。而单独地审视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相较于郑板桥的画竹论而言,它还缺乏与四象论中想象相对应的层次。同时,图像意识理论中的物理事物或物理图像只是强调和突出图像客体的物理载体的物理属性,而四象论的直象则肯定物理事物(或物理图像)在睁眼即见的直观表象如郑板桥眼中之竹中,作为视觉意向经验的图像意识特质。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言,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后期[8](p365),的确存在想象意识理论,有趣的是,它和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郑板桥的画论一样也可归纳为三层结构:图像客体、幻象客体(也即幻象图像)、图像主体。与四象论相较,胡塞尔想象意识理论也缺乏四象论的直象层次,同时胡塞尔想象意识理论所侧重强调的是图像客体作为记忆符号,所引发的幻象客体对图像主体的符号代现关系,胡塞尔并不否认图像客体在此过程中所引发的幻象客体的内在图像特性,但更为突出强调的是图像客体作为符号的记忆功能,因此相较于四象论中的间象而言,胡塞尔想象意识理论中的图像客体并不凸显其作为视觉意向经验的图像意识特性,而是强调奠基于其上的符号记忆功能。而胡塞尔的想象意识理论也只是将图像本体作为幻象客体符号代现的主题,和胡塞尔图像意识理论中的图像本体一样,并不具备四象论本象的现象学视觉意向经验的整体性内涵。因此,综合起来看,四象论以直象、想象、本象裨补胡塞尔图像意识理论的缺漏,以直象、间象和本象裨补了胡塞尔想象意识理论的缺漏,以本象裨补了郑板桥画论的缺漏,将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郑板桥的画论乃至胡塞尔的想象意识理论结合起来,建立由本象、直象、间象、想象所组成的四层次视觉意向经验图像意识理论。从现象学上看,四象论是以视觉意向经验作为基础的更为完善的图像意识理论。四象论经过与中国传统视觉意象理论形态——郑板桥画论的融合,又成为视觉意象理论,是中国意象理论现代转型的理论形态,相较于郑板桥的画论而言,具有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更加广泛的理论阐释效力。因而,四象论的四象:本象、直象、间象、想象就不仅只是视觉意向经验的图像意识层次,而且也是视觉意象层次。
三、四象论与视觉意象层次结构
这就意味着说,意象层次结构,或者具体地说视觉意象的层次结构是四层:本象、直象、间象、想象。从王夫之开始,意象情理交融的结构阐释一直延续及今,大有老生常谈的态势。而四象论的四象:本象、直象、间象、想象则将意象层次结构的讨论引向深入,同时能够得到中国传统意象理论和文献的佐证。这既可以从前文所引郑板桥画竹论中得到理论印证,更可以从中国古代意象理论的源头得到印证和发展。
此处所强调的意象理论的源头,首先是指象字的产生对于意象理论的开端意义。许慎《说文解字》对“象”解释道:“长鼻牙,南越大兽,三秊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凡象之属皆从象。徐两切。”[16](p459)事实上,象并非只是南越猛兽,在中国历史的早期,中原地区(现在的河南(豫[17])一带)的生态气候还是适合大象生存的,就有大象存在,并为中国先民创造象字提供了字源学的生态气候基础和事实根据。早在许慎之前,春秋战国时代的韩非子就在《韩非子·解老》篇中记载了象字在字源学意义上的产生过程。韩非子说道: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18](p148)
到韩非子所记述的时代,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较难以见到活生生的大象。也即,从四象论的角度看,人们已经很少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大象的直接的视觉意向经验,即直象中的大象。人们所获得的大象的直象仅剩大象的骨架,以此,造就了象的原初象形文字形态,即是与大象骨架相似的作为象形文字“象”的象形符号图像——间象。中国人乃至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象形文字,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符号图像,在四象论看来,是一种典型的间象。南唐徐锴就说道“韩子曰:象南方之大兽,中国人不识,但见其画,故言图写似之为象”[19](p164)。这种间象有引发对大象的本象进行想象的功能,想象不在场的大象的本象和大象的活生生的直象。“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18](p148)。从大象的直象残留——大象之骨所产生的作为象形文字“象”的间象,成为了引发对大象本象进行想象的象形符号图像。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一方面指出了象是像产生之前的假借字,另一方面看到了象字所引发的想象,也说道“韩非曰:人希見生象,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似古有象无像。然像字未制以前,想像之义已起。”[16](p459)段玉裁这里所说的想像,正是作为间象的象形文字之象所引发的想象。有趣的是,胡塞尔在论及想象意识的符号代现机制时,也将象形文字[6](s35-36)作为例子。作为象形文字的象字也是引发想象,具有记忆功能的符号。不过,和上文所说的照片例子一样,胡塞尔的分析陷入困境,并不能绝对有效区分乃至切分关乎图像客体的图像意识和图像客体所引发想象意识。图像客体对图像主体的内在代现,图像客体所引发的幻象客体对图像主体的符号代现,其实都是相似性代现的具体类型,都需要以相似性作为基础。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也看到了类似的相似性机理。“象也者,像也”,“像者,似也。似者,像也”[16](p459)。就象形文字的“象”而言,是一种象形符号图像,在现象学上,也属于图像客体。因此,在实际的现象学审视中,和对待照片的例子一样,并不能有效区分乃至切分,作为象形文字象的图像意识观看和想象意识观看,他们是同时发生并融为一体的。因此,只有四象论将象形文字之象作为间象,将作为图像主体的大象归入到本象层次,肯定象形文字之象的图像客体特性和记忆符号特性,同时融合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和胡塞尔的想象意识理论,通过视见象形文字之象的间象引发对大象的本象的想象,也不排除通过直接视见大象的直象(骨架)引发对大象本象的想象,在想象中综合大象的直象和象形文字之象的间象,乃无限切近具有意向经验整体性的大象的本象,才是符合现象学事实本身的。由此,四象论在中国意象理论字源学的源头得到了印证。
其次,四象论能在中国意象理论的源头——《周易》中得到发展。其发展的理论突破口在于想象,其发展的理论视野在于中西会通,其发展的理论进路在于承续宗白华先生中西融合的道路。诚如前文所言,四象论中的想象也具有对不在场事物进行表象的特点。这一点也能通过象形文字之象字的字源学生成获得印证。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就指出韩非子关于象字起源的字源学解释包含想象,并将其与《周易》联系起来:
“周易系辞曰:象也者,像也。此谓古周易象字即像字之假借。韩非曰:人希見生象,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似古有象无像。然像字未制以前,想像之义已起。故周易用象为想像之义”[16](p459)。
通过象形文字的象,也即间象之象,对于不在场的生象,也即本象之象的“意想”,即是四象论之想象,“想像之义已起”[16](p459)。诚如前文所论,段玉裁所指出的“想像”即是“想象”,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于图像客体作为记忆符号诱发幻象客体对图像主体进行符号代现的胡塞尔想象意识理论,而且契合于西方想象理论传统中的想象观念。“对缺席的感性事物生产感知的能力被称为想象或想象力”[9](p54),“想象是在直观中再现一个不在场的对象的能力”[10](p151)。因此,四象论就能通过想象将西方最深刻的思想融入到中国意象理论的现代转型中。有趣的是,段玉裁,以中国意象理论字源学源头作为例证、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所蕴含想像(想象)时,也提及了中国意象理论的思想开端《周易》。不过,与段玉裁不同的是,在四象论看来,《周易》从想象的维度吸收西方的想象理论思想,但是,又不仅仅只涉及想象层,还包括间象,这一点在下文还会详细阐述。
在此之前,必须指出的是,将西方想象思想融合到中国意象理论的现代转型和现代阐释建构中来,并不是笔者牵强附会,学贯中西的宗白华先生就是这方面的理论先驱。宗白华先生在意象研究中一直想将康德形而上学[20]思想,特别是康德先天图式(Schema)思想融入到《周易》的阐释中,强调易象的形而上学意义,特别是鼎卦[21](p612)、革卦[22](p616)对中国人、中国艺术的时间、空间观念的影响。其实,宗白华还没有明确意识到他所主要借鉴的康德先天图式论其实是康德的想象理论。
康德的先天图式论是康德三重综合理论的关键部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演绎部分提到了直观(Anschauung)、想象(Imagination)或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概念(Begrift)或图式(Schema)构成的三重综合理论。康德通过三重综合:直观的领会综合、想象的再生产综合、概念或图式的认定综合考察了人的直观认识的综合过程,康德认为想象和统觉综合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借助于想象或想象力,直观与概念、对象与图式综合联系起来。而其中,图式就涉及到想象和想象力。事实上,康德的想象可以分为生产性想象(die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23](s193),productive imagination[24](p51))和再生产性想象(die re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23](s193),reproductive imagination[24](p51)),再生产性想象即为一般经验中的想象,生产性想象则是诸如时间、空间的先天图式。
当然,一般而言,从感官感觉的角度上看,想象涉及到从多种感官感觉所获得的意向经验,不仅包括视觉意向经验,而且包括触觉、听觉等其他感官感觉类型的意向经验。那么将康德的想象思想融入以视觉意向经验作为基础、以视觉意象理论作为初始理论定位的四象论的建构中是否存在理论困局?其实不然。因为康德的想象理论不仅涉及到视觉,而且涉及到图像,这一点可以从康德本人的论述和海德格尔的阐释得到佐证。这也就是说,康德的想象理论可以完全融入到与视觉意象经验、图像意识相关,以视觉意象理论作为初始定位的四象论的建构中。具体而言:
康德的三重综合内含着凸显生产性想象的先天图式论,直观认识通过直观、想象、概念或图式的三重综合完成。直观表象是世界所直接给予给我们的表象,特别是视觉表象。康德发现,我们对现存事物直观表象的想象或者直观表象的呈现受到概念的影响,如犬的概念制约着我们对犬的想象,三角形的概念根本上规定着三角形的视觉图像呈现。而根本的概念则是图式(das Schema),它是生产性想象的产物。“图式(Das Schema)本身在任何时候都只是想象力(der Einbildungskraft)的产物”[23](s223-224),“想象原则就是图式”[25](s98)。海德格尔指出了,在康德的三重综合中,想象力和想象是同一个概念,并且产生图式,规定制约感性经验中的图像。“时间起因于纯粹想象力(der reinenEinbildungskraft),从属于想象力(der Einbildungskraft)(‘想象’)(“Imagination”),想象“应该……产生图像(Bild)”[25](s90-91)。的确,康德本人也说道:“图像是生产性想象力的经验能力的产物,感性概念的图式(如空间中的图形)是一种纯粹想象力的产物”[23](s243)。这就意味着,康德三重综合中的先天图式,是生产性想象进行生产的纯粹感性化的先天原则,需要在视觉图像的直观领域确证和显现自身,因此,甚至包括时间、空间的先天图式都具有图像性。海德格尔发现了这一点,称其为图式-图像本质。“由此,图式-图像(Schema-Bildes)的本质才变得清晰:它的视觉图像特征,不仅而且最初来自其可见的图像内容,而且来自于它,就像它来自于符合它的规定的被表象的可能性展示,而且,因此,似乎,这个规则进入了可能的直观领域。”[25](s99)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图像(“Bild”)一词,“对存在者的直接视觉图像(unmittelbarer Anblick eines Seienden),对存在者的现有描绘性视觉图像(vorhandenerabbildender Anblick eines Seienden)和关于事物的根本性视觉图像(Anblickvon etwas überhaupt)”[25](s92-94)。尽管在海德格尔看来,不能对康德图像概念作孤立的理解,应该看到康德先天图式论中图式-图像本质,应该明确先天图式对图像的根本规定性。不过,海德格尔对康德图像的分类可以作为笔者所提出的四象论的材料证据,“对存在者的直接视觉图像(unmittelbarer Anblick eines Seienden)”正对应于直象,对存在者的现有描绘性视觉图像(vorhandenerabbildender Anblick eines Seienden)正对应于间象,关于事物的根本性视觉图像(Anblickvon etwas überhaupt)正对应于本象层次。唯一缺少的是与想象对应的层次,而这正是海德格尔对康德图式-图像本质分析所强调的。
而海德格尔关于图像一般看法的分类则裨补了这一缺漏,同时成为了四象论最具说服力的佐证材料。海德格尔说道:
“图像最初可能意味着:某个存在物的视觉图像,只要它作为存在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它提供了视觉图像。在此含义的推导中,图像可能还意味着:描绘现存的事物(印象)的视觉图像或者再现不现存的事物的视觉图像,或者只是将要产生的事物的示范性视觉图像。”[25](s92-94)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四种图像,关于某个存在物直接的视觉图像、描绘现存事物的视觉图像、再现不现存事物的视觉图像、将要产生的事物的示范性视觉图像。与四象论相参照,在笔者看来,关于某个存在物直接的视觉图像正与直象相对应。描绘现存事物的视觉图像正与间象相对应。再现不现存事物的视觉图像正与想象相对应。而将要产生的事物的示范性视觉图像则与本象相对应。海德格尔在论述中反复区分了关于某个存在物直接的视觉图像和描绘现存事物的视觉图像,肯定了睁眼即见的直观表象的视觉图像特性,看到了它和对存在物直观性的视觉图像的描绘和记录式的图像的分野。被直观到的“这个-那里”,例如整个风景作为视觉图像(Anblick)的图像(Bild),与保存这种直接显示性图像的记录图像(Abbild),例如照片就不同[25](s92-94)。不过,海德格尔只是从一般意义上探讨图像,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康德先天图式论中图式-图像本质应该归于哪一种图像类型。与海德格尔对康德所使用的三种图像概念分类不同,海德格尔在此提及了再现不现存事物的视觉图像,也即再现不在场或缺席的事物的视觉图像,从四象论角度看,也即是想象,同时也符合西方想象理论传统对于想象的界定。因此,借鉴康德哲学中生产性想象和再生产性想象的孪出关系,图式-图像的本质所对应的图像功能层次应该是对应于再现不现存事物的视觉图像的图像分类层次,尽管海德格尔在图像的一般分类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这也就意味着,在将康德生产性想象的先天图式论吸收进四象论的过程中,需要将其归入到四象论的想象中来。此外,笔者将海德格尔这里所提到的将要产生的事物的示范性视觉图像与四象论的本象相对应。本象是存在物完整的视觉图像,具有示范性意义。
在此,值得强调的是,海德格尔对康德三重综合中先天图式论的分析,敞开了将西方的想象理论传统融入四象论的大道。这是因为:首先海德格尔的分析有着现象学研究的特点,揭示康德三重综合直观认识的现象学本质。其次,从康德本人的哲学出发,直观表象确实是感性经验的领域,而先天图式则是纯粹的感性化领域,不仅直观表象具有视觉图像性,而且纯粹感性领域的先天图式也具有视觉图像性,“因此,纯粹的感官化必定是对某种事物的接受,这种接受首先是在接受本身中形成的,因此是一种视觉图像(Anblickes)”[25](s91-92),并为其他类型的图像提供根据,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具有图式-图像本质。因此,四象论完全可以将康德的生产性想象的先天图式论吸收进四象论中,而与现象学上的感性视觉意向经验所获得的视觉图像保持内在的一致,并不乖背。因此,将康德三重综合中的生产性想象先天图式论吸收进四象论,对视觉意象的现象学研究而言也并不违和。视觉意象说到底正是建立在视觉意向经验基础之上的图像意识,它与康德所说的感性直观所获得的视觉图像、纯粹感性化领域的先天图式的视觉图像性以及先天图式对感性视觉图像的规定都具有理论契合的可行性和内在一致性。当然,四象论在此融合的过程中,并不会将康德生产性想象的先天图式论仅仅局限于四象论的想象层,还会根据中国意象理论的传统进行具体的分析,发现中国意象理论传统中意象的形而上学先天生产衍生机制。
将康德的三重综合所内含的生产性想象的先天图式论吸收进四象论中,阐发意象的形而上学先天生产衍生机制,首先体现在,在四象论的四象,特别是想象中,保留康德生产性想象与再生产性想象的区分,通过想象的契机,将康德的想象理论吸收进四象论中,保留生产性想象先天图式作为直观认识基础的形而上学地位。同时,以想象为契机,将西方想象理论思想传统中的思想都融合进来,扩大四象论和视觉意象理论研究的问题域,深化四象论和视觉意象理论的研究深度。
其次,结合中国意象理论的缘起来看,中国意象理论传统中意象的形而上学先天生产衍生机制不仅限于想象,还表现在间象中。“见(易经·系辞上传)……。作者(按:宗白华)于此段上注曰:‘中国形而上之道,即象”[26](p612)。宗白华先生就曾借鉴康德先天图式论阐发过中国意象理论中易象的形而上学意义,如鼎卦、革卦衍生中国文化中的空间、时间,并对中国艺术空间、时间观念、审美思维产生重要影响。“易者,象也”[27](p303),《周易》中的易象其实是从直观表象中总结出来的卦象。“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7](p294-322)伏羲的先天八卦乃至周文王推衍的六十四卦,都是这种卦象的典范而初始的形态。从四象论来看,易象主要是从直象中总结归纳出来的间象形态。“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说的正是从直象中进行归纳总结,而所作八卦,正是间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27](p294-322),它具有与神明会通的功能,与万物类似的相似性特点。自从《周易》的易象产生之后,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传统、文化理念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铸造了中国的形而上学先天生产衍生机制。因此,可以借鉴康德生产性想象的先天图式论,将间象分为生产性间象和再生产性间象,而作为卦象的《周易》的易象就属于生产性间象,它具有形而上学先天生产衍生特性。在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作为生产性间象类型的《周易》卦象所具有的先天性与康德先天图式论的先天性的异同及其会通的可能性。康德哲学的先验性(Transzendental),也称先天性,“我认为所有认识都是先验的(transzendental),这些认识根本不是与对象有关,而是与我们认识对象的方式有关,只要这些认识被认为是先天(a priori)可能的。这种概念的体系将被称为先验哲学(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23](s82)康德的Transzendental突出地表现为先天范畴或先天图式对经验、现象提供规定性,为认识提供先天根据和可能性。宗白华在借鉴康德哲学阐释易象的形而上学意义时,认为“象与理数,皆为先验的,象为情绪中之先验的。”[28](p628-629)因此,作为生产性间象类型的《周易》卦象与康德先天图式论一样具有先验性,也即先天性。当然,二者的先天性也存在一些差异,作为生产性间象类型的《周易》卦象所具有的先天性是通过直象领域的经验归纳总结之后所具有先天性,在易象的阐释中,强化了作为生产性间象类型的《周易》卦象衍生世界万物、奠基时空的能力。《周易》卦象产生之后对中国艺术空间、时间观念、审美思维产生的重要影响,则是在长期的文化习得和文化传承中所形成的先天规范,它依赖于文化经验的传承。而康德的先天图式论的先天性则凸显不依赖于经验的先天存在的先验性,它需要在直象乃至间象领域中显现出来。这或许是宗白华认为象所具有的先验性是情绪中的先验性的原因在之所在。因而,用先天性翻译康德先天图式论的先验性,用先天性指称《周易》的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所具有的先验性,就凸显了二者的理论会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尽管《周易》的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所具有先天性与康德先天图式论的先天性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并不妨碍借鉴康德先天图式论对作为生产性间象的《周易》卦象形而上学先天生产衍生机制的阐发。诚如宗白华反复强调的“象即中国形而上之道也”[26](p611-612)。在《周易》的卦象中,不仅鼎卦、革卦奠基了中国文化的时间、空间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且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卦等都具有形而上学意义。
具体而言,《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所奠定的中国意象理论的形而上学先天生产衍生机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是生产衍生的“始基”,生产衍生宇宙万物。《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所具备的形而上学生产衍生机制的“始基”从根本上植根于以易作为中国形而上学的始基建制。“‘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虞曰:准,同也;弥大,纶络,谓易在天下,包络万物。”[26](p609-610)易不仅能囊括宇宙万物,更为重要的在于生产衍生宇宙万物。“生生之谓易”[29](p256-292),具体而言,易的形而上学生产衍生机制是怎样的呢?“是故《易》有太极,(虞翻曰:太极,太一,分为天地,故生两仪也。)(郑康成曰: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道也。)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26](p611-612)“(虞翻曰:四象,四时也,两仪,谓乾坤也。)四象生八卦”[26](p611-612)。“八卦相错……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26](p610-611)。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太极,也即太一,是能生产衍生天地(空间)、四时(时间)、万物的形而上学“始基”。在此意义上,易正是弥纶天地的道。又“易者,象也”[27](p303)。因此,中国以易为始基的形而上学生产衍生机制其实质是以象为始基的形而上学生产衍生机制。从这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宗白华所说的“象即中国形而上之道也”[26](p611-612)。的确,“象即道”[26](p612)。《周易》的象主要是指《周易》的卦象,《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就具有形而上学生产衍生机制的始基地位,能够生产衍生宇宙万物,恰如老子所说的道一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0](p117)。所以说,“‘象’为万物创造之原型(道)”[28](p628-629),“象”如日,创化万物”[28](p628-629)。
其二,《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是生产衍生的“范型”,生产衍生时间、空间、社会秩序等。时间与空间不仅是《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居于始基地位、生产衍生的结果,更是形而上学生产衍生机制的范型。也即,作为生产性间象,《周易》卦象与康德先天图式论中作为生产性想象的图式(Schema)具有相同的特点。时间与空间作为生产性想象的先天图式,已经植入在感性经验领域成为感性直观、认识综合的基础,是感性显现得以呈现的先天范畴。而《周易》卦象所具有时间与空间内涵本身具有生产衍生特性,也是先天图式,宗白华借鉴康德的先天图式论将其称为范型。“故“象”能为万物生成中永恒之超绝“范型”[28](p628-629),“抱一为天下式Schema”[31](p626)。《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所具有的时间与空间内涵,本身具有生产衍生特性,他们如同康德的先天图式或范畴一样,成为事物与现象得以呈现的先天条件,为认识的可能性提供先天基础,具有先天性、永恒性、规范性、基础性。宗白华在研究意象的过程中,借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观点看到了这一点,“‘象’为建树标准(范型)之力量(天则)……,亦如指示人们认识它之原理及动力”[28](p628-629),的确,《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是有时间、空间内涵,具有生产衍生能力的范型。不仅革卦“致历明时”[26](p612),具有时间内涵,是典型的的时间意象,鼎卦“正位凝命”[26](p612)具有空间内涵,是典型的的空间意象,“空间意象为鼎,时间意象为革”[26](p612)。而且包括先天八卦在内的《周易》卦象,本身就具有时间、空间意象的意义,是典型的的生产性间象。“乾坤生春,良兑生夏,展翼生秋,坎离生冬者也”[26](p611-612)。先天八卦不仅与时间相关,构成万物生成之演历,而且先天八卦本生就是空间,构成万物存在之境遇。“八卦者何?乾(天),离(日),坎(水),展(雷),龚(风),天象;坤(地),民(山),兑(泽),地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26](p611-612)先天八卦与自然事物相对,构成万物存在的地理空间,这是《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生产的空间意象范型的直接内涵,而相较于康德生产性想象中作为空间的先天图式,《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生产的空间意象范型的特殊内涵在于,《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包含社会空间范型。这可以从鼎卦的空间范型意义——“正位凝命”[26](p612)见出。“正位凝命”[26](p612)绝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范型,而强调的是父系血缘封建宗法等级制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其实质是社会空间。因而,在先天八卦中以乾坤为纲纪建立的天地空间,也绝不是单纯意义上地理空间范型,而是社会秩序,也即社会空间范型。“空间不离天地乾坤,为表情性的……而为八卦成列之‘象’(意象)……所以成位,非依抽象之空间地位以示物理。”[31](p620-622)这其实是符合中国人认识事物空间秩序的实际情况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空间,绝不只是地理空间的三维容器,而是笼罩在父系血缘封建宗法制社会秩序的社会空间范型之中,“中国空间意象:‘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31](p620-622)乾坤表面上所建立的是一以天地为矩度的地理空间,其深层实质则是与父母、男女相比拟的父系血缘伦理的社会空间。因此,总体来看,《周易》的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是中国意象形而上学生产衍生机制的范型,构成了宇宙万物存在和显现的时间演历和空间境遇。所以说“易,日月也,象如日月,使万物睹!”[28](p628-629)“象如日,明朗万物”[28](p628-629)。
其三,《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是生产衍生的“本源”,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此处的“本源”,并不是强调《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是中国形而上学生产衍生机制“始基”而所具有的开端性。它所突出的是,《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对中国人思维观念、思维方式的影响。宗白华就具体研究了《周易》卦象,也即易象对中国人艺术观念、艺术创造、审美思维的影响。宗白华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等论文中就反复论述《周易》的卦象:革卦、鼎卦、离卦、贲卦对中国的艺术思维、绘画艺术、绘画的空间意识、艺术品制作(如青铜器等)、建筑艺术、审美思维、文质观的深远影响。他将《周易》的卦象作为影响艺术创造和审美思维的法象和范型来看待。从四象论角度看,这其实意味着,作为生产性间象的《周易》卦象作为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的生产衍生本源,从根本上,仍然依赖于作为生产性间象的《周易》卦象所具有的生产衍生“始基”和“范型”地位。事实上,单纯地强调《周易》卦象对中国艺术创造、艺术思维的影响并非宗白华的首创。中国古代早就有“以制器者尚其象”[32](p283)的观点,王微《叙画》引颜延之的话也说“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33](p585)。宗白华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将康德先天图式论与易象相融合,意识到易象所暗含中国意象形而上学之道。不过,他没有指出,易象作为意象,主要呈现为《周易》的卦象,是一种符号图像式的间象存在,其实质是生产性间象,如果强调《周易》卦象作为观念形态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则会从符号图像的间象存在形态转化为想象,从而更为接近康德所说的生产性想象。
可能,囿于具体历史条件下德文文献搜集与阅读的限制,宗白华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弄错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三角形(Triangel)图式概念对三角形直观表象构形影响的具体出处[28](p628-629)。宗白华认为他所用的康德三角形例子出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超越方法论第二部分。但是,综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提及三角形的有25处,宗白华所用的三角形例子并不出于《纯粹理性批判》超越方法论第二部分[34](Der transzendentalen Methodenlehrezweites Hauptstück,案:现在一般译为先验方法论第二部分)[23](s830-860),而应该是出于《纯粹理性批判》先验分析第二部分(Der transzendentalen Analytikzweites Buch),先验判断学说(Der transzendentalen Doktrin der Urteilskrafterstes Hauptstück)关于三重综合论述的部分[23](s239),同时在先验方法论第二部分(Der transzendentalen Methodenlehrezweites Hauptstück)根本就没有提及三角形。而且,宗白华很多论述具有哲学断想的性质而缺乏严密的逻辑条理性。但是,宗白华将易象与康德先天图式论相融合,将易象作为范型,指出其中内涵着中国形而上学之道,其筚路蓝缕之功则值得称赞。而四象论正是沿着宗白华先生所开创的康庄大道,将康德的生产性想象和再生产性想象的分类吸收进四象论的想象中,将间象分为生产性间象和再生产性想象,将康德生产性想象的先天图式论与中国意象理论的源头《周易》结合起来,指出易象,也即《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的实质内涵,揭橥易象作为中国形而上学之道的理论内涵,发掘建基其上的中国意象的形而上学生产衍生机制。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