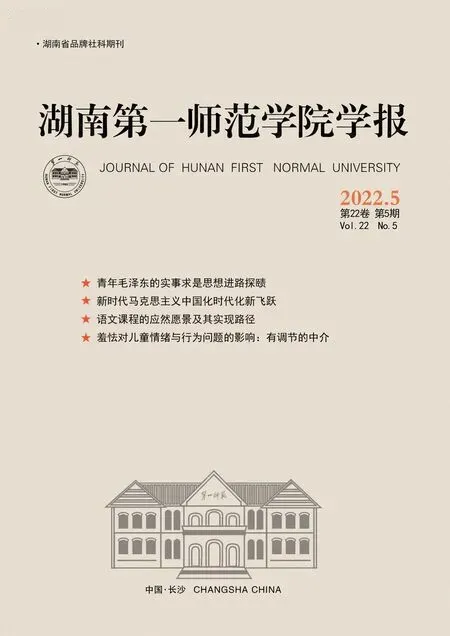认知诗学视角下《沁园春·雪》革命意象英译实践研究
张昀霓,陈 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省毛泽东诗词外译研究基地,湖南 长沙 410205)
《沁园春·雪》发表于诗人毛泽东为中国民主革命亲赴重庆谈判期间,富含革命意象,既反映了诗人长期的革命生活,又饱含着诗人深厚的革命情感。该诗影响深远,传诵甚广,有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译本,其中英译本就有三十多个且风格不一,如:许渊冲译文秉承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1],张纯厚译文力求反映原诗完整准确的信息[2],赵甄陶译文尽量保持原诗的艺术风格和感情色彩[3]等,都尚未着力于诗中革命意象的传译。
诗人毛泽东曾说过,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4]2。学者李正栓也提出“译者应尽量走近毛泽东,但不能超越毛泽东。尽量避免或减少译者介入”[5]。毛泽东是诗人,也是革命家。解读其诗,也是解读其诗的革命意象。译者,也是读者,只有走近诗人,体验诗人的革命生活,体悟诗人的革命情感,才能准确识解诗中集革命生活和革命情感于一体的革命意象,真正解读和传译其中的革命意蕴。这种基于“体验—体悟—识解”的阅读体认正是认知诗学的核心内容。认知诗学非常重视读者的认知感受,从文学作品的阅读视角挖掘文学作品的本质问题。就翻译实践而言,认知诗学能帮助译者以原诗读者的身份体悟原诗蕴含的创作背景和诗性情怀之间的认知交互,审视、剖析诗中蕴含的认知机理,寻根溯源,找到准确的译语诠释原诗,在形式和语义上更好地还原原诗意象,架构起诗人和译语读者沟通的桥梁。
一、认知诗学与意象识解
认知诗学源于二十世纪末,以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美学等跨学科理论为指导研究文学文本或文学话语,提出“认知是关于阅读的心智过程,诗学关注文学的技巧”[6]7。意象,作为人类生活体验心理活动中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普遍存在于文学作品中,是认知诗学研究的重要范畴。认知诗学透过诗的形式挖掘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的交互下意象在语境中的构建,探究文学意象所营造出的情感、审美等非概念意义,帮助读者在诗性语言中“发现文本与情感体验之间的结构相似性”[7],循迹诗性突显的审美情感,透悉基于情感体验和审美认知交互构建的完整意象,即在阅读中从体验性、突显性和整体性的三个角度识解意象。
就意象的体验性而言,认知诗学提出“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属于认知活动,文学作品是人类心灵的产物”[6]6。诗源于诗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体验,是客观实在在文本世界的认知投射。诗性文本世界是以现实世界为参照对象,以人的内心感知为体验基础建构的最基本的心智空间。诗人通过内心感知将现实世界投射于心智空间,运用普遍的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进行诗性创作,从而构筑诗性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就诗人而言,诗意形成于诗人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基于诗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认知活动、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而产生的情景虚构和认知迁移。就读者(译者)而言,诗意根植于阅读过程中读者的身体感知经验和认知直觉,是读者对诗的情感认同和转介。因而,文本阅读过程中意象的形成与阐释不是简单的理解过程,而是一种认知行为;不仅涉及诗性语言的表达,而且涉及由虚拟的文本世界反观现实世界,由彼及此的生理和心理的体验反思过程,更取决于读者在诗语中体悟到的跨时空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体验。
就意象的突显性而言,认知诗学认为,在阅读行为的特定知觉领域中,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即认知对象,并不是同等重要的,有些会轮廓分明,突显出来形成能被明确感知的图形,而另一些对象则退居其次成为背景[6]25。这种突显就是对语言所传达信息的取舍和安排。意象,现实世界“概念化”映射的产物,既可指一种感知印象,也可指超越感官的认知体验。诗索物以托情,融物以起情。诗的意象,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映射。诗中意象的突显性使读者随诗人的感知跳出纷杂的物象,切身体会诗性语言所描绘的视域场与诗人思想情感相携,多层次多侧面的突显某个情景交融的焦点。因为认知突显,读者触摸的诗性意象往往会超越语言表征的视觉领域,成为具有典型特质的映射符,并衍生出新的诗性内涵和思想情感。
意象的整体性受益于独立的突显意象联结后生成的完整形象。朱光潜曾提出:“一个境界如果不能在直觉中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那就还没有完整的形象......就还不能算是好诗”[8]。认知诗学尤其注重意象的完整,认为完整的意象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在头脑中建构一个场景,将读者引领到诗所营造的意境之中,从而实现情感体验的交互。而且诗中大多数完整的意象不是由独立的意象构成,而是由两个甚至多个突显意象组成意象群,有时甚至会派生出为意象含义和诗人抒情所服务的非意象成分。究其根本原因,诗中独立的突显意象不能很好地体现出诗人的情感以及诗的意境,由多个不同意象构建的意象群才能勾勒出一幅幅画面,在阅读过程中经认知统一协调后从整体上体现出诗的意境,传递诗人的情感体验。由此可见,“一首完整的诗就是一个复合意象”[9]71,是多个不同意象的组合,或者突显意象的不同变形层面,甚至意象的重复;是多个不同意象经审美认知和情感体验形成的统一意境。同时,意象的整体性以读者的审美认知和情感体验为契机打破诗中形式和意义的二元对立,生成诗的整体价值。
故读者只有理解诗人的社会生活,体悟诗人的情感内涵,才能切实把握诗的意象,从整体上挖掘诗性语言中所蕴含的“情”与“志”;只有科学合理解读意象的体验性、意象性和整体性,才能更贴近原诗意蕴,发现其中真意。
二、基于认知诗学的《沁园春·雪》革命意象英译实践
诗的阅读认知决定着读者对诗的识解程度。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首先是原诗的读者,其次才是译文的创作者,因而作为读者身份的译者对诗的识解程度直接决定着译文的质量。从认知诗学视角来看,意象作为诗性解读的重要一环,“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10]3,并非外在物象在诗中简单的图像式的重现,不仅承担着译者对原作者所处现实世界的感知,还与译者在现实生活中的设身体验息息相关。
基于认知诗学,《沁园春·雪》的英译实践重在挖掘并重现原诗蕴含的革命意象。首先,通过查阅、剖析创作背景、诗人以及相关学者对本诗的注解,创设情境,体验原诗语言表达所映射的革命生活和革命抱负;然后,借助意象创生所突显的客观景象,挖掘中英表达的认知内涵;接着,借助独立意象之间的认知联结,在整体上还原诗中的革命情志,重现原诗中蕴含的美好革命前景;最后,形成译文,具体如下表:

表1 《沁园春·雪》中英文对照图表①
三、《沁园春·雪》革命意象英译的认知诗学阐释
不同于以往将译者或文本置于中心地位的分析方法,认知诗学强调译者在文本鉴赏过程中要发挥其作为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从身体感知和心理体验上体悟原诗和译语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建构意象认知语境,形成类比性的创造认知,理解、欣赏、解释原诗中的意象认知要素,实现译语读者和认知语境的交互、译语读者和诗人的认知交互。对于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意象而言,译者需“结合毛泽东同志的生动而又丰富的革命生活,分析阐释其诗词的每一词语,真切品味其蕴含在词语背后的浩瀚革命精神”[4]4,才能找到准确的译语表达。
(一)《沁园春·雪》革命意象的体验性及译语表达理据
认知诗学认为,读者要科学阐释一部作品就需走近作者,而“对于作品的作者所处的文化氛围的关注则成为一种必由之路”[11]。就诗人而言,“诗言志”,“言”既是“表达”,更是“全盘实现”,既包含语义上的再现,又包含形式上的展示;“志”则指“某人在某一刻的全部经验”[12]。
就革命背景而言,《沁园春·雪》创作于1936 年1 月诗人毛泽东亲率红军抗日先锋队渡过黄河,东征前往华北前线对日作战时期。面对壮美的高原雪景,诗人感慨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才有这首振聋发聩的诗篇。诗中,诗人描绘自然风光,赞美祖国山河,表达了长征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勇斗争气魄;评析历史人物,指点江山,表明了要超越古代英雄人物获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豪情;记载历史轨迹,展望现实,指出必须依靠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革命路线。原诗白描高原雪景,勇评历史帝王,隐写曲折困难,着笔表达革命必胜的信心。
在阅读体验中,“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被表现的东西。”[13]原诗首行中的视觉体验:静态的“冰封”和动态的“雪飘”,诗人亲自批注为“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4]87,用以喻写革命道路的曲折和艰辛。而且,诗人在1945 年8 月将《沁园春·雪》回赠柳亚子先生,于《关于重庆谈判》中说:“世界是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4]82可知,诗人借雪景细数封建社会杰出的英雄豪杰——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他们尽管雄才大略,但都缺乏某种东西。故诗的主题应归结为赞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和人民大众,表达诗人在革命斗争中远大的、坚定的革命抱负。
原诗的革命背景和诗人的批注说明为革命意象英译实践提供了认知基础和译语表达的基调:以雪景为媒介抒发革命情志。从译语读者的文化生活来看,译语ice sealing 仿写固定搭配heat sealing (热封)的结构,激发了译语读者的生活想象:冰如同塑料薄膜一样的封住了大地,与snow flying 一静一动之间透射出诗人的生活设身体验,暗示着革命道路的曲折与艰辛。而sharply halts its roaring 中,表示“运动状态的物体因中途抓住而暂时停止”的语词halt 和音色洪亮表正在进行的语词roaring 一起强化了本应滔滔而下的动态河水突然暂时中断,突显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严峻,预示革命前途是光明的。同时,Big River up and down 没有将大河翻译成传统的the Yellow River,而是直译为Big River,一是在中国读者的文化认知中,黄河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河流,因河面辽阔,水流浩荡,在北方就被称为“大河”;二是在美国读者的文化生活中密西西比河也因其大而被称作Big River,因此big 一词更贴近诗人和译语读者面对大河时一望无际的视觉感受。而“上下”没有翻译成high and low,而是翻译成up and down,因为在译语读者的文化生活认知中,沿河而上为up,沿河而下为down,相较high 和low“高于或低于地面(海面或另一参照点)”而言,更贴近原诗,表达黄河一望无际的视觉体验。
可见,革命意象的译语表达探究了译语蕴含的生活体验从而还原了原诗背后的革命精神:以冰雪象征革命道路的艰难险阻;以壮丽景观抒发革命豪情;以历史人物歌颂无产阶级英雄,最终表明革命必胜的信念;挖掘了译语读者的文化生活体验,故能准确选择符合原诗认知体验的译语表达。
(二)《沁园春·雪》革命意象的突显性及译语表达理据
诗的意象源于体验,故客观世界中的景与物是诗中意象的创生之源。客观世界投射于诗中的意象可以是视觉的、听觉的、味觉的、嗅觉的,甚至多感官的联觉和联动。从体认角度来看,这些感官意象在诗中会呈现出不同的突显程度,即一个认知域中会有一个意象在认知上特殊突显,比其余部分更加显眼,催发诗的内在情志,让诗行情景相生,相互碰撞、相互渲染,契合无间。
在意象突显中,上片中“北国”“冰封”“雪飘”“长城”“大河”“山”“塬”“晴日”和“红装”等诸多意象从五个层次以认知域突显认知焦点的方式描写了诗人对于北国雪景的感官意象,叙写了诗人内心的革命信念。
1.以“北国”为认知域突显广袤深透的冰雪意象。语词“北国风光”锁定认知域“北国”和认知对象“风光”,劈头统摄,突显“千里冰封”和“万里雪飘”的认知概念。空间意象“封”覆盖大地和大地上的山、塬、河等,空间意象“飘”统辖天空,一静一动加上“千里”“万里”的视阈,在视觉上描绘了严冬威猛雄奇的意象,激活了冰雪铺天盖地、肆虐而来的视觉意象,影射反革命浪潮的汹涌来袭。翻译时,表达冰雪覆盖面积之广的“千里”“万里”分别对应infinite 和unending,其理据为:infinite 表示“没有边、无边无际的”,将译语读者带入“千里冰封”的无边无际的意象;而unending 则表示“没有尽头、没有结尾”,让译语读者感受到无穷无尽、形势严峻的革命意象。
2.以“长城”“大河”为认知域突显冰雪肆虐下万物寂静的景象。诗行以“望”字带出地域背景:“长城”和“大河”(黄河),以烘托“惟余莽莽”的视觉意象和“顿失滔滔”的听觉意象。视觉意象和听觉意象反复强化的寂静交织在一起,描绘了革命形势险象环生。翻译时,译语only left 和whiteness表达了反革命浪潮反扑后的萧瑟之感,强化了白茫茫、万籁寂静的核心意象;语词sharply 和halt 则描绘了寒威之速、之烈,令黄河滚滚滔滔、波涛汹涌的雄壮气势戛然而止。两者在结构上相互呼应,让译语读者深刻感到革命形势不容乐观。
3.以“山”“塬”为认知域突显与天斗的豪迈气概。寂静雪景下“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动态意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拟人化的凌云壮志,写的是大雪茫茫,天低野阔的北国风貌下蕴含的内在气势。译语wave 从形描摹我国民间舞蹈表达欢庆的彩带舞中的彩带,从音突出群山的高低错落,动感十足;译语prance 则以西方文化中欢跃、欢腾的赛马来刻画象欢脱跳跃的动作,两者都以动的意象突显了革命的万丈豪情。
4.以“晴日”为认知域突显“红装”“妖娆”。漫天风雪突转为“晴日”时红日与白雪交相辉映,“红装”与“素裹”构成强烈的颜色对比,表达了对革命前景的乐观和革命信念的坚定。译语The light red velvet in white,以雪为背景、红光为图形描绘了上午9 点左右平坦开阔的北方,皑皑白雪在阳光照射下覆盖上了一层红色绒光,仿佛少女薄薄的白纱下透出的红衣,映证了美好、光明的革命前景。
5.以“无数英雄”为认知域突显当今的“风流人物”。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文采不足,武略有余,“只识弯弓射大雕”,全不如今朝为社稷民生幸福而奋斗的风流人物。译语King,Sovereign 和Emperor 淡化古代帝王的个人名号,强调他们的历史地位,故译语读者即便不熟悉中国历史,也会基于自己国家历史以及上下文的语境推断出这些帝王主要功绩,并反思古代帝王的不足,强化当今无产阶级革命英雄。
原诗革命意象的营造中,认知域场面恢宏,大气包举;认知焦点动静结合,虚实相间。认知域的恢宏意象和认知焦点的动静意象是诗人坚定而又乐观的革命情志的外射或概念化。基于认知诗学,革命意象转码可通过挖掘语词意象中蕴含的革命体验和文化认知来还原原诗宏大的意象突显;可立足译语读者的生活体验来跨越文化屏障在译语读者的脑海中有效重现诗人所要表达的革命情志。
(三)《沁园春·雪》革命意象的整体性及译语表达理据
诗的整体性源于认知的整体性,即读者会根据自身知识与经验,把阅读中感知到的互相影响、高度混合的独立意象综合成一个整体。而诗的整体性就构建于独立意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混合的关联意义之上。“每一意象的意义完全在于他与其他意象的关系。意象没有‘实质性’意义,只有‘关系上’的意义。”[14]92“它们互相解释、界定。”[14]111独立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解释则进一步构建诗的整体语境。中国诗论中“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之说也印证了意象与客观实在之间的映射关系,暗合着创生于独立意象之上的整体语境。
从整体性看,原诗中的系列动词“望”“看”“引”和“惜”整合了多个意象,对整体意境的构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登高远眺的“望”字以“北国风光”为背景,引出“长城”“大河”“山”和“原”等诸多写实的独立意象,从整体上营造出革命形势的残酷。满是憧憬的“看”字以“晴日”为背景引出“红装”“素裹”的妖娆景象,在总体上指出风雪过后必有阳光的自然规律,也表达了不畏时艰、革命必胜的信念。“引”字则以“江山多娇”为背景,叙写为美好江山所倾倒并为之而奋斗的“英雄”人物的整体意象。而“惜”字承上启下,整合有着显赫功绩的五位帝王文治武功的不足,指明能与美好河山相配的只有当今的风流人物——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翻译时,溯源动词“望”“看”“引”和“惜”的认知结构和意象图式有助于选择具有相似或相同体验认知的译语,还原诗的整体意境。首先,“望”表辽阔意境。“望”从字形上看很像一个人站立在大地上睁大眼睛向远处眺望,在古代指帝王遥祭山川、日月、星辰;而英文overlook 的词形结构over(above)+look 表“往下看”,暗合登高望远之意。overlook 从视觉的整体意象上还原了原诗“北国风光”的辽阔之境,指出长城、大河、山、塬尽收眼底。其次,“看”表对比意境。“看”字在字形象一个人因为阳光太过于强烈用手遮住额头观望,隐含观察之视觉印象;译语介词in 将颜色红(red hue)与白(white)对比传达鲜明的视觉意象,通过一个心理印象置于另一个之上,来构成强烈的映衬,在视觉上还原原诗中风雪过后红日与白雪交相辉映的完整意境。再次,“引”表行为意境。“引”字是个指事字,本义指拉开弓,泛指拉伸的动作,有“领”“招来”之意。译语attract 描绘“拖过来”的动作,表达“招引、吸引”之义,与“引”语义相似:暗合无数英雄被“江山多娇”所吸引的整体意境。最后,“惜”表惋惜情境。“惜”字以“心”为偏旁,表示与心理、情感有关,以“昔”(表洪水肆虐,太阳西沉的过往时间)为声部,表达对历史的“可惜、遗憾”。译词Alas(唉)表感叹,在整体上以唉声叹气的声音意象唤起惋惜之情,点评历代帝王的不足之处。
诗的整体性既源于具有同种特质的多个意象构建的完整意境,也在于关键语词在意境形成中承上启下的构建作用。在译语表达中,关键语词影响着意境结构,而其认知机理的探究能让相对独立的意象相互关联、相互界定、相互解释。
结语
认知诗学有助于从体验性、突显性和整体性三个方面识解诗中意象。同时,诗的体验性、突显性和整体性相辅相成,直接影响译语表达和诗意创生。意象源于社会生活体验,又因情志而得以突显,创生整体意境。在《沁园春·雪》的认知诗学翻译实践中,译者基于诗人的革命生活和读者的文化生活,体悟诗行中突显的丰富意象,感知诗行音、形、义、意等多维度意象构架的整体革命意境,溯源语词的认知结构和认知机理,科学选择具有相似或相同认知结构的译文语码,传译原诗表达的坚定、乐观、必胜的革命信念。
认知诗学指导下的英译实践聚焦于革命意象的传译,强调译文读者的对于革命意象的认知感受,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没有像传统译文或添加阐述性词语,或补充注释,而是借助语词的社会认知,让译语读者回归生活情景自己去体验革命情景;二是没有执拗于语词的语义对等,而是突显语词的文化认知机理,让译语读者基于自身的文化认知去感受革命情志;三是没有执着于独立意象的阐释,而是着眼于语词构词的认知理据,让译语读者从词形的认知内涵识解革命意象的整体意境。可见,认知诗学注重读者的认知体验,使得译者转变译者为中心的传统思维,以读者的身份在文本鉴赏过程中基于心理体验和文化认知来走近诗人,靠近读者;从读者的视角以语词词源和结构的认知机理为基础传释原诗中的心理意象和整体意境,在原文和译文间形成社会生活认知交互和文化内涵认知交互,让译文遵循生活认知实然,符合文化认知规律。
注释:
①文中《沁园春·雪》表中译文为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