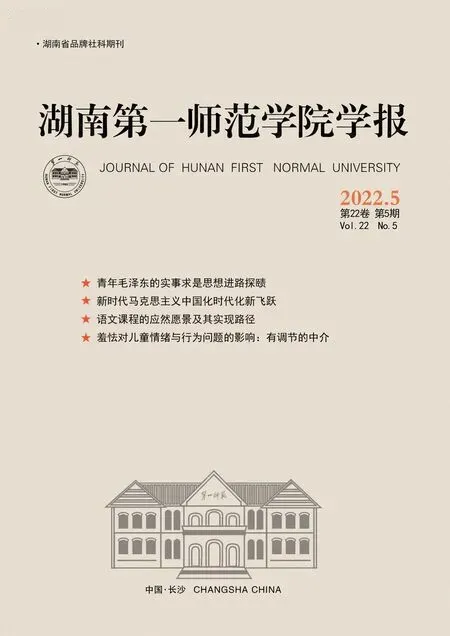《交友论》在华翻译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策略研究
王佳娣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交友论》出版于1595 年,是“西儒”利玛窦在华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译作品,也是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译著的首部世俗作品。该书采用中文和拉丁文双语的形式编译了百则西方格言,引用了大量欧洲名言警句,向中国人展示了西方关于友谊的论述,内容丰富,语言精练,包含了西方关于友谊的伦理思想。该书在中国当时的文人阶层,尤其是士大夫中产生了共鸣,被多次刊刻,先后被编入《天学初函》《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流传甚广。对《交友论》的研究始于20 世纪中期,大体上经历了20 世纪中期的求证考据、世纪之交的价值回归以及21 世纪以来的多视角研究三个阶段。早期研究主要关注《交友论》一书写作和刊刻的背景、所选格言的出处以及产生的影响。20 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中文资料为中心的利玛窦研究的转向,国内学界重新发现《交友论》的价值,相关介绍性文章开始出现。2009 年美国学者蒂莫西·比林斯(Timothy Billings)将利玛窦的《交友论》译成英文,推动了《交友论》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1]。进入21 世纪以来,国内历史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交友论》及其影响展开研究,出现一些以其为专题的论文、学位论文以及著作章节,主要集中于《交友论》的思想研究、《交友论》与《逑友篇》的比较研究、利玛窦的交友观等方面[2-4]。虽然有学者关注了《交友论》的著译策略,但其侧重于探讨利玛窦的翻译伦理观对著译策略的影响[5]。《交友论》一书集中体现了利玛窦的友谊观,对其研究有助于了解明末清初中西友谊观形成的共鸣,以及此共鸣背后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对《交友论》在华译介传播历史的梳理,以及对其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对于深入理解利玛窦的翻译策略和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对《交友论》在华传播的发起、编译、传播与接受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其中的文化适应策略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从文化传播的视角重新解读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重要作品,并为当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交友论》在华翻译传播的过程
在传播学领域,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首次提出了5W 模式,将传播的五个构成要素按序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链式结构,成为传播过程研究的里程碑[6]。

图1 拉斯韦尔5W 模式示意图
尹飞舟、余承法在拉斯韦尔5W 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译者要素,构成翻译传播的六要素,即翻译传播主体、译者、讯息(原语讯息与译语讯息)、媒介、受体及效果,并将翻译传播过程可分解为活动发起、翻译、传播与接受四个环节[7]。根据该观点,《交友论》在华翻译传播的过程可分为传播发起、编译、流传和接受四个阶段。
(一)《交友论》在华传播的发起
利玛窦来华后先后在广东肇庆、韶关等地定居,但由于在当地生活受到限制,便萌生了到南京定居的想法。在定居南京的打算失败后,他接受学生兼好友瞿汝夔的建议,来到其家乡江西南昌。在瞿汝夔及名医黄继楼的引荐之下,利玛窦很快结交了当地文人及权贵。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多次详细描述了与乐安王和建安王的交往,他们互送礼物,其中利玛窦送出的礼物常常是自己绘制的地图或刻制的日晷等,送给建安王的日晷上还用中文书写一些西欧伦理格言[8]189,于是建安王邀请利玛窦写一本记录西方人论述友谊的书,便有了《交友论》的编译和刊印。
由以上的史料记载可见,《交友论》的在华传播是由传播主体建安王发起,译者利玛窦和其朋友瞿汝夔、黄继楼等共同推动的结果。该书在华传播活动的发起存在偶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中西文化相互吸引后带来的深层次文化交流。从深层追溯历史文化原因,《交友论》传播活动的发起与晚明社会阳明学重视友伦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玛窦用来自西方特有的礼物成功地吸引了中国士大夫和贵族阶层的注意,凭借其深厚的儒学积淀和卓越的中文表达水平,成功地为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建安王正是在看到西欧伦理格言与中国传统友谊观存在相似之处,才提出由利玛窦编译《交友论》一书。这不仅是对一本书的兴趣,而表达了建安王想要了解中西友谊观异同的强烈意愿,这也成为《交友论》一书在华传播发起的重要动机。
(二)《交友论》在华的编译
关于《交友论》编译时采用的底本,方豪曾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指出《交友论》里的名言警句主要出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第奥杰纳斯、柏罗多亚尔、奥古斯丁、荷拉西、西塞罗等作品中关于友谊的论述[9]。史景迁则进一步补充雷森德、塞涅卡、马提阿利、普鲁塔克等人的格言,并指出这些可能都来自利玛窦当年在罗马读过的雷森德著作[10]。孙尚杨、何俊、荣振华等也对此进行过考证,提出不同的观点,其中荣振华指出在《交友论》中,利玛窦不仅引用了欧洲的著作,还从《诗经》《论语》《礼记》等中国传统经典中获得借鉴[11]。据利玛窦书信记载,他在编写这部书时,“为了尽量迎合中国人的兴趣,根据需要,将许多西方哲人的名言或西方谚语都作了随意的改动[8]236-237”,该观点也与研究者的观点相互印证。
《交友论》一书用拉丁文和中文双语的形式编成,里面收集了西方关于友谊的名言警句,其中运用了大量正反说、比喻、类比、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使其兼具哲理性与文学性。通过正反说“友友之友,仇友之仇”来表达对待朋友的友和敌之不同态度;“友与仇,如乐与闹”则将朋友与敌人分别比喻为和谐的音乐和嘈杂的噪声;他还将“世无友”类比为“天无日”“身无目”,将“交友”类比为“医疾”。《交友论》中还大量运用了对偶和排比句式,简明且深刻地展现了西方关于友谊的论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利玛窦采取的翻译策略使译文与原文更倾向于功能上的对等,而非字面意义转换。因此,融合了摘译、阐译、译写等在内的编译是《交友论》的主要翻译方法。由于该书的编译主要是应建安王要求发起,编译时间较短,因此《交友论》一书仅收集了部分西方关于友谊的格言,而未对这些格言的出处加以说明,造成后世对《交友论》一书中翻译策略的研究未能深入到文本层面。同时,该书篇幅较短,探讨的主题仅限于友谊,未对西方伦理观进行全面的阐述。
(三)《交友论》在华的流传
关于《交友论》的具体编译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为1595 年在南昌即有了初版;其二为1599 年在南京刻印。著名学者方豪持第二种观点,但据《利玛窦书信集》记载,利玛窦在1596 年10 月13 日写给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提及了前一年中《交友论》的译作过程[8]231-232。这说明该书的初稿在1595 年就已完成,利玛窦还依当时中国士人的惯例,邀请官员冯应京为该书作序。
根据裴化行的记述,利玛窦在该书初稿的正文后还附有其编写的汉语拉丁文拼音,并附有冯应京的序言。当时这本小集子收有76 则格言,被赣州知府偷偷拿去付印,但刻印时省去了拼音方案[12]。由此可见,利玛窦的《交友论》在完成之初有多个刻印版本,绝大部分未经他的同意便私自翻印。1599 年8 月14 日,利玛窦在写给高斯塔神父信中写道他在1598 年已将《交友论》中的文本又译成了意大利文,后寄往罗马,保存在额我略大学(Pontificia Universita Gregoriana)文献馆,并于1825年及1885 年发表,其中论友道的内容是76 则[12]。因此该书初刊本并非百则格言,而是76 则,初刻本可能题为《友道》或《友论》,后补充至100 则,直到1601 年冯应京再刻时,才将其名定为《交友论》。因此该书有《友道》《友论》《友道论》《交友论》等不同书名。该书除了在中国和欧洲传播外,也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
(四)《交友论》在华的接受
《交友论》一书一经刊行,便流传甚广。至明崇祯二年(1629 年)李之藻将其收入《天学初函》前,刊行的次数已无法考证。冯应京所作的《刻交友论序》对利玛窦其人和该书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利玛窦来到中国实属不易,为人真诚、慷慨,对友谊的论述详尽。他对《交友论》一书中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进而提出“视西泰子迢遥山海,以交友为务,殊有余愧,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13]116。利玛窦的学生瞿汝夔在《大西域利公友论序》中对该书大加称赞,并认为其精髓与儒家思想相符。陈继儒也在《友论小叙》一文中赞同《交友论》中的观点,认为“四伦非朋友不能弥缝”,认为“刻此书,真可补朱穆、刘孝标之未备”[13]119。朱廷策也在《友论题词》中指出“利山人集友之益大哉”[13]120,肯定了《交友论》的积极影响。
除现存序、跋、题词等外,也有文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交友论》加以评论,姚旅在《露书》卷九中引用了数条《交友论》中的格言,并感慨中国和西方虽各处地球一方,其为人交友之道却有众多相似之处[14]。可见其对《交友论》一书友谊观的认可。王肯堂在《郁冈斋笔尘》中对《交友论》的语言大加赞赏,直言“病怀为之爽然”,并引用了其中30余则格言[15]。在利玛窦与金尼阁合著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中,多处记录了《交友论》在当时被传诵的情况。其中提到利玛窦在赣州某县任知县的朋友刊印了该书的中文版。此后该书又在北京(疑为南京)、浙江和其他一些省份重印,每每受到文人们的好评[16]。
在《交友论》一书的编译过程中,利玛窦把中国传统经典中提及却没有做大量阐述和具体论证的友谊作为论证对象,与西方格言进行对比阐释[17]。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适应”的思想,《交友论》一经发行便受到了中国士人的热烈响应,推动了《交友论》的在华传播与接受。
二、《交友论》对中国文化的适应
文化适应作为一种传教策略,首先由范礼安提出,主要强调在不违反教会规定的情况下,传教士应主动学习所在国家的语言,习惯所在国人民的生活方式,适应当地习俗,尊重当地传统。利玛窦继承了范礼安的观点,并灵活地加以运用,将其具化为思想适应、语言适应、礼仪适应和生活适应等。在其中文著译作品中,利玛窦表现出明显的文化适应倾向,主要体现在对儒家思想的阐释和融合、对中国传统认知的认同、对中国人接受心理的关照以及对汉语语言习惯的尊重等方面。利玛窦在《交友论》一书中不仅引用古代儒家经典,也对明末阳明学的友谊观加以调和,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适应。
(一)《交友论》中的合儒、补儒策略
早在编译《交友论》之前,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的编写中已经大量引用古代儒家经典,也曾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可见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入了解。他还考察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了解该考试全以“四书”为范围;“此外尚考伦理,这伦理来自六经。……我们曾从他们的经中找到不少和我们的教义相吻合的地方”[8]209。可见利玛窦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统地位,在伦理观念上,利玛窦也在儒家经典中寻找到了共鸣。
首先,利玛窦寻找与儒家著述中谈论友谊相合的西方格言,让二者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儒家经典中关于友谊的论述很多,比如关于择友要择善,近朱者赤。《论语》中将朋友分为益友和损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曾子曾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交友论》中也说:“居染廛而狎染人。近染色,难免无污秽其身矣。交友恶人,恒听视其丑事,必习之而浼本心焉。吾偶候遇贤友,虽仅一抵掌而别,未尝少无裨补,以洽吾为善之志也。交友之旨无他,在彼善长于我,则我效习之;我善长于彼,则我教化之。是学而即教,教而即学,两者互资矣。”这些关于择友应择善的观点与《论语》中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交友论》中关于重义轻利,时穷品见,友贵诚信,表里如一等观点,也可以在《论语》等儒家经典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
其次,利玛窦在《交友论》中也涉及了死亡、平等、博爱等主题。比如“既死之友,吾念之无忧。盖在时,我有之,如可失;及既亡,念之如犹在焉。”这与儒家思想中“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齐家》)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但儒家的生死观主要围绕“孝”展开,在祭祀和怀念逝去的亲人时谈论生死,在这里利玛窦将其引申到了朋友之谊,是对儒家“孝”思想的拓展。《交友论》中倡导平等的交友观,这与古代儒家思想相悖。古代儒家思想中将朋友置于五伦之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理是社会的主要关系,而利玛窦将朋友视作第二个我,且提出了爱敌人,将敌化为友的观点,这种平等、博爱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补充。
(二)《交友论》与明末阳明学友道观的契合
关于《交友论》中的友谊观与晚明社会思想之间的关系,业内学者基本持两种观点:一种以何俊为代表,认为《交友论》中包含的西方世俗伦理与儒家传统存在一致性,同时认为该书并没有提供真正富有启发性的新思想[18]。另一种以郝贵远、关明启等的研究为代表,认为该书对阳明学友道观思想的形成带来了影响[19-20]。黄芸在比较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对《交友论》在晚明社会的接受基础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利玛窦的友道论与阳明学友道观念之间的关系[21]。
晚明阳明学对传统的儒学友道观进行了新的诠释,同时还有部分明末士人如王畿、何心隐、顾大韶等将友伦置于五伦之首,从而改写了五伦的传统位序。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为重,友伦常被忽视。而晚明阳明学则将友谊提升到其他伦理关系之上,提出“同志于道”和“以友辅仁”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同志于道”的关系才最牢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关系均应以友谊为基础,否则只是在利、情、色的基础上的暂时结合,易于因各种变化而导致关系破裂,从而形成“以友辅仁”的观点。利玛窦的《交友论》对为什么交友、如何交友、如何维护友谊等西方交友观进行了较全面的说明,非常契合阳明学“以友辅仁”的需要。利玛窦的友道观与阳明友道观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
第一,都认为朋友有通财之义。《交友论》认为对朋友的财务馈赠并不需要回报,这与阳明学者的理念和作为是一致的。阳明学者对贫弱者的帮扶和朋友间的馈赠和资助常见于各类记载,有些甚至写在他们的会约中。第二,都认为朋友关系高于父子兄弟关系。《交友论》中将朋友视为“第二我”,将其比作“双目、双耳、双手、双足”。认为好朋友常以兄弟相称,好的兄弟关系也可以成为朋友。该书还列举了亚历山大王与臣子的对话,力证君臣关系也可以成为朋友关系。但在这一点上,阳明学不及《交友论》的平等观念彻底。由此看来,阳明学的友道观在利玛窦《交友论》完成之前就已形成,其为《交友论》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社会思想基础,利玛窦的《交友论》中关于友谊的观点契合了中国晚明社会阳明学派的友道观,因此受到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欢迎。
利玛窦在编写《交友论》时采用的文化适应策略有力地推动了该书在华的传播。利玛窦在《交友论》一书的署名为“大西域山人”,暗示自己是远离世俗的文化隐士,以拉近与明末文人间的距离。该书选择百则西方格言编写而成,在形式上,与儒家重要经典《论语》相类似。《论语》中的大部分内容也是以短小格言、警句的形式表达,这样的文体更适合反复阅读和思考。除形式上的适应,《交友论》在内容上也为适应中国人心理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利玛窦在编译《交友论》时在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寻找关于友谊的表述,做到合儒;同时对儒家思想进行拓展补充,做到补儒;另一方面该书顺应了明末社会友道观的演进,特别是与阳明学友道观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此,该书在出版后迅速传播,引起明末士人的广泛关注。
三、《交友论》在华翻译传播的当代启示
《交友论》一书首次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关于友谊的观点,促进了中西伦理思想的交流。利玛窦也因此声名鹊起,受到士人阶层的接纳,以“西儒”的身份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交友论》在华翻译传播发起看似是偶然契机下的行为,实际上与利玛窦一直奉行的“文化适应”策略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史为鉴,在国家“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交友论》翻译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策略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传播主体要适应译入语的社会环境
《交友论》在华传播的成功与利玛窦的个人魅力和策略选择存在重要的关联。利玛窦具有较高的语言天赋,中文表达流畅、谈吐高雅,自称“西儒”,且知识渊博,从自然科学到人文历史均有所涉猎,所到之处皆受到中国士人的欢迎,为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交友论》在编译的过程中,采用合儒、补儒策略,又从明末阳明学的友谊观中找到中西方友道的共通之处,适应了明末社会环境。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依靠传播主体和译者的共同努力,高素质的翻译传播人才是重要的一环。从事翻译传播的主体不仅要具备所需的语言能力,还要具备适应译入语社会环境的能力,将翻译传播行为融入主流社会场域,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触动中国文化传播的契机,使文化传播成为自然而然发生的行为。
(二)传播内容要适应译入语文化的需求
《交友论》翻译传播活动发起的直接动机是建安王想了解西方友谊观的愿望,体现了中国士人贵族阶层想要了解西方伦理观的需求。随着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定居,一些西洋器物,如钟表、日晷、地图等逐渐进入明末士大夫阶层的视野,中国士人存在猎奇心理的同时也首次面对全新的“世界”观,思想上受到较大的冲击,萌发出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化的愿望。中西方对友谊观的同等重视、友谊具有的价值使《交友论》一书大受欢迎。由此可见,文化需求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异质文化之间的沟通要从具有共性特征的文化开始,共性的传播内容才能促成异质文化的共生。
(三)传播方式要适应译入语受众的习惯
受众是译语讯息的接收者,翻译传播的效果通过受众的反应得以反馈。《交友论》的目标受众是明末士大夫阶层,因此在编译该书时,利玛窦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使语言表达颇具文学性,因而能使中国士人发出“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的感慨。因此,作为翻译传播的直接对象,受众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以及讯息接收习惯和动机都会影响翻译传播的效果。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根据不同需要将受众分层,再针对不同层次的受众采取不同的策略做好精准传播,同时也要利用媒介技术的发展,开展多渠道、多模态的翻译传播形式,以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结语
《交友论》不同于利玛窦以宗教和科技为主题的著译作品,是一本论述西方友谊之道的格言集。该书由利玛窦选取素材、编译成书,因而其中蕴含着利玛窦个人的友谊观。从翻译传播的视角看,《交友论》的在华传播是在明末社会背景下,以西方格言警句为传播内容、以图书为媒介、以明末士大夫为受众,由传播者建安王和译者利玛窦共同推动的一次中西友谊观的交流。其中的友谊观一方面受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借鉴了儒家伦理观中友伦的观点,尤其适应了明末阳明学的友伦观,是中西文化适应与调和的产物。利玛窦在编译《交友论》时采用的“文化适应”策略有力地推动了该书的在华传播,开启了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当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