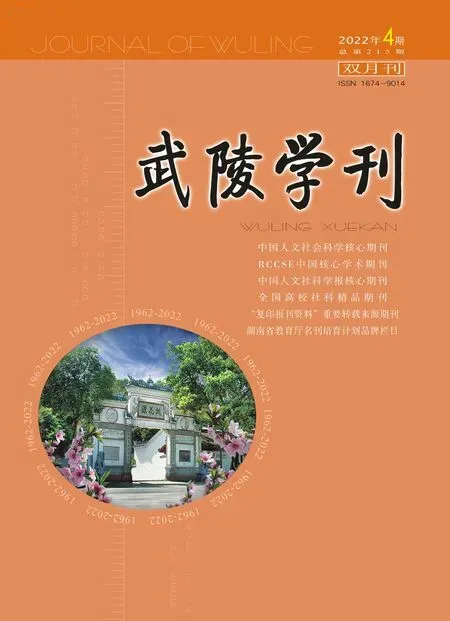晚清湖南武陵杨氏家族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衍
马延炜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作为明清时期重要的文化世家之一,湖南武陵(今常德)杨氏的相关研究一直较为学界所重视。21 世纪以来先后出版的两部相关著作中,均为其设有专章讨论①。但这些分析多将视野集中于明清之际,主要关注杨鹤、杨嗣昌父子的诗文成就,而对嘉道以降,同样存在于武陵地区,由杨丕复、杨彝珍、杨琪光、杨世猷四代人所组成的学术家族缺乏注意。本文钩沉史料,对这一家族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衍情况进行分析,冀有助于学者更加具体而微地了解晚清湖南地方学术史。
一、家族世系与著述情况
虽然同为生活于武陵地区的杨姓氏族,但杨丕复、杨彝珍家族与杨鹤、杨嗣昌家族却并非一源。后者于明洪武年间由安徽广德迁武陵,前者则为明永乐年间由江西吉水徙武陵。关于本族的世系源流及迁湘过程,杨彝珍曾有一番说明。根据他的记述,这一支杨姓家族可以追溯到南宋理学家杨万里。明洪武年间时,族中有仁山公者,曾为武将傅友德筹划平蜀,后抗节不仕永乐朝,并由江西吉水迁至湖南武陵,于迴龙桥定居,是为该族始迁祖[1]140。
进入湖南后,该族主要以读书务农为业,至清中叶时,方有名杨健者中举出仕。杨健,字任庵,乾隆十七年(1752)举人,官石门教谕。其人排斥浮屠,提倡程朱理学,在任期间,“诸生无有敢以事干县庭者”[2]2。杨健治家有方,儿孙列庠序者有六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杨健九十岁时,以五世同堂获赐“耄龄垂裕”坊及黄缎银米[3]1166。杨健有七子,第五子名杨文斗,字炳章,虽以岁贡生终老,未曾中举出仕,但其不废家学,“正体嶷然,造次必于儒者”[1]140。《武陵县志》编纂期间,杨文斗曾被时任武陵知县杨鹏翱聘为采访[3]1166。杨文斗有杨丕复、杨丕树二子。杨丕复,字愚斋,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后官石门训导。杨丕树,字松坞,乾隆六十年(1795)举人,嘉庆十三年(1808)大挑一等,官广东四会知县。
在这一支杨氏家族的繁衍过程中,杨丕复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人物。正是从他开始,该家族从一个普通的乡里望族开始转变为以研究、著述见长的学术家族。杨丕复著述颇丰,有《仪礼经传通解》五十八卷、《春秋经传合编》三十卷、《舆地沿革表》四十卷、《朱子四书纂要》四十卷等。杨丕复有三子,长子、次子早夭,第三子为杨彝珍。杨彝珍(1806—1898),字性农,一字湘涵,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改庶吉士,官兵部主事。时太平军初起,由粤西入湘,杨彝珍乃乞假归里,倡乡兵以卫桑梓,后不复出,光绪十七年(1891)以重宴鹿鸣,赏加四品卿衔。杨彝珍擅长古文,是晚清湘籍桐城派文士代表人物之一。
杨彝珍有五子,次子名杨琪光,字仲琳。杨琪光“年踰弱冠,即补弟子员,旋食廪饩,因为制举文不习为软美语以逐时好,七赴棘闱无所遇”[1]146,捐江苏候补道,后病逝于南京任上。他热心时政,曾多次上书陈言,仅其《博约堂文钞》卷九中就保存有8 篇奏议,内容涉及屯田、钱法、洋务、兵制等多个方面,然“尚仅十之一二”[4]1。热心时务之余,杨琪光也不忘著述,有《经义寻中》十二卷、《史汉求是》五十五卷、《百子辨正》二卷等著作。此外,还有诗文集《带星草堂诗钞》一卷、《博约堂文钞》十一卷、《瑞芝室家传》二卷。
杨琪光有世垣、世猷、世墉三子。次子杨世猷,字继之,关于他的详细生平,由于资料缺乏,目前还了解得比较有限,只知道其“习闻祖父言古文法,瓒承丕替,为文措辞甚艰而不苦于晦,用意虽琐而不伤于繁”,曾官县学训导[5]。杨世猷著述虽不似其父、其祖丰富,但仍有《希贤斋文集》四卷、《旧史内篇》八卷二种著作。
从杨丕复开始,杨氏家族每一代都有从事学术研究的杰出人物出现,虽各人著述多寡不一,但始终不坠家声,洵可谓一学术家族矣。
二、学术研究及其成就
“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治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6]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历史上,学术研究在家族中的代际传承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仅在清代,比较重要的学术家族就有吴县惠氏、高邮王氏、常州庄氏等多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术世家大多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研究领域,比如吴县惠氏专注于《易》学研究,高邮王氏父子以小学研究见长,常州庄氏家族则提倡春秋公羊学,与此不同的是,晚清湖南武陵杨氏家族虽也是数代从学,却各人术业有专攻,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在传统学术的不同门类中都有所成就。
(一)经学
晚清武陵杨氏家族的经学研究,既有专门著作中的集中探讨,也有散见于文集、信札等处的文字。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在尊奉程朱理学的同时又不废考据之功,兼采汉宋二家之长。
以《仪礼》为例。一般认为,《仪礼》一经,书成于秦统一六国之前,西汉武帝时列为五经博士之一,东汉郑玄遍注群经,将其与《周礼》《礼记》并列,形成了所谓“三礼”。“三礼”之中,又以《仪礼》叙述上古礼制,最为难读。清代汉学兴起后,《仪礼》学研究者分化为两派:一是以乾嘉学者为代表的汉学派,研究重点在于对古今异文进行疏证;一是以姜兆锡等清初学者为代表的理学派,其特征是继承朱熹理学,研究“以广博著称,注重群经文献记载与《仪礼》之贯通”[7]。
杨氏家族的《仪礼》研究属于朱熹一派。朱熹原有《仪礼经传通解》一书,杨丕复认为其“规模齐整,条目疏通,洵读礼者所必考矣”,但由于其中《王礼》一篇尚未完成,《丧礼》《祭礼》二篇又出朱熹弟子黄干之手,“未经是正,亦非朱子之成书也”,而在朱熹手定的篇目中,也存在着部分可商榷的内容,乃“不辞僭妄,更取而参校之”,“所有增损更易,总期归于一是而已”[8]。这说明杨著撰写的初衷,就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朱熹的相关著述,阐明朱子学。杨琪光的研究虽不似其祖卷帙浩繁,但也体现了“尊朱”的基本立场。其所撰写的《经义寻中》第四卷《仪礼》,收录了《读仪礼全经》《读士冠礼》《读士昏礼》《读士相见礼》《读乡射礼》等13 篇文献,均为其研治《仪礼》的心得体会。杨琪光十分重视“礼”的教化作用,认为“人生初服,不宜或苟也,苟任其纵于奇褒,将滑正丑贤,不极于奸恶之雄不止”,解决的办法则是“崇学修礼”,士冠礼”虽十分繁琐,也正是由于“其严肃繁重若此,即同顽冥,亦足振其荒怠之气,而勉进于贤人硕夫之列”[9]12。
杨氏家族的《春秋》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杨丕复的《春秋经传合编》三十卷、《春秋宗经录》十四卷。杨琪光也在《经义寻中》一书中,用四卷的篇幅对《春秋》进行了研究。与对《仪礼》的研究类似,杨氏家族的《春秋》学研究也较为尊崇程朱之学。在《春秋经传合编》卷首所胪举的该书“引用姓氏”中,杨丕复称程颐、朱熹为“子”,其余学者则称氏。与一般《春秋》学研究者多专主一传不同,晚清湖南武陵杨氏家族的《春秋》学研究较为重视经文本身。杨丕复的《春秋经传合编》推崇朱熹所创立的“纲目体”,该书“以经为纲,以左氏传纂辑为目,随经分附,无传则但列经,无经而有传者,或足备参考之资,则亦随类附之。要使纲目分明,庶几案断简易”[10]。《春秋宗经录》更是直接以“宗经”为题,该书以经文为主,折衷三《传》之说,意在革除前人轻经重传,违经从传之弊[11]。与杨丕复类似,杨琪光也十分强调经文本身,在经与传的关系上,他认为“非三传而春秋之事无征,泥三传而春秋之义晦”,重要的是要“采择”,“三传之与经合者,吾采之,三传之与经违者,吾弃之。非弃传也,从经也”[9]3。
需要指出的是,杨氏家族的经学研究虽崇敬宋学,但也不排斥汉学。杨琪光就曾提出,“后人每左汉学而右宋学,假非诸诂家为先发藻,莫识端倪,……又奚能折中尽善而归于一是,是紫阳之能成集注者,赖群儒为启其户牗也”[4]3,表现出汉宋兼采的学术倾向。
(二)史学
与经学研究相比,晚清武陵杨氏家族在史学领域的撰著更为丰富。杨丕复的《舆地沿革表》赢得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赞誉,成为我国近代历史地理学史上的一部名著。杨琪光对《史记》《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撰成《史汉求是》五十五卷,杨世猷则编写了一部东汉一朝的历史人物纪传。
《舆地沿革表》是一部关于历代地名沿革的工具书,全书共四十卷,前四卷为“总纲”,第五卷起为“分纪”。“总纲”上起唐虞,下至清代,简要叙述了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变迁情况。“分纪”依作者所生活的清嘉道时期的省级行政区划设目,各省卷帙依内容多寡不同,奉天、顺天、浙江、福建、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各一卷,湖北、湖南、广东、甘肃、山西、陕西各二卷,直隶、江南、四川、山东各三卷,河南四卷。在内容编排上,各省又依省、府、县三级行政区划分别叙述,均首列当代(清代)区划,然后梳理沿革变迁。以湖南为例,杨丕复首先叙述了清代湖南省境四界、巡抚设置和所领州县数量,然后依时间顺序,对唐虞至明代的湖南省级区划演变情况进行梳理,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对湖南各府、县的沿革演变进行了梳理。杨丕复还在建置沿革下附录各地山川脉络,注重对自然地理情况的梳理。《舆地沿革表》完成于道光五年(1825),但一直未曾刊刻,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方由杨琪光在南京刊刻,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赞誉。梁启超所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叙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时,将杨丕复此书与康熙时陈芳绩著《历代地理沿革表》进行比较,认为:“陈书按古以察今,杨书由今以溯古。陈书以朝代为经,地名为纬。杨书以地名为经,朝代为纬,两书互勘,治史滋便。”[12]这一看法后为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所继承[13]。支伟成也在所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中,将杨丕复列入“地理学家列传”,盛赞此书成就。
《史汉求是》是杨琪光撰写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著作。作为我国传统史书中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史记》和《汉书》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史学的热门领域。《史记》记载了三皇五帝至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汉书》记载了西汉一朝的历史。“西汉二百年历史,《史》《汉》两书重叠部分整整一百年有余”[14]570,加之《史记》成书在前,班固在撰写《汉书》的不少篇目时都参考了《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因此,《汉书》对《史记》内容的剪裁,二书对同一历史事件、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记载,以及在此基础上二者孰优孰劣等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话题,并产生了“扬班抑马”和“扬马抑班”两种观点。杨琪光的观点属于后者,《史汉求是》一书除了对《史记》《汉书》进行文字内容上的仔细比较外,还在每卷末以“枉川子曰”的形式论赞二书优劣。如关于吕后史事,杨琪光认为《史记》文字至善至当,《汉书》无此史识,以致详略失当,文字破碎,“太史公作本纪等,先将其人衡当,然后量而汇事。吕氏为汉贼,其所载皆植吕倾汉之为,而于当时于彼无关系者概屏焉。傥胪列之,讵不邻于褒乎?班氏不识此义,于详者转略,略为详,又无篇法,不啻张米盐杂碎店矣”[15]。再如对项羽事迹的记载,杨琪光认为:“《项羽本纪》迺史公极惨淡经营者,字字如铜铁壁垒,无一可摧破,班氏故倒裂以矜己能,真不堪识者之一盼。”[16]在他看来,《史记》“其标目条流皆各有义例之不可紊,且褒讥笔削皆曲当有体,足称赅赡而吴舛误者”,班固应该对司马迁“未及纂属者而续补之”,而非“篡易其篇章,而致使词宏者纤驳,绮丽媺雅者无采,神清折者气薾而弱”[17]。杨琪光的这一观点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当代学者张大可先生在对比了《史记》《汉书》对吕后史事的记述后,认为《史记》“从史的方面完整记叙了吕太后临朝,诸吕擅权始末,从文的方面生动塑造了一个刚决残狠的女政治家形象”,而班固把《吕太后本纪》所载的吕太后鸩杀赵王如意,残害戚夫人,以及立诸吕为王等事移入《外戚传》,将吕太后欲鸩齐王刘肥,害死刘友、刘恢,以及大臣诛诸吕、立文帝等事移入《高五王传》,又把陈平、周勃等大臣有关谋除诸吕事移入《张陈周王传》,使“史事零散,人物形象模糊,于史于文两失之”[14]571。
受其父影响,杨世猷也十分赞赏司马迁的史识,他认为廿四史除《史记》外,其他诸史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于是拟将东汉至明史事另撰一书,计划“或一人为一传,或数人一传,默陟予夺,悉一秉至严,曹操、司马懿群辈,皆载之列传中,弗入帝纪”[18],后因东汉文先成,友人见之,深为嘉许,促亟刊刻,乃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付梓,是为《旧史内篇》一书。该书共分八卷,所涉及的人物,自光武帝刘秀始,至孙坚、孙策止。每卷末以论赞的形式进行评论。
(三)子学
清代子学研究在鸦片战争以后进入高潮[19],在湖南,随着本地汉学研究风气的流行,也有不少学者从事子部典籍的整理与校释,催生了一批学术成果,如王先谦《荀子集解》《庄子集解》,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曹耀湘《墨子笺》等。
杨氏家族在子学领域亦有撰述。杨琪光《百子辨正》二卷,为其阅读96 种子部典籍后的心得汇编。总体来看,该书于典籍真伪问题颇为留意,如怀疑贾谊《新书》“《修政语》上下篇,半采陈言”,认为系“后世盗古人名,摘此装饰成书,如《鹖冠子》之类”[20]10;又认为《新序》与刘向清俊的文风不符,疑该书为“其时好纂辑者所序,子政名列其首,如某某鉴定之类,后残去,检书者误指为其所自撰耳”[20]13。除了对文本本身的考订,杨琪光还对一些典籍进行了评论,颇有独到之处。比如《孙子》一书,他一方面肯定“此十三篇固为孙子独出独入操胜算者”,但同时也指出,战争胜利的根本在于武器装备,“倘不济以盈盈武库之兵械,如邱如阜之粮糈,亦必不能战胜攻取”[20]40。
(四)文学
晚清湖南武陵杨氏家族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勤于创作,留下了数量颇丰的诗文;二是编辑诗文选本,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成绩最突出者,当属作为晚清湘籍桐城派文士代表人物之一的杨彝珍。
杨彝珍擅长诗文,尤以古文闻名于当时,著述颇丰,有《移芝室文集》十三卷、《移芝室诗集》三卷、《紫霞山馆诗抄》一卷等。郭嵩焘曾将晚清湖南古文家进行排序,认为曾国藩得古文之雄,吴敏树得古文之逸,杨彝珍得古文之洁,并云“洁字尤难到”[1]193。杨丕复还编有《国朝古文正的》五卷附二卷,该书选录了从清初顾炎武至咸丰时人姚谌等70 多位作者的400 多篇古文,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排列,是晚清时期重要的古文选本之一。
杨彝珍还十分看重诗歌的教化作用,认为“士生当世,若幸得志,则当佐天子,赏罚于明堂,以进贤退不肖,使天下耸然,思所以自饬,不敢诡随曲谄,以苟容于时。若偃蹇不得进,伏处于野,犹当考哲人谊士之终始,勒为一编,阐扬褒大,以震动当时人之视听,使之诵慕感奋,俾有以立天地之间而持伦物之纪”[1]36。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他对学者邓显鹤编辑《沅湘耆旧集》的行为大为赞赏,除了赞扬其保存地方文献之功外,还特别指出其“勤一世以尽心于斯将,以佐国家褒贬黜陟之所不及,其用意为深也苦也”[1]36。
三、学风的传衍与家族形象的塑造
学术研究风气在晚清湖南武陵杨氏家族的出现和传衍,与该家族几代人的接续传承密不可分。他们重视读书,注重藏书,又特别注重对先人著述的收集、整理、刊布和传播,对家族形象进行了有意识地塑造。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这一学术家族本身,也有助于从一个剖面更加细致地观察晚清湖南地方学术。
重视读书、注重藏书是晚清湖南武陵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曾于乾隆中叶担任石门教谕的杨健“渐次储书”,首开家族藏书之风,传至杨丕复时,已有藏书200 余种,8 900 多卷,分存诸从兄弟者尚不计。杨健还取《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将家族藏书处所命名为“之五堂”,杨丕复认为“所以示我后人读书之法也”[21]。杨氏家族的每一代学者都十分重视对子弟的亲身教导,杨文斗“以课徒为专务,子姓皆不易教于人,而自为督课”,“故邑中饬身修谨之英俊,不问而知为杨氏弟子也”[2]4-5。
除了教导子弟读书向学,这一支杨氏家族还注重通过对先人著述的搜集、整理、刊刻与传播传承学风,延续学脉。杨彝珍曾于弊簏残书中偶然发现父亲杨丕复的一部早年著作,乃“惊喜狂拜,不能自主”,特作跋语一篇,要求子孙“袭而珍藏也”[1]204。杨丕复著述虽多,但生前均未刊行,原因是他认为“凡艺文之足以垂远者,不遽求知于人,其名当俟诸没世之久。必欲汲汲期传布于时,如操奇货入五都之市,深虑折阅其本,遂不暇计其值之与货两相等者而贱鬻之焉,何以异于是”[1]81。其子杨彝珍感叹父亲“抱等身之著述,踬一第以蹉跎,竟不遇于其身,盖有待于我后”[1]139。为了将杨丕复的著述刊布于世,杨氏家族三代人付出了艰辛努力。杨琪光到南京任职时,将祖父《舆地沿革表》随身携带,送给时任钟山书院山长孙锵鸣和好友范志熙阅读。孙锵鸣,字韶甫,号蕖田,浙江瑞安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曾任广西学政,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是李鸿章的房师。范志熙,字月槎,湖北武昌人,咸丰十一年(1861)举人,有木犀香馆藏书,系晚清著名藏书家。在得到二人肯定后,杨琪光更加确认了祖父此书的学术价值,随即将其刊刻于南京任上,他还在该书卷首附上了一篇自己撰写的家传,对祖父生平进行了介绍,此时距离杨丕复去世已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春秋宗经表》则于光绪十三年(1887)由杨彝珍刊行。《仪礼经传通解》因为卷帙浩繁,倍于沿革表三之一,雠校颇难,杨世垣乃独任斯役,并出私钱助刻赀之半。其人为杨彝珍第三孙,杨丕复曾孙[1]81。
杨彝珍著述的刊行与此类似,杨世猷对其祖古文进行了校订刊刻,成《移芝室文集》十三卷,他还为其中每篇文章撰写点评,字里行间,颇多赞誉崇敬之语。如评《荡平粤寇颂》称:“渊懿深浑,原本班固典引,及柳子贞符者,昔李厚庵见望溪《北征颂》,以为韩、欧复出,七百年无此作者,惜未见斯文。”[1]17评《河洑榷署记》称“柳永州之镵刻,苏黄州之俊逸,曾南丰之硕茂,无所不有,唐宋而后,此集其大成。”[1]25虽不无过誉之语,却也可见其传播先人著述的良苦用心。
除了整理刊行著述,杨氏家族还特别注重对先人事迹的书写编撰,教导弟子效仿先祖,不坠家声。杨彝珍《移芝室文集》第十一卷为《家传》,刻画了父、祖读书、治学的生动形象。杨琪光撰写的《瑞芝室家传》二卷,开篇即称“俾吾子姓览之如睹前型”[2]1,用意显而易见。他还将该书送予友朋观览,瞿鸿禨就曾是这些读者中的一个,在为是书撰写的序言中,瞿鸿禨称书中文字皆悱恻动人,“令读者油然生孝弟之思”[2]1。正是这些对先人形象的有意塑造和对外传播,在勉励子孙效仿先人,传衍学脉的同时,也使整个家族的学术形象更广泛地为世人了解并接受。
结 语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演进中,湘籍士人大放异彩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时期,以往“碌碌无足轻重于天下”的湖南先后涌现出多个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家族的崛起与繁盛应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从晚清时期开始,湖南大地世家辈出,先后出现了以湘乡曾氏、湘潭黎氏、浏阳欧阳氏等为代表的名家望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个个家族的“代有人才出”,才有整个近代湖南人才繁盛的局面。武陵杨氏学术家族数代从学,且术业有专攻,在传统学术的不同门类中都有所成就,是晚清湖南学术发展与演变的一个缩影。
注 释:
①参见应国斌著《亦文亦武,儒雅传家——明清之际武陵杨氏世家》,收录于《中国文化世家·荆楚卷》第326-33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王勇、唐俐著《武陵杨氏》,收录于《湖南历代文化世家:四十家卷》第137-15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