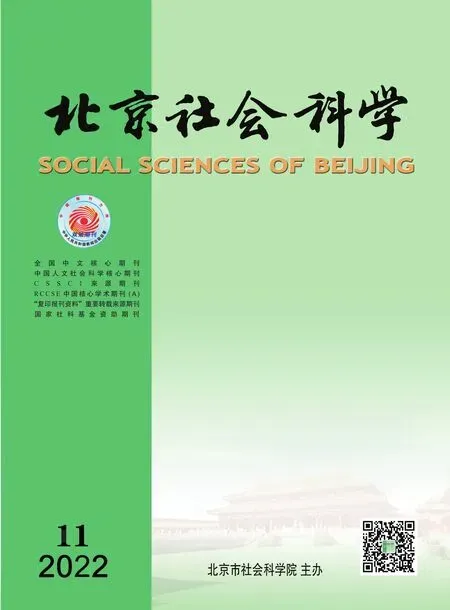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评估
谢永乐 王红梅
一、引言
随着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引致的资源高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失衡等问题日益严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保护相统一,已成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生态文明“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对此,我国根据自身发展实情与全球气候治理共性需求提出“双碳”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规划、十九届六中全会、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等均指出,要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与区域协同攻坚,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对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的大气污染物连片排放与跨域迭代传输问题,分散性属地治理的权责界定模糊、天然“搭便车”倾向等,[1]导致其成效有限,提升协同合力始终是攻克这一困境的共识。现阶段,在以地方政府为“主责者”、中央与地方双重推动型“七省区八部委”联防联控机制体系建设的同时,行政区划分割主导的属地治理模式与特殊任务推动的合作治理模式仍并存于治理实践,虽创造出“奥运蓝”“阅兵蓝”“APEC蓝”及“两会蓝”等显著成效,但这种整体性质量改善却未能可持续化、长期化。为此,遵循大气环境的演化规律,从自主治理能力、协同互动机制、专职绩效考核等层面,切实提升区际精细化分工与通力协作水平,是“十四五”期间推进深化治理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二、文献述评
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效果何以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学术界已从多元维度提出相关认识。例如,魏娜、孟庆国等从制度环境与资源禀赋双重约束的“结构—过程—效果”考察提出,协同立法模糊、协同结构差异、协同过程非均衡性等导致的“被动回应型”模式,虽可获短暂效果,但运行成本巨大且存在着明显的反弹效应。[2-3]王红梅等受“协同多维度模型”[4]启发,通过地方利益类型剖析指出,非对称复合型府际利益关系,是难以达成稳固型合作联盟的根本原因。[5]李牧耘等从联防联控机制演进发现,领导组织及机制不完善、地区“位势差异”、政策工具类型失衡等,使地方政府之间缺乏长效的横向沟通路径。[6]臧雷振等以区域壁垒为视角分析揭示,各地区设置的技术、经济、环境等壁垒,以相互迭代方式阻碍了整体性协同治理进程。[7]贺璇等从模式转型角度提出,由于自然环境承载力约束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的多重差异,中央与地方在协同治理过程中的财政转移支付可能会违背市场运行规律,引发权钱交易、寻租等低效率问题。[8]
在我国由高增速向高质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根据大气污染复合性、公共性、外溢性等特征,立足于区域动态空间发展战略布局,促进经济、社会及生态协调发展,妥善解决属地内部成本—收益失衡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综合绩效水平,是推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持续深化的关键。目前,关于多地区、多系统发展协同度评估与环境治理绩效评估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例如,Christophe B等进行的双元分析表明,建立协同伙伴关系会造成成本提升,阻碍了与远距离、差异化潜在伙伴拓展协作。[9]基于Sieber等的耦合评估思路,吴传清等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检验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绩效的区际差异大,但整体协同效应强劲。[10]张怡梦等针对城市生态脆弱性与政府绩效的耦合协同评估揭示出,狭隘化的绩效法律法规,泛经济化的绩效目标,离散化的绩效主体行为、技术与制度弊端等,使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度较低。[11]孙久文等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分析得出,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辐射力不足,非核心城市联系紧密度较低,内部空间结构有待优化。[12]赵琳琳等根据京津冀生态协同度的动态测定提出,应从整体层面的合理分工、差异定位、精准定责,建立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区域利益均衡机制,促进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13]同时,借鉴Kubiszewski I、Jorgenson A K等生态福利测度框架,[14-15]龙亮军、李成宇等运用超效率DEA模型、Super-NSBM模型、窗口分析法等,测量发现我国省级与市级环境治理绩效水平具有非均衡性空间分布及非对称演化特征。[16-17]杨钧检验发现,户籍城镇化可提升环境治理绩效,产业城镇化具有负向作用,建设城镇化的正面影响不显著。[18]林春等揭示出,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即在东部地区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则具有抑制效应。[19]彭珍珍等基于环境治理联盟竞合的机制考察提出,关系治理在波动的环境中更有效,而契约治理在竞争的环境中更有效。[20]此外,目标责任制、晋升锦标赛、信息公开、社会信任、环境监管等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变动的复合性影响被日益重视。
综上可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正处于大气污染深化治理阶段,随着我国“五位一体”“双碳”等战略的实施,如何逐步化解属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负荷过重的矛盾,破除功能定位、生态补偿等的地区利益博弈困境,持续提升区域整体的低碳—循环—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参照现有探讨多地区、多系统协同发展逻辑与绩效测度的相关成果,本文将融合复杂系统理论、协同理论及大气污染本质属性,评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期(2013-2018年)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耦合协同程度,并从静、动态层面测定地方政府综合治理绩效情况及其演化特征,以探索出提升区域“协同—绩效”水平的可行性路径,为政策措施制定与执行提供相关参考。
三、“协同—绩效”评估体系构建
(一)评估思路
根据大气污染无界性溢出与污染物空间流动特征,从两个维度考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治理的“协同—绩效”情况:第一,基于“五位一体”战略视角,考察同一地区经济、社会及生态系统互动关联程度的耦合协同度,即通过耦合度和协同度测算它们相互影响及协调情况。其中,耦合度衡量两个及以上系统的相互依赖情况;协同度衡量系统之间相互促进的和谐程度。耦合度越高,表明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关系越强。在高耦合度前提下,协同度越高,说明系统和谐共生的关联性越强,地区可持续发展潜力越大。在低耦合情境下,协同度的实际测度意义较差,难以说明系统互动情况。第二,基于成本—收益视角,考察一定时期内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治理绩效水平。政府作为非营利性公共组织,其大气污染治理是一个多对象、多投入、多产出的过程。因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经济社会基础、技术条件、政策导向等差异性约束,各地区在实践中均具有相对优劣势。为此,运用以求解帕累托最优为核心的数据包络分析(DEA),通过投入—产出效率的静、动态测量,对地方政府的绩效水平进行评估与比较。
(二)指标选取
目前,针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成效的指标设计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污染排放与处理情况,如二氧化硫(氮)排放量、工业烟(粉)尘净化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率等;二是资源消耗与节约情况,如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原材料消耗强度、单位GDP能耗削减率等;三是绿化建设与保护情况,如森林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等。同时,根据区域多元系统交叠演化态势、政府多元职能交融承载特征、“五位一体”和谐共生战略目标,逐步融入经济增速、产业结构、贸易规模、城镇化、教育程度等考察内容,构建起多层次、统筹型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在此,基于地方政府可调控原则,将经济、社会及生态系统的要素细分为经济增长、人口发展、资源利用等11个二级指标。通过借鉴“敏感性—弹性—压力”模型、“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等研究,[21-26]参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现行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共选取100个可行性三级指标——经济发展指标29个、社会发展指标26个、生态发展指标45个。通过相关性检验、可鉴力检验及信度检验,筛选出46个有效指标(表1)。由于区域复杂系统的各个领域变化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主观评估的偏好差异较大,故全部选用客观指标。受新冠疫情、暴雨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2019年以来部分地区的数据发布时间及统计口径变动较大,可直接应用的效能相对不足。为此,本文聚焦于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期(2013-2018年)的“协同—绩效”评估,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地区《统计年鉴》《环境质量公报》《财政预决算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少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加以补充。

表1 经济—社会—生态“协同—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三)模型设置
为全面和准确地考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成效,参考已有研究,立足于区域多元系统互促共生情况与地方政府综合治理效率维度,构建耦合协同评估模型与政府绩效评估模型。
1.耦合协同评估模型


表2 经济—社会—生态耦合协同程度分级标准
2.政府绩效评估模型
沿路线运动隐喻描述了路线与数字之间的隐喻映射。与量尺隐喻相同,沿路线运动隐喻也不仅可以描述加法、减法的隐喻映射,同样可以延伸到乘法、除法和分数,并需要创造实体隐喻,以得到0。限于篇幅,我们此处仅摘录莱考夫对加法、减法的隐喻说明,如下:
根据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特征,政府绩效评估分为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


四、经济—社会—生态耦合协同评估
基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2013-2018年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得出适配的指标权重(表1),并按耦合协同评估模型的操作步骤,依次测算出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综合序参量、耦合度及协同度(表3)。
(一)综合序参量分析
根据功效系数测定原理,系统综合序参量值越高,则发展水平越高。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而言:第一,经济发展综合序参量U1的值域为(0.275,0.693),平均值为0.395。其中,U1<0.3的地区为邯郸、邢台、保定与长治;0.3

图1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发展情况
(二)耦合协同评估分析
根据耦合协同评估规律,在高耦合度条件下,达到高协同度需具备两个前提:一是综合序参量整体处于较高值;二是不同综合序参量之间的差距较小。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而言:第一,耦合度C值域为(0.861,0.999),平均值为0.927。即,所有地区处于“高度耦合”,表明三个系统之间具有强劲的相互依赖关系。第二,协同度D值域为(0.526,0.862),平均值为0.601。即,全域处于“初级协调”,但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阶梯性差距。其中,北京处于“良好协调”;天津、济南与郑州处于“中级协调”;石家庄、沧州、廊坊及太原等6个地区处于“初级协调”;承德、张家口、秦皇岛等21个地区处于“勉强协调”(表3)。可知,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综合序参量小且系统之间差距大,导致现阶段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处于“高耦合、低协同”层级。

表3 经济—社会—生态耦合协同情况
基于“高耦合、低协同”特征,可揭示出三个问题:第一,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之间存在着强劲的嵌套型互动关系,均是区域复杂系统形成及演化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的大气污染深化治理,必然是一个牵涉广、关系网络复杂且见效较慢的过程,需具备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的统筹型绩效理念,以实现三者可持续性和谐互促。第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之间的和谐程度低,区域内部负外溢效应大于正外部性影响。一方面,区域生态发展综合序参量(0.540)明显高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序参量(0.395、0.243),表明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顾此失彼”问题,建立在经济、社会等损失基础上的环境质量改善,缺乏长期有效的内在动力机制,难以持续提高生态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大部分地区(占比约为67.74%)的协同度未达到“及格线”,存在着显著的协同治理“短板”。这不仅缘于资源禀赋、政治位势、技术水平、市场环境等现实约束,更是由常规治理和运动治理转化连续谱系[33]中“搭便车”“向底线竞争”等行动博弈理念驱使的结果,[34]难以形成有序联动的区域治理空间格局。第三,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战略布局的多中心、复合型“高耦合度”与“高协同度”互促体系亟待建立与完善。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差异,短期内难以实现发展进度的完全一致,应全面调整“重区域目标、轻属地诉求”倾向。目前,根据不同系统演化规律与空间分布特征,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细分为主体权责功能明确、比较优势交叠互补的多个“小圈层”,是进一步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凝聚力与向心力,提升集体自组织行动效率的可行性推进方向。
五、经济—社会—生态综合绩效评估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大气污染治理是一个多投入、多产出(期望和非期望)过程,地方政府作为主责者,往往希望获得多期望产出和少非期望产出。为此,参照Liu W.B.等的扩展性强自由处置原则,[35]共细分出15个投入指标(X)和31个产出指标(Y)(表1)。
(一)静态绩效评估分析

表4 静态性经济—社会—生态绩效评估情况
基于省域范围划分的平均绩效来看,河北11个城市的值域为(0.741,1];山西4个城市的值域为(0.981,0.995);山东7个城市的值域为(0.835,0.998);河南7个城市的值域为(0.890,0.996)。由此可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大气污染治理的绩效水平差距集中体现于河北,山东次之,这与前文验证的“地区之间综合发展协同度低”结论相符。究其根源,资源禀赋、政治位势、产业结构、市场环境等的同质性程度高,使个体利益为主导的地区竞争意识强,未形成有效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联盟,难以通过互补方式实现投入—产出的帕累托最优目标。从时间维度来看,平均绩效前10名城市的年度变化幅度很小——波动距为0.117。第11-21名城市的年度绩效变化幅度相对较大——波动距为0.239,且具有较显著的单向演化特征。如淄博、太原与长治呈上升态势,衡水与聊城为下降态势。第22-31名城市的年度绩效变化幅度大——波动距为0.456,且存在着多元化演化特征。其中,滨州与邯郸呈下降态势,濮阳、秦皇岛、石家庄、保定及唐山呈“降—升”态势,阳泉与菏泽呈“升—降”态势,安阳呈“降—升—降”态势。这表明,现阶段仍有较多地区缺乏明确的中长期经济—社会—生态统筹发展目标,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易采取“弃卒保车”的措施,致使阶段性绩效水平不稳定、整体成效偏低。按自身实情制定并完善可持续性战略政策,是提升属地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绩效水平、强化区域专项分工协作合力的必然要求。
(二)动态绩效评估分析
任何组织的绩效水平,都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呈现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仅对地方政府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绩效开展静态评估,难以精准把控同等约束条件和测度标准下的演化规律,故需从动态层面进一步探究。所以,融合交叉效率评估和动态窗口分析的机理,取窗口宽度σ=2,即共分为5个窗口——2013-2014年、2014-2015年、2015-2016年、2016-2017年、2017-2018年,依次测定出同一地区在不同窗口的绩效值及变动情况(表5),进而得出平均绩效值与排名。

表5 动态性经济—社会—生态绩效评估情况
在此,可从三个维度探寻演化特征:第一,横向比较。平均绩效值排前10名的依次是济南、开封、北京、晋城、济宁、德州、承德、廊坊、天津、淄博;排最后5名的是菏泽、石家庄、保定、阳泉、唐山。即,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绩效“三阶段”排名格局的变动较小,但前10名城市的排序变动较大,这缘于它们绩效评估优势的差异更为显著,对测度标准的变化更敏感。第二,纵向比较。区域2013-2018年平均绩效值呈小幅度“升—降—升—降”态势——波动距为0.043,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绩效水平比较稳定。与此同时,各地区在不同窗口的绩效有增有减,但整体呈下降态势。其中,绩效变化幅度排前5名的依次是阳泉、保定、滨州、安阳、长治;整体下降幅度排前10名的依次是衡水、沧州、张家口、邯郸、阳泉、承德、石家庄、秦皇岛、天津、新乡。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属地大气污染治理具有显著的“运动式”特征,尚未探寻出有效的全面、平稳的发展路径,导致其绩效水平受经济贸易环境、特殊政治任务及资源存储容量等因素的影响大。[36-37]二是区域内部潜藏着较严重的“搭便车”“向底线竞争”等问题。虽然目前能确保正外部性影响与负外溢效应基本持平或抵消,但属地常态化治理的内在动力逐步衰退,不利于区域联防联控战略的持续性贯彻执行与优化。第三,立足于省域层面的横—纵向比较。除北京和天津以外,河北11个城市的平均绩效值为0.864,极差为0.256;山西4个城市的平均绩效值为0.843,极差为0.244;山东7个城市的平均绩效值为0.910,极差为0.170;河南7个城市的平均绩效为0.894,极差为0.118。可知,在动态窗口评估中,山东片区的平均绩效水平最高,河南片区的绩效水平差距最小,而河北和山西片区的平均绩效水平偏低且内部差距较大。这与静态评估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在省域内和省际,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正、负外部性问题均显著,需参照大气污染集聚演化格局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技术与教育结构、城镇化发展水平等实情,同步做好省域、市域、县域层面的专项责任目标分解、主体功能区划分、复杂任务分块等联防联控统筹工作,以“共同但有差别”的属地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推动区域大气污染深化治理成效的稳步提升。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大气污染复合性、流动性与极强的外部性特征,决定其治理必然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随着全球气候治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多维系统复合联动的投入—产出规模效益最大化,已成为新时代密切关注与努力追求的核心目标。为此,本文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2013-2018年大气污染治理开展“协同—绩效”评估。基于“五位一体”战略视角的耦合协同评估发现:一是经济、社会及生态系统之间具有强劲的嵌套型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复杂多变的区域动态空间系统,使大气污染治理的牵涉面广、关系网络错综且见效较慢。二是经济、社会及生态系统相互促进的和谐程度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偏低,相对较高的生态发展亦尚未达到及格线。同时,各系统内部均存在着显著的阶梯性差距,且大部分地区处于“低阶”层级,致使区域整体的负外溢效应大于正外部性影响。根据“成本—收益”考察视角的地方政府静态与动态绩效评估得出:其一,同一时期的地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性差异。资源禀赋、政治位势、产业结构、市场环境等的高同质性,促使属地之间的利益竞争意识强,难以通过优势互补的协作路径实现投入—产出帕累托最优目标。其二,区域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绩效的“三阶段”排名格局比较稳定,虽然各地区在不同评估窗口的绩效水平有增有减,但整体呈下降态势。即,在相对优势差异及其敏感性变动的影响下,属地大气污染治理具有显著的“运动式”特征,潜藏着较严重的“搭便车”“逐底竞争”“责任分散效应”等问题,不利于区域联防联控的可持续性深化推进。
扎根于我国“双碳”目标等战略政策导向,全面提升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绩效水平,可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协调好属地发展诉求与整体协同治理目标的竞合博弈关系。一要正视“促动发展”“防疫安全”“保护环境”等多重使命共同引致的地区经济社会差距与现实需求变化。通过政府联席会、政治动员会、专家论证会、环评共商会等,组建专项领导/小组、完善跨地区跨部门协作机制、细化监测—督察—预警标准设定等,健全区域联防联控的纵横向环保利益差核算与转移支付、补偿体系,促使“任务驱动型协同”向“自主参与型协同”有序转变。二要统筹好全域与局域“共同但有差别”的联防联控步调。以主导能源、要素禀赋、核心污染物排放存量为依据,以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太原等为地缘辐射基点,逐步完善多中心、多层级、多梯队的复合型“地域+领域”协作体系,使各地区充分明确自身的比较优势与专项责任目标,制定财政资金分配、污染物排放限值、应急响应等适配方案,实现精细化“韧性”治理。
第二,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与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协调好经济—社会—生态“三维一体”耦合协同机制建设。对经济发展而言,一要根据经济基础、技术条件、市场环境、地理位置等,明确各地区的研发、制造、贸易等主体功能区定位,打造复合型、互补型局域经济圈体系,增强内部协作契合度与外向性竞争力。二要积极推动高经济附加值等知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吸引优质外资企业。同时,提高煤炭、石油等非再生性能源的使用效率,加强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性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提升区域经济增长“量引导”向“质驱动”升级的低碳—循环—绿色型全要素生产率。三要健全各类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加强外商投资分类管理,推进环保型工业园、经济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等建设,逐步优化绿色供应链和生产者责任动态监管机制。对社会发展而言,一要制定差异化政策协调机制完善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网与绿色型城镇化发展,提升地级、县级市在产业承接、科技创新、市场拓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质量和效率。[38]有效解决北京、天津、郑州、济南等“虹吸效应”引致的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二要运用税费、贷款优惠、财政性专项补贴、共同融资基金等激励型政策工具,提升新能源汽车、新型污染物处理技术设备等的应用普及率,实现区域市场消费结构的整体性升级。对生态发展而言,一要以石家庄、邯郸、衡水、邢台、唐山等为典型代表,提升地区环境治理投入比重及其使用效率,完善省—市—县(区)层级的不定期巡查与通报措施,实时督察地区责任目标的执行进度。二要根据地形、土质、降水等情况,分域、分类推动草地、森林、湿地等绿化空间的延展,强化区域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与“可持续性负荷”能力。通过打造森林氧吧、生态民宿、有机牧场、生态农业科技园等联动运营模式,增加生物多样性维护的经济与社会附加值。
第三,完善地方政府综合绩效考核及奖惩机制改革。一要参照国家“五位一体”发展战略布局,深化推行经济—社会—生态导向型目标责任制,以拓展官员政治晋升的环境绩效维度、调减经济权重等为“风向标”,构建“共性+个性”的评估体系,贯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多部门“分责”制度集合。二要基于结构性与程序性评估结果,探索数字信息化治理、绿色GDP核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等方法,将行动成本、经济损值、个体及共同收益等影响因子,有效纳入地区综合发展效益评估范畴,并根据不同阶段的区域空间格局演化实情,精准执行环境绩效“一票否决”“奖惩分明”“动态调整”等措施。三要严格落实相关领导干部的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离任审计要求,健全环境治理问责制和终身追究制,有效防止任期制、分管制等引致的政治“短视”与被动应对式行动策略,倒逼地方政府树立全面发展的绩效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