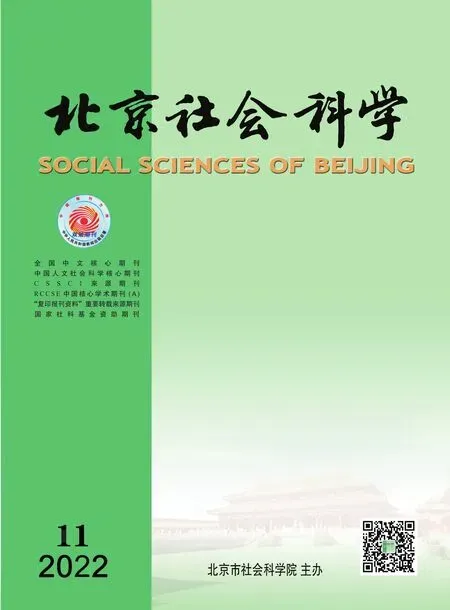“共同体”概念词源、译介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脉络考察
周子伦 刘樊德
一、引言
《共产党宣言》科学预见并提出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在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探索“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过程。进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科学而深刻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其对构建美好世界的重大价值和时代意义。共同体思想概念史研究以词源为出发点,以跨语际视角探究其历史、来源,厘清概念在跨语际中最早出现的记载,追溯其词义的演变、翻译等方面的历时性发展及互文性,是跨学科的创新研究,从而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真正共同体”的思想精髓,彰显《共产党宣言》历久弥坚的科学道理和熠熠生辉的当代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跨文化跨语际视角研究共同体思想概念词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脉络,对了解欧洲古希腊以降的观点、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演变、共同体概念的译介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演变、发展的目标任务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关系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重要内容。
二、“共同体”和“联合体”词源
跨语际词源的研究可以追溯其根源、语义变化、翻译和互文性脉络。研究发现,“共同体”和“联合体”有共性,但是在文字表述和语义方面不尽相同。通过文献梳理,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的关系,可以归纳出两个概念的字词含义、翻译及语义演变。
(一)中西方“共同体”语义溯源
“共同”一词犹言“一同”。《孟子·梁惠王上》曰:“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汉赵岐注:“言古之贤君,与民共同其所乐,故能乐之。”共同的含义是“大家一起(做)”。《前汉书平话》曰:“刘武受诏牌金帛了,即请宋公达、李德、程彦雄共同商议。”共同的含义是“属于大家的,彼此都具有的”。“体”既指“人、动物的全身”,身体、体重、体温、体质、体征;也指“身体的一部分”,四体、五体投地,引申为“事物的本身或全部”,物体、主体、群体。“人类命运”“共同”和“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偏正词组,表示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应该携手相助、和谐共处,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家园。
在西方,共同体的社会性主要表现为社区(community)的群居生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新华字典》将其注释为“同一地、同一地区或同一国的人所构成的社会”。直接的族群关系培养共同体的社交意识,维系共同体持久存续关系,这些共性对共同体成员身份确认、社交活动、家庭、工作以及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与社会或整个社会机构中的互动关系均具有重要意义。对个人而言,共同体可以指共同居住的“社区”,也指大型团体和机构,如国家社区、国际社区和虚拟社区。共同体的出现,是因为人类社会可能会有共同的意图、信念、资源、偏好、需求和风险,从而吸引社会成员作为参与者加入到某种形式的共同体中以凸显某种社会身份,进而增加共同体的凝聚力。《共产党宣言》中的联合体(association)在《柯林斯词典》中的原意是生态概念,指“在某一地理区域共同生活的一组有机体如植物和动物而组成一个群落,是某种植物或动物的联合”。根据《杜登词源词典》的解释,德文的“联合”(assoziieren)作动词用表示“志同道合地联和起来、团结起来、把思想上的想象和某物连接起来。”它是从同义法语词s’associer借用而来的,拉丁语是associare,意思是“陪伴、统一、连接”,这个词是由拉丁语ad(对应德语hinzu,附加)及拉丁语sociare(对应德语verbinden,连接)组合而成的。16世纪中期,其派生的名词是assoziation,表示“统一、志同道合地团结和联系”,17世纪早期从同义的法语词association而来。在生态学中,群落(community)是不同物种种群的集合,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群落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促使物种生存趋向多样性,群落物种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包括竞争、捕猎和互惠。所以,互惠论证明,两个群落中物种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竞争的同时也能够达成合作使物种生命得以延续。人类的群体和生物学的群落定义揭示了“联合体”association和“共同体”community是同义词,联合体(association)一词在16世纪30年代表示“为共同目的而聚集的行动”,源于中世纪拉丁语associationem(主格association),动词associare意思是join with(加入),ad指unite with(接近)。17世纪50年代开始,socius指companion,ally(同盟),指“有共同目的和组织的团体”;17世纪60年代指“心理联系”;1810年演变成“一概念与另一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和联想性”的含义。希腊语的“共同体”(Koinonia)的词根就是“共同”(Koino),指基于共同利益的人群的结合。
(二)中西方“联合体”语义溯源
“联合”本来是医学术语,指“两块以上的骨头长在一起或固定在一起”,如耻骨联合、下颌骨联合等。“联合体”的论说古已有之,《周礼》载有“以官府之六联合邦治”,其中的“联合”说明凡小事也都有合办。儒家的“大同”理想及其国家治理理念就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墨子的“爱无等差”称为“兼”,主张在一个社会群体的联合体内,“爱”是不分亲疏、不分贵贱的,对一切群体的成员都是一律同等之爱。《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主张天下为大家所共有共享,突出了“联合”和“共同”的含义。明朝李贽的《答耿中丞》言:“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主张把人们的自然真实之性推而广之,成为天下的公共原则,这就是“道”,这种“道”蕴涵的观点是人作为社会成员,其个体之真善美可推崇为社会关系的准则。孙中山在《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中提出:“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这些论说都表达了个人不可独善其身,而应联合群体的联合精神。孙中山在遗嘱中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以上文献可知,“联合”的同义词包括“结合”“联结”“共同”“协同”“连合”“统一”等。日语“共同体”原指“以血缘、地缘或感情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人的共同生活的状态。最典型的共同体有村落共同体、企业共同体、政治、外交中的命运共同体以及社会交往中的兴趣共同体(如各种协会)等。”[1]1933年前后费孝通等一批学者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克论文集中的community译成“社区”,并在中国社会学界流通并沿用至今。我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社会运行学派的开创者郑杭生认为,社区是“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2]可见,将community翻译成“社区”应该只适用于社会学的语境之中。
“有关共同体的概念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世纪的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对村庄和公社历史感兴趣的人。”[3]按照《牛津大字典》的community条目注释,community源于拉丁语communitas,古法语为comuneté和communitauté,意思是拥有共同地域和精神信仰(shared locality and public spirit),两词皆源自拉丁语communis,译成“共同的、共性的”(common),拉丁文前缀com-表示“共同”,拉丁文鼻祖伊特鲁里亚语词根munis表示“承担”。Common一词和community一脉相承,汉译是“属于所有人的、共同拥有或使用的、具有公共性质或特征的”。Common来源于古法语comun,汉译是“普通的、一般的、自由的、公开的”,到现代法语变成commun,也是源于拉丁文的communis,本义是 “共同的、公开的、由所有人或许多人共享的、不具体的、众人所熟悉的、不是与众不同的”等多种含义。古罗马西塞罗的《论义务》中使用communitas一词指代“共同体”,这一词语逐渐演化成现代英语的community。
“共同体”的希腊词源κοινωνiα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概念,城邦是指人类聚居组成联合,旨在满足生活的多样性需求,追求特定的共同体利益,以实现生活的尽善尽美,因而是“以公正和具体共同利益为目的,具有共同的伦理取向与共同的利益诉求的人的生活方式”[4]。“政治”(politics)和“城邦”(polis)的词源的希腊语词根都是polis(citadel, fort, city, one’s city; the state, community, citizens),即城市就是邦国,其核心含义是“相互依赖的个人与社团组织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及社会”。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藤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共同体概念的德文是Gemeinschaft,英文是community,汉语译为“社区”,含义的范围稍稍萎缩,指村庄和街坊邻里等地域性的人群结合。后来,各家学说对共同体的定义无不围绕着“基于感情、血缘、地缘、相同生活价值观和目的天然聚集的组织、群体。”与community密切相关的communism(共产主义)源于古法语communisme和拉丁语communis,原意为communal,community,其最初是指动物群居而形成的一个群体,也指部落群体,如animal community(动物群落)和人类的“共同体,社团和群落”。日语将communism译为“共产”,原意是“共同集体”,communism表达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关系,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严复将community翻译成“人群”,后来费孝通将其翻译成“社区”,有的翻译成“社会”,有的翻译成“组织”或 “人群”。滕尼斯在其《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阐述了人类生活的两种群体模式:一是共同体;二是社会。他在书中深刻分析了“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概念,认为 “共同体”是指“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群体”,认为“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可以理解为动物生活的相互关系,犹如精神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心灵的生活的相互关系一样。”[5]他还描述了两种类型的人类群落:Gemeinschaft通常被翻译为“社区”,Gesellschaft被翻译成“社会”或“协会”,他认为可以通过Gemeinschaft、Gesellschaft这两个概念的二分法来界定人类的社会关系,Gemeinschaft强调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基于这种互动的角色、价值观和信念;Gesellschaft则强调间接互动、非个人角色、价值观和基于这种互动的信念。
综上所述,共同体是基于群居人类的相互依存性而产生的一个社会学概念,中西方文献中都有记载国家治理、哲学、社会学和伦理文化的“共同体”“联合体”的思想传统,而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但是都共同指向个体(individual)和群体(community)之间的联合(association)关系。
三、共同体思想的根源与译介
(一)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体思想
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礼记》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其中的政治思想有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等,其中的“大同”就是治理国家的理念,蕴含了政治共同体的范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孔子的 “君子和而不同”则主张君子不是独自生存的,他应该与他人保持和谐融洽的氛围。“博施济众”语出《论语》:“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其表明了古代崇尚同舟共济、乐于助人的思想。典籍所记载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不仅体现了人际关系共处共生的共同体精神,也体现了“公天下”的理想,是先秦儒家思想和国家政治理念的核心内容,即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其把实现社会和国家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一种理想追求。除《论语》《礼记》典籍所主张和推崇的“共同体”“联合体”意义上的“大同”思想外,《中庸》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同样也主张个人和群体之间的道德互信,追求“信赖社群”,并认为“政治的目标不仅在于达成法律和社会秩序,而且还在于通过道德说服来建立信赖社群”[6],之后才有超越社群建立国家并最终达到“天下为公”的可能性。这些思想均蕴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因。
到了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言:“吾既为人,吾将忍心而逃人,不共其忧患焉?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7]其体现了“大同”思想的内蕴和济世观点。人类之所以能够繁衍生息,是因为族群的联合而成的家庭、家族、部落乃至国家,国家的产生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国家的统治阶级颁布法律法规及认可某些社会道德规范族群之间的关系以维持阶级统治,但“有国之害”的民族之间的自相残杀现象必须通过建立民主共同体进而实现大同世界才能消灭。孙中山在“天下为公”思想的启发下主张“三民主义”,旨在追求实现全国人民一律平等,不会有民族、阶级、男女、职业、宗教的区别,全国人民秉承互助合作的精神,谋求与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平等以促进世界大同,即体现人人有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均匀、人人饱暖的理想社会。联合形成合力就是力量,因而,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毛泽东赞同“大同”思想,在后来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用“大同”一词指代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8],只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后才能实现大同。
(二)欧洲思想家传统的共同体思想
共同体最早的形式是因婚姻而形成血缘共同体,基于家庭和宗族而成,也有基于血缘、地缘的共同体。在规模和范围上,共同体有大有小,如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村庄、城市社区,是一种持久的共同生活模式。这种人类群体中的成员服从权威,关系比较亲密,是具有共性的社会群体,共同居住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如国家、村庄、城镇或单元社区。以人为主体的共同体概念起源于“排他性的生物学物种”并演化到“族群的人类”层面,其过程是“自然界共同体——国际社会共同体——国家共同体——家庭共同体等共同体形式”[9],其理念自低而高发展,体现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即这一理念是基于世界各民族利益相融相依、风雨同舟的客观事实而产生的。
古希腊共同体思想的言说只是萌芽,城邦共同体是“善”的共同体。柏拉图主张实行消灭家庭及私有财产的共产制度,并认为“妇女儿童的公有”是“最大的善”[10]。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civitates societas)[11]思想强调,市民社会(Koinonia Politike,Political Society)所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又称“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12]。阿奎那在《论法的本质》一书中认为,“因为国(公民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是完善共同体(perfecta enim communitas civitas est)”,所以拉丁字典把civitates societas和perfecta societas解释为“城邦共同体”和“完美共同体”,德文翻译为denn die vollkommene Gemeinschaft ist das bürgerliche Gemeinwesen,法文翻译为la société parfaitec’est lacité,英文翻译为since the state is a perfect community,台湾学者刘俊余对应的汉译是 “完整的团体即是国家”,马清槐的汉译本是“完整的社会就是城市”[13]。以上这些学说无不围绕着宗教和神,这是维护神权的信仰共同体思想。
欧洲著名哲学家之一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提出:“现代共同体思想所缘起的对过去业已消失的共同体生活的缅怀思绪伴随着西方的历史,它激励着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一系列的思想家。”[14]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共同体思想有过论述,他们的文明理论都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共同体,从人性出发寻求建构一种尊重人性、符合人性的政治共同体,但都停留在思想萌芽状态。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和“无人有意为恶”,认为城邦应该是一种为了某种善的目的而存在的,包括全体公民的道德共同体。这也是柏拉图的世界共同体思想渊源,即他在《理想国》提出的:“由于需要许多物资,我们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彼此的伙伴和助手,从这个聚落开始,我们把它叫作城邦”[15]。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共同体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以幸福、智慧和德性为基本范畴,以共同体城邦为前提的完整的幸福主义德性伦理学,认为“城邦的团结就类似于友爱,他们欲加强之;纷争就相当于敌人,他们欲消除之”[16]。城邦兼具生活的共同体、政治的共同体和德性共同体的特征,可见,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语境中的城邦(政治学的语源polis就与之有关)是最高的共同体,但是他们还缺乏“世界”的视野。
霍布斯、孟德斯鸠及卢梭等的“社会契约论”蕴含了丰富的共同体思想,构成了近代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霍布斯认为,公民是理性的存在者,必须通过订立契约,放弃自己的某些权利,建立一个牢固的政治共同体。他提出:“由群聚的人同意授予主权的某一个或某些人的一切权利和职能都是由于像这样按约建立国家而得来的。”[17]孟德斯鸠认为,所谓好的共同体,必须是基于法的精神构建的共和制。卢梭的“共同体”则是通过“公共意志”构建起来的。他认为只有依据社会契约论构建的政治共同体,社会成员才能获得自由与平等。黑格尔推崇自由、理性共同体,主张“能够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到人自身自由和理性本质的全部表现、外在客观存在及其实践活动所创造的道德、政治和法律的伦理世界”[18]。黑格尔认为:“自由恰恰是通过对个人主观冲动的限制而实现的,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19]换言之,国家是绝对精神遵循严格理性安排而生成的自由的共同体,人只有成为共同体(即国家)的成员,才具有了客观性。因此,黑格尔称国家为“伦理共同体”。赫斯认为,自由与平等、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统一“就是自由共同体”[20]。这种个体化的类的真正生活,就是由类的真理和统一走向不同个体的自由现实,又从这种个体的自由现实返回到本质即类的不同表现的统一或社会生活产物的过渡。费尔巴哈指出:“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21]也就是说,共同体使“人之为人”,将爱、友谊和情感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通过这种联系结成的共同体是一种“爱的共同体”。
(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超越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视角考察人类社会,而康德的伦理共同体则以道德法则作为基础,伦理共同体最后归于宗教的色彩,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则直接体现自由人联合体,其发展脉络包括自“自然共同体”到“虚幻的共同体”乃至“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人剥削人的客观事实后揭示了“虚幻的共同体”实质,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在论及共同体时使用了Gemeinschaft,Gemeinde,Gemeinwesen和Gemeindewesen等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Gemeinschaft指“由市场和法理建立起来的关系”,即马克思所称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市民社会”(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而将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和之后的共同体称为“Gemeinwesen”或“Gemeinechaft”[22],认为共同体概念并非指有血缘之人群的集合。马克思的“政治共同体”迥异于城邦共同体,认为共同体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人的利益的相关性,剥削阶级国家称为“虚幻的共同体”,“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23]。可见,“共同体”的内涵由抽象变为具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性转变。赫斯在《人类的圣史》中指出,人类未来社会“是个人自由与社会平等的统一”。[24]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提出超越抽象人性观和德性观的共同体思想,是因为他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立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继承“城邦共同体”,融合“世界市场”“普遍交往”“世界性历史”等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实现共同体思想的飞跃。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25]马克思还深刻分析了异化劳动,指出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以普遍人权、政治自由等为幌子,“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6],深刻阐述共同体并非国家之类的“虚假共同体”,而是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超越了“自然共同体”和“虚幻共同体”,对原始社会、族群、家庭、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资本、共产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个人社会关系全面性等概念的论述无不彰显了 “共同体”概念的含义。《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及“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科学地勾画了共产主义的蓝图,明确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和举措及社会的经济特征,所以,自由人联合体才是人构成的世界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7],Association和德文的association(联合、联合会)皆来源于法文的association(联合、联合会),成仿吾、徐冰译成“集体社会”,陈望道译成“协同社会”,博古译成“团体”,华岗借用了陈望道的“协同社会”译法,台湾的唐诺译本译为“联合体”,还有其他译本的译法(表1)。不同的译文反映了译者不同的角色定位和认知模式,但大多译出了“协同”“大同”和“联合”的思想。

表1 《共产党宣言》的association汉译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逻辑
放眼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发展的思想引领,其核心是凝练、概括全人类共同的价值,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契合各国人民期待,为人类文明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依归
人类发展史产生了原始共同体、以婚姻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共同体、古代出于政治斗争需要的政治共同体、到中世纪的基于宗教信仰的信徒共同体、近代异化的市民共同体、民族共同体、阶级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乃至现代国家共同体、国际共同体和全球共同体等各种形态的共同体。社会的发展有其共同的逻辑性,所谓“逻辑”(logic)源于古希腊语logike(语法形式)后来引申为“事物变化的准则、本质和规律”(nature and law)。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逻辑),即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全部政权,消灭私有制,夺得民主,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经济基础以及“真正的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按照这个构想,认为落后的东方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28]。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二)《共产党宣言》科学真理的提炼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曾指出:“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29],也就是把资本家的资本变成社会主义财富并扩大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明确了发展生产力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先决条件,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目标实现的首要条件。《共产党宣言》科学预见资本的全球扩张推动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下从事“异化”劳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0],只有通过“两个决裂”才能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人的解放”,但是必须以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及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平等为条件。可见,脱离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及生产力水平来讲利益是空洞的,更谈不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长远目标的实现,无产阶级只有“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并“争得民主”,才能实现人类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思维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飞跃。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事业最忠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吸收借鉴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客观把握了各国人民相互依存、各国文明呈多元共生的客观现实,符合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科学规律,符合全人类共同的核心利益。
(三)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大变局与必然趋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全球性意识。从卢梭的“契约共同体”所主张的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相互签订契约,到黑格尔的“伦理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屋建瓴地洞察世界生产、经济和交换的普遍规律,预测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2]。世界市场的构建和发展必然导致国家、民族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全面深度融合的全球化趋势。欧盟、北美、非洲、东盟等区域性组织和共同体组织无不闪烁着人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助互利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广泛的共性。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思考和解决的是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福祉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丰富并发展了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展现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特有的理论品格和张力,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和而不同的价值共同体、共建共享的安全共同体、同舟共济的行动联合体。在中国方案中,具体表现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金砖+”的合作模式,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威胁的法宝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应对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因素的法宝。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多次论述了gemeinde,gemeinschaft和gemeinwesen,这三个词都含有“共同体”的意思,gemeinschaft和gemeinwesen相当于英文的common,由gemeinde派生出来,gemeinschaft则侧重于“本源共同体”和未来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gemeinwesen后来发展成“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马克思论述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冒充的共同体)”是 “非政治的联合形式”[33]。所谓“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指古代生产力低下而形成的抱团取暖式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依仗群体力量应对大自然恶劣的环境所带来的威胁,是一个“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34]。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35]。除了生态环境恶化威胁到地球家园外,国家间的战争冲突也使得战区国家的人民流连失所,人类命运共同体凝练和概括全人类互利互助、互通有无、和平发展的基本价值共识,顺应世界和时代发展潮流,契合各国人民期待,为人类应对自然和社会灾害,为世界文明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享发展理念继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马克思指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36]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只是有悖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虚幻共同体”,所以号召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彻底改变腐朽和剥削的资本主义旧世界,只有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状态的“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涵的政治观倡导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安全共同体倡导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经济共同体倡导开放创新;文明共同体倡导包容互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生态共同体倡导尊崇自然、绿色发展。这些共同体是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为宗旨而结成的集体,目的是实现共同价值,采取联合行动,维护全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真正体现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成果,是对《共产党宣言》的创新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闪烁着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光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水涨荷花高” “一棵树挡不住寒风”;“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命运与共、唇齿相依”;“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等朴素却深邃的话语反映了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命运相连的光辉思想,充分表明世界经济要走出由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垄断的困境,让全世界人类的大家庭成为无法割裂的整体。
五、结论
英语、法语、德语的community,association都拥有共同的拉丁语词源,从词源视角分析发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association)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community在语义上有共性,association从生态学概念发展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的community概念,欧洲各家学说都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共产党宣言》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的异化劳动,指出 “虚幻共同体”的实质,在《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的使命是争得民主,才能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就是由每一个自由人所组成的共同集体,超越了“自然共同体”和“虚幻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在翻译association时都译出了“共同”“协同”的含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与发展《共产党宣言》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同时,科学性和创造性地提出了谋求人类共同福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推向时代前沿的理论自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思想内涵,理顺和挖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各国文明的同质性,用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解决当今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在经济发展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伟大理论构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