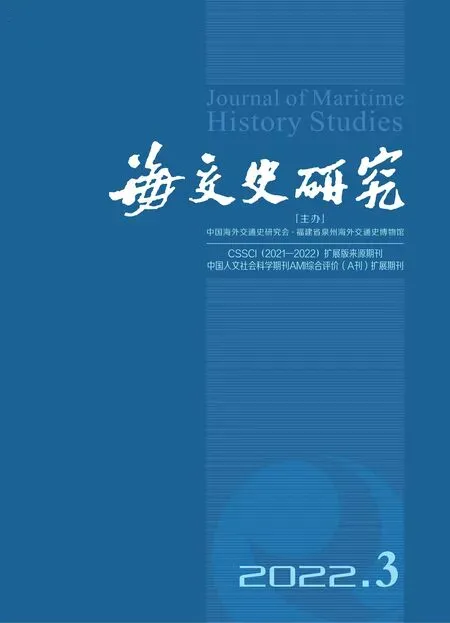明末清初民间海外贸易航路的发展变迁*
聂德宁 张元
引言
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历史久远,尤其是明初郑和七下西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海岸,更是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彰显出中国古代航海科技曾一度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因此相关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向达先生就曾对郑和下西洋时所用的海图针经编绘而成的《郑和航海图》,以及明末清初舟师所用的远洋航海针簿《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进行整理和校注(1)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有关航海交通航路的研究依然大多侧重于航海图籍的整理和研究,诸如:章巽《古航海图考释》(2)章巽:《古航海图考释》,北京:海洋出版社,1981年。、陈佳荣和朱鉴秋编著《渡海方程辑注》(3)陈佳荣、朱鉴秋编著:《渡海方程辑注》,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和《中国历代海路针经》(4)陈佳荣、朱鉴秋主编:《中国历代海路针经》,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6年。、刘义杰《〈顺风相送〉研究》(5)刘义杰:《〈顺风相送〉研究》,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值得一提的是,自从2011年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首次公开示出其所庋藏的《雪尔登中国地图》(6)《雪尔登中国地图》(The Selden Map of China),中国学界称之为“明中叶彩绘航海图”“明代东西洋航海图”或“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交通图”等,Bodleian Library, MS.Selden supra 105,http://seldenmap.bodleian.ox.ac.uk/,2022年6月19日获取。以来,引发了中国海外交通史和航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和探讨,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7)中国学界对这幅明代古航海图的论述甚多,主要有:钱江:《一幅新近发现的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图》,载《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7页;陈佳荣:《〈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图〉编绘时间、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析略》,载《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52—66页;郭育生、刘义杰:《〈东西洋航海图〉成图的时间初探》,载《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67—81页;龚缨晏:《国外新近发现的一幅明代航海图》,载《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56—160页;孙光圻、苏作靖:《中国古代航海总图首例——牛津大学藏〈雪尔登中国地图〉研究之一》,载《中国航海》2012年第1期,第84—88页;林梅村:《〈郑芝龙航海图〉考——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图〉名实辩》,载《文物》2013年第9期,第64—82页。,充分显示出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力和水平。本文则拟从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视角考察明末清初海外贸易航路的发展变迁,并从中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明代后期福建海澄月港的东西洋贸易航路
自15世纪初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之后,由于明朝政府厉行海禁政策,只允许海外诸国朝贡人船前来中国进行朝贡贸易,而不允许本国之人出洋贸易,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商出洋贸易被视为违禁非法活动而倍受压制和打击。直到明穆宗隆庆皇帝即位后,鉴于嘉靖“倭患”的惨痛教训,于隆庆元年(1567)在福建漳州设立海澄县,并有限度地开放海禁,允许商人告给商引,“准贩东西二洋。盖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交阯、占城、暹罗诸国,皆我羁縻外臣,无侵叛。而特严禁贩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例。”(8)[明]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132页。起初发舶地在诏安之梅岭,后因盗贼梗阻,改道海澄,由此开启了明代后期福建漳州海澄月港的“东西洋贸易”时代。
根据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的记载,明季于海澄开港之后,海商从海澄月港出洋贸易的航路主要有两条:一为“东洋航路”;二为“西洋航路”。无论是东洋抑或西洋贸易,启程地均为海澄月港。前往东洋、西洋贸易的商船从海澄月港启航,一潮至圭屿(鸡屿),半潮抵中左所(厦门岛)之曾家澳(现名曾厝垵),于此接受明朝驻防官兵的盘查检验之后,“候风开驾,二更船至担门(大担岛与二担岛之间),东西洋出担门分路矣。”(9)[明]张燮:《东西洋考》卷9,《舟师考·内港水程》,第171页。此段航程为在厦门湾内之内港水程,有崖岸可寻、村落可志、驿程可计,趁潮出入,习以为常。而大担、二担以外则为浩瀚大海,连通东西二洋,须恃指南针为导引,故分别有“西洋针路”“东洋针路”之称。

在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初编成的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中,亦记载了若干条以镇海卫之南太武山下的浯屿港(14)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244页中有谓:“本书《相送》与《正法》所提到之浯屿,仍指金门岛而言。”然则在《顺风相送》“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中则明载:“太武山内浯屿,係漳州港外。”(第32页) 对此,刘义杰先生指出:“大凡明清两代形成的针路簿,太武山均指南太武山,尤其明中叶开海后,山下不远处的浯屿岛驰名中外,针路簿中往往将浯屿与太武并称。”参见刘义杰:《南海海道再探》,载《南海学刊》2020年第1期,第34页。作为启程和返回港的西洋针路,计有:(1)福建“往柬埔寨针路”及“回针”;(2)“浯屿往大泥吉兰丹”及“大泥回针”;(3)“太武往彭坊针路”及“回针”;(4)“福建往爪哇针路”及“回针”;(5)“浯屿往杜蛮饶潼”及“回针”;(6)“浯屿取诸葛担篮”及“回针”;(7)“浯屿往荖维”。(15)《海道针经(甲)顺风相送》,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50、53—55、57—59、70、72—73页。相对于《东西洋考·舟师考》中有关“西洋针路”的记载,《顺风相送》所载西洋航路的诸条航线,不仅大多包含了去程和回程两个部分,而且还有前往婆罗洲西岸诸葛担篮(Sukadana)和荖维(Laut)港口的两条航线。
海澄月港的东洋贸易航路,起自镇海卫太武山,终至文莱国(Brunei),即所谓“文莱国即婆罗国,此东洋最尽头,西洋所自起处也,故以婆罗终焉。”(16)[明]张燮:《东西洋考》卷9,《舟师考·东洋针路》,第184页。据《东西洋考·舟师考》“东洋针路”的记载,具体的贸易航线大致有8条:(1)从太武山(厦门东南)经澎湖、虎头山(台湾高雄)、沙马头澳(台湾最南端之猫鼻角)、笔架山(Calayan,巴布延群岛之加拉鄢岛)、大港(Aparri,吕宋岛最北部之阿帕里港)等地至密雁(Vigan);(2)从密雁经由玳瑁港(Lingayan)等地至吕宋(Luzon)、猫里务(Burias);(3)从吕宋至磨老央(Balayan);(4)从吕宋至以宁(Ilin,民都洛南面的伊林岛);(5)从以宁经汉泽山(班乃岛西南之Antique)、呐哔啴(Dapitan,棉兰老岛北部)至沙瑶(Sayao);(6)从汉泽山经交溢(Kawit,棉兰老三宝颜附近)、魍根礁老(Maguindanao,马京达瑙)、绍山(Sarengani,棉兰老岛南部萨兰加尼岛)等地至美洛居(Maluku,马鲁古群岛);(7)从交溢经由犀角屿(Sangbay,巴西兰岛之桑格贝岛)至苏禄国(Sulu);(8)从吕蓬(Lubang,马尼拉湾外的卢邦岛)经巴荖圆(Palawan)、圣山(Banggi,婆罗洲沙巴北部之邦吉岛)等地至文莱国(Brunei)(17)[明]张燮:《东西洋考》卷9,《舟师考·东洋针路》,第182—184页。。
此外,在《顺风相送》中亦记载了若干条从太武浯屿开船前往吕宋以至文莱等地的东洋往返航线,计有:(1)“太武往吕宋”及“回针”;(2)“吕宋往文莱”及“文莱回吕宋”;(3)“浯屿往麻里吕”及“回针”。(18)《海道针经(甲)顺风相送》,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88—90、93—94页。在《顺风相送》所记载的第1和第2条东洋往返航线中,启航地均为太武或浯屿,中转地为吕宋,目的地为文莱,这与《东西洋考·舟师考》所载的东洋贸易航路大体一致。其中,吕宋是海澄月港东洋贸易中首要的贸易港口和中转港口。在明万历十七年(1589)福建巡抚周寀奏议中,将海澄月港的海外贸易商船每年限定为88艘,东西洋各限44艘,而东洋吕宋一国因水路较近,定为16艘,其余各国限二、三艘。(19)《明神宗实录》卷210,万历十七年四月丙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3939页。至于第3条“浯屿往麻里吕”及“回针”往返航线中的“麻里吕”,在《诸蕃志·三屿》中作“蒲哩噜”,《岛夷志略》作“麻里噜”,皆指马尼拉(Manila)。实际上,Manila一名乃西班牙人占据以前之旧名,源于他加禄语Maynila,意为“树林之城”。(20)[南宋]赵汝适原著,[德]夏德(F. Hirth)、[美]柔克义(W. Rockhill)合注,韩振华翻译并补注:《诸蕃志注补》,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0年,第278—279页;[元]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0页。
在海澄月港的东西洋贸易航路中,中国商船出洋兴贩的对象“西洋则交趾、占城、暹罗、下港、加留吧、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亚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辰;东洋则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单、美洛居、文莱、鸡笼、淡水。”(21)[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2,《赤嵌笔谈·商贩》,《台湾文献丛刊》第4册,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第45页。上述地方除鸡笼、淡水之外,均位于东南亚。因此,海澄月港的东西洋贸易实际上可谓是东南亚贸易。当时出洋贸易的中国商船贩至东西洋各地的中国货物大致相同,但贩回的货物则有所不同。西洋暹罗、柬埔寨诸国的物产有苏木、胡椒、犀角、象牙诸货,是皆中国所需;而东洋的吕宋,当时已为佛郎机(西班牙)人所据,地无他产,悉以墨西哥银钱易货。中国商船“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得其银钱。”大体而言,海外诸国对于中国的丝绸尤其是生丝等货物的需求甚为迫切,“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22)《崇正十二年三月给事中傅元初请开洋禁疏》,参见[清]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第37—38页。
明代后期海澄月港东西洋贸易及东西二洋航路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明朝政府海洋政策的变化所致,另一方面也和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殖民势力东渐及其与中国政府间的冲突与交往息息相关。
首先,自明初以来明朝政府实行的是“惟不通商,而止通贡”的朝贡贸易政策,只允许海外各国以朝贡的名义随带货物前来明朝,由官方给价收买,且给予贡使大量的回赐物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薄来厚往”的不等价交换的朝贡贸易不可避免地日趋衰落,但明朝政府对于民间商人的出洋贸易活动依然严厉禁止,从而使得民间海外贸易不得不走上了一条从海外“导夷入贡”混以图利,进而“纠番诱倭”在东南沿海地区私相交易的曲折发展道路。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起,明朝政府对私市贸易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力镇压,结果引发海寇商人的激烈抗争,“联倭肆掠”的海寇活动一直持续到隆庆、万历之交,延绵二十余年。有鉴于此,明朝福建巡抚涂泽民在发兵征剿闽粤海寇的同时,于隆庆初年(1567—1572)奏疏朝廷,请开海禁,易私贩为公贩,“议止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磺铜铁违禁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23)[明]许孚远:《疏通海禁疏》,参见[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40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333页。正是东南沿海地区接连不断的海寇商人活动,最终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有限度地开放对民间“泛洋通商”的禁制,在海澄月港准许海商“告给文引”、纳饷出洋兴贩,从而为隆庆、万历以后民间海外贸易的生存和发展开辟了一条“合法”的途径。故时人有云:“自纳饷过洋之利开,豪狡之徒咸趋利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24)[明]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利·论海市》,明万历乙未(1595)刊本,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7册。
其次,自16世纪初以来,陆续东来的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荷兰等西方殖民者最初均以打开中国门户直接与明朝进行贸易为目标。1553年(嘉靖卅二年),葡萄牙人以曝晒浸水货物为由窃据澳门,进而以此为据点独享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之利。后来的西班牙人、荷兰人也曾效法葡萄牙人窃取澳门的伎俩,试图在中国沿海地区获取一个能够与明朝进行直接贸易的据点。1577年(万历五年),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曾派遣船队驶抵厦门、漳州等地,企图在福建沿海寻觅一处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据点,结果为明朝所拒。(25)[美]菲律·乔治著:《西班牙与漳州初期之通商》,薛澄清译,载《南洋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第45—46页。西班牙人转而在吕宋极力招徕中国商船前来马尼拉贸易,从中获取所需的各种货物。马尼拉的繁荣及其与墨西哥之间大帆船贸易的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商船带来的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尤其是生丝和丝织品。荷兰人于1595年首航驶抵爪哇之万丹,开始跻身东方海上贸易的行列。为了能够与先期到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相抗衡,1602年5月在荷兰国务总会的主导下,十几家从事东方贸易的荷兰小公司合并组成“联合东印度公司”,并被赋予征兵、造币、立法、任免官吏、建立商馆等特权。(26)Femme S. Gaastr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Expansion and Decline, Zutphen: Walburg Pers, 2003, p.20.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曾多次试图谋取澳门取代葡萄牙人,进而独占对华直接通商贸易之利,但由于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在欧洲已合二为一,在对华贸易上业已取得一定的优势,故而合力排斥荷兰人,致使东印度公司的谋划均以失败而告终。在谋求对华直接贸易的努力屡遭挫折之后,荷兰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把注意力集中到当时出洋兴贩的中国商船上来。早在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就下达指示要求务必想尽办法来增进对华贸易,首要的目的是取得生丝。“因为生丝利润优厚,大宗贩运能够为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和繁荣。如果我们的船只无法直接同中国进行贸易,那么公司驻各地的商馆就必须前往中国商船经常往来的地区(如北大年等地)去购买生丝。”(27)Kristof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Kopenhagen/Den Haag: Danish Science Press und Martinus Nijhoff, 1958, p.112.1619年5月荷兰人夺取雅加达后,将其改名为巴达维亚(吧城)并作为东方殖民地的大本营。之后,荷兰人更是千方百计招徕中国商船,甚至不择手段迫使中国商船前来贸易,以维持巴达维亚贸易的繁荣。1619年12月28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三任总督燕·彼得逊·昆(Jan Pieterszoon Coen)指示前往占碑(Jambi)的公司船长:“你们此行任务不只是装载胡椒,还要留意从中国来的商船,要会同当地公司的商馆制定一个完善的计划,使所有的中国商船都驶来吧城,以便繁荣吧城的贸易。”(28)Colenbrandar H. T., Jan Pietersz Coen, Bescheiden omtrent zijn verblijf in Indi⊇, Vol. I,’s- 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19-1923, p.632.到1625年,驶往巴达维亚的中国商船已达到甚至超过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有回程的总吨位。(29)J. 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Hague: W. van Hoeve Publishers LTD, 1967, p.198.因此,得益于这一时期中国商船东西洋贸易活动的发展,无论是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抑或是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均可从与中国商船的间接贸易中获取其所需的中国货物。而对于明朝政府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借此使欧洲殖民者远离国门,防止其假借通商之名妨害东南沿海的安全。
最后,明代后期起自漳州之海澄月港而终于婆罗洲之文莱的东洋贸易航路,实际上来源于宋代开辟的一条从泉州经由麻逸(今菲律宾民多洛岛)前往渤泥(文莱)的航路。明初是中国与文莱政治经济交往最为密切和频繁的时期,双方使节往来皆以福建泉州为起讫港口。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朱元璋诏命浡泥(文莱)国“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30)《明史》卷325,《外国六·浡泥》,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12页。。文莱在与明朝建立和保持密切政治经济关系的同时,也与当时东南亚的第一个穆斯林苏丹国——马六甲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关系。文莱人经由这一经贸联系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于15世纪建立了文莱苏丹国,成为在婆罗洲的第一个穆斯林国家,由此与东南亚各地的伊斯兰世界建立起了广泛联系。1511年葡萄牙人侵占马六甲之后,导致马六甲的穆斯林商人纷纷远走文莱,并把大本营迁至此地,使文莱迅速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中心,同时也使文莱成为婆罗洲地区新兴的穆斯林商港,成为周边地区的贸易集散地。(31)[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1册,贺圣达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6页。到了明代后期海澄月港开禁之后,文莱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商船东洋贸易航路的终点。地处“东洋尽处”的文莱是婆罗洲地区热带丛林动植物产品以及其他热带海产品的主要出口港,主要物产有:真珠、玳瑁、玛瑙、车渠、片脑、黄蜡、萪藤等。其中,片脑是为梅花片脑之简称,以其成片状似梅花故也,乃龙脑香之上品,中医称之为冰片,具有开窍醒神、清热止痛的功效。“主内外障眼三虫,疗五痔,明目镇心秘精。”(32)[五代]李珣原著,尚志钧辑校:《海药本草》(辑校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55—57页。自唐宋以来,龙脑香就已为中医五官科常用必备之药,且价格昂贵。故明人有云:片脑以勃泥国出者为佳,“有大如指,厚如二青钱者,香味清烈,莹洁可爱,谓之梅花片,鬻至中国,擅翔价焉。”(33)[明]黄衷:《海语》卷中,《物产·片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第28—29页。此外,文莱港还是当时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据记载,1578年西班牙人进犯文莱时,在文莱港遇见大量来自中国﹑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北大年﹑彭亨﹑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鲁古和棉兰老群岛的船只和商人。(34)“July 29, 1578: Letter from Francisco de Sande to Felipe II”, in Blair, E. H. and Robertson, J. A. The Philippines Islands, vols. 4, Cleveland, 1903-1909, p.131.文莱港所具有的国际贸易商港的地位,无疑也是吸引当时中国商船将其作为东洋贸易航路终点一个重要因素。
二、明末清初民间海外贸易航路的变化
明末清初是中国海外贸易航路变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变化发展可以从新近发现的《雪尔登中国地图》以及清初的《指南正法》等相关航海图籍中初见端倪并得到验证。
根据专家考证,庋藏于英国牛津大学的《雪尔登中国地图》编绘时间,一说约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明代万历年间。(35)钱江:《一幅新近发现的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图》,载《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6页;郭育生、刘义杰:《〈东西洋航海图〉成图时间初探》,载《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81页。另一说大约在1624年。(36)陈佳荣:《〈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图〉编绘时间、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析略》,载《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58页。从该图所绘制的航海路线显示,当时由漳州、泉州为启航地的东西洋航路大体分别如下:
东洋航路:(1)漳泉―五岛(Goto-retto)―笼仔沙机(Nagasaki,长崎);(2)漳泉―琉球(Ryukyu);(3)琉球―兵库(Hyogo);(4)漳泉―吕宋(马尼拉);(5)广州―吕宋;(6)吕宋―文莱;(7)吕宋―苏禄;(8)吕宋―马军礁老(Maguindanao,马京达瑙);(9)吕宋―万老高(Maluku,马鲁古)。共计9条航线。
西洋航路:(1)漳泉―七洲(海南岛东北之七洲列岛)―东京(交趾);(2)漳泉―七洲―占城―柬埔寨―暹罗;(3)漳泉―七洲―占城―大泥―彭坊(彭亨);(4)占城―乌丁礁林(柔佛)―麻六甲―吉礁(吉打)―苏文达(亚齐);(5)占城―乌丁礁林―旧港(巨港)―顺塔(Sunda)―咬□吧(Kelapa);(6)顺塔―咬□吧―吧哪(巴哪大山,保老岸山(37)保老岸山,“山与吉里问相对,俗讹呼巴哪大山。”参见《东西洋考》卷9,《舟师考·西洋针路》,第180页。)―猪蛮(Tuban)―饶洞―磨厘(Bali,巴厘)―里吗(松巴哇东北部之Bima)―池汶(帝汶);(7)占城―玳瑁洲―失力大山(Serasan岛)―勿里洞(Billiton)―吧哪(保老山)―池汶;(8)占城―乌丁礁林―失力大山(Serasan岛)―马辰(Bandjarmasin)―傍伽虱(Makassar,望加锡)―唵汶(Ambon,安汶)―援丹(Banda,班达);(9)马六甲―古里(Calicut);(10)古里―忽鲁谟斯(Hormoz);(11)古里―佐法儿(Dhufar);(12)古里―阿丹(Aden)。共计有12条航线。
在《雪尔登中国地图》所绘制和显示的9条东洋航路支线中,不仅包含了明代后期海澄月港东洋航路中前往菲律宾群岛以及文莱、马鲁古群岛的大多数航线,而且还增加了广州―吕宋航线,尤其是漳泉―日本五岛及长崎、漳泉―琉球,以及琉球―日本兵库的航线。东洋航路贸易航线增多,这一变化显然与明末通倭私贩活动的兴盛息息相关。
尽管明代后期海澄月港政府官方核准的东西洋贸易并不包括日本诸岛,然而实际上民间海商的通倭贸易不仅屡禁不止,反而愈加兴盛。一则是因为日本诸岛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衣带水,商船从闽浙沿海前往日本诸岛,“顺风旬月至”。二则是由于当时日本诸岛,“彼中百货取之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瓷,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辗转灌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38)[明]徐光启:《海防迂说》,参见[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491,第5442—5443页。出洋贸易商人最初的违禁通倭私贩活动,只是假道海外他国诸如交趾、暹罗、吕宋等地,与前来当地贸易的日本商人进行交易;后来则是假借沿海渔樵贩籴文引,“称往福宁卸载,北港捕鱼,及贩鸡笼淡水者,往往私装铅硝等货,潜去倭国,徂秋及冬,或来春方回”;亦有“藉言潮惠广高等处籴买粮食,径从大洋入倭,无贩番之名,有通倭之实。”(39)[明]许孚远:《疏通海禁疏》,参见《明经世文编》卷400,第4334页。至于“托名进香,尽多私载,以普陀为寄寓,”(40)[明]王在晋:《越镌》卷21,《通番》,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00页。取道浙江舟山潜往日本贸易;或是“托引东番(台湾),输货日本,”(41)[明]黄承玄:《条陈海防事宜疏》,参见《明经世文编》卷479,第5271页。亦时常有之。甚至还有“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夤缘所在官司擅给票引,任意开洋,商桅巨舶,络绎倭国,”(42)《明神宗实录》卷476,万历三十八年十月丙戌,第8987页。以至于“洋船违禁以暹罗、占城、咬□吧为名,以日本为实者,丝宝盈衍而出,金钱捆载而归,”(43)[清]陈寿祺等纂:《福建通志》卷86,《海防·历代守御》,清同治十年重刊本,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第1734页。往来不绝于道。每年潜往日本诸岛私贩的船只,大多“从福海中开洋,不十日直抵倭之支岛,如履平地。一人得利,踵者相属,岁以夏出以冬归。”(44)[明]董应举:《崇相集》疏一,《严海禁疏》,明崇祯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8页。另据记载,到明万历四十年(1612),仅在福建一地的违禁通倭者,“合福兴漳泉,共数万计。”(45)《明神宗实录》卷498,万历四十年八月丁卯,第9389页。
在《雪尔登中国地图》所显示的12条西洋航路的航线中,前8条航线基本上保留了明代后期海澄月港的西洋航路中的绝大多数航线。至于后四条从马六甲经由古里驶往波斯湾及阿拉伯半岛南端亚丁(阿丹)的航线,在图中只有简要的文字说明而无具体的航线标识,表明随着郑和七下西洋的结束,尤其是葡萄牙人东来占据马六甲以后,已鲜有中国船只自马六甲取道印度南部前往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地区。(46)刘义杰:《〈顺风相送〉研究》,第263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雪尔登中国地图》西洋航路中第6条和第7条前往帝汶(Timor)的航线以及第8条前往安汶(Ambon)及班达(Banda)的航线,这三条航线实际上均为香料贸易航线。其中,帝汶岛以出产檀香而闻名,自宋元时就已成为中国商船采购檀香的目的地之一。据《岛夷志略》所载,古里地闷(Giri Timor)“居加罗之东北,山无异木,唯檀树为最盛。以银、铁、碗、西洋丝布,色绢之属为之贸易也。”(47)[元]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209页。到明代后期,帝汶岛更是成为海澄月港西洋航路东南方向航线上最为遥远的目的地。在《顺风相送》中也载有一条“万丹往池汶精妙针路”(48)《海道针经(甲)顺风相送》,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66页。。万丹(Bantam)又作顺塔、下港、新拖,位于爪哇岛西北岸。此条航线起自万丹终至小巽他群岛最东端的帝汶(Timor)岛。之所以称之为“精妙针路”,一是其确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在其他针路上均无物产的记述,唯有此条针路上不断注记产香之地,显见是一条以香料贸易为主的航线;二是该针路对航线上岛礁港湾的描述准确形象,可与《东西洋考·舟师考》“西洋针路”中从“保老山”到“池闷”的航线相互印证,互补不足。(49)刘义杰:《〈顺风相送〉研究》,第247—249页。而在《雪登中国地图》的西洋航路中不仅标注有两条前往帝汶的航线,而且还绘制了一条从加里曼丹岛(婆罗洲)南部的马辰一直延伸至苏拉威西的望加锡、马鲁古群岛的安汶以至班达群岛的航线。此条航线均不载于《东西洋考》和《顺风相送》之中,显然是自17世纪初以来新开辟的一条香料贸易航线,(50)据载,中国帆船首次直接从中国驶抵望加锡是在1613年。随着到访的中国商船日益增多,望加锡的贸易网络逐渐形成。到17世纪20年代,中国商人已成为该地的常客。参见Heather Sutherland, Seaways and Gatekeepers: Trade and State in the Eastern Archipelagos of Southeast Asia, c. 1600-c, 1906, Singapore: NUS press, 2021, p.41, p.196.其中望加锡,尤其是安汶、班达等地,为檀香、丁香和肉豆蔻的主要产地,有着香料岛之美称。
《指南正法》是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之乙种,成书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大约完成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另一说大约完成于清康熙末年即18世纪初期。(51)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序言》,第4页。《指南正法》所记载西洋针路(航线)大多为厦门及其附近之口岸,诸如大担、太武、浯屿等地为起点往返西洋各地的航线,以及宁波往东京(Tonkin,交趾)的针路。但在《指南正法》中已没有马六甲以西的航线针路的记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到18世纪前后,马六甲已成为中国商船西洋航路的一个终点。
相对于成书于明末的《顺风相送》侧重于记载西洋航路,清初的《指南正法》则更注重东洋航路的记载。除了有多条从厦门等地前往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以及文莱的航线之外,还有不少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前往日本、琉球的航线,诸如:(1)福州往琉球;(2)宁波往长崎;(3)温州往日本;(4)凤尾往长崎;(5)普陀往长崎;(6)沙埕往长崎;(7)尽山往长崎;(8)广东往长崎;(9)厦门往长崎。其中,属于福建的港口有福州、厦门、沙埕;属于浙江的港口有宁波、温州、普陀、尽山、凤尾。由此可知,到了明末,不仅明朝后期以来所实施的“通倭禁令”已荡然无存,而且从海澄月港一口出洋贸易的限制也已一再被突破。
《指南正法》所记载的从东南亚地区往来日本的航线计有:(1)双口(马尼拉)―长崎;(2)暹罗―日本(长崎);(3)广南(会安)―长崎;(4)咬□吧―长崎;(5)大泥(北大年)―长崎。无论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还是从东南亚各地前往日本的贸易航线,均以日本长崎为目的地。为此,《指南正法》中还有《长崎水涨时候》的专门记载,(52)《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124—125页。对长崎港每日潮汐涨落变化的时间做了准确的记录,作为商船进出长崎港的航行指南。由此可知,日本长崎在当时已成为中国商船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贸易对象之一。
不仅如此,《指南正法》还载有《暹罗往长崎日清》《咬□吧回长崎日清》《长崎往咬□吧日清》,以及《大泥回长崎日清》。此种《日清》类似于航海日志,据此从中可以推算出其各自往返于日本长崎港的航程时间。例如,《咬□吧回长崎日清》有载:“四月二十八日在澳内开船,……(六月)十四日方得进(长崎)港。”(53)《指南正法》,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182—184页。总计航程约为47天。《长崎往咬□吧日清》有载:“十一月初九日开舡,……(十二月)初十日……巡合板屿东入门,午至浅口住舡。”(54)《指南正法》,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184—186页。此段航程约为31天。《大泥回长崎日清》记载:“五月十六日西南风在浅尾开船,……(六月)十九日……下午入长崎可也。”(55)《指南正法》,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188—190页。此段航程约为34天。
除东西洋航路的记载之外,在《指南正法》中还记载了从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前往澎湖及台湾的多条航线,诸如:《乌坵往彭湖》《寮罗往彭湖》《湄洲往台湾》《祥之(芝)往彭湖》《崇武往彭湖》《南澳往茄荖湾(鹿儿门)》,以及从福建沿海前往菲律宾群岛等地的东洋航线中所历经的台湾(北港,安平港)、打狗(高雄)、沙马崎头(台湾南端貓鼻头)等船舶行经停泊的港口。此外,还有多条从台湾往日本,(56)《指南正法》,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133—136页。以及台湾往来咬□吧(巴城)的航线。(57)《指南正法》,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186—188页。这一方面充分体现出明末清初台湾海峡两岸往来之频繁,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时台湾已成为东西洋贸易航路中的重要一环。
《指南正法》虽然成书于清初,然其所载内容涵盖并跨越了明末清初,尤其是明清鼎革之际的17世纪中叶(1630—1660),这可以从书中频繁出现的“大明”“大清”,以及“思明”(58)思明即厦门。郑成功于(南明)永历九年(1655)三月,“改中左(厦门)为思明州”。参见[清]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2—113页。、“东都”(59)东都即台南之赤崁城(红毛城)。郑成功于(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五月,“改赤崁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参见《先王实录校注》,第253页。等名称进行印证。而这一时期主导和控制东南沿海地区海上贸易活动的正是郑氏海商集团。《指南正法》所记载的有关东洋航线的变化,出洋贸易口岸的增多,以及东南亚地区往来日本的多条航路的开辟,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当时郑氏集团海外贸易活动的内容与形式。
郑氏集团的创始人郑芝龙自明崇祯元年(1628)受抚于明朝以来,假借朝命东征西讨,镇压和兼并了其他海上势力,逐步控制了福建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居为大贾。”(60)[清]林时对:《荷牐丛谈》卷4,《郑芝龙父子祖孙三世据海岛》,《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8辑,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155—160页。其中,对日本的贸易以及与当时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的贸易,就是郑芝龙及郑氏集团海上贸易的重要方面。到郑成功时代(1647—1661),出于抗清复明养兵取饷的需要,郑成功继承并发展了明末以来郑氏海商集团的海外贸易活动。郑成功强盛时期,以厦门、金门为基地,“上踞舟山、下及南澳”,(61)[清]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卷7,《闽海遗兵》,《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5辑,第158页。从而据有闽浙粤沿海地区与清朝相抗衡,其属下的东西洋贸易商船也频繁地从其控制的东南沿海各地往来于海外各地从事贸易活动。(62)据清康熙七年(1668)降清的原郑氏部将史伟琦密报:“郑成功强横时期,原以仁义礼智信五字为号,建置海船。每一字号下,设有船十二只。”史伟琦“曾督船亲临日本、吕宋、交趾、暹罗、柬埔寨西洋诸国。”《候补都司佥事史伟琦密题台湾郑氏通洋情形并陈剿抚机宜事本》,参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1—83页。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其子郑经仍继续以台湾为基地从事海外贸易活动。郑氏的东西洋贸易商船所采用的航线通常有两条:其一是中国─日本的直接贸易航线,其二为中国─东南亚─日本的“三角贸易”航线。这两条主要贸易航线之所以均以日本长崎为终点,与这一时期东亚海上贸易格局的变化发展息息相关。
日本德川幕府于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开始实行锁国政策,在取缔朱印船贸易活动的同时,将对外贸易口岸限制在长崎一港,仅允许中国船与荷兰船入港。因此,日本锁国后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地货物的需求,除荷兰船提供外,主要依赖往来于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各地及日本长崎的中国商船。采购日本物产,“下贩吕宋、暹罗、交阯诸国”,(63)[清]徐鼐撰,王崇武校点:《小腆纪年附考》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74页。或是装载东南亚各地货物前往日本,以易日本银货,这种多边的海外贸易方式由当时拥有众多商船和雄厚资本的郑氏海商集团开创和掌控,并由此构建了连接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地的庞大贸易网络。
从以上《雪尔登中国地图》和《指南正法》中有关东西洋航路航线发展变化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明末清初中国海外贸易航路的一些新的变化特征:其一,东洋贸易航路的航线在原先的菲律宾、婆罗洲及马鲁古群岛的基础上,不仅在明末增加了漳泉至日本五岛、兵库,以及漳泉至琉球的三条航线,到了清初又加了九条从闽浙粤沿海前往日本及琉球的航线;其二,出洋贸易口岸从原先局限于海澄月港一隅,扩大到闽浙粤沿海诸地,突破了明朝后期海澄月港一口出洋兴贩的限制;其三,航线更加多样化,开辟了多条从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日本多边贸易的新航线;第四,自明末以来台湾已成为东西洋贸易航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清康熙开海后民间海外贸易航路的新发展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平定后,清廷“诏开海禁”,分别设粤、闽、浙、江四海关,以管理海外贸易和征收进出口关税,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沿海居民拥有的五百石以下的船只,均允许出海贸易,民间海外贸易因而重新焕发生机。“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浡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 。(64)[清]陈寿祺等纂:《福建通志》卷87,《海防·总论》,第1760页。中国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由此迅速发展,盛极一时。与此同时,海外贸易航路也因此得以进一步发展,即从明末清初的东西洋两大航路扩展到东洋、东南洋和南洋三大航路。
约成书于清雍正八年(1730)的《海国闻见录》系由陈伦炯根据其亲身经历及咨询海外客商撰写而成,书中对清初的东洋、东南洋和南洋三大航路载之甚详。据《海国闻见录》一书载,东洋航路的具体航线有三:(1)普陀─萨□马(萨摩)─长崎;(2)厦门─鸡笼山(台湾基隆)─萨□马─五岛─天堂─长崎;(3)福州─鸡笼山(台湾基隆)─琉球。(65)[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东洋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5—37页。其中,福州往琉球之航线自明代一直沿袭至清代。琉球国学者程顺则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所编著的《指南广义》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四条明朝册封使之封舟从福州、漳州前往琉球那霸港的往返航线,以及十条由明初闽人“三十六姓”所传往来于琉球与福建之间的针路。(66)[琉球]程顺则:《指南广义》,“针路条记”,清康熙四十七年“雪堂汇辑”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东南洋航路起自福建厦门,经澎湖─沙马崎(台湾南端貓鼻头)─宰牛坑(吕宋岛北端)抵达吕宋(马尼拉),而后再以吕宋为起点前往东南洋各地的航线计有:(1)吕宋─利仔犮(Legaspi)─甘马力(Cama Rine,合猫里,吕宋岛东南部);(2)吕宋─班爱(Panay,班乃);(3)吕宋─恶党(屋同,Oton);(4)吕宋─宿务(Cebu);(5)吕宋─猫务烟(Bohol,保和);(6)吕宋─网巾礁老(Mindanao,马京达瑙);(7)吕宋─万老高(Maluku,马鲁古);(8)吕宋─丁机宜(马鲁古群岛一带);(9)吕宋─苏禄(Sulu);(10)吕宋—文莱(Brunei)。(67)[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东南洋记》,第41—44页。
南洋航路以厦门为起点,大约计有10条航线:(1)厦门—七洲洋—交趾;(2)厦门—南澳—七洲洋—占笔罗山(Cham Pulau)—广南;(3)厦门—七洲洋—柬埔寨;(4)厦门—七洲洋—外罗山(呴唠哩)—玳瑁洲(越南平顺外海岛)—昆仑(Poulo Condore)—大小真屿(金瓯角外之奥比岛和假奥比岛)—笔架山(曼谷湾口西岸之三叠峰)—竹屿(位于湄南河口)—暹罗;(5)厦门—小真屿—斜仔(Chaiya)—六坤(Ligor)—宋脚(Songkhla)—大哖(Patani)—吉连丹(Kelantan)—丁噶呶(Terengganu)—彭亨(Pahang);(6)厦门—昆仑—茶盘(Tioman,马来半岛东岸外的潮满岛)—柔佛(Johore)—麻喇甲(Malacca);(7)厦门—昆仑—茶盘—万古屡山(Bengkulu,明古鲁)—噶喇吧(Kelapa,雅加达);(8)厦门—七洲洋—昆仑—茶盘—诸葛礁喇(Sukadana,婆罗洲西岸的苏加丹那);(9)厦门—噶喇巴—马辰—芒佳虱(Makassar,望加锡);(10)厦门—噶喇巴—池问(Timor)。(68)[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南洋记》,第48—55页。
在清初的东洋航路中,中国帆船对日本长崎的贸易在康熙开禁之初曾兴盛一时,每年前往日本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迅速增加,从康熙二十三年开禁之年(1684)的24艘,翌年(1685)增至85艘,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更增至102艘。(69)参见[日]林春胜、林信笃编,浦廉一解说《华夷变态》(上册)卷9,“甲子”,东京:财团法人东洋文库,1958年,第411—412页;卷10,“乙丑”,第445—448页;卷11,“丙寅”,第537—543页。与此同时,前往日本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启航地点也遍及中国沿海各地和东南亚各地。当时日本长崎方面将入港的中国商船分为“口船”“中奥船”和“奥船”三大类。“口船”指的是短程商船,来自距日本较近的中国沿海省份,诸如江苏的南京船,浙江的舟山船、普陀山船、宁波船、台州船、温州船,山东船亦属“口船”之列。“中奥船”指的是中程商船,有来自福建的福州船、泉州船、漳州船、东宁(台湾)船、沙埕船,以及广东的潮州船、广东(广州)船、高州船、海南船等。而所谓“奥船”指远程商船,均为来自东南亚各地的商船,诸如:东京(交趾)船、广南船、柬埔寨船、暹罗船、六崑船、宋居朥船、大泥船、万丹船、咬□吧船。(70)Yoneo Ishii(石井米雄),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Translation from the Tosen Fusetsu-gaki, 1674-1723, “Introduc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8, pp.2-3.实际上,这些来自东南亚各地前来日本长崎的商船并非其本国所遣,而是出自“唐土中华”的唐船。(71)[日]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卷3,“柬埔寨”条,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和刻本,第18a—18b页。它们大多先是从宁波、厦门、广东等地出发前往东南亚各地,然后在当地装满货物后驶往日本。中国各地的商船通常在年底至次年的正月时节南下,五月前后北上向日本进发。(72)[日]大庭修著:《明清的中国商船画卷——日本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藏〈唐船之图〉考证》,朱家骏译,载《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19页。
为了防止金、银、铜等贵重金属的大量外流,日本德川幕府从1688年开始限定前来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数量不得超过70艘。正德四年(康熙五十三年,1714)又颁布“正德新商法”,规定每年前来长崎的中国商船为30艘,贸易银额限定为6000贯,每艘约为191贯。幕府每年向中国商船颁发信牌,凭信牌互市,严禁私下贸易。(73)[日]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49—650页。此举导致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逐渐减少,纷纷转赴南洋各地。尤其是雍正五年(1727)清廷正式解除“南洋禁航令”后,中国“洋船贸易往东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74)“广东道监察御史李清芳为陈南洋贸易不宜尽禁缘由事奏折”(乾隆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年间议禁南洋贸易案史料》,载《历史档案》2002年第2期,第26页。
当时福建的厦门港、广东潮州的樟林港是中国商船前往东南亚贸易的主要出洋港口,贸易范围遍及东南亚各地,计有“噶喇吧、三宝垄、实力、马辰、仔、暹罗、柔佛、六坤、宋居朥、丁家卢、宿务、苏禄、东浦(柬埔寨)、安南、吕宋诸国。”(75)[清]周凯、凌翰等修纂:《厦门志》卷5,《船政略·洋船》,道光十九年刊本,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138页。到18世纪初期以后,中国商船的东南洋航路及南洋航路的贸易活动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其中,吕宋(马尼拉)和噶喇吧(吧城)分别成为清初中国商船东南洋航路及南洋航路上的两大贸易港口。
吕宋国原为菲律宾古国之一,位于吕宋岛的马尼拉湾一带。西班牙人自1565年占领马尼拉之后,于1571年将马尼拉作为其往返于菲律宾与美洲墨西哥南部阿卡普尔科(Acapulco)港之间“马尼拉大帆船”的启航地,从此以后,“大西洋货物尽转移至吕宋”(76)[明]何乔远:《闽书》卷146,《岛夷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62页。。而明朝自隆庆年间(1567—1572)于福建海澄开港以来,“闽人以其地富饶,商贩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77)[清]高宗敕:《清朝文献通考》卷297,《四裔考五·吕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464页。迄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以后,福建人前往吕宋“耕种营运者甚盛。年输丁票银五、六金……听凭贸易。东南洋诸番,惟吕宋最盛。因大西洋干丝腊是班呀(Castila Spain的音译,西班牙)番舶运银到此交易,丝绸、布帛、百货尽消,岛番土产云集。”(78)[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东南洋记》,第42页。因此,直至清初中国商船与马尼拉的贸易依然繁盛。1684—1700年间,驶抵马尼拉港的中国商船共计256艘,年均16艘;1701—1716年间,驶抵马尼拉港的中国商船总计达274艘,年均17艘;其中,1709年驶抵马尼拉港的中国商船多达43艘。(79)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XVIe, XVIIe, XVIIIe, siécles),Paris: S.E.V.P.E.N., 1960, pp.169-180.
噶喇吧原为爪哇万丹国属地,原名巽他·加拉巴(Sunda Kelapa),中国史籍称之为“噶喇吧”(亦作咬□吧,又称吧城)。荷兰人在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占领噶喇吧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大本营后,改其名为巴达维亚,并着力将之打造成为国际性贸易港口。由于巴达维亚地处连接太平洋、印度洋与欧洲之间贸易往来之交通枢纽,不论是欧洲各国船只,还是印度、中国、日本、安南、马六甲、交趾、苏拉威西之船只,无不云集于巴达维亚。所以,自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开放之后,巴达维亚继续成为中国商船南洋贸易中最主要的港口之一。从厦门岛扬帆启程前往吧城,“计水程二百八十更,每更五十里,约一万四千里可到。”尽管路途遥远,但中国商船却络绎不绝,年复一年,“鼓棹扬帆而往者,皆闽广之人。”每年“于冬至后厦岛开棹,廿余日可达。吧城连衢设肆,夷民互市,贵贱交易,所谓利尽南海者也。”(80)[清]王大海:《海岛逸志》卷1,《西洋纪略·噶喇吧》,香港:学津书店,1992年,第1—4页。故时人有云:兴贩南洋各地“惟噶喇吧一国为最远,亦惟噶喇吧贸易为最盛。”(81)“福建水师提督王郡为报访查噶喇吧国杀戮汉商事奏折”(乾隆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年间议禁南洋贸易案史料》,载《历史档案》2002年第2期,第23页。据估计,1731年至1740年间驶抵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年均达17艘之多。(82)Leonard Blussé,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1986, p.123.
陈伦炯在对南洋航路的论述中还特别指出:马六甲以西的海洋,“中国洋艘,从未经历,到此而止”。(83)[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南洋记》,第54页。的确,自16世纪初葡萄牙占据马六甲以来,“佛郎机与华人酬酢,屡肆辀张,故贾船希往者。”由于当时驶往苏门答腊的中国商船“必道经彼国,佛郎机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数年以来,波路断绝。”(84)[明]张燮:《东西洋考》卷4,《西洋列国考·麻六甲》,第70页。荷兰人于17世纪中叶据有马六甲以后,又控制了隔海对峙的苏门答腊亚齐港,往来于该海域的多为荷兰商船。对此,陈伦炯有云:“凡红毛呷板往小西洋(印度西海岸)等处埔头贸易,必由亚齐经过,添备米水。自亚齐大山生绕过东南,为万古屡,尽处与噶喇巴隔洋对峙。红毛回大西洋者,必从此洋出,然后向西南过乌鬼呷(好望角),绕西至大西洋(欧洲)。”(85)[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南洋记》,第55页。
值得一提的是,清初康熙开海之后,随着东洋、东南洋及南洋贸易航路的全面展开,极大地促进了华人的海外移民活动,并使得贸易与移民活动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对海外华商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东洋、东南洋及南洋航路的各航线上的主要港口和城市遍布华人移民的聚居地,诸如东洋航路上的日本长崎,东南洋航路上的吕宋(马尼拉),南洋航路航线上的广南会安,暹罗的阿瑜陀耶(大城),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以及爪哇岛上的噶喇巴、三宝垄等地,到17世纪中叶以后均已成为海外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其中,“华人之客吕宋者,恒乐其舟楫之利,而喜其制度之巧焉。”(86)[清]黄可垂:《吕宋纪略》,参见[清]王大海:《海岛逸志》卷6,“附刻·黄毅轩先生《吕宋纪略》”,第166—168页。荷兰人自占据雅加达之后,“建城池,分埔头;中国人在彼经商耕种者甚多。……住此地何啻十万。”(87)[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南洋记》,第55页。而位于越南顺化岘港附近的会安,早在16世纪中叶就已成为广南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到17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日本实行锁国,停止向海外派遣朱印船,而清初虽厉行海禁,但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即开放海禁,使得广南国的对外贸易几乎为中国商人所包揽。据1695 年(康熙三十四年)曾访问会安的英国人保衣亚(Bowyear)在写给印度马德拉斯(Madras)英国东印度公司评议会的信函中记载,会安的“一切贸易乃华人经营”,包括对中国、日本、暹罗、柬埔寨、马尼拉以及巴达维亚等地的贸易,“每岁至少有十艘至十二艘中国船只在此交易。”(88)Alexander Dalrymple, Oriental Repertory, London: George Biggs, 1793, p.87.
清初以来,东洋、东南洋及南洋贸易航路中多边贸易航线的开辟,以及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之间乃至岛际间贸易航线的全面展开,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东亚乃至东南亚地区彼此间的贸易往来的内容与范围,同时在突破西方殖民者的垄断贸易,沟通各地间的贸易往来,以及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雍正至乾隆年间与暹罗等国频繁的大米贸易,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由于人口增多引发的粮食短缺问题,同时也为暹罗等国大米的出口打开了销售市场。
自16世纪末以来,以苏禄群岛为统治中心的苏禄国与西班牙人展开了持续近3个世纪的反侵略斗争。苏禄之所以能够与西班牙殖民者进行长期抗争的因素之一,乃在于中国帆船与苏禄频繁的贸易往来,为其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战略物质。明末至清初,“厦门商船时由吕宋往贸易。由厦至苏禄,水程一百一十更。”(89)[清]徐继畬:《瀛寰志略》卷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5页。直到18世纪,每年依然有4艘中国帆船驶往苏禄群岛贸易,其中2艘大商船来自厦门,每艘的载重量达800吨。(90)John Crawfurd,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rts, languages, religions, institutions, and commerce of its inhabitants, Delhi: B.R. Publishing Corp, First published 1820, Reprinted 1985, vol.3, pp.183-184.中国帆船给苏禄带来的货物,既有陶瓷器、丝织品、茶叶、家具等日常生活用品,也有用于打仗的军事器械,这些物资对苏禄抵抗西班牙人的殖民征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91)《推广瀛环志略·南洋各岛·苏禄能自强》有载:“按其岛地小而兵强,岛民五万人齐心一力,深固不可摇。刻华人以军械易其燕窝,彼得利器,朝夕操演,武备因之益精。”参见[清]张煜南:《海国公余杂录》卷1,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2a—2b页。
17世纪以后,由于荷兰人在婆罗洲西南部地区殖民扩张及其在香料群岛实行的贸易垄断政策,加上西班牙人在西属菲律宾殖民统治的巩固和扩张,以及苏禄王国的崛起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文莱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只有中国商船依然与文莱保持着实质性的贸易往来。在18世纪,每年都有8艘来自中国的船只驶入文莱港贸易,其中6艘分别来自宁波、厦门和广州,另有两艘来自于澳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前来文莱贸易的中国帆船大多是在文莱河口由中国人利用当地丰富的木料自己建造的,船只的拥有者亦大多是文莱当地的华人。(92)John Crawfurd,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 and Adjacent Countries, London: Bradbury & Evans, 185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71, pp.68-70.
自17世纪中叶实行“锁国”政策以后,日本对中国以及海外(主要是南洋)各地货物的需求,除由荷兰船提供外,主要依赖往来于中国东南沿海、南洋各地及日本长崎的中国商船。此一时期中国商船开展的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多边海外贸易方式,既满足了中国海商海外贸易自身发展的需求,同时又促进了东亚与东南亚之间贸易往来。
结语
明末清初中国民间海外贸易航路经历了连续性的发展变迁,其中最为显著的发展变化就是在明代后期海澄月港“东、西二洋”航路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东洋航路”“东南洋航路”和“南洋航路”的三大贸易航路,从而使得中国民间海外贸易范围从东南亚拓展到整个东亚海域。这一时期海外贸易航路的这一系列发展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变化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民间海外贸易自身力量的发展所使然。
纵观明末清初民间海外贸易航路的演进历程,从明后期海澄月港一口出洋,到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地区的多口出洋通商格局的形成,从东洋、西洋航路的限定,到东洋、东南洋和南洋三大航路的全面铺展,乃至中国—东南亚—日本多边贸易航线的开辟,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充分显示出这一时期中国海外贸易活动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适应生存发展能力,同时也奠定了中国海商在这一时期东亚及东南亚海上贸易活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彰显出中国海商在促进中国乃至东亚及东南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