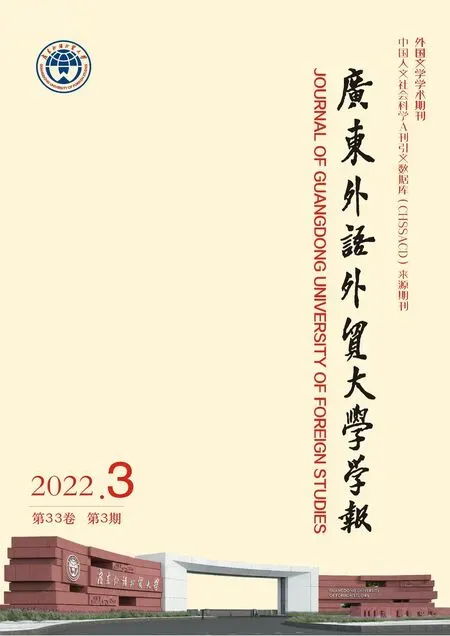德语左翼作家笔下的中国革命英雄叙事
陈丽竹 张帆
引 言
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动荡、思想纷争、政治派别林立。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德语国家左翼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实现平等民主的政治愿景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创作契机。一批具有世界革命意识的作家,如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克拉拉·布鲁姆(Klara Blum)等人将书写视域延展至正在经历无产阶级革命与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国,他们选取中国革命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将自身的政治热情与救世理想倾注于笔下的人物身上,塑造了廖汉新、泰扬和林家明等一系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勾连起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性文学空间。
但两德统一以来,德语左翼作家的创作成果长期受到西方主流政治话语的遮蔽,德语学界倾向于将德语左翼文学作为一种“煽动性文学”来研究,将其视为政治附庸,强调它作为意识形态化的功能性文学的特性①。在中国学界,西格斯、沃尔夫等知名作家的作品已有译介②,但总体而言,针对其中的中国革命叙事文本、主题性和类型化研究仍相对不足。
本文追溯至20世纪上半叶特殊的现实语境,以政治神话(Politischer Mythos)的视角切入德语左翼作家笔下的中国革命故事。政治神话被理解为一种非理性的政治叙事,它通过对历史现实以叙事性的意义建构进行阐释,确立集体认同的意义标的,并由此衍生出符合其价值标准的社会秩序主张(Voigt,1989:9)。政治神话作为特定政治共同体对世界及自身历史的重构性叙述,它所选择的叙事策略服务于政治伦理的诉求,因此在自我描述的过程中,政治神话往往诉诸普通群众,借以与唯物史观所肯定的“人民性”达到意义共契;同时又采取历史书写的神圣化与崇高化策略,为自身代表的政治秩序完成合法化论证。它整合社群的利益、需求和取向,并将之简化为一组角色、一套行为模式和一个制度结构(Patzelt,1988:252)。名流群体既影响大众日常的行为,又控制大众的思想。公众对政治、经济、政策、规章制度等方面的看法以及价值观的树立、理想的建立、知识的获得与态度的形成都受到名流群体的左右(章茜、郑佳,2020:27)。其中,“英雄”作为理想秩序的实践者和服从者,他与秩序的结合直指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服膺并关乎宏大政治概念的庄严,同时凭借自身的崇高性对外划清界限、对内树立模范,标记并明确群体特征,以此激活集体记忆意义上的共同体信念(Hein-Kircher,2006:421)。因此,具有典范意义的英雄形象成为政治神话重要的文本表征。德语左翼作家沿袭了西方英雄叙事的古老传统,将英雄人物作为叙事文本中神话之神圣性与意识形态之世俗性的聚合体,吸纳了神话的非理性行动主义原则,同时又使自身成为政治神话所传递的价值规范的人格化表征。英雄的生命轨迹往往与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互为表里,叙事者通过隐喻、象征等修辞,使个体存在与宏大历史形成共轭,用政治意识形态的置换打开文学审美的通路(王寰鹏,2005:34)。本文选取英雄叙事视角,从成长、爱情与受难三大英雄生命主题剖析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德语左翼作家笔下中国革命文本中的建构方式及叙事策略。
成长:革命主体的启迪与觉醒
作为文本的浅层逻辑,政治神话内蕴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需要诉诸道德、情感和精神归属的叙事外壳得以实现,其具体策略之一是与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成长接轨,将政治理性与斗争激情囊括在英雄觉醒的成长过程中,借以完成革命正当性的闭合因果链。根据这一叙事目的,德语左翼作家吸收德语教育小说的传统,对古典主义的人本观念进行继承和改造,以无产阶级斗争理论代替资产阶级教育理念,把“自我实现”置换为“自我改造”,将立足个体的成长对接为政治层面的觉悟,将精神理性投射为政治理性,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取代启蒙意义上的“人”,教育的过程实质上成为英雄的革命意识觉醒、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因此,左翼文本中英雄人物的成长往往以挫折对抗到觉醒斗争的人生转折为标志: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戏剧《泰扬觉醒》中的女工泰扬原本害怕流血斗争,幻想中国的资本家能和工人站在统一战线上,力图促成双方的和解,她天真地认为,“我去跟褚富先生说,我的朋友一个都不会再被打了,一个都不会!褚富先生会下令的”(Wolf,1988:152)。但厂长褚富命令监工开除咳血的工友,威胁泰扬不要发布煽动言论,甚至扬言武力镇压工人,至此,泰扬的幻想轰然破灭。克拉拉·布鲁姆(Klara Blum)小说《香港之歌》的主人公林家明起初天真质朴、一味忍让,但中国海员无休止的工作、低廉的薪水和遭受的歧视暴打触动了林家明,在他心中埋下愤怒与反抗的种子,他“将顾虑抛之脑后,不顾自己还没有站稳,举起瘦弱的拳头开始反击”(Blum,2001:385)。苏珊·万托赫(Susanne Wantoch)小说《难路》中的医学生小李“看到自己信任的东西被欺骗、看到生活的残忍、看到世界与自己在课堂上学的大不相同”(Wantoch,2018:38),学校的职工陆森被强行征召入伍,“当他走向难路镇的东门取回自己的行装去军营报道的时候,心中却沸腾着”(Wantoch,2018:41)。鲁特·维尔纳小说《不平凡的少女》中的主人公薇拉怀着解放中国人民的政治理想来华,却因中国现状而怀疑能否如愿地爱上中国人民,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想在这里生活……但是我该怎么做?我想回家”(Werner,1961:155)。在建构以革命话语为核心的政治神话过程中,人物对社会现状的思考与意识的转变“特别重视来自外部的教育干预,往往是以与‘社会主义指导者’进行学习谈话的形式进行”(Mayer,1992:342)。在主人公与现实世界的对抗中走向失落时,无产阶级革命理念以强势姿态介入其中,对人物进行积极的思想改造,推动他们向自身代表的历史前进方向转轨。因此,以“觉醒”为关键词的成长叙事往往会设计一个以启迪者身份出现的“革命导师”。作为服务于主人公的功能性角色,革命导师具备一定的学术背景和知识储备,且有成熟的斗争经验,在政治新秩序的传播中成为革命意志的号召者和解释者,亦是分配给主人公的革命监督者和受托者(Thomas,1983:150)。他们发挥神话的刺激功能,以自身人格魅力与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召唤和吸附迷茫的年轻革命者,并作为政治话语的人格化表征,与成长中的主人公建立起亦师亦友的“父子”关系模式。
在具体的“启迪—觉醒”情境中,《香港之歌》中的苏兆征与《泰扬觉醒》中的老王这类罢工领袖的身上充满无产阶级工人气质,他们出身平凡,有深刻的奋斗痕迹。林家明、泰扬等成长中的革命者往往以未经实践检验的朴素世界观解读表层现象,而启迪者的政治理性则是对感性思维的超越和洞见。在政治神话框架下,革命意识与生命意识互渗,启迪者强调行动主义原则,注重引导角色树立民族团结与阶级团结的思想,使主人公迅速明白其中关键,坚定地投入斗争中:苏兆征向林家明解释工人运动等共产主义理论,林家明体内作为“中国人”与“工人”的主体意识蓬勃生长,年轻人的精力与苏兆征传授的革命智慧在他身上找到交汇点,在工人斗争中他“长大了,更有男人味了……他从早到晚、从晚到早都站在港口,颀长柔韧的年轻的身体永远挺得笔直,永远充满活力”(Blum,2001:411)。老王在生存与阶级斗争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使泰扬意识到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她选择“回到你们身边,重新站在工友们身边”(Wolf,1988:173)。一方面,在政治神话的简化叙事策略下,这种凌驾于思辨之上的觉醒已经预设了一个有意识的,即不再被异化的革命英雄,而这一成长路径的预设旨在传递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行动主义的激情致使人物性格的转变过于迫切,概括大于呈现,对话多于思索,角色失去沉思以及批判性思考的空间,未能“以反思的方式处理自己的经历”(Mayer,1992:350)。相应地,张道卫与冯这类更具文人气质的精神导师身上体现出人道主义关怀与思辨的力量。张道卫要求小李“必须得去那里看看,如果你想看到未来”(Wantoch,2018:39);教会陆森保护农民、信任战友、珍惜生命(Wantoch,2018:41)。冯则向薇拉解释中国的社会与传统,告诉她“不应该忍受,而应该去改变。找到原因,并与之作斗争”(Werner,1961:161)。面对迷茫革命者的求助,革命导师并未坚决迅速地抛出革命的立场,比起单向的理念输出,他们更擅长以聆听和互动的形式拉近与觉醒者的距离,并通过心理置换暗示后者的选择。革命导师对主人公的启迪是战争环境下柔性的怜悯与克制的凝视,他们以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和关切,成为投射主人公心理需求的一面镜子,并搭建起革命者通向深层社会肌理的桥梁,从而唤起革命者的主体意识与生存斗志。
上述文本中,叙事者以英雄的成长历程象征无产阶级觉醒斗争的历史自觉,扮演启迪者的革命导师代表革命的历史主体来到具体个人面前,文本中的主人公看似站在求知思变的主动地位,革命导师的设置实质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对具体革命者的召唤,二者形成的结构关系“隐喻革命历史主体渴望民众起来反抗社会统治者的革命意识”(王烨,2005:95),传递政治神话救赎式的必然性历史维度。通过自我校准,革命者在全新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中更新自身生命体验,建立起个体与民族的联系。启迪者与觉醒者的关系结构既保证了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统摄全篇的话语权,又增加了小说叙事的传奇色彩。“父子”关系模式作为无产阶级价值规范的积极指涉,构建起具有归属性和情感支持的政治神话,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个体向革命话语的归附过程(Heer,2013:101)。
爱情:革命信仰的激情与理性
在革命与爱情的关系中,德语左翼作者笔下的中国革命英雄展现出对个性的独立追求。“爱情”主题作为英雄叙事维度之一,政治神话对其在政治上的有用性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塑造了以革命事业为核心的爱情。华裔学者刘剑梅(2008:3)在论述现代性与革命时指出,“爱情至少包含个人的身体经验与性别认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一种自我实现;革命指称的则是进步、自由、平等和社会解放的轨迹”。无论革命还是爱情,二者都指向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实现”。当这种“实现”的具体指涉在性别、个体及社会三个层面达成统一,即女性“成为男性理想信念的承载者和守护者,成为他烦恼和灾祸的战友,成为他奋斗的伙伴”(Zetkin,1988:14)。叙事者将爱情成功纳入革命叙事的政治神话框架中,文本中的革命与爱情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和谐共生系统。作为奋斗共同体的革命夫妻之间既有爱侣的心有灵犀,更有同志般共同进退的统一阵线,革命爱情的最终结果,即爱情所迸发的能量被转化为更浓郁的革命激情,并被有机地编织进政治神话中。
《不平凡的少女》与克拉拉·布鲁姆自传小说《牛郎织女》均以东西结合的革命爱情展现无产阶级革命信仰对个体情感的全面超越。薇拉与电报培训老师凯尽管有语言、文化与民族的隔阂,但同为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理想与阶级立场却以其超民族的包容力,使二人产生了跨越民族和语言的爱情,“凯在她的温情下焕发光彩,和小屋中的室友,也是最好的朋友们交流,学习服务于革命的知识,无拘无束地生活”(Werner,1961:263)。阶级的认同成为爱情的原动力与坚实基础,推动革命者迸发出思想与灵魂的火花。在离别时,二人坚定的爱情宣言“红色阵线”(Werner,1961:267)超越了纯粹的生命体验,政治神话主动吸纳琐碎具体的个性情感与主体意志,并将之升华为一种英雄式的、通向自我实现的人生路线与历史前进方向。同样地,在《牛郎织女》中,汉娜被中国革命者牛郎口中的东方深深吸引,并自认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共通之处,误读的生产性将超越民族的文化认同感置换为革命认同感。汉娜将发生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内化为自身的使命,“我阅读每一篇我能找到的关于中国的报道。那些无名的、饱受折磨的人民。你说得对,牛郎,你必须战斗。不顾一切地战斗。而我,我会向你展示我和你一样强大”(Blum,2001:98)。她作为一个“热衷于中国革命并自觉与中国革命有关的局外人角色”(Yang,1996:12),立志成为恋人的战友,独自来到中国,为牛郎的事业与民族而奋斗。通过对爱情之美好神圣不加掩饰地赞颂,个人情爱成为踏板,推动汉娜向革命的历史觉悟跃升,她将革命视为自身爱情的延续,“在持续的延展关系中自我升华,而这种自我升华能够加剧和扩大本能地满足感”(Marcuse,1969:179),使流血牺牲的革命在政治神话中以浪漫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从而解构了革命本身的暴力和残酷特性。政治神话展现出其激荡的情绪化叙事特征,英雄的爱情为革命注入一剂精神上的强心针。
在《泰扬觉醒》中,对泰扬暗生恋慕的王没有放弃对泰扬的思想与灵魂进行拯救,他鼓励泰扬:“当你陷入柔软而厚重的沼泽地,它想要慢慢吞噬你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坚硬的石板路上,向你伸出手,这其中是否包含‘勇气’?”(Wolf,1988:161)王所发出的暗示中既包含政治层面的思想改造,同时又以保护者、引导者的姿态对泰扬进行爱情表白,情爱的传递隐匿在革命下,体现出政治话语对个人情感高屋建瓴的掌控。从对剥削阶级的幻想中清醒过来的泰扬在接受革命思想的同时接受了王的爱情(Wolf,1988:164)。无论是王的主动启蒙抑或泰扬的被动觉醒,从拒绝到接受的爱情发展始终是革命事业的隐喻和伴奏,最终二者奏出高度调和的双赢结局。在安娜·西格斯长篇小说《战友们》中,当廖彦凯要回到祖国进行革命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妻子如此说道:“我们彼此相爱,始终相濡以沫。现如今却到了分别的时刻。我们要回国斗争,只得将孩子托付给国家了”(西格斯,2021:107)。在西格斯短篇小说《将新纲要送往南方委员会》中,廖汉新看着“这张脸,这张世上他最爱的脸。再次分别后的每一次呼吸都让他锥心地痛”(西格斯,2021:129)。两幕离别场景中,革命者的自述以缺乏个体激情的过场式速写抽离了情感的内容,敛去分别时刻的具体渴望、挣扎和痛苦,借爱情与亲情显示革命者无条件的斗争决心。革命者私人化的情感欲望被革命驯服,自觉地内化为政治神话框架内的功能性元素,始于激情、归于理性,爱情成为“革命意识的透明载体”(刘剑梅,2008:95)。
在政治神话对英雄的建构逻辑中,革命被诠释为爱情存在的前提以及理想未来的现实载体。革命女性“不再是男人的经济竞争者,她成为男人的合作者,成为他奋斗和工作的伙伴”(Zetkin,1988:13)。性别身份的主动退隐与私人情感的克制将爱情解释为一种普遍化的、超脱的同志情谊,个体层面的儿女私情被融进关乎民族大义的政治神话中,它所迸发的激情被转化为革命能量,形成文本中革命与爱情的“互惠公式”。革命借由爱情进入个性私情的领域,完成大我对小我的全面压制和整编。
殉道:革命英雄的死亡与永生
英雄人物具有“人”的生理和情感特征,附着在英雄这一文化符号之上的意志和力量往往又使其具备了半神裔的神话色彩,使英雄身上同时孕育出一体两面的人格与神格:“人”的生理局限决定他同样会死亡,但“神”的异质则赋予他死而不朽的崇高价值。相对于创世神话,现代民族国家对英雄之死的崇拜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为祖国荣誉、政治理想倒在荣誉场上的人,“理应得到与基督教殉道者同样的名声、同样的崇敬”(Könczöl,2008:72)。在这一置换下,现代意义的殉道者被确定为一种最高价值的守护者和保护者。“英雄之死”赋予生命超越死亡、对抗死亡的崇高意义(Brink,etal.,2019:10),这一美学意识契合了政治神话神圣化的美学诉求,并以其爆发力和感染力成为革命英雄叙事中的常见主题。如在安娜·西格斯的《驾驶执照》中,吴佩礼“猛一转方向盘,载有两个总参谋部军官、通信兵、两个便衣和他自己的汽车划过一道分明的弧线跃入了江中。这道弧线也永久地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西格斯,2021:4)。在革命叙事中,死亡主题的叙事核心不再是以个体经验具体地处理“受难”过程,而是将“殉道”主题化、历史化,置入民族的层面进行把握和拔高。通过剥离苦难的艺术性解读,“死亡”本身似乎不再产生任何痛苦,而是在民族大义的语境中被转化为永恒的力与美。
安娜·西格斯小说《失散的儿子们》与《战友们》都以“弟死兄生”的形式处理了英雄的仪式性死亡与成长。立平受到资本家虐待而死亡,寥寒时则被出卖遇害。陶生“以前经常嫉妒立平,因为立平生下来就身体柔弱而备受宠爱,还可以额外加餐”(西格斯,2021:33),但随着立平的死亡,陶生身上属于自然的、瘦弱的、嫉妒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同样消亡,他摆脱了幼稚与天真,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战斗,在抗战中成为党的优秀战士。廖彦凯感受到弟弟的死亡时,“一阵让人抽搐的痛楚席卷他全身,那痛楚就好像失去手足一般”(西格斯,2021:111-112);当廖彦凯最后一次登场的时候,他如同陶生一样已经奔向革命的征程,“廖想起了他的弟弟,不过他已不再心痛”(西格斯,2021:117)。二人化死亡的悲愤为革命的动力,“兄弟”一词在语义和伦理上的双生结构使兄弟成为生命体验的共同体,弟弟死亡获得的崇高性被移植到哥哥的血脉中,从而建立起向新生的过渡,即他为自己的兄长提供了“在精神中重生”(Eliade,1973:145)的通路,兄弟融合为语义上的一体两面,从而在语义和情感上生成了超越死亡本身的崇高意义:弱质的人格在此灭亡,英雄的神格随之诞生。叙事者以“英雄之死”强化了政治神话在伦理层面的话语保障,对“暴力死亡”的美化解读使它作为英雄意义序列中的一环,成为现代革命理念中“生存、解放、胜利甚至救赎的保证”(Koselleck,2001:33)。
对死亡主题的美学重构同样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象征结束的“死亡”在为英雄接生的同时也孕育大团圆的结局。正如西格斯在《战友们》的初版和第二版前言中强调的那样,革命斗争还在继续,“尽管已被自身经历搞得身心俱疲,却依旧坚韧勇敢”(西格斯,2021:92)。政治神话中常见的对立二元论,即光明未来与黑暗势力的永恒斗争,在英雄叙事中找到一锤定音的最后结果。在《战友们》中廖彦凯的故事结束于对革命未来燃烧的希望火焰中,他走到苏维埃根据地,对弟弟死亡的愤怒已经平息,廖彦凯的悲情重聚为澎湃的革命冲动,这次,“他挥动着双拳,恼怒地敲打着门:‘喂,喂,里面的人,听到了没,决定了没,快开门!’”(西格斯,2021:117-118)《失散的儿子们》则在抗战胜利的庆典中落幕,欢呼的人们重聚在广场上,“街上开始热闹起来,烟花的光芒闪耀在墙上……当他到达时,陶生听到了人们爆发出的欢呼声”(西格斯,2021:40)。在《香港之歌》中,尽管林家明已经牺牲,但“他们的悲痛不会破坏这欢乐的舞蹈旋律,这战斗的旋律”(Blum,2001:431),高歌行进的革命脚步绝不会因为个人英雄的死亡而停滞,“‘我们的未来快到了,’中国的工人们想,‘一个没有屈辱、没有折磨、美好的、有尊严的未来’”(Blum,2001:427)。对罢工胜利场面以及资本家灰溜溜离开的描写展现出对革命充分的信心,在时代转折这一未来隐喻上承担了前瞻的功能。革命者的牺牲被视为胜利结局的前奏,其中包括对未来积极前景的开辟和对接班人的召唤,正因如此,英雄的精神必将永存:“英年早逝的家明默默无闻地隐匿在无产阶级无名英雄和烈士当中。但是他的《步步高》旋律却将永存……社会主义建设很快将会谱出新的歌词,共产主义还会有另一首。但它的旋律得以保留。它是死去的家明不灭的灵魂,是人类前进的螺旋桨”(Blum,2001:431)。英雄的个体性在肉体方面被消灭,但其精神却通过死亡复活,前瞻的希望、信心、时代转折和夺取权力的畅想赋予林家明、廖寒时等英雄的牺牲以弥赛亚式的意义,体现出革命者虽死不朽的品格。从叙事结构来看,死亡主题作为通往英雄之路的仪式,仪式之门背后承诺的不朽神格是理想主义的政治神话在英雄叙事中的投射,通过神圣意义的赋予,死亡成为英雄规范的最高体现。
结 语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环,参与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德语左翼作家的书写展示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性因素。我们认为,德语左翼作家笔下的中国革命叙事文本结合传统英雄叙事的个人化策略,以成长、爱情与死亡三个维度概括性地塑造出无产阶级革命观中理想的中国革命英雄形象。他们在激荡社会中探求人生价值,在革命中追逐信仰理想,无论是亦步亦趋追逐革命导师的成长,抑或被革命话语收编的爱情,抑或革命战斗中的死亡,左翼作者将英雄塑造为理想秩序与完美人格的模范,英雄作为政治神话所传递的价值规范的人格化表征,勾勒了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叙事轮廓。德语左翼作家对中国革命主体的英雄式塑造既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及主体性发现打开新的窗口,又揭示了中国革命所内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涵,推动了中国革命叙事在世界文学中的接受。
注释:
① 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Menger M.2016.Der literarische Kampf um den Arbeiter. Populäre Schemata und politische Agitation im Roman der späten Weimarer Republik[M].Berlin, Boston: Walter de Gruyter;Schimdt H, et al.2007.Totalitarismus und Literatur: Deutsche Literatur im 20. Jahrhundert-Literarische Öffentlichkeit im Spannungsfeld totalitärer Meinungsbildung[C].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② 相关译介如下:沃尔夫.1955.沃尔夫童话集[M].吴郎西,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西格斯.1955.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M].季羡林,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沃尔夫编.1957.德国现代短篇小说集[C].张威廉,等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安娜·西格斯,等.1959.民主德国作家短篇小说集[C].严宝瑜,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安娜·西格斯.1999.第七个十字架[M].李士勋,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安娜·西格斯.2021.安娜·西格斯中国作品集[M].张帆,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