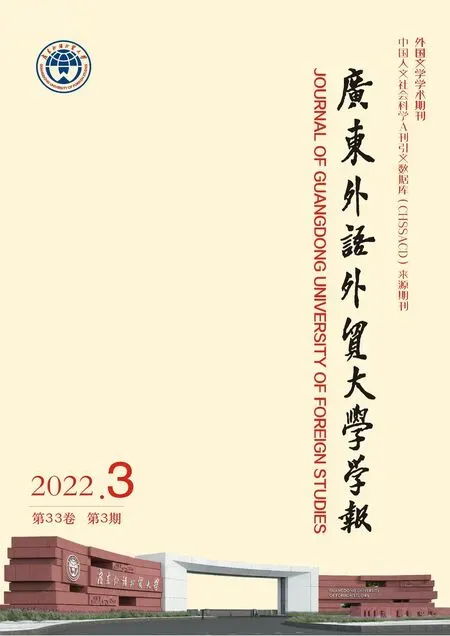《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新型战争叙事
陈蔚青
引 言
反法西斯战争是俄语文学史上长盛不衰的重要题材。自20世纪末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传统的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除了阿斯塔菲耶夫(В. П. Астафьев)、弗拉基莫夫(Г. Н. Владимов)等老一辈作家弱化自身的国家立场,重新反思战争的意义外,以阿列克谢耶维奇(С. А. Алексиевич)为代表的一批战后出生的新作家也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在2013年新修订的小说《我是女兵,也是女人》(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①中阿列克谢耶维奇通过塑造新型女性群像,完善“声音小说”的形式和对传统的战争话语进行去英雄化书写建构了一种新型俄语反法西斯战争叙事。
新型女性群像
有批评家认为,“俄罗斯文学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史从来就是一部俄罗斯文化的‘寻父’史,一部以男性精英的精神求索为主线的思想史,一部以男性主人公为中心的人物演进史”(张建华,2016:281)。作为俄语文学的重要一环,传统的反法西斯战争叙事自然也深受男性精英意识的影响。回首苏联时期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三次浪潮,我们发现这一题材的创作主体是男性,而作家们也往往通过对笔下男性主人公的重塑与颠覆实现创作模式的突破。尽管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战死沙场的男性英雄形象逐渐得到弱化,但战争中女性的生存境遇与情感遭际却少有人问津。连有限的从事军事题材创作的女性作家也在父权传统与苏联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参与或附着于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男性书写。
纵观传统的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我们能将最常出现的女性形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忠诚、纯洁、柔弱的女性,在作品里一般具化为战争后方苦苦等待战士归来的纯真少女、忠贞少妇或慈爱的母亲;第二类是温柔体贴、在战争中充当男性“辅助者”的女性,作品中往往具化为不直接参加战斗,却对男性主人公关怀备至的护士、卫生员等。前两类女性形象与俄语经典文学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一脉相承:从《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里的塔季扬娜到《贵族之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中的丽莎再到拉斯普京笔下的纳斯焦娜,“理想女性”依托俄罗斯宗教观里的圣母崇拜,承载了作家和男性主人公的审美与道德理想。然而,传统的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里还有第三类:看似“叛逆”的女兵形象——她们在战争中褪去了所谓的“女性特质”,英勇无畏,浴血奋战。可事实上这些拥有反差色彩的女性形象与前两类女性形象一样,同属于作家笔下的扁平人物——作者之所以塑造“叛逆型”女性形象,往往意在宣扬自己的某种理念,而非探索其独特的生命逻辑。就连家喻户晓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的作者瓦西里耶夫(Б. Л. Васильев,1981:142)也坦言:“没有任何一个女主人公是以某个具体人物为蓝本的。我力求再现的不是人物性格,而是年轻妇女的典型。她们只有一个目的:保卫自己的祖国。她们体现了奋起同法西斯进行神圣战争的我国全体人民的意志”。传统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或是被排斥在战场之外,默默承受男性离去的伤痛与孤独;或是在战争中履行男性辅助者的“义务”,默默奉献,不求回报。哪怕是为数不多的与男性并肩作战的女兵,传统作家认同并大力宣扬的也是她们“战士”和“英雄”的身份,而非这些女兵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情感逻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所有的女性形象都出自男性创作者的主观臆想而与事实不符,笔者也并非指控作家们在切入反法西战争题材时刻意使用了“性权术”,而只为指出与复杂多样的男性形象相比,传统的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数量的丰富性,还是性格的立体度都稍逊一筹。更重要的是,即使男性作家对战争中的女性曾进行并仍有可能进行更为精彩和深刻的书写,男性话语体系中的女性经验依旧不能代替女性自身的表达。随着20世纪70、80年代苏联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阿列克谢耶维奇以还原战争中女性的真实面貌为己任,在小说《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展示了一批与传统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大相径庭的、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其中,“新亚马逊女战士”“新美狄亚”和“女性思想家”这三类承载着女性主义隐喻和象征的形象尤为引人注目。
相较于西方世界,俄罗斯传统文化对母亲身份的强调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正教的圣母崇拜与古罗斯的大地母亲崇拜相结合,奠定了俄语作家将母亲形象理想化的传统。俄罗斯经典文学中的母亲形象往往承担着生儿育女和相夫教子的“神圣”使命,温顺平和、无私奉献。可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既描写了众多心系家庭、关爱孩子的母亲,又展示了一批亲手将儿女推入战争、甚至像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般无情扼杀亲生骨肉生命的“新美狄亚”形象:战争中怀孕的密码破译员恰尔娜雅不顾法律和教会的双重禁令,毅然选择自行流产;一位妇女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被法西斯开枪打死,便亲手摔死了还在吃奶的婴儿;而一名无线电报员为了不暴露游击队的位置,便将因饥肠辘辘而大哭不止的孩子缓缓浸入水中……“新美狄亚”作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一根螺丝,虽拥有孕育生命的能力,却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的身份冲突。传统的血缘伦理在残酷的战场上分崩离析。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审母”为叙事策略,解构了传统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叙事中的理想母亲形象,展现出“新美狄亚”们在战争中被迫剥离“母性”的挣扎和她们为在民族主义的大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思想家主人公是俄罗斯文学的核心现象之一”(尼科尔斯基,2012:4)。回望俄罗斯经典文学,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笔下的巴扎罗夫对社会局势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里的别祖霍夫不停追问着生命的价值;巴赫金(М. М. Бахтин,2009:2)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思想家式的人物,时常发出哲理议论。在俄罗斯文学大师笔下,一系列才智过人、明若观火的男性思想家形象面前,俄罗斯女性似乎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生活哲学的权利。而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中,阿列克谢耶维奇除了描写一部分思维简单,缺乏主见,将生儿育女视为天职,认同并甘心归顺于父权文化的女兵,还向我们展示了众多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对历史、人性等问题展开多维度思考的“女性思想家”形象。
首先,这类打破传统的“女性思想家”在接受作家的采访时大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我想说,我要说话,统统说出来……我知道有人会来,一定会来的(Алексиевич, 2013b:53)”,“这些(痛苦的)记忆必须保留下来,必须告诉所有人。这个世界应该保存我们的哭声,我们的哀号……”(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341)。阿列克谢耶维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一群平凡衰老的妇人,而是一个个被激烈的思想冲突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灵魂。有的女性大胆表达了对斯大林政权的质疑,有的则对现存的历史投以轻蔑的一笑。工兵排长沃尔科娃直言一些女兵的参战行为是“飞蛾扑火”(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232);而在谈到自己因当过兵而备受男性嘲讽时,狙击手谢……娃③不无讽刺地反问作家:“我们是嫁人还是不嫁人?是为爱而嫁,还是不爱也嫁……”(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267)。《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的“女性思想家”从自身在战争中独特的生存体验出发,对个体乃至全人类的价值、尊严与理想展开了深刻的思考。
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的这几类形象并不都是独立存在、相互排斥的。有时在一个女性身上会体现出两种甚至多种形象质素,这也更加印证了战争中女性的真实生命形态的复杂性。阿列克谢耶维奇并未臣服于父权文化和民族主义的严酷秩序,而是对传统俄语反法西斯战争叙事中的“女性气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里鲜活丰满的新型女性群像填补了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一片空白。
“声音小说”
除了在形象上推陈出新,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对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体裁进行了更新。2015年瑞典文学院在为作家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点出其“多声部创作”(многоголос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的体裁特征(Шебалина,2015)。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将自己的创作合称为“乌托邦之声”(голоса утопии)系列。俄语批评界有学者直接使用“声音小说”(роман голосов)(Лаптева,2015:430)来界定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
“声音小说”并非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独创。其雏形来自20世纪70年代阿达莫维奇(А. М. Адамович)、布雷利(И. А. Брыль)和科列斯尼克(В. А. Колесник)合著的《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Я из огненной деревни…)一书。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多次谈到这部小说对自己的重大意义:“我在寻找一种写作体裁。它能描述我眼前的世界,承载我的所见所闻。有一回我偶然得到一本书——《我来自火光熊熊的村庄》。我体会到了那种只有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才能获得的震撼。这部小说拥有非凡的形式——它由生活里的各种声音组成。这些声音我儿时听到过,现在在马路、房子、咖啡厅和电车上也能听见。范围锁定了,我终于找到了寻求已久的体裁。阿列斯·阿达莫维奇成了我的老师……”(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8-9)。
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与反法西斯战争初期的战地特写和60年代风靡一时的朱可夫(Г. К. Жуков)、格列奇科(А. А. Гречко)等军事统帅的战争回忆录大相径庭。小说的主人公是白俄罗斯乡村里300多名亲历法西斯屠杀暴行的幸存者。作家们花了4年时间,在录音机的帮助下采用口述实录的方法记下了法西斯士兵的累累恶行。虽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为《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搜集素材时使用了和阿达莫维奇同样的口述实录方法,甚至作家的一部分“启动资金”也由阿达莫维奇提供,但与《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相比,《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这部“声音小说”在以下三个方面展现出全新的风貌。
首先,在《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一书中,阿达莫维奇三位作家的“声音” 始终占据着叙事的主导位置。作家们在每篇文章的开头都会细致地交代采访地点和受访人的各类信息。文章里也常常出现作家与被采访者的直接对话。作家们甚至会在这些段落中的每个问题前都标上“问题”(вопрос)一词。这种写作形式使整部书看上去更像是一组新闻纪实报道,而非文学作品。此外,作家们有时还会在受访者叙述时插入自身的评述,这就使读者感受到,作家本人的“声音”始终凌驾于被采访人的“声音”之上,推动着叙事的发展。而在2013年新修订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阿列克谢耶维奇主动放弃了自身“声音”的主导地位,并和读者一起将“整副身心都沉浸于倾听之中”(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206)。她不仅大幅删去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写下的介绍型文字,只保留少量的导引信息,还把人物介绍缩减至文末的姓名和战争期间的职业,作家的“声音”遁于无形。此外,《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鲜见作家与女兵的直接交谈。全书16个章节的主体都是女兵的自白,作家本人的“声音”则以创作笔记的形式被单独置于书首。如此一来,作家的“声音”便和受访者的“声音”处在一个完全平等的位置上,彼此独立存在,互不干扰。
根据联合体人员存在形式的不同,该维修集约范式又可分为劳务委外和委托人力资源公司两种。劳务委外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将维修业务中必要专业技术支持人员全部委托给服务商管理,服务商监督管理维修质量;委托人力资源公司则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将维修业务中的非专业技术支持人员调配与管理工作集中委托给人力资源公司进行招聘与管理,这些人员的培训工作由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公司或服务商负责,服务商监督管理维修质量。
其次,阿列克谢耶维奇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了更为复杂的剪辑。《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里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遵循同一个叙事模式,有完整的起因、发展和结束,每个受访者的叙述分量也差不多,读者不免会读到一些形式和内容都极其类似的故事。而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记录女兵的“声音”之前就对“声音”的主体进行了筛选。最后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访女兵获得在小说中发声的机会。其中大部分是出身民间,在战场上默默无闻的普通士兵、护士、厨娘和洗衣员,担任指导员等领导职务的女兵只占少数。这是因为作家在采访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普通人会更加真诚……她们的词语来源于自身的痛苦,而非报纸和书籍上别人的话。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的情感和语言反倒更容易被时间加工,沾染上派生出的知识和神话”(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11)。小说第三章“只有我一人回到妈妈身边……”(Одна я вернулась к маме…)的主人公——在坦克部队担任卫生指导员的维什涅夫斯卡娅便是一例。在接受作家的私人采访时,她如同和女儿谈心一般,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的战地生活。其中有女兵打开水的趣事、认错人的笑话、男性士兵的言语骚扰和女友接连丧命的悲剧。可在作家将根据录音带记下的稿件邮寄给她后,这位指导员却恼羞成怒,将稿件改得面目全非。她在有关男性士兵对女性进行言语骚扰的段落旁画了三个问号并愤怒地写下批注:“对我儿子来说,我是个女英雄。上帝啊!读过这些之后,他会对我怎么想(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116)?”女兵最本真、原始的“声音”在宏大的民族主义话语和父权话语的双重压制下再次失去了性别特征,倒退为传统俄语反法西斯战争叙事中的“空洞能指”。通过展示女兵采访前后的不同态度,阿列克谢耶维奇将战争中的女性“声音”所承受的种种无形压迫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作家对那些与传统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的女兵格外关注。上文提到过的“新亚马逊女战士”“新美狄亚”“女性思想家”等人获得了更多的发声空间——在小说中占据较大的篇幅,叙述的完整度也更高。
第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章节编排比《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更为巧妙合理。《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的章节排列总体上较为粗糙。同一个主题常常会出现在不同章节里,给人以杂乱无章之感。例如小说第二章“母亲和孩子,孩子和母亲”(Мать и сын. Cын и мать),第六章“没有孩子”(Без детей)和第八章“十岁出头”(Свыше десяти)中就记录了几段几乎一模一样的叙述,给读者造成一定的审美疲劳。而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小说中庞杂的女性“声音”进行了全新的排列组合,赋予作品一种“形乱神不乱”的魅力。例如,小说的第九章“我们没有打过枪……”(Мы не стреляли…)里的“声音”都发自在战场后方辛勤工作、默默无闻的洗衣娘、邮递员、炊事兵和理发师等人。作家通过集结在“第二战线”辛勤工作的女性的生活碎片,呈现了这些无名英雄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而在第十章“当然是需要军人……可我也还想做美女……”(Требовался солдат… А хотелось быть ещё красивой…)里“爱美”则成了女性“声音”的关键词——“不管女人们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哪怕说到死,她们也绝不会漏掉美的话题”(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196)。第十二章“哪怕让我只看他一眼……”(Только поглядеть один раз…)汇聚了一批打破禁忌、谈论爱情的女兵……此外,《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十六章章节的名称都是女兵自己的话语。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不同女兵的“声音”中挑选出一句点睛之语用来涵盖章节主题的做法更加凸显了“声音小说”的独特魅力。“对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说,声音是源泉,是技巧,是诗学,是世界,是她的唯一的艺术生命”(李正荣,2016:4)。
有批评家认为,“非虚构写作中的作者是事实的见证者、调配者、发布者和阐释者,也是自我情感的书写者”(洪治纲,2021:41)。通过对众多混杂的“声音”进行筛选、剪辑和整合,阿列克谢耶维奇进一步完善了“声音小说”的形式,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推向新的高峰。
去英雄化书写
传统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英雄书写一直是学者讨论和反思的话题。“从整体上说,(在俄罗斯)战争的英雄主义题材始终被陈旧的观念和陈旧的方式反复表达着。尽管有极少数作品对卫国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行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和质疑,却很少有作家全面、严肃、深刻、哲理地重新反思这一场战争以及与其有关的众多理念”(张建华,2010:40)。而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中,阿列克谢耶维奇紧扣女兵的生命逻辑,对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爱情”和“死亡”两大主题进行了去英雄化书写。
与“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相比,爱情话语在传统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居于次要地位。为了维护英雄的“纯洁性”,一些作家在切入战争题材时或是将人物的私人感情搁置一边,或是将个人爱欲视为民族大义的对立面,也有作家采取将爱情话语“革命化”的叙事策略以对英雄人物进行“无菌处理”(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27)。然而,“战争催生人的爱欲状态”(尼·别尔嘉耶,2007:168),虽然军中严令禁止恋爱,但许多士兵都无法坚持当年立下的誓言。狙击手克利盖尔承认:“我们都在恋爱……如果在战场上我没有坠入爱河的话,那我根本就活不下来。爱能救人,我就是被爱情拯救的……”(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255)。在残酷的战争中,爱情是抚慰平凡个体心灵的一味良药。除了记录众多在战场上勇敢拥抱爱情的女兵,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揭开了一部分“禁欲女性”的爱情面纱。例如,卫生指导员格罗兹比偷偷爱上了自己的战友却始终没有表露心迹,可惜战争还没结束,年轻的少尉就牺牲在敌军的炮火之下。当连队埋葬他时,所有战士都让格罗兹比最先与少尉告别,那时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爱情早已被大家收进眼底。“莫非他也知道?可是太晚了,他已经长眠……但当我想到他或许知道我爱他的时候,却不禁狂喜起来……我一生都会记得那一刻:炮弹在乱飞,而他就躺在担架上……可我竟然高兴地笑了出来,就为他可能知道我的爱”(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148)。想到自己深埋于心的情意或许早已被心爱的人知晓,格罗兹比走上前去,当众亲吻了少尉,这也是她的初吻。这个吻别在现代人的眼里或许稀松平常,然而正是这轻轻地一吻替无数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被爱情撩拨心弦却被迫沉默不语的女兵发出了无声的抗议。难道只有在爱人死亡之后,人才能获得表达情感的权利吗?当民族主义需要靠个体的巨大激情去填注时,个体的爱欲也往往被民族主义压制甚至剥夺。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普通士兵的爱情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情感概念,还象征着一种具有悲悯性的、反压迫的文化的萌芽,它与战争中的苦难相结合,以一种更隐蔽同时也可能更顽强的方式啃噬着英雄主义的大厦。
达琳·M·尤施卡(Darlene M. Juschka,2015:97)在《性别符号学》(TheSemioticsofGender)里指出,“关于男性英雄和牺牲的神话叙事仍以多种方式继续在战争意识形态中发挥着作用。这种叙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有效”。如果说传统的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对男性主人公不畏死亡、勇于献身的英雄话语情有独钟,阿列克谢耶维奇着力呈现的则是战争中的女性面对死亡时的纠结与迷茫。大部分女兵在接受采访时都表达了对死亡的恐惧和抗拒。侦查员汉吉穆洛娃在目睹了无辜的列宁格勒男孩因《斯大林227号命令》④被残酷处决后从心底发出质疑:“是的,我们胜利了。但胜利的代价又是什么啊?这代价是多么可怕啊(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68)”;而步兵斯特洛采娃在看到战友牺牲后悠悠吐出的那句“她躺在棺材里这么漂亮……就像一个新娘……”(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206)何其可悲、又何其讽刺。对一些深陷战争泥潭中的女性而言,死亡或许是一种解脱,是逃离生存之重负的独特形式。
在采访过程中,最出乎作家意料的是女兵们“谈论死亡比谈论爱情更加直白”(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245)。因为“战争结束后,她们自己还有另一场战争,其可怕程度并不比她们刚刚走出的那场战争轻”(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245)。胜利的钟声敲响,劫后余生的女兵们本以为会收获“英雄”应得的尊重与荣誉,谁知等待她们的却是众人的鄙夷与唾弃。“那么,祖国又是如何欢迎我们的?我真是忍不住要哭出来……四十年过去了,说起来还是面孔发热。男人们沉默不语,女人们则冲着我们大喊大叫:‘我们知道你们在前方干的那些好事!用你们年轻的身体去勾引我们的男人,前线的婊子!穿军装的母狗……’侮辱的话语五花八门……俄语的词汇很丰富……”(Алексиевич,2013b:267)。许多向作家全盘吐露战争中真实经历的女兵会在采访结束后恳求作家改动自己的姓氏或不要公开发表。战争体制的性别化不仅造就了女性在战争中的悲剧生存逻辑,还以一种结构性的冷暴力参与了战后文化的重建。女兵们在和平年代依旧消散不去的失落正是对传统的英雄话语的背离。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问世之前,我们几乎听不见这群“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女性的声音。阿列克谢耶维奇通过对“爱情”和“死亡”两大主题进行去英雄化书写将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带向新的高度。
结 语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也存在一些局限之处。首先,俄语文学没有声势浩大的人权运动背景,这就使具备性别自觉的作家往往身负“启蒙者”和“拯救者”的重任;其次,贯穿于俄罗斯经典文学中的批判意识与“勘探”社会的惯性也使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担负了许多女性话语之外的使命。这两点都使《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所包含的社会批判性得到加强,审美价值遭到削弱。此外,口述实录的写作方法也在无形中造就了作品语言朴素、风格简约等降低作品“文学性”的特点。小说带给我们的悲愤与震撼似乎要多于蕴藏在文字间的精妙动人。但相较于少量的遗憾,《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的价值更值得肯定。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新型战争叙事动摇了传统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习焉不察的思维定式,使人们对战争中女性的历史和生存现实开展新的观照和思考。如今的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也已成为俄语世界人民所熟知的成语(Алексиевич,2013a:495)。
反法西斯战争是俄语文学史上长盛不衰的重要题材,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也和任何一种当代的文学现象一样,在世界多极化格局日益巩固和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的形势下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正如弗拉基莫夫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前夕所作出的预言:“在新的千年还会有战争胜利后出生的人来写新的关于战争的书。对战争的看法会改变,新的理念会变得成熟。战争会被揭示出一些从前不为人知的奥秘,展现出迷人的神韵”(Кардин, 1995:199-200)。
注释:
① 书名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的汉语意思是“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作品于1984年初首次发表在《十月》(Октябрь)杂志上,其他章节则于同年在《涅曼》(Нёман)杂志上刊登。可作品中有不少内容都被苏联书刊审查机关以“和平主义”“自然主义”和“抹黑苏联女性英雄形象”等理由删除。1985年,乘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春风,小说迅速推出单行本,并于同年由中国学者吕宁思以《战争中没有女性》的书名翻译出版。21世纪之交,阿列克谢耶维奇开始大规模修订自己的早期作品并陆续将其再版。2013年,莫斯科“时代”(Время)出版社以“乌托邦之声”(Голоса Утопии)的名称再版了作家重新修订的四部旧作——《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1985)、《最后一批证人》(Последние свидетели)(1985)、《锌皮娃娃兵》(Цинковые мальчики)(1989)、《切尔诺贝利的悲鸣》(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1997),并添加了全新的第五部小说《二手时代》(Время секонд хэнд)。其中新修订的《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几乎可以说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重新创作。作家发表了大段曾被审查机关删除的内容,并对小说的结构进行了新的调整。2015年,吕宁思重新翻译了新版小说,并以《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书名再次出版,这也是该小说的唯一汉语译本。为方便国内读者查询,本文也使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译名。
② 女性主义批评家琼·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曾在著作《女性与战争》(WomenandWar)(1995)中指出,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使男子常被塑造成在前线厮杀、勇于牺牲的“正义勇士”(just warrior),而女性则被定义为后方劳动、悲叹战争甚至偶尔反战的“美丽心灵”(beautiful soul)。
③ 部分被采访者要求作家在发表时隐去或改写自己的姓名。
④ 《第227号命令》(Приказ № 227)是二战中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面临愈发严峻的战局下达的一道命令,签署于1942年7月28日。概括来说,《第227号命令》要求苏军在面对德国法西斯的进攻时,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誓死保卫祖国,不准后退一步(Ни шагу назад!)。擅自撤退的军官和政工人员将被视作“懦夫”和“叛徒”,并遭到军法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