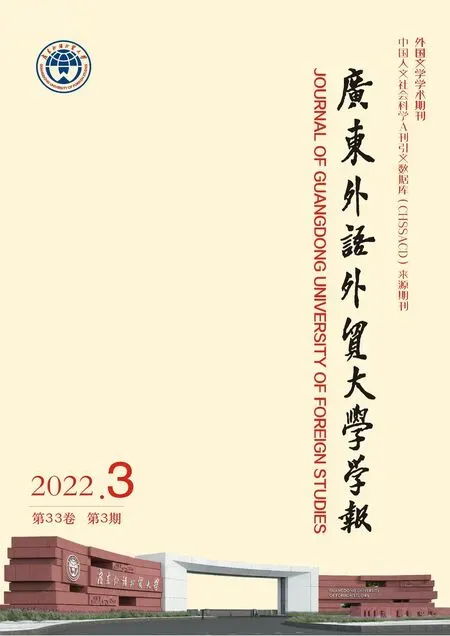笔尖上的美国之音:《白鲸》的美国口头传统研究
黄永亮
引 言
美国学者丹尼尔·布尔斯廷(Boorstin,1965:295)认为,美国文学最大的特点是口语化,是一种声觉文学,它很清楚“自己的声音和对象”以及说者和听者之间产生共鸣的效果。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口头语言,因此被视为美国文学口语化的先驱。早在19世纪中期,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白鲸》(Moby-Dick,1851)中就运用了美国口头传统对民族文学独创进行尝试。主人公埃哈伯(Ahab)船长被一头名叫莫比·迪克的白鲸咬去一条腿,他带领“披谷德号”(Pequod)的船员一路追杀企图复仇,致使整艘船被凶猛狡诈的白鲸撞沉,唯有以实玛利(Ishmael)得以幸存。论者向来大多从种族、宗教、政治等方面给予分析,如弗卢斯恩(Fruscione,2008:14)认为小说模糊了白人与他者、文明与野蛮的界线;郝运慧和郭棲庆(2015:143)认为作者陷入宗教虚无主义的困境;段波(2020:135)指出小说展现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扩张版图。《白鲸》体现“一种力图摆脱旧传统的束缚、渴望民族文学独立的心理”(黄永亮,2016:47),而学界对它和美国民族文学的关系则关注较少。本文从口头文学的角度考察其中的演说、布道、民间文学等具有本土特色的口头传统,指出它们是美国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对民族文学的独立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演 说
演说是美国人民生活和文化的重要部分,他们喜欢以此方式讨论公众话题,宣传政治和文化理念。美国早期的政治家认为演说对自由社会体制来说很重要,它培养人的雄辩能力,避免产生暴君,“领导应该靠说服力而非武力来动员选民”(Gilmore,1994:578)。美国演说文化始于殖民地时期,到18、19世纪,关于社会、政治等问题的讨论和演说随处可见。从独立革命到内战,美国历史几乎是在一系列伟大演说中进行的,展现了“一幅通过演说辩论来解决重大问题的画面”(Boorstin,1965:298)。当时的美国文学作品也多有政论色彩,注重修辞和口才。演说在美国是一种政治活动,也是一种娱乐文化活动,经常出现在19世纪的历史性场合,如某个历史事件纪念日。那时还掀起一股讲学热潮,口才好、名望高的讲学者广受青睐,像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很多作品都是由讲学发言整理而成的。有人将演说文化流行的美国比为庞大的讲演厅,“讲坛从波士顿起,经过纽约、费城到华盛顿连成了一条直线”(坎利夫,1985:150)。演说和辩论也是学校常见的课程和活动。梅尔维尔年少时参加过这些活动(Parker,1996:110),并影响他后来的创作。
《白鲸》的演说突出了人物性格乃至美国的民族精神,彰显了小说中的社会关系。埃哈伯的出场常伴随着演说式的语言,体现一种偏执自负和善于控制、蛊惑他人的个性。第36章就展现了他如何用演说鼓动众人帮他向白鲸复仇。他没有直接说要追杀白鲸,而先用煽动性的问题接连发问,诱导船员不假思索地做出积极冲动的响应,让人觉得捕猎任何鲸鱼(包括白鲸)是捕鲸手的正常业务。勒庞(Le Bon,2004:96)在分析大众心理时指出,群体容易失去判断力,极端轻信。一个独处时有教养的人在群体中会变成残暴狂热的野蛮人,行为受本能支配,易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打动,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埃哈伯抓住群体容易被感染的心理,激起船员“慷慨的豪侠心肠”(梅尔维尔,2001:274)①,使其觉得追杀白鲸是义不容辞的壮举,连一向理智的以实玛利也不由得跟大家一块叫喊,“心里有一种野性的神秘的同情的感觉”,感到埃哈伯的仇恨“就是我的仇恨”(232)。这种感觉正是群体残忍性的无意识。勒庞强调群体捕猎的热情凶残是这种大众心理的体现。尽管众人纳闷自己听了埃哈伯的发言怎么会变得这么兴奋,但在其煽动下,他们捕猎的野性苏醒了,一双双狂热的眼睛望着他,就像“狼群的血红的眼睛瞅着领头狼的眼睛”(214)。唯一提出反对的人是大副斯塔勃克(Starbuck)。他指出白鲸伤人是出于本能,而对没灵性的动物报仇则有伤天理。对此,埃哈伯发表了雄辩且有哲理性的演讲进行反驳:
凡是肉眼看得见的东西,伙计,都是跟硬纸板做的面具一样……某种未知但仍可理喻的事物会从不可理喻的面具后面推出事物面貌的原型……白鲸就是那堵墙壁……有不可思议的歹毒心肠支撑着它。这不可思议的东西正是我憎恨的主要东西。(213)
埃哈伯的思辨能力让其他人自感不如,这一点和他的个性、心智、雄辩以及权力一起加强了他的震慑力。演讲中他指出万物隐含着某种真实存在的象征,反驳了斯塔勃克视白鲸仅是没有灵性的动物的观点。埃哈伯认为它是上帝的化身,而这个上帝是邪恶歹毒的,他令人无法捉摸,高高在上,沉默、冷漠地俯视众生在其所编织的命运之网中挣扎,而对其“诉求与苦难视而不见”(郝运慧、郭棲庆,2015:144)。埃哈伯痛恨上帝无形的控制,所以企图通过反击象征上帝的白鲸来证明他能够摆脱命运的主宰。
接着埃哈伯对斯塔勃克施以激战法,说众人都和他同一条心要追杀白鲸,一想到它“就狂笑,表示轻蔑”,而斯塔勃克是“全南塔克特最好的镖枪手……不用说是不会从这么不起眼的一次捕猎中退缩的吧?”(214)他似乎在警告,其他人都表示支持,斯塔勃克还反对就等于自我孤立了。第25章以“骑士与随从”为名对斯塔勃克进行人物特写,说明《白鲸》这部“赞颂英雄的伟业”(周玉军,2012:207)的民族史诗有意将勇敢的骑士精神作为衡量人物男性气概的标准。此处,埃哈伯故意贬低捕猎白鲸的难度,称斯塔勃克为“最好的镖枪手”,显然,后者还犹豫的话,那就不够男子汉了。
埃哈伯的另一次精彩演说出现在第119章。“披谷德号”的帆臂顶端遭到雷击而燃烧起来,他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叛逆行为的警告,于是愤怒地在暴风雨中发表一番挑战式的演说:
你有毋须言说也毋须占有地盘的威力,这我承认;可是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也要和这种无条件主宰我的威力抗争……只要我活在人世间一天,我就有一天自己的高贵的人格,而且觉得我自有我的至高无上的权力。(615)
这段激情澎湃的演讲揭示了人物坚韧不屈的个性,道出了人类想摆脱命运主宰、渴望自由的心理。埃哈伯的抗争意识“高扬着人的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蒋承勇,2003:22)。他视自己的本性高于一切,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具有当时美国民族精神的烙印。作者肯定了个人主义在美国民族建设中的积极意义,也认识到自由意志既能为善,也能为恶。过度张扬、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会导致邪恶,对埃哈伯将个人意志凌驾在他人之上、将全体船员推向毁灭的做法,作者显然是批判的。
刚愎自用、盛气凌人的埃哈伯控制着全船,其他人缺乏发言的自由,随波逐流,变成他“运用的工具”(273)。他的演说都是一种单声部表演,缺乏对话辩论的色彩。这种演说没有如人所宣扬的,成为捍卫自由民主的武器,却成了独裁统治、煽动群众的工具。周玉军(2012:207)指出,作者要塑造一个向白鲸展开伟大战斗的英雄群体、书写民族史诗,“对等级压迫的观察与批判在《白鲸》中退居次要地位”,所以和作者其他航海小说相比,它描述的社会关系相对和谐,阶级矛盾得到控制。这是作者的美学选择,换个角度看,这也体现了他的民族忧患意识。将船作为国家政治的喻体,从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到北美开拓者威廉·布拉特福德(William Bradford)再到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都有这样的修辞。“披谷德号”显然也指涉美国民族。作者借斯塔勃克之口指出埃哈伯式民主的实质是自私的唯我至上,对“在他之上的人,他要当一个民主派”,对“在他之下的人,他是多么作威作福”(219)。作者在此提出一个重要的美国政治课题——如何避免一个国家成为独裁者操纵的机器,避免“披谷德号”那样船毁人亡的民族灾难?答案也许是民众要有自由的发言权,而不是成为一群消声、盲从的乌合之众。理智冷静的斯塔勃克是唯一能和埃哈伯抗衡、有望扭转整条船命运的人物,却在关键时刻患上哈姆雷特式犹豫,甘愿让“刚强意志彻底沉沦”。对这位面对海上风险不乏勇气、却抵不住那些精神上的“恐怖力量”的人(156),作者明显表示感慨批判。
布 道
布道不是源于美国,但对其社会和文化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形成具有美国特色的一种口头文化。清教徒在北美的定居开创了美国民族和文化,他们将清教主义作为个人奋斗、社会建设和民族建构的指导思想。清教主义是美国文化的起源之一,“包含着美国文化的重要基因”(钱满素,2010:5)。传教布道是清教徒宗教生活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些布道文还经常印发成书进行广泛传播(Bush,1988:56)。布道的内容不只关乎宗教,也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使它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美国各种社会改革,如禁酒、废奴、妇女选举权等运动,都少不了牧师布道的参与,“至今,牧师仍是美国民权最雄辩的演说家”(Ferguson,1994:524)。
《白鲸》中的布道情景给小说蒙上浓重的宗教色彩。这些旨在使人认识上帝恩惠、皈依宗教的布道在小说中却无法改变人物堕落的命运,体现作者的宗教怀疑和对人性的思考,深化了小说思想主题。例如,作品开头一个黑人牧师在漆黑的寒夜给一群黑人布道,内容“是关于墨黑的幽暗那一处以及幽暗中的人哭泣哀号、咬牙痛悔的光景”(36)。该描写以一个个阴郁的意象暗示了整部小说的悲剧基调。又如,第9章梅布尔(Mapple)神父借《约拿书》给船友布道。讲坛嵌板前身像个船头,《圣经》放在突出来的托板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意味深长的呢……讲坛引领着这世界”(71)。这暗示了布道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性。梅布尔以约拿因犯罪而受惩罚、最终悔改获救的故事阐释了世人要服从上帝的道理。该故事可视为埃哈伯悲剧的前奏和对照。他也亵渎上帝,但拒绝服从和悔改,终遭报应。
美国布道文常有一个因世人堕落而发怒的上帝形象,并以天灾人祸来象征上帝的惩罚。梅布尔布道的内容也是上帝用风浪和鲸鱼来惩罚罪人,此时教堂外风雨交加,外部环境和布道内容里外呼应,起到造势烘托的作用。讲坛背景的画上一艘船正迎着狂风暴雨破浪前进,如书中所言,暴风雨“象征上帝突发的怒气”,而“飞溅的浪沫和滚滚乌云之上高高浮着一片小岛似的阳光,从中映射出一张天使般的脸庞”(70)这一象征希望的画面也和美国布道文结尾常有的乐观主义精神吻合。
布道要吸引、感动人,得有创造性和艺术性,避免千篇一律、枯燥无味。布道者得注重措辞、修辞和气势,“将抽象的神学和救赎理论与实际现实相结合”,从日常生活中援引例子,用文学和修辞学的手法,如设计人物形象、对话、场景等,使布道带有戏剧或虚构叙事的色彩,增强感染力(Bush,1988:57)。梅布尔以船民熟悉的日常事物作为比喻,把《圣经》比作缆绳,《约拿书》是其中一股线;把约拿的良心比作吊灯;把世界比作一艘船;把人世的喧闹比作滔天巨浪。排比句式增强讲话的节奏感和旋律感,使情感表达痛快淋漓,布道气势磅礴,如“谁不把它当回事,谁就会大祸临头……谁在上帝使海水酿成狂风的时候,想在水上浇油,谁就会大祸临头!”(80)拟人彰显人物忐忑不安的心理,如“吓得脸色发白的月亮从漆黑的天空的深沟里露出脸”(78)。设问和反问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使其与牧师产生互动和共鸣,如“《约拿书》到底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船友们,这教训是双股的”;“船友们,这你们还看不出来吗?”(74)头韵和尾韵产生了音乐感,如:
Delight is to him, whom all the waves of the billows of the seas of the boisterous mob can never shake from this sure Keel of the Ages. And eternal delight and deliciousness will be his, who coming to lay him down, can say with his final breath. (Melville, 2002: 54)
这里构成头韵的词有“billows”“boisterous”“shake”“sure”“delight”“delicious”;尾韵有“waves”“billows”“seas”“Ages”“lay”“say”。梅布尔还虚构人物对话,而狂风巨浪、约拿的狼狈鬼祟、内心的自我谴责以及被鲸鱼吞没等人物和场景的描绘栩栩如生,唤起人们丰富的想象,使布道更有感染力。
梅布尔的布道还体现口头文化的表演性。在朗诵具有哀诉味道的赞美诗时,他那庄重的长腔像“大雾中失事的船上不断响起的钟声”,最后几节改变声腔,“怀着激奋欢乐的情绪洪亮地吟唱”(72)。讲到约拿遇到风暴时,他完全投入角色,“似乎也受着风暴的颠簸。他那厚实的胸膛像随着巨浪而起伏,挥舞的手臂犹如各种自然力量在交战;从他黝黑的额头发出的隆隆雷声,眼中射出的电光使淳朴的听众无不怀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之心仰望着他”(79)。如此生动的表演使教众将约拿的困境在脑海中形成逼真的形象,令人无不惊惶动容。
第64章弗利斯(Fleece)的布道可视为对梅布尔布道的戏仿,两者构成互文关系。一次,二副斯德布(Stubb)正在贪婪地吃弗利斯做的鲸鱼肉排,一群鲨鱼也在抢食挂在船边的鲸鱼尸体,声音吵闹。于是斯德布要弗利斯给鲨鱼布道,让它们安静些。与梅布尔典雅的语言相比,弗利斯布道连叫带骂,很有戏谑性。布道中他称鲨鱼为“同伴”“兄弟”,似乎在说其实人类和鲨鱼一样凶狠野蛮,经常为争夺利益互相残杀。作者指出自相残杀的普遍性,“自有这世界以来不是你吃我,就是我吃你,始终进行着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351)。捕鲸手无止境的猎杀鲸鱼和掠夺大自然,斯德布爱吃半生不熟的鲸鱼肉排,这跟鲨鱼的野性毫无区别,如弗利斯所说,斯德布其实比鲨鱼还鲨鱼。他告诉鲨鱼要收敛贪婪,“因为天使无非就是好好管住自己的鲨鱼”,最后意识到布道对鲨鱼的本性起不了作用,它们照样争夺,等吃饱了,“便沉到海底下去了……永生永世也不会再来听啦”(373)。这些话可视为对“披谷德号”命运的预言,梅布尔布道也无法让水手们收敛捕猎的野性和虔诚地信仰上帝,埃哈伯对白鲸穷追不舍最终让捕鲸船永远地沉到海底。作者借弗利斯的布道批判了人类贪婪、残忍的掠夺行为,并预言这种行为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叙事者以实玛利也有布道者的特点。比如当法勒(Peleg)质疑季奎格(Queequeg)的宗教身份时,他就来一堆关于信仰的说理,以致法勒说他不如去当牧师,“我还没听人布道布得比你更棒的”(127)。此外,他在叙事中经常插入离题章节,如第58章“鲸鱼食料”、第60章“曳鲸索”等,他都是从叙事跳到介绍鲸学,然后借鲸鱼讨论人类问题。有论者视这些鲸学章节为“对生活的说教”(Milder,1988:435)。它们看似偏离故事情节,和小说主题却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第96章“炼油间”,以实玛利从讲解炼鲸油的程序到最终引用《圣经》典故奉劝世人不要沉溺于内心的黑暗,否则会自取灭亡,他的“布道”成了埃哈伯悲剧的一个注脚。
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的创作主体为人民群众,主要以口头形式在他们中间流传。作者深受美国民间口头文化的影响,并将歌谣、传说、边疆幽默等文化融入创作。他的人物为来自各地的、不同肤色的水手。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接触了丰富的民间文化,也是这些文化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民间文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精神面貌。《白鲸》体现了早期开疆拓土的美国人在艰难环境中的生存状态、生存策略和欲望追求以及他们的独立个性、坚强意志和奋斗精神,突出了民族性格。民间文学的多元特征有利于丰富作品叙事内容、塑造人物形象和活泼小说语言,它天生具有戏谑、轻松、自由的特点,为小说悲剧气氛提供喜剧性和趣味性的缓和剂。由于和英国有过殖民关系,独立不久的美国的主流文化更趋同于欧洲传统,而民间文化向来是游离在官方、主流文化的边缘,所以它成了作者建构美国民族文学的重要源泉。
巴赫金(Bakhtin,1998:389)认为民间文化以轻松诙谐、自由包容的特点构成对权威严肃、压抑阴郁的官方文化的颠覆力量,甚至能抵抗对宇宙的恐惧,即对如星空、山岳、海洋这样的大块物质和宇宙变迁及自然灾害的恐惧。《白鲸》中那些嘻嘻哈哈的水手所唱的歌谣体现了民间文化的狂欢情调。如第22章水手在起锚时高唱下流情歌,跟此刻唱悲怆的赞美诗的比勒达(Bildad)形成对照,反衬了后者虚伪的宗教虔诚。在漫长凶险的航海生活中,只有像歌谣这样的民间文化才能给人带来活力和解放力量,而严肃僵化的宗教力量毫无作用。第119章斯德布在暴风雨中唱着曲子,“大风刮得好开心,/鲸鱼是其中的一个小丑,……海洋!你真是个……爱闹、爱哄骗戏弄的家伙”(610),这首轻松活泼的歌曲把可畏的鲸鱼和大海比为小丑和爱闹的家伙,将危险和死亡当作儿戏,具有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色彩。
《白鲸》中的传说为这部史诗式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增添了超凡神秘的色彩。如第14章老鹰引导印第安人到南塔克特岛定居的传说可视为一个创世神话,老鹰是神灵的化身,引导人类来这里开辟新生活。在印第安人神话中,麝鼠、龟、郊狼和鹰等具有神力的动物创造了世界和人类(高歌、王诺,2006:24)。这些神话表明印第安文化对大自然神灵和万物的敬畏。作者认为“自然界中没有禽兽,万物都是有灵魂的存在”(Sanborn,2014:17),他的观点和印第安人的万物有灵论不谋而合。《白鲸》也展现了一个有灵魂、并非只有物质存在的自然,埃哈伯因亵渎神灵和大自然而丧命的悲剧揭示了人类需要敬畏大自然、同它和睦相处的道理。
作者认为捕鲸叙事本身也有传说色彩,因为多数捕鲸事迹在公共档案中没有记载(266),它们得以传播靠的不是文字记载,而是口头流传。事实上,《白鲸》的构思是基于19世纪早期太平洋一头叫作摩卡·迪克(Mocha Dick)的抹香鲸的传说。谣传中它像魔鬼一样凶狠狡诈、神秘。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化都有魔鬼的传说,人和魔鬼的关系是西方文化中的常见话题,比如浮士德和魔鬼的故事成为一些作家的创作素材。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魔鬼之说在北美找到了特殊的滋生土壤。它的荒野莽林及其动物让早期移民感到恐怖。这种恐怖具有神秘色彩,不能看见但能被感知,是内心的恐怖幻觉(程巍,2007:43)。荒野在北美大量存在,对早期移民来说具有双重意义。新世界虽然险恶可怕,却充满自由,为人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因为他们要生存下来,必须依靠毅力、勇气和智慧才能战胜生存的威胁,所以荒野“逐渐从一种地理空间上升为一种审美意象”,成为19世纪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冯月季,2018:77)。《白鲸》中的荒野意象是大海,它的荒蛮神秘孕育了人们的恐怖心理和白鲸的传奇色彩。白鲸被视为上帝的化身,超然神秘,无处不在,但它对人的敌意和狠毒狡诈又与恶魔无异,对人的生存构成威胁,这样小说将人与动物较量的故事提升到人神或人魔之战的史诗高度。
埃哈伯和《圣经》中一位亵渎上帝、十恶不赦的古以色列国王同名,他自己也有神秘的传说色彩。他喜欢离群索居,出场前有关他的各种传闻制造了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也让人对他产生一种捉摸不定和害怕的心理,如“他没有病”“也不健康”“是个怪人”“了不起的,不信上帝又像上帝似的人物”“喜怒无常到了极点”(117-118)。埃哈伯身上那条印痕到底是受伤导致的还是与生俱来的,水手们也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它强化了他天生堕落的邪恶形象。他丧心病狂地追杀白鲸,在船员和他自己眼里,他和白鲸已经合二为一,“成了恶魔”(218)。小说开头作者提到希腊神话中纳克索斯(Narcissus)因沉迷水中自己的身影而溺水身亡。白鲸正是埃哈伯水中的倒影,是让他痴迷、“捉摸不住”的魅影(29)。为了复仇,他专门锻造一支锋利的镖枪,并用几个异教徒镖枪手所献的鲜血去淬钩尖为它举行洗礼,吼道:“我不是以天父之名,而是以魔鬼之名为你举行洗礼!”(595)这种巫术般的仪式让他俨然是一个反基督的魔鬼。
《白鲸》的传奇元素、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人物的半文明半野蛮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冒险主义和英雄主义使小说含有美国边疆幽默的色彩。边疆幽默植根于美国民间文化,是人们在恶劣艰苦的边疆生活中的一种解脱方式。擅长此道的马克·吐温说他讲故事的方式是“口头讲述,不是书面——是美国原创的,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做到如鱼得水”(唐文,2019:105),这说明边疆幽默具有典型的美国口头文化特色。边疆幽默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大话故事(tall tale),源于19世纪初美国一种基于历史人物或民间英雄的幽默讽刺性故事,其主角(包括动物等)具有超凡的力量、勇气或智慧(虞建华,2015:220)。它经常涉及边疆拓荒生活,初为口头流传,后来逐渐出现在《时代精神》(SpiritoftheTimes)等纽约著名的时尚周刊上,该周刊因为刊发过许多边疆幽默故事而在全美广受读者欢迎。梅尔维尔小时候喜欢听一些年长的亲友讲奇闻怪谈,后来他当了水手,航海生活的危险艰辛、寂寞枯燥远甚于边疆生活,讲故事、说笑话便是水手一种消遣娱乐和缓解压力的方式。除了口头来源,作者也阅读书刊上的大话故事,像幽默作家索普(Thomas Thorpe)发表在《时代精神》的《阿肯色的大熊》(TheBigBearofArkansas,1841)对《白鲸》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Grobman,1975:20)。
大话故事的主要特征是大量运用夸张手法对人物或者地方习俗进行描述,以“达到或恐怖、或浪漫、或幽默的艺术效果”(唐文,2019:109)。像《阿肯色的大熊》的主角在吹嘘他家乡的风土人情,《白鲸》也有炫耀美国捕鲸业的夸夸其谈。例如,“尽管这世界轻视我们捕鲸人……在全球点燃的所有小蜡烛和灯盏,与燃点在许多圣殿前的巨蜡都得归功于我们!”“美国的捕鲸人的总数如今比全世界其他结伙的捕鲸人加起来还要多”(147)。《白鲸》盛赞美国捕鲸业的话语表现了作者对美国这个新生民族的自豪感。值得指出的是,“民间的吹嘘总是反讽性的,总是在多多少少地自我嘲笑”(巴赫金,1998:182)。作者对美国捕鲸业既有肯定的一面,也看到它具有美国资本主义扩张的侵略性和掠夺性,埃哈伯的疯狂行为正是这种侵略性和掠夺性的表征。
边疆幽默的又一特征是常有欺骗和恶作剧的场景。因为早期美国边疆的生存竞争残酷,社会秩序混乱,人们为了生存,尔虞我诈的现象很常见。有论者将大话故事与19世纪美国口头文学中的“恶作剧”和“骗局”联系起来,认为吹牛皮、说夸张荒诞故事是边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周静琼,2009:69),他们也以此来愚弄外来者或不明就里的人,多为来自东部的未见过世面人,也有来自欧洲的。实际上,当时欺骗在美国到处存在,成了美国幽默的一部分,“人们把欺骗的丑恶编入笑话,甚至认为欺骗非常好玩。幽默减轻了欺骗的丑恶,就像月光把西部城镇横七竖八的街道美化了一样”(坎利夫,1985:148)。《白鲸》不乏这样的场景。如第91章斯德布利用法国船的船长不懂英语和自以为是,对他戏弄一番,还骗走了他的鲸鱼。边疆的艰苦环境使人们更注重实用,排斥浮夸没用的文雅和学识,这种环境为美国人(或美国民族文化提倡者)讽刺文雅造作的精英文化(欧洲文化)提供了场所。斯德布这个粗鲁的美国佬智胜穿着体面却无知的法国船长,暗含作者对一向有优越感的欧洲文化的讽刺,也透射出美国资本主义扩张中巧取豪夺的一面。
《白鲸》的美国民间文学元素体现了梅尔维尔对普通民众和多元文化的关注,但在19世纪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其作品的价值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作者去世时可谓是默默无闻。到了20世纪初,古典高雅的精英文化(如欧洲传统)逐渐让渡于大众文化,他的作品逐渐得到人们重视,“成了美国文化的一个新的标识”(张科,2020:88)。
结 语
早期美国绅士派文人的创作常被国内外人士视为过于文雅,欧化气息太浓,缺乏创新,缺乏美国气质。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期待看到一种美国本土文学。梅尔维尔(Melville,2002:527)提倡民族文学独立,称“与其模仿得成功,不如独创而失败”,要“像个美国人那样地来写作”。美国民族文学建构必须将美国本身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白鲸》利用捕鲸业这个具有本土特色的题材进行民族叙事,并融入演说、布道和民间文学使小说的思想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生动逼真,反映了美国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民族精神风貌,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白鲸》蕴含丰富的民族文化积淀,体现了作者对本土口头文化传统的利用和对民族文学建构所作的努力,给读者带来一种新鲜感。本文证明了基于美国本土文化的研读能深入地分析梅尔维尔作品有别于欧洲文学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以及它们和美国文学、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
注释:
① 本文主要引文出自梅尔维尔.2001.白鲸 [M].成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略有改动,以下仅标注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