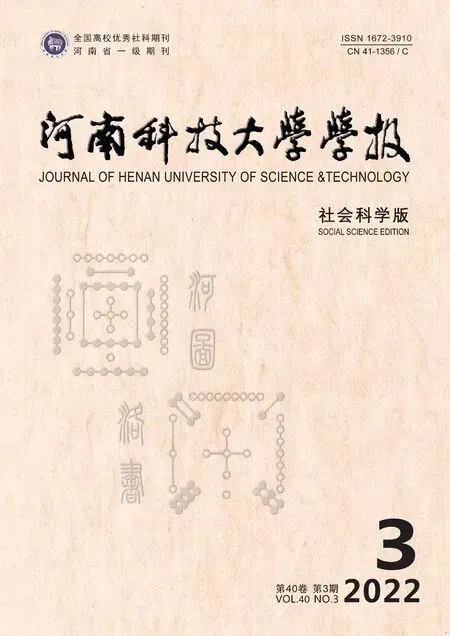多重生命视角下道教诗词的审美境界
——以金元全真诗词为中心
郭中华
(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道教文人的审美活动,视阈十分开阔,天地万物、世俗人情、生机道法等,有形、无形之物均在审美之列;审美视角亦丰富多重,既有有形的具象审美,又有无形的宗教修行体验式的抽象审美。但就其核心与本质而言,道教文人的审美活动最终可归结为生命的审美,其关注的重点是生命价值与境界的实现和提升。正如余虹在其《禅宗与全真道美学思想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任何宗教都必须悬置一个理想的境界,它是宗教信仰的终极关怀,也是宗教修养之目标与归依。”[1]金元时期全真道教的生命理想境界,就是明心见性、成真证仙,实现生命境域的开拓与超越。而这一生命境界追求,也是其诗词作品的审美理想。具体到诗词创作上,这一审美理想与境界表现为生命归置视角下的“天人合一”、生命修养视角下的“性命圆融”、生命价值实现视角下的“真善美相统一”等三个方面。
一、生命归置视角下:天人合一
道教的终极生命目标是得道成仙,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就是要通过修道、悟道、证道、与道合一。这一过程在道法的视角下,就是从“五行”“六道”之中回归生命的本源之处;在生命归置的视角下,则是从“天人相离”走向“天人合一”。在修行者看来,实现“天人合一”无疑是对自我生命最好的安置。金元全真教诗词对“天人合一”这一审美境界的阐释,主要从有形层面的回归自然林泉、无形层面的与道合一两个方面进行展开。
(一)回归自然林泉
全真宗师笔下的“自然林泉”,是与尘俗天地相对立的淡绝尘味又深浸道性的客观时空存在。对自然林泉的回归,全真宗师首先展现的是对林泉天地的审美参悟,着重对林泉之中深浸的理趣与道法,进行审美发现与体证,为自我的回归寻找清晰的方向与充足的动力。全真道教的这一审美风尚首创于教祖王重阳。
王重阳在其诗中说:“自然认得三光秀,决定通和四序春。外假莹明内真乐,凡人不觉做仙人。”[2]8“三光秀”所指不仅仅是日、月、星的明亮与辉耀,亦包含其高居霄外,恒常不变、独立不改的精神品质,此皆深切道法。所以王重阳又说:“精神炁候谁能比,日月星辰自可同。达理识文清净得,晴空上面观虚空。”[2]9道教讲求对自我精气神的调适和炼养,基本的方向就是回归清净自然;而远离尘嚣的日月星辰,不着尘情、无待无恃,无疑深切于自我调持之理趣。可以看出,作者对日月星辰及青霄的观察与审美,不着意于外趣而用力于内理。马钰《题文登于疃于庵主契遇庵》诗曰:“好山好水好松竹,契遇庵前清我目。福地堪名锦绣川,洞天宜盖仙家屋。”[3]29和王重阳的审美参悟相比,马钰的体认与感知更显具体与切实。他对山、水、松、竹的审美感知均着一“好”字,主要体现在“清我目”上,即能清新自我的视角感知。由如此“好”的山水松竹构置而成的林泉天地堪称福地洞天。“洞天宜盖仙家屋”一句语则把自我回归林泉的审美决断直白托出。谭处端《踏莎行》词有云:“静静清清,天长地久,春花秋月坚坚守。腾腾兀兀向前行,昏昏默默合着口。”[4]56自然天地,静静清清,不言不语,却可长久存在,亘古如一;春花秋月,年年如旧,却从不失信爽约。它们在时间的流转中,坚守自我,不辍前行与运转。这样的精神内质对修道之人来说,无疑有着莫大的启迪与警悟。又如刘处玄《蓦山溪》词、丘处机《易州西山睒公堂》诗、于道显《幽居》诗等,皆在阐释此类审美参悟,是全真宗师对天地自然有形之中所蕴含的无形理趣与道性的深切认知,对自我宗教修行与境界提升有着莫大的启示与促进,亦为自我对自然林泉的回归打下了深刻的审美根基。
在对自然林泉进行一番深刻审美之后,全真宗师便坚定了自我回归自然林泉的认知与决心,并将回归自然视为自我宗教修行的路径与归处、生命境界擢升的阶梯。王重阳诗句“无极云霞为伴侣,半空风月作因缘”[2]12,马钰《赠众道友》诗“长生有路好追寻,譬似无常好歇心。云水闲游寻好伴,自然得遇好知音”[3]18,谭处端《畅道》诗“云水逍遥逐处家,任他乌兔易年华”[4]13及“云水逍遥物外仙,闲闲静静本来天”[4]13等诗句之中回归云水的审美理想逍遥、闲定的审美心境清晰而彰显。
刘处玄词《满庭芳》传达了同样的审美理想与境界:“今日山林且住,他时去、高卧云烟。洞天隐,松峰之畔,保命是修仙。”[4]129从今日的山林且住,到他日的高卧云烟,再到洞天隐逸,作者审美心路历程清晰可见,审美理想也明确突显——回归林泉、得道成仙。其《神光灿》词:“他日功成厌世,效渊明乐道,闲伴林泉。自在无拘,笑吟洞外松前。”[4]131回归林泉、进而获得自在无拘之境的审美表达亦可谓深蕴独具,全真宗师对陶渊明归去情志、隐逸境界的欣赏和推崇亦明白可见。
历代道教文人是类诗词并不鲜见,作者或显或隐地把自我回归林泉的审美理想进行阐释,揭示林泉摒弃喧嚣、淡绝浮华的天然理趣,为自我审美理想的表达提供了立论的基点与动因。这也为世俗文人山水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审美指引与思想借鉴,更增加了中国山水诗词的哲思与内涵。
(二)与道和合
在天人相合一的修行及审美实践中,回归林泉只是浅层有形的回归与融合。天人最终的和合,则是与道法的和合,和合于道、融归于道,实现生命的终极超越而逾入仙境。与道和合,是天人合一的终极形式与结果,也是道教文人生命审美的最高理想与境界。王重阳《磨镜》诗堪称对此境界的绝好表达:“磨镜争如磨我心,我心自照远还深。鉴回名利真清净,显出虚无不委沉。一片灵光开大道,万般莹彩出高岑。教公认取玄玄宝,挂在明堂射古今。”[2]5该诗以磨镜的实践比作炼心的修行。磨镜要磨除锈蚀,炼心要剔除名利;锈蚀除则镜面清亮,名利尽则内心清净。清心净意则道法可证。颔联中的“显出虚无”则寓示与道相合。颈联与尾联所述就是与道和合后的审美感受。
王处一《望蓬莱·述怀》词与道和合的审美境界十分显现:“天之道,妙用不虚传。一点生成真法性,二仪炼就出尘仙。随步结金莲。明明了,颠倒显根源。四大扶持真水火,五光照彻九重天。七祖尽朝元。”[4]364
该词上阕开头两句便交待了整词叙写的核心:“道之妙用”,此妙用作者概括为“不虚传”三字,说明其有着切实的合道体验。后面的内容皆可视为合道后的审美体证,包括发明真性、脱尘而仙,显现真源,照彻九天等。这种体证实则就是道法视角下生命审美的最高境界。体证愈美好,愈说明审美境界的高妙。
全真后学于道显《梁老姑告》诗对审美境界的表达同样清晰明了:“学人莫事苦熬煎,大道元来本自然。真静真清成运用,不雕不琢就方圆。五明宫内生芝草,七宝山头长瑞莲。折得一枝归缥缈,瑶池会里荐诸仙。”[5]14这是一首说理阐道之作,阐述的是作者对修道审美的感悟。首联“学人莫事苦熬煎,大道元来本自然”是对道法的深切认知及修行方法的劝寓。颔联“真静真清成运用,不雕不琢就方圆”,是对具体修行策略的阐释,倡导在真静真清、不雕不琢中参悟道法。其中“成运用”“就方圆”深有合道、体道的蕴含。颈联两句,说的是修行之中丹药的采获。尾联“折得一枝归缥缈,瑶池会里荐诸仙”则把采药归仙的终极归宿进行了阐释。采药归仙实质就是对合道而仙境界的展示。不难看出,该诗在生命审美境界上,依然倡导和合于仙道,天人合一。
从回归自然林泉的有形融入,到和合于道的无形归依,这些均彰显和寓示着道教诗词在生命归置视角下审美活动“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而这一审美境界的获得,与道教文人对生命来处与归处的审视是分不开的。具体来说,“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是道教宗师对生命来处与归处进行深刻审视后的理性抉择,亦是道教生命智慧深具超越性的一种体现。
二、生命修养视角下:性命圆融
尊生重生是道教一贯的生命哲学,在具体的生命修养中,无论外丹修持抑或内丹修行,均重视对自我性命的养护。金元时期的全真道教倡导内丹修行,“性命双修”思想亦十分突出,由此也致使金元全真诗词在审视生命修养时以“性命圆融”为理想境界。
(一)何为“性命”
对于“性”与“命”的谈论,金元全真宗师著述中很多。王重阳《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曰:“性者是元神,命者是元气,名曰性命也。”“根者是性,命者是蒂也。”[2]294又说:“神者是龙,气者是虎,是性命也。”[2]294马钰深悟王重阳之意指,他在《丹阳真人直言》中对性命进行总结说:“夫大道无形,气之祖也,神之母也。神气是性命,性命是龙虎,龙虎是铅汞,铅汞是水火,水火是婴姹,婴姹是阴阳,真阴真阳即是神气。种种异名,皆不用著,只是神气二字。”[3]252马钰所论与王重阳一脉相承,揭示了性命乃神气、真阴真阳的本质;同时也把全真诗词创作中“龙虎”“铅汞”“水火”“婴姹”等丹道修行类意象的本质进行了交待。
性是神、命是气的说法终归有些抽象,具体到实际修行中,性指的是无形的精神层面的生命,命指的是有形的肉体层面的生命。性是命的主宰,性对命起着统领支配的作用;命是性的承载,命对性具有保养和护持的作用。《郝太古真人语》中有云:“夫吾道以开通为基,以见性为体,以养命为用。”[4]430《长春真人规榜》亦曰:“见性为体,养命为用。”[6]147所以就生命修行来说,修性与修命不可偏废其一,只有双持双全,方可臻于至境。刘处玄在其诗中对性命的关系进行类比:“性光命似油,灵焰照无休。”[4]104性若为光,命便是油,油充足,光才能明亮,这就道出了命对性的养护作用。尹志平亦有诗曰:“不是性根超造化,如何命宝得圆成。”[5]85此又说明了性对命的提携作用。
鉴于对性、命本质及其关系的认知,全真宗师在生命养护及宗教修行中,十分珍视性命,以突显性命的核心价值。马钰有诗曰:“富贵荣华全小可,于身性命天来大。”[3]3刘处玄《五言绝句颂》有云:“明道泯争爱,真通性命大。”[4]100又说:“清真保性命,爱尽心猿定。”[4]102性命是世人生命的核心价值之所在,所以全真宗师倡导世人要“顿省性命,竞甚人我”[4]113“真修性命,伪养形骸”[4]114“速修性命,暗有贤圣提汝”[4]133“修性命,体延年,别近云霞伴”[4]135。从“顿省”“真修”“速修”的措词上,可明显感受到全真宗师劝化之中情感的真切与急迫。这种真切与急迫,源自他们对性与命深刻的审美与认知,更源自他们对性与命的深切珍视与持重。
(二)圆融性命
金元全真教主张在具体的修行中,将“炼精”“炼气”所得的“命丹”与“炼神”所得的“性丹”和合成性命双全的“金丹”,“金丹”成则仙道可证,追求性与命融合为一的大美之境。
马钰在其《功圆》一诗中,将圆融性命的审美境界深刻地传达了出来。诗曰:“断情割爱没忧煎,绝虑忘机达妙玄。意净心香三处秀,命通性月十分圆。”[3]29诗以“功圆”为题,“功”所指乃生命修行之功,“圆”所指乃生命修行的圆满之态。由题目即可看出,全诗阐述的是生命修行的完美状态。诗前三句是对修行方略的具体交待,包括断情割爱、绝虑忘机、清心净意等。末句则是这种完美修行的具体体现,是“命通性月十分圆”。性命相通相融,则真性之月晃朗而圆融。“十分圆”三字,意在表明性命圆融的审美之境的高妙。
谭处端《满庭芳》词云:“只要君心慷慨,慧刀举、劈破昏蒙。还知否,般般撒手,性命可圆容。”[4]30该词中圆融性命的审美追求同样清晰可见。刘处玄在其《五言绝句颂》中说:“真趣道眸开,善清无祸灾。冲和全性命,蜕壳到蓬莱。”[4]98在这里,刘处玄在传达和合性命的审美境界的同时,亦将性命冲和的结果与趋向进行了揭示,那就是“蜕壳到蓬莱”。这是生命价值终极实现的标志,亦是生命审美的理想境界。刘处玄又说:“至死常清静,忘情完性命。超升免下鬼,大罗朝贤圣。”[4]101又如其《三字歌》云:“汾阳解,性命存,超三界。”[4]108其《上平西》词曰:“清平道德,修完性命隐蓬茅。他年蜕壳朝贤圣,名列仙曹。”[4]129在全真文人看来,性命和合圆融的境界就是仙道境界的映射与实现,这无疑是对生命审美境界在绝对意义上的提升。
性命和合之境,在一定意义上几乎等同于功成丹圆的仙道之境,所以全真宗师倡导向道者,在实际修行中要以保命全性为鹄的。王处一的《劝人弃假归真》诗曰:“诸公好把轮回咄,一志宜将性命全。收拾光明投内补,悟真达本复周圆。”[4]259他的《赠李节判明威》诗亦说:“阴阳颠倒人难见,性命圆成世莫量。法界灵明俱透彻,亘容天外自飞扬。”[4]263丘处机亦在《学仙记》中指出,得道之士皆“内全性命,外逆人情”[6]175。这就促使全真后学在生命修行及审美中,以性命圆融的境界为追求与指向。
前文提到,金元全真宗师认为性命即为神气,性命圆融也即神气冲和。这就致使他们在诗词创作中,多以神气的攒聚来表示性命和合的审美追求。如王重阳《修行》诗曰:“子母相随真彩结,气神攒聚异光殊。”[2]15其《苏幕遮·劝化诸弟子》词曰:“气传清,神运秀。两脉通和,真行真功就。”[2]73这里的神、气皆可作性、命解。谭处端《满庭芳》词曰:“宝鼎祥烟攒聚,神气会、结就灵芝。”[4]30刘处玄亦有诗云:“日用自然真,冲和气养神。意清全癸耀,阴尽碧霄人。”[4]101这类诗词皆是阐述内丹修行的理路之作,其中的神、气或许不完全代指性、命,但其中和合圆融的审美追求却是清晰而明了的。
无论直言性命,抑或借述神、气,在生命修养的视角下,性命双修双全的境界追求并不隐晦。就生命个体来说,“保性”之体与“养命”之用,只有互通互融,才能更好地促使生命价值的实现与超越。这种性命体用互通互融的境界,也正是生命审美的境界。
三、生命价值实现视角下:“真”“善”“美”相统一
在生命价值实现的审美视角下,金元全真道教诗词有着求“真”、求“善”、求“美”的目标追求,亦有着“真”“善”“美”相统一的境界理想。
(一)全真教视阈下的“真”“善”“美”
在全真思想文化体系中,“真”“善”“美”的意指皆有多重性,除包含有世俗的意义外,还有着深层的文化特质。
就“真”来说,其在全真诗词中除具有与“假”相对立的文化意义外,还有祛妄幻、代指仙道与真性等层面的文化意指。金源璹在《全真教祖碑》中说:“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理,释教得佛之心者,达摩也,其教名之曰禅;儒教传孔子之家学者,子思也,其书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传,不行而到,居太上老子无为真常之道者,重阳子王先生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妄幻,独全其真者,神仙也。”[7]“屏去妄幻,独全其真”,可谓把“全真”之“真义”一语道破。刘处玄《上平西》词说:“崇真道,敬真圣,明真理,了真修。”[4]129此处“崇真道”“明真理”“了真修”,皆寓指仙道的修行。谭处端写有《如梦令》词数首,其《赠修武贾信实》曰:“要见本来真,闲里擒猿捉马。”[4]35这里的“本来真”指的就是人的本性、真性,因为它是人天生具有之物,所以称其为“本来真”。无论“祛妄幻”抑或代指仙道与真性,全真教视阈下“真”的文化意指远非世俗之“真”所可涵括,此亦是全真道教名为“全真”的用意之所在。
就“善”而言,在全真著述中除具有与“恶”相对立的意思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含义,它直指纯朴反对雕琢,指纯朴之境下的行为与状态——随缘、无我、无私,讲求“善”的本质与形式相统一,被称之为“上善”“大善”。老子《道德经》第8章云:“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8]老子把“上善”之态形象地比拟为水。水有着随物赋形、因势而动,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等德性,这实则正是水的随缘、无我、无私的特性,所以老子说水德几于道。而上善若水,故上善也几近于道,也具有随缘、无我、无私等纯而朴的深层意涵。全真宗师对善的审美与追求多有上善的境界指向。
刘处玄在《黄帝阴符经注》中说:“如上善,方圆曲直,万派清通,于江河淮济,入巨洋而混成归一,谓之深通。”[4]181这段话是对“天人合发,万变定基”一句的注解。所谓“天人合发”,意指天人相通也,天人相通,世间万化便有了定基。刘处玄以“上善”例举,“上善”之境下,方圆曲直万派清通,就如江河淮济一样,汇流融通,入巨洋而混成归一。江河淮济之所以能够汇流入海,是因为它们的随缘就势无私无为。方圆、曲直、万派这些各有所别的事与物,要想融通为一,就要以“上善”为前提,显而易见,“上善”所指就是一种纯朴、无私的境界,只有在这种纯朴无私的境界之下,各有所别的事物才可以融会贯通。
刘处玄《五言绝句颂》诗中说:“上善应清清,行通似水平。天青悬万象,性阒命光成。”[4]97又说:“念道命光圆,无形性达全。自然通上善,蜕壳是真仙。”[4]100此处的“上善”直接与明心见性、证道而仙相关联。见性、证仙下的生命,自然是复归于纯与朴状态下的生命。显然这里的“上善”超越一般的文化意义,而直指一种无我、无私的境界。于道显在其《寄洞霄宫完颜提点》诗中,亦将“善”之深意进行了深刻揭示:“寄语洞霄客,天姿幸有余。善行本无迹,处世不如愚。”[5]17诗中的“善行”当指真朴状态的所作所为,真朴之下的“行”已无关形式与外在,所以此时之行才为无迹之行。
金元全真宗师倡导“上善”“大善”的生命价值审美,其根本的文化认知与动因,可用尹志平一首七言绝句来概括:“本来一点最孤灵,染着人情万事生。欲要归根清净去,应须返朴入圆成。”[5]83生命原本之境,无粘无着,灵通万息,和合天道;而自染着凡俗之情后,便万事生发,千虑萦心,凝心积虑之下,绝非善境。所以归根溯源,返素归朴,方有清净之味,生命方有上善、大善之圆觉。
对于“美”之内涵的挖掘,全真道教同样有多重境域下的践行。就浅层的意义而言,美与丑相对立,是指能够给人带来愉悦视角冲击的外在审美素质的结合。金元全真宗师对这一浅层意义的阐释多不直言其美,而是以秀、幽、好、胜境等词汇来表示,内容多为对山水风光的外在描写。对于道教文人来说,发现浅层外在美的素质,并不是他们审美的终点。他们的审美目标,是要发现天地万物及生命所蕴含的大美,即“道性之美”。对于天地万物深浸的道性之美,全真宗师在诗词中展现颇多,如全真后学姬志真的《居山》一诗。该首七律展示的是作者林泉悟道的情境,及其对林泉之美的深刻体悟。其中颈联两句意蕴非常:“溪水茂林俱演道”,是说潺潺的溪水,茂密的树林俱在演示天地之道法;“野花飞鸟尽通玄”,是说遍地的野花,穿梭的飞鸟皆能通达自然的玄理。加之颔联“灵岩月窦排幽胜,风伯山灵助法筵”[9]两句,不难推出诗中所传达的,是林泉万物皆含道性的思想主旨。
阐扬生命具有的“道性”之美,是全真教诗词进行生命审美的焦点之一。在道教看来,万物源自于道,人的“道性”与天地道法相融通,是生命价值的核心之所在。修行者“明心见性”证道而仙,实则就是对自我“道性”的发明与回归。生命的“道性”有着尘俗之物所不具有的“大美”。这种“美”是一种内境之美,可使人的精神内在获得一种自足、自适、自在而逍遥的充实与愉悦感。马钰《赠白岩镇鲁周瑞》诗说道:“乐道逍遥豁畅人,自无劳苦与劳辛。洞内炼烹金鼎药,壶中赏玩玉楼春。”[3]58诗中所谓“炼烹金鼎药”就是对自我“道性”的审美与回归,在这一过程中,精神内在获得的是无劳无辛、逍遥豁畅、赏玩春色的美好感受。谭处端写有《长思仙》词数首,其中一首把生命的“道性”之美表现得更为充分:“得玄玄,悟三三,火灭烟消风害谭,昏昏保玉男。趣闲闲,认憨憨,一性浑如月正南,澄澄现碧潭。“[4]52这是一首阐述修行之作,述说的是明心去境,趋闲证憨以见性的修行理路。词末两句“一性浑如月正南,澄澄现碧潭”,表现了自我所见的“道性”之美。此中使用了比喻的手法,把“道性”的美,比作正南之朗月映现于澄湛的碧潭之中。这种无以言传之美,顿现眼前,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刘处玄《山亭柳》词曰:“气结神灵异,自然有、霞彩光生。宝鉴碧霄晃耀,真个先生。”[4]135王处一《赠门人南吕哥》诗曰:“周天数足神丹结,五色威光簇十洲。”[4]265丘处机《玉炉三涧雪·暮景》词亦说:“渐渐放开心月,微微射透灵台。澄澄湛湛绝尘埃。莹彻青霄物外。”[6]88可以看出,这类阐述“道性”炼养与发明的诗词作品所展现的审美愉悦感,皆非来自尘俗事物的外在视觉冲击,而是源于自我修心、修性中的内境体悟。这种“美”毫无外在的依附性、凭借性,而有着自足、恒常的特点,故称之为“大美”。
(二)“真”“善”“美”和合统一
由上述所论不难看出,全真道教作品在生命价值的审美上,倾向于“真”“善”“美”的深层意蕴,且有着“真”“善”“美”和合统一的境界理想。具体到全真诗词,对这一审美境界进行充分展现的作品,多为生命价值得以终极实现的“内丹圆成”之作。这些作品把内丹生成所需要的求真、归善的过程,以及金丹圆成后所展现的超俗之美,进行完整的串联与统一,形成“大美”之中含摄“真”“善”的审美效果与境界。
王重阳《喜迁莺·赠道友》词,颇能映现出生命价值实现下的审美境界追求:
问公为善,这大道无言,如何回转。猛舍浮华,搜寻玄妙,闲里做成修炼。认取起初真性,捉住根源方便。本来面,看怎生模样,须令呈现。
亲见,堪相恋,请向绛绡宫里,开琼宴。会上明明,霞辉万道,射透玉丝瑶霰。一粒宝珠晶莹,衮出光同飞电。彻中边,大罗天归去,永除迁变。[2]81
该词是典型的阐道说理之作,阐述的是内丹修行中的求真而归仙的修持理路。就生命价值审美而言,又是一首追求生命“真”“善”“美”圆融统一之作。上阕所述就是内丹修行中求真归善的过程。“问公为善,这大道无言”交待了归善的需求,“舍浮华”“搜玄秘”“闲里修炼”说的就是对生命之“真”的发明与探寻,去浮华、雕饰,实则也是对“大善”的回归。稍后的“认取真性”“捉住根源”,既是“真”的实现,又是“善”的映射。词之下阕所表现的是自我“真性”发明,大丹圆成后生命的内境之美,如词所描绘“霞光万道”“晶莹飞电”。如此深富“大美”的一粒宝珠,其得来是凭借求真归善的修行努力,所以这颗“射透玉丝瑶霰”的金丹宝珠,就是“真”“善”“美”三者的凝结。
郝大通写有《金丹诗》30首,其第25首曰:“学道先须绝外华,修真养素属仙家。忘情盖为烹金液,息虑都缘桎紫砂。一性朝元攒五气,万神聚顶放三花。从兹得达长生路,永向清霄混彩霞。”[4]427该诗和上述王重阳的《喜迁莺·赠道友》词一致,有着“真”“善”“美”三者相统一的审美境界。首联“学道先须绝外华,修真养素属仙家”开启了整诗的阐述主题:学道、修真。该联同时又引出了“绝外华”“养素”的修行诀窍。颔联承接而来,对学道、修真的主题继续阐发,并点出了“忘情”“息虑”的修行关节。诗的前两联中“绝外华”“养素”“忘情”“息虑”等修行理路,实则就是内丹炼养中抖尽凡尘、独存纯素的归真、归善的审美追求。颈联“一性朝元攒五气,万神聚顶放三花”两句是对前两联修行效果的总结,真性得以显现,阳神得以全聚,这也是归真、归善审美活动的升华,直指性丹的圆融之美。尾联平稳收合,收合于生命价值的实现与超越。“从兹得达长生路,永向清霄混彩霞”,这就把内丹圆融的价值,在长生、永恒的时间长河中进行彻底地激活,同时也把价值审美的境界,在时光无限中进行了绝对的提升。至此,和合仙道的生命大放异彩,在永恒之中作伴彩霞,这是生命至真至朴至素的大美展现。
全真后学于道显《示赵道人》一诗是一首说理阐道之作,其中的价值审美境界同样清晰易见。诗曰:“收拾精神向内观,莫教穷贼外相瞒。六门玄钥尘根断,七返还丹道气攒。玉露降时珠颗颗,金霞飞处月团团。水精楼阁真人位,赤凤乌龟上下蟠。”[5]16不难看出,诗的前两联是内丹修行中归真致璞的审美表达,颈联是生命价值的实现,亦是价值审美中“美”的映射。“珠颗颗”“月团团”,是生命修行中内境之大美,亦是至真至朴的生命精髓共同促生的生命大美。
综上所述,道教诗词的审美境域开阔,既涵括有形天地万物,又融摄无形自然道法,而所有审美活动的展开始终不曾脱离道教实现生命价值——得道成仙这一终极追求。由此对生命的审美也就成了道教诗词审美活动的逻辑起点与终点。不难看出,全真诗词审美境界的展开,是以对生命的审视与探析为基点的,最终的审美指向依然回归到生命的自我实现上。这清晰地展现了道教文人“知来处方知去处”的审美理路与轨迹,也集中展现了道教诗词对生命之美审视的彻底与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