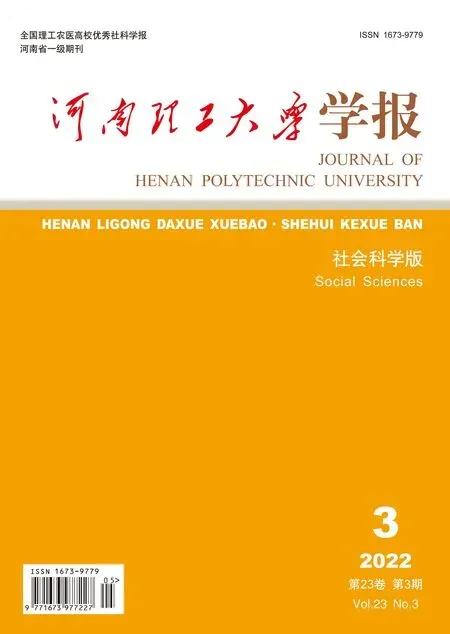父子关系与新旧交替:再论北宋“濮议之争”
杨锐明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濮议之争,始于治平二年(1065),历时18个月,作为英宗初登皇位之大事,不仅影响当朝政事,更是为宋代后期朝政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学界对此事从多方面进行了讨论,其中具有代表性论述有程光裕《北宋台谏之争与濮议》重在论述台谏与宰执在濮议上的对抗[1];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指出“濮议”是曹太后与英宗的矛盾所导致的,朝中由此分成两派[2];张钰翰《北宋中期士大夫集团的分化:以濮议为中心》则是讨论濮议所引发的党争[3];张吉寅的《“水不润下”与北宋濮议》指出“濮议”中的两派,以“水不润下”的灾异理论为中心互相攻讦,既是政治立场的不同,也是新旧思想冲突的体现[4];许玉龙的《台谏群体与宋英宗朝政治》则指出“濮议”之争实质是英宗对仁宗的不满,而参与争斗官员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帝系正统[5];王旭、刘莹的《从濮议看北宋英宗时期的文人之争》指出统治者为了限制文人权势,使用“异论相搅”策略,消除威胁,而“濮议”之争便是这种手段的一次实施[6];王云云的《北宋礼学的转向——以濮议为中心》认为“濮议”是融礼仪、礼制、礼意、礼经为一体的礼学争议问题[7];郭艳丽的《从濮议之争看北宋对传统礼制的承传与变通》指出这场论争涉及北宋王朝对于传统礼制的态度,对立派之间的争论,体现出当时人对于传统礼制传承与变通的态度[8];此外还有袁晓阳的《略论北宋英宗时代的濮议之争》[9]等等,所涉已经非常全面,但笔者发现作为濮议之争的主人公,分析仁宗、濮王、英宗三者关系的文章较少,此外对于仁、英二宗的矛盾也较少涉及,部分文章只是进行事实陈述,或是简略提及仁宗对英宗的影响,并未展开分析。对此笔者将讨论英宗与生父和养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对濮议之争产生影响的,同时指出濮议背后所隐藏的先帝与新帝和新旧朝交替的矛盾。
一、英宗与濮安懿王:亲厚的血缘型父子关系
“濮议之争”向我们展示了两种类型的父子关系,一种是天然形成而不可变更的血缘型父子关系,一种是在实践中后天形成的收养型父子关系。由于二者性质的不同以及其他原因,濮议中血缘型父子濮王和英宗凭借着血缘以及长时间相处,有着良好的感情基础;而收养型父子仁宗和英宗,因为二者之间关系复杂,矛盾较多,使得濮议之争的结局在冥冥之中便已经注定,接下来笔者将详细分析这两对关系是如何对濮议之争产生影响的。
“濮安懿王允让字益之,商王元份子”[10]8708,作为濮议之争的主角之一,英宗的生父,《宋史》列传中载其“天资浑厚,外庄内宽,喜愠不见于色”[10]8708,就是这样性情温厚的人,亲身经历了两次由宗室子到皇嗣。据《邵氏闻见后录》载“真宗时,皇嗣未生,以绿车旄节迎濮安懿王,养之禁中。至仁宗生,用箫韶部乐送还邸。后仁宗亦以皇嗣未生,用真宗故事,选近属,得英宗,养禁中,以至嗣位。英宗盖濮王第十三子,殆天意也”[11]128。一次是真宗朝自身被养禁中,作为皇嗣未承大统;一次是己子作为皇嗣养于禁中,终继承皇位,乃英宗。《宋史》载“周王佑薨,真宗以绿车旄节迎养于禁中。仁宗生,用箫韶部乐送还”[10]8708,周王指悼献太子赵佑,他死于景德初年,之后赵元份的儿子赵允让作为皇嗣教养宫中,直到大中祥符三年(1010)仁宗出生被送出宫。
景祐三年(1036)仁宗在保庆皇太后的劝说下,选宗室子养于宫中。对于宗子的挑选,真宗时遵循了“选近属”的规则,又因为宋代非常重视家族的昭穆顺序,便从关系近的同辈兄弟中进行选择,保庆皇太后在劝说仁宗选皇嗣时亦是“择宗子近属而贤者”[10]8618。此外,也许是出于真宗时期送还允让的愧疚,加之懿王子嗣众多,仁宗便“遣内夫人至濮宫选择诸子,欲养之禁中”[12]90。就这样四岁的英宗与郇国公赵允成的儿子宗保一起被送养宫中,但未被封为皇子。宝元二年(1039),豫王生,英宗便被送回府邸。
嘉祐四年(1059)濮安懿王薨,英宗与其生父允让相处二十多年,父子之情深厚。虽然尚未发现英宗与其生父互动的记载,但从其他史料中亦可推测出二人之间的父子情深。《宋史》载嘉祐七年(1062)八月,“戊寅,立为皇子。癸未,改今名。帝闻诏称疾,益坚辞。诏同判大宗正事安国公从古等往喻旨,即卧内起帝以入”[10]254。英宗被立为皇子,但是依然称疾推辞入宫,在《宋史》中,对英宗推辞入宫的原因没有明确记载,但此事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却有一些线索:“癸未,皇子犹坚卧不肯入肩舆,(赵)宗谔责之曰:‘汝为人臣子,岂得坚拒君父之命而终不受邪?我非不能与众执汝强置于肩舆,恐使汝遂失臣子之义,陷于恶名耳。’皇子乃就濮王影堂恸哭而就肩舆。”[13]167《宋史》所载事件与《涑水记闻》所载的应该是同一件事,原因有二,其一,《涑水记闻》中司马光称其为“皇子”,当是立为皇子后,可知此事在英宗被立为皇子后发生,《宋史》对事件的记载也是立为皇子后,时间吻合;其二,《宋史》载“帝闻诏称疾,益坚辞”,《涑水记闻》载“皇子犹坚卧不肯入肩舆”,两处记载内容相互印证,因此笔者认为此为同一件事。据《涑水记闻》记载可知,英宗入宫前曾于濮王影堂痛哭,可知英宗的无奈和对生父的感情深厚。此外,论说英宗“天性笃孝,昔在藩邸时,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道”[14]140“帝天性笃孝”[10]253等诸多评价,不仅是对于英宗品性的称赞之词,而且侧面反映出濮安懿王与英宗的关系确实亲厚。
二、仁宗与英宗:复杂的收养型父子关系
英宗与其生父关系亲厚,使得濮议中尊称生父为“皇考”的提议更对英宗的心思,这容易理解。然英宗得位于仁宗,却在濮议之争中,始终未显露出对仁宗的回护之意,这又体现了英宗和仁宗怎样的一种关系?又是什么让这对养父子的关系如此复杂?是仁宗对血缘的执着,亦或是英宗本身的无法介怀,种种缘由都让“濮议”变得复杂。
养父对养子疼爱的同时又很无奈和冷漠,就是这样复杂的情感让这对父子感情淡漠甚至互相防备。仁宗久无子嗣,便循真宗故事于景佑三年(1036)在宗室内选子养于禁中。宗室赵允让之子赵宗实(即英宗)便被抱养宫中,时四岁。英宗入宫,仁宗心情复杂,既是喜爱,但又并不亲厚,而更多的是出于无奈。英宗不是亲生子,却不得不养于宫内,而养子的存在只是象征意义。犹如多年后司马光奏闻的那样,“但愿陛下自择宗室仁孝聪明者,养以为子,官爵居处,稍异于众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属,以系远近之心”[15]4722。养子只是为了安民心。对于英宗,仁宗也曾对曹皇后语:“吾夫妇老无子,旧养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各已长立。朕为十三、后为滔滔主婚,使相嫁娶。”[16]18亲切称其为十三,为他操心婚嫁事宜,也有“上及皇后鞠视如子,既出还第,问劳赏赐不绝,诸宗室莫得比”[15]4406的记载,以显示这位曾经的养子是与众不同的。然而更多的是漫不经心的对待,以致初为皇子的英宗“居禁中,其时先帝为左右奸人所喋,不无小惑。内外之人,以至陛下旧邸诸亲,无一人敢通信问者。陛下饮食悉皆阙供,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晓夕惶恐,百方为计,偷送食物之类者甚多”[15]4879。身为皇子却无人敢与其亲近,甚至潜邸亲人都避之不及,此外就连基本的衣食也是短缺的。若不是仁宗的冷漠猜忌,内侍又怎会有如此胆量来苛待皇子;如不是仁宗心存芥蒂,岂至于曹皇后作为英宗名义上的母亲竟不敢公开表现对儿子的关心。仁宗对英宗的苛刻、冷漠有目共睹,不仅时人如此认为,今人研究中也持相同观点,这就不难解释英宗在濮议之争中对仁宗的冷漠态度。
英宗被立为皇子的过程十分坎坷,即使最终继位,也依然没有安全感。养父没有给予养子应有的情感付出,也就不难想象养子对父亲的冷漠了。英宗从四岁接进宫,到豫王出生被送出宫,始终未被承认是皇子。直到仁宗儿子相继死亡,生子无望,加之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又范镇、司马光上书请求立储嗣,随后许多臣僚都上奏请立皇子,如包拯、吴奎、赵概、欧阳修、韩琦等。直至嘉祐六年(1061)十月才起复英宗为知宗正寺,嘉祐七年(1062)在韩琦、欧阳修等宰执官员屡次进谏之后,才立英宗为皇子,改名为赵曙。在此过程中英宗也数次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不屈于命运对自己的安排,据《长编》载,英宗在被任命为宗正时便已经是四次推辞,即便是要立其为皇子也是坚持不受,便有了“己亥,从古等言皇子犹固称疾。是夕,使者往返数四,留禁门至四鼓,皇子终不至,乃诏改择异日”[15]4776的记载。
皇子之位确立,收养事实已定,养父依然不甘心养子继承自己的地位,因此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也就使得英宗在濮议中也不想履行自己尊称的义务。仁宗最终也没有放弃让自己亲生子成为皇帝的希望,从私生韩虫儿案中便可窥探一二。据欧阳修留下的案件记录载:“去岁(嘉祐七年,1062)腊月,上闲居,见一宫婢汲井,有小龙缠其汲绠而出,以问左右,皆云不见。上独见之,以为异,遂召宫婢视之,乃宫正柳瑶真之私身韩虫儿也。其后柳夫人宿直阁中,明日下直,遣虫儿取夜直坐塾。上独处阁中,召而幸之,遂有娠。”[17]18仁宗宠幸宫人的原因是宫婢身有异象,是皇子降生的祥兆,表明仁宗对亲生皇子的执着。韩虫儿嘉祐八年(1063)正月传出有孕,到皇子(英宗)迁入宫中(嘉祐七年八月)仅五个月,使得英宗心生疑惧。如若不是嘉祐八年(1063)三月三十日午夜,仁宗崩,待到韩氏如期产下皇子,仁宗必会让亲生子取代养子赵曙。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英宗定会处于尴尬境地,初次送回潜邸因年纪还小并没有什么怨言,那二次送回就会使成年的英宗颜面扫地,成为天下谈资,更有甚者为了确保小皇子的顺利继位,同时扫清日后潜在的威胁,英宗极可能会陷入残酷的政治迫害乃至丧命。案件的最后韩虫儿并未诞下皇子,被“决臀杖二十,送承天寺充长发”[17]19。糟糕的情况并未发生,但确让英宗因“韩虫儿事籍籍不已”[17]18。可见仁宗虽死,却给英宗留下了祸患,养子对于养父的怨气更深。
上述英宗在两次入宫所受到的冷漠待遇,立皇子过程中仁宗所表现的反复迟疑态度,以及成为皇子后继承权依然受到质疑等情况,让仁宗和英宗的矛盾不断加深。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但养父与养子的矛盾并没有随着其中一方的死亡而减小,反而在增加,这就使得英宗在濮议中始终缄默其口,用行动来支持尊其生父为“皇考”的宰执官员。
长期的身体疾病困扰,容易让人产生心理疾病,让病人处于敏感多疑的状态,也是英宗对仁宗冷漠的原因之一。史料多处载英宗“不豫”、继位前也是称疾不入,继位后“忽得疾,不知人,语言失序”[15]4795“上疾增剧,号呼狂走,不能成礼”[15]4795,虽有故意说辞的情况,但身体疾病应该是存在的。如此英宗更是多疑敏感,而朝臣屡上奏疏让其尊崇自己怨怼的养父,更是让英宗产生反叛心理。就如《长编》中司马光、王珪等所说:“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15]4971一句“先帝之德”可能刺中英宗之逆鳞,上奏大臣都认为尊亲之前首先要明确英宗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仁宗对其施以恩德的结果,也就是说仁宗的功德是超越英宗生身父母的,此外还有诸多大臣上奏疏(例如吕诲),让英宗感恩先帝,无形中让敏感的英宗加深了对仁宗的怨怼之心。
此外,养父的成功又无形中给养子施加压力,《北窗炙輠录》载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18]无论此话中的褒贬,仁宗作为官家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这就给后继者英宗带来了压力。英宗想要摆脱前者,就要降低仁宗的地位和影响。仁宗作为前统治者的地位已经不能改变,就只能从与英宗的关系上做出变动,称其为皇伯而非皇考便成为了最好的选择,故濮议之争可以说是二帝矛盾的必然结果。除了对仁宗称呼的变化,英宗早在此前便有所行动,嘉佑八年(1063)十一月,司马光曾上言“臣切见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亲其礼,使宗正卿摄事,臣切惑之”[19]1010。要求英宗亲临虞祭,不得对仁宗亡灵过于无礼,但是第二天继续上言“今日礼仪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复使宗正卿摄事,在列之臣,无不怅然自失”[19]1010。可见英宗虽然没有拒绝司马光的要求,但是也并没有出席参加虞祭仪式,表明早在濮议之前,英宗就已经表现出对仁宗的轻视,并释放出了自己想要摆脱前者的信号。在濮议之后,为了继续降低仁宗的存在感,英宗开始对仁宗的子女出手,首当其冲的便是其主婿李玮,将其移到外镇,傅尧俞的《上英宗言李玮不当外移奏》认为“大行皇帝举天下而畀之陛下,顾念恩德,岂有既乎!其所以累陛下者独数女耳”[20]1050。英宗应当善待仁宗子女。养父的光伟形象让养子不得不在其故去后,通过各种方式来削弱这无形的压力。
濮王与英宗之间感情深厚,与之相对仁宗和英宗感情淡漠且矛盾丛生,不同性质的父子关系,由于内部和外部的作用,对濮议之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看似简单的“皇考”与“皇伯”的礼制之争暗藏矛盾,在矛盾的作用下,宋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旧二帝与两朝更替使得仁宗朝完善的台谏制度产生变化,同时期形成的“共治”局面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走向破裂。
三、新旧之争的影响:帝后矛盾及旧朝格局的破坏
在濮议之争中,“皇考”派获得胜利,旧朝终是服从于新朝走向改革。濮议,既涉及礼仪之争,又是一次政治事件。对濮王是“皇考”还是“皇伯”名位的争议,既是朝臣们对新帝政治倾向的试探,也是英宗为选拔新朝班底而对朝臣们进行的考验。先帝与新帝的矛盾,使英宗不会百分百遵循仁宗的治世理念,甚至会对持有仁宗理念的官员加以排斥。
先帝与新帝的矛盾作用于濮议之争,使得“皇考”派最终获得胜利。英宗治平二年(1065)“夏四月戊戌,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15]4957,濮议之争正式拉开帷幕。围绕英宗如何称呼濮王的问题,使朝中划分为两派,一派以台谏、两制以及礼官为主,称“皇伯”派,另一派以中书官员为主,称“皇考”派,两派相论甚久,甚至到了互相攻讦的地步,直到治平三年(1066)太后内降手书,赞同了对濮安懿王的称亲之举,紧接着英宗下诏称濮王为皇考,同月又制定了尊奉濮王的典礼。似乎至此大局已定,但以司马光为首的“皇伯”派,并没有善罢甘休,相继上言,无果。随之而来的便是吕诲罢言职出知蕲州,范纯仁、吕大防于同年三月亦罢言职,而与宰相意见相合的傅卞、刘庠、吴申等相继出任台谏言职。“皇考派”的胜利,先帝与新帝的矛盾起着影响作用。此外,英宗对台谏官员的处置也暴露出其并不像仁宗一样,善纳人言;对台谏官员的替换对仁宗朝渐趋完善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架构产生破坏。
新旧之争,也是引发了帝后矛盾的因素之一。对“濮议之争”中矛盾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英宗与曹太后关系的矛盾上,却忽视仁宗和英宗的矛盾同样是引发前者矛盾的重要因素。英宗作为养子应该对自己的养父尽孝,但是仁宗已经西去,曹太后便要代替仁宗享受双份的孝道;更何况曹太后在英宗生病期间代管朝政,稳固了英宗的地位,英宗理应亲近曹太后,然而英宗却在病中及濮议之争时与太后不睦。凡此种种在世人看来皆是帝后矛盾,但实际上曹太后所代表的是仁宗的“旧政”。新帝登基肯定是想要摆脱先帝的影响,曹太后及她的掌权就像是仁宗的权力遗留,为此英宗便将对仁宗的怨怼迁移到曹太后身上。《长编》载“皇太后事先帝日久,稔详治道”[15]4867,指出曹太后陪伴先帝时间长且熟悉治世之道,此“治道”便有可能受到仁宗治世的影响,就意味着曹太后掌权的宋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朝,而是旧朝的延续。此外欧阳修等大臣在劝说曹太后还政时,言“仁宗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驾,天下禀承遗令,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12]91。即便是解决太后还政问题,都还要搬出已故的仁宗,可见仁宗余威之大。
两帝矛盾引发的新旧之争,同样也暗含着危机。旧有仁宗朝享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并历时四十二年之久,《宋史》仁宗本纪载:
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缯絁。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吏部选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终身不迁。每谕辅臣曰:“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用辟乎!”……《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10]250
仁宗一能心怀敬畏与民共情[21],以身作则为天下作榜,二能以仁义治国,拒用酷吏,三能君臣一体,共筑王朝之基石,因此恭俭仁恕的赵祯当之无愧地享以“仁”为其庙号。仁宗朝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共治”,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与完善,皇帝、宰执、台谏大致构成了中央政府中的三角,皇帝握最高立法权,宰相握最高行政权,台谏握监察之权,三者互相限制,互相倚赖,便构成稳固的中央政府架构,形成“共治天下”的局面[22]。然濮议之争使得台谏的相对独立性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体现在:台谏与宰执之间的关系在英宗朝时经历了由相互独立合作到台谏逐渐受到宰执影响,且濮议之后所任命的台谏官员苏寀、吴申、蒋之奇、刘庠等,都是与宰执合意的官员[5]。台谏制度的破坏正是由宰执与台谏的相互攻诋和台谏任用的以私不以公引发的,任何制度的破坏都不在一朝一夕,而是长时间累积的结果[23],这也是英宗朝衰落的开始。仁宗时的谏言风气,在此时已然开始被破坏。如濮议之争,台谏官对英宗极力谏言,试图让新朝像旧朝一样受到台谏部门的监控,从而保持皇帝同士大夫共治的局面,随着皇帝罢免范纯仁、吕大防等台谏官的言职,这似乎已经不太可能;新旧朝矛盾使得原有的政治格局被破坏,新旧交替之危机浮现,而因濮议之争荒废近十几个月的朝政,仅是矛盾危机的冰山一角。
可以说濮议之争是新旧之争的必然结果。顺势利用濮议之争,通过改任台谏官员的方式,打破“共治”及仁宗朝的皇帝、宰执、台谏三足鼎立的局面,招揽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是为英宗的真实目的。英宗作为养子且晚期才被立为皇子,在朝中信任和可用的人本身就少,而旧朝势力根深蒂固,只有瓦解旧朝势力打破旧时格局,才能摆脱旧朝的影响,完全地掌控朝政。此外仁宗在位四十年,积弊较多[10]251,而改革既能革除旧朝积弊又能聚集新朝力量,相比于正常继统的皇储而言,似乎对英宗来说更为合适。
四、余 论
总之,濮议之争持续时间长,牵扯人员多,作为濮议之争的核心人物——仁宗、英宗和濮王贯穿事件始终,英宗与生父濮安懿王血浓于水,感情深厚,与仁宗矛盾丛生感情复杂,都是濮议中,英宗偏向濮王的重要原因。自从英宗四岁入宫,以及后来的出宫再成为皇子过程坎坷复杂,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对英宗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成为皇子却依然要面临继位的困境,仁宗对皇子英宗的不重视也使得英宗压力倍增,宗室成年男子都是英宗的潜在对手,同时仁宗仁明之君的风评,对英宗产生了较大的心理压力,也会让英宗自然而然地对仁宗产生不满。
不同性格的人有不同的行事风格,就会形成不同的朝堂,仁宗性格柔软,就会包容异见,英宗寡言却坚持己见,势必会让新旧朝形成不同的政治环境,而身处新旧交替的大臣,就势必要做出改变来平衡。大臣是否愿意走出仁宗朝的工作舒适圈,融入新皇的变革中,成为新朝面临的问题之一。同时,英宗也是一位愿意励精图治的皇帝,亲政次日便招来众臣询问“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年老的富弼已然没有了当年的雄心壮志,竟搪塞“恐须以渐厘改”[6]4868,并没有提出任何的改革意见;其后宰相韩琦面对改革的难题,提出尊崇濮王夫妇的礼遇问题,竟对改革决口不提,其目的是否为了转移朝廷上下焦点,便想用濮议之事来拖延英宗改革的步伐,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此事确实占据了帝王和朝臣的诸多时间,荒废了诸多政事。“濮议”随之成为英宗朝的主要“政事”,对于朝臣来说礼制问题的探讨不会触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然一旦改革必然触动现有的某部分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就像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等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改革触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看来就有理由认为濮议之争很可能是朝臣为了拒绝改革的缓兵之计。此外从濮议之争所历时长和激烈程度来看,仅仅是礼制的变通就如此的困难,更何况是多年积弊;由于濮议之事,英宗虽然没有实现变革的愿望,但是似乎也在这场争论中排除了异己,将不听话的大臣赶出了权力的中心,留下了忠于自己的人。此举削弱了台谏的舆论监察力量,增强了宰执的行政权力,而宰执又是听命新主,无异于就是增强了皇权,方便权力的集中,尽管在英宗朝没有发挥其优势,却意想不到地为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减少了阻力,真可谓无心插柳。
濮议之争作为英宗朝最不可忽视的政治事件,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同的父子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成为事件的导火索,而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皇权加强是整个古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权力的集中有利于政令的通行和朝廷的改革,但又容易滋生专权之弊,新旧朝的更替是对权力重新洗牌的好时机,英宗确实抓住了机会,奈何英年早逝,其抱负雄心也只能由其子孙来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