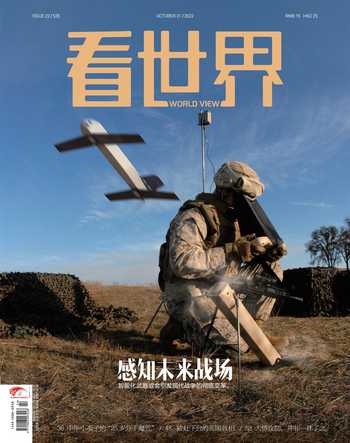长亭外、古道边,忆叔同
怜青

1919年,弘一法师在杭州玉泉清莲寺留影,此时的李叔同出家不久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在今年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一曲《送别》响起,舞蹈演员携柳而出,各国运动员依依惜别,曲中之意让人动容。
《送别》传唱百年,被无数歌手翻唱。狂傲不羁的摇滚乐队唐朝为之倾倒;歌手朴树曾说,如果这首歌是他写的,那自己死而无憾。
歌词的作者名为李叔同,出家为僧后,法号弘一,今年10月13日正是其逝世80周年纪念日。
出身富家的李叔同,是国内较早旅日的留学生,在戏剧、美术、音乐、宗教等领域都有建树。他在日期间所创的春柳社,开启中国近代戏剧先河;其师法西洋的美术思潮,深刻影响了丰子恺等一大批优秀画家;而他创作的一批学堂乐歌,更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里程碑。
1880年,天津桐达李府,时年67岁的李筱楼迎来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这个孩子被取名为文涛,字叔同。
父亲李筱楼年少时与李鸿章、吴汝纶齐名。他为人正直,在吏部主事的官任上辞官经商,终成一方巨富,又因笃信佛学,乐善好施。但在幼子出生5年后,他驾鹤西去。

李叔同早期书法
李叔同13岁时以书法闻名乡里,3岁时奥地利公使赠给李家的钢琴,让他自幼对西方音乐也有所涉猎。不过,17岁那年,因赞同戊戌维新,他被目为康梁同党。
变法事败后,他不得已避居上海。火车一路南下,黄河决口后,蔓延数省的灾民惨状给了李叔同很大的冲击。黄浦江畔,十里洋场,李叔同在这里度过了8年时光;北望京津,那里经历了庚子国变,清廷主权进一步沦丧,但租界内依然灯红酒绿,歌舞不休,这让李叔同深感不安。
17岁那年,因赞同戊戌维新,他被目为康梁同党。
沪上岁月里,李叔同开始将艺术与救国的抱负相结合。他先是与任伯年等创立“上海书画公会”,后与黄炎培等成立“沪学会”,宣传进步思想。
这期间,他写下了《文野婚姻新戏册》的剧本,其创作的《祖国歌》广为传唱。
1905年,沪学会遭到打压,又恰逢生母仙去,李叔同扶柩北归。但因其母为妾,族人以礼法为由,不愿让棺椁从正门入,李叔同非但不理会,反而将钢琴搬到母亲灵堂中。
“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李叔同用一首名为《梦》的歌谣送别了母亲,也宣示着他与旧家庭和礼法的决裂。
“富贵终如草上霜。”接连的变故让26岁的李叔同越发理解自己15岁时写下的这句诗,遂毅然东渡日本求学。
来到日本后,李叔同备考东京美术专科学校。他写下《图画修得法》和《水彩画法说略》两篇美术论文,在同盟会月刊《醒狮》上发表—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介绍西洋油画和水彩画知识的文章。
1906年,李叔同考入该校西画科,拜入著名油画家黑田清辉门下学习绘画。《清国人志于洋画》的报道,见诸日本报端。
求学期间,他曾两度参与在日本久负盛名的西洋画美术团体“白马会”年展,“新奇独特的画法”也给日本评委留下了深刻印象。1911年,东京美专第11期西画科的优秀毕业生中,自然少不了李叔同的名字。
除了绘画外,李叔同在戏剧方面的探索,同样赢得了满堂喝彩。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一种名为“新派剧”的戏剧形式引领着该国的风潮:其将日本传统歌舞伎表演与西方经典小说内容相结合,是日本当时社会团体宣传的重要载体。
在舞台表现上,新派剧开一时之新风。它采用西方话剧舞美效果,给观众以强烈的视听冲击。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叔同与友人观看了新派剧领袖川上音二郎夫妇的戏剧表演。李叔同意识到,这种比中国传统戏曲更直接的戏剧形式,对于观众而言也更具感染力和亲和力,而这与李叔同以艺术作为社会教育手段的思路不谋而合。

李叔同在话剧《茶花女》中反串飾演女主角玛格丽特
那场的观众里,一位名为周树人的浙江学子看得津津有味。
在朋友的引荐下,李叔同拜晤了著名戏剧家藤泽浅二郎。在后者的帮助下,1906年冬,春柳社文艺研究会宣告成立,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
在李叔同等人所写的《春柳社演艺部专章》中,他们提出,要以欧美所流行之“言语动作感人”的新派演艺为主,以旧派脚本为辅,且场面布景必须改良。
余秋雨在《中国戏剧史述》中称,春柳社说是“新派为主”“旧派为附属科”,实际上完全立足新派,以日本为中转,引进欧美戏剧。
1906年,江淮流域遭遇罕见水灾,在日中国留学生决定举行赈灾义演。1907年2月,东京神田美土代町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内,春柳社诸人排演的《茶花女》正式亮相。李叔同反串饰演女主角玛格丽特。为了演好这一角色,他剃去胡须,自制了多套漂亮的女西装。
别开生面的演出,让春柳社名扬东京。日本戏剧评论家滨一卫观看了演出后,直接跑到后台要见李叔同,并称对方为他最佩服的中国俳优;多年后,已是著名剧作家的欧阳予倩回忆起初见春柳社演出时,仍激动不已:“这一回的表演可说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
初演告捷,春柳社诸人余兴未减。数月后,他们改编自《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黑奴吁天录》同样相当轰动。三千人的会场不仅全部满座,甚至走廊里也站得人山人海。那场的观众里,一位名为周树人的浙江学子看得津津有味。剧中借角色之口,激励国人、力排清朝的桥段,让他很受触动。
“誓渡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接连的演出成功,与李叔同的改良社会初衷和在艺术上的广泛涉猎不无关系。日本剧评家伊原青青园称,春柳社诸人对西方生活颇有研究,扮演的外国人物生动逼真,连藤泽浅二郎等名角都有所不及。
欧阳予倩表示,“那时对于艺术有见解的只有息霜(李叔同)”,因为后者不仅对中国词章很有根底,还从作画中领悟到了表演的技巧。“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

艺术是相通的。李叔同钟情话剧的同时,对音乐的追求并未停止。他赴日之初,便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介绍西方音乐知识,鼓吹音乐陶冶性情的作用。
留日期间,日本学校歌曲给了李叔同很大启发。他日后改进学堂乐歌,推广近代民主主义,启迪教化民众,就是深受此影响。
1872年,日本政府对近代教育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在中小学设置音乐相关课程,音乐自此成为日本国民教育的重要一环。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当时的日本学校歌曲主要有三个来源:沿用西洋各国的民歌或古典音乐的旋律填词而成;采用日本传统雅乐、民歌,配上《古今集》中的古歌词或新作歌词;日本音乐家完全新创而成。
日本学校歌曲里,中西交融、简单却不失深意的创作思路,让李叔同受益匪浅。他后来创作学堂乐歌中的经典之作,几乎都遵循着这一准则。无论是《春郊赛跑》这样贴近孩子实际生活的作品,还是《送别》《清平乐》等古雅十足的歌曲,所配旋律都出自欧美作曲家之手。
中国第一首学堂乐歌,是1903年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乐歌课教师沈心工创作的《男儿第一志气歌》。而李叔同对学堂乐歌的改进,让这一音乐载体在艺术性和影响力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首先是声部方面。早年间,国内的学堂乐歌多为单声部的齐唱作品,旋律虽朗朗上口,艺术价值却不足。李叔同接连创作出了《春游》等多首合唱作品,开启中国合唱创作的先河。
再就是词曲的契合。《送别》本质上是“三创”作品,原曲由美国作曲家奥特威写成,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广泛传唱;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后,1904年,日本音乐人犬童球溪为歌曲填上了日文歌词,并将其改名为《旅愁》;李叔同在日期间,听到了这首歌曲,这才有了后来的《送别》。
乐评人马世芳表示,《送别》流行了一百多年,很少人怀疑它的旋律不是中国出来的,是因为李叔同的词填得实在是太好了,不但词意优美,而且词曲咬合无懈可击。
这种完美的契合,彰显的是李叔同的音乐功底。在填词中,很容易出现“倒字”的情況,即歌词的字,配上旋律后,字原本的读音听不出来,反而变成了另一个音调。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送别》取消了前两版中的多处倚音,使歌唱中字音与原本读音更为契合;在歌曲节奏上,其也做了适当调整,让词曲连携更为紧密。
在歌词方面,《送别》在《旅愁》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国民记忆中的经典意象,长亭、古道、芳草、笛、柳……无一字刻意用典,但又无一字不是典故。文风典雅,不仅勾勒出凄美的惜别意境,而且在表达惜别之情时,也能反映出那个动荡岁月里,国人最真实的愁苦与感伤。
带着从日本学成归来的成果,李叔同回国后,担任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图画音乐教员。其学生中,不乏后来的艺术大家,诸如丰子恺、刘质平。十余年后,国内彼时中小学里的音乐教员,大多是李叔同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或许,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吧。
责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
——《李叔同—弘一大师年谱长编》评介
——《李叔同——弘一大师影像》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