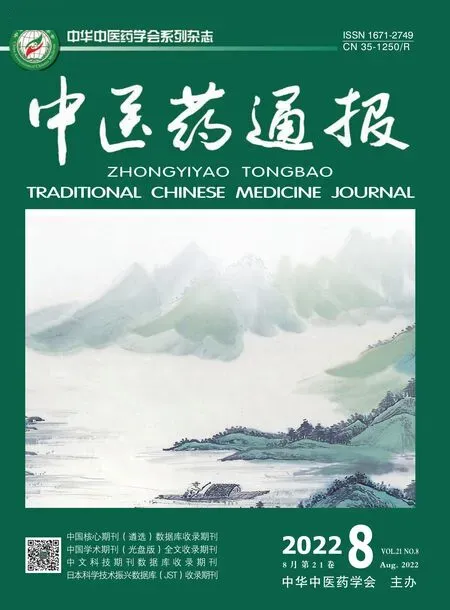旴江医家喻嘉言治疗膈气危症特色浅析
朱夏莲 叶明花 王河宝 杨曼丽 宋 鑫 童海涛
“膈气”又称鬲气、噎膈,是由于食道狭窄或食管干涩等原因导致食物下咽困难,甚至阻隔不下,食之即吐的一种吞咽障碍疾病。《伤寒杂病论》对膈气作了较为完整的描述,从其论述可将膈气病分为“膈气实”和“膈气虚”[1]。后世医家对膈气的理解不一,有将其解释为膏肓病的,有将其病变部位划分到肺、胃的,可见其病因病机之复杂,非但如此,若其病程迁延日久,可发展为危症,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
喻昌(公元1585—1664 年),字嘉言,江西新建人,世称西昌老人,是明末清初最具代表性的旴江医家之一,为清初三大医家之一。《寓意草》成书于公元1643年,该书不分卷,所收集的医案皆为内科杂病,且议病格式规范,着重强调“先议病,后用药”[2]。该书所录三则膈气危症医案也是如此,由浅入深,内容详实,清晰地体现出喻氏对膈气危症病因病机及治病用药的独到见解,本文试对其进行浅析。
1 发展源流
“膈气”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书中多处提及该病的病因病机及辨证施治方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厥阴之胜,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甚则呕吐,鬲咽不通。”记录了肝气犯胃,损伤胃脘导致噎膈。从汉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的描述可推断出,水热互结的大结胸病属于“膈气实”的范畴,而“膈气虚”指膈间有无形之热的一种病态,与有形实邪的大结胸病相对[1]。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首次提出“五噎五膈”的说法,将致病因素从六淫、七情、饮食等方面进行了概述。唐代孙思邈对不同原因所导致的噎膈症状进行了阐述,如气膈、食膈、忧膈[3]。宋代医著《圣济总录》云:“人之胸膈,升降出入,无所滞碍,命曰平人。若寒温失节,忧恚不时,饮食乖宜,思虑不已,则阴阳拒隔,胸脘痞塞,故名膈气。”并提出膈气病在肺、胃。金元四大家对膈气病又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如李杲在《圣济总录》指出血属阴、气属阳,膈气为阴阳拒隔,当从气血论治;朱丹溪认为膈气发展到后期易致液燥血亏,治疗上宜滋阴养血,并指出膈气不治之症的表现有反胃、口吐痰沫、下如羊屎等。到明清时期,贲门为噎膈之病位、噎膈乃食管狭隘使然等接近现代医学的说法逐渐被中医家提出。现代医学认为,食管癌在临床症状上归属于中医“噎膈”范畴,但史慧娟等[4]研究表明噎膈除涵盖食管癌、贲门癌外,还包括食管良性狭窄、食管炎等消化系统疾病。吕翠田[5]团队研究食管癌和噎膈证素,发现食管癌的病机更为复杂,至今仍是临床一大难题。
2 病因病机
历代医家未曾停止过对膈气病因病机的探究。《黄帝内经》首次提出其与外感、情志相关。现代临床证素组合研究[6]表明,噎膈病的基本证候为气滞食管、血瘀痰阻、肝气犯胃、脾胃虚弱、肾阴亏燥。喻氏议病十分注重对病因病机追本溯源,《寓意草》中关于膈气危症的病因病机可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
2.1 夹食伤寒,胃阴亏虚《寓意草》中膈气危症有两例提及伤寒夹食,迁延日久,致胃阴亏虚。如李案中“李思萱的妻子发春温病,病后不调养却连食性热之鸡子鸡面,复伤食,吐泻交作五次,前后七十日,滴饮不入,脉乱无根,胃气将绝”;倪案中“患者不得解衣睡十四日,稍好转便脱衣图安寝,然冷气一触,便呕,遂饮前药,复好转,然胃口稍佳便急饮粥六盏,复呕”。病初愈,脾胃气弱,消谷无力,食不节则脾胃升降失常,饮食隔阻,吐泻交作。正如喻氏在《医门法律·虚劳门》中指出“三损损于脾,饮食不能消化。自上而下者,过于胃则不可治;自下而上者,过于脾则不可治”。人体外感寒邪时,正邪相争,中气虚馁,脾胃虚损,纳化失常,宜建中并辅以易消化之物,缓慢进食。若复伤食,则会导致水谷不化、饮食中阻、吐泻交作等病症,致使气血生化无源,日久损及津液,气随津脱,胃气不存,出现无根之脉,可危及生命。
2.2 阴乘阳位,蛔虫居膈喻氏尤其推崇李杲的重脾胃思想,将脾胃视为养生治病之本,认为“土为万物之母,万物之蕃茂,莫归根于土,人体生命活动无不与脾胃休戚相关”。《黄帝内经》提出脾胃体用阴阳之说,人之脏为阴、腑为阳。李东垣在阐述形体与官窍的联系时也提及了“体用”,喻氏在《医门法律·中寒门》中首次提出“然人身脾胃之地,总名中土,脾之体阴而用则阳,胃之体阳而用则阴”,即脾脏虽为阴中之至阴,但脾升清阳、主运化,生理功能皆用阳之性;胃主受纳、主降浊,胃虽为阳腑,却喜润恶燥,主养胃阴,功用阴之性。脾胃作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一旦体用阴阳失衡,阴乘阳位,则易导致纳化失常,中焦受阻,迁延日久可致浊阴不降,反而上逆不止,严重耗伤津血,危及生命。喻氏在倪案还提出“久不进食,必致蛔虫上居膈间,气机无法正常上传下达,甚而涌吐肠中之物,肠燥津枯,迁延至危”。《素问·通评虚实论》云:“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
2.3 气血亏虚,气滞痰阻水谷精微乃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是人体后天精微物质摄纳的关键。《寓意草》中三则膈气危症的患者皆为病情迁延损及脾胃,久不进食,呕吐不止,不仅水谷精微摄入乏源,脾胃无法纳化气血,而且呕吐损耗气阴,气逆不下达,致使尺脉不现。在中医理论中,津血属阴,气为阳,水浆不入,呕吐日久,气血虚脱,最终导致脉象无根之死症。脾胃虚损,升降无力,致气滞中焦,无法运化水湿,遂生痰饮,涌吐痰涎,正如《寓意草·闻案》提及:“饮食不消,故易成痰。”《金匮翼·卷三》云:“噎膈之病,有虚有实。实者或痰或血……虚者津枯不泽,气少不充……不可不辨也。”喻氏认为,脾胃健运有力,则气机升降出入有序,人之水湿自消[7]。
3 用药特色
3.1 强调健脾理中喻氏强调脾气若天之有日,是人体健运之阳气,指出“脾为中土,中央气弱,不能四迄”,临证十分重“脾者孤脏,以灌四旁”的后天之本地位。三则膈气危症医案中,喻昌分别用人参汤、六君子汤、理中汤配合重镇下坠之旋覆代赭汤施以治之,旨在先建中,恢复脾胃的纳化、升降功能,以恢复虚衰的气血津液,使人体恢复正气,抵抗病邪。喻氏不仅施药祛邪不离健脾理中思想,善后亦不忘调脾胃,如李案中四君子汤、丸调理;黄案中拒绝下药而用食养法复脾胃正气;倪案中服补药理中。三则医案皆体现了喻氏重视人体脏腑与脾胃、气血的关系。脾胃化生气血,气血濡养脏腑,若气血生化乏源,则脏腑营养不足。因此,喻氏论治疾病时重视调理脾胃,气血和畅,脏腑得安。
3.2 重视药食相参饮食服饵自古有之,养生医家尤喜研究饮食服饵,但喻氏将食物与药饵相参视为健脾理中之佳珍。在李案中,以人参、陈橘皮药渣加粟米煮粥,巧借粥之黏附作用,使药物稍停胃中。喻氏选食也颇讲究,煮粥用粟米,即小米,其色黄味咸性微寒,春种秋收得土气最厚最养脾胃。六日后,胃稍安,便仍稀,则以陈仓米替粟米。陈仓米色白甘淡性平,和胃止泻、渗湿除烦,越陈则补脾胃效果越佳。在黄案中,喻氏不受患者举家催加泻下药的干扰,拒用润肠之归、地,及苦寒之硝、黄,坚持待患者饮粥食足,气下便通,体现了其“护胃气,守胃阴,慎攻下”的理论思想。在倪案中,患者呕止气回,不遵服半盏粥的医嘱,急饮六盏,脾胃复伤,旧疾再发。三则医案从正反面体现出喻氏的重脾胃理论,其临证治病始终强调药食相参,若治病不善理脾胃,则食少脾胃弱,牵连五脏不安,反之,则诸疾易瘥。
3.3 善用经方,灵活变通喻氏是旴江医学重《伤寒论》《内经》之风的开创者,其多本医学著作皆强调经典理论和经方的重要性,《寓意草》所载之医案大多以经方为本而进行加减化裁。根据《伤寒论》所述,病久胃虚而气逆痰阻者,当首选旋覆代赭汤。喻氏以其为本,临证变通,用药之效,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其变通之妙,值得深究。在李案中,患者胃气将绝,仅存一丝胎元之气,喻氏用人参汤处之,人参用至九两,患者元气得复。赤石脂初研末送服,后改丸剂;病邪已去,先以四君子汤善后,再改四君子丸调理。盖因在中药传统剂型中,汤剂能较快地吸收、起效,适用于病情不稳且症状较重的患者,而丸剂在制备中通常以蜂蜜凝固,能益气和中、降低药毒性,其吸收慢,作用持久,有利于调和气血,适用于久病体虚或慢性病患者。在黄案中,喻氏因患妇尺脉不现,思其有孕不查,用药时恐干姜辛燥复伤气阴,遂换成煨姜;赤石脂易赭石,取其酸涩固胎元;六君子汤加旋覆花,不仅能降药性之急,又能建中、祛痰、降逆并行。在倪案中,喻氏忧患者蛔虫壅膈,故取理中汤理中焦,盖取《医方集解》理中汤治疗“厥冷拘急,或结胸吐蛔,及感寒霍乱”[8]之意,且用辛辣之干姜力下蛔虫。先嘱服理中汤六剂,后以旋覆代赭汤建奇功,盖因理中汤已分阴阳、健脾胃,胃阴不恐半夏之燥,胃气不惧赭石之重坠。
4 结语
喻氏熟读经典,推崇经典医理和经方,同时格外重视经典的实用性,临证时善于推陈出新。《寓意草》中的医案大都提及不可拘泥经典,要善辨析、取精华;要全面诊断、谨守病机,随症创新,形成自己的临证用药思想体系。喻氏在治疗膈气危症时,面对复杂的症状,力求悉数理清,综合考量,直察病机,并始终坚持“脾胃不和,百病由生”“气机失调、阴乘阳位,则中焦壅塞,痰涎涌吐,泄泻不止”“脾胃生气血,气血养五脏”的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喻氏严守病机,灵活变通,不泥古方,不唯药是尊,而是中病即止,强调饮食调护,恢复身体机能与自愈能力的重要性。膈气在现代医学中大多指食管癌或其他消化系统疑难杂症,是临床一大难题。喻氏治疗膈气危症的治疗思路和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提高后世医家对此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