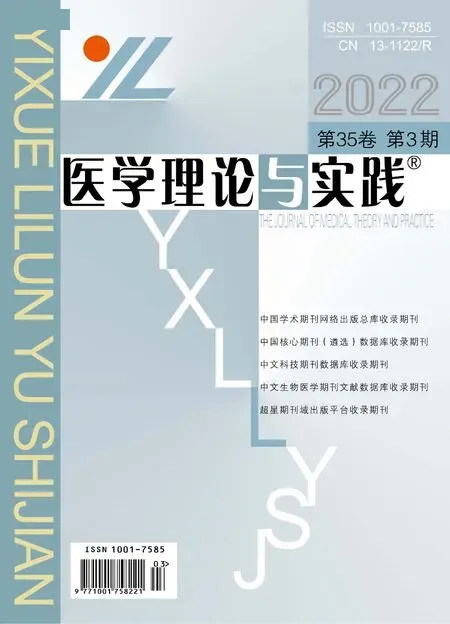重型颅脑损伤多模态监测现状与进展
蒯 冀 高志远 陈治军
湖北民族大学医学部荆门临床医学院 448000
自1969年Lundberg将持续颅内压监测应用于临床以来,该技术在颅脑损伤重症监护中的应用日趋增多,被认为是神经重症监护的奠基石。此后,各种神经监测工具被开发出来,以监测不同的生理参数,如脑氧合、脑血流量(CBF)、脑自动调节(CA)、脑电活动和大脑代谢以及脑压。然而,目前还没有一种单一的监测方式足够和理想地适用于所有患者。在20世纪90年代,多模式监测的概念被引入,并将CBF、脑组织氧合和脑内微透析进行综合监测[1]。我们目前正处于所谓的多模态监测和神经生理学决策支持的时代,本文将系统介绍目前的多模态监测技术。
1 颅内压(ICP)监测
1.1 有创ICP监测 已知ICP升高对患者有害,与不良预后相关,需要进一步治疗。脑室内监测ICP被认为是金标准,不仅是因为它的准确性,还因为它还可以通过释放脑脊液来达到治疗目的。根据实际指南,对于格拉斯哥评分(GCS)≤8且头颅CT异常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推荐进行颅内压监测,这一建议是基于一些证据表明ICP引导的治疗可以降低早期死亡率[2]。虽然对ICP波形的定性评估是当前临床实践的一部分,一些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已经被提出和试验,以作为处理这些数据的潜在方法[3]。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仅使用波形特征和深度学习算法检测ICP升高的准确率约为92%[4]。
1.2 无创性ICP监测 无创ICP监测包括经颅多普勒(TCD)、视神经鞘直径(ONSD)和鼓膜位移(TMD)。这些无创性ICP监测工具不如有创性ICP监测准确[5]。然而,非侵入性ICP传感器有可能减少对一系列患者进行侵入性干预,因此有必要开发。TCD是目前最常用的无创性颅内压评估技术,根据平均动脉压(MAP)变化或脉搏信号特征预测ICP的方法似乎是最可靠的。与脑氧合相比,非侵入性ICP结果的分析,无论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都通过使用有创ICP监测作为参考测量而得到简化。但该技术严重依赖于操作员,且大多基于间歇性测量。TCD通常用于计算Gosling搏动指数,它与脑灌注压(CPP)和ICP有很好的相关性[6]。
ICP升高可以通过蛛网膜下腔的脑脊液传播,导致视神经鞘扩张,这可以用经眼超声检查来检测。在侵入性监测不能及时获得的情况下,ONSD测量可能是ICP的一种有用的筛查工具[7]。最近的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了ONSD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并建议将直径5.6mm作为诊断ICP升高的最佳界值[8]。
2 脑组织氧合监测
2.1 脑组织氧分压(PbtO2) PbtO2最初是作为一种在控制ICP的过度通气治疗过程中避免脑缺血的方法出现的。脑组织氧合不等于外周血氧饱和度,实际上是脑动静脉氧分压差(CBF)和组织氧摄取的组合。因此,影响PbtO2的因素很多,包括脑灌注压(CPP)、血红蛋白浓度、血氧饱和度、代谢率和脑血管痉挛。PbtO2可通过PET(金标准)、实质内氧气传感器、磁共振光谱、颈静脉球血氧饱和度(SjvO2)和近红外光谱(NIRS)进行测量。最常见的监测PbtO2的方法是使用改进的Clark电极的侵入性探针,实质内氧气监测有潜在的并发症,如出血、移位和感染,虽然并发症发生率较低。PbtO2还受到氧扩散的进一步调制,例如在脑组织中,氧的扩散不仅受组织和内皮水肿的影响,还受微血管塌陷的影响[9]。因此,很难为PbtO2定义足够的目标值。低于20mmHg(1mmHg=0.133kPa)的值通常是供氧不足的可接受阈值,与TBI较差的预后相关。一项Ⅱ期试验(Boost-Ⅱ,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脑组织氧气监测和管理)显示,PbtO2靶向治疗组住院期间的缺氧负担显著降低(74%)。
2.2 近红外光谱(NIRS) NIRS是基于生物组织根据其氧饱和度不同的吸收红外线的机制。尽管NIRS是非侵入性的,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光线穿透颅骨的深度(2~3mm,仅限于灰质),受到颅内和颅外来源的污染,以及红外光在脑脊液层的均匀分布[10]。与PbtO2相比,近红外光谱在检测缺氧事件方面相关性低,准确性有限。
2.3 颈静脉球氧饱和度(SjvO2) SjvO2可以测量全局脑氧合。作为一种侵入性手术,SjvO2有导管错位、感染和颈静脉血栓形成并发症可能。需要干预的缺血的公认阈值是血氧饱和度的55%。SjvO2的最佳应用是脑外伤和全脑损伤患者[11]。
3 脑微透析(CMD)
微透析技术可以通过插入大脑间质的薄的(0.6mm)开窗双腔透析导管对小分子物质进行采样和收集。脑外伤后放置在易损伤区可在线分析细胞外/间质的生化变化,例如乳酸、丙酮酸、葡萄糖、谷氨酸和甘油。它允许对几种分析物进行直接测量和趋势分析。
高LPR是缺血和/或弥漫性缺氧的标志,提示存在能量代谢危机,是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LPR的减少可能是有益的治疗效果的标志。2014年国际微透析论坛发表的共识声明将乳酸/丙酮酸比率(LPR)>25和低脑葡萄糖<0.8mmol/L确定为与不良结局相关的病理阈值,需要进行干预[12]。
低脑葡萄糖(<3mmol/L)受动脉血糖(<6mmol/L)的影响,导致乳酸(LP)和LPR比值升高,而脑乳酸/葡萄糖比值在脑糖水平高于5mmol/L时最低,这表明高血糖和低血糖对脑能量代谢都是有害的。相反,输注高渗乳酸显示出明显的大脑葡萄糖节约效应,但仅在有病理性高LPR的患者中。最近的指南证实了 CMD 在检测脑葡萄糖以个性化血糖为目标时,可以避免代谢衰竭[13]。
谷氨酸是大脑中主要的兴奋性氨基酸。在急性颅脑损伤后,细胞Ca2+内流引起神经元去极化,随后间质谷氨酸增加,无氧糖酵解活性增强,乳酸生成增加。谷氨酸被认为是脑缺血的早期标志[14]。
虽然这些参数被认为是临床参数和ICP之外的独立预后预测因子,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干预措施来纠正错乱的CMD监测数值。这反映了潜在病理生理学的复杂性,导致数值异常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缺血、皮质弥漫性抑制、线粒体功能障碍、微血管塌陷和弥漫性缺氧[15],但是早期识别这些模式,尤其是与其他多模式监测参数(如ICP、PtiO2、EEG)结合分析时,可能会为临床干预创造机会之窗,以防治继发性脑损伤。
4 脑血管自身调节与脑灌注压
大脑在CPP改变的情况下维持恒定脑血流量的能力被称为CA,预测急性TBI患者预后最准确的CA指数是压力反应性指数(PRx)、平均流速指数(Mx)和自动调节反应性指数(Mx)。PRX依赖于动脉血压和颅内压之间的相关性(-1~1),负值表示完整的CA,正值表示CA功能失调[16],在重型颅脑损伤中,阳性的PRX与较高的死亡率相关[17]。
最佳脑血流量(CBF)是满足损伤脑的代谢需要所必需的,目的是保护缺血半暗带,避免二次损伤的恶化。当CPP低于50mmHg时有缺血迹象,而CPP高于60mmHg可以避免脑氧饱和降低,这表明CPP的临界阈值在50~60mmHg之间。以CPP为基础的治疗以此水平为目标,已被证明与更好的结果相关,并可能预防脑低灌注和脑血流量过多[18]。然而,由于颅脑损伤后脑血流和代谢的异质性,以及对CPP需求的区域性时间差异,脑监测技术,如颈静脉血氧饱和度(SvJO2)、PbtO2监测和脑微透析可以提供补充和特定的信息,以便为个体患者选择最佳的CPP。
5 生化标记物
值得注意的脑损伤生物标记物包括胶质细胞相关的生物标记物(GFAP、S100B)、神经元/轴突相关的生物标记物(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神经丝轻肽、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tau、淀粉样蛋白β,αⅡ-血影蛋白分解产物等)和其他炎症相关的生物标记物(高迁移率族盒蛋白1、各种细胞因子和自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在重型颅脑损伤中使用生物标志物的指南。血清半衰期(T1/2)较短的蛋白质生物标志物[如S100B(T1/2为24h)]可能比血清半衰期较长的蛋白质[如NSE(T1/2为48~72h)]更有用。较长的半衰期为检测严重脑外伤患者的二次神经损伤提供了较长的损伤后窗口[19]。
6 脑电活动
脑电活动通常通过脑电图(EEG)来测量。脑电图既能检测癫痫样活动,又能预测临床结果。连续脑电图(EEG)通常用于监测出现创伤后癫痫(PTS)、亚临床癫痫风险增加或药物无效的患者。脑创伤基金会的指南建议,在重型颅脑损伤中,临床PTS的发生率可能高达12%,而亚临床癫痫的发生率可能高达20%~25%[20]。EEG监测也被用于监测镇静药物的监测,防止过度镇静或者镇静不足。
7 人工智能
目前分析重症监护数据的人工智能方法主要有两种:基于模型的方法和数据驱动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已经证实了分析大量患者数据的能力,虽然这些人工智能系统都不是为了取代临床医生的判断,但这些系统有可能减少医疗成本和医疗管理中的错误或延误。
虽然人工智能已经在预测未来平均ICP和评估ICP变异性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实施人工智能的下一个令人兴奋的操作将是直接响应ICP升高的自动化治疗。有了对ICP的持续监测,一旦AI检测到ICP持续升高超过20mmHg,在由强化治疗分配的预先指定的时间内,AI就可以实现自动给药。虽然人工智能不能取代医疗团队的警惕,但AI自动化将增加ICP突然变化得到更快解决的可能性[21]。
8 展望
重型颅脑损伤救治的未来在于多模态监测,其中颅内压监测及脑血流监测是基础,也是核心。多模式神经危重监测考虑患者或其损伤的个体病理生理变化,并允许临床医生量身定做个性化的管理决策。多模式监测数据并不是单纯的叠加模式,需要相互结合、促进、补充,数据的集成几乎不可能手动进行,是对硬件+软件技术的整合,因此需要信息学和涉及临床医生、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以及信息学和复杂系统分析专家的协调努力,AI智能控制系统的出现将在神经重症管理方面带来无限前景。多模式神经危重监护为强化治疗人员提供了一个综合脑功能生理测量的机会,以便为急性脑损伤患者提供及时和个体化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