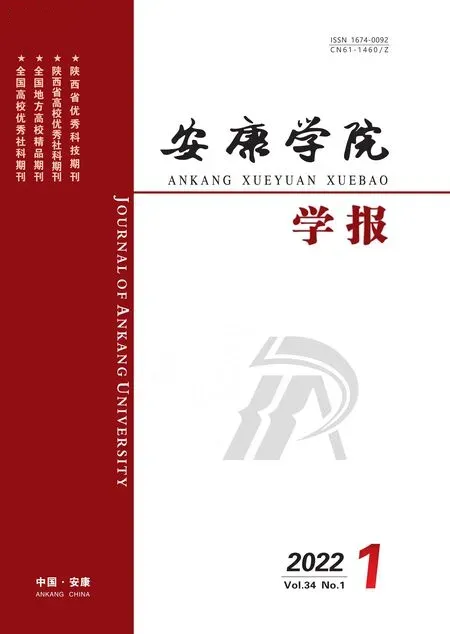多元文化杂糅与身份认同焦虑
——文学地理空间下的《午夜之子》研究
张印文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午夜之子》是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成名作。这部小说以广阔的印度次大陆社会现实为背景,描写了印巴分治前后的政治动乱、社会变革和宗教纠纷等复杂历史问题,并涉及印度的许多传统习俗。同时,因着作家特殊的文化身份和生存体验——出生于印度的穆斯林家庭,后又在英国接受教育并加入英国国籍,使得他能够从博弈的双文化情境中以全新的视角来书写印度独立前后的社会现实、母语文化与宗主国文化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背后的文化反思。拉什迪的移民经历带给了他不同的地理空间体验和敏感的多元文化身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地理空间中的迁徙同时也是文化心理空间中的精神之旅”[1]。可以想见,拉什迪由弱势文化进军强势文化的精神之旅,势必伴随着其本人强烈的身份焦虑感以及因多元文化杂糅而带来的错乱感。而作家的这种焦虑与错乱在其自传体小说《午夜之子》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空间的边缘化与人物的身份认同危机
《午夜之子》以主角萨里姆·西奈讲述自己家族史的方式展开叙事,小说故事时间跨越了六十余载,覆盖了包括整个印度次大陆在内的广阔地域。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再现萨里姆家族中人物的活动经历,作家成功地建构起其文学想象中的多维地理空间。小说中的印度次大陆作为地理意义上的空间领域曾长期处于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对于英国人来说,这里不过是他们诸多殖民地中不起眼的一个,和居于“世界中心”的欧洲相比,呈现出远离中心的边缘化特征。通常来说,地理空间的环境会使人物身上带有无法抹去的特有“印迹”,直接影响着人物自身的生存体验,而且地理空间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则更富于内在性、群体性。因此,文化作为个体的内在身份属性,常常“积极地与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而且时常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义”[2]4。不难设想,在印度这样一个被边缘化的地理空间里,无论是出于对自身文化立场的顽强坚守,还是对外部世界的积极向往,生活其中的人物都很难逃离困惑和迷茫的窘境,从而导致他们经受着自我身份得不到认同的命运。
萨里姆的讲述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克什米尔一个群山环绕的湖畔城市,这里是萨里姆外祖父阿达姆·阿齐兹的家乡,当时正处于英国人的殖民之下,年轻时的阿达姆曾留学德国,但对于欧洲人来说,西方统治之下的克什米尔就是一个边缘化的“异质空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是连上帝也无法拯救的异教徒。所以在欧洲学医的阿达姆就被当作来自边缘地域的异类,尤其是当时的西方人普遍深信印度次大陆在被欧洲“发现”之前是没有文明的,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欧洲人是现在印度人的祖先,是欧洲将先进的文明之光带给了印度。因此当阿达姆在德国以穆斯林的方式祈祷时,他的朋友们纷纷报以嘲讽和戏谑的姿态,让他受尽冷眼和委屈,这使得阿达姆陷入对自己宗教信仰的怀疑中,“他永远给卡在那个中间地带,他无法崇拜真主,但又无法完全不相信他的存在”[3]7。不仅如此,学成归来的阿达姆也没有感受到家乡温暖的慰藉,当他提着印有“海德堡”几个字的问诊包坐船前去治病时,小时候的偶像船夫塔伊不再把他当作自己的忠实听众和伙伴,而是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塔伊将问诊包上的图文视为是外国文化的入侵,甚至还把阿达姆看作是被欧洲文化荼毒的人,认为他纯正的穆斯林血统已经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污染。塔伊由阿达姆幼时的一个慈祥长者变成了现在充满敌意的顽固老人,其态度上的巨大反差使阿达姆感到痛苦和迷茫,这种不被家乡穆斯林所接受的处境迫使他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山谷,也更加动摇了他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徒的信仰。后来,离开家乡的阿达姆来到阿姆利则,并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米安·阿布杜拉,阿布杜拉一生都在为印度千百万穆斯林的自由奔走呼号,他的行为带着一股强烈的感召力,并一度让失落的阿达姆找到了奋斗的目标。可惜事与愿违,阿布杜拉纵然是印度伊斯兰教的忠诚使者,却依然没有得到真主的庇佑,最终被政敌暗杀身死,他的死亡让阿达姆原本的信仰遭受到致命一击。正因如此,阿达姆余生一直对真主的存在抱有强烈的怀疑,“他这辈子一直都极力使自己相信主已经死了”[3]347。直到阿达姆在行将迟暮之际,才于睡梦中看见了真主,但此时他正经历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因为小儿子哈尼夫刚刚离开了人世。为此阿达姆表现出极大的愤怒,认为他一生迷茫流离的遭遇都是真主对自己失去信仰的惩罚,安拉的圣光始终没有眷顾过他。阿达姆就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一样,不仅无法融入欧洲的文化之中,而且也一直游离在本国的传统文化之外,“始终处在一种彷徨犹豫的状态之中”[3]7。
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扩张不单纯表现为殖民掠夺,它更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入侵,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在侵略过程中将自己的文化逐步渗透到殖民地中,使那里的人们不得不潜移默化地接受殖民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言:“帝国主义又在文化中获得了一种协调一致,一套经验,还得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2]12宗主国不断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殖民地进行文化输入,一方面想借此掩盖自己野蛮的殖民掠夺行径;另一方面也在同化着被统治的人民。因此生活在印度次大陆的人们一方面痛恨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被帝国主义的文化所规训,甚至有些人主动向欧洲文化靠拢,并以此作为夸耀的资本,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当时印度地区的上流阶级中。克什米尔当地一位名叫格哈尼的地主就非常喜欢欧洲的绘画,常和别人一起谈论各种文学艺术,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格哈尼却是一个盲人。而且这位盲人地主除了爱好“欣赏”绘画以外,还欲将女儿嫁给阿达姆为妻,原因就是阿达姆曾在欧洲留学,能将其招为女婿会极大满足自己的文化虚荣心。除了格哈尼,库奇纳西恩王公夫人也热衷于效仿西方文化,她身上散发着后天习得的欧洲贵族女子的气息,待人接物总是温和有礼,她在阿达姆夫妻吵架时派人劝阻,显示出自己的通情达理,她在别人都嘲笑纳迪尔汗所写的“没有一处是押韵的”[3]50诗时,称赞诗歌有现代派的风格,礼貌地化解了尴尬。在王公夫人身上可以明显看出其对欧洲贵族妇女气质的模仿,即使在她患上白癜风之后,也没有表现出忧愁,而是说:“我的皮肤是我精神上国际主义的外在表现”[3]50。由此可见,英国在印度地区长期的文化输入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部分人有意识地向这种文化靠拢,逐渐被同化与规训。同样地,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固守传统文化习俗、强烈抵制西方文化的人也会处于一种不被认同的边缘化地位,比如一直在达尔湖和纳金湖上摆渡的老船夫塔伊,他的年龄老到成了当地的未知之谜,而他的思想正如其古老的年龄一样陈旧。在已经受到英国文化浸染的克什米尔地区,塔伊作为传统穆斯林的代表总是不被周围人所接受,加之长期嗜酒带来的疯癫和身上布满的虱子和臭味,除了年幼的阿达姆之外没人愿意同他交流。而长大之后的阿达姆远赴欧洲留学,从国外归来的他“换上了见过世面的旅客的眼光”[3]5,不再是当年缠着塔伊讲故事的小孩子了。在塔伊眼中,阿达姆已经成为追慕西方文化的叛徒,尤其是当他选择依附于地主格哈尼并娶了他的女儿后,塔伊彻底爆发了,他认为阿达姆已经背叛了内心的信仰,曾经唯一理解自己的人改变了。塔伊愈发自暴自弃,他不再盥洗,身上的臭味愈发浓烈,周围的人再也不愿靠近他,直到阿达姆离开了家乡的山谷,塔伊彻底无人问津。
小说主人公萨里姆似乎是沐浴着圣光出生的孩子,他的家庭属于享有一定特权的上流阶级,父亲阿赫穆德是一位富商,母亲阿米娜是一位大家闺秀,这给予了他富足优渥的生活。不仅如此,萨里姆还出生于印度建国日的午夜零时,赋予了他神秘的能力,让他成为午夜之子的领袖,他又是圣者口中的“穆巴拉克——老天保佑的人儿”[3]140,为他的身份增添了许多神圣感。但细读作品会发现,这些身份并不是真实的,只是多种偶然因素在机缘巧合之下造就的,最终只会走向幻灭。由于助产士玛丽的掉包,使得原本应该是街头艺人之子的萨里姆出生在了穆斯林富商之家,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英国人梅斯沃德与一个印度歌女的私生子,这些因素造成了萨里姆的混杂身份,他并不是一个纯正的印度人,而是英国人和印度人的混血;他的生父梅斯沃德是基督教徒,而当前却处于穆斯林家庭;他原本应该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贱民”,却因调包摇身一变成为富商之子。再者,虽然萨里姆拥有召唤其他午夜之子灵魂的能力,但后来由于和另一位午夜之子湿婆产生了分歧,并且竞争失败,逐渐失去了午夜大会的领袖地位。因此,萨里姆的一生都处于这些混杂身份带来的自我分裂的痛苦中,“故事中,萨里姆体内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裂口,预示着不断临近的死亡”[4]。他无法融入其中任何一个身份,成为一个游离于多重身份之间的边缘人。故而萨里姆只得寻找一处可以躲避外界纷扰的边缘之地,于是家中白色的大洗衣箱成了他的心灵净地,在萨里姆看来,“洗衣箱是世界上的一个窟窿,文明将这个地方排除在外,不予接受,这使它成为最理想的藏身之处”[3]197。
《午夜之子》在表现人物生活经历的同时也建构起他们的自我身份,同时又体现出人们对自我身份能够得到他人认同的渴望,身份认同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5]。即个人的文化属性能否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属性相吻合,这里所说的“文化”是相当广博的一个概念,它是“复杂生活的整体,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其他各种能力与习惯”[6]。所以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为一个生活经验整体,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由于不同的地理空间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相差迥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会相应地呈现出地域性差异。因此在《午夜之子》这个地域文化广泛接触的大背景下,个人身份得不到认同的危机就成了小说想要表现的主旋律。
二、空间的文化杂糅与人物的文化身份冲突
在前文中谈到身份认同的本质就是文化的认同,而文化的内涵植根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基础上,虽然帝国主义的扩张使不同地域空间中的文化能够发生交流,但由于宗主国的文化通常体现着强权与压迫的性质,所以这种文化杂糅的局面并不能消除双方浓厚的排他心理,也就无法形成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的状态。正如乔治·拉伦所言:“在文化的碰撞过程中,权力常发挥作用,其中一个文化有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时尤其如此。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的文化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7]作者拉什迪生于孟买的一个穆斯林富商家庭,在少年时被父母送往英国的格拉比中学读书,由于双方文化差异过大,在英国人眼中,来自前殖民地的拉什迪自然成了文化上的异类;而在拉什迪眼中,所在的学校就是一个毫无温情的陌生场所,年少的他饱受身为“异乡人”的孤独与困惑,总能感受到与宗主国同学之间的隔阂,因此在《午夜之子》这部小说中,作者有意识地表现生活在印度这个多元文化杂糅地区的人们所面临的身份上的隔阂与冲突。
萨里姆的外公阿达姆和外婆纳西姆就是这样一对生活在间隙和分歧中的夫妻,阿达姆是从德国学医归来的青年才俊,纳西姆是克什米尔本地的大家闺秀,如果不是地主格哈尼的有意撮合,这两人几乎不可能走到一起。初次见面的他们被一条开洞的床单拦在了中间,因为在当时医生是不能和未婚女患者直接接触的,这条床单挡住了阿达姆在欧洲浸染上的开放激进,也掩盖住了纳西姆常居深闺形成的保守娇羞。结婚后尽管有新婚燕尔的甜蜜,但文化身份的差异终究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阿达姆希望妻子做一个开放的现代女性,而纳西姆却不愿抛弃克什米尔好姑娘的身份,想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于是,面对丈夫对自己的要求,纳西姆逐渐将自己封闭起来,“她生活在她自己建造起来的一个无形的要塞里面,由传统和坚定的信仰构成了铁桶似的堡垒”[3]44。这个“要塞”的大门就是纳西姆头上的面纱,这一点与阿达姆的母亲很相似,她们总是不肯摘下自己的面纱,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身体任何的裸露部分,“一条平纹细布大围巾把头裹得严严实实”[3]48,甚至不愿意保留自己的照片,并将这种行为看作是传统好姑娘的标志。虽然在丈夫的一再要求下,纳西姆被迫摘下自己的面纱,但她依旧没有妥协,她将厨房和食品储藏室当作自己的阵地,控制着全家的饮食习惯,以此作为对丈夫企图改变自己的反抗。同样,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阿达姆和纳西姆也存在着巨大分歧,阿达姆希望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现代化的教育,教他们学习西方的语言和知识,而纳西姆“在教育上她只做出了一个规定,那就是宗教教育”[3]46。她希望孩子能成为像自己一样的虔诚的穆斯林,所以当丈夫把她请来的宗教导师赶出家门时,纳西姆大发雷霆,一度停止对丈夫的食物供给,只到孩子们求情才肯罢休。
“午夜之子”是在印度独立时刻出生的孩子们,他们是印度这个新生国家的见证者,都拥有神秘的特异力量。萨里姆和湿婆的出生时间最接近午夜零时,因此被赋予了最强大的能力,萨里姆掌握着通灵之术,可以聚集其他午夜之子的灵魂召开午夜大会,而湿婆拥有常人无法匹敌的力量,是勇武的象征。按常理来说,他们两人应该共同主持午夜大会,带领其他午夜之子利用自身的异能为新兴的祖国做出贡献,履行作为午夜之子的使命。然而萨里姆和湿婆却无法做到同心协力,他们不仅有着迥异的特殊能力,而且对于午夜大会的观念也截然不同,萨里姆意图建立“一个彼此平等的松散的联盟,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3]278。湿婆却认为午夜大会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并且崇尚用武力解决问题,“对湿婆来说,世界完全由物质构成,历史只能看作是自己同人群的不息的斗争”[3]356。其实,他们观念上的对立是由相差悬殊的家庭环境造成的,而家庭环境的不同会进一步导致文化教育上的差异,萨里姆优越的家庭条件使他能受到良好的西方现代教育,培养他开放、自由、理性的现代人文属性,在宗教方面,他受到父母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接收到一些保姆玛丽信奉的基督教思想。相比之下,湿婆出生于街头艺人家庭,而且父亲早亡,悲惨的身世境遇使他很早就明白了弱肉强食的社会法则,由于没有什么机会接受教育,所以他行事只求达到目的而不在乎手段,也不管社会规则的约束,他是土生土长的印度教徒,他的名字正取自印度教的毁灭之神——“湿婆”,这也与他的行事风格相吻合。与之同理,其他的午夜之子也都是出生在不同的家庭,生长于不同的环境,有街边的乞丐、有洗衣工的女儿、银匠的儿子,还有女巫,尽管同属特异能力的拥有者,可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生活方式都大相径庭。因此,虽然萨里姆可以将他们的灵魂聚集起来召开午夜大会,但这个集体中没有统一的身份认同感,他们彼此的联系非常松散。最终,当萨里姆跟随家人来到巴基斯坦之后,印巴之间的国界阻断了他与午夜之子们的思想联系,也切断了他的能力来源,他被迫脱离了“午夜之子”这个群体。
《午夜之子》中的德里原本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却由于文化属性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被划分成新旧德里两个部分。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建立了“粉红色石头的宫殿”[3]81,形成了德里的新城区,并且以印度教作为这里的宗教信仰。而旧城区则保留着德里原始的面貌,“那些狭窄的巷子里的房子东倒西歪地、乱糟糟地簇拥在一起,挡住了视线”[3]81,从新城区向旧城区靠近时,会觉得“街道越来越窄,地方越来越拥挤,使人感到一种压力”[3]96,这里到处是牙齿乌黑的小孩、衣不蔽体的女性、不可接触的“贱民”以及刚出生就被父母弄残疾而乞讨的乞丐,所以当萨里姆的母亲阿米娜第一次从新城区来到这里时,就感到极为的不适应,“像置身于某个可怕的妖怪的包围之中了,这个妖怪长着数不清的脑袋”[3]96-97。生活在这里的大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当时正值印度独立前夕,在英国人有意地推波助澜下,印度和巴基斯坦即将分治,因此旧城区的穆斯林饱受印度教徒的威胁和排挤,他们被认为是“亚洲的犹太人”,印度教徒企图将他们赶出德里。由此可见,新旧德里迥异的城市环境和世情风貌形成了一道文化上的屏障,将居于此处的原住民分隔开来,使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频繁爆发大规模的斗争冲突,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灾难。
《午夜之子》中的印度是一个西方文化、伊斯兰文明以及印度教信仰多元杂糅的地域,它可以向世界各地的人敞开怀抱,但到达这里的人却拥有着不同的文化身份。由于人类固有的社会属性,这些在同一时空中相遇的人们需要寻求认同,这种认同其实就是文化价值判断的立场,它将人按照文化身份区分开来,于是有了西方人和东方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西化的上流阶级与劳苦民众的区别,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场。在当时印度政治动荡、宗教纠纷严重的社会背景下,这些难以相容的文化群体在这片纷繁复杂的土地上展开了冲突和较量。
三、空间的权力延伸与自我文化的失根
当西方的殖民活动向全世界蔓延之时,帝国主义的权力也在进行空间上的延伸,英国于19世纪中期就开始在印度次大陆进行殖民体系的建构,这种建构的内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哲学、历史等各种知识话语,“这些话语与帝国权力相结合,形成强大的意识形态语境”[8]。也就是说,英帝国在印度的权力渗透会裹挟着自身的意识形态语境,殖民地的文化根基也在这种入侵之下呈式微之态。拉什迪出生于印度取得政治独立的1947年,但作为前殖民地的印度在精神或文化上的独立却远未实现。“帝国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继续以‘结构’的形式‘询唤’其文化主体,在不知不觉中对他们产生教化的作用。”[8]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的拉什迪,无根性就是对其创作观念的最佳概括,他在小说中着重表现了印度原有文化特性的逐渐消失,人们陷入了文化失根的迷茫之中。
萨里姆的养父阿赫穆德是一位穆斯林富商,但拥有的万贯家产并不能掩盖他精神上的贫困。少年时的阿赫穆德将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他曾经的理想是把《古兰经》按精确的时间顺序重新修订,“而不是继承父业,干漆布商这个行当”[3]98。可财富在带给他富足奢华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逐渐热衷于享受别人在金钱上对他的奉承,尤其喜欢妻子阿米娜甜言蜜语地向他讨钱,这些虚假的荣耀成了他的精神慰藉。阿赫穆德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贫瘠,重新修订《古兰经》的梦想也被他抛到脑后,穆斯林的信仰不再是他精神文化世界的支柱。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强烈渴求财富的价值观念取代了他原有的文化与信仰,使他的全部身心放在对资本的追求和享受财富带来的虚荣上,这也为他以后精神世界的崩溃埋下伏笔。生完孩子的阿米娜不再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对丈夫的讨好上,而是全身心地关怀萨里姆的成长,阿赫穆德感到在家庭中的位置受到了损害,“想起往日的得意真叫人黯然神伤”[3]164。金钱带来的虚荣是他贫瘠的精神世界中唯一的支柱,因此阿赫穆德绝不允许这个支柱倒塌,这个动力被他转化成了对财富更大的渴求,于是他轻信了纳里卡尔大夫投标“填海造地”的建议,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他不顾一切地朝着梦想中的金钱帝国进发。最终,阿赫穆德的资金被政府冻结,财富梦想的破灭于他而言就是精神根基的毁灭,他的生命“就像冰锥子一样——断掉了”[3]175。
在子女纷纷成家之后,阿达姆潜心研究如何将西医和伊斯兰传统医学结合起来,不过这种尝试总是徒劳无功,因为接受过的西医知识使他不相信传统的巫医和迷信,但他本身又是伊斯兰教徒,无法完全忽视自身的宗教信仰。在这种情况下,阿达姆陷入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中,“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虚幻,他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3]78。印度新一代孩子们的童年生活与西方文化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萨里姆来说,蝙蝠侠和超人的故事陪伴他度过了将近九年的童年时光,另一个小孩松尼则把西班牙斗牛士当作自己的未来目标。可见殖民者的文化入侵不仅改变了印度居民的生活方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印度新一代人的价值观念。
小说中的孟买曾经是渔民聚集的美好家园,在欧洲殖民者抵达这里之前,这片土地原本是长满了椰子和稻米的渔民之乡,慈祥的女神孟巴德维是原来居民心中的信仰。但之后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相继在这个港口登陆,葡萄牙人将它命名为孟买希亚,英国人又在这里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座古老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堡一下子建了起来,又是围海造地,你眼睛还没来得及眨一眨,一个叫孟买的城市已经出现了”[3]112。这里原有的稻田都变成了一座座高楼大厦,长满椰子树的沙滩上也建造了许多度假酒店,曾经古朴的建筑都变成了林立的夜总会、酱菜厂和电影院,甚至象头神塞犍陀也取代了孟巴德维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孟买众多的传统渔民也被逼到了艰难的境地,“他们如何给挤到形状像手一样的半岛的大拇指上的一个小村庄里”[3]113,这些渔民才是以前孟买的主人,可如今他们不仅失去了往昔的家园,而且丢失了曾经的文化,“孟巴德维的节日到哪儿去了呢?日历上找不到。捉鲳鱼、捉螃蟹的人的祈祷到哪儿去了呢?”[3]113孟买渔民的文化根基伴随着往日与殖民者竞争的失败和家园的丧失一同丢掉了。
梅斯沃德庄园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个庄园的主人原本是一个名叫威廉·梅斯沃德的英国人,随着英国在印度统治地位的结束,他也将返回祖国,于是把自己名下的庄园出售给印度本地的几位富商,萨里姆的父亲阿赫穆德就是其中一位。但梅斯沃德对庄园的出售还有自己的要求,那就是“新房主必须将内部的一切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3]116。其实这也是大部分将要离开印度的英国人心中的想法,他们不甘心放弃在印度享有的特权。梅斯沃德要求新房主保留庄园原有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英国的统治能够以这种方式延续,尽管这个庄园是英国殖民者建立在对印度的破坏和压榨上的,但依然希望宗主国的文化能够继续主导印度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如恩吉吉·瓦·提昂戈所认为的那样,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殖民经济和政治安排上的……某种变化”[9]。帝国主义想要文化殖民继续在印度延续,而历经近乎百年英帝国统治的印度人对宗主国文化的排斥心理也不再那么强烈,虽然买下梅斯沃德庄园的新房主们一开始对庄园的设施非常不适应,萨巴尔马抱怨“这里每个房间里都有叽叽嘎嘎的虎皮鹦鹉,衣柜里又有虫蛀的衣服和旧乳罩”[3]120,易卜拉欣害怕天花板上的吊扇“会掉下来的——会在夜里割掉我的脑袋的”[3]120。但生活得久了,新房主们都慢慢习惯了这个庄园里的生活方式,“梅斯沃德山庄也在改变他们。每天傍晚六点钟,大家都坐到自己的花园里,高高兴兴地喝鸡尾酒”[3]121。钢琴、虎皮鹦鹉、吊扇、威士忌……这些象征着西方文化的元素组成了梅斯沃德庄园的特色景观,是文化空间的内在表征形式,它隐喻着帝国主义文化在印度独立之后的延续,也象征着印度自我文化根基的缺失。
《午夜之子》立足于后殖民时代地域空间的碰撞带来的文化心理的交流,并结合作者拉什迪自身的经历,展现了印度次大陆复杂的历史文化状况,反映了生活于此的人们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文化身份差异带来的冲突以及自我文化失根的困惑。拉什迪作为生活在东西文化夹缝中的作家,努力想融入英国的社会文化,但始终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如他自己所说:“有根的作家都有他们的地盘,他们的作品从那里源源不断流出,他们更是不断探索它,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我却没有地盘……每当我要着手写一个句子时,都感到不得不虚构出一块土地来,虚构出一块供我立足的土地来”[10]。因此拉什迪创作《午夜之子》这部小说,不仅出于打破与宗主国之间的文化壁垒的目的,也表现出他欲摆脱自我无根性身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