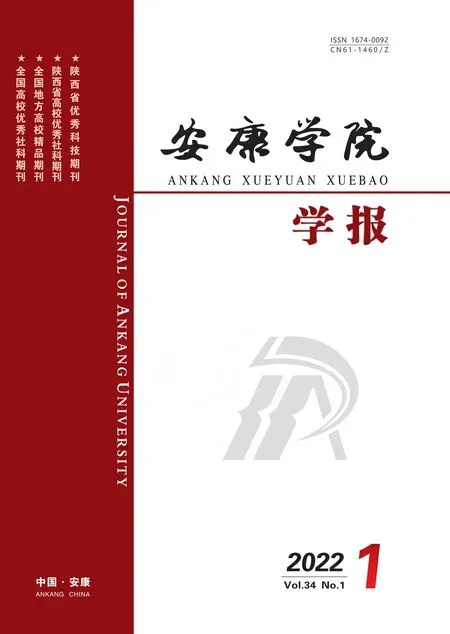论加缪荒诞创作的叙事艺术
陈 阳,蒋 丽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加缪的荒诞创作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其在《西西弗斯》中针对荒诞创作所提出的看法,这是荒诞创作的理论依据;二是指加缪在其荒诞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加缪创作的诸多小说即在此类。加缪认为:“荒诞之极乐,就是创作”[1]99,创作是呈现荒诞的最佳载体。加缪的所有作品,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论著,篇幅都较为短小,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正如加缪自己所说的那样:“深刻的情感,如同伟大的作品,其蕴含的意义总比有意表达的要多”[1]11。在加缪看来,无论是情感还是作品,其深层内涵都需要通过对表层言语的深入挖掘来还原。这一看法在叙事学理论中也可以找到与之呼应的观点,热拉尔·热奈特认为:“叙事可用较为直接或不那么直接的方式向读者提供或多或少的细节,因而看上去与讲述的内容(借用一个简便常用的空间隐喻,但切忌照字面理解)保持或大或小的距离”[2]107。在加缪创作的几部较为重要的小说中,读者与文本内世界的距离并非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展现荒诞的实际需要而不断发生变化。就实际效果而言,读者与文本内世界的距离似乎一直处在一种既近又远的矛盾之中,如在《堕落》中,加缪以克拉芒斯为主角,并让克拉芒斯成为展开所有情节和对话(主要为隐含对话)的载体,这似乎弥合了叙事者与叙事内容之间、叙事者与读者之间、叙事内容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然而,这样的安排会让读者产生接受混乱,从而使作品的“荒诞感”得以凸显。
一、受叙者——《堕落》中的隐性角色
有学者认为,“《堕落》是一个单向的对话”[3],理由是《堕落》中的受述者的话语也是由克拉芒斯转述的,因此,对话便成为克拉芒斯的自我倾诉。如果照此理解,《堕落》中的对话便成为一个虚假形式,这部小说也就成了一部自述体小说。加缪对克拉芒斯转述受述者的答语这一行为的安排,实际上是将受述者转换成了文本内的隐性角色。这更像是一次文学创作的实验,在文本中留下对话的空白,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与克拉芒斯共同填补隐性角色在文本中遗留下的对话的空白,从而形成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这明显与《局外人》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效果。但这并不代表加缪热衷于创作实验,相反,他在创作时所选择的形式,取决于文本要表达荒诞的哪些方面,换言之,在加缪的创作中,文本的形式是为表现荒诞主题服务的。
“隐性角色”这一概念出自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热奈特认为:“如果说故事内受述者存在的后果是他总夹在我们和叙述者中间,使我们与后者保持一定距离……那么接受主体越隐蔽,在叙事中提得越少,每个真正的读者就或许越容易、或不如说越难以抑制地把自己视为这个潜在的主体,或用自己去替代这个主体。”[2]185对于《堕落》中的陌生人来说,从文本而言,他并不是克拉芒斯的“偷听者”而是受述者,从克拉芒斯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会对克拉芒斯的话进行回应或补充。但从阅读效果而言,他又是隐藏在文本之下的,加缪并没有赋予他明确的身份,他的所有话语也都是由克拉芒斯转述的,这样来看,他又似乎成了《堕落》的隐含读者。由此,《堕落》中的陌生人实际上是隐含读者与故事人物形象结合的产物,由于这一人物形象在文本中的独特作用,使得他没有被赋予明确的身份(姓名、地位等),文本中也不直接涉及他对克拉芒斯的“答语”,从阅读效果而言,他的确是隐形的。由此,可以认为,“隐性角色”即是参与文本情节发展、在文本中并不被赋予明确的身份、其角色功能的实现需要依靠文本中其他人物的话语或动作的角色,他与作品中的主要角色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共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堕落》中的隐性角色并不是小说的主要角色,但他的存在使得叙事者在文本中的活动成为可能。克拉芒斯与他的倾听者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墨西哥城”酒吧相遇的,这家酒吧与寻常酒吧不同,它的老板是一只听得懂荷兰语的大猩猩。在这位陌生人点完酒后,本该离去的克拉芒斯并没有走,而是继续与这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搭讪。从他们的第一次会面而言,这似乎的确是克拉芒斯的自言自语,因为这位陌生人对他的话并不感兴趣。在长达六页的话语中,克拉芒斯与这位陌生人严格意义上的互动仅有两次,一次是问这位陌生人是否要在阿姆斯特丹长留,另一次是根据陌生人的外貌以及他在听克拉芒斯说话时的诸多反应来推测他的身份。在陌生人表示要走时,克拉芒斯还热情地帮他带路,在带路的过程中不断地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及对时人时事的看法。从克拉芒斯的话语中可以推断出,这位陌生人是一名没有财产的男性,职业是律师,但是加缪却并没有在作品中给他名字,这使得读者在填补这位陌生人在文本中所留下的空白时可以将自身带入其中,这无形之中缩短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克拉芒斯与这位陌生人的对话并不是静态的,他们的对话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完成的。以克拉芒斯与陌生人的第一次对话为例,他们的对话从酒吧偶遇开始,到克拉芒斯把陌生人送回酒店结束,在离开酒吧后,克拉芒斯除了向这位陌生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之外,还对他们在回旅馆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此时,情节的推动是通过场景的无缝衔接来实现的,而场景则是通过两个人物“离开”“散步”以及相关动作的完成来实现切换的。“空间背景自身的性质是由叙事决定的。”[4]在这里,人的行动、空间转换、情节推动之间形成了一个三维三元关系网:场景伴随人的行动而转移;场景的切换使人物无时无刻都处在一个新的环境之中,而促使人物对新的环境做出反应(如克拉芒斯对阿姆斯特丹市民们的评价等);而这些反应在文本中便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话语,这三者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形结构,它们既相互作用,又相互牵制。
与《局外人》和《鼠疫》相比,加缪在《堕落》中对受叙人的塑造更能拉近读者与文本的距离。加缪认为:“为使一个荒诞作品有可能产生,思想必须以其最清醒的形式加以干预。”[1]103但他又强调:“思想必须不在作品中显露,要不然作为智力来指挥也行。”[1]103《堕落》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思想的实践。《局外人》与《堕落》一样,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这两部作品对受述人的选择却有很大不同,热奈特认为,受述者一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故事内的受叙者,其对应的是故事内的叙述者,即在文本结构内,受叙者和叙述者总是相对应而存在的;另一种是故事外的受叙者,但他特别指出,“故事外的叙述者也可以和默尔索一样,假装不面向任何人”[2]184-185。前文提到,《堕落》中的受叙者是一个隐性角色,他的行动和言语在文本中都依靠克拉芒斯的转述交代给读者,于是便在文本中形成了明显的召唤结构,吸引读者以自己的经验去填补该隐性角色在文本中留下的空白。在《局外人》的文本中,故事内的叙述人是默尔索,但在故事外的叙述人却并不存在,此时,文本于读者而言,是相对独立的,读者在这里所充当的是一个“局外人”,并不能参与到文本的叙事中,而这所产生的阅读效果就与《局外人》这一题目发生了关联。因此,可以看到,加缪在《局外人》中所选择的故事外的受叙者,实际上在叙事者的叙述过程中只充当了观众的角色,在文本中几乎不会有读者与文本进行互动的机会,而就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以理性支配其阅读活动,但对应而言,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便在读者的眼中显露无遗。这便与加缪理想的荒诞创作存在一定的距离。在《堕落》中,由于文本的受述人本身就是某种空白,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到文本之中,从而造成某种身份上的混乱,这实际上是有利于隐藏作品的思想的。
二、叙事结构——元故事叙事与内聚焦
加缪在《堕落》中采用框架式故事结构,将文本中相对松散的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框架式故事结构”这一概念,其内涵与热奈特所强调的元故事叙事相一致。热奈特认为,元故事叙事是一种二度叙事,它将文本分为故事外层叙事和故事内层叙事,并可根据因果关系、主题联系、叙述牵制等因素将元故事叙事分为三种类型。按照热奈特对元故事叙事的分类,《堕落》属于元故事叙事的第三种类型,即“在故事中起作用的是不受故事内容牵制的叙述行为本身”[2]162。在《堕落》的每个部分结束,克拉芒斯总是会得到继续与这位陌生人谈话的机会。如在第一部分,克拉芒斯就在与受叙者的对话中留下一个悬念:感化律师是什么?这便为第二天与受叙者的见面提供了可供叙述的话题;在第二部分的结束时,他又对受述人说“我大概明天能再见到您”[5]32,这实际上是他在向这位受叙者所发出的第二天见面的邀请;第三与第四部分实际上是在一天内发生的,第三部分结束时,克拉芒斯留下了感化法庭法官的悬念,为第四部分的叙述做了铺垫,他意图先向受叙者“说纵欲和土牢的事”[5]75,但克拉芒斯的叙述并没有在他讲完“纵欲和土牢的事”之后结束,相反,他又给受叙者留下了一个关于在大城市里游荡的独身汉的悬念。在上述几个部分中,克拉芒斯的叙述都相互独立,但由于这些悬念的存在,使得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内容得以联结。从文本的整体来看,克拉芒斯的叙述行为构成了故事外层叙事(或第一度叙事),克拉芒斯在每个部分所叙述的内容是文本的故事内层叙事(或二度叙事),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得以存在的合理框架。
与此相对应的是,《鼠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二度叙事,但《鼠疫》的第一叙事层并不像《堕落》一样在文本中与第二叙事层不断交替,从而不断地产生新的叙事内容,相反,《鼠疫》的第一叙事层仅设置在整个故事的开始和结束,呈现出一种闭环结构。在《鼠疫》中,第一叙事层与第二叙事层相对独立,从叙述顺序的角度而言,《鼠疫》的第一叙事层采用倒叙,而第二叙事层则使用的是顺序,在第一叙事层的开始,叙述者便说:“构成此编年史主题的奇特事件于194-年发生在阿赫兰”[6]1,并在随后的四页内容中,就阿赫兰这个城市以及叙事者所应注意到的事项进行论述,随后便迅速将第一叙事层隐匿,同时将第二叙事层展现给读者。在第二叙事层结束之时,第一叙事层又展现在读者眼前,并交代了“里厄大夫正是在这一刻下决心编写这个故事”[6]272,意在告诉读者,里厄大夫才是这本书的记录者。在此,从阅读效果而言,第一叙事层与第二叙事层发生融合,并形成了一个复合的叙事结构。
诺埃尔·卡罗尔认为:“一段话要具有叙事性的联系,就必须显示出至少具有一个统一的主题。”[7]189在卡罗尔看来,贯穿于作品的统一的主题是使作品的叙事之所以成为叙事的一个关键因素。他强调:“事件和/或情况必须被联系起来,它们不可能仅仅是一连串彼此分离的事件和/或情况。”[7]189在《堕落》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叙事相对松散,各个部分的叙事内容所表达的主题也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仅从文本所体现出来的结构上来分析《堕落》的叙事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就连加缪本人也认为:“在稀薄的荒诞空气中维系的一切生命,如果没有某种深刻的和一贯的思想有力地激励着,是难以为继的”[1]99。荒诞即是贯穿《堕落》始终的主题。克拉芒斯自诩他的礼貌远近闻名,他喜欢帮助盲人过街,当他在遇到另外一位向盲人伸出援手的陌生人时,总是要抢在另外一个人之前将盲人带到安全地带;他会从卖花老太太那里买下她们从公墓亲友献花处偷来的鲜花,并自认为这是在帮助她们;他一方面十分享受来自周围世界对他的迎合,另一方面又认为“友谊一旦获得,就没有办法甩掉,而且必须加以应付”[5]25。克拉芒斯自诩出身正派,只喜欢高处,讨厌地洞、深渊之类,并尤其讨厌洞穴学者,但他却在家里却藏了“穴居人”偷的画,这些无疑不体现出克拉芒斯行为的自相矛盾,而这正是作品荒诞主题的体现。
与《鼠疫》采用多重式的聚焦叙事不同,《堕落》采用固定式叙事视点。在《堕落》的文本中,展示给读者的只有克拉芒斯的“有限视野”,他向受叙者所讲述的有关他的过去生活的回忆以及他对于某些实事的看法,其立场都出自克拉芒斯自身,与前两部作品相比,《堕落》的情节性并不连贯,这样便使得这部作品无论从文本结构还是从叙事内容而言,都能够给读者带来混乱感,从而不断地增强荒诞感。此外,由于隐性角色这一特殊的受叙者的存在,使得文本出现大量引导读者介入的召唤结构。由于“有限视野”的存在,克拉芒斯在夜间不过桥的原因便成为一个悬念。在第一部分中,他对此解释为,“这是由于某种祈愿”[5]12。但他随后的话也暗示了他夜间不过桥是另有原因的。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克拉芒斯又向受叙者提到某夜他在艺术大桥散步的事情,这便与他先前所述的他“夜间从不过桥”形成了矛盾,这次在桥上散步时,他听到了笑声,但他却找不到笑声的来源,因为在他的身边并没有其他人,于是,他推测笑声来自水上,并认为这笑声是“善意的、自然而然的、几乎是友好的”[5]32。这便能引起读者的怀疑:为什么在无人的桥上他竟可以听到笑声?这一悬案终于在第三部分得以解释:克拉芒斯不过桥的真正原因是他某次在桥上散步时目睹了一位黑衣少女投水,而克拉芒斯既没有对这位少女伸出援手,也没有在这位少女投水之后采取任何救援措施。在解释完后,他还对受叙者表示他对这位落水女子的后续一无所知,甚至有好几天都没有看报纸,他看似对此毫不在乎,但在克拉芒斯后续的回忆中,我们会发现,这名女子是他永远的阴影,与女伴乘客轮时,他还误把远处洋面上漂来的一个黑点看作是那名溺水的女子,在小说的最后,他再次向受叙者提到了这位溺水者,并说道“如今为时已晚。永远是为时已晚”[5]115。溺水少女是贯穿故事始末的一个因素,她使克拉芒斯“原罪意识”得以形成,也正是由于这位溺水少女的存在,使得克拉芒斯那些自相矛盾的话语有了合理的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加缪在文本中建构荒诞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对荒诞进行解构,而这种建构与解构之间的矛盾正是加缪所追求的荒诞。
相比较而言,《鼠疫》的聚焦叙事要更加多样。多重聚焦使得作品的视角不断发生变化,由于加缪在《鼠疫》中安排了众多人物角色,这也就使得多重聚焦成为可能。前文提到,《鼠疫》同《堕落》一样,也呈现出元故事叙事的结构,因此,我们将逐叙事层对叙事焦点进行分析,以探求其特征。《鼠疫》的第一叙事层为“鼠疫”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行为和话语都提供了一个框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里厄医生在第一叙事层和第二叙事层都充当了主要的叙事者,但并不能将这两个叙事层之间的里厄医生等同。第一叙事层的里厄医生是《鼠疫》这个文本的叙事者。在《鼠疫》的最后,文本中又出现这样的话语:“厄大夫正是在这一刻下决心编写这个故事”[6]272。此处是一个典型的作者介入,但这里的作者并不是加缪,而是里厄医生,他成为沟通读者与文本的桥梁。第一叙事层的里厄医生是故事的创造者,他所使用的是全知视角,他对文本中的每一个人物的行动、话语、思想的表现都有绝对的话语权。在第二叙事层中,里厄医生仅是鼠疫的经历者之一,尽管文本中有大量的篇幅是通过他的视角来展示鼠疫的发展的,但文本也多次出现视角的转换,来展现其他人在面对鼠疫时为逃离所做的种种努力,如朗贝尔以及在开始时处于旁观者的角度来记录这场瘟疫的塔鲁,在叙述他们的这些行动时,叙事焦点便自然而然地由里厄医生转换为塔鲁或朗贝尔。此外,在《鼠疫》中,加缪通过格朗的视角旁观了女商贩谈论阿尔及尔一名商行职员在沙滩上杀死一名阿拉伯人的案件,而女商贩所谈论的这名商行职员,自然是《局外人》的主角默尔索,由此,《局外人》和《鼠疫》形成了某种时空上的联结。
三、作家的隐匿与伪介入
作家的隐匿与伪介入都是针对加缪在小说中所塑造的叙述者所产生的阅读效果而言的。乔伊斯说:“艺术家就像创造万物的上帝,他存在于他亲手创作的成果的内部,后面,之外,之上……他升华到了存在之外……”[8]在乔伊斯看来,理想的艺术创作中不应该留下创作者的影子,他应该隐匿于作品之外,不着痕迹。纵观加缪的《局外人》 《鼠疫》和《堕落》,我们会发现,尽管这三部作品的叙事风格各有不同,但仍可以将这三部作品按照作家介入的程度分为两类:《局外人》与《堕落》属于作家隐匿于作品之外的一类;《鼠疫》属于作家介入程度较大的一类。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分类仅是从文本的角度来进行的,前文提到,《鼠疫》存在两个叙事层,第一叙事层形成一个闭环结构,在这个闭环的内部,第二叙事层得以展开,《鼠疫》第二叙事层的叙事者有多位,叙事视点也随着叙事者的变化而变化,但这部小说的叙事者始终是里厄医生,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作家介入是以文本所呈现的叙述效果而言的。在《鼠疫》的叙述者正式讲述阿赫兰发生鼠疫这一故事之前,写了下面一段话:
倘若他不曾有机遇去搜集一定数量的陈述词,倘若当时发生的形势未曾将他卷入他意欲详述的那些时间里(人们会及时发现他的)就几乎没有资格从事这个工作。……当然,史学家,哪怕是业余的,手上总有些文献,所以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本人的证词,其次是别人的证词,因为他扮演的角色是他有可能搜集这段历史中所有人物的心里话,最后是终于落到他手里的文字资料……[6]4
加缪在开始时便给读者设置好了陷阱,他通过对鼠疫的发生地——阿赫兰的社会和人文环境的介绍,给读者制造出一种作家介入《鼠疫》文本叙事的错觉,但我们可以从上述引文中可以提炼出一条关于叙述者的关键信息:叙述者是故事的参与者,且在故事中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鼠疫》中,加缪本身并不介入文本叙事,而是让作为故事的叙事者里厄医生不断地介入第二层叙事,从而产生一种伪介入的效果,即在含有多个叙事层的文本中,真实的作家并不介入文本叙事,但会通过文本中最外层级的叙事层中的叙事者不断地对下一级叙事层不断介入而产生某种类似于作者介入的效果。总而言之,伪介入不是作家对文本的介入,而是在存在多级叙事层的叙事者对文本的不断介入。文本开始时便交代了这是一个编年史主题的奇特事件,在上述引文中,作为历史而言,“本人的证词”之所以能够在叙事中有足够的可信度,那只有一个原因——本人是亲历者。且后面又提到“他扮演的角色……”,便让读者更加确信叙事者并非《鼠疫》真实的作者加缪,而是另有其人。而《鼠疫》的独特之处在于,叙述是以第三人称来进行的,而第三人称叙事最便于转换叙事视角,这便不得不让读者怀疑故事的叙述者到底为何人,谜底直到最后才被揭晓——叙述者就是在故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里厄医生,或许可以使用《鼠疫》的题记来形容这种阅读效果:“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6]1。
与《鼠疫》不同的是,《局外人》和《堕落》这两部作品是完全将作者隐匿,且在文本中也没有出现与《鼠疫》类似的作家伪介入的情况。我们前文提到,《局外人》其本身并没有特定的受叙者,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和读者都被隔离在故事之外,两者都不会对故事的走向产生影响,而这样就产生了布莱希特所追求的“间离效果”。布莱希特认为,所谓的“间离效果”即是“一种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9]从根本上来说,布莱希特所追求的“间离效果”只是为了能够让观众在面对戏剧时不受表演的影响,从而独立于戏剧之外,以便使读者就表演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内容进行反思。而《局外人》由于其本身并没有在文本中指明受叙者以及文本之外的理想的读者,因此,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所能够受到的来自文本叙述形式的影响较小,从而更能够对作品及作品中所隐喻的社会现实作出独立的反应。前文已经指出,由于隐性角色的存在,读者在阅读《堕落》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身份的混淆。此外,《堕落》的情节并不连贯,它是由几次对话所构成的,且克拉芒斯向受叙者讲述自己的往事时,还会加入大量的关于社会、宗教、道德等的评价,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读者容易受到叙事者的影响,从而在无形之中接受叙事者的价值标准,从这一角度而言,读者在此时实际上失去了自己作为独立的读者的身份。
上文提到,加缪的创作是主题导向而非文本形式导向,但是,对于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的等同性问题,加缪的态度一直是明确的,那便是作家不等于角色。加缪曾不止一次指出,他希望“自己能是一个客观型的作家”[10]160,所谓“客观型的作家”,是指在自己的作品中“从来就不把自己当作被描述的对象”[10]160。在《反抗者》中,加缪强调“小说中的人物永远不会是创造这个人物的小说家”[11]43,但“小说家可能是他同时创造的所有人物”[11]43。加缪认为,“反抗要得到一切,否则便什么也不要”[11]65,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作家是他“创造的所有人物”即是强调作家要“得到一切”。从本质上而言,加缪主张作家将自己渗透入作品中,将自己与作品交融,而非将作品中的角色塑造成自己,或自己的代言人,作家与作品交融的具体表现即是作家在作品中的隐匿。有趣的是,尽管加缪一再强调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不能将创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但他同时也强调,作品要能够表现自己的思想,在《西西弗神话》中,他提出“选择一部作品来阐明自己”[1]109,在手记中,他又写下这样的文字:“一位作家首先要学会的技巧,就是如何将他感受到的转换成他想要让人感受到的”[12]。无论是阐明自己,还是要让读者感受到自己的思想,都是在强调一种作家与阅读者之间的共情。如何实现共情?理想的途径是使用介入叙事。杰拉德·普林斯认为:“介入性叙述者用他或她自己的声音对被呈现的情景与事件、表述或其语境等做出评价。”[13]然而介入性叙述过于明显则会造成作品中的叙述者或某一人物成为作家自己的现象,这与加缪反对将作家与作品人物等同的观点形成了矛盾。于是,《鼠疫》中的“伪介入”与《堕落》中的对话形式便成为加缪解决自己创作主张与创作实践矛盾的方式。前文提到,《局外人》和《鼠疫》借助莫尔索杀阿拉伯人这一事件实现了时空联结,而加缪在创作的过程中所选择的作家隐匿与伪介入的统一则实现了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协调。
四、时序——时间倒错
加缪坦言:“我感兴趣的,主要不在于发现种种荒诞,而是荒诞产生的结果。”[1]16揭示荒诞的存在只是加缪的起点,如果对加缪的荒诞哲学分层,揭示荒诞属于第一层;提出解决荒诞的方法是第二层;而走出荒诞后追寻爱与自由是荒诞哲学的第三层。与哲学思想相对应的是他的小说创作,上文提到,加缪的小说创作是主题导向的,因此,加缪小说的叙事特征会随着加缪思想的发展而变化。然而,尽管具体的叙事形式存在差异,但加缪的小说却呈现出一种相对固定的效果——时间倒错。热奈特认为:“研究叙事的时间顺序,就是对照事件或时间段在叙事话语中的排列顺序和这些事件或时间段在故事中的接续顺序。”[2]14从热奈特对《追忆似水年华》的分析来看,他所谓的“对照”实际上是一种“还原”的过程,或者可以说,“还原”是“对照”的前提。热奈特把叙事与故事时间重合的状态称作“零度”[2]14,在文学作品的叙事中,零度是一种理想状态,大多数文学作品中都会或多或少存在时间倒错的现象,因此,无论是对于叙事学家而言还是读者而言,在研究和阅读作品的过程中都需要将故事内时间由原来在作品中呈现的形态还原为符合故事发展逻辑的形态。前文提到,加缪并不主张将作家等同于作品中的某个角色,但他早期的作品却带有自传性色彩,《快乐的死》是加缪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把自己所有的经历全部堆砌到作品中,就像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写其他作品,像要把所有的话全吐尽一样”[14]。由于出现过多的作家个人的经历,小说内部情节的发展便不再是符合逻辑的自然顺序,作家的意志与小说的情节发展之间也相对应地会出现一种矛盾。显然,加缪并没有处理好这一矛盾,或者可以说,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矛盾的存在,因此,在小说叙事中便出现了时空倒错。值得说明的是,除《局外人》之外,加缪的其他小说都或多或少存在这种时空倒错的情况,与《快乐的死》不同的是,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个人意志与小说情节发展逻辑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妥善地解决,加缪不再把自己过度展现在小说中,而是使用如上文所说的“伪介入”或“作家隐匿”的方式,将自己的主张隐匿于文本之下,形成召唤结构,等待读者发掘。
加缪小说中的时空倒错共有两种类型:中心—分散型和现实—回忆往复型,前者主要指《鼠疫》,而后者则包括《堕落》 《第一个人》等作品。热奈特认为:“故事时间几乎从来没有以必要的精确表示出来或‘推算’出来。”[2]54因此,对作品的时间线进行梳理,应该以故事发展的先后作为参照或时间单位,而非具体的时间。由于聚焦叙事多样,《鼠疫》中存在多条故事线,相对应的便存在多条时间线。反抗是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对抗鼠疫的过程是这部小说的主时间线。还应该注意到的是,《鼠疫》中存在两个叙事层,第一叙事层的叙事者是里厄,用全知视角交代了小说中所记载的事件是“过去”,小说的时间线从总体上来说是倒叙,在《鼠疫》中,第一叙事层对第二叙事层产生了几次干预,如小说开始介绍这是一部编年体事件,叙事者还谈到了他认为的理想的被记载下来的编年史事件应该具备的两个标准,即证词和材料。在小说的结尾,“记录者”又使用了“倒叙”,告诉读者“里厄医生正是在这一刻下决心编写这个故事”[6]272,接着,叙事者又写道:“故事到此为止,编写的初衷是不做遇事讳莫如深的人”[6]272。“故事到此结束”并不代表《鼠疫》这部小说的结束,而是第二叙事层的结束,同时代表第一叙事层的重新开始,故事时间的终点与叙事时间的新起点重合,这种重合便是热奈特理想的“零度”。尽管存在干预,但《鼠疫》的第一叙事层仍是一个闭环结构。但第二叙事层的时间线要比第一叙事层更加复杂。在第二叙事层中,各叙事者所属的时间线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呈现出相互交叉的复杂形态,而对抗鼠疫这条主时间线是各个叙事者、见证者的时间线融合的结果,其中,主时间线又以里厄医生的抗疫经历为载体,与各支线之间呈现一种离心型结构,即中心—分散型结构。除了里厄的时间线外,塔鲁和朗贝尔的时间线也占据了第二叙事层的大部分内容。各时间线之间的切换并不生硬,而是通过两个时间线之间的人物进行互动的方式来展现的。塔鲁是《鼠疫》中另一位较为重要的角色,他不是奥兰人,但他热衷于以第三者的视角记录奥兰城,“在全城居民惶惶不可终日之际,他却总以史学家的眼光竭力记述一些算不上历史的琐事”[6]20。小说第二叙事层中共有两处引用了塔鲁的记录,两处都与鼠疫有关,还有一处是塔鲁与里厄医生的对话,这是塔鲁的自白,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朗贝尔的时间线与塔鲁相比,独立性更高,但其仍与里厄的时间线存在联系。朗贝尔希望能够逃离奥兰城,柯塔尔成为帮他出城的中间人,但他逃离的过程也是成长的过程,最终,他放弃了外出的机会,选择和里厄医生一起对抗鼠疫,朗贝尔和里厄的时间线在此处发生融合,由此,《鼠疫》反抗的主题便更加明显。
与《鼠疫》不同,《堕落》与《第一个人》呈现出一种“现实—回忆”往复型时间倒错。克拉芒斯的对话主要有“评判”“回忆”“忏悔”这三大内容组成,其中,“回忆”占据了《堕落》的大部分篇幅。他向受述人所讲的感化法官、与女性相处的经历、纵欲和土牢、当教皇的经历等都是回忆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并不像《鼠疫》中的第二叙事层一样拥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克拉芒斯不断介入其所回忆的内容,或是以评判的方式,或是由于外界的干扰而中断回忆,而《堕落》叙事散乱的原因正是叙事者不断介入故事内部的结果,由于这种介入的大量存在,使得故事呈现出混乱的状态。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克拉芒斯对故事进行了介入,但《堕落》中有关克拉芒斯的回忆并不存在“零度”,原因便是克拉芒斯是以“现实时间”强行中断了“故事时间”,这两者在《鼠疫》中的关系是相互代替而非是融合与分离的关系。《第一个人》与《堕落》相似,但《第一个人》中的故事的完整性要高于《堕落》。寻父是雅克回到阿尔及利亚的目的,但他却在蒙多维“寻回了童年,而不是父亲”[15]。由此,雅克“寻父实际上是寻找文化身份”[16]对文化身份的追寻这一基调也使得这部小说是以回忆为主的。在《第一个人》中,回忆也大多被现实打破,如雅克对埃尔斯特舅舅的回忆就被后者的敲门声打断。现实的介入意味着故事时间的断裂,在加缪这里,故事的完整性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表现出小说的主题,《堕落》中故事的混乱是揭示荒诞、表现克拉芒斯忏悔的载体,而《第一个人》中现实与回忆的往复则是表现小说追寻与爱的主题的理想载体。
加缪以荒诞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展现了荒诞的不同侧面。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并不是相互孤立的,相反,它们不同程度地存在某种互动或联结,这些联结是加缪荒诞创作理论的内在要求。加缪并没有在《西西弗神话》与《反抗者》中建立一套完整的荒诞哲学体系,但他从多个侧面论证了荒诞的存在及反抗的必要性,他就像一位现象学家,注重“直接认识”。然而,在作品中,他总是能够通过情节的安排、叙述者话语的构造,使读者反思隐藏在文本之下的荒诞哲学。此外,尽管加缪一再强调荒诞,但他同时也强调作品与生活的联系,在加缪创作的篇幅较长的小说中,大部分故事都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尤其是他在阿尔及利亚生活以及他国游历的经历。这些经历对加缪而言,就像他评价《反与正》那样,是他“创作的源泉”[10]4。而这却并不与加缪的荒诞创作相矛盾,因为加缪始终认为,“荒诞的这种状态,重要的是要生活在其中”[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