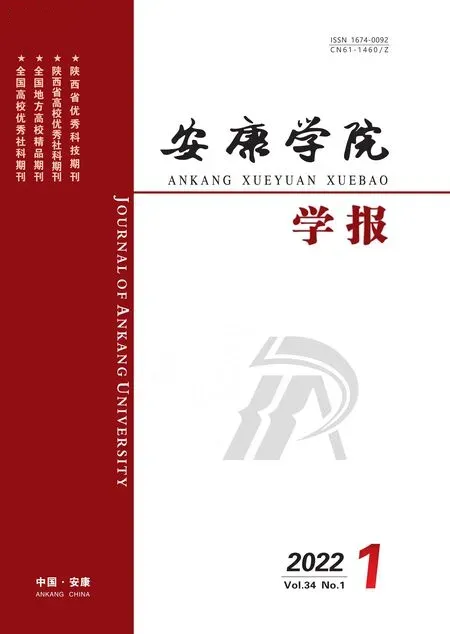认罪认罚视域下取保候审常态化路径构建
童椿楠
(浙江工商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问题的缘起:认罪认罚下取保候审率持续低迷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准确惩罚犯罪、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推动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具有重要意义,认罪认罚从宽包括实体上的从宽和程序上的从宽,虽有学者对“强制措施从宽”的提法持反对意见,认为其不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1],但不可否认的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强制措施的司法适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1款明确规定,将认罪认罚的情况纳入社会危险性的考量因素。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认罪认罚指导意见》)第19条也有类似表述。但是在推进认罪认罚的过程中取保候审却在实践中遇冷,未能发挥预期中提高非羁押率的效果。截至2018年9月30日,在法院审结的20余万件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候审的只有42%;被监视居住的更少仅为1.31%,二者合计为43.31%[2]。也就是说,超过一半认罪认罚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未因为自愿认罪认罚而被取保候审。
长期以来,我国取保候审率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即使是在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未决羁押率居高不下、羁押期限过长等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甚至出现逮捕羁押措施“惩罚性”的倾向,严重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矛盾,也与我国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以“非羁押为原则,羁押为例外”的规定背道而驰。未决羁押率高、超期羁押,取保候审难度大,加之缺乏法院事先司法审查,我国的强制措施制度极易成为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权司法保障的攻讦点,不利于我国法律与国际社会接轨,实现“走出去”的目标。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过程中,应当抓住时机,提高取保候审适用率,实现在认罪认罚背景下取保候审常态化。
二、认罪认罚背景下取保候审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未决羁押负面效应积聚
在推进认罪认罚的进程中,虽然两高三部在《认罪认罚指导意见》表达出对于认罪认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更多地适用非羁押性措施的倾向,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长期以来“羁押为原则”的思维惯性和对羁押措施的严重依赖,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措施的适用并未得到大幅提升,而未决羁押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在不断积聚。首先未决羁押带来沉重的财物负担,耗费了高昂的羁押成本。根据浙江省监狱管理局2020年度部门决算数据显示,2020年度浙江监狱支出合计646618.3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95128.40万元,占76.57%[3]。其次羁押监管场所的管理风险隐患在持续增强,新冠疫情对中国的社会秩序的平稳有序运行带来了巨大影响,监狱看守所等较为封闭的场所也未能幸免,截至2020年2月20日,全国共有湖北、山东、浙江3个省的5个监狱发生罪犯感染疫情,为全国的监狱看守所等羁押监管场所敲响警钟。虽然从全国范围看,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监所管理的风险和压力并不会有所减少。不仅如此,未决羁押容易引发人权保障风险以及高额的国家赔偿,例如2012年朱升机申请徐闻县人民检察院无罪逮捕国家赔偿案、2014年蒙庆争申请青秀区人民检察院无罪逮捕国家赔偿案,两案均是由于检察院无罪逮捕而导致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受到侵害,由此产生的国家赔偿。再者非羁押监管措施在实践中适用偏少,以杭州市2019年羁押情况为例,全市采取刑事强制措施36427人,其中看守所羁押刑拘和逮捕的24548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11879人,刑事强制措施非羁押率仅为32.6%,且非羁押人员进入审判程序不到70%[3]。几乎可以断定,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时持极为谨慎的态度,对于取保候审条件适用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把控。
(二)法院司法审查闭环缺失
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这相较于国外的检察机关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因此在逮捕羁押问题上,我国并没有建立由法院主导的司法审查制度,而是采取由检察机关主导的审查制度,在侦查阶段的批准逮捕,以及在审判前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均由检察机关进行。“捕诉合一”虽为检察机关内部机构改革,但在实践中这种合并存在着使本就薄弱的审查逮捕环节被强势的公诉审查环节所吞没的危险[4]。批准逮捕的独立性以及所具有的司法审查职能在逐渐丧失。而就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而言,其主要特征之一是监督权与处分权的分离,法律监督权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实体处分权[5],检察机关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均以法律建议书的方式作出,缺乏刚性保障。而就羁押必要性的条文而言,根据我国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95条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对所有未决羁押人员负有主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义务,但由于案多人少、审理期限限制、司法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并非会对所有案件均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第3章的规定,检察机关虽然可以对羁押必要性审查采取公开审查的方式,但是并未赋予“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方获取证据并质证的权利,听审的“对抗性”严重不足。并且没有任何法律对于取保候审申请被驳回后的救济措施做出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也无权就取保事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或向上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提起申诉。
(三)取保候审监管存在现实障碍
取保候审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立法对取保候审适用的问题以及保证人责任等规定均过于笼统,现实中“取而不保”“脱保”等情况频发。监管手段单一,缺乏创新,容易对取保候审监管形成困境。司法实践中,执行机关怠于开发有效方法对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期间遵守相关义务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考察[6]。多采用简单的定期传唤刑事讯问的方式作为监管。部分执法部门跟踪监管不足,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情况的变化缺乏有效的监管和跟踪,容易导致被保证人滥用取保的权利,擅自脱离监管范围,例如嫌疑人出于身体原因而被取保,在其病愈后,却因缺乏及时有效的跟踪监管而并未及时变更强制措施,使其所含的诉讼风险持续扩大。同时执法部门人员紧张,基层执法力量分配不足是客观上造成取保候审监管困境的重要原因。加之,取保候审监管主体之间协作难度大,难以有效调动犯罪嫌疑人单位、街道、乡村、社区和派出所等综合监管主体活力,使得监管力量薄弱、监管力度难以加强。加之保证方式单一,对于财保方式的限制过多,对于基金、不动产等非现金性财产持否定态度,更枉论个人信用担保。
三、逮捕羁押审查的国际发展潮流
无论是逮捕、搜查,还是羁押,都属于涉及限制或剥夺个人人身自由、财产权和隐私权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国外法治国家在涉及公民权益的强制措施上,基本都建立了由法院司法审查的制度。司法审查主要表现在法院同步实施的许可和授权以及事后进行的听审和裁决方面[7]267-269。
(一)推行“司法令状主义”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搜查、扣押、逮捕等问题上,大部分国家均采取了“司法令状主义”,即除紧急情况下,在侦查阶段涉及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财产权和隐私权的强制措施必须经过法院事先司法授权,而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未经司法授权的强制措施,也必须在事后立即接受司法审查。在美国,美国对警察所具有的查封、扣押、搜查、逮捕、羁押、保释、讯问等权力设置了严格的司法审查制度,并且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所享有的对抗防御性权利上升到宪法的高度,纳入“正当程序”的原则体系。除法定情形外,美国警察在采取逮捕措施前,必须取得法官签发的司法令状。在意大利,在紧急情况下司法警察可以在取得检察官许可的情况下直接实施涉及公民权益的强制性措施,例如逮捕、搜查、查封等,但在行为完成之后必须立即向预审法官报告,接受预审法官的司法审查[8]。“司法令状主义”推行限制了警察侦查权的肆意扩张,对保障人权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推行“严格事后审查”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针对严重涉及人身自由的逮捕和羁押均采取了严格的事后审查模式。在采取逮捕等强制措施之后,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必须被不迟延地带到法官面前进行逮捕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即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事后庭审和作出是否继续羁押的裁决。在美国,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无论是被令状逮捕,还是被紧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都必须在“无不必要拖延”的情况下被立即送到最近的法官处进行初次聆讯。与英美相比,德国的法官较少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保释的决定,更倾向于采取羁押措施,因此相较于英美,德国拥有更为严厉的司法事后审查。在德国,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的规定,凡涉及公民人身、财产、隐私权的强制措施一般都必须接受法官的司法审查。无论是经过事前法官授权的逮捕,还是未经授权实施的逮捕,都要在逮捕行为实施后立即接受法官的司法审查。而在羁押的任何阶段,无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提出撤销羁押的申请,德国法官都必须每隔三个月对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且德国的宪法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还可以对其所受的羁押进行特殊的司法审查[7]272-275。
(三)推行“对抗式听审模式”
国外针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继续羁押的问题多采用“对抗式”的听审模式,并增强了犯罪嫌疑人一系列相应的诉讼权利。在意大利,预审法官一般要进行一次专门的听审活动,公诉人、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均有权出席,并有权发表各自的意见,当不服预审法官在听审中作出的裁决时,控辩双方均有权提起上诉。在英国,治安法院收到保释申请后,会就保释问题举行由警察、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皆出席的听审活动,控辩双方陈述意见并进行辩论,法官做出裁判。若保释仍遭拒绝,犯罪嫌疑人就程序性问题有权上诉到高等法院;就侦查阶段遭受不当或非法拘禁的事由,有权向高等法院王座庭申请人身保护令,王座庭将就羁押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举行控辩双方同时在场的庭审活动,并做出裁判。
四、构建认罪认罚中取保候审的常态化机制
(一)严格遵循双重取保候审的双重逻辑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什么情形下适用取保候审制度作出直接规定,而是采用适用逮捕的条件来倒推取保候审的条件。而逮捕条件内含双重逻辑设置,一是具有社会危险性,二是具有不可替代性。就社会危险性而言,需要达到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1款规定的5种社会危险性的程度,即并不是指不具有社会危险性,而是社会危险性需要达到取保候审无法防止的程度,且此类社会危险性具有明确的法律限定,并非是不设边界的。换言之,即使具有一定社会危险性,但未达到法条明文规定的5种社会危险性的程度,就应当在原则上适用取保候审。而《认罪认罚指导意见》第21条提到的“没有社会危险性,不提请审查逮捕、不批准逮捕”实为对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社会危险性的误读。
当然社会危险性是种模糊的概念,在现实中经常难以精准把控,因此可以参照美国司法部研发的审前服务风险评估工具(PTRA)和英国青少年司法委员会推行的Asset和AssetPlus,由最高检牵头以近10年进入司法系统的所有犯罪嫌疑人为样本,进行大数据分析,建立适合我国的逮捕社会危险性模型。就不可替代性而言,采取逮捕措施时,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必备前提,且需要同时证明采取逮捕强制措施是不可替代的。“不可替代性”与“社会危险性”之间不能完全等同,“不可替代性”中内含证明过程,是“社会危险性”所不能涵盖的,在实践中不应当得到省略。
(二)构建取保候审制度的司法闭环
由于我国检察机关的特殊性以及我国“流水线式”的诉讼模式,不宜直接照搬国外的法院司法审查制度,容易造成“水土不服”的现象,而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最佳的选择是在检察机关原有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上进行优化。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程序上,采用“主动审查+被动审查”相结合的双轨模式。由于司法成本和案多人少的客观禁锢,对所有案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应当有重点、有方向地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检察机关要对具有防卫过当、认罪认罚、自首、立功、初犯、偶犯等情节以及一些轻微刑事案件进行重点主动审查,及时变更强制措施,以提高取保候审率,尤其是对于认罪认罚案件必须全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在《认罪认罚指导意见》中重点强调对于已经被采取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重要性,对无须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变更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一方面对刑事诉讼程序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减少了对证据的收集、提取和固定的司法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所具有的社会危险性和人身危险性降低。此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足以防范其可能具有的诉讼风险和社会风险。对于近亲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等申请启动羁押审查的案件需要高度重视,对于拒绝申请决定的案件,必须作出书面回应并注明理由。
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听审活动中,应增强审查活动的“对抗性”。逮捕措施决定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组成的“控辩双方”需要具备举证质证、进行辩论的权利。基于程序正义理论,“在一项政府决定中具有充分的利害关系或者权利攸关的人,在反驳不利证据武装时,应当被赋予面对面交叉讯问、获悉理由和不利证据的机会”[9]。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活动中,“辩方”应当有权获悉决定机关采取逮捕羁押措施的理由和证据,以便在此基础上行使辩护职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控方”同样有权充分论证其决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有权对“辩方”提出的意见进行反驳和质疑。“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交锋对决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重要来源。
拓宽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司法救济途径是完善中国特色羁押制度,提高非羁押率的必经路径,通过增加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司法救济渠道构建起取保候审制度的司法闭环。检察机关在进行羁押审查时所具有的权力是否为司法权一直存在争议,而即使是法院的司法权,犯罪嫌疑人也有权通过上诉等方式获得救济,但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时检察机关作出的决定却为终局决定,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救济权遭到剥夺。这与法治理念和人权保障是相悖的,应当在制度上增强对取保候审申请被驳回的司法控制与救济,增加对不服检察院羁押必要性审查决定向上级检察院申诉,或向法院起诉等司法救济途径。而针对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仅能提出法律建议的问题,应当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将检察建议逐渐变为事实上的“应当”,具有强约束力,提高检察建议的刚性制约,以提高检察机关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积极性,提高取保候审率。
(三)增强电子大数据监管措施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大数据、区块链的发展,有效运用大数据,采取电子监管等新型监管模式和定期讯问回访等传统监管模式相结合的方式,将优化取保候审的执行方式,化解取保候审监管难的问题。其一是佩戴电子环等电子跟踪装备,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控。例如2014年四川省出台《四川省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执行工作管理规定》对被监视居住人,可以采取GPS定位、电子手环、视频监视等电子监控措施,降低了执行人员的工作负担和压力。其二是利用现有的微信平台利用“位置共享”功能进行定位,用“视频聊天”功能掌握嫌疑人所处的环境[10]。其三是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数字监控APP结合智慧城市系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管。例如,2020年杭州出台《对刑事诉讼非羁押人员开展数字监控的规定》,利用“非羁码”APP对非羁押人员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的行为动向进行监控,并实行互动式监管模式。截至2021年2月8日,杭州市运用“非羁押”已对9196非羁押人员实行监管,无1人出现脱管情况,展现出数字监控的良好优势[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