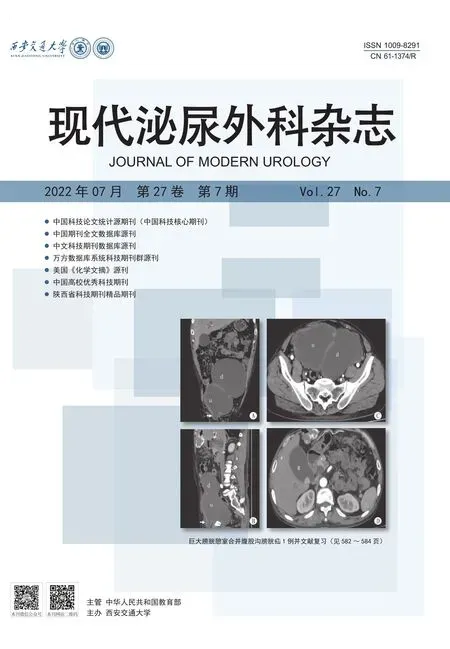循环肿瘤细胞在前列腺癌诊断及预后中的临床应用
谢张兴,高 亮,王 晨,汪道君,可龙龙,陈 捷
(1.南昌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院,江西南昌 330006;2.江西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江西南昌 330006)
前列腺癌(prostatecancer,PCa)是男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截至2020年,我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有所增加,与患前列腺癌相关的风险因素包括年龄、种族、家族遗传史和其他因素[2-3]。通常前列腺癌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初诊时疾病已经进展到晚期,甚至已经发生远处转移[4]。传统的前列腺癌诊断方法包括前列腺穿刺活检术、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imaging,mpMRI)检查以及测定血清肿瘤标志物,如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1, 5]。然而,经会阴或直肠前列腺穿刺活检是一种有创操作,且无法监测患者病情的动态变化,此外,PSA已被证明敏感性和特异性较低[6]。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检测作为一种新型的非侵入性诊断手段,弥补了传统方法的不足,具有高度敏感性,能及时反应肿瘤的恶性程度和侵袭能力,早于影像学预测复发和转移,相较血清学PSA检测,其灵敏度及特异性好,可定性、定量检测,并可作为肿瘤细胞分子生物学检测的标本,实现实时、动态监测癌症进展[7]。因此,随着精准医学的开展,CTC作为预测前列腺癌转移和预后的热点之一,CTC的研究可能更有助于临床工作者制定治疗策略。
1 循坏肿瘤细胞概述
1869年,ASHWORTH[8]在循环血液中发现肿瘤细胞,首次提出了CTC的概念,提出了肿瘤可能发生血液转移的机制。CTC是指自发或因诊疗操作由原发灶或转移灶脱落进入外周血循环的肿瘤细胞。它们非常罕见,在已经发生转移的癌症患者中,每10亿个正常细胞中约有一个CTC[9]。大多数CTC可以从循环中清除,但也有一些可以沉积在骨髓中,称为播散性肿瘤细胞,有的播撒于其他转移部位,重新种植于新的器官表达,导致肿瘤生长和血管生成加速的因子[10]。肿瘤细胞为了存活并播散至远处器官,在血液中需经历一系列过程[11],例如与血管壁、正常细胞的碰撞及遭受化疗药物的攻击、免疫系统的监测等,导致大多数CTC遭到破坏,幸存的CTC经历了上皮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这一生物学过程。EMT是黏附上皮细胞通过迁移和侵袭特性的过程,突破基底膜,逃离原发肿瘤,并在循环中存活[12-13]。目前已经发现CTC成簇状分布,可能代表癌栓或血管内增生的产物,簇状CTC的确切意义尚不清楚,但大量研究表明,它们的基因表达谱与单个CTC不同,并且其转移潜能是单个CTC的23~50倍[14-15]。曾有学者尝试从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CRPC)患者体内分离出CTC并将其植入小鼠体内,结果未发现任何肿瘤生长迹象,这表明CTCs具有异质性[16]。
2 CTCs富集与检测
CTCs的罕见性和异质性给CTC的富集与捕获带来巨大挑战,免疫亲和法是最常用的分离方法,即利用上皮细胞粘附分子(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EpCAM)等细胞表面标志物的表达。迄今为止,Cell Search®是使用最广泛的阳性选择方法,也是唯一一种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用于转移性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CTC的富集和分析方法[9]。Cell Search®用抗EpCAM抗体标记磁珠,用磁铁吸出细胞并对细胞角蛋白(CK8/18/19)和CD45进行染色,该技术的主要局限在于它们依赖细胞表面标记物,在某些恶性肿瘤中,这些标记物可能有变化或不表达,这种局限性在经历EMT的细胞中更为明显,导致CTC逃脱检测[17]。用于分离CTC的方法还有物理方法,如基于细胞体积、可塑变形性、密度、膜特性的分离技术。由于肿瘤细胞较外周有核细胞可塑变形性差,体积更大(>8 μm),尽管基于过滤和梯度离心技术已经应用于临床,具有EMT特性的CTC可能不会丢失,但在分离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血细胞的交叉污染[18]。近年来,研究人员开发了许多新的分离技术,例如KO等[19]开发了一种芯片平台,该平台结合了阴性免疫磁选择和芯片上的原位RNA分析。CHEN等[20]报道了一种具有抗EpCAM的新型3D打印微流控装置,旨在为CTC富集提供更高的灵敏度、特异性和准确性的方法。
3 CTCs在局限性前列腺癌中的临床应用
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提高患者存活率的关键,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radical prostatectomy,RP)可以显著降低前列腺癌的特异性死亡率、转移的可能性和总的死亡率[21]。LOH等[22]使用CellSearch系统对36例非转移性高危前列腺癌患者的CTC进行了一项研究,共有5例CTC阳性;然而,CTC的存在与组织学分期、年龄或PSA水平无显著相关性。CTCs检出率低可能与CellSearch平台有关,该平台仅在约11%的前列腺癌中可检出EPCAM低表达的CTC,并且部分CTCs可能为间充质表型。KUSKE等[23]结合CellSearch系统、GILUPI CellCollector和EPISPOT平台3种不同的富集方法来提高CTCs的检出率,在86例非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中,对52例在行RP术前进行了基线CTC测定,并在术后3个月进行了第二次检查,结果是至少有一种检测方法在81.3%的血液样本中发现了CTC,使用CellSearch系统、GILUPI CellCollector和EPISPOT平台检测,CTCs的检出率分别为37%、54.9%和58.7%。此外,23例检测出5个以上CTCs,手术前后CTC检出率有显著差异(66%vs.34%,P=0.031)。3种检测平台的联合应用首次发现了非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中CTC的高检出率,并且证明表达PSA的CTCs与肿瘤总负荷相关,可能说明CTCs和PSA水平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周旭东等[24]利用CanPatrolTM二代CTC检测技术检测73例行RP术的患者血清CTCs表达水平,按是否发生生化复发(biochemical recurrence,BCR)分为BCR组(19例)和非BCR组(54例),探讨RP术后CTCs水平与BCR的相关性,结果显示BCR组患者血清CTCs水平显著高于非BCR组患者(6.94±1.04vs.5.03±1.21,P<0.05),高CTCs水平是影响RP术后BCR发生的危险因素。PAK等[25]为研究前列腺癌患者术后CTCs检测与复发的关系,共纳入203例RP术后PSA水平检测不到的患者,循环肿瘤细胞取样中位时间为术后4.5个月,其中73例(36.0%)患者检测到CTCs,并且结果显示CTC阴性患者术后3年生化无复发生存率明显高于CTC阳性患者(81.6%vs.48.9%,P<0.001),术后循环肿瘤细胞检测与生化复发风险的增加独立相关(HR:5.42,95%CI:3.24~9.06,P<0.001),证实了CTC检测与BCR的风险增加相关,也表明在RP术后BCR病例中,CTCs检测先于术后PSA升高。
4 CTCs在晚期前列腺癌中的临床应用
雄激素剥夺疗法(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ADT)是晚期前列腺癌的标准治疗方法,去势抵抗转移往往发生在ADT治疗期间,并随着新转移灶的出现或原发肿瘤的进展而进展[26]。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信号转导在CRPC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有了ADT,但雄激素是由肾上腺和前列腺癌细胞本身产生的,它们维持AR信号通路并过度表达AR,所以后续有睾酮合成抑制剂(阿比特龙) 和AR阻滞剂(恩扎鲁胺和阿帕鲁胺)优化CRPC的治疗选择[27-28]。一项研究表明,基线时的高CTC数值(≥5 CTCs/7.5 mL)下降与良好的预后相关,并有望用于评估化疗和ADT的治疗效果[29]。DE LAERE等[30]纳入174例接受阿比特龙或恩扎鲁胺治疗的患者,评估了基线CTC计数、基线PSA水平、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和生存率之间的相关性,共有118例CTC阳性患者,其中69例在基线时为≥5 CTCs/7.5 mL,与内分泌治疗前CTCs<5的患者相比,≥5 CTC患者的肿瘤病理分期更高(LDH 2.6倍,PSA 5.3倍),疾病无进展生存率(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更短(3.9个月vs.11.5个月,HR:2.5,95%CI:2.8~8.3,P<0.000 1),总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降低(11.2个月vs.30个月,HR:4.7,95%CI:2.8~8.3,P<0.000 1)。在10~12周的随访中,CTCs下降的患者(n=44)或CTCs无变化的患者的PFS(12.98个月vs.13.67个月vs.4.03个月,HR:3.6,95%CI:1.9~6.8,P<0.000 1)和OS(未观察到的OSvs.11.2个月,HR:9.5,95%CI:3.7~24.0,P<0.000 1)均长于CTCs升高的患者(n=19)。LORENTE等[31]探讨了低CTC负荷(<5个)前列腺癌患者治疗前后CTC数量增加的意义,该研究中有212例(41.7%)CTC<5的患者在治疗后4、8或12周出现CTC升高。然而,与CTC在治疗后4周(23.8个月vs.14.8个月)、8周(24.1个月vs.14.7个月)和12周(27.1个月vs.13.6个月)升高的患者相比,无CTC升高的患者生存期更长。HELLER等[32]将1 552例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mCRPC)患者在基线和13周时的CTC数和白蛋白、LDH、PSA、血红蛋白和碱性磷酸酶水平(ALPHA模型)进行了合并,HELLER学者得出结论,与标准模型相比,在经典的ALPHA模型中加入CTC计数提高了低风险组的鉴别质量。一项Ⅲ期临床试验研究了接受多西紫杉醇和泼尼松治疗的mCRPC患者的CTCs与临床结局之间的关系,在初治时CTC阳性的患者中,87例(42%)检测到<5个CTC/7.5 mL血,121例(58%)检测到≥5个CTCs/7.5 mL血,结果显示基线时≥5个CTC患者队列与OS降低显著相关(P=0.0028),并且与化疗3个周期后CTC数量变化多于5个CTC的患者相比,CTC数量变化小于5个CTC的OS更长(P=0.025)[33]。
5 CRPC中CTCs的亚型和基因组分析
上皮细胞标记物已用于各种癌症的CTC研究,而包含EPCAM+、CK+、DAPI+和CD45-的CellSearch标准仍然是评估CTC的金标准。在胚胎发育期间发生的EMT会降低上皮细胞的极性,从而使它们能够获得更高的侵袭性以及凋亡抗性[34],该现象表明CTCs中上皮细胞标记物可能会表达降低,也意味着如果仅按照上皮细胞标准富集、分离和检测CTC,CTCs的中间表型和间充质表型可能会被遗漏,特别是对于正经历EMT的CTC或具有低上皮蛋白表达和高间充质蛋白表达的神经内分泌CTCs[35]。一些研究表明,通过随后的过滤和免疫荧光染色可以发现具有这些表型的CTC,此外还强调了不能将单个或包含EPCAM+、CK+和CD45-的细胞定义为CTCs[36]。对于CTCs的基因组分析,可从定性和定量方面对各种基因进行分析,除了研究目的之外,CTC的遗传信息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制定与靶向治疗相关的诊疗策略。液体活检显示雄激素受体剪接变异7(androgen receptor splice variant-7,AR-V7)与CRPC内分泌治疗后的不良预后相关,并且被认为是最重要的AR变异,AR-V7也与恩扎鲁胺、阿比特龙的耐药性相关[37-38]。SEITZ等[39]利用PCR技术量化了85例mCRPC患者外周全血中AR-V7的表达率,发现高AR-V7水平代表着不良预后,并且可以作为PSA水平下降低于50%的患者的独立标志物。SCHER等[40]评估了142例mCRPC患者在接受治疗前的CTCs,共有70例患者诊断为高危患者且血液中有AR-V7阳性CTC,其中接受紫杉烷治疗的OS优于接受AR抑制剂治疗(OS:14.3个月vs.9.3个月);相反,无AR-V7阳性CTC但接受紫杉烷治疗的患者的OS比接受ARS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更短(12.8个月vs.19.8个月)。同一组的另一项研究评估了具有AR-V7表达的CTCs与紫杉烷、ARS抑制剂的疗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有AR-V7阳性CTC的患者在接受紫杉烷治疗后有更好的临床结果[41]。一项基于AdnaTest的研究表明,在AR-V7阳性CTC的CRPC患者中,75%对激素治疗不敏感[42]。此外,目前已经发现了具有各种AR剪接变体的CTC,它们都与不良预后相关[43]。一项研究将mCRPC患者分为细胞周期增殖相关蛋白(Ki67)组和间充质标记物(Vientin)组,并通过分析CTC状态来阐述临床结果,基线时≥5个CTC的患者有更高的PSA值和更短的中位OS(375dvs.712d),并且在基线时有无Vimentin阳性CTC的患者OS差异显著(305 dvs.453 d);在Ki67组,Ki67阳性和阴性CTC患者的OS也有差异(512 dvs.751 d)[44]。
6 总结与展望
CTCs计数及对其表型的分析对PCa患者特别是mCRPC在诊断、指导治疗和对预后预测上的巨大潜力已经被证实,但仍缺乏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目前用于从Pca患者中分离和分析CTCs的设备方法层出不穷,各有优劣,均缺乏标准化的质量把控,因此,捕获CTCs的理想平台仍有待确定。未来应进行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研究,相信随着液体活检技术的发展,CTCs的检测能为PCa患者提供个性化的疾病筛查、治疗方案、预后评估以及探索更深层的肿瘤发生发展和耐药机制,真正实现精准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