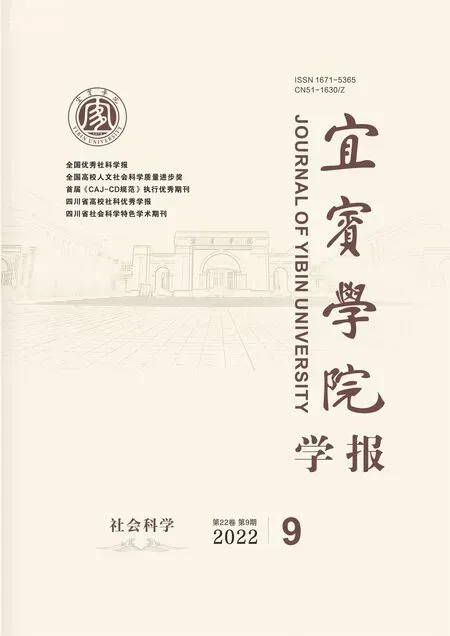“十七年”长篇小说的评书改编与广播传播
刘成勇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十七年”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十七年”长篇小说几乎被以广播为平台的“小说连播”节目“一网打尽”,其中大部分又是通过“评书广播”的形式而为民众所了解。
评书是以“说”为主、表演为辅的曲艺形式,以其跌宕起伏的故事、形象鲜明的语言而拥有数量庞大的受众。随着广播的兴起,曲艺艺人也从书场、书馆、茶馆走进演播间。1949年后,多数评书艺人开始到电台“说新书”“说红书”,有些代表性艺人还因此受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以评书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形式也进入文艺界领导者的视野。“评书+新书”的传播机制扩大了“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影响,对其经典化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学界对此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从言语文化的角度探讨“十七年”长篇小说被改编为评书并通过广播传播这一重要文学现象,从而加深对“十七年”长篇小说的认识和理解。
一、“广播+评书”与“讲小说”的兴起
1920年代,广播进入国内不久,评书艺人开始进入广播电台,演说《三国》《水浒》等传统故事。1949年5月25日,孔厥、袁静合著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时任锦州市曲艺协会会长的李鹤仙看到小说后,觉得故事很生动,于是将其改编为评书。之后李鹤仙每天到锦州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反响很大,“有人特意买个收音机收听这个广播”[1]。1950年张振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评书《铜墙铁壁》,赵英颇播讲根据赵树理《登记》改编的中篇评书《燕燕》,袁阔成播讲《小二黑结婚》。以上是新小说较早改为评书的例子。在这之后,《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暴风骤雨》等革命新书也纷纷被评书艺人改编后在广播上演播。有些小说还被多人多次改编,如《新儿女英雄传》除了被李鹤仙改编外,改编者还有北京的连阔如、云南的雷震北、湖北的李兴凯、河北的杨田荣、山西的狄来珍、辽宁的单田芳等。
有的广播电台开辟专栏播放评书艺人所说的新书,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辽宁鞍山广播电台。作为市级电台的鞍山台是1949年后第一家以新评书为主的电台,1956年元旦创办的“评书节目”播出了大量根据“十七年”长篇小说改编的新评书,如《三里湾》《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创业史》《红岩》《新儿女英雄传》《欧阳海之歌》等。自开办节目一直到1992年,鞍山台共录制了123部评书,播讲段数居全国首位,是我国生产评书的基地,也因此获得“评书故乡”之称。鞍山台在评书广播方面创造了几项记录:在全国最早录制播出现代广播评书,1960年代中最早恢复广播评书节目,最先录制播出新编传统评书。1950年代,鞍山汇集了京津等地曲艺名家26位。鞍山电台的杨田荣播讲过《新儿女英雄传》《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小城春秋》《暴风骤雨》《红旗谱》《红岩》等多部新书。1963年,《人民日报》发表《全国说新书的一面旗帜》一文,肯定了杨田荣说新书的成绩,将鞍山台广播评书推向全国。杨田荣的评书不仅在国内受欢迎,也影响到国外。朝鲜新义州一位老人听了《激战无名川》后,写信给杨田荣说:“听了您那动人的评书和惊人的口技,我简直忘记了自己是坐在收音机旁,就像我又回到了那战争的岁月”[2]166。
“十七年”长篇小说大规模改编为评书是1958年后,几乎是只要有新的长篇小说面世,很快就被改编并在各级各类电台播出。究其缘由有以下四点:
一是适合“说”的新书大量涌现。首先有些新书具有“拟话本”特征,如刘流的《烈火金刚》、曲波的《林海雪原》、梁斌的《红旗谱》等。其次,有的作家创作出的小说就是为“说”而作,如四十年代束为、邵挺军的《苦海求生记》、柯蓝的《乌鸦告状》、马少波的《新还魂记》等。1949年后具有明显评书风格的作品有赵树理的短篇《登记》、长篇《灵泉洞》以及马烽的《周支队大闹平川》等。出于普及民众文化的目的,赵树理将评书的价值定于现代小说之上:“我还掌握不了评书,但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这个主意我至今不变,如果我能在艺术上有所进步,能进步到评书的程度就不错”[3]。再有就是评书艺人创作或与作家合作了一些长篇小说作为演播的底本,如潘伯英、金声伯创作的《江南红》,连阔如、苗培时的《飞夺泸定桥》,李凤琪的《智闯珊瑚潭》,诸仙赋的《冷枪战》,柯蓝、蒋月泉、周云瑞创作(柯蓝执笔)的中篇弹词《海上英雄》等。
二是1949年后对传统艺术进行“改人、改艺、改制”活动,大大压缩了评书艺人“说旧书”的文化空间。为了鼓励评书艺人说新书,文化部门首先对评书艺人进行经济扶持。最常见的就是发给评书艺人固定工资,让他们不再有生存上的忧虑。有资料表明,与城市普通职工相比,评弹艺人是当时的高收入群体。其次是提高他们的文化地位,赋予曲艺艺人以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身份,承认他们在社会主义文艺活动中文化“尖兵”的地位和作用。再就是体制化管理,将分散的民间评书艺人归属于各级各类曲艺团、曲艺队、曲艺组或曲艺小组、巡回演唱队。有的地方还对评书艺人的政治情况、上演节目内容进行审查,合乎条件的发给“演员证”。体制化后,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多数评书艺人转向了说新书。
三是积累了更多“说新书”的经验。1950年代,一者新书少,二者新书故事不精彩、不紧凑,三者将新书改编为评书存在诸多技术上的难题,故而说书的和听书的积极性并不是太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曲艺领导机构和部分先进评书艺人通过集体合作、个人探索积累编新书、说新书的经验。如北京宣武说唱团1956年开始针对性的研究说新书。袁阔成改编了大量新书,通过对原稿的分段加工、重新安排关节等方法对原著进行相应的梳理和铺排,使其适合于口头说演。这些编新书、说新书的经验又通过种种途径被其他评书艺人借鉴学习,进一步扩大了改、说新书的规模。云南省评书艺人宋兴仁通过举办评书培训班、故事员培训班的方式将说新书的技巧传授给业余评书员及故事员。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邀请部分编说新书有成绩有经验的演员和干部座谈,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方法。
四是利用曲艺传播新书引起文艺界、曲艺界的高度重视。1949年后,面对文化水平偏低而又亟须进行革命化动员的乡村社会,以评书为代表的口头文学受到文化部门的极大关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中华全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团结各地分散的艺人创作和改编曲词、辅导艺人改造思想。同年9月,筹委会与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联合成立“曲艺广播小组”,通过广播演出反映新生活、新思想的曲艺节目。1958-1962年,对于曲艺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先后召开了全国曲艺工作会议和第一次中国曲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大会,组建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肯定了曲艺灵活轻便的演出形式,希望曲艺能够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周恩来、陈云以及周扬、老舍、赵树理等文艺界领导者不仅参加了重要的曲艺演出和会议,而且就曲艺如何繁荣发展作出过具体的指示。1964年2月5日,《人民日报》就全国文联和曲协召开的曲艺创作座谈会发表社论《积极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曲艺》,从节目内容、创作队伍、演出方式、曲艺作品的发表出版与评论工作等做出了部署,以更好地发挥其娱乐教育功能[4]。
《文艺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近年来,有些地方曾经把《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改编为戏曲或曲艺形式上演……有些作品,内容是好的,适合农民需要的,而形式上不完全适合农民的需要,经过改编,就易于为广大农民所接受,这都需要懂得一些曲艺、戏曲的而又热心于文艺普及工作的新文艺工作者同艺人合作,进行创造性的改编”[5]。既然“讲小说”符合群众艺术欣赏习惯,易于为群众接受,那么在广播上“讲”显然是一种更经济的做法。1962年,曲艺界提倡“说新唱新”,新体长篇小说被大量改编为曲艺的各种形式,而几乎所有的电台,都长期把播放小说作为重要节目。这其中,改编为评书并进行播放的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二、改编与改变:“十七年”长篇小说的评书化
新体长篇小说和评书是两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文体样式。为适应听觉对象的需要,“几乎每一篇都经过重新编写”,这种重编工作,在当时曾是一件很繁重、也很具有创造性的事情[6]272。当评书艺人按照评书的程式改编新体长篇小说时,这种“二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体长篇小说新的内涵,并在艺术方面有所提高。评书艺人对新体长篇小说的改编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结构的改变、细节的补充和丰富等方面。
首先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表现在英雄人物身上。“开脸”是评书描绘人物的常用手法,一般按照由上到下、由外到内的顺序介绍人物的相貌、打扮及其他外在特征,达到先声夺人、突出性格的效果。如袁阔成改编的《肖飞买药》中肖飞的形象:
看他年纪也就在二十七八岁,中等身材,白净子,宽脑门儿,尖下颏儿,细眉毛,大眼睛,真精神,留着大背头,头上歪戴一顶巴拿马大草帽。身上穿着灰纺绸裤褂儿,里面衬着“皇后”牌白背心,腰里扎着一根丝带,三指多宽,带穗头儿在两边儿甩出老长。脚底下平口便鞋,丝线袜子。这身打扮,没的说,绝对特务![7]77
在原作中,肖飞身材小巧玲珑、眉毛黑细、睫毛又黑又长、眼睛又大又亮、脸上有酒窝儿,是“一个俊俏的青年”。如果买药的时候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并且还做出特务的品性,显得有些不真实。改编之后,仅从外貌上就能迷惑住药店里的人。无独有偶,陈清远改编的《肖飞买药》也写出了肖飞的派头和特务式的打扮[8]870。
评书艺人塑造英雄人物主要还是关注英雄的性格气质的生成变化。“十七年”长篇小说中的英雄是国家和民族意志的体现。在政治理性的规范下,英雄人物只剩下阶级属性和民族属性,个人的思想、情感和欲望都被排除或屏蔽。因此,面对英雄人物,评书艺人在改编时顾虑重重。对于不能很好表现高级别英雄,李鑫荃自我检讨是思想感情跟不上。实际上这不是个人思想感情的问题,而是与思想上种种无形的束缚有关,对于高级别英雄人物无法进行创造性发挥。相比之下,评书演员在塑造那些具有民间草莽气质的英雄人物时发挥空间要大得多,人物形象更为丰盈饱满。这一方面是评书擅长于塑造英雄人物,另一方面也与评书艺人对生活的熟悉程度有关。为了说好《铁道游击队》,傅泰臣前后历经三年到枣庄和微山湖,访谈当年的铁道游击队队员,收集了很多素材。并且他还专程拜访知侠,探讨刘洪形象的塑造问题,认为“不要让他变得太快,太突然。失去了人物原有的个性,也会失去了真实性”[9]。
“十七年”长篇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呈现出“长成”的性格,其成长过程比较模糊。比如梁生宝、刘洪等,他们的英雄品格犹如天赋,缺少现实逻辑和性格逻辑。故而人物很高尚伟大,但并不真实。所以,评书艺人“说”出英雄人物性格的不足和缺点,让他们在行动中不断成长,既符合性格逻辑,也反映了历史逻辑。
根据评书的特点改变原作的结构也是评书艺人常用的做法。与评书单线发展的结构不同,“十七年”长篇小说情节穿插比较复杂,也有一些情节表现出游离状态,同时情节的发展常常伴随着人物思想感情活动,这些都不适合口语化的线性表达。于是,评书演员在改编时,要从原作错综复杂的人物纠葛和情节结构挑出主线,不枝不蔓,线索清晰,利于听众理解。也有的评书艺人根据传统评书《三国演义》或《水浒传》的结构方式以人物或事件为单元对原作情节进行重新组合,从而起到突出某个英雄人物或事件的作用。如李鑫荃以人物为单元将《红岩》改编为多个单篇,包括《江姐初上华蓥山》《彭政委就义》《甫志高叛变》《许云峰赴宴》《双枪老太婆劫刑车》《华子良装疯》《许云峰就义》等,每个单篇可独立演出。重庆曲艺团改编的《红岩》分三部分,有《暴风海燕》《挺进报》《红岩青松》,分别以江姐、成岗、许云峰为“书胆”。宣武说唱团的朱桢富则是以故事为单元改编了《林海雪原》,包括《杨子荣智识小炉匠》《刘勋苍猛擒刁占一》《小分队奇袭老狼窝》《杨子荣打虎上山》《小分队驾临百鸡宴》等。
新评书也很注重线索的起承转合,改编时采用传统评书中常见的“裁笔”“伏笔”加以表现。例如杨子荣假扮匪徒胡彪进威虎山,说是奶头山的副官,但前文消灭奶头山时,并没有提到胡彪这个人。这时,忽然在威虎山出现,就显得过于突兀。于是,评书演员在叙说消灭奶头山匪徒后加上一句:“那副官胡彪,背上中了一枪,往前一个抢步,掉下了山涧,不知生死。”就为后文埋下“伏笔”[10]25。最主要的是,这种安排还弥补了原著中的一个漏洞。原著中,杨子荣要扮成一个匪徒深入座山雕的巢穴。少剑波深夜在与杨子荣谈话中点出了这个匪徒叫“胡彪”,除此之外,没有更多关于“胡彪”的信息。但“胡彪”这个名字的突如其来却给读者造成一种暗示,这是一个信手拈来的名字。在与座山雕见面时的对话中,“胡彪”称自己是许大马棒的饲马副官,逃出奶头山。但这番杨子荣自说自道的话并不能使读者确定“胡彪”实有其人。在威虎山上,当被抓的栾平看到杨子荣时,心理活动中有一句话:“他明明认出他眼前站的不是胡彪,胡彪早在奶头山落网了……”这就说明确实有“胡彪”这个人。“胡彪”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杨子荣的生死,对这样一个关键性细节,原著显然安排得过于草率。相比之下,评书演员加上的一句就不是可有可无之笔。
对于细节方面的补充和丰富也是评书演员改编时的重要内容。评书很注重细节描写,一是因为艺人收入的问题,通过细节的渲染延长表演的时间;二是细节描写对于情节的发展起到铺垫、暗示的作用,使情节发展更为合情合理;三是口语化表达必须将对象具体化才能给听众以更直观的印象。有评论者就此而言:“作为听众,即使读过小说原作,知道事件的过程和结局,也还愿意听到更详尽的细节。这些和人物、生活场景有机联系的细节,与重要情节结合一起,就更易于从生活经验、感情变化上引起听众的共鸣与联想,在听众心目中重新构成动人的形象”[11]。
在对新书进行改编时,评书艺人增加了大量在意识形态许可范围内的生活化、趣味化的细节。增添的部分有些是评书演员的即兴发挥,有些是故事发展的必要。根据《林海雪原》,许多说书人都扩充了杨子荣的故事。如苏州评话说书人张效声等变化出《真假胡彪》一回,杨子荣与匪徒斗智斗勇,波澜迭起,堪称妙笔。陈云听过后多次表示赞许。东北说书家陈青波说《红旗谱》,仅朱老忠闯关东一段,就连说了二十多场。在朱老巩砸钟前后增补了《三世仇》和《下关东》的情节,使朱老忠的复仇心理和行为更具有历史合理性。傅泰臣调动自己的生活记忆对《铁道游击队》进行创造性发挥。比如他增添了牛三这一人物、“宪兵队过堂”一节踢狼狗的细节以及“打炮楼”的情节,使故事情节不仅合理,而且更加精彩,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刘田利说演《铁道游击队》时,增写了《小春下书》一回。小春是这回书的主要人物,是刘田利根据书情的需要精心设计的一位少年英雄,从而为整部书增色不少。同时,刘还充实了“打票车”的具体细节,使情节更加丰富。
交代清楚地点及环境背景,让听众身临其境,这在旧评书技巧上叫“摆砌末子”,是评书不可或缺的部分。有论者以《林海雪原》为例指出了“摆砌末子”的重要性:“例如《林海雪原》的杨子荣智取威虎山,威虎山究竟详细形势怎样?威虎山上的建筑是什么样子?原作品不够详细,改编时有必要添上,不然就显不出小分队的威力来,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条山道,小分队怎么进来的;小炉匠怎么进来的,也就不好明白了”[10]25。因此,评书艺人在改编新书时,大多会将其中含糊不清的地方和环境给以明晰化。重庆市曲艺团在改编《红岩》时,将江姐看到丈夫人头的华蓥山下的小城安放在广安、徐鹏飞设宴的地方是胜利大厦,将《挺进报》中的长江兵工厂改为长安机器厂。这样做不仅增加了听众的真实感,而且便于演员对环境细节的铺叙渲染,更便于穿插地方掌故、增加地方色彩。
“摆砌末子”还表现在背景环境的描写,起到烘托故事和人物形象的作用。《林海雪原》中在写到杨子荣舌战小炉匠进威虎厅时,场景描写只有一句话:“威虎厅里,两盏野猪油灯,闪耀着蓝色的光亮。”这样的描写太简单,烘托不出座山雕的凶狠狡诈。袁阔成在改编这一节时对座山雕所处环境大肆渲染,为下一步的矛盾营造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氛围:
拉门进来这么一看哪,嘶——呀!今天的威虎厅可与往日不同,屋子里的空气是万分的紧张。威虎厅十七间房子一通联,正面墙上挂着一张水墨大挑,画着一只老雕,独爪抓着山头,横展两翅,黄登登两眼,俯瞰威虎山。大挑两旁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群雄味聚威虎山靠天吃饭,下联配:众豪藏身野狼窝坐地分金。横匾上三个大字:威虎山。左上首一面鼓像磨盘似的,风磨铜的鼓架晶明瓦亮。正当中桌子后面椅子前头,站着一人,正是老匪座山雕[8]365。
总的来看,在对新书改编的过程中,评书演员既尊重了原著的文本事实,也有所发挥和创造,体现了民间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软性消解。就好像当时有人指出的那样:“原作中详细描写的,改编时可以从略,甚至一笔带过或舍去不表;原书中简略描写的,改编时可以加强,甚至大力补充,着意渲染;原书侧面交代的,改编时可以正面处理;原书分散叙述的,改编时可以集中凝练。改编者可以充分利用原作的艺术成就;可以根据主题要求和人物性格,以自己的生活积累,大加想象;有很广阔的创造天地”[12]。另有评论则更进一步阐明了评书艺人改编新书的创造意义:“如果抛开艺人的再创作过程,把曲艺作品作简单的理解,只看到它跟文人作家作品的联系,而没看到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错误的了。民间艺人,正如故事讲述者一样,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作品的单纯转述者,优秀的艺人往往是杰出的创作家,这难道不也是民间文艺的固有特征吗?”[13]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是包括曲艺在内的文艺工作者的中心政治任务。许多评书艺人对工农兵生活并不熟悉,对工农兵心理也不好把握。因此,要说好新评书就像文学创作一样,得熟悉、了解工农兵生活。杨田荣改编《铁道游击队》时,听说他们的市长过去在部队当过政委,就想办法接近,“体会老干部的思想感情。以后再说《铁道游击队》的时候,就有血有肉了”[14]。西河大鼓演员刘田利说《铁道游击队》时,多次去铁路部门体验生活,访问老工人,了解当时的生活场景。说另一部新书《红旗谱》时,刘田利还到农村参加劳动。傅泰臣改说《铁道游击队》时,经常看一些有关抗日战争的书籍、影片以熟悉小说中的生活,向战士了解武器的使用方法和构造机件名称,了解司机、司炉等不同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特点,“由于熟悉了生活,表演起来就比较逼真一些,不至于出漏子,闹笑话”[15]。1961年才开始学说新书的云南纺织厂业余评书演员朱光甲也有向生活学习才能说好新书的体验:“除了学习传统外,向生活学习是顶重要的。说新书时许多说白、手眼、身段都要重新创造,要应用新词汇、新穿戴、新脸谱才能适应新书的要求,要有熟悉新事物的生活经验,说起来才会生动真实感人”[16]。
评书艺人和作家一样,将深入生活学习和掌握工农兵语言作为主要任务。刘田利说:“工人和工人说话不同,车间里声音很大,工人高声喊,还要加上手势动作,才能听清楚。出钢分秒必争,炼钢工人不讲客套,语气肯定直接。同是铁路工人,火车上的司炉工人和站上的运输工人,就各有不同。”他认为,没经过观察之前,对这些语言特点并不知道,“只能把工人说成一个样儿,一个和另一个分不清楚。”他呼吁同行“要说好新书,我们一定要深入生活,通过各种方式去学”[17]。
评书艺人一方面是熟悉生活,另一方面是熟悉作品。刘田利酝酿改说《铁道游击队》有两年多时间,1958年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时才改编了个别章节。评书演员樊昌谈到自己创作新书的经验时说:“每讲一段新书时,我一般是先看一遍,找出书中主题,分析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并初步在脑子里把情节组织一下,接着又看上几遍,把书上的东西完全变成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番创作,把书的情节按评书要求安排好,哪里是高潮,哪里冷,多设计些身段表演和用生动的语言描写来弥补冷段子,并尽可能将传统书中的‘门坎’ 等技巧用进去”[18]。天津南开区评书西河队的邵增涛、顾存德和张立川为了说好新评书,租住在旅馆专心读书、背诵、研究、理解所要说的新书。在此基础上,根据评书特点对全书结构进行调整,对人物的身份、性格以及人物形象、语言声调等反复推敲、设计,不断修改后再上舞台试演。重庆曲艺团《红岩》改编小组在动笔之前不仅熟读原著,而且阅读与《红岩》有关的评论文章和参考资料。他们认为:“熟读原文,多读有关材料,才能对原书的内容和精神,有深刻的理解,才便于对情节进行裁剪和丰富。而且,只有深刻体会原著,思想上受到感染,才能把评书改编好”[19]。
改编新书时,向原作者请教的评书艺人不在少数。中国曲协请《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烈火金刚》作者刘流为北京市宣武说唱团作报告。《红岩》改编时,罗广斌、杨益言在一些地方给予改编者徐勍、逯旭初、程梓贤以具体而微的提示。预演时每场必到,鼓励演员、改编者进行大胆的改动。这样做,一方面加深了对原作的理解,另一方面增强了改编者的信心,他们既不会对原著一成不变的如实照搬,也不会出现对故事和人物形象任意歪曲夸张的做法,而是在意识形态和传统评书技法平衡的基础上对英雄形象进行适当的调整。高元均谈到他在演播《侦察兵》时如何处理人物动作:“在动作上我尽量地使它生活化,不去搬用旧的套子,因为新的人物与这些老动作是格格不入的,生搬硬套,往往会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假如把武二郎的动作硬按到侦察兵的身上,那就会歪曲了形象,不过在动作的节奏上,我是一点都不马虎的,因为动作上鲜明的节奏,会有助于动作的美化。”而为了突出人物形象,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高元均都给予适度的夸张[20]。陶湘九和袁阔成改编的《舌战“小炉匠”》在移植原作中杨子荣见到小炉匠之后焦虑、急躁、紧张情绪的同时,还突出了他的害怕和恐惧。如陶湘九文本中,杨子荣见到小炉匠时的第一反应:“杨子荣一看此人,吓的出了一身冷汗。”杨子荣猛一见到小炉匠,首先意识到的是自我安危,其次是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在危险面前,情绪紧张是人的本能性反应,非意志所能控制。因此,杨子荣的心理表现属于“人之常情”,这样的“惊人笔”增强了矛盾氛围的惊险程度。
重庆市曲艺团最初演《暴风海燕》第一段时,演员因为顾及江姐“区委书记”的身份,“对她的外形描写束手束脚,话也不敢多说了,动作也不敢多做了”,“恐损害英雄形象”。罗广斌、杨益言告诉演员:“可以放开描写她,外形更可以放开描绘,反正她是化了妆的嘛”[19]。罗广斌、杨益言的一些提示也深化了原作的内涵。比如江姐见到丈夫老彭的人头时:
老彭?他不就是我多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同志、丈夫么!不会是他,他怎样在这种时刻牺牲?一定是敌人的欺骗!可是,这里挂的,又是谁的头呢?江姐艰难地、急切地向前移动,抬起头,仰望着城楼。目光穿过雨雾,到底看清楚了那熟悉的脸型。啊,真的是他!他大睁着一双渴望胜利的眼睛,直视着苦难中的人民!老彭,老彭,你不是率领着队伍,日夜打击匪军?你不是和我相约:共同战斗到天明!
这段话在形式上是长短句子和感叹号、问号交错在一起,表现出江姐悲愤、怀疑、痛苦的复杂心理。要将这种书面形式转换为口语,需要准确把握江姐的心理特点。罗广斌、杨益言为改编者详细剖析了这一心理过程:“江姐此时的感情,首先是惊,内心震动;接着不信,怀疑是敌人惯使的鬼把戏,夸耀成功,瓦解我方斗志;再看,究竟是亲密的战友,辨认出来了,感到悲愤填膺,插叙她的回忆,由热转冷,悲痛已极……”[19]这样的理解和分析对于评书演员把握人物的性格也起到重要作用。
三、评书广播与文艺大众化
一般认为,“十七年”长篇小说主要通过期刊、书籍、电影、连环画等视觉性媒介传播。首先书刊是主要载体,当时的长篇小说印数动辄达到几百万册,李希凡认为“几乎是人手一册”[21]9。这一令人振奋的数字是就识字者的阅读概率而言,如果考虑到社会中还有大多数的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工农兵群体,“人手一册”恐要大打折扣——赵树理就对这一乐观的看法表示怀疑。电影也传播了大量“十七年”长篇小说。但在农村,看电影是比较奢侈的娱乐活动,交通、电力、经济状况等限制了电影传播空间的进一步拓展。连环画是老少皆宜的文学传播形式,但在长篇小说的图像化过程中,意义的大量损耗则不可避免。
不可否认,视觉媒介在“十七年”长篇小说传播中发挥了主渠道作用,也因其媒介特殊性而赋予作品以艺术新质。但这些以文字、图像等视觉符号构成的文本以及混合了现代艺术技巧的叙事语法与农民的审美经验终究还是有些隔膜,“还未能真正达到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地步”[22]。1964年,一篇发表在《边疆文艺》上的文章尖锐批评了有些文学作品“艰涩隐晦”,故意让人看不懂[23]。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更具有直观效果,但1966年有电影界人士指出,在一些偏僻山村和边远地区还有农民看不懂电影的情况,如《汾水长流》《红管家》《暴风骤雨》《李双双》等。这些影片故事情节过于复杂,人物过多,时间、地点、环境交代不明,在镜头控制、场景组接、蒙太奇句子等方面超出了农民的理解能力。除此之外,还有些电影不适当地使用了方言,阻碍了对故事的理解。
两相比较,以说书为代表的听觉传播在这种背景下显现出独特意义。“说”既是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生产机制,也是其传播媒介。“听”书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民众的审美情趣、道德观念和知识结构。1940年代的延安解放区已经有了利用说书传播革命思想的实践,这为1949年文艺政策存留、改造和利用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提供了历史性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说书人主要是讲一些自编的或是根据短篇小说改编的具有革命教育意义的短篇故事。1950年代中期,出现了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这些小说很快通过声音而为受众所知,说书这一民间艺术形式也在传播新体长篇小说的过程中成为意识形态实践的重要工具。两者相得益彰的背后隐含着思想主题、叙事法则、结构程式等方面的有机关联,比如说两者都有“讲史”的叙事动机,追求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着力于英雄人物的塑造,语言的口语化等。并且两者也都为对方提供物质性支持:“十七年”长篇小说对古典小说的借鉴使其自身具备了“可说性”,民间听书的文化惯习则为小说的声音传播奠定了心理接受基础。
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连阔如在中南海怀仁堂表演了根据红军长征途中强渡乌江天险的故事自编的新评书《长征评词——夜渡乌江》。他“神完气足、火爆有力、酣畅淋漓”的表演感染了在场的文艺界代表。连阔如的表演是“说书”这一民间艺术在国家意识形态舞台上一个完美的亮相。在随后所作的报告中,周恩来以《夜渡乌江》为例肯定了评书反映新生活的快捷和经济。1951年,《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强调以大鼓、评书为代表的曲艺“简单而又富于表现力,极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当加以重视[24]724。1957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芝明从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肯定了口头传播的价值意义。陈云、周扬、老舍、侯金镜等作家以及《文艺报》《人民日报》也对文学的口头传播给予了高度重视,1964年2月5日的《人民日报》还以《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曲艺工作者决心创新编新说新唱新,周扬同志在曲艺创作座谈会上鼓励大家发挥曲艺的战斗作用》为题,发表综述性文章,并配发了《积极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曲艺》的社论。国家层面对于曲艺改进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1963年,《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就农村文化生活分别在河南和河北进行的调查表明,一方面农民有接受新书的希望,另一方面新书在农民中的传播并不理想。事实上,“如何供给农民更多的新书的问题,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严重性表现在,如果新书不在说书这一具有广泛民间影响的领域表现出优势,那么这一领域就将被“内容反动封建”的“旧书”所占领。在调查者看来,化解这一矛盾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说书为代表的口头艺术。
事实确乎如此,在制度化的生产劳作中,说书以其简便灵活填补了民众的闲暇时间,其娱乐性和教育性的结合体现出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比拟的文化优势。就像《文艺报》记者调查的那样:
由一个人带上耳机子,听完里面讲的一段故事之后,就兴致勃勃地向周围的人复述一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更是入迷,因为她们平常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又不能阅读报纸、刊物,晚上收听自己喜爱的文艺节目,就成为十分快乐的事情了[25]。
经过评书演员编、演的努力,新评书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赵树理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评书的收听状况:“在农村中,收音机同时在广播评书和小说,人们一定去听评书”[26]1943。196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在河北饶阳县、晋县就收听文学广播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到农民最爱听的节目和作品是相声、评戏、河北梆子、革命故事、革命歌曲、民间故事和民族民间音乐,其次是广播影院、小说连续广播和广播剧院、文学爱好者栏目。由此可见,文学类节目中曲艺节目最受农民欢迎。同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也对河北保定地区三个县农民接受革命小说进行了调查。资料显示,河北定县南支合村有四五十架收音机,“听《红岩》时,热腾腾地挤满了一屋子。”这种听书的情形在所调查的保定专区定兴、望都、唐县非常普遍[27]。根据这次调查情况,侯金镜认为,在农村普及革命小说需要曲艺这种“最轻便最经常最普及也是影响最大的口头文学形式……”“将优秀的长短篇小说通过电台来播送”[28]。
文艺大众化是自五四就提出的艺术实践问题,也是提高民众思想文化的有效途径。但当知识分子提出文艺大众化时,一厢情愿对民众进行思想输出,却不去了解民众真正的需求。这种激进的启蒙主义思潮遭遇到的是民众无声的抵抗——就像赵树理所说:“‘五四’ 以来的小说和新诗一样,在农村中根本没有培活”[29],这不能不是对西方现代文化抱有莫大期望的知识分子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在此情形下,1938年毛泽东提出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之所以能引发那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开出了消除精英与民众之间文化对立、思想隔膜的药方,重构了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观察视角与交往方式。这也让民间形式在现代化语境中再度复活,四十年代解放区说书人说唱新书的成功实践让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同时发现了民间形式的启蒙价值。
1949年后这种口传文学形式更进一步放大到全国范围。《文艺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农村中文盲仍然不少,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限于文化水平,不能读小说,只好来听人讲。此外,我们现代小说的创作,在艺术风格上集成古典小说传统的表现形式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够民族化、群众化的特点,就连不少的优秀小说在内,都离群众的艺术欣赏习惯较远,还未能真正达到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地步。所以,在我国目前的农村里,讲小说确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文艺活动形式之一,它是不识字或虽识字,而读现代小说尚觉困难的农民接触文学的好方法,也是农村里一种传统的口头文学活动”[22]。
结语
对占社会中绝对多数的不识字阶层来说,看小说几乎是不可能,但听小说就简单得多。因此,讲小说——或者说是说书能够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重视,并非偶然。而下大力气构建的农村广播网无限放大了说书人的声音,弥补了口头文学口耳相授的不足,成为新形势下启蒙民众、重构乡村文化的有效工具,在“十七年”长篇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毕竟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首先就是受众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评书广播突破了书面阅读的障碍,使远比读者数量多得多的听众受到“十七年”长篇小说的艺术熏陶和思想教育。就此意义而言,评书广播在“红色经典”经典化过程中的意义,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