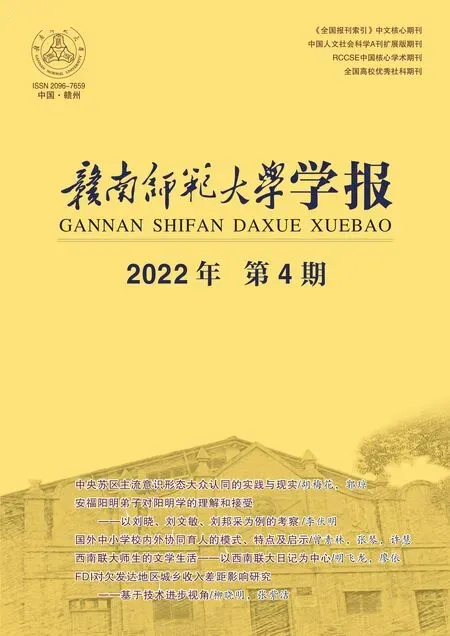民俗活动与乡村社会治理
——以赣南寻乌县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为中心的探讨*
郑紫苑
(赣南师范大学 客家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加快了深化改革推动治理现代化的步伐。社会治理是一项需要多方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国家的宏观引导与管理,而且需要民间社会以多种形式参与。尤其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以来,国家更是加强了对民间主体自治功能的关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振兴乡村,乡风文明是保障,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不能让传统乡村文化被破坏、被取代。”[1]作为一种由民间社会主导的民俗活动,不仅由于其族群性与地域性吸引着民众主动参与,而且因其聚集功能、协作功能与教化功能,在民众行为的规范与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当代社会积极发挥民俗活动在乡村社会中的治理功能,不仅有助于其自身的传承与保护,而且可以丰富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
一、 展演在乡村中的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
迎故事是一种融造型、色彩、表演等为一体的民俗,是通过乔装打扮手段,将小孩扮成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抬着出游的一种民俗活动。笔者根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客家传统与社会》丛书以及多地的地方史志的记载可知:迎故事类民俗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分布,而且具有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主要包括台阁、胎阁、飘色、扮故事、走古事、辨古士、扮景、扮古士、妆古史、古事以及故事队等。而“迎故事”则是客家地区的特殊称谓。所谓“迎”为客家话的音译,是“抬”“举”的意思,因此“迎故事”也即“抬故事”。
迎故事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在一些迎神赛社或者节庆举行。如:《梦梁录》卷一载:“初八日,钱塘门外霍山路有神曰祠山正佑圣烈昭德昌福崇仁真君,庆十一日圣诞之辰。……其日都城内外,诣庙献送甚繁……台阁巍峨,神鬼威勇,并呈于露台之上。”[2]再如《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开煮迎酒候所,……或用台阁故事一段,或用群仙,随时装变大公。”[3]又如《武林旧事》卷三载:“户部点检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煮,九月初开清。……每库各用匹布书库名高品,以长竿悬之,谓之‘布牌’。以木床铁擎为仙佛鬼神之类,架空飞动,谓之‘台阁’。”[4]这是关于迎故事类民俗的早期记载。到了明清时期这类活动更为丰富。如明代刘侗和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在描述弘仁桥元君庙的盛况时写到:“又夸儇者,为台阁,铁杆数丈,曲折成势,饰楼阁、崖木、云烟形,层置四五婴,扮如剧演。其法,环铁约儿腰,平承儿尻,衣彩掩其外,杆暗从衣物错乱中传下。所见云梢烟缕处,空座一儿,或儿跨像马,蹬空飘飘,道旁动色危叹,而儿坐实无少苦。人复长竿掇饼饵,频频啖之。路远,日风暄拂,儿则熟眠。”[5]
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抗日战争前夕。之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的波动、社会的不稳定以及经济的破坏,迎故事类民俗也遭到破坏,甚至一度停止。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曾经被视为封建迷信活动而遭到禁止的那些迎神赛会和民间节庆活动开始得到部分恢复。于是迎故事这类历史悠久的妆扮游艺民俗也开始重现于我国的众多地区,如福建连城的“走古事”,广州番禺沙湾和中山南朗、黄圃以及湛江吴川等地的“飘色”,汕尾陆河河田的“高景”,河南南阳等地的妆古饰,河北地区的背阁,四川渠县三汇镇的“彩亭”等,这在罗勇和劳格文的《赣南地区的庙会宗族》、杨彦杰的《汀州府的宗族庙会与经济》以及房学嘉的《客家民俗》等描写风土民情的典籍中都可以见到。广东省的吴川飘色不仅仅在1992和1997年先后两次赴京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艺术表演,而且2008年还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于 2009年作为广东省非遗项目的代表被选派到成都参加“第三届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即使是在寻乌县内部,迎故事也是一种喜闻乐见、历史悠久的民俗,除南桥村外,汶口村、周田、王屋以及黄岗等村也都有。清乾隆十四年刊本的《长宁县志》即讲到“上元十一至十七夜,家门张灯,剪罗彩纸,札为之,仍扮龙狮故事诸剧,笙笛锣鼓喧天震地,看灯者填溢街巷。所谓预祝丰年与他邑无异。谚云:雨打残灯碗,早禾得把稈。”[6]到了光绪年间的《长宁县志》卷一中又记:“五月五日包箬粽,捶蒲艾,酌雄黄酒,浴百草汤,以彩绦系小儿颈臂。十一日,散会关帝庙。二十七日城隍庙先后扛畁装,设台阁人物数十座谓之故事。”[7]
由上可知,不独在南桥村,迎故事类民俗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分布,尤其是在闽粤赣等客家人的聚集地,不但是种常见的民俗活动,而且多与当地客家人的民间信仰相关,一般在庙会期间或者岁时节日期间举行,起到了娱神娱人的双重效果,而与其他地域不同的是,南桥村的迎故事民俗不仅与当地的民间信仰有关,而且与本村的村落历史有着一定的联系。
寻乌县位于江西省东南端,居赣、闽、粤三省接壤处,原属于安远县。1575年,建长宁县时划入长宁。1914年,因避四川省与其同名的长宁县,又因城东有寻邬水和所辖地域内有寻邬堡,故改名为寻邬县。1957年又因为“邬”字生僻,改为寻乌县。南桥村位于寻乌县的东南端,位于原牛斗光圩南约1公里处,古称南水乡,又称为六派村,后因村中古石桥“南桥”而改名为“南桥”。“相传明朝末年,陈、谢、程、刘、曹、曾六姓客家人氏,先后从中原辗转迁移到南桥(当时称为牛斗光)落居。由于当时地广人稀,常常受到外人的欺负。后来六姓的先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大家不齐心协力,团结起来的话,那么便难以在该地生存下去。于是六姓先人们歃血为盟,并建庙两座。一座为汉帝庙,每年的立秋日为其祭祀日。一座为五显大帝庙,每年的农历九月二十八日(五显大帝生日)时为其祭祀日。而且在农历九月二十八五日(显大帝生日)时,六姓人氏先后进庙上香,并共同组织迎故事民俗活动。活动举行时,由从六姓中挑选出来的大约7、8岁男女孩童扮演传说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然后由人们抬着故事台从各姓的祠堂门口巡游。这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争相观看,并放鞭炮迎送。这让村民们在高兴的同时,还祈求神灵的护佑,增强六姓之间的团结。”(1)资料提供者:南桥村迎故事活动负责人陈治略,时间为2010年9月17日,地点为陈治略家中。
自此开始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一直流传。虽然由于抗战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停止了一段时间,但是在1982年南桥决定恢复这种民俗活动,并决定每3年举行一次。目前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不但在表演技艺、人物造型、故事内容等方面开始融入现代因素,而且在举行时间和目的上也有了更大的突破。尤其是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兴起,南桥村更是积极传承与传播迎故事活动,从2004年就开始着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2007年甚至特地为配合赣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而专门举行民俗活动。最终分别于2015年7月正式获批为赣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2017年11月10日正式获批为江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形成了自己成熟的传承谱系。表演不再局限于迎神赛会或节日庆典,有的甚至成为一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功能上看,这些民俗活动在娱乐与祈福的驱使下,不仅给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狂欢的机会,而且在社区整合方面也具有极大的功能。
二、迎故事民俗活动与乡村团结协作能力的提升
团结协作能力是乡村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要素。这种协作性是凝聚同族、同村的重要手段,也是民众主动参与乡村事务的重要方式。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产生于南桥特殊的生存环境中。从地理位置来看,寻乌县地处赣、闽、粤的交界区,三省的匪徒常出没其间,吉南赣宁道的江毓昌曾把寻乌县列为其所属县内盗风最炽的九属之一。历史上寻乌县境内的赌风也非常盛行,赌场和烟馆是赌徒们聚赌的主要场所。从自然环境来看,南方山区阴霾多雨,瘴气熏人,虫蛇出没、各种疾疫容易流行。这样的生存环境,对于迁入南桥的客家先民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挑战。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除了需要吃苦耐劳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外,团结互助和求助于神灵也成了他们的精神诉求。因此,该地也像临近的其他客家地区一样,民间信仰之风浓郁,村里供奉着汉帝、五显大帝、许真君、财神、观音、土地等多位神灵。这样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状况同样也为南桥民众同心协力举行客家迎故事民俗提供了空间。
根据当地民间传说与史料记载,定居于南桥的六姓开基祖们,从生存现状出发,同心协力建造庙宇,并举行娱人娱神的迎故事民俗活动,力求最大限度地促进村民的村落认同与凝聚。之后除战争与“文革”时期外,南桥每3年基本都会举行一次迎故事民俗活动。每当活动举行的年份,提前半年左右,南桥村迎故事筹备委员会就开始进入活动准备的阶段。所谓筹备委员会,“文革”前由陈、曹、谢、刘、程、曾六姓村民组成。后来随着该村姓氏的不断增加和陈、谢两姓的强大,筹备委员会也成为以陈、谢为主力,多个姓氏共同参与的民间组织。
发展到现在,在南桥村,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更是一项全体村民共同参与的,超越了血缘、地缘以及业缘的大型村落活动。从参与活动的人群来看,不仅包括迎故事筹备委员会的成员、演故事的孩童、抬故事和神像的人员,而且还有参与仪式的腰鼓队、洋号鼓乐队、舞蹈队、戏班等。所有参与的人群抛弃了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职业及年龄等的差别,同等地参与到这个狂欢化的场景中,实现了村落社会人群的合理分工。具体来看,迎故事民俗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往往由有经验的老人坐镇指挥,有组织能力的成年人负责统筹规划,将老老少少的村民全部动员起来,齐心协力,群策群力,为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而相互协作。例如,2007年申请赣州市非遗时的筹备委员会即由谢小洪担任总指挥,陈治略担任总理事与总策划,副理事包括曹人才、陈兆贤、谢运春、陈治奇、陈星炎、谢运周、陈人贱、谢运春、陈松林、谢瑞奇、陈庆红、陈先荣、陈树功。除此以外,还有谢荣镜、谢应豪、陈治群、陈兆年、陈来传、陈人露、陈新海、陈治其、陈安玉、钟己招、刘二妹、刘凤娣、汤沃莲、曾德开、陈招淑、钟同英、戴丽华、钟三妹、陈穴群以及谢运安等人作为理事会成员进行协助工作。
由此可见,在迎故事民俗活动中,村民们依据自身的角色分工互帮互助,增强了民众之间的沟通和感情交流,展示了村庄实力。尤其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传统上高度整合的客家村落已出现了解体的趋势:在居住上,村落空心化格局已经出现,村民多建造单门独户的住房,老屋基案大多被废弃;在经济上,外出打工取代了传统的农耕生产,传统的生产互助关系不断弱化;在文化上,集体式活动逐渐减少。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充分发掘迎故事民俗活动的团队合作能力,无疑可以弥补乡村社会的弱势,通过民众的默契感与配合意识的深化,提升其团结合作的能力,从而为其主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奠定基础。
三、迎故事民俗活动与乡村凝聚力的强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运用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及时代价值的价值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其中乡村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人际关系的凝结,而民俗传统则可以在不同的人群、社会以及国家中强化整体意识。“当这些成分比文化群体中别的东西更有代表性时,它们就成了焦点,它们开始承担着比其文字传达出来的还要多的意义,它们成为符号,并有表现群体认同的能力。”[8]产生于特定文化生态环境中的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正是通过这种弘大的仪式展演,将本村及外村村民纳入表演队伍,凝聚邻里关系,弱化阶层区隔。
首先,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通过弘大仪式展演强化了其凝聚性。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是一种大型的民俗活动。每次活动举行期间,不仅有经验的老人会参加,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也陆续开始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在外地做生意、打工的一些人甚至会特地赶回来参与活动。在村民心里,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是他们的义务,更是一件很有“面光”的事情,是很有荣耀的。以此同时,不仅村里的人会按照各自的角色分工参与活动的筹备、指挥、扛故事台、扮演故事仔、演员化妆、财务管理、敬神仪式的主持、烟花与爆竹的燃放、舞龙舞狮等各项工作,而且邀请亲戚朋友前来观看,民俗活动也成为亲朋好友团聚的聚会。因此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是一项涉及到每一个民众的仪式展演。在参与的过程中,民众因此而产生联系,实现了村际文化的共享,深化了邻里关系、亲朋关系以及社会关系。而在乡村社会中,民众之间的这种友好、和睦、强大的凝聚力,则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作用。其次,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通过彰显其族群性强化了其凝聚力。“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地域文化特色是遗产的一个重要属性,其中,很多地域文化并非都具有独特的族群属性,但因为地域文化与族群文化有时很难清楚的区分,所以很多时候,地域性的文化遗产被导向族群属性。客家文化遗产中也普遍存在类似的现象。”[9]南桥是个典型的客家村落。在迎故事民俗活动展演的时候,往往会通过寻根问祖的仪式活动或“客家迎奥运”等故事内容展现客家族群的特色,更是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为了彰显南桥迎故事民俗活动的特色,将其直接冠以“客家”的族群特色,并在申报书中强调其族群特色,以示与寻乌县汶口畲族村落迎故事民俗活动的区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数十人捆绑式的表演,充分配合,高度协调,最能代表迎神赛社这种全民性狂欢活动的参与意识与群体理念。这种在共同信仰(地方保护神灵的崇拜)的旗帜下,在祈福禳灾的共同利益驱使下的捆绑式表演艺术形式,具有极大的社区整合功能。”[10]在南桥,因为村民共同的生活经历、遭遇以及经验习得,形成了共同的情感认同,迎故事为南桥人的认同表达提供了可以接受、交流、理解的符号,也通过这种极具凝聚力的展演构建了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仪式空间。这种空间凸显了村落宗族史和村落史,唤起和强化了该村人对祖先们团结起来艰苦创业的一种集体记忆。这种文化资源的背后,是深扎于内心深处村民的乡土情结,是对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及表演艺术的民俗认同。也正是凭借着迎故事这种不断展演的记忆载体,南桥村的村民表达了其崇神敬宗的情怀,延续了村民的身份认同,提升了村落凝聚力,维系了他们全村一体的观念。
四、迎故事民俗活动与乡村德治功能的发挥
法治以国家制度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秩序,德治则以道德对人进行感化教育。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当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必要手段与创新路径。在乡村社会中,德治主要通过礼乐教化对民众开展或潜移默化或直接的教育,使其通过提升内在的意识与道德来对自己进行约束与管理。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众活动所传达的和谐共处、团结合作、积极向上等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生成社会治理中的牢固联系,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的故事内容选择中得到集中体现。
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是将小孩子扮成故事中的人物抬着出游的仪式。每次活动举行的时候都会有4个以上的故事,而故事的选择则是本次活动主题的重要体现。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故事内容是举行活动的时候特别重要的工作。根据陈治略与谢小洪等人的访谈可知,每次故事的选择既要考虑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又要体现国家的大政方针;既要考虑到村民的族群与村落认同,又要考虑到村民的国家与民族认同。自1982年以来,南桥客家迎故事民俗活动选择的故事大概有“梁祝姻缘”“牛郎织女”“天仙配”“嫦娥奔月”“武松打虎”“桃园三结义”“四郎探母”“五女拜寿”“艰苦岁月”“四化宏图”“南桥巨变”“祖国新貌”“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喜迎香港回归”以及“脐橙丰收”等。在这里面既有传统的古典故事,也有结合国家政策与当代新社会形势的、反映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斗争的、纪念长征胜利的、宣扬扶贫的、号召保护农村环境的等主题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内容选择使得参与的民众在传承民俗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切身体会与感受到国家的政策与社会的新变迁。人们在观看中感知,在感知中学习,在学习中反思。迎故事民俗活动正是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政策的宣传表达,对表演者和观看者起到直观的道德教化作用。不仅使人们在参与和观赏中精神得到满足,而且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从而在无形中强化了对国家与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
五、结论
“地域意识、认同是人们对在地理范围、文化方面与自己生活有直接关联的自然共同体的归属性观念与感情忠诚,是人们关于生活方式、情感等文化精神方面的地域性集体心理结构。”[11]迎故事作为南桥客家的民俗活动,它的产生与南桥村的人文地理环境、生产生活、价值观念直接关联。其继承了百戏游艺和宗教傩仪的部分文化元素。一方面作为一种集体狂欢式的活动,将平时疏离的民众,基于血缘、地缘或者业缘等多种关系聚集起来。另一方面,其作为一种仪式,真实地映照出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样貌和当地客家民众的文化心理,是一种“赋予感情神圣统一的表现形式,从而修正、补充和加强了社会稳固所依赖的情感体系。”[12]同时它也是地方认同的表达载体,具有建构地方认同的功能。作为一种模式化的仪式,其为维系村民们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一种社会环境,唤起他们对民俗文化、祖先业绩、村落历史等的集体认同,并通过不断的仪式展演提升了民众的团队协作能力,发挥了传统文化的德治功能。因此,迎故事民俗活动作为民众集体参与的民俗活动,无疑是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提升民众团结协作能力以及德治功能等层面的积极作用,将其作为乡村社会非正式治理手段与正式手段相结合,无疑会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