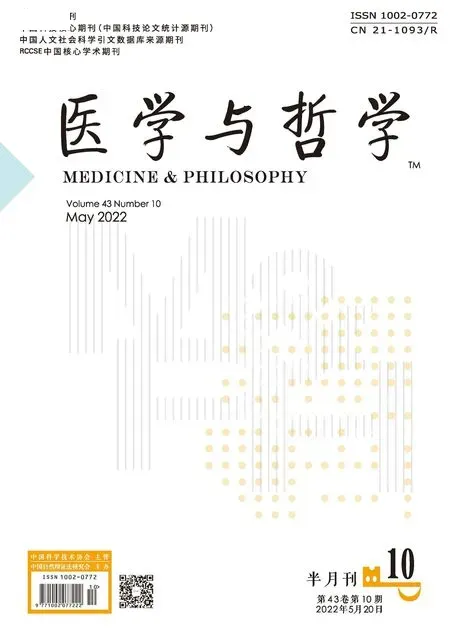叙事医学融入外科临床决策的思考*
张志强 杨琳琳 徐孟凡 尚慕寒 于德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生命健康的期望值亦逐渐增加。患者在罹患疾病时,诊疗过程中迫切希望获得最优化的治疗和最理想的疗效。疾病的诊治涉及医疗卫生、社会、家庭及经济等诸多因素,而临床决策是疾病诊疗的至关重要环节。临床决策是一个医患双方共同参与的复杂的过程,临床医生面对患者的实际临床问题,运用专业知识和经验,结合临床诊疗规范、指南及循证医学证据,制定符合医学伦理及法规的有效诊治方案,辅助患者做出抉择[1]。临床决策是基于医患合作的动态过程,贯穿于诊疗的全过程,受到医、患、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合理、高效的决策决定诊疗的质量,而传统的临床决策过于机械性,缺乏人文医学的渗透。如何寻求最佳临床决策是医患双方面临的棘手难题。叙事医学的逐渐成熟,融入临床诊疗工作,其关注与再现,共情与反思的特质,将人文融入临床工作中,让临床决策走向医患共享共赢。
1 叙事医学是临床决策的时代需求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逐渐成熟,传统的家长主义式的临床决策缺少对患者自主选择权的尊重,而合理的临床决策模式需要患者自主参与,临床决策逐渐向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making,SDM)模式转变。SDM理念是医学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医患追求的目标。Charles等[2]首先在医疗决策中提出医患SDM理念,就是在医患间有效的信息沟通情况下,让患者参与到临床决策过程中,结合患者意愿制定临床治疗方案。SDM在欧美国家的临床实践工作中已经发展成熟,而在我国则起步较晚,且缺乏适合我国医疗背景的地域化的理论体系及实践路径。
SDM鼓励医患双方共同参与到医疗决策当中,医生告知患者疾病诊断与相关治疗方案、各方案的证据及利弊,患者告知自身担忧、价值观和选择偏好,医患双方有效交换信息后,共同制定合理的诊疗方案[3]。SDM是近年来医学领域研究的焦点问题,其广泛开展有助于改善医疗质量,是健康中国战略的时代需求,但其实践仍存在较多问题亟待解决。共同决策的基础是医患有效沟通,达到信息的共享,心理情感的互动。当前国内外科领域的医患沟通多以知情同意的形式开展,有些医生将知情同意作为自我保护的“护身符”,致使医患沟通的平等性及有效性难以保证。当今临床SDM过程迫切需要有效的途径解决医患间信息交流、情感互动不足的瓶颈问题,而叙事医学可以实现医患互动、信息共享,构建医患价值共同体,在共同参与疾病的诊疗活动中实现SDM。
2 叙事医学弥补临床决策中的潜在陷阱
当前,医学知识逐渐形成完善的体系,医学不再是经验医学,临床决策也不仅依赖于临床经验。临床决策中的经验主义容易让临床决策陷入“偏执性陷阱”[4],形成定向思维,影响临床决策的质量。临床医生容易以“知识的权威”自居,聚焦医疗世界,忽视患者疾病背后的故事,尤其在门诊接诊过程中,面对繁重的门诊工作,问诊过程以医生的“问”和患者的“答”为主,忽视患者“倾诉”的权利,导致疾病诊疗线索丢失,常通过临床经验对疾病进行诊疗,而不是进行逻辑性的诊疗,无形中损害诊疗的质量;而具有叙事能力的医生,在诊疗过程中会认真“倾听”患者的疾病感受,通过倾听获取更为全面的临床决策信息,并形成逻辑性明显的诊疗思维,进行科学性的临床决策。但是医疗世界中,临床医生试图采用简单管理思维和“一元论”解析临床诊疗中的不确定性现象,事实上,无论是循证医学还是精准医学都在寻求临床决策的简化之道,但是缺少人文医学渗透只会让临床决策复杂化。循证医学关注的是群体利益,可以让患者避免无价值的治疗,却又忽视患者个体特征。循证医学指导下的临床决策将医生和患者、证据和病痛分离,导致“循证医学证据”去选择治疗“患者的病痛”的现象,而不是拥有证据的医生诊治罹患病痛的患者,缺少医学人性化考量。叙事医学情境下的临床决策可以促进循证医学和人文医学相向而行,而不是相背而行。叙事医学视角下,临床医生决策过程中应关注患者的疾病、社会生活状况及情感世界,平衡科学思维和人文关怀,寻求最为优化的决策。叙事医学和循证医学是医学决策的两翼,循证医学提供决策证据,叙事医学提供患者的“全人状况”。下文以一则案例来说明。
初见患者的医学诊断:一位36岁未婚青年女性患者由母亲陪同就诊,患者情绪低落,沉默寡言,并不能主动告诉医生疾病的情况,患者母亲告知医生“患者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10余天”,外院超声检查提示“左肾盂占位性病变”。住院后完善泌尿系CT检查亦提示“左肾盂占位性病变”,尿脱落细胞学检查提示“尿液内查见异型细胞”,膀胱镜检查提示“膀胱内未见明显肿瘤及出血病灶,左侧输尿管口可见血性尿液喷出”,患者否认任何用药史,初步诊断为“左肾盂肿瘤”。
医疗世界里,现有临床证据均支持患者“左肾盂肿瘤”可能性大,在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后可以在治疗上选择“左侧肾输尿管全长和膀胱袖套状切除术”的治疗方案,治疗的临床决策符合循证医学的证据及诊疗的规范,但是临床影像学检查是患者的真实世界吗?医生仅关注临床检查数据,却忽视了患者社会生活及心理状况。循证医学思潮下,临床医生关注更多的是医疗世界中疾病的证据,而对患者的社会生活现状(生活世界)、心理状况(情感世界)关注不足,并未还原“疾病真相”(如疾病的诱因),可能导致关键诊疗线索的缺失,影响临床决策质量。当前医疗背景下,临床医生在医疗工作中过度聚焦临床检查数据,而忽视患者的真实世界证据。患者的真实世界是指“医学世界、生活世界及情感世界的全部真实”[5],是“全人”的真实。叙事医学让医生关注两个世界,一个是患者的世界(疾痛),一个是医生的世界(疾病),而仅聚焦疾病维度时容易产生管状思维,陷入经验主义陷阱;叙事医学关注患者的疾痛,让医生自主地关注“故事的真相”,了解患者的病痛、心理状况、家庭状况及社会功能角色,也可以了解患者对治疗的期望值及家人对患者及疾病的态度。这则案例中的患者罹患“恶性疾病”却不关心自身疾病,医生获得患者个体信息有限(如疾病诱因),需要医生反思患者内心是否另有“隐情”,需要追问“故事的真相”,真相可能隐藏在患者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中。
3 追问故事真相:患者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叙事
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说:“了解你的患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了解患者得的什么病更重要。”临床决策中应秉承“以人为本”的思想,考虑患病的人,而不是仅仅关注患者的疾病。当叙事医学缺位时,临床医生在处理疾病时容易将疾病与个体分离,关注疾病,而忽视患者的“全人状态”,医生难以走进患者的内心世界。外科医生因其常见的“管状思维”习惯于以知识的“权威者”凌驾患者之上,削弱患者“讲故事”的能力,影响患者将问题外化过程,难以实现真正的医患对话。患者“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就是问题外化的过程,是患者为主体的叙事过程,蕴含叙事疗法的治疗价值,也体现医生对患者疾痛叙事的尊重。
临床实践中临床医生应关注患者的疾痛故事[6],而不仅仅是疾病本身,需要从患者及家属的交流中发掘内在故事,拉近医患的距离,而描述不应仅是医生“描述”,更应该是患者描述自己的故事,这样才能达到医患对话的目的。叙事的主体如果仅仅是临床医生,就会脱离叙事医学生根发芽的土壤,削弱叙事医学治疗价值。临床医生需要通过医患对话从患者的叙事情节中汲取材料,挖掘线索,了解患者的真实世界,患者也可以从医患对话中了解医生,实现医患共情,让人文融入临床,服务临床的诊疗工作。
临床工作中,患者隐瞒病史或者叙事闭锁现象并不少见,病史的不完整增加诊疗的困难,影响治疗的效果,而还原“故事真相”正是叙事医学的重要功能。患者叙事的引导和倾听,是叙事医学过程的开始。外科医生的叙事活动中,感知和识别患者的叙事需求是外科医生开始叙事活动的关键环节。但是,医生临床工作的繁忙,没有充分的时间引导和倾听患者的叙事,是叙事医学开展的内部困境[7],而外科医生的临床工作尤为繁重,工作中常“一刀繁华,一刀寂灭”,难以对每位患者开展叙事活动,就需要感知和识别特殊人群,而叙事医学在这部分特殊人群中发挥重要作用。“患者的故事”是叙事医学的根基,没有“患者的叙事”,叙事活动就是“无源之水”。外科医生引导患者“讲出自己的故事”,才能获得有意义的“叙事素材”。外科医生通过倾听“故事”才能走近患者,理解患者躯体痛苦和内心苦楚,形成医患共情态势,共情有助于形成医患相互信任,让医生真正了解患者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从而获取更多诊疗线索。
患者真实世界的故事:最初住院的5天,患者情绪一直比较低落,不愿意叙述疾病发生情况,对自身的病情严重性并不关心,患者处于“叙事闭锁”状态,叙事能力衰退,仅患者的母亲陪护,仅能获取“支零破碎”的疾病相关信息,笔者私下与患者母亲沟通,一位朴实的农村中年妇女用了1.5小时的时间将患者的身世、情感遭遇等详细说明。笔者得知患者上学期间,成绩优异,重点高中毕业进入重点大学深造,并保送研究生,毕业后拥有一份良好的工作,工作不久后因失恋罹患抑郁症失去工作,回到农村老家与母亲一起生活。
笔者通过患者母亲获得诊疗线索,但并未通过患者获得有效的线索。如何让这位叙事闭锁患者讲出自己的故事是全面了解患者诊疗线索的关键。笔者选择一间相对安静温馨的办公室,在患者母亲的陪同下,再次与患者交流。笔者并不是以“医生”的角色直接询问患者疾病的情况,而是像朋友一样的交谈,从彼此学生时代谈起,谈学习、业余生活,甚至人生,患者逐渐敞开心扉,讲出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患者研究生毕业之前生活学习一直很顺利,毕业后和男友一同远离家乡及家人去某大城市工作,工作成绩及待遇都很好,当患者憧憬的生活即将到来的时候,被男友抛弃,患者精神遭遇重大打击罹患抑郁症,失去工作后回到农村老家。患者在农村老家总是感觉周围人议论自己,自己亦自责对不住家人辛苦付出,因情绪低落,就医10余天前服下家里剩余的“鼠药”,服用鼠药后出现血尿却不愿意就医,患者母亲早期并未在意,1周前发现患者出血时间较长才强行带着患者就医。
“如果我们不仅进入患者的医学世界,同时进入患者真实的生活世界和患者的情感世界,临床判断有可能切合患者的实际,医患关系也有可能亲密起来。”[5]笔者营造患者家属“讲故事”的条件,让患者家属讲出患者的故事,初步了解患者的生活世界,进而创造外部环境,以换位思考的形式去打开患者“尘封世界”的窗,让患者讲出自己的故事,让医生还原“故事的真相”,走进患者的“生活世界”,获得诊疗的关键线索(药物服用史),让诊疗决策证据链更为完善。患者叙事闭锁影响医生解析患者的心理世界,是医患对话的障碍,叙事闭锁状态的解锁是个体化的过程,通过有效的手段完成叙事赋能,而叙事赋能首先是引导患者“用心讲故事”。外科医生临床工作繁重,难以普遍性开展叙事医学工作,因此外科医生应具有叙事医学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捕捉叙事医学介入的时机,通过倾听、沟通,实现有效的医患对话,获取全面的诊疗信息,实现SDM。总之,外科医生应利用好叙事医学这个充满温情的工具,走进患者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助力临床诊疗,弥补外科工作中冰冷机械的工作习惯。
4 叙事再现:让医生走进患者的内心世界
叙事医学需要对他人故事叙事再现,完成共情反思及升华。叙事再现就是将倾听的“故事”转化为感性或者理性认识,可以是书面文本的形式(如平行病历),也可以是非文字的形式(如口述叙事)。平行病历是“声(患者心声)情(医患共情)并茂”的病历,更是“患者心声和医患协同努力战胜疾病的凝结物”[8],但是,邹明明等[7]的调查研究表明医生的时间和现行病历书写的规范性要求仍然是制约我国平行病历书写开展的主要原因,而外科医生,尤其是高年资外科医生,由于临床及科研工作繁重更无充足的时间书写平行病历,口述叙事可以作为平行病历的补充,这也是灵活的叙事实践。叙事再现的目的是共情与反思,没有共情的叙事就失去叙事医学的灵魂;再现不仅是“故事”再现,更是“共情”的再现,是医生情感世界的再现,是医患情感共同体形成的有效途径。再现过程中,临床医生既需要批判性反思,也需要感悟性反思。批判性反思更直接,外科医生最为常见,外科医生可以通过批判性思维直接评判手术方案的效果;而感悟性反思常被外科医生忽视,但可以反思个体的整个诊疗活动,总结临床决策的经验与教训,反思患者对治疗的需求及不足。笔者从患者及家属的叙事中了解患者的遭遇(患者的生活世界),进而感受到患者内心的痛苦(患者的情感世界),反思医生在医疗世界中并没有对患者进行“全人”的了解,进而叙事医学再次介入,给予患者倾诉的权力,获取更多的信息,进而调整临床诊疗的思路,形成证据链完整的临床决策。
临床经验固然重要,没有了患者参与的诊疗工作,临床经验就像折翼的飞鸟无法发挥应有价值。一位高学历的青年女性为什么会对自己的生命毫不关心?我们忽略患者内心潜隐的“死亡是解脱”的无助感,患者将自己囚禁在抑郁的囚笼中无法自拔。患者需要一扇窗,让希望之光照进内心,驱逐阴霾。事实上,我们在诊疗中给予患者的些许人文关怀与帮助,让患者重燃生活的信心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讲出自己的故事。年轻女性可能会由于情感问题而产生心理创伤,甚至选择极端处理方式。诊疗中自发的叙事医学实践可以让医患建立价值共同体,共同面对疾病,共同实现治疗的价值最大化。
5 叙事医学的归属:SDM走进现实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患者参与临床医疗决策的意愿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患者倾向以“自我”为中心,希望参与到自身的临床决策中,驱动盛行已久的被动接受的模式逐渐向主动参与型演变,实现合理共享决策的“憧憬”[9]。SDM受到患者自身、患者家庭状况、医生、医疗水平及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SDM是基于医患双方的合作关系实施的医疗决策,需要医患双方在信息交流共享(疾病诊疗信息、期望值等)的基础上,共同参与达成治疗策略的共识,进一步共同决定要执行的诊疗方案[2,10]。SDM需要具有共同决策能力的“合格”的医生和患者参与,临床实践中患者作为“弱决策能力者”(如文中的患者),需要医生引导患者成为“合格”的SDM参与者。SDM患者必须有参与决策的意愿及叙事的能力。叙事医学情境的临床决策能力需要患者叙事条理清楚、真实,并信任医生的专业知识及技能[11]。从叙事医学视角进行临床决策,可以给予患者更多的叙事空间,建立医患信任及合作的关系,让患者较为轻松地了解诊疗信息,实现信息共享;医生更为全面地洞悉患者的内心状态、家庭及社会功能状况,实现情感共鸣,提升临床决策过程中患者参与程度,改变传统“家长式”的临床决策模式。
患者最后的医治方案:患者的倾诉让笔者获取更为全面的诊疗信息,患者的血尿可能是鼠药导致,需要多学科介入治疗。笔者向患者解释,血尿的原因很多,其中肿瘤、感染性疾病比较常见,而患者血尿可能由鼠药导致的凝血功能障碍导致,暂时不需要外科手术的干预。患者获知不需要手术治疗后,心情明显好转,愿意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经血液科和肾内科多学科讨论后,诊断为鼠药继发的凝血功能障碍,经过补充维生素K1、碱化尿液等治疗后血尿逐渐消失,笔者在心理科医生的指导下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1个月后再次门诊时,患者情绪明显好转,可以看到患者久违的笑容,主动要求医生详细地为自己检查,复查肾脏超声提示“左肾盂未见明显占位”,尿常规未发现红细胞。患者的母亲告诉笔者,患者出院后心情好了很多,能和周围的人主动聊天,走出家门参加集体活动。当笔者告诉患者目前已经恢复正常,患者充满对医院及医生的感激之情,同时告诉笔者“自己要重新回到社会工作”。
文中主人公因处于叙事闭锁状态缺少临床决策的意愿,不能参与SDM,需要临床医生给予患者叙事赋能,引导患者参与临床决策;正是临床医生走进患者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让患者重返社会,实现临床决策方案调整,进而获得治疗利益的最大化。SDM需要患者有参与决策的能动性及意愿,患者如果参与临床决策的意愿不强,SDM无从谈起。临床医生需要合理调动患者参与SDM的能动性,叙事医学实践可以洞察患者对疾病认知态度,对生活的态度及参与SDM意愿,从而适时引导患者及家属参与到临床决策的过程中,而不是被动接受决策。医生应知晓影响患者参与临床意愿的因素,如年龄、文化程度、个人偏好及家庭状况等,有助于医生识别干预人群。家庭环境(功能)、社会支持功能完善的患者,可以获取更多的外在支持与帮助,更容易学习并吸收诊疗相关的信息,参与到临床的SDM过程中,并主动评价决策的效果。患者的真实世界感受是评价临床干预效果的证据,文中患者干预后自身感受良好是对临床决策效果的最好评判指标之一。叙事医学走进患者的生活世界及情感世界,从“全人”的角度引导患者进行医患对话、临床决策及决策效果的评估。
此外,医疗情境下,医生掌握专业知识, 在临床决策中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无疑会将医生的价值观及意志凌驾于患者之上[12],无形中削弱了患者主动参与临床决策的权力。传统思想影响下,医生作为医疗信息的权威者深深植入患者心中,致使患者缺乏医疗知识质疑能力,主动参与临床决策能力不足,阻碍患者参与SDM。叙事医学视域下的临床决策尊重患者的自主选择权,也可以识别患者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充分从诊疗需求、治疗期望及体验等方面解析患者真实世界需求,为SDM创造有利条件。总之,叙事医学背景下,通过患者的叙事,外科医生可以了解患者家庭及社会情况,获取患者疾病“潜隐的信息”,并洞悉患者及家属内心需求、价值观及期望值,建构基于生活世界、情感世界及医疗世界的三位一体的临床诊疗决策模式,保证SDM的质量。
6 叙事医学营造医患共同体,促进SDM
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等、临床医生程序化的解释说明、指令式的嘱托,让医患的交流沟通过多流于形式,难以实现信息共享,不利于形成医患知识共同体,导致医患双方临床决策地位的不平等,不能有效主动参与到临床决策。医患间的叙事可以有效进行信息共享、信息互通,构建医患知识共同体,而知识共同体的建构是高质量临床决策的基本要求。
患者受病痛困扰,内心较为脆弱,甚至叙事闭锁,难以将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的真相呈现给临床医生,而疾病诊疗及临床决策的关键信息常潜隐在患者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中。叙事医学的共情与反思具有叙事赋能的潜质,而倾听给予患者更多倾诉空间,倾诉给予医生更多疾病诊疗相关线索,而倾诉本身具有“治愈”功能。临床医生的共情与反思可以赢得患者的信任与尊重,实现有效沟通,这正是叙事医学所倡导的理念。一项在990名国内实践叙事医学的医务人员中开展的调查研究表明了多数医务人员认同叙事医学能促使医务人员理解患者的处境,实现共情,做出更为合理的临床决策[13]。叙事医学情境下,外科医生可以走入遭受疾痛的患者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洞悉患者遭受的疾病带来的痛苦、心理冲击、家庭社会压力,更容易换位思考,实现共情与反思,让医疗活动充满人文关怀,建构医患情感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有利于形成相向而行的医疗价值观和选择偏好,铸造医患价值共同体。叙事医学有助于医生认识患者的全部真实世界,形成集医学世界、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三位一体的临床诊疗生态,建构医患知识、情感及价值共同体,助力SDM。
7 结语
医患之间是一个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其努力的目的是实现医患合作共赢,而在当前医疗环境下,医患之间的博弈更加趋于对抗而不是协作及趋同,侵蚀医患间应有的信任[14]。健康中国背景下,外科医生迫切需要重塑医生与患者的合作关系,让人文融入到临床决策的过程中,SDM更具科学性及人文性,避免决策的机械性及普适性,实现患者利益的最大化。临床诊疗工作中,外科医生注重外科手术的结果,忽视“信息共享”和“共同决策”的过程,限制患者叙事的权利,削弱患者参与SDM的权利。叙事医学改善医患双方的临床决策能力,弥合医患信息不对等的鸿沟,尊重患者参与临床决策的权利,完善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叙事医学情境下的SDM,关注患者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让医患平等对话,形成集认知、情感及行动为一体的诊疗活动,弥合医患分歧,营建医患同心的医疗生态[15],缓和现代医学技术对人文精神的侵蚀,让医学与人文相向而行,形成医学技术与医学人文融合的人文医疗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