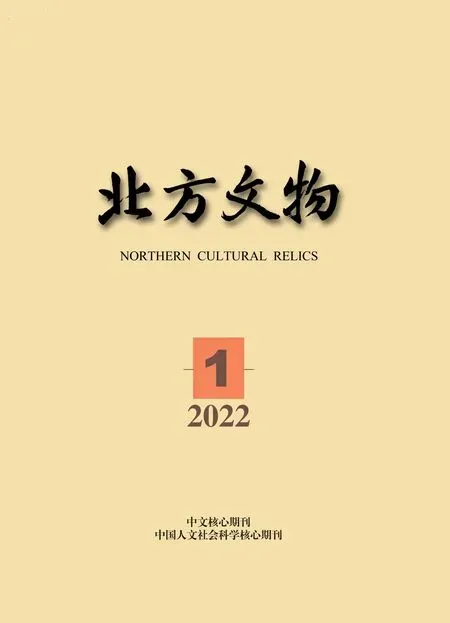辽东属国再探讨
史话 焦彦超
(1.山东大学东亚文献研究中心;2.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学校)
〔内容提要〕 辽东属国设立于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设置的主要背景在于东汉初年乌丸的内附,直接原因是安帝时期鲜卑与高句丽对幽州的侵扰。辽东属国首县昌辽(昌黎)经历了从西汉辽西郡东部都尉治所,到东汉初辽东郡西部都尉治所,最后到辽东属国都尉治所的变迁。东汉末年,辽东属国废于公孙氏政权。曹魏灭亡公孙氏政权后,鲜卑内附,复置辽东属国,后改其为昌黎郡,并为晋所继承。
汉晋之际,古代中国的边疆频有盈缩,以东北区域为考察对象可知,在建制方面存在较大的变动,除东部玄菟等边郡内徙之外,辽西郡近塞诸县也有废迁,尤其是“辽东属国”在郡县之间的建立,成为边疆控制的新模式。学界对辽东属国已有一定的关注①,然而,在辽东属国设立的时间、目的,以及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辽东属国的变迁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探讨的空间,进而有必要对东汉的边疆治理做进一步研究。
一、设立辽东属国的目的
汉代的属国制与秦代典属国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②可见,属国有管理与安抚内附少数民族的作用。不过辽东属国究竟是安抚哪一个民族,学界有一定分歧,主要有乌丸③、乌丸和鲜卑④等认识。要想解决此问题,必须先弄清辽东属国设立之前,乌丸、鲜卑二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分布状况。
《三国志·魏书·乌丸传》注引《魏书》云,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予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⑤。这是乌丸人在东汉的第一次大规模内附,东汉将郝旦所率领的人众分散到塞内包括辽东属国在内的广阔地区,以防止其反叛。至汉安帝时,“乌丸稍复亲附,拜其大人戎末廆为都尉。至顺帝时,戎末廆率将王侯咄归、去延等从乌丸校尉耿晔出塞击鲜卑有功,还皆拜为率众王,赐束帛”⑥。由此来看,戎末廆所率领的部众在安帝时也已经居于塞内,按照东汉政权处理郝旦部众的方法,这批内附的乌丸人中一部分也应被分配到后来设立了辽东属国的地区居住。
鲜卑的情况与乌丸不同。安帝之前,鲜卑首领多次向汉廷请求封赏,如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率种人诣阙朝贡,封于仇贲为王”;明帝永平年间,“祭肜为辽东太守,诱赂鲜卑,使斩叛乌丸钦志贲等首,于是鲜卑自炖煌、酒泉以东邑落大人,皆诣辽东受赏赐”⑦,但文献中并没有鲜卑首领带部众内附的明确记载。
据《后汉书·鲜卑传》载,东汉中期,辽东鲜卑和辽西鲜卑经常侵扰边郡。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辽东鲜卑寇右北平,因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殇帝延平元年(106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安帝永初四年(110年),“辽西鲜卑连休等遂烧塞门,寇百姓”;顺帝永建二年(127年),“辽东鲜卑六千余骑亦寇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率众王出塞击之”⑧。这些记载表明,“辽东鲜卑”与“辽西鲜卑”的主要聚居区都不在塞内。
在东汉政府设立辽东属国之前,这一区域内主要聚居的少数民族为乌丸。尽管汉族、乌丸与鲜卑之间的交往比较密切,当有部分鲜卑人居住,诚如程妮娜认为的:“到东汉初年,东北的辽西郡和辽东郡内,已经居住了许多乌桓人的部落和少量的鲜卑人部落。”⑨不过,相对于乌丸,鲜卑人的数量不多,不足以影响东汉政府改易地方建制。
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后,随着乌丸的内附,辽东属国设立⑩。虽然乌丸内附的详细情况不见于记载,对东北的影响程度也难以判定,但内附乌丸人是辽东属国设立的基础,而鲜卑与高句丽对幽州的肆意侵扰则是辽东属国设置的直接原因。据《后汉书·鲜卑传》载,元初二年(115年),辽东鲜卑围无虑(今辽宁省北镇县东南大亮甲村),攻扶黎营(今辽宁省朝阳市东南郭家窝堡村)。元初四年(117年),鲜卑寇辽西,被辽西郡兵与乌桓击破。另据《后汉书·孝安帝本纪》载,元初五年(118年),高句骊与秽貊寇玄菟;八月,鲜卑寇代郡,杀长吏;冬十月,鲜卑寇上谷。元初六年(119年),鲜卑寇马城,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击破之。建光元年(121年),高句丽与东汉政府更是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战争;十一月,鲜卑寇玄菟。安帝早期,东北地区基本上是稳定的,鲜卑与高句丽的同时发难,使得幽州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采取特殊措施处理边疆问题迫在眉睫。
在汉代的军事体系中,属国兵一直是重要的军事力量,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张珰曾上书云:“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闲,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由此可见,在鲜卑和高句丽的侵扰下,出于借助属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其中的乌丸兵)以解决边疆问题的考虑,东汉政府设立辽东属国。
二、辽东属国设立的时间
关于辽东属国设立的时间,学界大体有两种认识。《后汉书·郡国志》:“辽东属国,别领六城。”李贤注曰:“故邯乡,西部都尉,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同书《和帝纪》又载,永元十六年(105年)十二月,“复置辽东西部都尉官”,所谓西部都尉,“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在辽东郡昌黎城也”。由这则记载出发,传统观点认为,辽东属国设置于安帝时期(107—125年)。然而,由上引《三国志·魏书·乌丸传》注引《魏书》所载可知,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之前已有辽东属国。“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实际上,光武帝时期所设立的“属国”,应指所恢复的安定属国和建立的越隽西部属国,而辽东属国则是“安帝又命属国别领比郡者六”中的一个。《后汉书·和帝纪》中所记载的永元年间(89—104年)复置的“辽东西部都尉官”,则有可能是在建武六年(30年)之后初次设立。有学者认为,辽东属国很有可能设置于光武帝时期。
辽东属国置于安帝之前的记载仅有上述一条史料,而在安帝时期及其以后则多次出现。如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四月甲戌,“辽东属国都尉庞奋,承伪玺书杀玄菟太守姚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冬,“鲜卑后寇辽东属国,于是耿晔乃移屯辽东无虑城拒之”;桓帝延熹六年(163年)五月,“鲜卑寇辽东属国”。对《三国志·魏书·乌丸传》注引《魏书》中所出现的“辽东属国”,金毓黻认为是辽东郡之误,因而把辽东属国设立的时间定在汉安帝时期更为准确。
元初二年(115年),“辽东鲜卑围无虑县,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鲜卑无所得。复攻扶黎营,杀长吏”。有观点认为,当时并未见属国都尉派兵出击,同时,通过建光元年(121年)三月,辽东属国都尉庞奋杀玄菟太守姚光这一事件判定,辽东属国的设立是在元初二年(115年)及建光元年(121年)之间。这一判断基本可信。
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判断辽东属国设立的时间。建光年间,高句丽与东汉政权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战争:“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遣使诈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据险阸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秋,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安帝即位之年(107年),将原辽东郡的高显、候城、辽阳改属玄菟郡,西汉时期,玄菟郡所辖三县也早已西迁,此时,其地域大部分是原辽东郡的,而辽东属国也是从辽东郡中分置出来的,这三个地区完全可以看作一个整体。属国都尉庞奋能以伪玺书诛杀姚光,可见有一定兵权,但这一年春季,幽州刺史所率领的军事行动只有玄菟太守和辽东太守参与,说明此时并没有设立辽东属国。辽东属国的设立当是在建光元年(121年)春季,高句丽人遂成寇略玄菟、辽东郡之后不久。
三、辽东属国的首县
《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辽东属国下辖六县:昌辽、宾徒、徒河、无虑、险渎、房。首县昌辽,《后汉书·郡国志》记:“故天辽,属辽西”。然而,在《汉书·地理志》中辽西郡下并没有天辽县。《汉唐地理书钞》引《十三州志》:“辽东属国都尉治昌黎,道有黄龙亭,魏营州刺史治。”《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交黎县条”下颜师古注:“应劭曰:今昌黎。”因而惠栋认为,“昌辽”当作“昌黎”,“天辽”当作“交黎”,钱大昕则认为“昌黎”亦作“昌辽”。基本上可以认定,此昌辽即昌黎,是西汉时期辽西郡的交黎。
对于昌黎城的位置,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认为位于今辽宁省义县;王绵厚、王成生、韩宝兴皆将其考定在今凌海市(原锦县)境内,具体位置则略有差异;冯立民将其考定为今锦州老城。
要明确昌黎城的位置,则先要考订汉代东北地区的水系。“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东部都尉治,莽曰禽虏。”大部分史家皆认可“渝水”指今大凌河自下府(大凌河与牤牛河汇流处)东南流入辽东湾一段。冯立民将渝水考定为今小凌河,但此说证据不足。咸康二年(336年)春正月壬午,慕容皝曾“率其弟军师将军评等自昌黎东,践冰而进,凡三百余里。至历林口,舍辎重,轻兵趋平郭”以征讨慕容仁,可见昌黎必在大凌河下游近海处。讨灭慕容仁后不久,慕容皝“徙昌黎郡,筑好城于乙连东”,箭内亘根据《资治通鉴》认为,慕容皝徙置昌黎郡的时间在咸康三年(337年)。
后世诸多著作皆混淆了辽东属国都尉所在的昌黎与慕容皝徙置后的昌黎,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的讹误,如《十三州志》在“辽东属国都尉治昌黎”后有“道有黄龙亭,魏营州刺史治”记载,便属于此类。“白狼水北迳白狼县故城东……又东北迳昌黎县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东部都尉治,王莽之禽虏。应劭曰:今昌黎也……又东北迳龙山西……又北迳黄龙城东。”黄龙城乃今朝阳,由此来看,《水经注》中的“昌黎县故城”距海极远,显然不是东汉时期的昌黎城,《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据《水经注》将昌黎考定为今义县,亦误。综上来看,昌黎城当在今凌海市。
考察其具体位置,我们可以参考考古资料。考古调查发现,辽宁锦州市凌河区向东到凌海市东部右卫镇,大凌河下游一片河网密布的区域是辽西地区一处汉墓集中地区,包括东花墓群、东张墓、西彭墓、西网墓群和右卫墓群。其中右卫墓群中的一座石椁墓,有着鲜明的乌桓鲜卑文化特征。交黎县城址大约位于距墓群不超过5千米的范围内。王绵厚将昌黎定为锦县(今凌海市)北之大业堡汉魏古城址,但大业堡汉魏古城址位于大凌河南岸,墓葬群却在大凌河北岸。王成生将昌黎考定为今凌海市白台子乡王家窝堡的南城子汉魏晋古城,但此城址面积为200×500米,定为昌黎城故址显然过小。韩宝兴将其定位于今锦县东花乡西花村,并认为此处尽管尚未见有城墙遗迹,但若将昌黎定于此,与平郭的距离与《资治通鉴》所记载“凡三百里”基本相符,这一认识更具合理性。
关于昌黎另有一说,张博泉认为,东汉的昌黎并不是西汉的交黎,而是西汉的柳城(今朝阳)。因为“昌辽,故邯乡,西部都尉,安帝以为属国都尉”中的西部都尉是指西汉辽西郡西部都尉。尽管昌黎在西汉时属于辽西郡,但此西部都尉并非指西汉辽西郡西部都尉,而是指《后汉书·和帝纪》记载中复置的“辽东西部都尉官”,这里涉及东汉辽东郡辖域范围变迁问题。
《后汉书·郡国志》中有关郡县的记载,反映的是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左右的建制情况,并不能反映出之前以及之后地方建制的变迁。西汉末年开始,由于受乌丸和鲜卑侵扰的影响,辽西地区县治弃置与边塞内徙的情况十分严重,整个东北地区的地方建制也有所变动。同时,东汉早期辽东郡较西汉时期有很大变化,辖域远大于《后汉书·郡国志》中的记载,甚至曾一度向西扩张辖有辽西郡的肥如,而辽东属国的六县都是从这一辖域更为广大的辽东郡中分置出来的。
《后汉书·郡国志》:“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汉安帝时期所设置的其余几个比郡属国——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分别是从张掖郡、广汉郡、蜀郡、犍为郡中分置的,并冠以原郡之名。由此可见,在比郡属国设立之前,属国所辖县应当从属于同一郡,也即“本郡”,辽东属国也不例外,而且辽东属国的“本郡”就是指辽东郡。对于西汉时属于辽西郡的昌黎、宾徒、徒河三县,《后汉书·郡国志》都记作“故属辽西”,而对于西汉时属于辽东郡的三县无虑、险渎、房都不写其“故属辽东”,可见,所谓“故属辽西”是指这三县在划到“本郡”辽东郡之前曾属辽西,而非是指其划到辽东属国之前曾属辽西。昌黎在新的辽东郡中位置偏西,设有辽东西部都尉亦是应当。退一步讲,假使辽东属国是从原辽西郡、辽东郡中各分一部分所置,按“置本郡名”的原则,显然是应该按首县的本郡命名,那么这一属国便会被叫作“辽西属国”,而不是“辽东属国”,因而东汉的昌黎是从属过辽东郡的。
有汉一代,辽东属国的首县昌黎城,经历了从西汉辽西郡东部都尉治所(此时叫“交黎”),到东汉初期辽东郡西部都尉治所,最终到辽东属国都尉治所的变迁,而这种变迁所反映的是汉代东北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
四、辽东属国的变迁
东汉末年,东北地区动荡,既有乌丸、公孙氏政权与曹魏的争衡,也有鲜卑与高句丽的摩擦。在这种形势下,辽东属国数易其主,自身建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首先,乌丸发展迅速,至汉灵帝初年,“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又辽东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这里的“辽东”并不是指“辽东郡”,而是指“辽东属国”,《三国志·魏书·乌丸传》中明确记为“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汉灵帝光和(178—184年)年间,“渔阳张纯诱辽西乌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蓟中,自号将军,略吏民攻右北平、辽西、属国诸城,所至残破”,后来公孙瓒“迁中郎将,封都亭侯,进屯属国,与胡相攻击五六年。丘力居等钞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瓒不能御”。以往乌丸只劫掠边郡,如今竟敢长趋至青州、徐州,而身居乌丸后方的公孙瓒,与乌丸相互攻击五六年也没取得什么成果,可知他在辽东属国只是勉强维持。中平五年(188年),刘虞被任命为幽州牧,公孙瓒也被调入右北平。尽管在刘虞的安抚下,乌丸之乱得以平定,但此后史籍便再也不见有汉廷所任命的辽东属国官员,不难推测辽东属国应在中平五年(188年)之后不久,基本上被乌丸所控制。
然而,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很久。曹操北征三郡乌丸、讨伐袁谭之前,“柳城乌丸欲出骑助谭。太祖以招尝领乌丸,遣诣柳城。到,值峭王严,以五千骑当遣诣谭。又辽东太守公深康自称平州收,遣使韩忠赍单于印授往假峭王。峭王大会群长,忠亦在坐”。后来曹操方面的使者牵招同公孙康的使者韩忠发生了冲突,牵招“捉忠头顿筑,拔刀欲斩之。峭王惊怖,徒跣抱招,以救请忠,左右失色。招乃还坐”。这里的“峭王严”就是自称峭王的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本来要派兵协助袁谭的是“柳城乌丸”,换言之就是辽西乌丸,但实际上却是苏仆延要“以五千骑当遣诣谭”。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苏仆延已经被逐出了辽东属国转而居住在辽西的柳城,已与“柳城乌丸”无异。
《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记载,公孙度任辽东太守时,“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苏仆延西走辽西必然是公孙度“西击乌丸”的直接结果。也正是因为遭受过公孙氏的军事打击,因而深知其实力,当牵招要斩杀公孙康的使者时,苏仆延的反应十分激烈,他显然不敢因为使者被杀而问罪于公孙康。公孙度于中平六年(189年)开始任辽东太守,他“东伐高句骊”一事按《三国史记》之记载,是在197年,尽管《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将“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写在“初平元年”(190年)之前,但公孙度“西击乌丸”一事未必发生在初平元年之前。曹操准备大举进攻袁谭是在建安九年(204年),在此之前,辽东属国之地已为公孙氏政权所占据。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定三郡乌丸之后,“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熙奔辽东……公引兵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三郡乌丸之首领与袁尚、袁熙在柳城战败后向东径直投奔公孙康,而不曾在辽东属国试图阻击曹操,曹操亦不再向东攻城略地,这也是公孙氏政权已据有辽东属国的一个依据。
《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记载,景初元年(237年),公孙氏“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等赍玺书征渊。渊遂发兵,逆于辽隧,与俭等战”,翌年春,“遣太尉司马宣王征渊。六月,军至辽东。渊遣将军卑衍、杨祚等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东北历史地理》以这两条史料为依据,认为“辽隧为公孙氏西境之门户”,进而认为“公孙氏之西界,仅至辽河东之辽隧,辽河以西的辽东属国不属公孙氏管辖范围。而魏初幽州所辖,仅止于今河北省东部的辽西郡。辽东属国地,在魏初当属两不管之地,故建制废”。
尽管公孙渊两次面对曹魏的攻击都采取了据辽河守辽隧的方法,但这并不能说明公孙氏政权的西界就在辽河(或辽隧)。后世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征高句丽,《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对此事的记载皆从隋军强渡辽河开始,但高句丽在辽河以西也有领地,即隋朝此次战役后,“唯于辽水西拔贼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之地。文献中关于曹魏与公孙氏政权两次战斗的记载都是从辽水之战开始的,公孙渊的两次防御策略都是放弃辽河以西城市,直接据辽河而守。因为辽河作为自然的天堑,据此而守显然要比以辽河以西的城市为据点的防御代价更小一些,所以,不能以此断定公孙氏政权的西界就在辽河。
公孙度曾对辽东地方建制有所变更,“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金毓黻对此的解释是:“分所领辽东郡,为辽东中辽辽西三郡,除辽东太守仍由自领外,其余二辽,亦各置太守。”之后学界大多认为,公孙度分辽东郡成辽东、中辽、辽西三郡,但也有学者倾向于认为公孙度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两郡。
《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中有“众立恭为辽东太守”“明帝即拜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等记载,显然分辽东郡为三郡说更为合理。建安十八年(213年),“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此时已是公孙康任辽东太守时期。《后汉书·百官志》注引《献帝起居注》“冀州得魏郡、安平……辽东、辽东属国、辽西、玄菟、乐浪,凡三十二郡”,其中并不见有公孙度分置的辽西、中辽郡,因而有些学者认为,公孙度所分置的辽西、中辽郡已被废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曹操柄政之时倡复九州,划郡分国,亦颇郑重其事,惟其建置仅行于其势力范围之内,其他命令不及之处则固仍因旧制,吴人不废交州,即其明证”。公孙度分设中辽、辽西两郡是为了适应东汉末年大量流民流入辽东的形势,同时也是出于增加建制显示自身实力的考虑。而到了公孙康时期,这两个条件依旧未变。正如东吴政权不曾废置交州一样,公孙氏政权也不会废置辽西、中辽两郡。
清人吴增仅在《三国郡县表》中认为:“献帝起居注所载幽州属郡犹有辽东属国,相传废于公孙氏。”吴氏后一句可提供的信息,值得关注。我们认为,公孙度所分的辽东郡,已经不再是《后汉书·郡国志》中所记载的辽东郡。公孙度驱逐了据有辽东属国的乌丸首领之后,辽东属国本身为安抚乌丸所存在的价值便已不大,况且辽东属国本就是从东汉初期的辽东郡中分置出来的,公孙度将其归于自己直辖的辽东郡是顺理成章的。对于公孙度所分置的辽西郡,王绵厚认为,“应限于医巫闾山以东,辽河以西的故‘辽东属国’的一部分”;金毓黻认为,“应在辽河以西,为辽东属国之地,后来以置昌黎郡者也”。公孙氏政权基本上占有了原辽东属国的全部之地,显然是金说更为合理,公孙度所分置的辽西郡与原辽东属国的地域范围基本重合,而昌黎也很有可能是这一新置辽西郡的行政中心。
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讨灭公孙渊。正始五年(244年),“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这是曹魏所复置的辽东属国。鲜卑在此时内附并不是偶然,公孙氏政权据有原辽东属国之地时,鲜卑势力是被遏制于这一地区之外的,而当公孙氏政权覆灭后,这一地区出现了一定的权力真空,鲜卑正好趁机南下。
这里本就是乌丸内附之地,其自然地理环境应对乌丸、鲜卑这样的游牧民族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公孙氏政权覆灭时,史书有“辽东、带方、乐浪、玄菟悉平”之语,此处不见有中辽、辽西两郡之名,在我们看来,应当是曹魏平定公孙渊后不久,便将公孙度所私设的辽西、中辽两郡又划归到了辽东郡里,毕竟这两郡乃公孙度所私设,且辽西郡之名曹魏政权亦有,若不改并必然会引起混乱,而带方郡则因有“倭韩遂属带方”之要事而被保存了下来。曹魏所复置的辽东属国当是从辽东郡中所分置的,与汉安帝时期的情况一致。
《晋书·地理志》:“昌黎郡,汉属辽东属国都尉,魏置郡。统县二,户九百。昌黎、宾徒。”曹魏复置辽东属国不久,便改为昌黎郡,并为晋所继承。昌黎郡的治所昌黎县就是东汉辽东属国都尉的治所,所辖的宾徒也是东汉时辽东属国的辖县。可知,魏复置的辽东属国以及后来的昌黎郡,都是承东汉的辽东属国而来。
综上所述,由于鲜卑与高句丽频繁侵扰幽州,导致东北动荡,为了安置内附的乌丸,安帝以原西汉辽西郡东部都尉治所(即东汉初辽东郡西部都尉治所)为核心设置辽东属国。公孙氏“雄张海东”时,辽东属国废止。曹魏灭亡公孙氏政权后,重新设置辽东属国以置内附的鲜卑人,晋时改为昌黎郡。辽东属国从东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设置之后,在近百年的时间中,经历了废除、重置,以及改置为昌黎郡等多重变迁。每一次嬗变都是中原王朝同周边的乌丸、鲜卑、高句丽、公孙氏等交流或角力的结果,是汉晋之际古代中国东北边疆局势的缩影。
注 释:
① 张国庆:《东汉“辽东属国”考略》,《历史教学》1990年第2期;苏卫国、张旗:《有关东汉辽东属国问题的一些看法》,《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韩宝兴:《辽东属国考——兼论昌黎移地》,孙进己、冯永谦、苏天钧主编:《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10),北京出版社1997年,下同,第815—818页;王宗维:《汉代的属国》,《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年,下同,第41—62页;金毓黻:《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下同,第88—90页;王绵厚:《秦汉东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下同,第130—133页;程妮娜:《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华书局2011年,下同,第51—53页。
②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年,下同,第735页。
③ 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9、80页。
④ 金毓黻:《东北通史》,第90页;程妮娜:《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制史》,第51、52页;张国庆:《东汉“辽东属国”考略》,《历史教学》1990年第2期。
⑤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传》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下同,第833页。此事《后汉书·乌桓传》记为:“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三国志·魏书·乌丸传》注引《魏略》叙述毌丘俭东讨公孙康时,曾经投奔辽东的乌丸大人“率众五千余人降”,曹魏政权“封其渠帅三十余为王”。由此来看,若有八十余乌丸渠帅,其部众人数当以九千余人更为恰当。
⑥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传》注引《魏书》,第832页。
⑦ 《三国志》卷30《魏书·鲜卑传》注引《魏书》,第835页。
⑩ 王绵厚:《秦汉东北史》,第131、132页;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版,下同,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