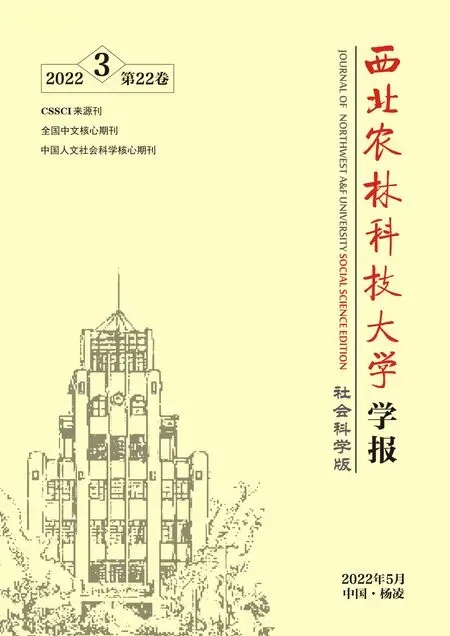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农业经营模式的形塑机制
——基于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发展的思考
陈 航 英
(陕西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西安 710119)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全国性土地流转大潮的兴起以及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大量涌现,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正在发生转变,即从原先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经营模式逐步转向规模化的、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的转变已引起社会学界的关注,甚至有学者呼吁应该“把农业带回来”并将之置于今后我国农村研究的中心位置[1]。
相较于国外相关研究,国内有关农业经营模式转变的社会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不少学者已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农业经营模式转变的动力机制研究。有学者认为,推动我国农业经营模式转变的主要动力是农业企业公司[2]。而亲小农学者则认为我国农业经营模式转变主要是由行政力量推动的[3]。但黄宗智等认为,我国农业经营模式转变的主要推动者是农户家庭[4]。严海蓉等认为,自上而下的“资本下乡”、自下而上的“农民分化”以及上下结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同推动了我国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变[5]。第二,农业经营模式转变的影响研究。农业经营模式转变对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本身都带来深远的影响。小部分学者认为,农业经营模式转变有助于我国农业实现规模化和现代化[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有助于再造乡村经营,实现乡村振兴[7]。但大部分学者则认为,农业经营模式转变特别是“资本下乡”不一定会带来农业现代化,反而有可能削弱我国的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国家粮食安全[8],而且“公司吃农户”的现象还会使小农户陷入无产或半无产化的境地[9]。此外,“资本下乡”还会使乡村治理面临更多的挑战[10]。第三,农业经营模式转变受阻原因分析。有学者认为农业经营模式转变不顺的根源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身,主要是因其规模小、实力薄弱以及“动机不纯”[11-12]。部分学者则将之归因于农地制度不合理[13]、农村信贷和保险发展滞后[14]等外部环境因素。而亲小农学者则认为,农户家庭“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15]是使以规模农业为导向的农业经营模式转变之路受阻的主要原因。少部分学者则认为农业经营模式转变遇阻的根本在于遭遇到乡土社会的排斥[16]。
已有研究对于深入理解我国农业经营模式转变、推进农业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大有裨益。尽管如此,但当前具体是哪些基本因素在塑造着我国的农业经营模式,对这一问题已有研究却并未给予答案。即便有一些讨论,也只是基于相关理论展开的预设而已。事实上,农业发展本身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目的论式的演变过程[17];相反,在各种现实因素和力量的相互交织作用下,塑造出的极有可能是一个并不符合理论预设的多元的、具体的农业发展形态。本文以宁夏黄高县蔬菜产业为例探究一个全新的、资本化、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模式是如何在当地兴起、发展和稳固的。笔者于2018年8月和2019年8月两次在宁夏南部黄高县(1)依据学术惯例,本文所涉及的地名、人名和公司名都已做匿名处理。开展实地调研,调研围绕蔬菜产业重点访谈了菜场管理人员、一线工人以及相关部门的政府官员和地方村庄干部。通过这一具体案例分析探究我国农业经营模式的形塑机制。
二、搭台唱戏: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
黄高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属于半干旱地区。全县耕地面积约为147万亩,但只有约1/7的耕地为水浇地,其余均为旱地。2002年,在山东省寿光市的援建下,当地政府开始大力推动本地农户家庭种植蔬菜。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替民致富”、市场销售不畅以及土壤连作障碍等问题,本地农户家庭的小规模蔬菜种植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
面对这一情况,黄高县地方政府开始转变发展策略,意图推动蔬菜产业的转型升级。自2011年开始,当地政府将原本分散投放的农业产业化、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集中投放实施于以C镇为核心的蔬菜产业项目区。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项目区,当地政府也开展了各种服务工作。第一,地方政府主导并强力推动土地流转工作,全县水土条件最好的C镇的土地流转面积短期内就达到4万亩,土地流转工作为蔬菜项目区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第二,政府整合项目资金,加大对项目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土地平整、机井打造、管网铺设和配套的沟渠路网、电力设施等的建设。这些基础性工作极大地改善了项目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满足了规模经营对农业基础设施较高的要求。第三,地方政府还直接给予入区经营者资金补贴和信贷扶持。对于进入项目区连片经营规模超过200亩的经营者,地方政府提供每年每亩400元的补贴;此外,地方政府还成立了产业扶贫投融资公司,通过整合涉农资金和扶贫资金为蔬菜规模经营者提供信贷支持。这些扶持政策极大地缓解了规模经营者的资金压力。从黄高县案例的效果来看,地方政府的介入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当地蔬菜产业的发展。2011年,姚村党支部书记林华率先在C镇的姚村和严村流转1 000亩土地开展蔬菜规模经营。由此,黄高县蔬菜产业的经营模式开始从农户家庭经营向公司、大户规模经营转变。
但转变的过程并没有如地方政府设想的那般顺利。起初林华等经营者仍旧种植西芹、西兰花、娃娃菜等本地蔬菜品种,本地蔬菜规模经营遭遇到了严重的市场滞销问题。2011年蔬菜上市之际,由于行情低迷,林华当年就亏损了70万元。这一打击让林华心灰意冷,直接导致他在2012年歇业一年,也使黄高县刚刚起步的蔬菜规模经营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之后两三年间徘徊不前,直到2014年才开始出现转机。通过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2014年,广东商人王峰和刘良来到黄高县,并带来了菜心这一外地蔬菜品种。由于精通菜心种植且有充足的资金和市场销售渠道保障,广东商人在黄高县种植菜心的第一年就获得了不错的效益。菜心种植的成功,让林华等本地蔬菜规模经营者纷纷跟进,而广东商人为了能够在当地更好地立足,也选择与其展开合作,并给予了他们在菜心生产、市场销售等方面的帮扶。伴随着广东商人与本地规模经营者的合作,黄高县蔬菜产业的转型升级再次启动,蔬菜品种也从原先的本地“杂菜”转变成为以广东菜心为主。截止到2019年底,全县菜心播种面积达9万亩。
从黄高县案例来看,地方政府推动的“资源下乡”以及各类基础性工作无疑为当地蔬菜产业经营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前提条件。面对农业规模经营的高风险,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推动土地流转、提供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工商资本定然不会贸然进入。但如果凭此就判断行政力量是推动我国农业经营模式转变的主导因素,则有失偏颇。行政力量虽能在推动农业经营模式转变的初期发挥重要作用,但之后这种转变能否顺利完成则并不一定会完全如地方政府所愿,其转变过程也未必会一定顺着地方政府设计的路径而演进。如上文所述,起初政府推动的规模经营并没有让黄高县的蔬菜产业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如果不是2014年广东商人的进入,黄高县的蔬菜产业或许仍徘徊不前。广东商人的到来和外来资本的加入不仅加快了黄高县蔬菜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也完全改变了当地蔬菜产业的经营模式。这说明,在农业经营模式转变过程中,行政力量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对于影响农业经营模式转变的其他因素仍需深入探究。
三、市场导向:工商资本日常管理实践
从黄高县蔬菜转业升级实践可以看出,即便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力量成功扶持起了一批所谓的“典型”企业,但是行政力量并不能代替这些“典型”企业进入市场展开经营。换言之,工商资本下乡建立规模农场之后,首先需要处理好自身内部的经营管理问题,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
具体到黄高县,规模农场内部的经营管理问题主要是劳动力问题。相较于主粮作物等“旧农业”,菜-果种植等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型的农场更需处理好劳动力的管理问题[18]。黄高县仅一茬菜心每亩的人工投入就高达1 006元,占到总成本的38.2%。正因如此,菜场经营者直言,“最大的问题,也是最紧要的问题就是劳动力”(L菜场老板,2019-08-17)。“种菜心虽然有优势,但菜心主要是工人的问题”(R菜场老板,2018-08-16)。显然,劳动力的使用和管理问题对菜心产业来说至关重要。那么,菜场需要何种类型的劳动力,又是如何来满足这一需求并实现有效管理的呢?
(一)产业链上的菜心生产
既然“新农业”是一种高度市场化的农业,那么“新农业”生产能否获利,根本上还要取决于市场。为了“取悦”市场、实现获利,经营者必须按照市场的要求进行生产。因此,市场特征就会直接影响到“新农业”经营者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
首先,菜心经营者必须直面波诡云谲的市场行情。从调研来看,每件(15公斤)菜心的生产成本近几年大致稳定,约为86元,但其售价则涨跌不定。行情看涨时,售价可达170~180元/件;而价格低落时只有50~60元,不少菜心经营者感叹经营犹如赌博。幸运的是,菜心的作物特性可以极大地帮助菜心经营者规避市场行情带来的风险。不同于一年一茬的果蔬,菜心是一年多茬。一茬菜心的生长周期约为50天,黄高县每年有7个月(4月初到11月中旬)的生产菜心季节,一般可种植4茬。在菜心行业闯荡多年、深谙其道的王峰说,“尽管菜心这个价格是波动的,(但是)你每天只要保持这个量出去,就不会亏”(L菜场老板,2019-08-17)。事实上,在将近半年的出菜期中,只要茬口安排得当、管理合理,保证出菜量的稳定,那么价格的波峰就能填补波谷,从而实现盈利。尽管如此,要实现最终的盈利还需满足两个条件:(1)经营者需拥有雄厚的资金可以扛过价格低谷期。没有雄厚的资金,一旦碰到价格低谷期,正常的生产经营便难以维系。(2)需要有一支数量充足稳定的劳动力队伍来确保每天稳定的出菜量。因为“没有一定的劳动力,收的菜肯定不多,菜的浪费肯定也比较严重”(F菜场经理,2018-08-01)。因此,波诡云谲的市场行情对菜心经营者的生产经营提出了两个要求,即资金和劳动力数量。
其次,菜心经营者还要善于面对买方主导的市场结构[19]。事实上,即便菜心经营者生产再多的菜心也不行,因为最终还是要将菜心销售出去才能盈利,而菜心能否销售出去以及售价高低的关键在于其品质是否符合采购商的要求。“我是客商,你这个菜怎么样,我会挑的,所以种的不好也不行。客商肯定要挑好的……(现在)竞争比较激烈。所以这个质量一定要保证好。质量把握好,我们卖的也轻松点嘛”(J菜场老板儿子,2019-08-09)。在菜心产业链上采购商占据着更为主导的地位,采购商对菜心的品质要求会直接影响菜场的生产与劳动力。
萨尔维娅指出,“采购商至少在四个层面可以对生产者施加影响,包括生产计划、品质、运输时间以及方法”[20]。作为一种高档蔬菜,采购商对菜心在大小、花叶、长短、摆放和新鲜度等各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首先,采购商会将菜心按照大小、粗细区分为三个等级,等级不同、价格有别。因此,为了确保菜心品质符合采购商的要求,菜场会制定严格的工作标准。其次,在采收环节上,菜心必须在适宜期(齐口花期)采收,提前和延迟采收都不允许,下雨天也不允许采收。工人采收菜心时必须区分大中小不同等级,且要确保每株菜心植株切口平整、虫口少、无发黄发蔫、无机械损伤、无泥土、无病斑,最后手工整齐摆放进筐。为了防止压坏菜心,每一筐菜心重量不得超过9公斤。再次,菜心入筐之后,需覆盖上一层保湿布以确保菜心的新鲜度。同样是为了确保菜心的新鲜,菜心需要连夜在冷库中打包封箱,并由冷链货车运走。有了这些程序保障,一般在48小时之内黄高县的菜心就可以出现在广东市场上。因此,采购商对菜心的品质要求直接影响了菜场对劳动力的质量要求。例如,在最为重要的采收环节,劳动力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能以及细心、耐心的工作态度;在冷库打包封箱环节,劳动力必须能够适应不固定的工作时间。
总之,菜心经营者不仅要直面变化多端的市场行情,还要应对买方主导的市场结构,而市场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又会直接影响到菜场经营者的日常生产管理。一旦市场行情对菜场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提出了要求,那么买方主导的市场结构则会对菜场雇佣的劳动力提出质量要求。这种产业链的结构性压力,使得菜场必须拥有一支数量稳定、技能可靠、素质优良、适应不固定工作时间、能够随叫随到的劳动力队伍。如果没有这样一支符合要求的劳动力队伍,菜场这种资本化、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模式显然也就难以为继。那么,菜场从哪里招募这样一支劳动力队伍呢?
(二)招募外地劳动力
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菜场理所当然的做法是雇佣当地村民来满足自身的用工需求。但调查过程中菜场管理者直言,“我们就不喜欢用本地人”(F菜场经理,2018-08-01)。因为菜场管理者认为本地劳动力并不符合菜场的用工要求。
首先,本地劳动力数量不能满足菜场需求。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黄高县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在村庄的劳动力数量不能满足菜场密集的用工需求。“本地人总共才几个,这么大一片场子……那几个人不够。这边1 000亩地,咱们村庄总共二三十个人,7个组才来30个人,你说30个人怎么搞?”(J菜场本地合伙人,2019-08-07)其次,本地劳动力质量不能满足菜场的要求。采购商对菜心的高品质要求使得工人不仅要有一定的采收技术,而且还要能投入大量的劳动时间。但是,一方面本地劳动力缺乏相应的技术。“我们也试着用本地人去种去收,不行。种是好种,但最重要的是收(菜心),他/她们(本地人)没那个技术”(F菜场经理,2018-08-01)。本地劳动力自己也承认这一点,“那个菜难割死了,大个的不要,太小的也不要,就是那个刚好的要,谁能那么准呢?”(J菜场本地工人,2019-08-16)。另一方面,本地劳动力也无法保证能够投入大量的劳动时间。不同于外地劳动力,本地劳动力的家庭生活、社会关系都嵌入在当地,导致本地劳动力的生产生活时间与菜场要求的劳动时间有较大偏差。“每个家庭都是农村家庭,都有事的,她家种了小麦、玉米这些东西。她要去挖马铃薯,就不来这里了。还有养牛的、养羊的,还有我家媳妇生小孩了,要照顾下。这些都有的”(L菜场老板,2019-08-17)。在这种时间冲突下,本地劳动力就会时不时缺席菜场的劳动,直接影响菜场的生产进度和计划安排。
与之相反,外地劳动力却非常符合菜场的用工要求。首先,外地劳动力的数量能够满足菜场的需求。这一需求的满足得益于外地劳动力独特的招募模式。调查得知,菜场并不会直接招募外地劳动力,而主要是假手于一个中间人——总管。总管主要依靠亲戚、朋友、邻里、乡亲等先赋性社会关系为菜场招募劳动力,一个总管可以带来一支100~200人的劳动力队伍。其次,外地劳动力的质量也能满足菜场的要求。就劳动技能而言,这些外地劳动力从事菜心生产多年,无论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收技能上都很娴熟。即便有新加入的人员,在亲戚、朋友、邻里等人带领下,也可以很快掌握这些技能。就劳动时间而言,外地劳动力都是“以场为家”生活在菜场提供的工人生活区,整个日常都是围绕着菜场的工作打转,可以满足菜场长时段、不固定的劳动时间要求。而更为重要的是,外地劳动力还易于管理。因为工人是由总管招募的,所以其日常管理也主要是依靠总管。和招募一样,总管对工人的管理更多也是依靠先赋性的社会关系。所以对于菜场主来说,只需通过总管等少数管理人员,就可凭借其与外地劳动力之间的先赋性社会关系,实现对众多外地劳动力的有效管理。
四、入乡随俗:乡土社会中的调适融合
显然,按照市场经营的逻辑,菜场最好是雇佣外地劳动力而弃用不符合要求的本地劳动力。事实上黄高县的菜场也确实是招募了大批外地劳动力,但与此同时,菜场也并未放弃雇佣本地劳动力。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于黄高县菜场仍旧雇佣本地劳动力的问题,农业经济学者可能会将之归因于外地劳动力的短缺,这种经济学的解释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调查发现,只要菜场老板愿意支付1 000~2 000元不等的“买人费”,总管总能找来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所以,问题的根本不是外地劳动力的短缺。细究发现,这一问题的根源还在于菜场所处的社会环境。陈锡文指出,“传统国家与新大陆国家的农业和农村,最大的区别其实不在于农地经营的规模而在于农村的社会形态——有无村庄的存在”[21]。这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涵:第一,我国的国情使得农业企业要实现规模经营就必须要落地到乡村之中,并从数量众多的农民家庭手中流转土地。第二,“乡土社会有着极为鲜明的特征,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人有着特殊的行动伦理”[22],这使得农业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多少总要与那些秉持特定行为逻辑的农民打交道。因此,对于下乡农业企业来说,其日常经营不仅会受制于市场经营的逻辑,而且还需顾及到乡土社会的逻辑。正如一位菜场经营者所言,“你去那里做事,肯定还要把地头拜好”(L菜场老板,2019-08-19)。而正是后一种逻辑,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黄高县菜场的日常管理实践。
(一)遭遇乡土社会的菜场
众多研究揭示出乡土社会中“内外有别”的乡土逻辑会严重影响外来资本化农场的生产经营[17,23-24],这种“内外有别”的乡土逻辑直接影响黄高县菜心企业的生产经营。下面以黄高县“本地人”和“外地人”菜场的情况来举例说明。
J菜场、L菜场是由广东商人经营的,与全国大部分下乡的资本一样,这两个菜心企业在来到黄高县之前与当地村庄和村民并没有任何关系,毫无疑问,他们是进入村庄的“陌生人”。在“内外有别”的乡土逻辑下,村民不但不信任这两个菜场,甚至对其抱有敌意。再加上地方政府强制村民流转土地和菜场生产影响村民生产用水等问题,更是激发了村民和两个菜场的对立。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村民不但要求菜场按时缴纳土地租金,而且还不愿意签订长期合同。“刘老板那块地是B村的,B村的村民有点小意见,就只愿意签3年……土地是个不稳定的因素。这边如果村民一闹,场房投资几百万下来就没用了”(L菜场老板,2019-08-19)。此外,村民还会去菜场“偷菜”。“以前刚来的时候,村民是想摘就摘”(J菜场老板儿子,2019-08-09)。“(偷菜)多着呢,他们(本地村民)不吃菜心,但是把整棵菜都拔走,当卷心菜用了”(L菜场老板,2019-08-19)。最为严重的还是劳动力的问题。流转土地一部分村民失去了工作机会,他们就要求流转他们土地的菜场提供工作机会。“第二年工人(指本地村民)就要求做事了,不安排给他们工作,他们就过来闹事”(L菜场老板,2019-08-17)。然而,即便是雇佣本地村民来菜场干活,但“外地人”菜场还是遭遇到了本地村民的各种“欺负”和“排斥”。第一年L菜场雇佣本地村民干活,由于村民“磨洋工”,菜场效率低下。“第一年效率不行……那些本地人真的是拿那个蛇皮袋往菜地里一放就睡觉了”(L菜场老板,2019-08-17)。为此,L菜场还专门雇佣了监工,监督本地村民的劳动。不仅如此,本地村民还极容易团结一致、共同对外。L菜场老板就遭遇过本地村民的威胁。“本地人特别团结,前两年我开除了四五个(干活的村民),他们一下子就把我围住了。七八十个人把我围住了,说要立刻结账、立刻走人……还威胁我。完了之后,他们不准我收那个菜”(L菜场老板,2019-08-17)。“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嘛,你到哪里,肯定会有点被当地人欺负的嘛”(J菜场老板儿子,2019-08-09)。
与之相反,黄高县C镇副镇长、姚村党委书记林华经营的R菜场则是另一番景象。作为一个“本地人”,无论是本村人还是附近村庄的人,不仅对林华个人的经济实力知根知底,甚至可能还沾亲带故。也正因如此,所以林华在流转土地时,几乎没有遇到阻力。不要说“偷菜”,即便在土地租金上,当地农户对他也是极为放心的。“有一部分人都不在乎这个租金的问题,主要是要把这个田头守好,不是要多少钱的问题”(R菜场老板,2018-08-16)。相对于L菜场的雇工难题,R菜场则较少受到困扰。“本地工人是自己找过来的,你经常干的嘛”(R菜场经理,2019-08-14)。实际上,林华在菜场用工上还是遵循着“乡情原则”,他主要给土地流出的村民和贫困户提供在菜场的就业机会。“土地流转之后,(村民)就近可以务工……最少的人能挣个1.5万,还有两三万不等……这就说到脱贫了,只要我有劳动力,一家一个人挣个两三万……脱贫不是问题”(R菜场老板,2018-08-16)。目前,在R菜场务工的本地村民达到150人左右。相较于“外来者”L菜场在劳动监督上面临的难题,R菜场的劳动监督成本则是较低的。
总而言之,相较于“本地人”菜场,“外地人”菜场在用地、用水、用工等日常经营过程中会遭遇到农户的各种“欺负”和“排斥”,这种“欺负”和“排斥”背后正是农户“内外有别”的行动逻辑在发挥着作用。尽管外来的工商资本可以借助行政力量、甚至黑恶势力暂时压制农户的这种“排斥”,但这不但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工商资本与当地农户的关系,反而会使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对立。因此,在无法改变乡土逻辑的情况下,如何调适自己的生产经营实践并使之适应于乡土逻辑、处理好与当地农户的关系,对于作为“外来者”的工商资本来说也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二)“土客”结合的用工制度
按照前述逻辑,如果只雇佣外地劳动力,那么菜场就有可能变成乡土社会中的一块“飞地”而遭受到本地村民的“欺负”和“排斥”。反之,如果菜场顾及到乡土逻辑而大量雇佣本地村民,虽可确保菜场在当地经营的顺利,但结果是菜场有可能因为生产不出符合市场要求的菜心而导致经营失败。因此,处理好用工问题上的“两难”,对于菜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事实上,要处理好“两难”,最为直接的解决办法是“土客”结合——菜场既招募外地劳动力,也招募本地劳动力。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菜场管理者该如何来安排劳动力的岗位才能确保菜场既能在乡土社会中顺利经营,又能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菜心呢?
黄高县菜场采取的解决办法就是“因岗选人,人岗相适”。要做到“因岗选人”,前提是要明确整个菜心生产过程中有哪些岗位,为此,菜场对原本连续的农业生产过程进行了拆分。整个菜心生产流程被细分为前期准备(整地、拉沟、撒底肥等)、播种栽苗、日常管理(追肥、打药、洒水、除草等)、采收、入库检验、打包发货等环节。在菜场管理人员的统筹协调下,各个生产环节的工人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像在工厂流水线上一样有条不紊地将菜心“组装”出来。各个生产环节上的岗位要求不同,因而对所需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也就各不相同。具体来说,菜心采收环节不仅用工需求量最大,而且对劳动者有较高的技能要求,这主要是因为机械化的缺失、采收时间的紧迫和采购商的高标准要求;入库检验和打包发货环节,因为涉及到菜心保鲜和及时运输问题,所以工作时间上最不固定;日常管理环节则因为涉及到机械化操作和一定的专业知识,所以对劳动力也有一定技能要求;唯独前期准备环节和栽苗环节的岗位要求相对来说最为简单,技能要求也低,劳动力的可替换性较高。
在清楚岗位要求后,管理者在准确了解各类劳动力各自特征属性的基础上,将其恰当地安排到相应的工作岗位,确保“人岗相适”。对此,黄高县菜场管理者针对本地劳动力和外地劳动力特点安排用工。“比如采收这个行业,完全是本地工做不来的……下雨天去割菜,本地人就不去,你给他多少钱他都不去。这个外地工人,只要我明天要干啥,计划做好,必须得给我去,披着雨衣都得给我出去干,他有这个好处……所以,本地工人和外地工人就没法比。贵州、四川的工人你别看个头小小的,但是干活就可以。他们干重活也干不了,但干这些需要耐心的活,他们干得很好”(R菜场老板,2018-08-16)。“本地妇女就只会栽菜和耙地,她们不学(采收),说慢得很,(因为)我们要手工排的嘛,她们不学。就说,你们给我条塑料绳子,我给你们扎成一把……要是雇当地人,我们得贴死,还不如不种”(J菜场本地合伙人,2019-08-07)。基于上述认识和考虑,在相对重要的、岗位要求高的日常管理、采收、入库检验和打包发货环节上,黄高县的菜场管理者全部安排的是外地劳动力。从调查来看,只要上述环节安排外地劳动力,那么菜场就可以确保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菜心。而在较为次要的、岗位要求低的前期准备环节和播种、栽苗环节,因为工资待遇较低,外地劳动力不愿意干,菜场管理者就“顺水推舟”将这些工作全部安排给本地劳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菜场还对本地和外地劳动力采取了不同的工资制度。对于外地劳动力,菜场更多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比如,最为重要的采收环节就是以每斤合格的菜心0.6元来计酬,目的就是为了激发外地劳动力高强度地工作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菜心。而对于本地劳动力,菜场更多采用的是计时工资制,当地通行标准是9~10元/小时,干几个小时给几个小时的工资。这样的安排,一则是为了节省成本;二则更是为了契合本地劳动力的时间安排。“要是家里有事就可以不来,半天班也行”(J菜场本地工人,2019-08-11)。“哪个不行,让他/她先休息一两天,换别人来,轮着来。他们家里有事,可以处理家务这些事情”(L菜场老板,2019-08-17)。
总之,通过对菜心生产环节的“拆分”并将本地劳动力和外地劳动力分别安排在不同的生产环节,黄高县菜场创造性地构建出了一套“土客”结合的用工制度,这一用工制度使得菜心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巧妙地兼顾了市场逻辑和乡土逻辑。通过使用外地劳动力并将其安排到较为重要的生产环节,菜场可以顺应市场逻辑,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菜心;通过雇佣本地劳动力并将其安排到较为次要的生产环节,菜场可以在不影响菜心生产的前提下,顾及到乡土逻辑并较好地处理与当地农户的关系。现今,黄高县菜场从附近村庄雇佣了大约500多名本地劳动力,从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雇佣了约2 000名外地劳动力。凭借“土客”结合的用工制度,黄高县菜场的生产经营一直较为顺利,出产的菜心也深受市场的欢迎。这一切表明,以菜场为代表的资本化、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已经顺利地建立和发展起来,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黄高县的蔬菜产业顺利实现了转型升级。
五、结论及讨论
回顾黄高县蔬菜产业发展历程,自2011年当地政府开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当地的蔬菜产业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发展,不仅实现了品种的转变,更实现了经营模式的转变。从具体的发展历程来看,黄高县蔬菜产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并非是单一因素主导的,而是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行政力量所投入的大量资源、所做的基础性工作构成了当地蔬菜产业经营模式转变的前提条件。而这种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主要还在于作为经营者的菜心企业能够恰当地调整自身的生产管理制度。作为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产业,市场逻辑要求菜心企业必须雇佣外地劳动力;但菜心企业落地乡土社会的现状也使其必须在用工问题上顾及到乡土逻辑。所以,在市场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作用下,菜心企业通过分割生产环节,创造性地建构出了“土客”结合的用工制度,从而确保了自身的顺利运营。总之,立足于地方政府提供的发展条件,菜心企业通过调适自身生产管理制度使之契合于市场逻辑和乡土逻辑,从而实现了自身经营的成功。而伴随着菜心企业经营的成功,资本化、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得以建立,黄高县的蔬菜产业也随之顺利实现了转型发展。
尽管案例本身有其特殊性,但其背后揭示出的影响因素却存有一般性,本文的分析揭示出,行政、资本和乡土社会是形塑我国农业经营模式最为基本和重要的三个因素。具体而言,在农业高度市场化的情况下,资本对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势必产生极大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资本”不仅包括农业生产环节中的“农业经营资本”,还包括产业链上游的“农业投入资本”和下游的“农业食品资本”。实际上,在当前农业产业化发展态势下,“农业投入资本”和“农业食品资本”对于农业生产环节的生产结构、用工及管理问题都将发挥重要影响。正因如此,美国农业社会学者弗里兰德等人强调,农业社会学应该关注商品的整个生产、加工和分配环节,而不仅仅只是种植环节。商品的仓储、处理、加工、运输、推销、促销以及销售都应包括在分析框架内[25]。正是基于对农业全产业链的控制,可以说,资本在我国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但资本因素这种关键作用的发挥,也绝不能离开行政力量和乡土社会两个因素的支持。首先,通过土地流转的推动、土地制度的修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农业技术的推广等活动,行政力量显著地影响着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而且政府自身的行动逻辑、目标也势必会影响到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就此就断定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完全或者主要是由行政力量所形塑,则有失偏颇。事实上,行政力量更多发挥的还是一个激发转变的引导作用和提供条件的保障作用。在具体的经营实践、应对市场方面,行政力量并不能代替资本发挥作用。其次,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农业是“落地”在乡土社会之中的,因而整个农业经营模式转变过程也就必然受到乡土社会中结构、文化等力量的影响。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及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建立必须立足于乡土社会这一“社会基础”之上。因为农业经营模式转变不单只是一种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外来的、新的文化理念与乡土社会中固有文化理念相碰撞的过程。如果下乡的工商资本处理不好与乡土社会中固有文化理念的调适问题,那么农业经营模式转变和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建立必然困难重重,甚至遭遇失败。总之,行政、资本和乡土社会三个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形塑了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及未来的发展形态。
相较于国外,我国的农业社会学无论是在问题意识、研究范式还是在学科体系方面都处于尚不明晰的状态,因而展开的研究也大都属于案例研究。不可否认,无论是对于问题意识的明晰,还是研究范式的构建,案例研究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但问题是,案例研究的具体性也会带来其解释上的局限性。更有甚者,一旦过度陷入案例研究,所做的研究很有可能只是为某一理论学派思想提供经验注脚而已,并且还会由此产生各种无谓的学术争论,显然,这不仅会阻碍理论的创新和讨论的深化,甚至还会限制我国农业社会学学科本身的进步和发展。有鉴于此,本文目的就是在具体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理论的思考和讨论的提升。尽管本文探究尚存诸多不足,但或许代表了我国农业社会学研究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