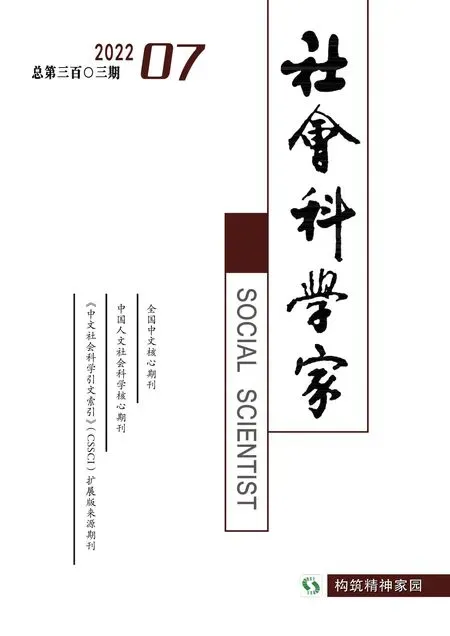舞蹈文化中的历史叙事及其价值体现
——以苗疆走廊的汉苗舞蹈文化为例
满梦翎
(1.北部湾大学人文学院,广西 钦州 535011;2.宣素那他皇家大学艺术学院,泰国 曼谷 10900)
一、舞蹈文化的研究现状与新的视角
舞蹈文化作为动态语言具有“长于表情、难于叙事”的特点,大多数的中国传统舞蹈文化善于表达喜悦、痛苦、欢庆、悲伤的情绪,因此对舞蹈文化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分析其情感表现力以及如何增强其情感表现力上,而很少研究舞蹈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情节。舞蹈文化又是一种难以保存的动态文化,每一种舞蹈形态即使通过祖辈之间的亲相授受来代代相传,也难以百分之百完整复制和保留下来,而教学相习的过程更是不断变异的过程。舞蹈文化活态传承的特点使得舞蹈文化的研究难以开展。在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致力于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的保存与传承,另一部分学者则致力于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不管是侧重哪种研究,大部分学者对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的本体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不同的民族舞蹈文化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排他性,研究民族舞蹈文化就是研究其独特性。因此,很多学者的研究是围绕某个舞蹈文化的某一特性来展开,或者围绕几个舞蹈文化的不同特性来开展比较研究。事实上,专门研究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学者很多,对不同民族舞蹈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也有一些,但研究多种舞蹈文化之间交融性的学者却还不多见。特别是对于苗族舞蹈文化的研究,由于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也是一个无文字的民族,学者们大多致力于研究苗族舞蹈文化的特殊性,如学者杨鹃国就认为苗族舞蹈与巫教文化关系密切,强调了苗族舞蹈文化的特殊性与排他性。
随着苗疆走廊的开辟,汉族人民逐渐进入苗疆地区,汉文化给苗族舞蹈文化带来了冲击,苗族舞蹈文化的特性也影响着汉族舞蹈在西南地区的发展。苗族人民长期以来使用舞蹈、图腾记录着民族迁徙中发生的故事,从而感怀先辈的伟大,激励苗族人民奋勇向前,创造更安稳美满的生活。汉苗民族相互交往的历史故事也随着汉苗舞蹈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流传至今。苗疆走廊地区的汉苗民族运用舞蹈手段对民族历史、传说进行了记录与叙述,将汉苗舞蹈的叙事性与文化的交融性结合在一起,透过汉苗舞蹈文化的叙事见证了汉苗民族文化的交融。
汉苗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打破了民族文化的单一性,使两个民族的文化得以融合,且共同谱写了同一段历史,这也要求我们在研究汉苗舞蹈文化时要突破单一民族舞蹈文化研究的固有思维,必须用联系的眼光来观察、发现舞蹈文化中潜藏的交融性以及二者间的文化交流史。同时,我们的研究方法不能够局限于单一的舞蹈艺术分析方法,而要综合运用人类社会学和文化生态学等研究方法,来分析论证不同文化间的涵化现象以及现存汉苗民族舞蹈文化的共生性和交融性。通过分析苗疆走廊地区汉苗民族舞蹈文化的交融性与叙事性,我们还可以发现汉苗舞蹈文化中新的类别划分,彻底打破固有的单一民族舞蹈文化的特殊性和排他性,从而为民族舞蹈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舞蹈文化中历史叙事的理论建构
1.程式化的历史叙事
固定的动作程式搭配上舞蹈表演者的随性发挥是大多数中国传统叙事性舞蹈的呈现方式。程式化就是对阶段性表演内容的固定要求,便于观众在无声的表演中去感受舞蹈传达的意义。“戏”的程式性是舞蹈叙事的重要环节。赵太侔先生提出戏曲具有程式之上的程式,强调程式化在戏曲叙事中的核心地位。[1]戏曲是从纯舞蹈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周代的“戏礼”就是通过礼仪性乐舞来表达简易的叙事内容,汉代“戏象”的“东海黄公”角抵戏中就出现了戏剧化的舞蹈人物形象,唐代“戏弄”在叙事性舞蹈上增加了喜剧性的情节,丰富了叙事色彩,也使得舞蹈向“唱、念、做、打”的戏曲发展,在“戏”的不断强化和“舞”的弱化中,形成了现在的戏曲艺术。而在数千年的叙事性演变中,舞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戏”的表演本体,程式化叙事体系在舞蹈发展当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民族舞蹈中的程式性是民族舞表演的内在规则,是民族精神的寄托,具备一定的功能性,是程式性与即兴共存的状态。民族舞蹈的表演具有一定的功能性,或祭祀祭祖、或谈情说爱、或信仰崇拜、或鼓舞士气,通过舞蹈的程式性表演更易于表达出祖先的功勋、战争的残酷、情爱的挑逗,使得舞蹈在族群的流传中发挥更为准确且长久的功能性,并在祖祖辈辈中代代相传。因此,程式性是民族舞蹈叙事的重要工具。学者杨鹃国认为苗族舞蹈是在较为严格的规范中展开自如随心的表演和创作。[2]苗族舞蹈的表演具有一定的程式性,讲究既定的场地、时间、服饰、道具,什么人跳什么舞,什么人不能跳什么舞,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而这些规定也是苗族舞蹈叙事的重要部分,会对观赏者的解读具有重要影响。杨鹃国先生把具有严谨程式的舞蹈过程以及由这个过程构成的舞蹈形象称作“戴着镣铐跳舞”,是苗族舞蹈程式化叙事的重要表现。
2.感怀式的历史叙事
关于舞蹈的起源有着许多的说法,例如劳动说、模拟说、生殖崇拜说等等,但无论何种说法都可以看出舞蹈是对环境、思想、情感的反映。中国舞蹈文化中存在许多怀念先辈、纪念历史苦难的舞蹈,这些舞蹈通过情感的寄托从而达到叙述历史的作用,并且传达出一个族群面对历史的精神和态度。我国周代开启了“礼乐治国”的策略,通过乐舞叙述前朝的故事,表达对前人的感怀,从而教化民众向善守礼。六大舞则是“制礼作乐”的典型代表。例如感怀“黄帝”的舞蹈《云门》叙述了“大施天下道而行之”的故事;感怀“夏禹”的舞蹈《大夏》叙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由此可见,我国自古便有以感怀先人的形式,叙述先人事迹,从而教化民众的叙事性舞蹈。
在苗族舞蹈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苗族对巫鬼的崇拜以及万物有灵的信仰,苗族人民认为祖先逝去后会化为鬼神回到亲人的身边,因此产生许多怀念祖先的叙事舞蹈。苗族人民对自己的祖先非常虔诚,至今还保留着祖先崇拜的风俗。贵州地区的苗族,最初崇拜枫树与蝴蝶,而后变为崇拜苗族的祖先之一“姜央”,并把“姜央”称为蝴蝶妈妈。苗族感怀式的舞蹈文化在苗族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苗族感怀式的舞蹈文化随着苗族社会发展不断濡化变迁,并与苗族文明息息相关。它不仅是信仰祭祀的关键环节,还是记录苗族历史的史诗性文化。当今苗族丧葬仪式舞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白天请道士做法事,将灵魂送往西天,而晚上用苗族的传统仪式舞蹈将死者的灵魂送向祖先故土东方这样的有趣现象。通过这些舞蹈叙事,反映出苗族舞蹈文化受到了道教文化影响,叙述了不同宗教背景下对祖先的怀念,印证了苗疆走廊的开辟为苗族社会带来了新鲜的文化基因,儒家文化、佛道文化等中原文化融入了苗族信仰和原始宗教当中,并呈现出缤纷多彩的文化生活图景。
3.隐喻性的历史叙事
以一个动作短剧代表一种情节内容,通过这种暗藏隐喻的“代号”动作传达舞蹈想要表达的内容,即可以称为隐喻性舞蹈叙事。在以隐喻性的舞蹈动作进行民族历史叙事时,族群内部因共同的文化认识达到对舞蹈动作一致的内容理解,使得表演者与观赏者在不断重复的表演中加深民族共同文化认识,进而加强族群对民族身份的肯定。
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身体人类学的研究中提出过“两个身体”的概念,即物理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舞蹈的隐喻性叙事是将观念与人、事件与技术贯通起来,将人身体的物理特性与社会特性联系在一起。隐喻性舞蹈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它作为社会身体的功能性,也可以看到它作为物理身体的技术性。J.布莱金(John Blacking)在此基础上将身体与文化联系在一起,提出精神上的文化塑造着物理上的身体,且社会身体的隐喻,意味着社会是一个动力系统,在那里身体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也是一种生物现象,是进化过程的产物。[3]
人们在身体隐喻文化上的共识是达成民族文化共同意识的基础。例如含胸正步为汉族舞蹈体态,沉肩后仰为蒙古族舞蹈体态,松弛、前倾、一边顺为藏族舞蹈体态等等,都是中国人在身体隐喻文化上的共识。在单一民族内部也有着各民族族群的身体隐喻文化共识。例如苗族迁徙舞中的探步:身体前倾,双腿微屈,脚尖向前旁三个方向轻探,后迈步向前,换脚前探。这个简单的步伐,反映出苗族人民在压迫中寻找出路,为躲避战争踟蹰前行的场面,动作虽简单却承载着苗族迁徙的历史,是对历史事件的隐喻,也是苗族族群间的动作共识。扬·阿斯曼(Jan Assann)认为,在无文字社会的时代,个体要参与族群的文化记忆,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场,在节日、仪式中建立身份认同。[4]因此,族群舞蹈与舞蹈文化中的隐喻性叙事是建立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式之一。
三、苗疆走廊上汉苗舞蹈文化的历史叙事表征
苗疆走廊是在元明清时期由国家开辟的一条官道,是当时的中央王朝为了“开边”以及加强对西南疆域的治理而开辟的一条从湘西经贵州的入滇之路。苗疆走廊中的“苗疆”并非自古存在,而是西南各民族在不断迁徙、交流、交融过程中在西南地区形成的一种历史文化区域。苗疆走廊上汉苗舞蹈文化中的历史叙事主要是指表现西南地区苗族与汉族共有历史故事的舞蹈文化,这些文化体现了西南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
1.蚩尤戏中的历史叙事——汉苗历史人物的共同记忆
蚩尤崇拜是苗疆走廊上表达汉族与苗族共有历史的舞蹈文化,且表演内容具有汉苗交流的共同历史记忆。蚩尤崇拜是汉苗自古共有的舞蹈文化之一,分布于苗族湘西地区与汉族地区的山西太原等地,是汉苗舞蹈交融最为古老的案例,既属于苗族蚩尤崇拜舞蹈文化的濡化,也属于苗文化在汉文化地区的传承。
汉苗民族的蚩尤戏表演是通过对蚩尤形象的模拟表达对祖先的感怀之情,从而达到对汉苗历史的叙事功能。蚩尤为苗族祖先,是苗族传说中的民族英雄,在各苗族地区皆存在对蚩尤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祭祀活动。然而在中原汉族地区的山西太原,自先秦时代便以表演蚩尤戏的戏曲舞蹈来祭祀蚩尤,同时在中原朝廷的军祭中以战神之礼祭祀蚩尤。蚩尤崇拜舞蹈文化是汉苗民族文化交流留存至今的历史印证。对于蚩尤崇拜的汉苗舞蹈文化,我们可以从三个视角来分析:一是古汉族视角,二是古苗族视角,三是现代学术视角。在古汉族地区的文献记载中,有关蚩尤最为代表性的故事便是“逐鹿之战”。在上古时期,蚩尤与黄帝、炎帝战于逐鹿,蚩尤败,随即蚩尤一脉退出中原之争,上古三足鼎立的局面破碎,黄帝执掌中原。在《管子》的文献中写道“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文中指出黄帝在蚩尤死后,封闭了蚩尤的死讯,昭告天下,称将蚩尤纳入麾下,以震慑天下,由此可以看出蚩尤在当时的军事影响力之大。秦朝时期,秦始皇将蚩尤奉为兵主,在东游祭八神时位列第三。[5]直至宋朝,蒙古进中原前,蚩尤一直都是朝廷整军出师前祭祀的战神,军中对蚩尤的武力抱有极高的崇敬。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记载:“有蚩尤神,俗云:人首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提掘得髑髅如铜铁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6]可见早在汉代中原地区就有对蚩尤进行模拟的舞蹈,并流传至今。在古苗族地区,蚩尤一直被奉为祖先,受到苗族人民最高崇敬,但没有系统的文献记录,信息来源多依靠于苗族古乐舞。在黔西北的“大迁徙舞”中叙述了苗族人民从“逐鹿之战”蚩尤战败后的迁徙史,以及在湘西苗族地区至今流传着祭祀蚩尤的蚩尤戏。在现今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提出蚩尤在东部方言中的苗族群体中被称为“剖尤”;在中部方言中的苗族群体中被称为“榜香尤”;在川黔滇方言中的文山一带的苗族族群中被称为“格蚩尤老”“之尤”和“杨鲁”。[7]因此,我们认为与此类称呼有关的舞蹈皆可列入蚩尤崇拜的舞蹈文化行列。虽然各地对蚩尤的称呼有所不同,但是蚩尤所留下的文化精神一直存留在各个苗族群体中。例如牛图腾、崇祖、尚巫等。而现今学术界认为山西蚩尤戏“是一种舞蹈性很强的仪式性戏剧”,强调了蚩尤戏的舞蹈性、历史性、祭祀性与戏剧性,认为蚩尤戏符合“演员当着观众演故事”的戏剧定义[8]。而其中所说的戏剧内容则是黄帝与蚩尤的故事,是汉苗民族共同传承的历史传说。[5]
由此可见,无论是汉族还是苗族对蚩尤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崇拜心理,蚩尤文化贯穿了汉苗民族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乐舞的形式保留至今,呈现出汉苗民族共同的蚩尤尚武精神、蚩尤历史传说、蚩尤崇牛图腾,是汉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佐证。
2.芦笙舞中的历史叙事——汉苗历史交流的一种表达
苗疆走廊上苗族部分芦笙舞是表达汉族与苗族共有历史的舞蹈文化,且表演内容具有汉苗交流的共同历史故事,是以苗族叙述苗族历史的角度形成的乐舞文化,其中很多片段涉及汉苗战争的历史,是汉苗舞蹈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其中以十二套古代芦笙组舞与大迁徙舞最具代表性。十二套古代芦笙组舞流传至今已经很难再完整复现了,其原因之一是可以表演的老艺人年事已高,而该舞蹈需要的技艺要求较高,体力、能力上已经难以有人将完整的组舞表现出来。另一个原因则是组舞所表现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不合时宜了。在组舞中记录了汉苗之间的战争与反抗,主要记录在《出征曲》与《破阵曲》等与战争有关的舞蹈中,在当今汉苗和谐杂居、汉苗民族友好交往的社会环境下,已经不适宜再演出这部分内容了。
在苗族人民“千年跳一舞,一舞跳千年”的芦笙舞表演当中,程式化表达相对强化,情绪化表现相对弱化,使得乐舞叙事条理清晰,形成了存贮汉苗历史的印记。“十二套古代芦笙组舞”主要流传于昆明市安宁县的苗族村寨中,正套组舞一共包括十二个部分,每个部分都记录了苗族人民迁徙中所遇到的事件或苗族人民的心愿与精神。这套组舞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在吹奏芦笙的同时表演相应的歌和舞,其表现内容主要是从苗族人民自我的角度表达苗族历史,表达苗族人民所经历的战斗、迁徙过程,表达苗族人民对和平幸福生活的追求。苗族是一个无文字民族,这使得他们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主要途径就是口头文学和歌舞艺术,他们将历史化作诗歌、歌词、舞步世代相传,流传至今。从历史时期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十二套古代芦笙组舞分为庆悦、战争、流亡三个阶段。第一套《探路曲》与第二套《祝愿舞曲》主要反映了苗族历史中较为繁盛的阶段。通过屈腿前探的舞蹈动作,表现苗族人民跋山涉水、徒步迁徙,千里迢迢不辞劳苦顽强地探寻美好家园,寻求安顿之地的情境。苗族先民经历了与大自然拼搏的艰难历程,探寻到了适合居住的好地方,便开始围圈而舞,喜悦祈福。这两套舞段是最为欢喜明朗的舞段,因此归为庆悦阶段。第三套《出征曲》、第四套《群舞曲》、第五套《邀请舞曲》、第六套《团圆舞曲》、第七套《敬酒舞曲》、第八套《盼鸡鸣曲》、第九套《破阵曲》都反映了苗族人民战乱不断的阶段,多以武舞动作表现战斗场面的舞蹈,是十二套芦笙组舞的战争阶段。在这一套舞段中主要表现了沉浸在喜悦中的苗族人民突然遭到外敌入侵,即将出征的转折情形。出征归来,苗族人民载歌载舞,重新建立家园,但是苗族首领一度贪图享受,麻痹大意,致使再次遭受外来侵袭,战事再次告急,战况从东、西、南、北传来,苗族人民重拿武器,饮鸡血酒,立下盟誓,发出苗族族群的战斗令,组织苗民斗争和撤离。战争焦灼,战况不利,苗家跳起盼鸡鸣曲组织更换首领,一首破阵曲,激起苗族人民的战斗激情。第三阶段的流亡主要是由第十套《鸡鸣舞曲》、第十一套《天明曲》与第十二套《结亲舞曲》进行演绎。主要表现出苗族人民面对战败的结局,积极进行内部整改,任命新的首领,带领苗族人民开始迁徙流亡。他们一路向南,为了摆脱追捕,翻山越岭,终于在高山之上寻找到适合苗族人民安顿的地方。苗族人民开始耕种,为安宁的美好生活而欢庆,杀猪宰羊开展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乐舞活动。十二套古代芦笙组舞是苗族的历史教科书,在苗族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对于苗族族群具有民族凝聚作用,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功能性。十二套古代芦笙组舞保留了苗族舞蹈古老的民族风格,是目前最为古老的芦笙舞遗存,现在还能够完全掌握这十二组舞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老艺人。这是一份值得人们珍视的苗族民间文化遗产。同时十二套古代芦笙组舞还是大多数芦笙舞的源头,例如迁徙舞。十二套古代芦笙组舞包括一部分迁徙舞的内容,现在的大花苗迁徙舞更像是在十二套古代芦笙组舞迁徙部分的基础上展开的表演。
芦笙舞不仅是对汉苗民族历史的记录,还充满了对汉苗历史的感怀。苗族舞蹈的起源与祖先为了生存而斗争的传说有关,与祖先发明芦笙、创造芦笙舞,希望通过舞蹈为族人带来幸福有关。[9]尽管在芦笙舞中对汉苗历史的叙事充满了悲伤的色彩,但也表达出苗族人民不忘祖先、勇敢向前的民族精神。大迁徙舞,是苗族人民回忆迁徙之路的叙事性舞蹈,苗语称为“够嘎底嘎且”,主要流行于大花苗群体中。大迁徙舞共分三大段落:一是告别故土。舞者应用贴脚、踢走、级比(爬坡)等悲痛忧伤的舞步,叙述苗族先民们为躲避追捕,怀着悲痛的心情踏上长长的迁徙之路。二是行路难。舞蹈者们用回首拜别故乡的动作表达对故土的怀念;通过模拟鸟兽的形态,表达苗族先民们在迁徙征途中过着兽鸟充饥、野菜下肚的艰苦生活;通过探路、甩腿的动作表达前行中小心翼翼地跨越险阻、艰难迁徙的过程;通过饮酒等动作表达出苗族人民团结一心对抗困苦,向往美好的心愿。三是追忆与欢乐。这个部分描绘苗族先人击败敌人,顺利渡过浑水河,欢庆胜利的情景。在“追忆昔日”的舞蹈过程中有十多种套路动作,每套动作都展现出汉苗民族间的战争历史。跳大迁徙舞时,家庭院坝、野外草坪都可作为舞场之地,任何人不得干涉。在上述场合中,禁止跳唱祭祀舞和祭祀词(歌)。舞中的角色,第一人手持着火把,唱着古歌于前引路,歌声苍凉沉重,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民族苦难的迁徙史;第二人吹葫芦笙为指挥者(民间俗称“芦笙高手”),整场舞蹈表演的好坏,全在其指挥引导的水平;第三人直到尾数的第二个人都是队员。队列中所有的舞蹈者都必须注意与指挥者保持一致,若指挥者更换脚步,后众舞者则随之更换。最后一人为护尾,其责任是维护队伍中儿童妇女和弱者的安全。
大迁徙舞的舞蹈动作古朴无华,粗犷强劲,庄重沉稳。肩、手和脚部的形体动态是构成大迁徙舞的舞蹈要素。肩:有肩臂着地倒立,左右翻滚,倒身后翻,翻滚则要求动作敏捷灵巧,笙声不息;手:双手捧笙,要把握松中有紧、腕力灵活、指法顺畅的要领;脚:有抵脚板、勾脚跳和双脚倒挂等。用群舞形式表演大迁徙舞蹈,其场面大,气势雄浑,悲愤壮烈,凄凉真切;用双(单)人跳大迁徙舞,则热情欢快,敏捷灵巧,显示舞者的超群技艺。大迁徙舞的舞蹈服饰颇具古风。最具特色的是“城墙服”(民间俗称“劳绰”),即花衣衣领颈背上方的一块刺绣。苗族民间认定“劳绰”四周刺绣的花纹是山川,中间为平原,外围有城墙保护着平原地带的肥田沃土。女裙有开间裙、炒麦裙和田坎裙等等,形象地再现祖先居住的故土,表现着对故乡的怀念和对迁徙的追忆。跳大迁徙舞时,引路者(舞队前第一人)高声吟唱古歌,其八度和三度音程的跳进和下滑,使人顿生悲壮、凄凉、留恋之情。舞蹈进行中,古歌要唱多段,音乐则自始至终根据歌词反复。舞者手持芦笙且奏且舞,中音芦笙多奏主旋律,音乐伴奏古歌,形成一种慷慨悲凉、沉郁神秘的气氛,舞蹈动作与古歌所唱的内容浑然一体,真切地表现着一幅苗族大迁徙的悲壮的历史画卷。
苗族人民通过芦笙舞的程式化叙事、感怀式叙事、隐喻式叙事记录了汉苗民族间的交往与战争,程式化芦笙舞清晰地讲述了苗族迁徙以及汉苗战争的历史事件;感怀式芦笙舞表达了苗族人民在困苦与斗争中不畏艰险、向往美好的民族品质;隐喻式芦笙舞反映了苗族人民的创作智慧以及特定的动作语言与特定场景的对应性,并展现出了苗族艺术对历史的宏大叙事。
3.屯堡地戏戏曲舞蹈中的历史叙事——汉苗文化交融的共同见证
贵州的安顺地戏于2006年被评为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明朝时期的文化遗存。安顺地戏是明朝军队进入苗疆地区驻扎并定居后,其后代居民的舞蹈表演形式,具有明传奇的特点,即将乐舞融入戏曲故事之中。安顺地戏用乐舞讲述军队、战争的故事,以鼓舞士气,其中的舞蹈多为武舞。地戏的表演形式是头戴面具而舞,与傩相似,因此很多学者将地戏归纳为傩。但从面具的意义而言,傩的面具是在扮演神仙的角色,地戏的面具是为了使得表演更贴近战场更具威慑力。因此也有学者将地戏称为军傩,充分体现出了地戏的军事功能。
屯堡地戏是汉族视角下的程式化的战争叙事表演。屯堡地戏戏曲舞蹈是从汉族视角出发,表现汉族西南军队的恢宏气势以及作战场面的汉族舞蹈文化,是西南地区未识别民族屯堡人的舞蹈文化,分布于贵州安顺,也是西南民族舞蹈文化共同交融的典型案例,属于以舞蹈文化反映西南民族共同历史的文化现象。安顺位于苗疆走廊的中心地带,是明朝时期中央政府驻兵屯兵之地,由于朝代变迁明朝汉兵滞留于此,由于屯堡密集集中,汉多“苗”少,且汉族掌握着更为先进的经济技术,有着强大的作为汉族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并在婚姻观念上讲究汉族血统,由此导致屯堡文化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仍保持着明朝时期的汉族传统,并由此见证了汉文化进入苗疆的历史。安顺地戏的表演内容为金戈铁马的征战故事,其舞蹈以打斗动作为主,头戴面具而舞,极具表演特色,客观上是对西南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是西南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屯堡地戏是苗疆地区汉族族群的感怀式文化信仰仪式。在朝代交替中,作为明朝汉族屯军的屯堡人受到了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屯堡人在战争的轰鸣中丧失了原本的政治信仰,处于既融入不了当地少数民族,又回不去江南故乡的矛盾状态。在这样的逆境中,屯堡人更加坚定了维护明朝汉族的文化本源,通过服饰、习俗以及地戏表演的形式,延续着明朝汉族的文化血统。这时的地戏是对屯堡人内心信仰的守护,是屯堡人坚持自我的精神支柱。如今,屯堡人仍然保留着明朝江南汉族的服饰习惯,仍然表演着独具一格的地戏舞蹈。这看似保守的文化却又充满着包容。据安顺地戏传承人鲍吉祥先生口述,当地汉族为了保护当地苗族群体,教授了当地苗族群体一套汉族棍法与汉族拳法,当地苗族将这种棍法与拳法融会贯通后,结合着苗族的生活用具扁担形成了扁担舞。虽然无法考证此段历史的准确性,但是从舞蹈动作的角度来看,屯堡地戏中的棍舞与娄家庄苗寨的扁担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屯堡地戏是汉苗舞蹈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贵州的屯堡人是明朝时期的汉人移民,与西南少数民族杂处而居,因受当地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渗透,形成文化变异,兼具汉族、苗族、布依族文化特色,例如屯堡建筑中仿布依族的屋顶建造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提出屯堡汉族不同于一般汉族,是与当地苗族杂居并交融的汉族,并从其服饰、头饰等方面论述了其观点。中国学者曲六乙、钱弗提出了傩发源于汉族,并在不断的发展中融汇了儒释道等中原文化,并传至中华各地,包括苗疆地区。屯堡地戏就是汉族军傩流传至苗疆地区的典型案例。中国学者韩照丹认为屯堡地戏是在战事前的一种鼓舞士气、祈祷胜利的舞蹈,戴面具而舞,其道具主要是战鼓与战旗,其服饰多似西南少数民族服饰,但佩戴着京剧中常用来表演武戏的旗与翎。学者吕燕平提出屯堡文化具有地域性特点并区别于后移民,至今保持着中原汉族诸多已消失的特点,并论证了屯堡地戏与花灯是随汉军进入苗疆的舞蹈文化。
四、汉苗舞蹈文化中历史叙事的价值体现
汉苗舞蹈文化中的历史叙事是民族文明的“活化石”。汉苗舞蹈文化中的历史叙事记录了苗族人民的迁徙之路,记录了汉苗族群的分分合合,记录了汉苗人民的欢喜也记录了汉苗人民的苦难。而经历历史变迁、异地迁徙,汉苗的文化、文明一直被记录在其乐舞之中,经久流传,可见其艺术生命力之强健,其文化凝聚力的强大。
汉苗舞蹈文化中的历史叙事反映出汉苗民族舞蹈文化的交融性。蚩尤戏在河北汉族群体和湘西苗族群体中的流传,迁徙舞中对苗族人民斗争经历、迁徙过程的描述,屯堡地戏对战斗场面的表演,皆可见苗族族群因战争从黄河沿岸迁徙至西南地区,在迁徙与斗争途中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痕迹。汉文化作为中原地区的代表性文化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通过移民、经商、战争、技术等方式一直在向苗疆地区渗透。在苗疆走廊开辟前迁徙至苗疆的汉人多数已经“苗”化,并密切融入了“苗”族群之中,我们现今在苗疆地区发现的可辨识的汉文化大多数是在苗疆走廊开辟后的文化遗留。与自然变迁的文化不同,中央集权利用国家力量强行打开苗疆门户,短时间大量汉人涌入,安屯驻兵,在苗疆这个曾经相对封闭的地区,两种文化产生了急剧的碰撞。这种猝不及防的文化碰撞使得两种文化交融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强势的汉文化还是土著苗文化都无法将对方完全吞噬,反而显示出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文化交融现象。因此,汉苗舞蹈文化特性不仅具备排他的独特性,更有相互影响的交融性。
汉苗舞蹈文化中的历史叙事反映出汉苗人民民族文化身份的变化。文化作为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人类创造物,它包含着人类学和社会学两个方面的互补意义。文化是人类的高级适应行为的结果,在发生学意义上有别于人类体质进化的自然进程,是不脱离这个过程的派生物。具体说来,就是与动物本能和遗传方式相关的系统,人类就是基因与文化的组合。从社会关系上看文化,它反映在人的思想及行为方式的特点中,它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心理素质、行为方式、经验知识、价值取向等组合构成。一般而言,文化的本质主要在文化的社会学方面,因其结构特征不仅多姿多彩,而且易于变化。因此,汉苗文化亦主要是指汉苗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创造行为。文化身份在当代中国社会具有特别的意义。文化身份在权利实施过程中具有杂交的必然性以及身份的动态性。[10]从汉苗舞蹈文化中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汉苗人民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变化,以及从单一民族身份向融合的中华民族身份变化的过程。
汉苗舞蹈文化中的历史叙事,体现了西南民族间以及西南民族与中央政府之间自古以来便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因为战争、政治或者经济而存在,都不可避免地促成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交融,使得我国多民族之间不断接触、交往、融合,大大增加了文化、文明融合的机会。汉苗人民通过舞蹈文化的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身份意识的形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条件。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各民族都存在交流、交融的历史,这种交融或是润物细无声的渗入,或是民族力量的强势干预,从而形成现存民族文化的交融性、杂交性。在苗族社会的变迁中,汉文化的传入具有转折性的影响。在现存汉族中存在“苗”族汉化人群,苗族中也不乏汉族“苗”化人群。例如未识别民族的湘西瓦乡人与贵州的屯堡人。聚居在湖南沅江中游及其各支流山区的一部分群众自称“果熊人”,当地汉族群众根据其自称把他们称为“瓦乡人”,是我国西南地区未识别民族,兼具汉族、苗族、土家族文化特点,是“苗”民汉化的代表,见证了汉族、苗族、土家族文化的交融。贵州的屯堡人是明朝时期的汉人移民,与西南少数民族杂处而居,现为我国未识别民族,因受当地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渗透,形成文化变异,兼具汉族、苗族、布依族文化特色。瓦乡文化与屯堡文化皆证实西南民族文化存在交融现象,见证了历史洪流中西南民族文化的巨大变革。与此同时,苗族人民还通过苗疆走廊带着中华文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泰国、越南等地生根发芽,同时也传承与发扬着绚烂夺目的苗族舞蹈文化。海外的苗族游子处于不同的地域,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可以拥有同样的舞蹈,用舞蹈文化传递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精魂。苗族舞蹈文化承载着中华文化交融的特征,也是海外苗族对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