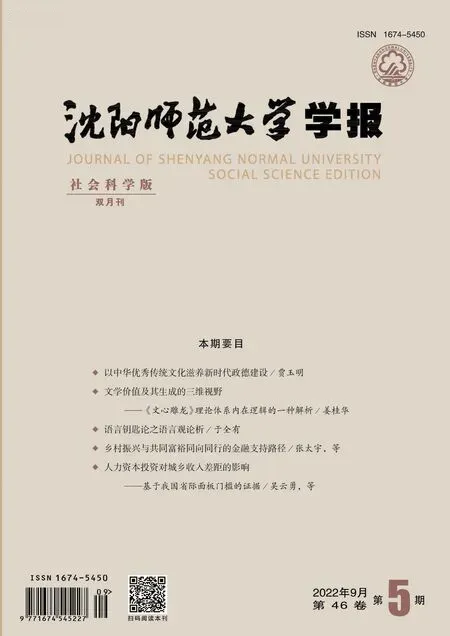《王僧孺集》流传与辑佚考
郝继东,何 好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王僧孺(465—522年),东海郯人,三国时魏卫将军王肃八世孙。其人学识渊博,文采卓然,为南朝梁时著名文学家,又喜好典籍,其藏书多为异本,与同时代的沈约、任昉并称为南朝三大藏书家。王僧孺历经齐、梁两代,在齐时曾任治书侍御史、钱塘令。至梁代,又任南海太守,后迁尚书左丞,兼御史中丞,后任南康王长史,又因汤道愍谗言而被罢官。晚年患病,光景凄凉。著作有《王左丞集》《十八州谱》《百家谱》《东宫新记》等。
王僧孺的文学创作集中体现在《王僧孺集》(即《王左丞集》)之中。《王僧孺集》从最初的三十卷本一直到现存的一到三卷不等的辑佚本,其流传从时间上大致经历十数个朝代,从形态上说可分为存续、亡佚、辑佚三个阶段。本文将对此集的流传状况、亡佚情况、辑佚情况、现存版本以及版本间承继关系进行研究,以探寻其作品存佚脉络、寻求文本原貌及揭示其版本间的层累关系。
一、《王僧孺集》的存续与亡佚
现存史料中,最早提及《王僧孺集》的是唐代姚思廉奉诏编撰的《梁书》。《梁书》卷三十三《列传》第二十七有王僧孺本传,其传载:“僧孺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两台弹事》不入集内为五卷,及《东宫新记》,并行于世。”[1]474《梁书》虽成于姚思廉之手,完成于唐初,但其父姚察对此功不可没。姚察为南朝梁史学家,至陈朝时,他已开始着手对梁史进行编撰。在《梁书·列传第二十七》之尾,有“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的署名[1]487,可见《梁书》的半数在姚察之手已初具规模。由此看来,《梁书》所载王僧孺“文集三十卷”当在梁时便已整理完成是相当可信的。此“文集”即后世所辑之《王左丞集》,亦即《王僧孺集》。因此,《梁书》可以说是《王僧孺集》的最早记载。
《梁书》之后,隋唐时期官修目录对《王僧孺集》也有记载。《隋书·经籍志》有“梁中军府谘议王僧孺集三十卷”[2]989,《旧唐书·经籍志》[3]2069和《新唐书·艺文志》[4]1593均载“《王僧孺集》三十卷”。从梁代至唐代,《王僧孺集》始终以三十卷的形制流传。可见,雕版盛行以前,《王僧孺集》一直以全本存于世。明代彭大翼(1552—1643年)的《山堂肆考》曾记载一件事:“唐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又谓同官曰:‘昨买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范知其误,应声曰:‘文范亦买得《张佛袍集》,胜于僧孺远矣。’由古应之不觉。”[5]虽是一则笑话,但也说明当时《王僧孺集》为手边之物,极为常见。至宋代,公私目录中唯有郑樵《通志》对《王僧孺集》有记载:“中军府谘议王僧孺集三十卷。”[6]1755这条记载明显来源于《隋志》。而郑樵著录书籍素来主张“广古今而无遗”[7],今人王树民在对《通志》中二十略的点校中也认为郑樵“通著古今,不遗亡遗,全面记有”[6]1807。从上述事实与评价可以想见,郑樵所谓“《王僧孺集》三十卷”并非其当时所亲见,而是应记尽记的结果。可见,《王僧孺集》流传至宋代已渐有亡佚之势,已非三十卷原貌,至少已非手边常见之物。宋之后,元明两代公私目录对《王僧孺集》已绝无记载,想见其集在这一时期已完全散佚。
王僧孺的作品除了以“集”的形态进行流传之外,亦散见于各类总集和类书。最早对王僧孺作品进行收录的是南朝梁时徐陵(507—583年)的《玉台新咏》,共收王僧孺诗 19 首,其中17 首收于卷六,2 首收于卷十。《玉台新咏》是距《王僧孺集》初创时间最近的一部诗歌总集,所收王僧孺诗歌大致可认为是《王僧孺集》旧制,所以这也成为明清两代对《王僧孺集》进行辑佚的重要来源。唐宋时期的类书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王僧孺集》原始面貌。首先,由欧阳询(557—641年)等人奉敕编纂于唐初武德七年(624年)的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官修类书《艺文类聚》,共收王僧孺诗25 首、文22篇。《艺文类聚》成书时间与南朝梁时《王僧孺集》和《玉台新咏》的成书时间相距不远,所收录的王僧孺作品继承了《玉台新咏》所收王僧孺的诗歌部分。如《在王晋安酒席数韵》一诗中,首句“窈窕宋华容”之“华容”,《玉台新咏》与《艺文类聚》均作“容华”。再如《为姬人自伤》一诗中,“断弦犹可续”之“断弦”,《玉台新咏》与《艺文类聚》均作“弦断”。可见,《艺文类聚》所收王僧孺诗与《玉台新咏》是存在承继关系的。其次,宋代由李昉(925—996年)等人奉敕编写的官修类书《文苑英华》,共收王僧孺诗15首、文2 篇。《文苑英华》所收王僧孺作品亦来源于《艺文类聚》。如《至牛渚忆魏少英》一诗中“绿草闲游蜂”之“闲”字,《艺文类聚》与《文苑英华》均作“间”字。再如《秋日愁居答孔主簿》一诗中“首秋云物善”之“秋”字,《艺文类聚》与《文苑英华》均误作“夏”字。由此可见,从《玉台新咏》到《艺文类聚》,再到《文苑英华》,三书收录王僧孺作品的关系一脉相承,均是后代对前代的借鉴与传递。此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对散见于前代各总集与类书中的乐府诗进行了整理,其中收录王僧孺乐府诗6 首。《白马篇》一诗“长驱绕岷棘”之“棘”字,《文苑英华》与《乐府诗集》并作“僰”。《湘夫人》一诗“日暮思公子”之“暮”字,《艺文类聚》与《乐府诗集》并作“莫”。此二例也可说明《乐府诗集》与《艺文类聚》《文苑英华》所收王僧孺诗歌也是有共同源头的。
除此以外,唐代释道宣的《广弘明集》、宋代吴曾的《能改斋漫录》、高似孙的《纬略》、李刘的《四六标准》、任广的《书叙指南》、祝穆的《古今事文类聚》等书都对王僧孺其人和作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记载与收录。
总体来说,《王僧孺集》成于南朝梁代,传于唐宋,散于两宋之际,至元时没而不闻。究其原因,其一是战乱。唐末、两宋之交以及南宋末年战乱不休,前代典籍也因之常常泯灭,《王僧孺集》历经唐、宋之乱,已渐非其本来之貌,仅以零散作品存于类书之中。其二是学术上不重视。宋代疑古之风兴盛,对前代作品批判多于褒扬,因此并不注重前代别集系统的整理和辑佚,在公私目录中也是仅著其名。前代的作品均有散佚,仅类书、丛书留有部分别集的内容。《王僧孺集》中的作品散见于唐、宋时期的类书之中,由此可见一斑。其三是收藏条件的限制。元代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统治者本身对华夏文化与典籍不感兴趣,因此对书籍收藏并不重视,这一时期便成为藏书史中最为低迷的一个时期,并且无藏书目录留存于世。可以想见,《王僧孺集》流传至元代,便进一步散佚乃致不存。然《王僧孺集》其集虽已亡佚,但其作品的流传并未中断,明代以后,辑本与收本逐渐多了起来。
二、《王僧孺集》的辑佚
明代初期的文学受理学思潮及台阁体影响而呈现出萎靡不振之态,由此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应运而生。主要活动于弘治、正德年间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8],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开始得到关注。嘉靖时期后七子接替前七子继续提倡复古,其主张以秦汉散文、魏晋古诗、盛唐律诗为典范,汉魏六朝时期文学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外,明代雕版印刷技术和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前代的总集、类书等因之能够得以大量刊行,这也为前代文献的辑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以此为前提,明代学者开始对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进行整理与辑佚,现所见《王僧孺集》便是在这一时期整理而成。清代承袭明代整理成果,进一步系统整理与刊刻。明、清及近代所见《王僧孺集》主要有如下辑本。
(一)明冯惟讷《古诗纪》本
冯惟讷(1513—1572年),字汝言,号少洲,山东临朐人。其整理的《古诗纪》,是继郭茂倩《乐府诗集》后的又一部古代诗歌总集。《古诗纪》是明代现存最早对王僧孺诗歌进行收集的总集,其卷八十八收录王僧孺诗歌37 首,其中包含乐府6 首。对王僧孺诗歌整理的体例,首题王僧孺名字,名字下为双行小字生平简介,次为所收诗歌。遇所收诗歌的标题或者内容存有异文时,一一标明并将异文用双行小字列于正文下。《古诗纪》所收王僧孺诗歌多照录前代类书已收辑的作品,如《为人伤近而不见》一诗中“脈脈如牛女”之“脈”字,《古诗纪》与《艺文类聚》均作“脉”。再如《秋闺怨》一诗中“协光隐秋璧”之“璧”字,《古诗纪》与《玉台新咏》均作“壁”。现存《古诗纪》以明万历吴琯刻本较为精良,也是四库全书所收版本。之后的《王僧孺集》辑本诗歌部分多对《古诗纪》本加以参考与吸收,因此可见《古诗纪》本在《王僧孺集》辑佚方面的重要价值。
(二)明梅鼎祚《梁文纪》本
梅鼎祚(1549—1615年),字禹金,号胜乐道人,安徽宣城人。一生以读书、藏书、著书为乐,建有藏书阁“天逸阁”。梅鼎祚一生著述颇丰,其中以集毕生之力完成的《历代文纪》一书最为有名。《历代文纪》中《梁文纪》以《梁书》《南史》等书为基础,对诸家文集进行辑佚,审校精良,是明代现存最早对王僧孺文章进行收集的总集。《梁文纪》卷十一收录《王僧孺集》,包含文体9 种,共有作品19 篇,作品出现异文时所采用的注释体例与《古诗纪》同。《梁文纪》也对前代已有成果有所接受,例如《为南平王让仪同表》一文中“非能声均吴楚”之“吴”字,《艺文类聚》与《梁文纪》均作“河”。再如《从子永宁令诔》一文中“悬符矩彟”之“彟”字,《文苑英华》与《梁文纪》均作“雘”。《梁文纪》本并未收录王僧孺赋一类的文章,文体收集不全,这是辑本的不足,但其所辑《王僧孺集》为之后的辑佚整理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三)明张燮《七十二家集》本
张燮(1574—1640年),字绍和,自号海滨逸史,福建龙溪人。一生著述有15 种七百余卷,其中以《七十二家集》用力最勤,所收之集多数成为后代刊刻的底本。张燮辑成的《王左丞集》3 卷,收入《七十二家集》第一百一十卷。卷首为张燮所写《王左丞集引》,主要叙述王僧孺生平与生活时代,并对其人及其文学创作做出评价。《王左丞集引》之后附三卷的目录,卷一收录赋、乐府诗与其他诗歌,其中包括赋1 篇、乐府诗6首、诗33 首,卷二、卷三收录文章27 篇,其中包含表 6 篇、笺 1 篇、启 5 篇、教 1 篇、书 3 篇、序 2 篇、碑 2 篇、墓志铭 1 篇、传 1 篇、诔 1 篇、祭文1 篇、佛事文3 篇。正文卷端自右向左分两行竖题“梁东海王僧孺僧孺著”“明闽漳张燮绍和纂”。正文后又有附录,其中分别为姚察《王僧孺传》、李延寿《王僧孺传》、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谢朓《别王僧孺》、任昉《赠王僧孺》、吴均《入兰台赠王治书僧孺》,最后一篇为《遗事》,取自《梁书》,资料详实,收辑全面。
张燮所辑《王僧孺集》是明代首部将王僧孺的诗与文编在一起的文集,以《梁文纪》所收19 篇文章为基础,再次对前代各史书、类书与总集进行搜罗,新辑文章数篇;又以《古诗纪》所收37 首诗歌为基础,新添《何逊赠王左丞僧孺附》和《何逊敬酬王明府僧孺附》,然此两首显为何逊所作,是何逊赠与王僧孺之诗,故应为增收进此集的相关作品。现所见此集较好版本是明天启崇祯间刻本,此版本也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收。
(四)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
张溥(1602—1641年),字乾度,号西铭,江苏太仓人,晚明文学家。为“兴复古学”[9]47,在《七十二家集》稍后,张溥以此为基础汇成一部规模宏大的总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亦名《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集中卷九十二为《王僧孺集》,共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曰:“自冯惟讷辑《诗纪》,而汉魏六朝之诗汇于一编。自梅鼎祚辑《文纪》,而汉魏六朝之文汇于一编。自张燮辑《七十二家集》,而汉魏六朝之遗集汇于一编。溥以张氏书为根柢,而取冯氏、梅氏书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是集。”[10]1723此集对《古诗纪》和《梁文纪》的承继关系,显而易见。此本收录王僧孺文章数量与《七十二家集》本同,诗歌数量较之少两首。张溥编撰体例承袭张燮但体裁编次又有所变化,首为赋,次为文,再为诗歌。
据《中国丛书综录》载,《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如下几个版本:娄东张氏本、滇南唐氏寿考堂本、彭懋谦信述堂重刊本、善化章经济堂本、长沙谢氏翰墨山房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四川官印局本等[11]825。现可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王左丞集》有四库全书本、四库荟要本、信述堂重刻本和扫叶山房本。四库全书本《王左丞集》封面从右至左题负责此本的官员的姓名,依次为“详校官庶吉士臣谢恭铭”“主事衔臣徐以坤覆勘”“总校官检讨臣何思钧”“校对官编修臣沈清藻”“謄录监生臣李长清”。此集体例为前附《王僧孺集题词》,后紧接目录,之后正文卷端竖题“明张溥辑”,后无附录。四库荟要本《王左丞集》与四库全书本体例大致相同,区别在于四库荟要本前无题词。此本封面最左端题“详校官侯选知县臣吴甸华”,首卷卷端竖题“明张溥辑”,后亦无附录。信述堂重刻本与扫叶山房本《王僧孺集》体例一致,其中信述堂重刻本刊于光绪五年(1879年),扫叶山房本刊于民国六年(1917年)。此两本前有题词,题词末尾竖题“娄东张溥题”,之后为目录,卷端竖题“王僧孺集卷之全”,下方题有“梁东海王僧孺著”“明太仓张溥阅”,后均有附录,附录中有王僧孺本传。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不仅对前代成果进行承袭和借鉴,其内部诸版本也存在同源关系。例如《白马篇》一诗中“不许跨天山”之“跨”字,信述堂本、四库荟要本、扫叶山房本均作“誇”。次如《为萧监利求入学启》一文中“不如修戈”之“戈”字,四库荟要本、扫叶山房本、四库全书本均作“弋”。再如《礼佛唱导发愿文》一文中“验画水之随合”之“验”字,信述堂本、四库荟要本、扫叶山房本均作“黔”。
(五)明叶绍泰《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
叶绍泰,生卒不详,字耒甫,浙江嘉兴人,辑成《增订汉魏六朝别解》。叶绍泰曰:“六朝之文,惟梁称盛,而贵游子弟,为朝士羞,此名人集中所以多代人之作也。”[12]154虽为偏左之词,但也承认六朝时梁代文学的鼎盛,也是其辑《汉魏六朝别解》的初衷。《增订汉魏六朝别解》卷六十收录《王左丞集》一卷,本为选集,共选录王僧孺《为韦雍州致仕表》《与何炯书》《答江琰书》《太常敬子任府君传》4 篇文章,文后均附有叶绍泰的评价。此本虽仅收录4 篇文章,但也是在前代辑佚成果基础之上形成的。例如《为韦雍州致仕表》一文中“高春之景一斜”之“春”字,《增订汉魏六朝别解》《艺文类聚》《四六法海》《梁文纪》皆作“舂”。《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出现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后,但不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校勘精良,且收录篇目过少,对后代王僧孺作品的辑佚、整理与研究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目前,可见较好版本为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采隐山居刻本。
(六)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本
严可均(1762—1843年),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清代文献学家、藏书家。清嘉庆年间开馆始辑《全唐文》时,严可均认为唐以前之文章也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辑佚与整理工作,故而遍阅群书,将上古至隋代以前的文章编纂成集,即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该书中《全梁文》第五十一卷、五十二卷收录王僧孺作品,共30 篇。严氏在继承前代辑佚成果基础之上,新辑《论任昉》《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二经序赞》二篇。该本所收王僧孺作品皆在其后标明收录来源出处,如《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广弘明集》《南史》《释藏》等,便于后人查找,是其优于前人的地方,体现其辑佚整理的学术观。事实上,与前代辑佚成果比较,亦能发现其借鉴承继的痕迹。例如《谢历表》一文中“曾无昃朓”之“朓”字,四库荟要本《百三家集》《艺文类聚》《全梁文》均作“眺”。次如《与何炯书》一文中“正复除名为民”之“正”字,扫叶山房本、四库全书本《百三家集》《梁文纪》《全梁文》均作“止”。再如《中寺碑》一文中“晋大元五年会稽王司马道子之所立也”之“大”字,四库全书本《百三家集》《艺文类聚》《渊鉴类函》《全梁文》皆作“太”。此类例证繁多,不胜枚举。
(七)近代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本
丁福保(1874—1952年),字仲祜,号畴隐居士,江苏无锡人,近代藏书家、书目专家。明代以来所辑诗歌总集以冯惟讷《古诗纪》收集最为详实,但不足之处是其中掺杂着诸多伪作,而且考证不甚精良。后清人冯舒又作《诗纪匡谬》一书,对冯氏及其书加以辩正。近代学者丁福保以此二书为蓝本,系统收集汉代至隋代的诗歌,并于1916年出版《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其中《全梁诗》卷六收录王僧孺诗歌39首。除依托《古诗纪》之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本亦从《玉台新咏》《文苑英华》《艺文类聚》等类书中进行王僧孺诗歌辑佚,并保留了诸书所收诗歌原貌。例如《为何库部旧姬拟蘼芜之句》一诗中“敛容裁一访”之“裁”字,《玉台新咏》与《全梁诗》皆作“纔”。次如《为人述梦》一诗中“工只想成梦”之“工”字,《玉台新咏》与《全梁诗》均作“已”。可见,《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在进行辑佚时,新辑作品不仅标明所辑来源,还保留了所辑诗歌的原样,体现了与所辑来源的一致性和承袭关系。
上述七个版本为明代以来较为重要的《王僧孺集》的辑佚本,可据其中体裁内容分为三种不同形态:其一为诗集,如冯惟讷《古诗纪》本和丁福保《全梁诗》本;其二为文集,如梅鼎祚《梁文纪》本、叶绍泰《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和严可均《全梁文》本;其三为诗文合集,如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和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虽各个版本之间存在差异,但每一版本都是对已有成果的再次整理与勘正,由此可见,已成定本形态的《王僧孺集》是逐次叠加而成的,其版本及内容呈现出层累关系。
除上述七个版本之外,明清以来还有不少关于王僧孺作品的记载,如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明王志庆《古俪府》、清张英等《御定渊鉴类函》、清张玉书、陈廷敬等《钦定佩文韵府》、清吴汝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以及近代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可与这七个版本的《王僧孺集》相互参照。
三、结语
《王僧孺集》初名“文集”,为三十卷,南朝梁时集成,至宋时官私目录中偶有记载,但已不见全本,至元时不见著录,可见已完全散佚。明人开始辑佚,亦名“王左丞集”,仅为一卷之制,可见已难觅当年三十卷之旧。明清以来王僧孺诗文辑佚者较多,然无论诗集、文集还是全集,都无法恢复旧制。而且明清以来的辑本多为互相借鉴,多出而同源。可见,《王僧孺集》自形成到流传,以至后代的散佚与辑集,经历了南北朝以来不同时代的风风雨雨,遭遇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种种坎坷。即使后人尝试通过辑佚的方式力求还原《王僧孺集》的全貌,但毕竟人力有限,要想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辑出还是有相当的困难。另外,随着时代的演进,散佚的文献也越来越难以恢复。我们通过《王僧孺集》的流传、散佚与辑集,既可寻绎到其流传脉络和辑本情况,也可发现历代学者对此所做的努力。因此,以《王僧孺集》为代表的汉魏六朝别集仍亟待系统科学的整理。利用科学合理的辑佚方法和其他手段对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与文献整理研究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