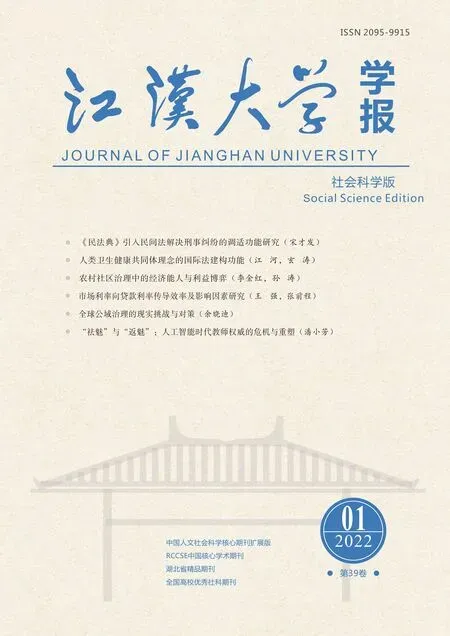“祛魅”与“返魅”: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权威的危机与重塑
潘小芳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最早于1956年在达特茅斯学院一次会议上由麦卡锡(J.Mc Carthy)等人正式提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通过特定的方式和媒介实现变革教育的目的,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教育信息化的基本要素包括设施设备、平台系统、各种教学资源、参与教育活动的人等。教师作为教育活动中的重要角色之一,无法回避人工智能带来自身角色和权威的挑战与危机。学术界对教师权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普遍持有质疑和批评,主张“祛权威化”、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有观点从感召权威、法理权威、对法理权威的超越和去权威化的复杂历史演进中论述教师权威的丧失与重建。[1]有观点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导致教师教化权威衰落的主要原因。[2]然而,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时代急需的不是用网络教育代替学校教育,彻底消解教师权威,而是要理性审视与回应技术时代的教育诉求,重建教师的教育权威。[3]什么是教师权威?教师权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何在?新时代教师权威面临哪些困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师权威?如何重新认识教师权威,重塑权威?这是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思考并厘清的一系列问题。
一、理论溯源:何谓教师权威
“权威”(Authori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auctoritas”,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代表集体或个人作为权威主体在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并具有支配力量;在法学中,权威代表立法与司法的公平、公正;政治学中的权威代表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影响力与公信力。教师权威是权威在教育领域的延展和运用,“指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使学生信从的力量或影响力”[4]。作为学校教育中一种重要的影响力,教师权威在教育活动中有其独特且重要的价值。本研究主要探讨教师权威与教师权力、教师威信以及与我国传统师道尊严之间的关系,明确教师权威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一)教师权威与教师权力、教师威信
社会学对权威的研究以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的描述与分类较为经典。他将权威的来源分为三种类型:(1)传统的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是在长期的传统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权威;(2)人格感召的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是由个人魅力所获得的权威;(3)法理的权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的或法理的权威,另一类是官方的或法定的权威。R.克利弗顿和L.罗伯特在韦伯的基础上对教师权威做了深入探讨。他们认为教师权威主要取决于制度性因素和个人因素这两个方面,其中,“制度性因素形成教师的制度性权威,个人因素形成教师的个人权威。制度性权威主要由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赋予教师的法定权限所决定。个人权威主要由教师的个人学识、专长和人格魅力所决定”[5]。对于教师权威有着不同的分类,从权威的来源看,有感召权威和法理权威,形式权威和实质权威;在具体内容方面,有知识权威、道德权威、人格权威等;从伦理学角度,有理性权威和非理性权威。
教师权威与教师权力、教师威信的内涵有其“重叠域”,拥有权威、权力和威信的主体在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方面占主导地位,对作用的对象产生影响力。但“教师权威”并不等于教师权力,亦不是“教师权力”和“教师威信”这两个概念的合成。教师权力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利用教师权利等资源形成的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这种强制性力量的运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学生的权利,也违背了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权力关系中的师生处于强迫与被迫服从的状态”[6]。由此看来,与教师权力相对应的是“学生权利”,两者是矛盾冲突的对应关系。传统尊师文化赋予教师一定的权力,法律法规使教师具有教育教学的权力,教师拥有的知识可转化为一种权力。与权威不同,权力大多来自于教师对教育教学权利的不当使用和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其滥用和误用易造成师生关系的扭曲与异化。同时,权威比权力有更为严苛的条件,教师权威倾向于在积极层面发挥作用,教师权力往往在消极方面引起师生关系的撕裂和异化。威信代表一种客观存在的心理现象,是有威望的人受到众人的尊敬和信任。教师威信指教师凭借自身的学识、教育教学能力、人格魅力等受到学生及其他人心理上的信赖和尊敬,体现一种积极的人际交往。由此看来,教师权威比威信的来源和表现方式都更为丰富和复杂。基于以上,在探讨教师权威时,应避免以权力代替权威的权力主义,以及以威信代替权威造成的权威弱化。应在吸收权力和威信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构建教师权威的意涵。
(二)教师权威与师道尊严
谁赋予教师权威?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首先应追溯传统的尊师文化,我国的尊师传统由来已久。《礼记·学记》被公认为是“师道尊严”的最早出处,“师严而道尊”倡导教师作为“道”的传播者,通过尊师重道以达到化民成俗、教化社会的目的。什么是“师道”以及教师需要传什么“道”成为“师道尊严”的两个核心问题。荀子的“天地君亲师”,认为教师的地位和高度与“天”“地”“君”相并列,且尊师重教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废,必贱师而轻傅。“师道”,即为师之道,强调教师的尊严、权威和崇高地位,这种地位又在“传道”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确立的教师权威地位不可动摇,师道尊严的背后是强大的封建伦理文化作为支撑。韩愈在《师说》中指出教师角色是“传道,授业,解惑也”,并将“传道”作为教师的首要任务。教师所传之“道”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中国“官师合一”的传统使教师作为官方文化、官方知识的代表者,实现其政治目的。由此,我国传统文化中明确了教师的重大责任,在师生关系中确立了教师权威的道德基础和文化根基。作为“经师”与“人师”的统一,教师不仅要钻研高深学问,还要有伟大的人格与道德修养,是知识权威、道德权威和文化权威的辩证统一。
不同于中国重视传统文化中“师道尊严”的伦理向度,西方社会的教师权威强调教师的知识权威并让位于求真本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爱吾师,更爱真理”是突破权威的真理至上观。神学思想中教师作为儿童的主宰和代理人,其权威地位不容置疑。近代的“教师中心论”强调教师在师生关系中的主导与权威地位,与此相对的“学生中心论”又打破教师权威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总之,西方的教师权威在权威与非权威之间博弈,来源于求真本质的教师权威不得不让位于师生交往中的平等、民主及学生自由。
(三)教师权威的正当性
权威从何而来?其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何在?如前所述,政治、文化领域的传统观念是权威的重要来源。同时,社会法律制度是制度赋权的重要来源,关系型权威的被支配对象——学生是赋权的又一主体。学生身心发展不完善且具有向师性,教师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学生的承认和服从,生成教师权威。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权威来源于外部,但同时它在内部也向我说话……权威既来自于外部,但同时它又总是发自于人们的内心中”[7]76。由此看来,权威建立在“合法”权力与权利的基础之上,是外在赋权与内在生成的辩证统一。
在韦伯看来,超凡魅力型权威——“克里斯马(chairsma)型权威”来源于领袖人物的非凡禀赋、个人特质及吸引力,其基础“可能是传统,即习惯了的、历来如此的东西的神圣性,传统规定某些特定的人要服从”[8]。魅力型权威来自于传统,是崇高又具有神圣性的存在。恩格斯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权威,在此基础上论证什么是权威及权威的合理性。他指出,“权威是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9]。恩格斯承认权威的客观存在及其必要性,辩证、全面地看待权威,将其作为强制、服从与价值认同的矛盾统一体。同时,权威与民主自治是相对的,并无孰优孰劣之分,这意味着教师权威与学生民主自治的矛盾统一,学生民主与自治不能脱离教师权威而存在,否则自治将成为一盘散沙。社会学家科尔曼也将权威作为一种合法的支配关系,这里的法不是外在法度而是指人们的内心法则,是权威主体与其服从对象在博弈中达成的共识。教师权威是源于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影响力,产生于学生对教师的学识、教育教学能力、人格品质等产生内在认同的基础之上,具备正当性、合法性和合理性,以此产生积极的教育力量。教师权威能够保障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合法地位,有利于保障和促进教育教学的公平公正,是教育正义的应有之义。
二、现状考察: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权威的式微
人工智能引起的社会大变革延展至教育领域,对教师权威带来新的挑战。权威旁落、式微和消解始于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加重了权威的危机。教师权威的式微主要体现在技术的“祛魅”和教师作为知识权威与道德权威的失落。
(一)现代性之教师权威“祛魅”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一般指曾被信奉或被追捧为神圣的人、物、情感、信念等,一切非理性的巫术、魔法、神秘主义等,在人们产生新的认识后地位下降,失去自身的神秘光环,祛除其“神性”与“魔力”,成为平常之物,人们也不再对其着迷、盲目崇拜,更不会去追寻、体验其意义。“一切终极的、崇高的价值都烟消云散”[10]。物质文明进步迅速,而生活却越来越无意义。近现代以来,尼采高呼“上帝已死”,一切价值都可以被重估,权威亦被重新审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及与其相适应、被尊崇的观念都被消除了,神圣的东西被亵渎。我国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批判传统儒家文化的旗帜,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中传统礼教对人的束缚和压榨。始于政治、文化领域权威的失落和“祛魅”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前就初现端倪,教育领域在新旧文化的冲击下出现不同理念的撕裂。在阿伦特看来,“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现代世界在我们这一百年里的发展,伴随着一种持续的,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加重的权威危机……这个危机最意味深长的征兆(同时也显明了危机的深重)是,它已经扩展到儿童的培养和教育这样的前政治领域中”[11]。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危机体现在各个领域,教师权威对于塑造学校场域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人际交往——师生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教师权威的失落是政治、文化领域中权威式微的必然结果,不仅是教育的危机,也是深层的政治与文化危机”[1]。政治、文化领域的权威式微与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交错,并不断进步。
祛魅的自然观支持科技万能论和技术统治论,主张人类中心主义,认为技术拥有驾驭一切的力量。“世界的祛魅”导致“价值多元化、信仰体系解体、价值理性日趋式微……”[12]高兆明认为,应正确审视技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当代人类在祛魅工具理性的同时,又应当避免附魅价值理性”[13]。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技术作为教学手段和媒介的价值不断凸显,权威在技术泛滥时代的失落似乎成为一种必然宿命。科学技术的成果运用于教育场域中,变革传统口耳相传和“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的教学方式。多媒体教学设备、电子白板等信息技术手段使知识学习更加便捷,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翻转课堂等教学方式出现,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促进者和合作者。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渗透和运用造成人对物的依赖,导致教师和学生作为主体的异化及师生关系的异化。祛魅的教育失去了理想性和超越性,世俗化、功利化的教育取而代之。由此造成“人工智能的教育迷思”,即“让人工智能成为‘魔法’一般的存在,扭曲社会各界对‘教育+人工智能’的观感”[14]。传统教师权威宣称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的形象不复存在,“依附于教育制度的(教师)权威现已‘祛魅’”[4],教师被看作“经济人”“职业人”,其职业定位扭曲,职业边界模糊,甚至缺失,社会中的“辱师”“轻师”“贱师”事件时有发生,让教师权威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二)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消解
教师拥有的文化资本是其作为知识权威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即学高才能为师。古代社会“学在官府,官师合一”,“以僧为师,以吏为师”的教育体系使教师权威实至名归,权威的践行以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为基本样态。人工智能时代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计算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也与教育教学相结合,加剧了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消解,这也是教师权威失落最突出的表现之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知识自身变革打破教师的“垄断”权威
知识教学首先要回答课堂上教授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中西方传统知识观强调知识的确定性、终极性、普适性、权威性,教师“闻道在先”并处于权威地位,传统教学观倡导的“一桶水理论”要求教师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以灌输式教学为主教授学生学习客观知识和真理,忽视了师生互动的参与性和知识的情境性,也忽视了师生在人格上的平等、在交往中的对话关系。现代知识观强调知识的生成性、主观性、默会性和不确定性,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大爆炸时代,海量的信息资源呈指数型增长,而教师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当有限的认识主体面对无限的知识海洋,教师也只能成为某一方面或领域的“先知者”,打破教师对知识的“垄断”。具体表现为,“教师知识权威的性质更迭,知识‘垄断者’的角色变迁,知识话语权受到限制”[15]等。与此同时,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知识的来源不仅仅是课本、教师讲授和生活经验,可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获取知识和信息,学生和知识之间的鸿沟缩小,教师作为真理发现者和传播者的知识权威被削弱甚至消解。学习知识的渠道多元化,学生在某些方面的知识储备可能超越教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成为现实境遇,学生会对教学内容产生“质疑”,大学课堂上与教师的“商榷”“探讨”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愈来愈成为普遍现象,教师作为“知识的‘独裁者’与绝对知识权威的角色受到挑战”[16]。
2.教学方式变革需要重审教师权威
自班级授课制出现以来,面对面的“班、课、时”是教学的主要形式。人工智能时代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计算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并与教育教学相结合。教育人工智能(EAI)的本质是以智能技术推动教育变革与发展。一些支持技术,如VR/AR、互联网+、AI和大数据分析运用到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习中,为教学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和各项资源,变革传统教学方式。翻转课堂、慕课(MOOC)、微课、STEAM教育、创客教育、在线课堂等教学模式需要人工智能的支持。智慧教育的各种教学场景,如虚拟现实教育、远程互动教学、人工智能教育教学评测、校园智能管理等,能够进行师生互动,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快速吸收新知识,进行个性化、定制化学习和沉浸式课堂教学体验。
人工智能时代学生借助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和智能设备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打破时间、空间的界限,也使教师从权威地位走向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促进者与合作者。如我国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居家学习成为常态,在线教学、在线答辩、视频会议、课堂直播等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师生教与学的主要方式。人工智能为特殊时期的教育教学转移至网络环境提供了技术支撑,教师和学生在网上授课、学习、讨论和交流,学习的场所、时间比较灵活,打破线下教学的时间和空间壁垒,进行“泛在的”“无边界化的”学习,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教育需求,进而保障并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线上教学、教学机器人和“真人教师+AI助手”等在知识教学中显示出自身独特优势,对传统知识教学和教师讲授提出挑战。如我国2017年在河南举行的人机教学大赛中,机器人工智能完胜真人教学。“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技术的不断突破,加之政策鼓励、资本涌入等因素的影响,人工智能将覆盖教学流程的更多场景、接入更多教学核心环节,对劳动力市场的替代效应也会不断增强”[17]。后疫情时代教育如何转型与变革?在线教育是否会取代传统的课堂教学?教师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和教学机器人取代?教师职业是否会消失?这些问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三)教师作为道德权威的失落
师生关系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关系,体现教育的道德基础。教师以“师道”“传道”成为“身正为范”“亲其师,信其道”的道德权威和榜样。教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还有“春蚕”“蜡烛”“园丁”的隐喻,教师享有崇高地位。近代以来,在文化、经济及信息技术的多重加持之下,教师形象失落,并出现“反权威”“去权威”的倾向。“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文化观念、思考方式与行为习惯,这对教师的道德权威冲击是直接的、强烈的、深刻的,引发传统型教师道德权威、法理型教师道德权威、感召型教师道德权威的失落”[18]。消费社会中的教育产业化使接受教育作为一种消费行为,教师与其他普通职业无异,只是提供教育产品的劳动者。教育法律法规将教师职业定位为专业技术人员,从一些硬性标准,如教师资格证、职称评定、专业技术等各种角度衡量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虽然这种技术化的衡量尺度列出了有关师德的指标,但是很难真正判断和考量教师的道德水平、人格魅力、理想信念等,教师道德隐去以致成为“悬搁”之物。
分析教师道德权威式微的原因,一方面由知识的道德价值和伦理价值衰落造成。“知识既有能力性和思维逻辑,也有伦理性和伦理逻辑。知识的伦理性是知识价值观的灵魂,是文以载道和教学具有教育性的基本途径和方式”[19]。随着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成为主流价值取向,知识成为符号、信息的代名词,“文以载道”的伦理价值失落。教师作为“传道者”所传之“道”已失去根基,其自身的“师道”及权威形象必然随之消解。另一方面是师德自身的沦落所致。师德沦落和师道沦丧是整个社会道德衰落的一种体现,体罚学生等教师的失范和违法行为时有出现,并进入大众视野,造成社会对教师职业,乃至整个教育行业的质疑及信任感缺失。人工智能教育推进了教育民主化的进程,人们对教育新闻有了更多的知情权。与此同时,加速社交媒体对教育信息和各项事务的曝光度,大众媒体将教育景观作为消费的对象,以非理性的情绪炒作学生坠楼、招生腐败、学术不端等热点问题,形成对教师职业形象,乃至中国教育的“妖魔化”与“舆论审判”。网络信息铺天盖地,教育舆情的研判和对突发事件把控常常较为滞后,教师的权威形象成为社会过度消费的对象,权威消解是其必然结果。
三、路径探析: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重塑教师权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论断,是新时代教师所必需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素养要求。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教师职业给予崇高定位,“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时代重任,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石”[20]。人工智能时代权威的失落和消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么人工智能时代还需不需要权威?需要什么样的权威?通过何种途径重塑权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后现代性之教师权威“返魅”
现代性的“祛魅”充分肯定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意味着一种支配关系,即统治的合理性,从“人—人”交往关系转向“人—技术—人”之间的角逐。“技术本来是人类文明的象征,然而祛魅之后的现代技术却推动着人类文明发展到了野蛮的境地,使技术越来越失去人性和理性”[21]。教师权威的“祛魅”消解了权威的合理性,“技术至上”“见物不见人”的人学偏离境遇导致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如何认识科学技术的人文化倾向,处理好人与自然、与万物、与技术的关系成为重建教师权威的前提和关键。此时,技术的“返魅”(reenchantment)进入人们的视野,为教师形象重新披上“魅”的光环,让我们看到技术的温情,实现人性和神性的统一。教育的返魅从教育和人的超越性角度出发,将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理想和乌托邦式的精神追求,重视教育的道德意蕴和道德责任,强调科学技术的人文化倾向,在技术时代倡导人的教育和人文教育。“返魅”需要我们重审权威的意义和地位,“真正的权威来自于内在的精神力量,一旦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消失,外在的权威也随之逝去”[7]70。教师个体的良知、对教育的信仰等超越性认识成为“返魅”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教育信息化步入2.0时代,互联网+教育、人工智能、大数据、超级算法等技术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环境下的教育形态改变了传统教与学的方式。大数据驱动精准教学、为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提供支撑。在线教学的兴起使海量信息不断积累和增长,如此次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平台为教学提供了技术支撑,保障教育教学顺利开展,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后疫情时代线上与线下教育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时代需要呼吁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人之于物、人之于技术的优越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们也许还是需要重返人文,重思古代的‘学以成人’,那‘人’是高于物、超越物的人,是能够把控物——其实首先是能够把控人自己的人,当然,今天人还不仅需要学会调节‘人际关系’,还要学会调节好‘人机关系’”[22]。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造成人被抽象化、符号化和工具化的严峻挑战,这需要我们重建人的价值世界和人之为人的本质与价值向度。
(二)以承认的尊严确保权威的正当性
承认理论是霍耐特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核心。在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的社会哲学基础之上,霍耐特阐发了承认与多元正义(包括教育正义)、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将爱、法权、团结作为相互承认以消除社会病理的三种形式,也是师生交往中确保双方尊严和自由的主体间性条件。承认是确保主体道德尊严的前提,“道德人”作为自身的目的和本质,享有至高无上的尊严。从承认理论出发,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教师权威正当性的重要内容。承认与尊严是保障权威合法性的前提,“真正的价值‘权威’只有与一种‘尊严’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才能在确证自己‘权威’的同时,有效担当起合法性实现的基础保证”[23]。承认的尊严向绝对权威发出挑战,消解权威至上导致的社会蔑视及主体之间关系的异化与物化。“承认道德的基本动机在于,追求人格完整、反抗社会蔑视;而追求人格完整、反抗社会蔑视又是承认理论的基本目标”[24]。人工智能时代人的自然生命延展至信息技术领域,获得数字生命。教师在师生互动过程中通过分层、控制等实现“话语霸权”,歧视和社会蔑视依然存在。为追求个体本质和人格完整以对抗社会蔑视和绝对权威,承认的尊严是必要且合理的,也是确保权威合理性、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前提。
(三)以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彰显新型教师权威
我国“师道尊严”的内涵从“师严道尊”到“尊师重教”的历史变迁和演进,其中有某种历史继承性和内在统一性。儒家文化推崇“师道”,虽然古代教师权威有工具主义倾向,不是基于信任的服从,是“学而优则仕”理念下对教师法理权威和知识权威的一种屈从。荀子“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高度肯定教师的地位,韩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强调“师”与“道”的高度统一。中国传统教师权威中更为重视教师的身份和特权,具有等级性和不平等性。新时代背景下重回“师道尊严”和“尊师重道”的良好传统,需要弱化“师道尊严”的政治性,强化其人文性和价值向度。人工智能时代要继续发扬我国尊师重教的历史传统,强化“兴国必先强师”的重要战略意义,是几千年前荀子“重师”传统穿越历史的叩问与回应。我国学者提出世界性的尊师日,尊师重道、重教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将古典权威、传统权威与新型权威进行整合。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专业发展,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人工智能时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对各行各业造成冲击。曾有数据分析各种职业在未来社会的“被淘汰概率”,但教师被教学机器人取代的可能性仅为0.4%。当传统教师权威和教师角色遭遇挑战和危机,需要重新审视教师的地位,在变与不变中树立新型教师权威。“教师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所具有的知识传授、信息收集、数据分析等功能必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所具有的指令性‘指导’角色将逐渐削弱直至消失,承担的‘教育角色’(诸如能力培养、价值引领、情感感化、信念确立、德性养成等)将会凸显”[25]。我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立功和立言可依靠信息技术实现,但立德需要教师的情感浸润、榜样树立等才可以达成。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作为“人师”“传道者”的新权威得以确立,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给学生以鼓励、倾听、眼神交互等等,这些是教学机器人所无法取代的。
(四)教师权威与平等、民主及学生自由间的张力
教师权威并不必然造成师生地位不平等、限制教学民主、削弱学生自由等不良教育影响,而权威主义、滥用权威是教育交往中需要规避的。教师运用信息技术,如智能教学测评系统对学生进行分层、控制,及技术自身带来的“数字鸿沟”,加剧了师生交往中的不平等和教育的诸种非正义。教师权威的本意是促进师生交往中的平等,首先是师生间的人格平等。讲自由并不是摒弃权威,权威是自由的保障,以权威促进学生自由,教师权威体现在“平等中的首席”和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合作者。“作为平等者中的首席,教师的作用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构建,从外在于学生的情境转化为与这一情境共存。权威也转入情境之中”[26]。人工智能时代学生平等与权威之间存在适度的张力,同时,与教学民主、学生自由密不可分。
师生关系的民主化要反对权威主义,注重实质权威和内在权威,以教师的道德感召力和人格魅力,增强教师权威中威信成分,减少权力控制。人工智能时代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由、平等、民主意识。运用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共享,以更为便捷的方式,使全体学生共享教育教学的成果。如教育“最后一公里”的实现,加速了互联网在各个地区,乃至农村偏远地区的普及,保障学生可以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线学习。权威与学生自由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正如涂尔干认为权威与自由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相联系的,“老师的权威就应该用来赋予儿童的这种自主性。因为教师的权威不过是义务的权威与理性的权威的一个方面而已。”[27]权威的最终目的是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承认学生自由是其前提。“教师所享有的权威总是有着自相矛盾的特点,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确认其权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由承认知识合法性的基础上”[28]。需要将教师权威转化为一种积极的教育影响力,以促进学生自由。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带来教学各个领域的变革,人工智能时代教与学的方式、师生关系等发生变化,根深蒂固的教师权威也面临失落和消解,教师权威的危机与重建、“祛魅”与“返魅”是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张力。权威作为人类弥久存在的社会现象,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人工智能背景下要正确把握技术和权威自身的限度及其张力,防止过度“祛魅”造成教师权威的旁落,或过度“返魅”造成教师权威压制学生的平等、民主和自由发展。总之,权威中强制、压制、权力控制的成分应该消解,权威作为一种内在精神和理想信念应发挥其积极作用,进而让人们享受到技术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