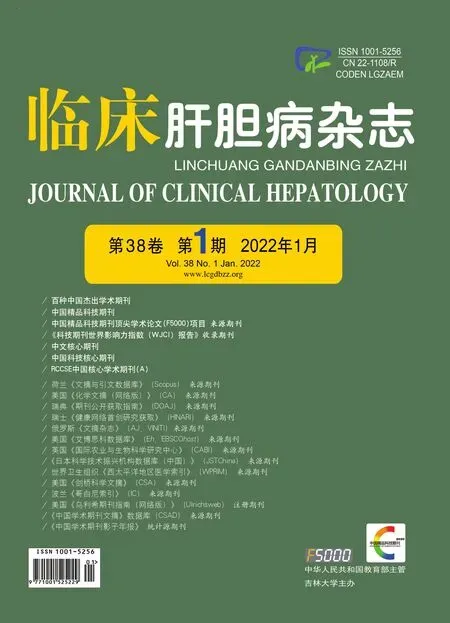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所致肝脏不良反应的研究进展
王 宇, 李钊颖, 李 爽, 刘成海
1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消化科, 上海 201999; 2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成都 610000;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a.肝病二科, b.肝病研究所, 上海 201203;
肿瘤的发生与抑癌基因突变及免疫监视失能相关[1]。基因突变重新编辑后的癌细胞抗原性较弱,而且在肿瘤微环境局部存在复杂的免疫抑制或免疫逃逸,这些均是造成难以有效激发免疫反应的原因。肿瘤的免疫疗法通过再次激活免疫抑制,恢复免疫系统的免疫监视功能从而达到抗肿瘤作用,但会破坏机体免疫耐受平衡,从而出现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irAE),其中免疫介导的肝炎(immune-mediated hepatitis,IMH)是重要事件之一。本文从肿瘤免疫疗法作用机制及类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肝损伤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损伤机制、病理模式、治疗措施方面进行论述。
1 ICI抗肿瘤作用机制及类型
免疫检查点是指位于效应T淋巴细胞上的一些激活性和抑制性受体调节开关,激活可以使得T淋巴细胞处于效应状态,抑制可以使得T淋巴细胞处于沉默状态。T淋巴细胞要完全激活,需要多个步骤,包括抗原特异性细胞的克隆选择、淋巴组织中的激活和增殖,然后在靶组织中执行它们的效应功能,这些步骤中的每一个都受免疫检查点蛋白的调节[2]。肿瘤突变负荷产生肿瘤新生抗原,肿瘤上调程序性死亡受体(programmed death-1 receptor,PD-1)等免疫检查点的表达,从而发生免疫逃逸[3]。目前临床上应用的ICI有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 4, CTLA-4)和PD-1及其配体(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的单克隆抗体。
ICI通过抑制T淋巴细胞沉默抗体,激活T淋巴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免疫应答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CTLA-4检查点抑制剂抗癌作用机制一方面增强对肿瘤细胞具有杀伤效应的T淋巴细胞活性;另一方面抑制调节性T淋巴细胞活性,使辅助性T淋巴细胞(Th)或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重新识别肿瘤新生抗原。PD-1广泛存在于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和Th上,PD-1的PD-L1和PD-L2两种配体,除了存在于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的表面,其在肿瘤细胞表面也有分布,肿瘤细胞表面的PD-L1和PD-L2配体会抑制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并上调调节性T淋巴细胞的活性从而使肿瘤细胞发生免疫逃逸。PD-1与PD-L1的抗肿瘤机制在于重启淋巴细胞增殖以及细胞因子的产生,激活对肿瘤细胞的免疫再识别及杀伤[4]。
2 ICI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
目前依据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CTCAE)对肝脏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严重程度分为4级:1级(ALT 或 AST>1×ULN~3×ULN),2级(ALT或AST>3×ULN~<5×ULN),3级(ALT或AST>5×ULN~<20×ULN)和4级(ALT或AST>20×ULN)[5]。ICI肝损伤主要在首次治疗后2个月内出现,2%~5%的病例出现AST或ALT升高,而肝损伤中1%~4%的病例中检出了3~4级的转氨酶升高[6]。
CTLA-4抑制剂引起肝炎发生率小于10%,PD-1/PD-L1抑制剂发生率约5%,联合使用2种免疫药物(CTLA-4和PD-1/PD-L1)的患者更容易发生肝毒性[7]。使用抗PD-1、PD-L1抗体治疗后,任何级别的IMH发生率为7.4%~14%,联合治疗为12.2%~37.8%[8]。具体涉及单药品种而言,接受常规剂量伊匹单抗、纳武单抗和派姆单抗单药治疗的患者肝炎发生率为5%~10%(其中3级反应1%~2%)。伊匹单抗 3 mg/kg和纳武单抗 1 mg/kg联合治疗的患者肝炎发生率为25%~30%(其中3级反应15%)[9]。
在接受ICI治疗的患者中,4%的患者观察到≥3级irAE肝炎,其中女性和ICI治疗史与≥3级irAE肝炎的发生率显著相关[10]。日本一项研究[11]发现,使用ipilimumab和初始ICI给药后24 h内出现发热是免疫相关肝损伤的预测因素。IMH风险可能是剂量依赖型[12],且联用ICI可增加IMH风险,当抗CTLA-4和抗PD-1药联用,肝损伤总体发生率28.8%,3~4级不良反应可达17%[13]。肿瘤本身也会影响其发病率,恶性黑色素瘤患者往往更容易发生IMH[14]。此外既往的自身免疫病史以及肝脏疾病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亦是IMH的风险因素[15-16],而且人白细胞抗原也在ICI的疗效和肝损伤易感性中发挥重要作用[17]。
3 ICI导致肝损伤的机制
在发生irAE的患者中一般抗肿瘤效果较好,这或表明诱导抗肿瘤免疫与自身免疫不良反应之间存在共同机制[18]。ICI导致irAE的机制为活化的T淋巴细胞攻击正常肝组织、自身抗体的产生、CTLA-4脱靶效应导致的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以及免疫细胞释放炎性因子介导组织免疫损伤[19]。
有证据[9]表明,PD-L1/PD-1通路以及CTLA-4对肝脏环境中的免疫调节很重要,通过调节CD8+T淋巴细胞活化和凋亡有助于维持耐受性。其中,CTLA-4基因多态性与肝脏自身免疫疾病之间存在关联,例如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和AIH。在正常的生理条件下,免疫检查点通过抑制树突状细胞介导的CTLA-4 途径的活化或通过在炎症部位诱导T淋巴细胞衰竭PD-L1/PD-1途径来预防自身免疫事件的发生。ICI通过靶向阻断肿瘤免疫逃避发挥作用,但会破坏机体免疫耐受平衡,从而引起IMH,ICI所致IMH是间接药物性肝损伤,为免疫反应增强所致。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在免疫治疗相关肝炎的发病机制中起核心作用[20],其机制为细胞毒性CD8+T淋巴细胞导致肿瘤细胞的破坏,并从正常组织中释放肿瘤抗原、新抗原和自身抗原。这被称为表位传播并导致免疫耐受性降低。这种效应与Th1和Th17 T淋巴细胞的激活一起导致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包括IFNγ和IL-17[21]。因此,细胞毒性的CD8+T淋巴细胞的错位攻击以及炎症因子的释放可能是造成肝损伤的机制。
4 ICI导致肝损伤的临床表现及组织学特征
RUCAM量表与结构性专家诊断程序对于ICI的诊断是支持性诊断而非排除性诊断,因此IMH的诊断更多需要排除其他造成肝损伤的混杂因素。如果患者患有基础病毒性肝炎或AIH,则IMH的诊断则具有很大复杂性。HBV DNA阳性的患者应在ICI治疗之前进行抗病毒治疗。肝功能Child-Pugh A级或者B级(≤7分)、HBV DNA小于500 IU/ml并且ECOG PS评分在0~1分的晚期肝恶性肿瘤患者可以一线选择阿替丽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进行治疗[34],并且治疗期间很少出现HBV DNA再激活但ICI对于晚期肝癌的疗效仍有待提升[22]。对于未经治疗的HCV和其他原因导致肝酶升高,应进行肝活检进行区分[23]。
累及肝脏的irAE临床表现相当异质,类似于自身免疫性药物性肝损伤。肝脏irAE患者与AIH或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 患者在临床病理特征方面:血清转氨酶水平无显著差异,但AIH患者的血清IgG和抗核抗体水平高于GVHD 或肝脏irAE患者。肝脏 irAE患者表现为肝小叶的炎症,而AIH 患者表现出门静脉和小叶炎症。免疫组化分析显示,在肝脏irAE和GVHD患者的小叶区域中,CD8+T淋巴细胞浸润占主导地位,并且表达叉头框蛋白P3(FOXP3)的调节性T淋巴细胞积累有缺陷。相比之下,AIH患者的门静脉周围病变的特征在于CD4+T淋巴细胞、CD8+T淋巴细胞、CD20 B淋巴细胞和FOXP3调节性T淋巴细胞的浸润[24],浸润细胞主要由CD8+T淋巴细胞组成,并且与肝细胞坏死呈正相关[25]。临床上,偶尔会出现右上腹部的疼痛和发热,而影像学检查无特征性意义[26]。
由于发病机制的复杂性,irAE相关的肝组织学表现是异质性的,包括小叶性肝炎、脂肪变性和脂肪性肝炎以及胆管损伤[27]。但组织学除了在诊断和评估肝损伤的严重程度外,也可区分抗PD-1/PD-L1单克隆抗体和抗CTLA-4单克隆抗体的毒性[28]。抗PD-1抗体引起的肝实质损伤主要表现为伴有轻度小叶浸润的小叶性肝炎[28-29],但在使用抗PD-1抗体治疗期间胆管损伤可能导致由淋巴细胞浸润性胆管炎引起的胆管消失综合征[30]。派姆单抗和阿替丽珠单抗不仅表现出小叶性肝炎,还表现出硬化性胆管炎、淋巴细胞管损伤和肉芽肿性肝炎,其原因或是PD-1与PD-L1相互作用受阻导致CD8+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紊乱亢进造成[31]。在较严重IMH的病例中,较多CD8+的T淋巴细胞聚集在汇管区及肝窦内,且有部分肝窦内皮细胞表达PD-L1[32]。显著的肝窦内炎症细胞浸润和中心静脉损伤伴血管内皮炎症可能有助于诊断伊匹单抗造成的肝组织学损伤[33]。CTLA-4抗体肝损伤病理特征显示活动性全小叶肝炎,伴有肝小叶大量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聚集的组成的混合炎性浸润。巨噬细胞可形成松散的“微肉芽肿”,并见分散的嗜酸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还可见融合性坏死灶、多灶性肝细胞凋亡和气球样变性[29]。
5 ICI肝损伤的治疗
IMH是对肝组织过度免疫反应或免疫耐受突破所致,停止ICI的肿瘤免疫疗法是治疗IMH的关键环节。但除了停用肝损伤药物外,由于阐述免疫发病机制的免疫基础研究较少,导致治疗选择的困境及异质性。有经验表明,轻-中度肝细胞损伤型和混合型药物性肝损伤,炎症较重者可试用双环醇和甘草酸制剂;炎症较轻者可试用水飞蓟素。胆汁淤积型DILI可选用熊去氧胆酸。有报道腺苷蛋氨酸治疗胆汁淤积型DILI有效。上述药物的确切疗效有待严格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加以证实[34]。目前绝大多数irAE推荐皮质类固醇作为一线用药选择,对于二线治疗依然推荐的是较为宽泛的靶向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细胞因子和自身抗体的药物,但由于缺乏依据免疫组织病理学进行的分层治疗选择,而临床应用性不高[35]。
皮质类固醇通过降低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等炎症细胞的活化、增殖、促进凋亡,来发挥免疫抑制效应。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南根据《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CTCAE) 4.03版》中AST、ALT或总胆红素的分级对ICI相关肝脏毒性进行分级, G1指ALT/AST<3×ULN、TBil<1.5×ULN,通常可继续使用ICI;G2(ALT/AST 3×ULN~5×ULN、TBil 1.5×ULN~3×ULN)需暂停ICI,予口服泼尼松0.5~1 mg·kg-1·d-1,1个月内逐渐减量;G3(ALT/AST 5×ULN~20×ULN、TBil 3×ULN~10×ULN)和G4(ALT/AST>20×ULN、TBil>10×ULN)需永久停药,使用甲强龙1~2 mg·kg-1·d-1)静注,若3 d后仍无改善则添加麦考酚酯0.5~1 g (2 次/d)或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等。但长期、较高剂量地使用糖皮质激素可能对治疗产生负性影响且目前并没有大规模的临床数据证明免疫抑制剂的临床获益程度[36]。
通常选择单克隆抗体英夫利昔单抗作为对皮质类固醇耐药不良事件的补救治疗,但不推荐英夫利昔单抗治疗肝炎不良反应,因为英夫利昔单抗有致肝细胞毒性及肝衰竭的潜在风险[37-38]。麦考酚酯通过耗竭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中的鸟嘌呤核苷酸抑制细胞增殖,因此可以抑制免疫应答和抗体产生。有研究[39]报道,麦考酚酯可作为皮质类固醇耐药的补救治疗措施。亦可以使用能使淋巴细胞、单核细胞、自然杀伤性细胞耗竭的ATG治疗皮质类固醇耐药的肝脏不良反应。研究[40]显示ATG应用于IMH时,外周循环淋巴细胞CD4+T淋巴细胞被ATG严重消耗,而CD8+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NK细胞和单核细胞相对较少。
6 展望
ICI通过激活抗肿瘤效应细胞,从而控制肿瘤生长和预防肿瘤复发的作用。但激活ICI往往在靶向调控途径的同时也会破坏外周免疫的稳态,从而造成一系列免疫相关性疾病。ICI造成的肝损伤是免疫新时代抗肿瘤疗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 ICI 对大多数癌症的使用越来越多[42],其免疫相关肝毒性的发生率将继续上升。但IrAE的临床表现及影响多样且复杂,ICI应用患者的管理往往需要在疗效、毒性和特定治疗之间取得平衡,并积极开展多学科协作。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王宇负责课题设计,资料分析,撰写论文;李钊颖参与收集数据,修改论文;王宇负责拟定写作思路,刘成海、李爽指导撰写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