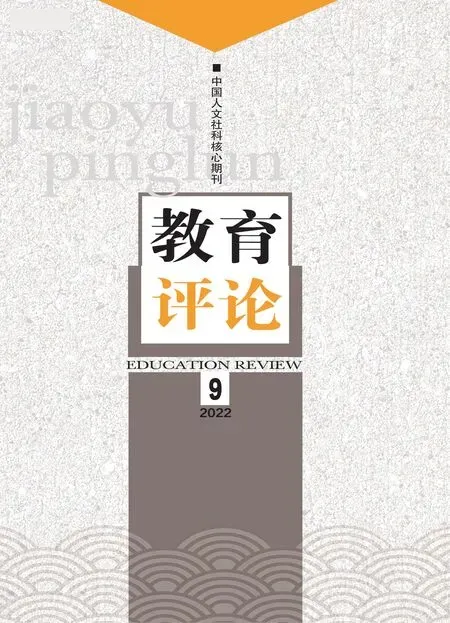老子无为思想的家庭教育意涵
●田 锐
就各级各类教育来说,越靠前的教育往往越重要。作为起点的家庭教育,自古到今都备受家长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因为家庭教育一旦出了问题,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且后来的学校教育也不好予以弥补。源于亲子之间固定的血缘关系以及时刻相伴的时空关系,在面对孩子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家长总是既紧张又焦灼,不能不管,又不能硬管,不能限于一时一事,又不能忽略一时一事,教育效果也易产生“过”或“不及”的偏差。老子的无为所蕴含的家庭教育心理思想适合用于处理这类深不得、浅不得的焦灼关系,而且引起的认知和行为偏差也相对小些。理解并探讨老子无为思想里的意涵,对家庭教育有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无为之家庭教育价值
(一)“无”的激发机制:因为无,所以想有
在老子的哲学体系里,无为之“无”并不是什么也没有,而是一种“‘无物’的存在”,又“是万物存在的依据”,[1]“无”是“有”的原始状态和产生根据。弗洛伊德用“不被知觉”、“潜伏”[2]等来描述“无意识”的“无”,也是强调“无”在暗处起作用的价值。美国汉学家查德·汉森从“存在与缺乏”的相对意义上把老子的“无”理解为“缺少某些事物”,又说“道家思想的迷人之处就是赞赏缺失的价值”。[3]由此老子的“无”含有“缺少”的意味,是一种匮乏而又期待填补的状态,因而“无”暗含一种心理机制:因为“缺少”,所以才凸显其“有用”。就如同空房间一样,正因为空无一物,才显示出能放置家具的功用。“无之以为用”,凡是匮乏的都有待于补充,都蕴藏着可开发的潜在可能性。需要源于缺乏,又促生了追求的动力,匮乏之处必然蕴含生机。所以老子说“有生于无”,亦即:正是因为“无”,所以才想“有”,继而经过努力才会真的“有”。
(二)“为”的连锁反应:从对立到预设对立
老子的无为之“为”即“伪”,指与天性相悖的那些不恰当的想法或做法。“‘为’与‘伪’古通用。凡非天性而人所造作者,皆‘伪’也”[4]。老子对刻意地“为”或“不为”都持排斥态度,“智慧出,有大伪”,“人多伎巧”,他把不遵循自然之理的妄为、乱为、强为、多为等伎巧称作“大伪”。尽管生活中一般意义的“为”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在“为”的过程中掺杂了违背自然的欲望,“为”就异化成“伪”。比如,家长看不惯孩子慢腾腾地做事,急不可耐地出手帮助,拔苗助长就是“伪”。
“伪”易引发亲子对立。源于人的向好本能,家长要求孩子“好了还想更好”的“伪”愿望几乎是欲壑难填的。为了敦促孩子的进步,有“伪”的家长往往产生错误的执着,会更多地关注孩子的缺点、错误等负面特征,这就不自觉地给亲子交往注入了对立的成分。当孩子的缺点越找越多时,家长“会忽略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尽管有时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是很明显的”[5]。即:只注意缺点,孩子的优点就被忽略。这些意识上的对立都会给亲子交往带来障碍。
“伪”易造成恶性循环。一方面家长因为不断地否定孩子而陷入批评怪圈,形成批评孩子的惯性,强行管控的“伪”的程度会逐渐提高。另一方面孩子则因为讨厌家长的教育意图而产生本能的抑制反应,甚至提前预设反对态度。结果造成越管越管不住,越管不住就越用力管。如此发展下去,家长的教育行为不但起不到督促和约束作用,反而造成亲子对立的恶性循环。
(三)无为家庭教育内涵:引导而不打扰
无为即“无伪”,也就是去除“人为”之“伪”,“不塞其源”[6],尽力在顺应事物本性的基础上“任物之自为”。[7]顺应本性是指引领方向,而任其自为则更强调不多加干涉。那么,家庭教育中的无为就是引导而不打扰,强调要去除那些违背孩子自然天性的意识和行为,顺势而为。
1.引导:以心虚心,使“伪”趋无
以心虚心,即以意识引领意识,让自己产生匮乏感,马斯洛表述为“让自己的大脑虚空以待”[8],是人的意识能动性发挥作用的结果。
家长完全可以自觉、主动地减少自己对孩子的拥有感、优越感,恰如“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即不居于“自己永远正确”,不居于“孩子是我的”,不居于作为养育者的功劳。减少不该为的,就便于选择该为的。如此,家长才能真诚、放松地同孩子一起去面对和感受生活,陪伴孩子并与之共同成长。
家长也完全可以自觉、主动地去除“孩子必须这样那样”的念头,通过“损之又损”而“致虚极”,达成“婴儿之未孩”“专气致柔(10章)”这种近乎“无”且拥有无限生机的状态。纯净的婴儿就是如此,他们没有人为的利害忧虑,有的只是无目的而又简洁地专注于当下的探究。“孩子以新鲜、纯真、率直的眼光看待生活,这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但多数人在社会适应中逐渐失去了它,而少数人却能失而复得,能像儿童一样富有创造性地观照世界”[9]。
2.不打扰:以无促有,使“有”自发
匮乏呈现出可供填补的“无”,从而显示“无”的有用性。因此,不管是现实性的“无”,还是意识性的“无”,只要处于“无”,就可容纳更多想有的。孩子如果知觉到自己有所欠缺(无),就会产生弥补亏空的动力(有),特别是当发现确实该有而又确实没有的时候,其焦虑、紧张感以及弥补的愿望和动力就会更强烈,这便是“有生于无”的过程。反过来,谦虚和以退为进的“退”便是意识引领的“此有彼无”的过程。由此,“有”和“无”一直互相引发并凸显对方,从而“有无相生”。
不管是“无中生有”还是“由有趋无”,“有”必须带有适度或顺势的意识成分。匮乏是“无”,因匮乏而生的动力就是“有”,但这个“有”所代表的动力处于中等偏上才是适度的动机,即让“有”产生于自然而然之中。同样道理,谦虚和以退为进的“退”也是在自然而然之中由“有”趋“无”。“有”的产生与“趋无”的效果都不是强求的,而是接近于自发的。家庭教育中的无为所强调的引导就是顺势让孩子发现自己缺少什么,从而近乎于自发地产生适当的前进动力。这个自发的过程必须在孩子尝试的过程中才能有机会出现,这是家长无法替代的。
二、“无为而无不为”之家庭教育目的
(一)无动机:天道无为的理想化目的
“自从达尔文和杜威以来,思维总的来说一直是自动地被看成是用以解决问题的,即机能性和有动机的。”[10]其实,对人类行为来说,有动机是绝对的,无动机是相对的。天道无为的目的意识是无动机的,这是一种理想化状态。人类无法企及这种状态,因为人类的意识时时刻刻都会参与到行为之中,根本无法像玫瑰散发香味那样,纯粹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本性。但是,如果减小动机强度,一直减小下去,终点就是无动机,那么比较靠近这个终点的动机就可以理解为相对的无动机,人可以使自己处于这种相对无动机的状态。“人的目的可以是不为他自己所知的”,[11]此时目的并非没有,只是没在明确的意识范围之内。老子的无为、“致虚极,守静笃”就是通过“损之又损”而使目的意识趋无,从而让行动近似于自发地从身体里自然而然流淌出来。一些心理现象可说明这种状态:内隐学习是发生于不知不觉之中的一种学习;人们仰仗技能、习惯带来的适应性无意识在社会上生存,同时并不需要清醒的意识,[12]就跟人们平常走路不一定非得大脑有意识地指挥一样;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阐述了“自带目的性”的状态,他说人们“通常为了自身目的去做某些事情,而不是为了达成一些日后的外部目标”。[13]总之,无为自带目的而看似无目的,虽然奔目标而去,但没有志在必得的那种强烈,就像婴幼儿自带目的、无拘无束地做他们喜欢做的游戏一样,没有刻意追求,只是为了游戏,无意图而又合乎意图、无目的而又合乎目的,这是受自身原发性目的的无意识推动而进行的自发行为。
无动机的目的意识有引领作用。尽管理想化的目的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如果把它当作追求的目标,它就可以发挥引领方向、提供动力的作用,并自动处理行为的方向和动力大小。马斯洛就带有崇拜意味地评价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无动机范畴的”道家风范能加强“对一个现象的多面性的非功利性的感知”。[14]减少功利性,人的感知能力会更强。无为就是不断地对功利意识“损之又损”,尽量向无动机、理想化的目的状态靠近,促成无意识追求,并收获“自动”成果。婴幼儿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这种无意识的、自发的、不费力的、不做作的特点,而正是这种非刻意和非功利的状态才使孩子在放松和静默之中更便于获得观察对象的真实面貌。家长对孩子的爱也须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表达,刻意地去爱反而降低了爱的品质。
(二)低动机:人道无为的现实性目的
人道无为必然处在“有为”的层面,但老子并不主张设定“强烈”的目的意识,他反对“用强”,“强梁者,不得其死”,高强度的目的意识会使人走向死胡同。耶克斯-多德森定律(The Yerks_Dodson Law)也说明中等动机水平的行为所带来的效率更高。老子认为,若以“虚其心”“弱其志”而致柔,则“柔弱胜刚强”。但“虚其心”至“虚极”是正常人难以企及的,因此人们在无法做到完全非刻意的情况下,只能尽量地“非刻意”,即通过“弱其志”,把“为”的动机水平、紧张度、努力程度之类的“志”的指标,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上,或者说,用降低、淡化目标强度的方式来反向达成目的。如此,在降低目标期盼程度的基础上尽量努力向上争取,既可减少思想负担,又能提高无不为的可能性。孩子在这种状态下学习,会精神放松,思维活跃,学习效率反而会提高;如果紧张度太高,动机过强,就会引起思维的停滞,反而不利于目标的达成。
因此,具有现实意义的目的意识往往是低动机的,低动机的行为最具可行性,也最有效,为无为更容易达成无不为。老子提出的为无为是用无为去“为”,尽管也要求“有所作为”,但其目的意识带有趋向于“无”的低动机性,亦即减少刻意程度,或者说淡化甚至似乎已经忘记了目的,刻意地“为”或“不为”都是老子反对的。人们专心做事时也会忘记“为了什么而做”,这都是为无为的表现,也就是“辅万物之自然”。在儿童的自然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的目标就是辅助儿童自然成长,家长是无为的辅助者,而不是 “强为”的命令者,也不是“乱为”的麻烦制造者。家长要以非刻意的、低动机的目的意识使教育“为”于无形,让孩子在自然而然之中达成某些自然愿望。
心理学的许多实验结论都印证了这类非刻意的、低动机的目的意识的功效。布朗(Brown)和瑞安(Ryan)以实验证明了刻意程度与障碍的关系:“专注(一种忘我状态)增强与心境障碍和压力降低相关联”。[15]如果专注于当下的情境,就可以在开阔流畅、无拘无束、无目的的坦率之中,超乎寻常地掌握和利用可靠信息,更利于达成目的。心理学家丹尼尔·魏格纳(Daniel M. Wegner)也验证了太刻意努力所造成的“讽刺效果”:“我们喜欢的不少目标,一旦刻意追求的话,可能被干扰和压力破坏,最后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适得其反。”[16]
维果茨基指出,在孩子已经具备的现实水平和可以达到但还没达到的潜在水平之间是其“最近发展区”,从这里选取稍带难度的内容让孩子尽力有所“为”,这也是为无为。“跳一跳够得着”的任务是孩子能完成,也容易超越的,在此付出一定努力可达成“无为而无不为”。心理学家维纳研究成败归因时提出了“可控与不可控”的研究维度,由此也可理解老子的无为:让孩子在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上做出努力,这是为无为,但要孩子在自己不可以控制的因素上做出努力,那就是“有伪”。总之,稍稍调低“志”的强度,更利于问题的解决。“我无为,而民自化”,家长塑造的相对宽松的教育氛围能带来更佳效果。
三、为无为之家庭教育途径
(一)以退为进:以处下而为无为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他物争着上进,而水却甘愿“下流”。在老子的思想体系里,知雄雌而后守雌,知荣辱而后守辱,知大小而后居小,知高低而后就低,知动静而后守静,知利弊而后不争,都是处下方略。与处高相比,处下是“去甚、去奢、去泰”之后,把自己置于退无可退的“低洼之处”,这里再往后退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反向的进步空间却因为退而增大。处下是更容易导致进步的积极策略,盈满则没有发展的余地或前途。
吴澄《道德真经注》谓“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17]由此,处下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一是被动处下,本身就在下或只能在下;二是主动处下,身虽居上,但心处下,即主动从上“走”到下。又鉴于真假程度的差别,主动处下又可分为假意处下和自然处下。老子所主张的是无做作的自然处下。成长中的孩子大多不愿意被家长教育,或者说不喜欢家长总想教育别人的意图。因此家长的“处高”容易引发孩子的厌烦和抵触,家长的假意处下也往往因为情绪的敏感传递而容易被孩子识破。如果家长从高处绕下来,允许孩子按自己的想法去说、去做、去探索,其教育效果就比总站在制高点上强行命令要好得多。不过,在分析孩子存在的问题时,家长也需要处高,以便能找到使孩子发展的根本点和切入点,但教育方式和具体教育过程应该处下。因而处下的实质是“从高处了解,到低处解决”,[18]亦即思想处高,行动处下。当然,家长也需要注意,了解孩子是处下的前提,不然就没办法知道应该“下”到哪个地方。
(二)协同共进:以不争而为无为
老子的“处众人之所恶”就是“为而不争”。争则情急,急则生误。“夫惟不争,故无尤”,不争高下,可以平静和缓地面对真实问题,降低了焦躁程度,没有那么多烦恼,错误也会减少。自然界从来“不强迫任何事物去进行非它自己的成熟了的力量所驱使的事”,“在自然的一切作为里面,发展都是自发的”。[19]幼儿做事时,他们以“能做”为前提,以“想做”为缘由,自觉、自发地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他们在这种放松的状态里与事与物达成自然呼应,只享受做事的过程,没有争的心态,其成长既是自然的又是必然的。不争虽不以获利为目的,但获利是不争的自然结果。
“争”更多时候是源于比较,“不尚贤,使民不争”,清世祖福临注“尚贤,则民耻于不若,而至于争。”“比较”在家庭教育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不同类型的比较会有不同作用。横比是孩子跟同伴比较,易发现差别;纵比是孩子自己跟自己比,易看到变化。纵比一般能敦促孩子向好处发展,因为这种自我比较不得不面对有缺点的自己,同时还须自我促进;而横比呢,其过程里或多或少会有被别人比下去的担忧,易出现诸如嫉妒、急躁之类的负性情绪。相比之下,横比的负面影响多一些,但人们不好避免总是进行横比的习惯。因此,家长最好是让孩子在横比之后,及时过渡到纵比,以促成那种淡化竞争的平和心态,使其在轻松愉快之中不焦躁地奋斗。
(三)留有余地:以不言而为无为
《说文解字》:“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直接讲说叫言,议论辩驳叫语。“不言”即别说得太直接,换种说法,迂回一点,间接地“言”,意在注重“言”的效果。“行不言之教”即弱化评判中的强求或打击,主张委婉兼具引导。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苏格拉底的“产婆术”都重在启发,而不是只给予评判。评判倾向于划分界限,携带了太多尖锐的锋芒,特别是家长在分析孩子的缺点时,评判只能证实孩子处在错误的那一边,这更多地强化了孩子面对错误的凝重感和压抑感。“事件本身并不会产生评价;我们把评价强加于我们的经历之上,从而创造我们对事件的体验”,[20]如果家长把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言教”标准,也就等同于强行让孩子认可家长“备份”的体验。这类“言”不但不能让孩子信服,而且还会招致厌烦。老子的“不言”有不打扰、不干涉的意味,就是弱化评判,减少打击力度,减小让人生厌的可能性,强调要善于表达,点到为止,深入浅出,“不言而善应”。其实,家长的面部表情、动作、姿势、语气、音量、声调以及自身的修养和生活态度等,都是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都可以代替说教,以不言胜有言。“不言”还体现于启发性的“金言”,关键之处的恰当提示,既能把孩子的思路引向更佳,又不至于扰乱孩子对自己能力的整体判断。只要孩子认定是自己解决了问题,他就会增强自信,也会自觉提高后继行为中的努力程度。相比之下,“多言数穷”,多言有伪。如果给孩子提供过多的评判信息,反而会扰乱孩子的思路,干扰孩子的成就感。因此家长要少点唠叨,多点余味渗透;少点包办,多点留白空间;少点俯视,多点平等交流。[21]
(四)更新区分:以弗居而为无为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家长若做到弗居,就可使教育无痕,不为子知,甚至家长也不自知,使亲子教育在自然而然之中进行并获得成效。老子看重弗居,或许是源于人们主观意识有某些缺陷,因为社会的复杂与精细表现为事物间的差异,人们对此有加以区分和确认的倾向,但人的主观见解里又包含很多偏见与误解。马斯洛曾经说过,人们“根据适合自己个性的标签把所有不能忽视的经验统统加以分类”,他称之为“经验的标签化”,[22]尽管这些标签化的经验渐渐过渡为习惯,并成了人们适应并自动地解决相似问题的可靠办法,但它们也可能会因为被剪裁或歪曲而成为解决新问题的阻碍。如果家长固执己见,就会堵塞一些正确解决问题的思路。美国汉学家查德·汉森也以区分意识来理解老子的弗居思想:“名称指导我们用自己的能力作出区别,由区别指导我们走向或远离其他”。[23]“居”就是根据“经验的标签化”走进一个类别而远离另一个类别,弗居就是减少人为地规定某些许可或禁止范围的意识及随之而来的爱憎之情,以防止区分可能带来的弊端。对孩子来说,通过排他性来掌握一种区分,这是学习,但孩子如果只停留于某些固定的区分,就不会再有进步。规则、惯例和习俗虽然是固定的区分,但其所应有的作用是引导而不是支配,不能人为地要求成长中的孩子“只能如何”。家长不限制孩子去想象和探索更多可能的区分,孩子就不会惧怕事物变化中的各种不确定,也才得以在比较中理解各种规则、惯例和习俗的合理性。
(五)保而不弃:以无弃而为无为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老子的“无弃”并非基于有备无患的功能开发而人尽其能、物尽其用,他强调以包容来对待“不善”,避免责罚,而代以救之保之,是保而不弃。在老子看来,之所以“无弃”,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弃”的理由。每个孩子都是善与不善的统一体,“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善与不善各有其价值,二者因为对立而相互促进,家长和孩子应该“相互重视其各自对立项的存在”。[24]尽管老子区分了善与不善,但他动态地看待其界限,要求在区分之后,不能止于这些区分,应该继而通过包容不善,促进从旧区分到新区分、从不善到善的内部成长。“无弃”这种积极的无差别对待正是罗杰斯“无条件积极关注”的理论所指。不管孩子表现得好不好,家长只能无条件地给予关爱、激励、支持、接纳和珍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助益性的积极关注始终是必须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既要扬“善”,又要救“不善”,孩子才能全面发展,如果家长擅长以鼓励优点来带动孩子主动改正缺点,那么没有哪个孩子是不可救药的。
(六)无偏无爱:以不仁而为无为
对老子的“天地不仁”,王弼注“无为无造”,高亨注“无所亲爱”,庄子注“不多仁恩”,天地的不仁是对万物的等量齐观,没有亲疏之别,不给以特殊对待,不外加干涉,任由万物自发生长。由此,老子的人性价值定向是中性的宽容,强调无偏爱、无区分,即不固定某个区分,学会某种区分,再忘掉这种区分。而很多家长做得正好相反,对孩子爱得太多,爱得没有原则。内心有“仁”的家长应该拥有不仁的胸怀和态度,以客观的情感看待孩子。面对孩子,家长应去除自身先入为主的意愿、希望、焦虑,像自然规律那样无偏无爱,不偏袒孩子的错误,不掩盖孩子的成绩,减少那些世俗的预估、评价和控制,更多地促进孩子的自觉、自动和自发,让孩子放松地在自然而然之中学会自相治理。同时对孩子不同的问题,要给以辩证的助力,“事善能,动善时”,孩子若太向“左”了,家长就往“右”带,孩子若太向“右”了,家长就往“左”带,[25]这也体现不仁的“不偏”、“不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