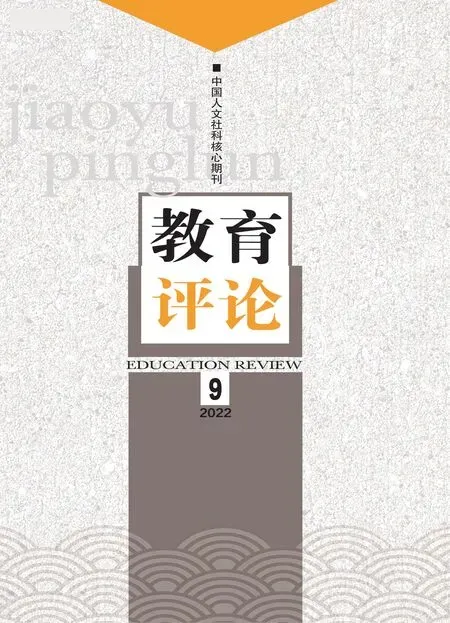教育隐喻研究省思
●皇甫科杰
隐喻是语言的基本特征。早在两千多年前,隐喻就已进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哲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范畴,经典文本中的思想阐述充满了隐喻的形式,因此经典文本常常文风朴素而又微言大义、思想深邃。随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隐喻逐渐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即隐喻是一种认知和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自觉选择语言的结果,标志着隐喻的研究开始从语言领域转向认知领域。教育隐喻自古有之,如经典的“洞穴”之喻、“种子”之喻和“生长”之喻等。教育学科学化进程中,隐喻语言受到科学语言的严厉批评,使教育学语言失去生命的鲜活性,成为冷冰冰的技术语言,以科学思维对经典隐喻命题的批评和反对销蚀了经典隐喻的核心精神。
从“社会”到“人”的主体转向是当代中国教育学40年来的重要理论成果,重塑教育话语的生动性和形象性需要全面省思教育隐喻,这不仅能丰富教育理论的资料来源和教育论述类型,而且有助于教育实践工作者更好更准确地理解和应用教育理论,也有益于教育思想理论的传播与普及。
一、隐喻与教育隐喻
(一)隐喻
隐喻不只是一种语言的修辞格,从中西文化思想对语言研究的历程来看,隐喻被认为是认知的思维方式。在近代哲学转向以前,作为认知思维方式的隐喻研究还是潜行暗藏的。过去对隐喻的认识一直视其为辅助认知发展的语言表达形式,只是具有部分的认知功能,直到近代隐喻认知理论的发展才使其真正进入到认知思维方式的层面。
先秦时期,我国古代思想家普遍将隐喻视为言说、认知和理解的重要方式。[1]儒家肯定了隐喻是言近旨远的喻意表达,以极其简略的语言文字表达深邃的思想意蕴,一字千钧。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2]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3]道家提倡“得意忘言”,弱化语言形式,与儒家“言近”相似但又并不强调简略,重视语言意义与儒家“旨远”相通,因此其主张通过“卮言”“重言”“寓言”,“以不同形相禅”“寓诸无竟(境)”[4]。名家以严谨逻辑见长,以“辩者”闻名于世,特别是对有关名词概念的辨析辩论,独树一帜。名家更是直接道出了隐喻的认知功能。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无譬,则不可矣。”[5]中国汉字自始创就有“意境悠远”的特质,因此所谓“字面意思”往往是浅薄的,真正的思想通常“隐匿”在形象或形式的背后。
西方最早对隐喻的研究始于古希腊哲学的修辞研究,至古罗马时期达到高峰。亚里士多德为隐喻所下的定义就是“为一事物借用属于另一事物的名称”[6],这与今天的语言修辞的理解基本一致,也与我们所理解的隐喻的学术内涵非常接近。西塞罗(M. Cicero)强调了喻体和本体的紧密关系,他指出:“隐喻是明喻的简化形式,它被缩减成一个词。这个词被放到一个不属于它的位置上,却好像就是它的位置。”[7]20世纪中后期,西方隐喻研究逐渐开始从表达功能转向关注认知功能,并且形成了系统的隐喻理论。英国语言学家理查兹(I. A. Richards)认为,“隐喻不是语言使用中的特例,不是对语言正常功能模式的违背,而是语言发挥作用的必由之路”[8],是更好发挥人类思维与认知的工具。美国符号论学者苏珊·朗格(S. K. Langer)强调,“隐喻是语言的生命”,人类借助隐喻符号初步把握“整体经验”,而这种非推理性的“原始符号”会逐步“淡出”,被“推理性的表达”取代,而这也正是人类语言、思维乃至全部知识的一般发展轨迹。[9]卡西尔(E. Cassirer)在对语言的分类分析中指出,真正的“基本隐喻”或根本隐喻,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即使是最原始的言语发声,也要求有一个从某一认知的抑或情感的经验转化为声音的变形(转化)过程。[10]真正实现将隐喻由修辞格推进到认知思维方式的是乔治·莱考夫(G.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 Johnson)。他们明确指出,隐喻绝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人类的思维过程大部分都是隐喻性的。”“隐喻无所不在,不但出现于我们的语言,而且出现于我们的概念系统。”[11]这一定程度解释了中国汉字和语言自带的“隐喻”特质。隐喻虽然只是整个思维过程的“结果性”呈现,是浮于海面之上的冰山,但反映着整个丰富的隐喻性认知思维过程,也就是说海面之下是更加庞大的支撑冰山的“冰山”,无此则“隐喻”就只是干瘪的语意表达,而不是思想表达。
隐喻扩展了人类语言表达的蕴涵意义。科学主义影响下的人类语言表达力求精准完备,因此对一个概念的表达会因为认识的推延而不断地丰富其内核、扩展其外延,继而与相关概念建立关系以不断补充,突破概念原初的界限,甚至沉浸在概念关系的层层裹挟和纠缠中,变得越发深奥和复杂。因此,我们视听的科学文字和语言往往与常用语文相去甚远,需要费力理解其真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主义的语言描述力求语义统一、示意精准、消除歧义,就不得不层层释义,对科学语言的作品的理解也就需要层层解读。隐喻表达与科学表达有很大不同,其意义图景表现为“言近旨远”“意蕴悠长”,其语文表现又通常是浅显、贴切,多重意思关联,而又将所有的可能性示意凝聚在唯一也是最突出的亮点中心。因此,隐喻表达目的不在于对话语本身的释读和理解,即隐喻的不可化约性,而是情绪、思维、意蕴的直接感同,在直接感同之后产生具有差异性与自我独特性的共鸣与理解,最终在核心意涵处实现认同。与科学主义语言表达的精确性相比,隐喻因情境性而产生多意性,是语言产生的情境性,还有释读者自身的情境性,通过对语言表达本身的压缩而扩展了其意蕴思悟。隐喻很难精确解读,也没有唯一解读,对隐喻的理解是一种诗意的审美,不在于其字意语意本身,而在于其“言外之意”和“话外之音”,需要一种体验、想象、情境与意义生成的思维再创造。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伽达默尔(H.G Gadamer)倡导的“视域融合”。隐喻的解读需要从海面之上进入海面之下看“冰山”。
(二)教育隐喻
教育学界对教育隐喻的认识理解并没有太多的分歧。一方面,教育隐喻仍然只是被当作单纯的修辞格,作为一种语言表达手法的简单认识;另一方面,与教育隐喻研究在教育研究中相对受到冷落有关,专门而深入的研究较少,概念辨析、观点争鸣、理论呈现也就寥寥。教育隐喻作为隐喻的下位概念,对其认识理解可以直接基于隐喻进行推演再认识。即使如此,相近的认识也因立场不同而出现一些观点的差异。黎琼峰认为,教育隐喻是“个人对教育理念的表达,内隐观念的流露”[12],强调“隐”的作用价值;束定芳将教育隐喻分为广义与狭义,前者是一切教育活动中对认知所使用的隐喻语言,后者是人们运用隐喻思维解释教育事实,描绘教育理想的认知活动和语言现象[13],其对教育隐喻的基本理解仍然是基于语言的修辞格。上述概念认识的共同之处是都将教育隐喻视作阐释工具,这也无怪乎有研究者进而将教育隐喻作为教育研究方法、路径。“以隐喻之法来导航教育理论生成的全程,是使教育理论更富生机、活力的重要途径。”[14]回到隐喻本身来看教育隐喻,工具、方法和路径的理解可能窄化和限制了对教育隐喻的认识,因为这样的理解并未进入到认知思维的层面。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指出:“隐喻主要是通过一个概念认识另一个概念的办法,它的基本功能是理解。”“隐喻的实质是通过一类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15]无论是教育隐喻的产生还是其功能、作用,都不只是语言工具和阐释工具,还应当反映教育认知方式和思维过程,是思维触角逐渐深入概念内核的过程。教育隐喻不是借用来的阐释工具,而是喻体即“是”本体的“是”之过程的语言形式。这一过程既包括教育隐喻产生中的认知思维过程,也包括教育隐喻解读、体悟中的认知思维过程。
如果以“工具”视角认识教育隐喻、解读教育隐喻,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其一,“工具”视角的教育隐喻解释与分析违背了隐喻的“不可化约性”,聚焦于本体、喻体和本喻的类比性上,就只是看到了海面上的冰山,而无法深入到本体与喻体的“是”之关系和过程。其二,脱离了隐喻的情境性,在解释与分析教育隐喻中“工具”视角更关注当下的情境,却容易忽视教育隐喻产生的情境,核心意涵凝结的情境,也会因此丢失掉甚至主动放弃教育隐喻的核心精神所指。如,对教师蜡炬精神、春蚕精神的批评、反驳甚至拒斥,显然是以当下的教育情境替代了“蜡炬精神”“春蚕精神”的创生情境、凝结情境,泛化了其意涵又放弃了其核心本意。其三,既然将教育隐喻视作“工具”,那就可以“用”到各种教育现象的阐释中,容易造成教育隐喻意义的泛化。简言之,教育隐喻不只是一种教育言说的修辞格,或是教育阐述的言说工具、解释工具,更应是教育认知的思维方式和过程,内含着特定情境中意指的某种特定精神,体现了本喻之间“是”的关系和联结过程。因此,对教育隐喻的理论研究应当突破视其为“修辞格”和“语言工具”局限,深入到认知过程和思维过程的层面,理解其语言文字背后的意涵。
科学主义的教育理论阐述力图使教育学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科学的教育语言褪去了教育原有的亮色,降低了教育原有的温度,印证着“理论是灰色的”格言。科学的教育语言致力于割断本喻之间的关系并消除喻体。“假如把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学作品中的隐喻都去掉,那还会剩下多少引起人们感兴趣的东西?”“人们倒是觉得教育学的精神式微了,失去了它的原创力。”[16]教育具有鲜活性,是生命场,因为教育观照人的生命成长,人的意义世界绵延,人的文化境界敞亮。对教育的认知与言说既应有抽象,也应有生动,还应有生命的诗意。如同不能将科学语言的意义无限放大一样,隐喻性的教育言说也应理性看待。对教育现象分析到位,对教育理论阐述得当,对教育认知释意清晰,于读者而言可以清楚获取、理解其意涵即可。若将其推向极致反而会消蚀教育隐喻原有的思维价值、理解价值。如不朽的教育名著《理想国》《爱弥儿》《民主主义与教育》都有科学理性的分析,有隐喻意蕴的表达,还有诗意文字的想象。
“立德树人”是当代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指针和基本遵循,回归育人成人的教育原点应当进一步凸显教育隐喻及其研究的时代价值。教育思想理论化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教育实践质量,科学化语言可以在教育理论界畅行,但学校、社会和家庭等教育实践常常面临“脱离”窘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因此教育理论需要采用实践者听得懂、思得清、学得透、悟得明的话语方式;教育理论的生命力还在于完整人的培育,因此教育理论语言除了信息功能,还表达着情感、需求、期望等。重新重视教育语言的隐喻性特质,呼唤隐喻言说回归教育研究,更能为教育增添人文的光彩和魅力、生命的温度和热情。教育隐喻与教育学话语的相关研究也充分肯定了隐喻性教育语言和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并努力寻找教育语言中科学表达和隐喻表达的平衡点和兼容性。
二、教育隐喻类型的省思
(一)学校之外的教育隐喻
西方学者纳派(Noppen)在《隐喻Ⅱ:1985—1990出版物分类目录》一书中共列出70余门研究隐喻的学科[17],如此之多的隐喻研究无不关注隐喻的分类问题。分类是学术研究走向繁荣与成熟的必要条件,标志着隐喻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因此需要将教育隐喻从尘封的角落重新置于学术舞台的亮光处。国内已有的研究从隐喻的来源、内容指向、存在方式、新颖水平、认知功能等方面[18]对教育隐喻进行了分类,如从来源上将其分为来自自然的教学隐喻、来自生活事物的教学隐喻和来自其他学科的教学隐喻,从认知功能上将其分为根隐喻和派生隐喻。这些教育隐喻的分类多是基于狭义教育的隐喻,且多是学校教育之内的隐喻,因此内容上普遍是“关于课程的隐喻、关于教与学的隐喻、关于教师的隐喻、关于学生的隐喻、关于学校的隐喻”[19]等,与之对应的基于广义教育的隐喻,或者说从社会、家庭角度出发关于教育的隐喻并未得到较多的教育学术关注。随着对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学校之外的教育隐喻应得到更多重视。
(二)反映时代教育精神的新隐喻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 Hobbes)认为,语言对人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人们的语言越丰富,他们比常人或者更聪明或者更癫狂”,因此语言的作用首先在于正确定义,而“确定意义”正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第一步。[20]由于科学主义盛行,语言的表述必须“尽可能地接近数学语言的明确性”[21]才能合法地存在,隐喻性语言因其模糊性和多意性而多受批评,不入学术法眼,难登大雅之堂。一方面,教育隐喻受到科学主义的排挤,语意方面难以符合科学的标准;另一方面,教育隐喻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言说方面的准确性、清晰度不断提升。如,在学校教育的课堂上,教师经常要求学生发言要“言简意赅”“表达准确”,表现了科学主义语言观影响,牺牲的是语言的丰富与美感。再如,对经典教育隐喻的“条分缕析”、精确阐释,泛化了其本意、弱化了其“生命”。
教育具有历史性,教育隐喻同样具有历史性。“成熟”的教育隐喻是经过历史淘洗沉淀下来、凝练出来的,能最直接、准确地触及读者心灵达到共鸣和共情,也是最能反映教育“根性”和“共性”的问题,其“活”与“死”[22]并不取决于时间维度和新颖程度。对“成熟”的教育隐喻,应当避免销蚀其已经被广泛认可的意境与意蕴。教育还具有时代性,时代的特殊性也反映在时代教育的特殊性上。“今天摆在教育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不是彻底地抛弃隐喻,而是创造出能够更好、更有力的传达时代教育精神的新隐喻。”[23]对于新的教育问题、教育现象的思考,应当积极创生新的教育隐喻来表达其内涵。
(三)基于喻意丰富程度的教育隐喻分类
当前教育隐喻研究的聚焦点在教育隐喻本身、功能、意义与价值等方面,对具体的“教育隐喻”分析则相对集中在经典的教育隐喻上,如柏拉图(Plato)的“洞穴”之喻、夸美纽斯(Comenius)的“种子”之喻和杜威(J. Dewey)的“生长”之喻。我们把这一类的教育隐喻称为理念型,因为这些隐喻实则表达了其整个学术主张的基础和起点,由此勾连起整个教育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经典常讲常新,理念型教育隐喻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其分析也最“有话可说”。“洞穴之喻”既构建起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其中“抬头”“转向”“上升”等生动形象又创造性地表达了柏拉图理论中的教育主张;“种子之喻”以及相关的“阳光”“雨露”“灌溉”“果实”等意指“神圣的可教性”,把“可教性”赋予了夸美纽斯独特的宗教热情、美好追求和坚定信念,也给了读者更为宽阔的语词和思想空间;“生长之喻”是杜威首次赋予植物学“生长”以教育的意义,认为生长是生活和教育的基本特征,是一个连续的、无止境的运动过程,其目的不在过程之外,而在过程之内,即生长是为了更多更好地生长,除此之外别无目的。生长自始至终孕育着一种积极的“势力”和“能力”,指向新的生长。
如果说理念型教育隐喻是可以铺开的“面”,那么与之对应的“点”状的教育隐喻则可以称之为指向型,在言语方式上多呈现为“……是……”句式,如“教师是蜡烛”“学生是璞玉”“课堂是剧场”“学校是象牙塔”等,通常是以物喻人、以物喻物。指向型教育隐喻多是独立存在,也有的是作为其他类型教育隐喻的构成部分,喻意直接而明了,可深挖和拓展的范围比较有限。这也是较少有对指向型教育隐喻进行深入分析、解析的原因。指向型教育隐喻最直接表达了教育隐喻中本喻之间“是”的关系,“是”并非本体等于喻体,而是在特定时代情境中对本体某一特定方面的认识和理解直接联系到了喻体的某一方面,对喻体的形象认识直接触及了对本体的抽象理解,如“蜡炬精神”,是以蜡炬的光和热表达教师对学生成长的奉献。指向型教育隐喻也最容易出现意义泛化而造成对教育隐喻的误解,如“蜡炬精神”中蜡烛燃烧带来的不可逆的消耗被认为是教师奉献的“悲壮”和忽视教师的持续学习与成长,这显然已经从其核心喻意越界了。
在理念型教育隐喻和指向型教育隐喻之间,还存在着“线”状的教育隐喻,通常用以表述教育现象、教育事件或教育问题等,具有相对的、基本的完整情境,可以称之为事件型或现象型教育隐喻。事件型教育隐喻多是复合的隐喻表达,由多个指向型隐喻联系组成,但又未能达到理念型教育隐喻那样作为体系元点的价值。事件型教育隐喻的时代性更加鲜明,更多是反映当下的教育现实和热点,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神兽回笼”等。“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将学生比作竞技运动员,将学校教育比作田径比赛,将学生发展的起点比作起跑线。此外,还存在着隐藏于背后的喻意,早期经验对儿童发展起决定作用,因此学习的发生越早越好、越优越好,如果错过了或不重视,从一开始就落后,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神兽回笼”,网络上较早出现近似的词语是“四脚吞金兽”,家长给刚会爬行的幼儿穿上动物形象的衣服,以此诙谐表达当下养育子女过高的经济成本,以及更多的精力付出。“笼”本指竹木编成可以包举的盛物器,人造之物,在此喻指学校,是受教之地,对学生而言是特殊人为的环境。“回”是从别处到原来的地方,“回笼”喻意开学返校。“神兽回笼”不仅仅是学校开学、学生返校的表意,其背后同样内藏着目前家校社合作共育的问题、学校教育育人价值的不可替代性、未来学校变革发展趋势的清思等等。
总之,依据喻意的可拓展性和蕴意的丰富深远程度,教育隐喻可以划分为指向型、事件型和理念型教育隐喻,它们之间可以形成相互嵌套的联系。面对不同类型的教育隐喻,对其理解乃至解读应当具有与之对应的阈限。指向型教育隐喻不应过度分析,理念型教育隐喻需要深度发掘,事件型教育隐喻则需要应时以对。如,“蜡烛”“春蚕”即是悲壮与牺牲,其中原因即是“分析”的超阈限。
三、教育隐喻研究进展的省思
依据皮亚杰(J. 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当认知主体遇到新的问题情境时原有的认知结构就会进入不平衡的状态,进而通过同化或顺应机制来解决新问题以达到新的认知平衡。也就是说,人通常会首先使用已有的相近概念来辅助认识新的概念,由思维到言说就表现为隐喻。由此看来,“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24],“语言本身就是隐喻性的存在,隐喻的权力是一种永恒的本源性权力”[25],并非夸大其词。
(一)教育隐喻的分析解读存在去情境化和意义泛化的倾向
对隐喻意涵的分析解读是教育隐喻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分析对象主要指向理念型教育隐喻和指向型教育隐喻。前者多已成为经典,除了前文提到的还有苏格拉底(Socrates)的“产婆术”,洛克(J. Locke)的“白板说”,赫尔巴特(J. Herbart)的“塑造”等。指向型教育理念更加多样,具体到教育的各个方面异常丰富多彩。如,课程是跑道、是脚本、是乐谱;教学是倒水、是演戏、是登山;教师是蜡烛、是园丁、是一泓清泉;学生是机器、是游客、是消费者,等等。隐喻具有不可化约性和情境性,也正是因此才有了隐喻的多意性。对教育隐喻的分析解读不能拘泥于其字意表面,不可脱离其话语情境。经典教育隐喻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和特定的精神内涵,对教育隐喻的分析解读应尊重其产生的背景,更要尊重现实情境,不能脱离这两点来孤立地解读;还应尊重其特定的精神内涵,本体与喻体的类比是为了凸显其相近的某一点,而非喻体全方位代替本体的特征。脱离了教育隐喻的情境性就难以焕发经典教育隐喻的时代生命,忽视了教育隐喻的特定精神内涵就容易出现意义泛化。
近些年来对一些经典教育隐喻的批评通常是以揭示现实教育教学种种弊端为初衷,如园丁说体现了师生先天性的不平等[26],工程师说使复杂的教育工作带有了极强的规训性[27],蜡炬说渲染了一种伟大而悲壮的色调,忽视了教师的学习与成长,淡漠了教师的尊严与劳动快乐[28],甚至出现了“‘蜡烛’‘春蚕’‘泥土’‘人梯’,见鬼去吧”[29]的声音。教育隐喻的分析解读乃至批判应注意其情境性,更应防范教育隐喻的意义泛化以及“历史虚无”的破坏。因此,我们不反对类似批判的初衷,但并不赞成如此消蚀教育隐喻生命力的批判内容。当前,教育中谈“春蚕”“蜡烛”而色变的现象,显然是经典教育隐喻不“应”承受之重。
(二)时代新隐喻和事件型教育隐喻应成为新视点
经典的教育隐喻之所以富有生命力,在于其“真理性”核心意涵在不同的时代情境中仍具思维理解的指示性。对新时期教育的言说,不仅需要有生命力的经典教育隐喻,而且应有意识地关注、洗练、萃取反映教育时代境遇、体现教育时代精神的新隐喻。基于教育隐喻内容丰富程度,我们把教育隐喻分为指向型、事件型和理念型三种,这也是依据其产生的难易程度的分类。指向型教育隐喻句式简单,内容相对单一、独立,也是教育活动中出现最多的一类,具有较强的认知工具性;理念型教育隐喻勾连起庞杂的教育理论体系,是最复杂也是最难形成的一类,具有理论根源性;事件型教育隐喻产生的难度居于两者中间,内容呈现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教育现象或教育实践,最能反映教育现实,因此也最具有时代性。
随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中国教育学原创性建构中,需要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也需要针对教育现实问题的思考。如,“牵一只蜗牛去散步”反映的理解和尊重儿童的生长节律。因此,当前教育隐喻研究应当多关注一些契合教育现实和教育问题的新隐喻表达,逐渐积累和丰富关联性的教育隐喻,以此为理念型教育隐喻的形成铺垫基础,也作为原创性中国教育学的内容构成。
(三)归正日常教育话语的隐喻分析
教育隐喻中有许多喻体来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如路标、镜子、阶梯、超市等,这样的隐喻虽“来自”生活却不“属于”生活,终是教育对日常生活的话语借贷而已。也就是说,教育隐喻研究仍是在教育之内,是在狭义的学校教育之内。教育倡导“回归生活”,教育研究就需要深入地“研究生活”,教育隐喻研究应当关注日常生活中教育话语的隐喻现象,也就是在广义教育中进行教育隐喻研究。日常生活话语中教育隐喻的分析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研究,相信随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研究意识和行动的逐渐兴起,相关的教育隐喻研究也将受到关注。西方学界已有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30],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日常生活中教育隐喻的研究分析需要首先澄清立场、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研究立场方面,不是站在学校教育里搜寻日常生活中的喻体,而是进入日常生活中发现对“大教育”的隐喻言说;研究的思维方式,不是用点状思维做“……是……”的连线题,而是用关系思维、融合思维联通教育和生活对完整教育现象或教育事件的认知与言说;研究的价值方面,教育隐喻应“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不只是反映学校的教育现实,更是家庭的、社区的、社会的教育状况。教育隐喻研究不只是服务学校教师和教育理论工作者,更应通过日常生活中教育隐喻的分析回馈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教育,助益形成家校社的教育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