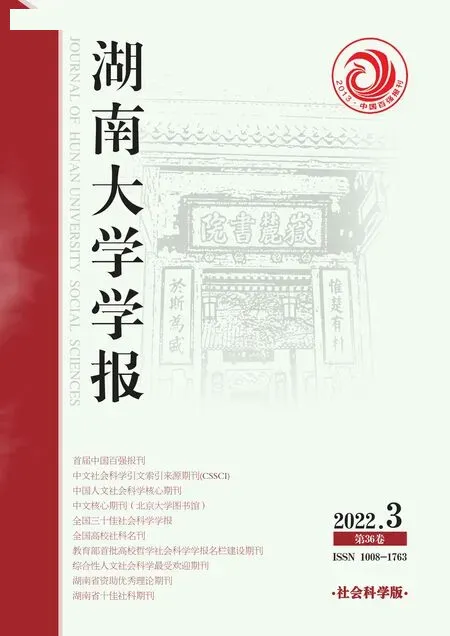东林学人高攀龙拟陶诗刍论*
渠嵩烽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明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高攀龙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后,在大理寺短暂观政,未及授官,便回乡丁嗣父忧;十九年(1591)十月服阙,次年春赴京谒选,六月得授行人司行人一职;二十一年(1593),因上疏参劾首辅王锡爵,十二月谪广东揭阳县典史;次年七月起身赴任,在任仅三个月,即告假归家。贬谪揭阳的这段经历对高攀龙的学术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自称:“自出至此,已三转手势。”[1]660此后,高攀龙闲居乡里近三十年,潜心学术,修身讲学,遂成一代名儒。不惟理学思想,贬谪揭阳的经历同样也是他诗风转向的重要节点。今存高攀龙此前创作的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题材丰富、风格多样,而之后创作的诗歌则基本以效陶为主,格律清和、诗意冲澹,构成了高诗的主要风貌,同时也是后世对高诗的主要审美接受。清人沈德潜赞誉高诗“无心学陶,天趣自会”[2]245,此说并不符合高诗效陶的实际情况。晚明时期,随着陶诗在士人心目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吴中地区形成了浓厚的效陶氛围。不仅高攀龙主动学陶,而且他的部分同道、挚友、门生同样慕陶、学陶,由此形成了一个以高攀龙为中心的效陶交游圈。高攀龙的效陶诗风,至其晚年复出,乃至深陷党祸、自沉而死,均未有太大改变。
一 晚明吴中效陶风气及高攀龙的效陶交游圈
李梦阳称:“三代而下,汉魏最近古。”[3]1912古体诗以汉魏诗风为尺准是前七子诗论的显著特征。其中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诗弱于陶”[4]576一说又奠定了七子派论陶诗诗史地位的基调。何景明认为陶渊明诗歌气格较弱,应指陶诗不符合雄浑高古、朴略宏远的汉魏诗歌的审美范式。后七子派代表王世贞既评价陶诗“淡雅而超诣”[5]186,又认为其“不得入汉魏果中,是未妆严佛阶级语”[6]994。就明中晚期诗人心中陶渊明的诗史地位,陈斌曾如此总结:“事实上,在七子派之外,无论是六朝派还是唐宋派,包括晚明的性灵与神韵诗说,均对陶、谢给予极高评价。”[7]316此说持论公允。此外,江南其他多数诗派和理学家诗人亦极推崇陶诗,而且越到明代后期,士人越发推崇陶诗,他们逐渐摆脱诗歌辨体批评的限制,不断抉发诗人主体情感和生命体验的诗学价值。尤其在东林学派理学思潮以及明末世局骤变浪潮的双重影响下,“江南子弟更加强调从‘节操’上肯定陶潜,并将之上升到与屈原并尊的地位”。[8]401
在上述诗学背景之下,晚明吴中形成了浓厚的效陶风气。效陶不仅表现为吴中诗人在实践中对陶诗神情韵致的自觉追求,如归子慕、姚希孟、魏学洢等人的诗歌创作,而且还体现在大量和陶、集陶、注陶等与陶诗相关集子的结集和编纂上。和陶诗集有嘉兴周履靖《五柳赓歌》、安吉陈良谟《和陶小稿》、嘉定黄淳耀《和陶诗》等,集陶诗集有吴江沈自南《沈子律陶》、昆山顾易《柳村律陶》等,陶诗注本有东林后学文震亨《陶诗注》等。究其成因,大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人生志趣、诗学风尚、地域环境。高攀龙《缪仲淳六十序》云:“东南士与西北异,士归田间,甘泉乡稻皆有以自乐,可以诵诗、读书、养心、缮性,无富贵之慕。”[1]613缪仲淳是常熟人,“东南士”应指吴中一带士人。高攀龙认为江南吴中士人不求富贵、甘守平淡,在田园生活中读书养性、怡然自乐,志趣与西北士人相异。此说虽未免以偏概全,但基本道出了吴中士人的整体风貌。人生志趣不同,诗风自然不同。唐顺之称:“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9]452徐泰也称:“吴下诗,自正统、天顺以来,调极清和。”[10]1207“柔婉”“清和”反映了吴中士人迥于北地的诗学风尚。这种人生志趣、诗学风尚使笃意真古、辞兴婉惬的陶诗成为吴地文人难以绕开的诗学传统。此外,地域环境也是吴地文人效陶风气浓厚的重要形成因素。太湖流域自然风光得天独厚,水是形成吴中自然生态之美和人文生态之盛的基础条件,水环境为吴中士人提供了隐逸氛围浓厚的文化空间,他们栖居水滨湖畔,占尽风光之胜,澄怀忘机、任真自得。罗时进称明清江南文学社团“大多数又与隐逸具有通约性,很多文人结社的事迹往往见于地方的《隐逸传》”,[11]413并进一步指出:“隐逸,是文人结社的基本出场状态,也是选择水滨湖畔的心理意向。”[11]414陶渊明乃“隐逸诗人之宗”,晚明吴中隐逸之风下的诗歌创作必然会效仿前贤。
高攀龙非常钦慕陶渊明,称其为“皭然不滓之人豪”[1]813。慕陶则会效陶,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陶诗为宗尚的文学群体。这一群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社团,更称不上文学流派,因为它没有明确的诗学宗旨,也不是由高攀龙及友人、门生自觉地组织而成,而是一个自然而生同时又受人际和地域限制的文学小社群,其成员包括高攀龙、归子慕、吴志远、安希范、陈龙正等人。归子慕、吴志远是高攀龙的挚友,三人交游最密;安希范既是高攀龙生活中的好友、姻亲,又是理学中的同道;陈龙正乃高攀龙门生。归子慕是归有光第五子,因追慕陶渊明风范,以“陶庵”为号,其韬光内照、淡泊自足的品格和他的效陶诗风在当时就已播誉江南士林。沈德潜称:“待诏(归子慕)诗雅淡清真,箪瓢童冠,无非乐趣。生平与高忠宪公敦道义交,诗品亦略相似,所云同心之音也。”[2]249朱彝尊亦赞称:“其诗学陶而得其神髓,韦苏州后,鲜有其伦。”[12]474-475安希范诗多冲淡平和、质朴自然,与高攀龙、归子慕诗品相类,其在《天全堂集》中还记录了拜访归子慕的缘起及见闻:“余雅闻高存之言归季思隐居萧寂之趣,与渊明田园诗首章绝类,不禁神往。乙巳年十月,还自云间,过昆山,访之。”[13]447他在详述访问经过以及归子慕家衡门流水、短墙疏篱的隐居风致后感叹道:“周行篱落,徘徊庭户,默诵渊明诗,真无一语不合。”[13]448高攀龙门人陈龙正不仅在诗歌创作上效陶,还编选《陶诗衍》一书,旗帜鲜明地指出“诗宜以渊明为正宗”。陈龙正在书中将归子慕、高攀龙纳入历代效陶诗人谱系,并极力表彰二人,赞誉归子慕:“目睹其人,咏其诗,仿佛乎陶翁复起。”又赞誉老师高攀龙:“《豳风》可以终变,高诗可以终陶。”[14]他们以陶为宗、相互激赏的情形是晚明吴中拟陶风气的一个缩影,效陶成为他们诗学风貌的集体标识,高攀龙在这一小型文学社群中无疑具有凝聚和引领作用。
二 对陶渊明思想的接受
陶诗不仅多为世俗文人所推崇,而且也是明代性理诗人热衷效仿的对象。陶渊明任真自得、鄙夷世俗、守正乐道的品格和理学家天然本色、崇古非今、怀正志道的思想不谋而合。宋儒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一文就已从经术正统的角度为陶渊明做过申辩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性理诗人看来,陶渊明的思想和性情是合乎天道的表现,其诗歌乃见道者之言,这与他们的理学追求相通相合,并无二致。高攀龙是理学大家,陶渊明思想与理学的相契无疑是其崇陶、效陶的主因。此外,高攀龙自揭阳告假归乡后,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起用,陶渊明辞官彭泽之后,也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平凡生活。虽然时代不同,遭际也不尽相同,高攀龙却将陶渊明视为异代知音,并且在诗中一再表达对陶氏的激赏。高诗《幽居四乐》其二云:
我爱陶元亮,采菊东篱时。悠然南山意,怡悦心自知。北窗初睡起,读书正解颐。正尔得樽酒,日夕欢相持。[1]16
诗歌开篇即直抒胸臆,用近乎口语化的表达来抒发对陶渊明的钦慕之情,接着化用陶诗《饮酒二十首》中多处诗句来描述陶渊明平淡闲适、达生任情的生活状态。高诗《夜步》云:
幽人夜未眠,月出每孤往。繁林乱萤照,村屋人语响。宿鸟时一鸣,草径露微上。欣然意有会,无与共此赏。千载怀同心,陶公调可仿。[1]20
诗人月夜独自漫步,看到繁林萤飞、草径露上,又听到人语偶响,夜鸟时鸣,欣然有得,感叹无人能会,因此发出“千载怀同心,陶公调可仿”的感慨。高攀龙又称陶渊明为“古之高隐”,并作《采菊》三首大加赞赏。《采菊》其一讲述了天地运转不息和人生短暂无常的道理,诗人认为世人皆不能深刻理解万物运作的内在规律,而陶渊明却能“悠然了斯旨”。《采菊》其二开篇云:“夫子古大圣,蔬水亦欣然。”[1]52高攀龙称陶渊明为古代大圣,不吝溢美之词。《荀子·哀公》载:“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孔子对曰:‘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15]400-402在高攀龙心中,陶渊明已经是道德完美、智慧超群的完人了。
元好问称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16]230,“真淳”一词是对陶氏思想和诗歌最为精准的概括。真淳是返璞归真的淳厚和物我交融、身心俱和的天性,其源头是陶渊明倍加推崇的上古民风。陶渊明鄙夷俗世,向往淳厚真朴的上古时期,他在《饮酒二十首》其三喟叹云:“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17]216他在《与子俨等疏》中又写道:“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良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17]441这些无不表达了陶渊明对上古时期的神往。羲皇指伏羲氏,为华夏民族上古传说中的帝王。古人认为羲皇时期人们思想淳朴、生活闲适,无后世虚伪诡诈、争名逐利之心。高攀龙同样有浓厚的崇古思想,“羲皇”亦是高诗最常见的语词之一。如“爰以风月谈,聊见羲皇心”[1]16(《幽居四乐》其二),“生与羲皇侣,殁与天地俱”[1]14(《游静乐寺》),“我爱山中坐,恍若羲皇时”[1]17(《静坐吟》其一)等,莫不表达了对上古生民之初的向往。躬耕是陶渊明崇古思想的实践之一,高攀龙在对上古时期的心往神驰之中,也同样表现出对农人的深厚感情。在家谱之中描摹其家族有记录以来第一代祖先孟永公耕田持家、怡然自乐的情形时,高氏居然用“几于厥初生民之始”[1]684来形容。而孟永公生活的年代大致在元末明初,远非上古时期,其对先祖近乎夸张的描述与陶诗《劝农》“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17]35所表达的审美意味相同。廖可斌先生在谈到中国古典审美理想的形成原因时曾说:
农人日日面对着和从事着的,是他早已熟悉的环境和生产过程,不可能有意外收获,也很少有彻底破产和死亡的危险。因此他排除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欢迎过分的冲动与激情,需要的是脚踏实地辛勤劳作的韧性和耐心。这样,保持内心的安宁,保持感情与理智的和谐统一,就成为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18]29-30
高氏诗云:“澹然心无事,宛若生民初。”[1]44(《弢光静坐》)“澹然心无事”即引文所说的早期农人“排除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保持内心的安宁”的心理状态。陶渊明崇古思想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审美理想,它强调情理、美善、意象和诗乐的统一,高攀龙追慕的陶渊明思想与之高度相契。
三 对陶诗语词的效仿和艺术化处理
高攀龙拟陶诗主要涵盖闲居、咏物、节序、即事等题材内容,对陶诗语词的效仿是高诗拟陶的显性表现。
高氏拟陶诗中有大量直接袭用陶渊明诗歌成句的例子。如《题欧阳宜诸素风堂四首》其三“历览千载书,高标信可慕”[1]15,前句引自陶诗《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的“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17]184,两诗后句虽然不同,但均接引上句表达了通过读古人之书而追慕前贤的意思。再如高诗《有鸟》“行止千万端,何能一其事”[1]22句,借鸟能施展羽翼、四处飞翔来说明人之趣舍万殊、行藏难一,进而表达“人生各有志”的道理,前句直接从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六“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17]223袭引而来。《即事》:“但觉闲居好,不知久离索。白日掩荆扉,庭花自开落。”[1]85其中“白日掩荆扉”亦陶渊明诗歌成句,出自《归园田居五首》其二“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17]77。类似直接引用陶诗成句的例子尚有不少,为省篇幅,兹不一一列举。
高氏拟陶诗除了直接袭用陶诗成句,还有在引用过程中变更一字或两字的情况。如高诗《舆中》“远望欲何为”[1]23与陶诗《饮酒二十首》其八“远望复何为”[17]226,仅一字之差;高诗《山居》“百营良有极,庶以善自悦”二句,申以人生应当知足而行善为乐之义,陶诗《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亦有“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17]128句,同样表达了富莫大于知足的思想;高诗《独坐》“独坐无余事,悠然见远山”[1]56,描写诗人闲坐无事、悠然远望的闲适状态,“悠然见远山”显然自陶诗名句“悠然见南山”而来,仅改动一字;高诗《八月四日从伯兄游山》“抚景有深怀”[1]54句则系效仿陶诗《岁暮和张常侍》“抚己有深怀”[17]148。
高诗对陶诗的效仿,更多体现在对陶诗诗句和词语的改造上。经过高攀龙艺术化的处理,被改造的陶诗为其所用,融合无痕、妙趣横生。试举四言诗《水居》为例:
举网得鱼,摘我园蔬。烹鱼煮蔬,载陈我书。酒中有旨,书中有腴。聊尔东窗,不乐何如?
饭饱欣然,荡桨菰芦。菱蔓摇漾,莲花芳敷。今日何日,吾长五湖。其来徐徐,其去于于。
微雨乍过,好风徐来。游云断续,众峰皆开。欢然抚景,尽兹一杯。世事如积,亦已焉哉!
薄暮登楼,四望远畴。时雨既降,农人乍休。乳燕来止,鯈鱼出游。万族有乐,吾亦无忧。
涉世愈拙,入山宜深。踽踽空谷,悠悠长林。支颐一卷,挂壁孤琴。游目闲云,倾耳鸣禽。
清昼扫室,中宵拥衾。无象之色,希声之音。咎誉可远,阴阳不侵。虽乖通理,爰得我心。[1]5
高攀龙《水居》一诗写闲居时餐饭、饮酒、读书、泛舟、登楼、扫室、困卧等日常生活,将“我”之看似琐碎零乱的日常小事置于菱摇莲放、燕飞鱼游、云卷云舒、风来雨过的山水田园风光之中,清新自然、交融无间,营造出一幅宁静和谐的闲居画面,最后以“无象之色,希声之音。咎誉可远,阴阳不侵。虽乖通理,爰得我心”收尾,有浓重的老庄道学色彩和魏晋玄理诗的意味。此诗多处化用陶诗语句,“摘我园蔬”直接袭自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摘我园中蔬”[17]335句,与前句“举网得鱼”衔接自然;“酒中有旨,书中有腴。聊尔东窗,不乐何如”四句,则是将陶诗《停云》“有酒有酒,闲饮东窗”[17]1拆解开来,补充新的内容后重新组合,浑融一体,斧凿无痕;“微雨乍过,好风徐来”化用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17]335二句,缩短之后对仗工整、声律优美;“欢然抚景,尽兹一杯”二句诗意取自陶诗《时运》“挥兹一觞,陶然自乐”[17]7,调换前后句位置再调整以新的表述,意味深长、顿生新趣。类似的情况尚有多处,兹不赘述。高攀龙对陶诗十分熟稔,使得他在诗歌创作过程中随手拾来,臻于化境。
四 对陶诗意象的袭用
高诗拟陶还体现在对陶诗意象的袭用上。陶渊明常借菊、云、鸟等意象来寄托自己的情思,通过客观物象寄寓主观情感,往往使得诗歌韵味无穷、寓兴深远。陶渊明将这些常见事物的自然特征与“我”之人格特征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抽象的生命体验变得生动具体。陶诗中常用意象亦为高攀龙所承袭。
陶渊明酷爱菊花。菊在陶诗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广为人知,已使得人们将菊花看作陶渊明人格的化身,所以高攀龙称陶渊明为“采菊翁”[1]52。高攀龙同样痴爱菊花,菊成为其笔下最为常见的景物之一。《采菊》其二云:“百荣率以瘁,秋菊乃独芳。爱此幽贞色,得我心之常。”[1]22诗人借菊花贞洁不争的品格寄寓自己孤傲脱俗的情怀。《秋花八咏》其一《菊》:“篱边见黄菊,相对不知还。”[1]74诗人赏菊,相对忘归。《吴子往荻秋庵二首》其一:“散金抚篱菊,鸣玉听丛篁。”[1]30诗人不仅自己爱菊,还以菊花品性与友人共勉。
陶渊明不仅爱菊,而且爱云。陶诗《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以“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17]128收束全诗,以遥望白云之缥缈寓意深怀古人之高迹;《与殷晋安别》中“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17]138二句用云之飘忽无常寄寓人之行踪不定的离别之情;《归去来兮辞》中“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17]391二句,诗人从云生云灭皆出无意的自然意象和鸟倦飞还巢的天性之中找到了自己归隐的依据:摆脱尘俗名缰利锁的羁绊,回归闲适自在的田园,如此方符合人的本性。高诗酷爱写云,诗人常将远离政坛、林下闲居的自己比作悠然自得、来去自如的白云。如《舟居》“为笑此身无住着,只和一片白云浮”[1]99,《水居漫兴》“问我此意如何,白云自来自去”。[1]90高氏专注性理之学,追求主体精神的独立,早年修身工夫尚未成熟之时,曾感到浑身受到拘束,大不自在。而当他自揭阳归乡之后,心性思想和工夫践履均渐趋邃密,在收敛身心之时获得了极大精神自由,故常常将身心与白云联系在一起。其曾作《白云辞》:
感彼地下人,仰见天际云。白云不可掇,使我心如焚。
大云出如盖,小云出如组。寸心不可道,但见云无数。
遥望白云来,转见白云去。白云去不来,不知散何处。
孤亭空落落,流水澹漠漠。白云归不归,坐断南山石。
心随白云远,亦随白云迟。欲随白云灭,白云无尽时。[1]77
白云高邈,令人神往,不可掇拾,而道学之奥妙,同样缥缈深邃,只可默识而难以言求。诗人向往和追求白云的心灵体验及意识流动酷似其修身悟道的心路历程,尾句借白云无尽寓意道之永恒。
“鸟”同样是陶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意象。陶渊明曾作四言诗《归鸟》抒发孤傲清高的情怀,与《饮酒二十首》其四“栖栖失群鸟”[17]218句同有托物言情之妙。“羁鸟恋旧林”[17]73(《归田园居五首》其一)表达对自由的向往,“鸟倦飞而知还”[17]391(《归去来兮辞》)则隐喻自身归隐的正当性,这些诗句无不以鸟寓托情怀。高攀龙晚年诗歌《始归》中“飞鸟脱笼中,游鱼归故渊”[1]47将从朝中辞任归乡的自己比作摆脱樊笼的飞鸟,取意与陶诗颇类,而且“鸟”在高攀龙笔下多有道德内涵,比如高攀龙在《有鸟》诗中描述了林中一只鸟因志趣独异而遭到其他林鸟攻讦的情形,显然有君子、小人之分的意味。高攀龙还经常在“鸟”字之前加一“好”字,以示区分。如《西湖十咏》其一《万松书院》“好鸟有情依古树,闲云无意度高岑”[1]148,借鸟儿栖息古树表达了诗人的吊古情怀以及对万松书院败落的感伤;《谪居》“好鸟一时鸣,静蕴流天机”[1]25描绘诗人在佳鸟时鸣的揭阳官舍中体认天机的谪居生活;《赴华燕超金玉家会,次诸公韵》“清歌细酌江天远,好鸟声声弄韵频”[1]125则将友人吟诗唱和的场景比作鸟儿翻声弄韵的情形等。
五 高攀龙拟陶诗的得失及原因
高攀龙自揭阳贬所告假还乡之后,一改早期诗风而专注学陶,诗歌创作语出天然、情理浑融,颇得陶诗真昧。高诗的效陶成就为后世所推崇,高氏门人陈龙正称:“先生不尽效陶,大都有陶韵,逸兴幽怀适与之符。”[19]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称其诗“冲澹入古,不事俳佻,足拔刀戟自成一队”,并指出明诗能返“正始之音者”,不在他人,而在高攀龙。[20]842钱穆先生编选《理学六家诗钞》,将高诗收录其中,并赞高诗“高淡近渊明”[21]220。无论是“逸兴幽怀”,或是“冲澹”、“高淡”,都是赞誉高氏效陶诗中委任自然、达天知化的一面。然而,高诗效陶成就虽高,但不及陶诗内蕴丰富、情感鲜活。如陶诗“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17]90(《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中因病而生的悲戚,“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17]93(《乞食》)中因贫而乞食乡里的困窘,“逸想不可湮,猖狂独长悲”[17]152(《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中因晚年缺酒乏粮而致的苦闷等情感同样是构筑陶渊明精神世界和诗学风貌的垒石。高攀龙自揭阳返乡之后的诗作几乎从不承载上述情感。诚然,高诗所学是陶诗的主要风貌,但陶诗的动人之处恰恰在于丰富而真挚的情感背后所表现出的平淡自然,如果剥离这些情感而仅谈陶诗的平淡自然,必不能反映陶诗全貌,也会使陶诗失去真情这一最为重要的文学质素。总体而言,高氏效陶诗不及陶诗生动耐读,这与两人不同的生活境遇及高攀龙的性理思想有着很大关系。
陶渊明虽然祖辈为官,但至父辈时家道已然衰落,且每况愈下。陶渊明自言:“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纟希绤冬陈。”[17]462自初仕江州祭酒到辞官彭泽县令,前后约十年时间,陶渊明数次仕隐,其频繁出仕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纾解家庭贫困。自彭泽县令解绶归田之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陶渊明再未出仕,一直过着贫苦艰辛的生活。其晚年生活更加贫窭,甚至乞食乡里。即便如此,陶渊明仍恪守己志,坚持耕作,隐居不仕。长年生计的艰难窘迫和躬耕陇亩的农人岁月使得陶诗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和人情冷暖,再加之其儒道兼有的独特人格、超然物外的自得心态、平淡清和的自然诗风,造就了中国诗学史上一个永恒的丰碑。高攀龙的生活境遇则与之大不相同。其祖父高材曾任黄岩县令,生父高德征一意治生,家境非常殷实。嘉靖四十一年(1562)高攀龙生,高材念及兄弟高校无子,遂将次孙高攀龙过继给高校。高校亦从事典质方面的营生,经济十分充裕,并且为高攀龙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高攀龙科考之路相对平坦,且在嗣父逝后继承了所有家产。自揭阳贬所归乡之后,攀龙构水居、建可楼,专心研习性理之学,后又讲学东林数载,在野将近三十年之久。晚年复入朝为官,政治热情高涨,主动且深度参与晚明政治斗争,最后身遘党祸,自沉而死,这与陶渊明晚年虽然穷苦但拒不出仕的情形构成鲜明对比。终其一生,高攀龙虽然生活节俭,但物质并不匮乏,更没有体验过生产劳动的艰苦,感受过饥寒交迫。他一心治学,不必亲自从事劳作,虽久居乡里,但从未真正融入田园生活。同样是诗酒田园,内涵却大不相同。不同的生活境遇造就了不同的生活体验,这是高诗不及陶诗真实生动的原因之一。
明代绝大多数性理诗人均推崇陶渊明。许学夷云:“靖节诗乃是见理之言,盖出于自然,而非以智力得之,非若元和诸公骋聪明、构奇巧,而皆以文为诗也。”[22]103“见理之言”“出于自然”是陶诗胜于元和诸家的主要因素,而这也是陶诗为性理诗人所推崇的最主要原因。高攀龙以程朱理学为宗,坚持性善之说,他认为天理乃天然自有之理,人之至善至美的本性皆来自天理,见理是理学家一切文学活动的宗旨。高攀龙云“稍着丝毫造作,即与本色天地悬隔”[1]1293,又云“吾性本来简易直接,不可自增造作”[1]177。陶渊明独立率真的性情和自然无华的诗风无疑被理学家认为是存乎天理、复归本性的表现。高攀龙坚持“得性情之正”的抒情观,他曾说:“中者,心之所以为体,寂然不动者也,性也。和者,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乐,情也。未发者,则性也。’二者指出性情,如指掌矣。”[1]221关于情的属性,高攀龙又云:“意、识、情俱是不好一边,若诚其意、智其识、性其情,道理又只是一个。”[1]313心未发为性,心已发为情,喜怒哀乐乃已发之情,气质杂驳,属于“不好一边”,所以高攀龙强调要使“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1]832,从而追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心体湛然空明的状态。高攀龙的性理思想严谨恭肃,主张以性收心,以性束情,而诗歌不过是“理学之余绪”[23],是其见性明心的工具。“天趣自会”的背后是对人之常情的有意压制,在诗中表达气质杂驳的凡情不符合高攀龙的心性论和工夫论,所以在谈及高攀龙诗歌时,其侄高世泰也不得不说:“偶有寄触,无非理趣。”[24]
六 结 论
要之,东林学人高攀龙并非无心学陶,而是有意效陶。晚明拟陶风气、高氏二十余年闲居田园的生活、陶渊明思想与理学的相通相契是构成高攀龙对陶渊明及其诗歌主动接受的主要因素。不仅高攀龙自己效陶,而且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挚友、同道、门生组成的效陶交游圈,乐群慕陶的普遍心态转化为一种群体性的性情系统和创作实践,并形成特征鲜明的效陶诗歌风貌。高攀龙作为代表之一,其诗歌创作对陶诗语典的引用已臻化境,故诗以拟陶著称于后世。但高诗仅得陶诗委任自然、达天知化的一面,而缺乏陶诗中爱憎喜忧的饱满情感,除两人不同的生活境遇外,高攀龙的性理思想也是其主因。陶诗的洒落恬淡是其生活和性情的本来面目,高诗的清真淡雅则是在沉潜义理中追摹陶诗而得,是学问之所见,因此不及陶诗生动。陶诗虽淡,却不压制常情,乃出于真情和肺腑而作;高诗以性束情,虽然表面淡泊平和,但实则出于学问和义理而作,反倒成为一种不雕琢的雕琢,因而缺乏真情,具有修饰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