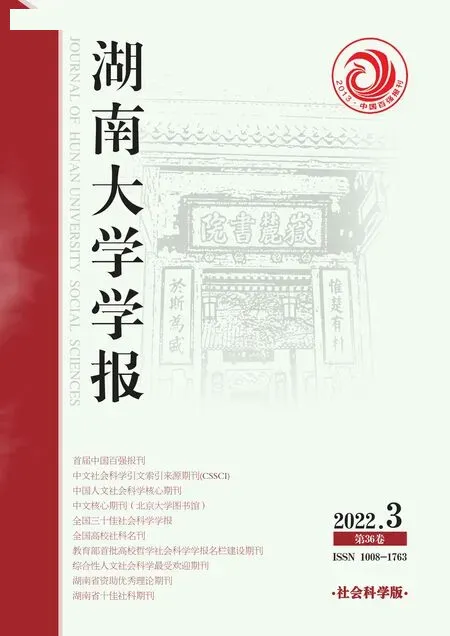《春秋》的“大义”与“微言”①**
姜广辉,秦行国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民国初年“废除尊孔读经”,传统经学传承衰歇,经典价值被深深覆盖,未能放光溢彩。近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号角已然吹响,经典价值的重估及其现代性阐释与转化成为大势所趋。六经中《春秋》一经,作为记载周王朝由盛转衰,诸侯争相称霸的历史,虽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1]3297的祸乱败亡之政,也有齐晋称霸、诸侯约盟以治的经国方略,其承载的治乱兴衰之道,是孔子借历史昭示治平之道的重要载体。然而,“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2]1968,孟子以“春秋无义战”[3]2773评价春秋,并以“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3]2772将春秋与战国等同评价,以致后儒误判春秋史的价值。事实上,五霸之国,其政之治,其国之强,殊为有方,足为史鉴。因而,将孔子借《春秋》所昭示的治平之道,亦即隐而不明、寄寓褒贬的“大义”“微言”进行发覆阐微式的阐释,正“大义”、明“微言”,显得极为重要。
诚然,学界不乏讨论《春秋》“大义”与“微言”的成果,如光绪年间就有日本学者藤川三溪著《春秋大义》,后又有辜鸿铭著同名书,更有不少春秋学者,撰有涉及“大义”“微言”的论文,但以当代价值观进行现代性阐释者则略显笔力不足,故笔者拟从“春秋之世”说起,将《春秋》“大义”与“微言”进行新的阐释。
一 春秋之世与《春秋》之书
传统史家将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前770—前476)取名借鉴孔子所作《春秋》,“战国”(前475—前221)取名借鉴《战国策》。《韩非子·五蠹》篇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4]445“上古”为西周时期,特点是竞“德”;“中世”指春秋时期,特点为逐“智”;“当今”指战国时期,特点是争“力”。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说: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5]522-523
顾炎武以六个对比,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作了区别。文中六个“犹”,是相对于“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而言,指春秋时期尚有西周礼乐文明的流风余韵。“七国”则指“兵革不休,诈伪并起”[6]1196的战国时代。概言之,若将西周视为“治世”、战国视为“乱世”,则春秋处于“治乱之间”、始乱而尚未大乱之世,诸侯国依旧可凭尚存的礼乐文明维持相对平衡。西周以后的中国历史,“治世”与“乱世”的时间相对较短,而“治乱之间”更表现为一种“常态”。因而春秋时期留给后人的政治经验尤其值得特别重视。
春秋时期,百国诸侯,大小不一,其时代特征为大国争霸,“你唱罢来我登场”,故可视其为“大国争霸史”“大国兴衰史”。春秋“五霸”,原称“五伯”,“伯”即“长”,为当时霸主,实际是“诸侯长”——盟主。诸侯争霸,就是争当“诸侯长”。诸侯长的职责是维护参盟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春秋“五霸”具体所指,说法不一。唐司马贞《史记索引》认为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其中,宋系小国,宋襄公试图以“仁义”成就霸业,最后身死国败,为后人笑,故不算霸业。宋国之外,齐、晋、秦、楚则是四大强国,各有势力范围,即:
齐国,东方;
晋国,中原;
秦国,西方;
楚国,南方。
四大强国之间,晋国东与齐国接壤,西与秦国接壤;而秦国南与楚国接壤;齐、晋与楚之间则隔着一些中等的诸侯国。这一时期的天下形势和社会矛盾主要是蛮夷与华夏之争。所谓“蛮夷”并非指周边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指南方的楚国和吴国(吴国在春秋末期才崛起)。楚国在南方,幅员广阔,疆土面积相当于中原各诸侯国面积的总和,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国家富庶,且民风剽悍,骁勇善战。这滋长了楚国统治者的骄矜心理,他们很早便自立为王,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且楚国常常发兵挑衅、滋扰中原华夏各国,对中原华夏各国构成严重威胁。所以,春秋时期,楚国长时间被中原华夏各国视作“蛮夷”。楚国国君也曾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1]1629
东周以降,周王朝已沦落为小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很弱,无法再号令天下。但周王室作为天下宗主、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名义还在。此名义仍是维系华夏族群团结的重要资源,作为一种“天命未改”的统一象征而存在。据此形势,齐国、晋国先后作为盟主国建立华夏联盟,以对抗楚国。两国高举“尊王攘夷”旗帜,“王”即指周王室,“夷”则主要指楚国。现代成语“称王称霸”,与春秋时期的“称王”与“称霸”有本质不同。楚国“称王”是不尊重周王室的表现,且想取代周王成为天下共主。正因如此,楚国“称王”被视作僭越行为。相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受到孔子肯定和表彰。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7]2511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7]2512
春秋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必须积极面对新的重大问题。其一,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其二,天下如何治理;其三,如何看待结盟;其四,如何伸张道义;等等。孔子正是在思索如何处理上述许多复杂问题的情况下写作《春秋》。《春秋》以鲁国纪年(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为线索,记载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列国的历史,以“春秋笔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孟子曾评价《春秋》一书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3]2714“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2715又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3]2670其后,荀子、董仲舒、朱熹等人说:“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8]207孟子与其后许多儒者的评论固然给予了孔子《春秋》一书崇高的荣誉,但他们对春秋之史评价未免过于负面,对“五霸”的历史作用几近全盘否定,这并不符合孔子的思想。以前的研究者受孟子等人的影响,多把春秋、战国连在一起,一同当作乱世。其实,相对战国时代杀人盈城、盈野的局面,春秋时代属于始乱而尚未大乱的时代,当世英雄是可以匡时救世、大有作为的,而齐桓公、管仲正是那个时代“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时代英雄。
《春秋》一书,如同一部大事记,记事极其简略(1)三国时张晏称《春秋》一万八千字,现实存一万六千五百余字。。所以,《春秋》若无传注说明,后人读之会感到一头雾水。《春秋》最著名的传注分别是《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即后世所称“《春秋》三传”。《公》《榖》主要讲《春秋》的宏纲奥旨,《左氏》所记为春秋之史。读《春秋》,唯三传结合,方能找到门径。正如宋代家铉翁所说:“不观《左传》,无以知当时之事,不读《公》《榖》,无以知圣人垂法之意。”[9]21
《公》《榖》所讲宏纲奥旨,即“微言”“大义”,二者对举,首出《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语——“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当然,《孟子》早已有载:“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载“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并借孔子之言“其义则丘窃取之”[3]2727-2728,道出《春秋》有“义”已为孔子所取,或是《春秋》“大义”之渊薮;而《公羊传》定公元年也有“微辞”一说,称“定哀多微辞”[10]2334,此“微辞”即为后世公羊学家谈论《春秋》“微言”的渊薮。元代赵汸将“其义则丘窃取之”之“义”理解为“此孔门传《春秋》学者之微言也。”[11]3若此,合言之,“微言大义”即“于微言中见大义”;析言之,“微言”是独家“秘传之奥”,“大义”则是众家公认的义理。
然而,后世学者对《春秋》及《公》《榖》是否有“微言”“大义”各持己见。一方面,董仲舒、何休、康有为以及多数清代公羊学者,特别强调《春秋》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董仲舒说:“《春秋》,大义之所本耶?”[12]143明确《春秋》大义有“六科”,或为“六旨”。又说:“《春秋》分十二世(即鲁国十二公)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于所见微其辞”[12]9-10,即《公羊传》所说“微辞”,也就是“微言”。康有为也以为,《春秋》有“微言大义”,且唯“大义”出自孔子,唯《公》《榖》所载为得孔子大义之门径。他说:“《春秋》之中,有《鲁春秋》之史文,有齐桓、晋文之事,有孔子之义,惟义乃为孔子所制作。”通过设问“求孔子之道于《春秋》之义,其不误乎?”“求《春秋》之义于《公》、《榖》、董、何及刘向之说,其不谬乎?”既强调“微言”“大义”之重要,并得出“据今二家(《公》《榖》)口说所存者,虽掇什一于千百,微言、大义粲然具在,浩然闳深。虽其指数千不尽可窥,然综其指归,已庶几得其门而入焉。”[13]6且康氏开篇即强调“《春秋》在义不在事与文”[13]11。
另一方面,朱熹认为《春秋》只是“直书其事”[14]3198,并无“微言”传授。但他认为《春秋》有“大义”,朱熹的学问广度与深度颇受学人推崇,学者多从其说。苏舆也认为《春秋》有大义,但对“微言”颇有微词,他说:“《春秋》为立义之书……故孔子曰:‘其义窃取’”[12]112“《春秋》以立义为宗。”[12]12他又说:“经有不见,有诡辞,皆为微言”,进一步指出:“《春秋》之微有二旨:其一,微言……其一,则事别美恶之细,行防纤芥之萌,寓意微渺,使人湛思反道,比贯连类,以得其意,所以治人也。……故吾以谓今日所宜讲明者,唯有大义。”[12]38-39
如此看来,如何正确处理“大义”与“微言”,是对其进行新的理解与阐释的基础。综合三《传》所阐及众多春秋学者所论,《春秋》自有“大义”,亦有“微言”,须分而言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春秋》有“大义”,应将其共识梳理出来,加以讨论和评判,再梳理董仲舒、何休以及清代公羊学家认可的《春秋》“微言”,并从今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出发,认真吸取其合理性与建设性的内核。
二 《春秋》“大义”
《春秋》“大义”,即《春秋》所载儒家之公理。董仲舒说:“《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谓也。……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属之分别矣;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12]143视《春秋》“大义”为绝属之分别、定尊卑之序、明君臣之职的显而可明的标准。晋杜预说:“圣人文乎鲁史,志乎周道。笔削隐显,有权有义,一正于周制而已……义焉,故有例典礼、贬僭乱、尊王以行法也。”[15]4他认为《春秋》有“例典礼”“贬僭乱”“尊王以行法”等大义,虽不全面,却是重要线索。今参读三《传》及其他《春秋》著作,结合时代需要,归纳如下:
(一)“尊王”“尊周”,反分裂
四库馆臣在《春秋左传注疏》开篇即有《御制书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一文,首载:“《春秋》,圣人尊王之经也。”[16]2其又说:“《春秋》……自隐公始,则不得不书隐公元年,而即继之曰:‘春,王正月。’前史所无有也。盖言公之元年,乃禀王之春、王之正而得是非、尊王之义。”[16]2以“春,王正月”所禀“王之春”“王之正”的意蕴,表达明是非、重“尊王”的深意。宋戴溪也说:“加天于王之上,此《春秋》之特笔也。先书‘王正月’,次书‘天王’,此尊王之大义,圣人作《春秋》之本旨也。”[17]4
上溯至汉唐,《公羊传》载:“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10]2287司马迁、董仲舒、何休、杜预皆拈出《春秋》具“尊王”“尊周”之大义。司马迁说孔子“据鲁,亲周,故殷”[1]1943;董仲舒以为,孔子作《春秋》,“黜夏,亲周,故宋”。[12]189他又说:“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12]198;何休则说:“《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10]2239“新周”“亲周”“存周”都含维护周朝礼乐文明、推重周天子之尊位的大义,即“尊王”“尊周”之大义,正合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政治理想。所以何休在注解经文“(僖公)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卒”时,说宋襄公有“忧中国,尊周室”之心[10]2252。《榖梁传》将庄公十六年十二月发生的“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一事赞为“同尊周也”[18]2384。清人齐召南就此赞誉说:“按,《左氏》《公羊》说,俱不如《榖梁》以‘同尊周’为解。”[19]624他还认为何休在“(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下注“甚恶郑伯无尊事天子之心,专以汤沐邑归鲁,背悖当诛”,实际是“明著尊王之大义”。[19]68据此,我们细读《春秋》之书,结合春秋之史,更容易理解孔子为何“尊王”“尊周”及反分裂和如何以“作《春秋》”传此大义。
儒家称夏、商、周为“三代”。夏、商两朝尚有原始部落联盟的胎记,其时小邦林立,各邦国对中心王朝(即“中国”)只是“宾服”,而非“臣服”,前者对后者并无直接隶属关系,正如王国维所说:夏殷之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20]466-467武王伐纣建周,自关中至晋、卫、燕、齐,范围数千里,成为周朝疆域。限于交通不便,如何有效控驭疆域,成为王朝重要议题。武王、周公审时度势,推行“分封制”,充分利用血缘姻亲以及功臣的默契,分封诸侯以统治广大疆域。血缘关系由此成为天然政治纽带。彼时,周王朝是宗主国,诸侯国是藩属国,两者系君臣隶属。就此而言,中国已是一个“分封制”的统一国家。异于秦朝“郡县制”的统一,周朝“分封制”下的各诸侯国拥有极大的自主权。
若干代后,周王朝与各诸侯、各诸侯之间血缘关系逐渐淡薄,诸侯利益冲突成为王朝内部主要矛盾。尤以平王东迁为界,周王朝迅速衰落,宗主国名实不符。彼时诸侯纷争,天下日益走向分裂。为使天下不致过快分崩离析,以齐桓公、晋文公为代表的诸侯盟主,借重以往周天子权威,以“尊王”“尊周”相号召,团结华夏各诸侯国,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所以《公羊传》称“齐、晋霸,尊周室”。[10]2271苏辙也说:“文武成康之德犹在,民未忘周也。故齐桓、晋文相继而起,莫不秉大义以尊周室,会盟、征伐以王命为首。”[21]2271因此,齐桓公、晋文公方能成就霸业。
齐桓公首先号召“尊王”。他倚重管仲辅佐,发展经济、军事,富国强兵。国内大治,方兴霸意。桓公霸天下之高明,乃举“尊王攘夷”大旗。其所以“尊王”,是为“正名”,以免成众矢之的,可谓抢占道德制高点,所以刘向说:“齐桓前有尊周之功。”[22]300同时,齐桓公以信义结诸侯、救邢国、复卫国,维护华夏地区各国安全,因此诸侯“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2)“就其利”犹今人言经济搭便车;“信其仁”是尊信其“仁义”精神;“畏其武”是畏惧其军事实力。[23]86,以入盟获得切实经济收益和安全保障。
晋文公亦以“尊王”号召诸侯。其为公子时,遭骊姬之难,逃难四方,待晋国内乱平定,回国收拾残局。他凭借已有国力,踵齐之履,争霸天下。争霸伊始,晋文公以谋臣赵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1]1663之谏,如齐桓公一般“尊王攘夷”。
孔子作《春秋》,处处显“尊王”“尊周”,实为肯定“五霸”行为。元代赵汸即持此观点,他以为,春秋时期的悲哀主要不在“天下无王”,而在“天下无伯(霸)”:“君臣大义以无伯(霸)而废,天理民彝以无伯(霸)而泯。”[24]699
“尊王”“尊周”,自然反对僭用“王”号。首僭“王”号者为楚。周初,武王始封熊绎为诸侯,子爵。三百年后,楚国强大,楚君熊通妄自尊大,藐视周天子,自封为“王”。古语说:“天无二日,国无二王。”[25]144楚国兴“僭”之始,若各诸侯国纷纷效法称“王”,则天下立刻诸“王”并出,政分国裂,周王朝或将分裂为诸“王”并立之朝,战国之战或将提前上演。孔子的态度是要维护天下统一,而且是“有道”的统一,即“尊王”“尊周”的统一,因此他对“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7]2521的一统局面甚为向往,对楚王僭越多加贬抑,削楚僭号,仍以子爵称之。凡记楚君去世,依例书“楚子某卒”。如:《春秋·宣公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旅”即楚庄王熊旅,又作侣);《春秋·襄公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审卒。”(“审”即楚共王熊审);等等。所以胡安国说:“荆楚僭号称王,圣人屏诸四裔而不赦之,大一统以存周,使民著于君臣之义也。”[26]616他明确指出圣人不赦僭号之楚,乃为维护大一统的周朝。清人叶酉也说:“圣人于楚,所以深恶而痛绝之者,只为其僭王。”[27]354
《春秋》“尊王”,易被误解为维护腐朽的“王权”制度。其实不然,春秋时期,西周典章制度、礼乐文明尚未完全崩坏。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仍是统一象征。所以顾炎武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可见春秋时期尚未败落成“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且彼时齐桓公、晋文公所倡“尊王”“尊周”,实际维持了天下的相对统一,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二)“选贤与能”,天下为公
贤能政治,是上古留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孔子颂扬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所反映的是原始共产制时代部落联盟领袖的选举原则,它成为尔后儒家所推崇的政治理想。《春秋》经传亦承载“选贤与能”的“大义”,宋代胡安国就说:“《春秋》大义在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26]354元代李廉也将孔子推崇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视作“《春秋》志大道、待衰世之微意”。[28]177
春秋战国的历史轨迹,是由西周松散、放权的国家统一形式,向秦汉整固、集权的国家统一形式的过渡,即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由“任人唯亲”到“任人唯贤”。春秋处于前半期,彼时“礼崩乐坏”伊始,政治、思想精英反省西周政治得失,思考如何保护已有制度文明,探索天下治道。孔子虽给人极力维护西周礼制文明的观感,实则在诠释西周礼制时,悄然质疑其原有意含。《礼记·礼运》载孔子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实则略有贬抑“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之意。因此,南宋高闶说:“天王不推至公,选贤与能,而使幼稚之子居大夫之任,以交政于诸侯,是示天下以私也。”[29]289
殷周鼎革,周人采取“分封制”掌驭全国,实行“任人唯亲”制度,此制度越往后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故而,“任人唯贤”思想便应运而生,集中表现在春秋时期儒、墨思想中系统的“尚贤”论述中。据《礼记·礼运》载,孔子曾提出“大同”“小康”之说。周朝“任人唯亲”属“小康”范畴。而尧舜“选贤与能”则属“大同”范畴。《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30]1414儒家“言必称尧舜”,其意即在于此。
从后世学者诠释《春秋》经的方向看,大多数学者赞同《春秋》笔法倡导“贤能”政治,获朱熹“《胡春秋》大义正”[14]2155赞誉的胡安国《春秋传》就是主要代表。元代后,《胡春秋》成为科举考试的官学定本。学者将其与“三《传》”并称为“《春秋》四传”。胡安国特别宣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其《春秋传》即如此。此“天下为公”非就尧舜时代的原始共产制意义而言,乃就“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社会正义而论。其隐含之义为: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乃是天下人之天下。故国家最高执政者的选拔不能拘泥于以往的“世袭”制度。胡安国说:
唐虞禅,夏后殷、周继。《春秋》兼帝王之道。贤可禅,则以天下为公,而不拘于世、及之礼;子可继,则以天下为家,而不必于让国之义。万世之通道也。与贤者,贵于得人;与子者,定于立适(嫡)。[31]48
“世”指世代相传,父子世传君位;“及”指“兄终弟及”,兄亡传位给弟弟。意即国君选择继承人时,应本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原则,破除“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之制,以免不达治道。故刘敞说:“王不推至公,选贤与能,而笃于下流之爱,使幼稚之人居大夫之任,交于诸侯,示天下以私,治何由兴哉?”[32]48
《礼记·礼运》所载孔子“大同”“小康”思想,是中国思想宝库中最可宝贵的资源之一。囿于秦汉以后的君主制,此类思想被选择性遗忘,以致后世绝少讨论。胡安国《春秋传》反复强调“天下为公”,其破“世袭”,选贤能的思想,不仅难能可贵,亦殊属大胆。
(三)天下治理,“会盟”共商
“会盟”共商,乃春秋时期的又一景象。据笔者粗略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诸侯会盟而有名者达五十余次,(3)据笔者统计,春秋时期有名的会盟有:皋鼬之盟,溴梁之盟、蜀之盟、清邱之盟、新城之盟、落姑之盟、鹿上之盟、重丘之盟、莒庆之盟、熏隧之盟、葵丘之盟、曹南之盟、首止之盟、阳榖之盟、虫牢之盟、亳城之盟、亳北之盟、萧鱼之盟、澶渊之盟、宋之盟、扈之盟、柯陵之盟、祝柯之盟、柯之盟、蔑之盟、郄犫之盟、幽之盟、贯之盟、召陵之盟、宁母之盟、牡丘之盟、垂陇之盟、蔇之盟、衡雍之盟、暴之盟、鸡泽之盟、戏之盟、平丘之盟、袁娄之盟、辰陵之盟、宿之盟、防之盟、处父之盟、黄之盟、薄之盟、谷之盟、鄟陵之盟、鄄之盟、拔之盟等。有的属于正式的结盟,有的属于盟国内部的会议。约四至五年就有一次会盟,实属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景象。
孔子作《春秋》,为何如此频繁记录诸侯会盟,其所寄寓的“大义”是什么?学者看法各异。一直以来,春秋学者对“会盟”持贬抑态度。《公羊传》称“凡书盟者,恶之也”[10]2198,几乎为“会盟”定性。胡安国也认为《春秋》“凡书盟者,恶之也”[31]24,完全以负面视角待之。西哲黑格尔曾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4)黑格尔此话的德文原文为“Was vern-ünftig ist,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eklich ist,das ist vernünftig.”范扬、张企泰译作:“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11.)北宋苏辙就从“会盟、征伐以王命为首”方面看到“会盟”的积极意义。南宋赵鹏飞也有感于此,认为诸侯会盟关乎天下大治,协同共商,“盟为美事”,故起而纠正“以盟为恶”之论。
赵鹏飞(生卒年不详),字企明,号木讷,乃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著《春秋经筌》十六卷,收入《四库全书》。明代李开先(1502—1568)说:“如杨慈湖之《易》,林之奇之《书》,《诗》则王氏《总闻》,《春秋》则木讷《经筌》,及卫湜之《礼记集说》,多有高出朱注之上者。”[33]567他认为赵氏春秋学造诣之高,胜于程朱学派(包括胡安国)。
赵鹏飞对春秋“会盟”,总体持肯定态度。他说:
《春秋》之书盟,凡以讥其不信也。然歃血要神,以期疆场之靖,不犹愈乎干戈相向,以雠兵毒民邪?以三王之世责之,则盟为不信;以春秋之时待之,则盟为美事矣。[34]7
上古之人质朴诚信,春秋诸侯会盟之所以要歃血盟誓,乃因时人已缺少古时的质朴诚信。另一方面,诸侯会盟,协商天下治理之事,减少诸侯国间的疆场厮杀、避免士兵和民众伤亡,维护天下相对和平稳定,何尝不是天下美事,何尝不是“天下为公”!所以宋人沈棐也说:“有朝聘、会盟,所以讲信修睦,辑宁邦国。”[35]42他又说:“《春秋》之法,善盟会,恶侵伐。盟会非先王盛礼,《春秋》且善之,以当时诸侯侵伐相寻,残民敌国,为害最大。圣人疾之,且幸其有会盟也。”[35]225他强调“非先王盛礼”的“会盟”可免“诸侯侵伐”“残民敌国”之害。
凡事皆有因。春秋时期,频繁会盟,主要出于夷、夏之争的需要。如前所述,那时的“夷”主要指楚,楚虽为周朝封国,因地处南方,在长期发展中远离华夏文明。因此,“楚王”凭其日益强盛的实力经常侵犯华夏诸国。华夏文明有被毁灭和取代的危机,即“以夷变夏”。中原虽有齐、晋强国,但单凭一国仍显“势孤,力不能抗楚,而楚之祸方深”[36]595,故中原各国有同心结盟的意愿,所以《公羊传》说:“同盟者何?”“同欲也”“同心欲盟也。”[10]2234诸侯“结盟”可迅速改变与强楚的力量对比,使盟军军力足以压制楚军北上,因此,春秋时期楚军始终未能冲破华夏的势力范围,由此而有近两百年大体和平之格局。所以《榖梁传》解释“同盟”时四次提到“同外楚也”。[10]2409就此而言,春秋“会盟”,维护了地区和平,维护了华夏文明的存续与发展。故而程颐会说“天王崩,而会盟不废”[26]614,以突显“会盟”在春秋时期的重要价值。
(四)倡仁道,鄙“诈力”
《论语·子路》载:“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7]2507一“世”为三十年。孔子认为,王者出世,三十年间可以推行仁政。孔子主张以仁义得天下,反对以诈力取天下。这也体现在其《春秋》笔法中,因此《公羊传》提出了“崇仁义”说,《榖梁传》则明确指出:“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18]2435《公羊传》说:“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10]2200宋人刘敞也说:“为天下,岂可以诈力哉?”[32]525他更直言:“居中国,弃人道,废仁义,则必死矣。”[32]498孔子作《春秋》,倡仁道、鄙“诈力”,具体表现在:
1.表彰齐桓公以“仁义”行天下
《论语·宪问》载孔子语:“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7]2511“九合”泛指“多次”,而非实数。史载齐桓公主持会盟十五次,以兵车相会者四次,不以兵车相会者十一次。《春秋·庄公二十七年》载:“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37]1780此“同盟”之“同”于《春秋》笔法,颇有深意。《榖梁传》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18]2387齐桓公、管仲以诚信结诸侯,爱惜民命,不轻启战争,所以孔子赞桓公和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表彰其仁道精神。
2.鄙视“诈力”
“兵不厌诈”几成后期兵家思想中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此思想较早见于战国法家著作《韩非子》,其《难一》篇载:“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4]347其意为:两军交战,不排斥诡变、诈伪的策略或手段。此类思想春秋时已有萌芽,尚未普及。那时,两军作战,须列堂堂之阵、竖正正之旗,以示先礼后兵的君子之风。故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7]2511“谲”就是狡猾、玩弄欺诈手段。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履行流亡楚国时对楚成王的承诺,若两国交战,主动退避三舍(九十里)。楚军贸然进攻,中晋军诱敌深入之伏,全军覆没,统帅子玉自杀,晋军大获全胜。虽如此,但孔子更欣赏齐桓公的做法。当时楚国恃强凌弱,觊觎华夏,齐桓公曾率九国联军进兵楚国边境,造成一种威慑气势,逼迫楚国求和,签订“召陵之盟”的“和平协议”,承诺互不进犯。齐桓公“不肯黩兵血刃,以轻用民命”[38]158,为后世称道,成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孔子反对诸侯间相攻不已,尤其反对灭国绝祀,是想保持诸侯国间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进而恢复西周时期的友爱和睦状态。《论语·尧曰》载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7]2535之语,即是此意。孔子反对诸侯以诈伪取胜,认为那样会互相效法,陷入恶性循环,世道人心会愈来愈坏。故其“《春秋》笔法”有意贬抑诸侯“诈伪”之行,哪怕两军交战,也不赞同“诈伪”取胜。
《春秋·鲁定公十四年》载:“五月,于越败吴于檇(音醉)李,吴子光卒。”[37]2150-2151此条材料如何体现“《春秋》笔法”?首先,按《春秋》笔法,凡诈伪之战,书“月”不书“日”,此经文只书“五月”,未书“日”,无形中将其定为“诈战”,认定是不值得纪念的战争。其次,书“于越”而不书“越”,有贬抑之意。《春秋》书越国有称“越”,有称“于越”。越国人读“越”字拉长音,读成“于越”,具地方色彩。《春秋》正常书越国之事时,单书“越”字,若越人行事不合道义,则书“于越”以贬抑之。如《春秋公羊传·定公五年》所说:“于越者何?越者何?于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10]2338最后,书“于越败吴”,即越军打败吴军。越败吴而不书“胜”,亦贬抑越军以诈取胜。
先前,吴、楚有“鸡父(楚国地名)之战”,吴军以“诈力”大败楚军,此次吴越“檇李之战”,越军又以“诈伪”大败吴军。宋洪咨夔就此评价说:“以诈遇诈,诈有时而穷;以力遇力,力有时而穷。穷则我之施于人者,人得以反诸我矣。”[39]699
三 《春秋》“微言”
“微言”“大义”最早并举于西汉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书载:“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2]1968。由此可见,“微言”“大义”对应孔子所修《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六经中内蕴“微言”和“大义”。但汉唐之世,强调以“微言大义”解释六经的学者并不多。春秋学,虽然有“微辞”“大义”之说,但二者有殊,且对“微言”所指,颇有异义。
至宋代,学者开始较多谈论“微言大义”,宋儒以为周敦颐、二程发现了孔孟的“微言大义”。不过,他们所说的微言大义,是从心性理气的哲学方面说的,不是从改制变法的政治方面说的。到了明代,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三十《续问上》载:
问:“刘歆曰:‘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夫果有‘微言大义’哉?”曰:“自六经四子,莫不有‘微言大义’。《诗》《书》《语》《孟》,大义悉于微言。《易·系》《中庸》,微言详于大义。故由大义可以升堂,由微言可以入室。”[40]665
胡直认为,只有洞悉“六经四子”的“大义”“微言”,才能登堂入室,优入圣域。他所说的“大义”“微言”也未专就春秋学而言。这意味着,直到明代,“微言大义”或“大义微言”还只是一种笼统说法。
着意《春秋》讲“微言大义”,大概是从清代公羊学派开始的。四库馆臣提出,春秋学著作有“大义微言”,盛赞北宋经学家刘敞《春秋意林》阐释“大义微言,灼然圣人之意者,亦颇不少”。[41]216晚清经学史家皮锡瑞认为,孔子《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法制”[42]261“大义显而易见,微言隐而难明。”[42]262
现代学者研究《春秋》经一般认为,只有公羊学派讲“微言大义”,《左传》学派,榖梁学派一般不讲“微言大义”。实际上,清代公羊学派中也分两派,一派如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皮锡瑞等特别强调“微言大义”;另一派如孔广森、凌曙、陈立等并不甚讲“微言大义”,他们因此被视为“不明公羊家法”。对此,今人该如何看待?
笔者以为,汉代公羊学派解释《春秋》时,认为孔子有“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思想以及新夷狄观等不见于《春秋》经明文的,即为“其义则丘窃取之”之“义”,同时也是“孔门传《春秋》学者之微言也”之“微言”。这些是孔子的思想精髓,是孔子通过口述或暗喻的方式传授给弟子门人的。唯其如此,公羊学派所主张的“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思想以及新“夷夏”观才能作为一种理论立足于世。公羊学派与《左传》学派、榖梁学派相比,其鲜明特点就是:对经典的解释采取一种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态度,其主要理论特色不在一般春秋学家所公认的“《春秋》大义”,而在“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思想以及新“夷夏”观等“微言”,恰是这几个“微言”构成了公羊学的理论支柱。这些理论对于历史规律的阐释以及对政治经验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中国经学思想史中的一份宝贵遗产,不应轻易否定和抛弃。
(一)“大一统”
此为国家统一理论,即国家必须统一于中央王朝。“大一统”就是尊重、重视国家统一,“大”是动词,即尊大、重视之意。这个理念由何而来?《春秋》经以鲁隐公元年开篇:“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0]2196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采用本国君主纪年,新君即位,纪年改元,以示万象一新。但鲁国采用周历法,“王正月”就是周王朝历法中的正月。《公羊传》的解释是将历法意义上的“尊王”变成政治意义上的“尊王”,而将政治意义上的“尊王”目的解释为维护“大一统”的理念,由此揭示孔子苦心孤诣作《春秋》,其“尊王”之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维护“周天子”的权威,而是维护天下所有族群的统一,避免走向分崩离析。
“大一统”思想的意义在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它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它为中国的长期统一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信仰力量。
(二)“通三统”
此为制度文化创新与包容的理论,即一个新王朝既要开创本朝制度文化的新传统,同时也要参考和吸收前两朝制度文化的旧传统。“通三统”理念缘何而来?《公羊传·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10]2204宋国系殷商后裔,公爵。何休《公羊解诂》阐发为何宋国国君是最高的公爵时说:“宋称公者,殷后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而不臣也。”[10]2204此前,董仲舒曾解释“封二王后”即分封夏、商两朝后人的道理,说:“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12]198此处,董仲舒提出了“通三统”的理念。其意是说,对于新兴的周王朝而言,尊重夏朝和商朝的历史贡献和制度文化,允许其后人继续保留其制度文化,“使服其服,行其礼乐”,将其视作国家上宾,而非臣子;意即:新兴的周王朝不是把夏朝和商朝的制度文化完全铲除掉,而是借鉴和参考这两朝制度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将其吸纳周王朝的“礼乐文明”中。对于周王朝这种文化包容精神,孔子极为赞赏,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中国文化中的“通三统”思想到后来发生了转化,不再是仅仅继承先前两朝的制度文化,而是有所放大,即在主流文化之外,参考和吸收其他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比如宋朝以儒为主,兼重佛、道,三教并用。南宋孝宗说“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43]756,可谓新的“通三统”。
“通三统”思想的当代价值,即圆融并包,取长补短,吸收一切优秀文明的精华,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可将其视作中国文化的遗传密码,它使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事实上,现在大学的哲学系同时开设“马哲”“中哲”“西哲”课程,或可称为另一种“通三统”。
(三)“张三世”
此系历史进化的理论,即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三大阶段:由“据乱世”走向“升平世”(小康社会),最后到达“太平世”(大同社会)。《春秋》经文原无此意,此理论是公羊学派先师一步步推演发展提出的。
董仲舒将《春秋》鲁国十二公分为三个阶段,其《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说: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12]9-10
“君子”实指孔子。昭、定、哀三世,六十一年,是孔子一生所见证的时代,称为“所见世”;宣、文、成、襄四世,八十五年,是孔子从其长辈那里听闻的时代,称为“所闻世”;隐、桓、庄、闵、僖五世,九十六年,因年代遥远,属传闻时代,称为“所传闻世”。三个时代远近不同,孔子的处置也不同。“所见世”系现世的人和事,不免有利害冲突,所以要“微其辞”,采用隐微避讳的笔法。对“所闻世”的社会弊端,因不牵涉利害冲突,可痛陈其祸。对“所传闻世”,因时代久远,恩义情感已大为减杀。故而孔子作《春秋》,对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笔法。
董仲舒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大时段,即后世所说“三世”。“三世”的客观历史并未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演化。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将其作为进化理论来阐扬。何休说: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10]2200
何休将“三世”定性为:由远至近,“所传闻之世”是“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所闻之世”是“见治升平”;“所见之世”是“著治太平”。此进化史观被后人冠以“张三世”的名目。(5)何休关于公羊学研究的著作有很多,如《春秋文谥例》《春秋汉议》《公羊墨守》等,今皆遗佚。从其所传世的《春秋公羊解诂》中并不见“张三世”的概念。今所见到的关于“张三世”的最早资料出自宋均。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载:“案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或许何休遗佚著作中有“张三世”的概念,或许宋均与何休意见接近,学者将“张三世”概念归于何休名下。事实上,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越往后越乱,为何硬要将其写成不断进化的历史?据公羊学家的解释,此乃孔子借《春秋》寄寓其理想。故学者强调,对于《春秋》,不应以历史书读之,而应以政治书读之。如清代皮锡瑞解释说:“孔子并非不见《国史》,其所以特笔褒之者,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孔子是为万世作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作史,而纪实以征信也。”[42]282这种看似何休借助“张三世”命题宣传的进化历史观,公羊学家把它说成是孔子本人的“微言”,或可将其视作一种经典解释学的别派。
“张三世”理论的当代价值,在于劝诫社会改革,劝导与时俱进,以免积弊兴乱。中国文化中有“大同”思想,但“大同”思想依托的是尧舜时代的原始公产制。若想实现社会“大同”,就要回到尧舜时代,那无异于倡导复古,开历史倒车。公羊学派提出的“张三世”思想则不然,它讲社会发展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是主张社会改革的理论。晚清康有为主导的“维新变法”即依托公羊派提出的“张三世”理论。
(四)新“夷夏”观
新“夷夏”观是一种对先进文化认同的理论,也是一种民族融合与平等的新观念。新“夷夏”观所说的“夷狄”与“华夏”不以地域和种族划分,而以文明先进性划分。夷狄之人文明先进,就是中国;反之,中国之人文化落后,即为夷狄。梁启超出于公羊学派的立场,曾作《春秋中国夷狄辨序》(6)此文发表于1897年8月18日《时务报》第36册,是梁启超为友人徐勤(字君勉)所著《中国夷狄辨》所写的序言。说:“《春秋》之号夷狄也,与后世特异。后世之号夷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44]124何种“政俗”与“行事”为区分中国与夷狄的标准?梁启超总论《春秋》之义说:“《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自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44]124春秋之时,偶有华夏诸侯行事恰与此相反,为《公羊传》所痛斥,如《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说:“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10]2327《公羊传》向往多民族的融合,提出的理想目标是华夏与夷狄和谐相处,“华夷一统”,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即《公羊传》所载:“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文化落后民族在文化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会逐步摆脱落后面貌,共同创造新的文明社会。
新“夷夏”观的当世价值,即学习先进文明,促进民族融合与文明交流。以当世言之,即为一种先进的民族观、文化观。
综上所述,“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新“夷夏”观等,均为《春秋》公羊学派的重要理论贡献。其对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激励社会改革、除弊兴利,促进文明交流、民族融合与团结均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四 结 语
自西周以降,中国历经三千年发展,虽然天下分分合合,总以统一为依归,其主导的精神力量就是出自《春秋》的经典诠释学的“大一统”理论。因此,回看春秋之史,虽然有孟子及其影响的儒者给予负面的评价,但却不能完全抹杀春秋史上遗留的宝贵思想与政治智慧。《春秋》经传很好地发掘和阐扬了春秋历史的正面价值。“春秋争霸”,诸侯之间上演了一部“大国争霸史”,却不同于当代的“霸权主义”。因为诸侯盟主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参盟各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目标是获得同盟国的尊敬,而不是侵伐他国利益,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古代大国争霸的范式,即在大国崛起、群雄并歭的形势下,如何在各国之间订立一种共生共存、相对平衡的社会准则。春秋时期频繁的会盟实际就是要解决此问题。孔子作《春秋》,就是要在天下将乱之时提出天下治理的是非准则,即《春秋》中寄寓的“大义”和“微言”,循此准则,天下将复归于“治”;违此准则,天下将日趋于“乱”。《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作《春秋》以前,《诗经》曾经作为社会价值观的载体;孔子作《春秋》之后,《春秋》便成为了社会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之一。这种价值观以“大义”与“微言”两种形式表现,具备与时俱进的特质和现代性转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