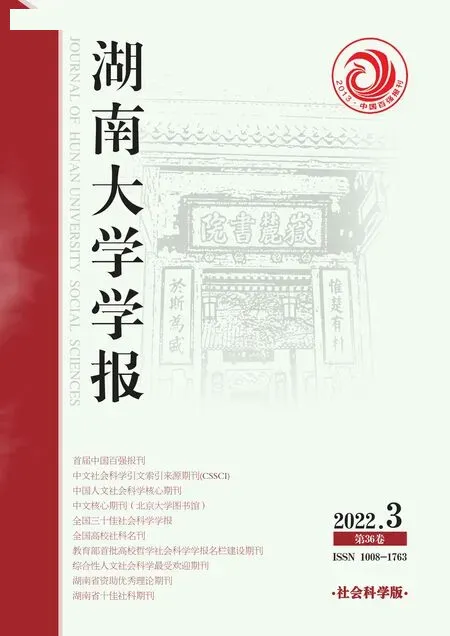《春秋正辞》的成书与清代公羊学的开山*
郑任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春秋正辞》是常州学派创始人庄存与(1719-1788)的代表作,也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山之作,在清代经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杨向奎先生说:“溯源导流,清代公羊学的首倡者当推庄存与。”[1]177然而《春秋正辞》迟至道光七年(1827)才刊刻,在此之前孔广森(1752-1786)《春秋公羊通义》已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撰成,嘉庆十七年(1812)刊刻,那为何还能称《春秋正辞》为清代公羊学的开山呢?
在《春秋正辞》正式面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世人的印象里的确是以《春秋公羊通义》为清代第一部公羊学著作。刘逢禄在嘉道年间就说:“清兴百有余年,而曲阜孔先生广森始以《公羊春秋》为家法。”[2]57刘逢禄作为庄存与的外孙,亦是推始于孔广森。《春秋正辞》刊刻的迁延,造成了清代公羊学开端的迷蒙,刘逢禄的话使之更为缴绕不清。清代公羊学究竟是始于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还是庄存与《春秋正辞》,这是清代公羊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学界争讼多年的一桩公案。目前关于此问题的看法,大体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意见以庄存与《春秋正辞》为首部著作。如陈其泰先生主张:“孔广森《公羊通义》撰成于乾隆年间,是清代继《春秋正辞》之后第二部公羊学著作。”[3]黄开国先生认为:“《春秋正辞》虽然早已成书,却未能刊刻。……决不能以庄存与著作的刊刻在后,就说孔广森是清代治《公羊传》的第一人,而否认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4]
第二种意见以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为首部著作。如朱维铮先生认为:“在清中叶,首先明言模仿赵汸的《春秋属辞》,对《春秋公羊传》进行专经研究的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孔广森所著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庄存与的书不仅了无新意,还较孔书晚出。”[5]166-168
第三种意见则承认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在时间上占先,但是从公羊家法出发,仍将庄存与立为公羊初祖。如梁启超先生认为:“清儒头一个治《公羊传》者为孔巽轩(广森),著有《公羊通义》,当时称为绝学。但巽轩并不通公羊家法,其书违失传旨甚多。公羊初祖,必推庄方耕(存与),他著有《春秋正辞》,发明公羊微言大义。”[6]192
笔者完全支持以庄存与《春秋正辞》为清代公羊学首部著作的意见,主张《春秋正辞》不仅在撰著时间上早于《春秋公羊通义》,而且从学术渊源上讲,《春秋正辞》也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山之作。
一 撰著时间的考察
考察《春秋正辞》与《春秋公羊通义》孰先,显然不宜由刊刻时间进行简单判断,否则刘逢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及凌曙《公羊礼疏》嘉庆年间皆已有刻本,道光七年刊刻的《春秋正辞》岂非要排到第四以后了?如若这样,清代公羊学的发展脉络也就彻底乱了。
之所以会产生孰为清代公羊学开山的问题,根源在于《春秋正辞》的撰成时间未能明确。《春秋正辞》的刊刻虽晚,而成书甚早。该书刊刻其实已在庄存与身后四十年。清人董士锡曾言:“乾隆间……庄先生存与侍郎官于朝,未尝以经学自鸣,成书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无闻焉。”[7]192陈祖武先生认为,“《春秋正辞》当撰于乾隆三十至四十年代间。”[8]635笔者大致同意,甚至认为可能还会更早一些。
据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叙》:“武进庄方耕少宗伯,乾隆中以经术传成亲王于上书房十有余年,讲幄宣敷,茹吐道谊,子孙辑录成书,为《八卦观象上下篇》《尚书既见》《毛诗说》《春秋正辞》《周官记》如干卷。”[9]237-238则《春秋正辞》正是庄存与在上书房为成亲王授课时的讲义基础上辑录而成的。(1)参见刘桂生《从庄存与生平看清代公羊学之起因》,《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王俊义《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坤对立”说辨析——兼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庄存与在上书房期间,“卯入申出,寒暑无间,皇子时亲讲说,爱敬日深”[10]227。乾隆三十九年(1774),庄存与出任河南学政,成亲王永瑆作《送庄方耕师傅提督河南全省学政序》送别:“先生教诲余数年,至意周尽,不可一二记忆。教以《周易》,谢未能也;教以《禹贡》,谢未能也;教以《春秋》,谢未能也;教以《周礼》《仪礼》,谢未能也;教以乐律、《周髀》算数,谢未能也。以为时日优(悠)远,可以次及耳。而先生今去余矣。”[11]197永瑆表达了对庄存与的不舍之情,明确提到庄存与授其《春秋》。在庄存与为永瑆授课的这几年中,《春秋正辞》作为讲义至少应当有一个初步的稿子。
永瑆还有诗《礼部侍郎武进庄方耕先生》:“成童稍识义,实赖与君居。餍饫游余志,深沉授古书。”[11]138“成童”按范宁之说为八岁,按郑玄之说为十五岁。(2)《穀梁传·昭公十九年》:“羈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范宁注:“成童,八岁以上。”《礼记·内则》:“成童舞《象》,学射御。”郑玄注:“成童,十五以上。”永瑆出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3)据《清实录》第14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六》,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50页。依郑玄说,其十五岁时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恰与庄存与乾隆三十三年(1768)受命在上书房行走的时间相当。庄存与出任河南学政后,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丁母忧,四十四年(1779)署礼部左侍郎,旋补礼部右侍郎,四十七年(1782)再度受命在上书房行走,直至五十一年(1786)“原品休致”。(4)据汤志均《庄存与年谱》,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29-38页。由此,庄存与两入上书房的时间,正合魏源所说的“乾隆中以经术传成亲王于上书房十有余年”(5)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说:“公通籍后,在上书房授成亲王经史垂四十年。”庄存与自乾隆十年(1745)登第始,全部仕途方有四十余年,而庄存与致仕时成亲王年方34岁。可见阮元此说必误(“四”字或衍),而魏源之说为是。。
或许,《春秋正辞》更远在教授成亲王之前即已有成稿。宋翔凤在为庄存与之侄庄述祖所作行状中曾提到,当庄述祖之父庄培因去世之际,“时伯父侍郎公于五经皆有论说”[12]3108。庄培因去世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当时庄存与于五经皆已有论说,如此则《春秋正辞》的成稿时间或又可推至乾隆二十四年之前。
《春秋正辞》成稿于乾隆二十四年之前,是完全有可能的。庄存与很早就显现出了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臧庸说他“长益沉潜经义,诵诗读书,惟以知人论世为准”[10]228。在乾隆十七年(1752)之时,庄存与已有“素精《董子春秋》”之声,熟谙公羊学。据刘逢禄记载:“越岁(乾隆十七年)大考翰詹,拟董仲舒天人策第三篇,公素精《董子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上大嘉叹,即擢侍讲。”[2]184在乾隆十七年的翰詹大考中,庄存与已经表现出了对董仲舒公羊学的驾轻就熟。在《春秋正辞》的行文中,庄存与也是大量地征引董仲舒之说,而且经常是不吝篇幅地大段摘录,因此阮元说庄存与“《春秋》则主《公羊》董子”[1]3。
《春秋正辞》早成还有一个佐证。庄存与乾隆二十三年(1758)任直隶学政期间,“按试八旗,防范周密”[14]122,试图整顿旗人考试走过场的现象。庄存与在《春秋正辞》中,痛陈“世卿者,失贤之路,蔽贤之蠹也”,强调“非贤不可以为卿”[15]59,主张不管是否是贵族,都要通过考察其贤能来委任官职,亦表现出了以“讥世卿”之义来改变满洲贵族世官世爵特权的意图。因此,他在直隶学政任上“按试八旗”的作为,是与其“讥世卿”思想相契合的,可以看作是对公羊学“讥世卿”的一种实践。由此,乾隆二十三年也可以成为我们考察《春秋正辞》撰著的一个参考坐标。
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我们很难断定《春秋正辞》究竟撰定于哪一年,但既然《春秋正辞》为庄存与为成亲王授课之讲义,其在乾隆三四十年代应当已经成稿。基于庄存与在乾隆十七年表现出来的对公羊学的精通,乾隆二十三年对公羊学思想的某种实践,尤其是从他在乾隆二十四年之前已“于五经皆有论说”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时《春秋正辞》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了。
二 乾隆皇帝态度的旁推
有学者认为,乾隆皇帝对《公羊传》持“抛弃”态度,庄存与“身处漩涡中心的上书房,他岂敢编写公羊讲章公开宣讲?”[16]乾隆确实对《公羊传》有一些微词,曾“御制”两篇《读公羊》,对《公羊传》的立嫡原则与许世子止弑君之论进行批驳。但考虑清代自立国始至于乾隆朝,包括乾隆皇帝自己,所有即位的皇帝均非嫡子、长子,乾隆更先后两次立嫡子为太子均遭夭折,其指摘“以长不以贤,以贵不以长之说实甚谬”[17]493当然可以理解。而对《公羊传》所说的许世子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18]586,乾隆虽然批评以“迂儒,失圣人之旨”,认为这是“逆天之诛”,许止之罪止于“不敬误投之咎”[17]189而已,但却又多次用《公羊》此义指示司法部门如何给有关案件定刑。乾隆二十八年(1763)有子放枪捕贼而致伤继母身死一案,乾隆依“《春秋》许世子止之义”,定以缳首。而且经此案,“向例子孙过失杀祖父母、父母止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也被改为“绞立决”[19]733。乾隆三十四年(1769)关于另一起案件的上谕,乾隆驳斥刑部所拟,称:“依经定律,其理本属相通。《春秋》著许世子止之条,义例具在,特罪其不亲尝药,即难逃一字之诛。刑部堂官中,岂无读书通义者?”[20],对刑部堂官不通《公羊》此义还进行了严厉斥责。
而且综观乾隆对三传的态度,也未见得对《公羊传》有什么特别的不满。他对三传其实皆有批评,说“三传为素王辅臣,而各有失”[21]430,既说“公羊、穀梁,去圣逾远”,也说“左氏或详于事而失之诬”[17]112“左氏浮夸”[21]317“邱明博于纪事,但逞其文藻,而昧于知理”[21]497。乾隆四十六年(1781)议定祈谷礼用上辛,所据经传即有《公羊传》何注。[22]23乾隆五十七年(1792)礼部尚书纪昀奏请考试《春秋》弃胡安国传,“俱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穀梁》”[23]1092,获准。
不仅如此,乾隆对汉代公羊大家董仲舒还特别推崇,称“汉仲舒董氏,经术最醇”[24]133,策论题、上谕、御制文更频频称引董子。正如蔡长林先生所说,“终乾隆帝一生,对董生之称扬未曾稍替,而屡屡表彰之”[25]182。也正因为如此,在乾隆十七年的翰詹大考中,乾隆才会对庄存与精通董说的表现“大嘉叹”。
可见,从乾隆皇帝的态度来看,庄存与实在没有什么避讳公羊的理由。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皇帝在教训永瑆的上谕中强调:“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己,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26]366而庄存与的治学风格正是讲求大义,“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13]。如此看来,《春秋正辞》作为讲义,其学术风格也正符合乾隆皇帝的要求。
我们看到,《春秋正辞》与这个时段乾隆皇帝对《春秋》的表述还有不少和拍的地方。乾隆非常重视《春秋》“大一统”之义,称“所谓大一统,……兹为开宗始义,乃贯《春秋》之本末”[27]4,更屡屡以“大一统”之义谕示群臣。《春秋正辞》中,庄存与则标举“大一统”是“治《春秋》之义莫大焉”[15]10,强调“《春秋》之义,务全至尊而立人纪焉”[15]51,以“大一统”之义鼓吹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
与乾隆一样,庄存与也否定《公羊传》主张的嫡长子继承制。庄存与在《春秋正辞》中只字不提公羊家“立适(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之说,并在鲁隐公与桓公孰正的问题上,坚持“惠公之命在隐公,不在桓公”,认为隐公有君父之命而得立,因而“宜为正”[15]77,69,完全不认同《公羊传》从“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出发而认定隐公“不宜立”[18]13-15的说法。
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皇帝为《春秋直解》撰序称:“中古之书,莫大于《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属辞比事。而原夫成书之始,即游夏不能赞一辞,盖辞不待赞也。……矧以大圣人就鲁史之旧,用笔削以正褒贬,不过据事直书,而义自为比属其辞,本非得已,赞且奚为乎?”[17]112乾隆皇帝这里表达了对《春秋》的重视,其以“属辞比事”概括《春秋》之学的论说,与元代经学家赵汸之说极为接近。赵汸作有《春秋属辞》一书,称:“《春秋》之学只是属辞比事法。”[28]258“《春秋》,鲁史策书也,……凡史所书,有笔有削,史所不书,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则史’,主实录而已。《春秋》志存拨乱,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29]330而庄存与明言自己作《春秋正辞》正是受了赵汸《春秋属辞》的影响,其在《春秋正辞》序中写道:“存与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辄不自量,为櫽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15]5可见,《春秋正辞》的书名都改自赵汸的《春秋属辞》。我们深度怀疑,《春秋正辞》的撰著与乾隆皇帝对“属辞比事”之法的推崇也有很大的联系。
自乾隆十七年(1752),庄存与“升侍讲,入直南书房”[14]16,常侍皇帝身边,备顾问、论经史,皇帝的态度自然会影响他,而他在经史方面的见解也多少会对皇帝产生一定影响。从《春秋正辞》看,庄存与遵循“属辞比事”之法,讲求大义,突出强调“大一统”,推崇董仲舒,否定《公羊传》的嫡长子继承制,与乾隆对《春秋》的态度和要求保持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皇帝推崇“属辞比事”的《春秋直解序》撰于乾隆二十三年,正与前文所提到的乾隆二十三年“按试八旗”、乾隆二十四年“于五经皆有论说”在时间上有所契合,这也进一步为我们说《春秋正辞》于乾隆二十四年之前已有成稿提供了佐证。
三 刊刻推延原因的分析
《春秋正辞》的刊刻实是迁延日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说:“阅庄氏《味经斋遗书》,凡《尚书既见》三卷,《尚书说》一卷,刻于乾隆癸丑,无序。《毛诗说》四卷,刻于道光丁亥,亦无序。《周官记》五卷,刻于嘉庆癸亥;而末有其孙绶甲跋,则题道光丁亥。又《周官说》五卷,据绶甲跋,《周官记》五卷及《周官说》前二卷,皆侍郎手定,其后三卷,则绶甲于遗稿中辑录者也。《春秋正辞》十一卷,附《举例》《要旨》各一卷,亦刻于道光丁亥,前有朱大兴序,题嘉庆辛酉。”[30]1167可见庄存与诸书,最早刊刻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嘉庆八年癸亥(1803)又有部分刊刻,最晚的即如《春秋正辞》,随着《味经斋遗书》一起于道光七年丁亥(1827)刊刻。庄存与生前未有一书付梓,即如最早的《尚书既见》《尚书说》,其刊刻已在庄存与去世后5年,而《春秋正辞》的正式刊刻更在庄存与身后40年。
《春秋正辞》卷首有嘉庆六年(1801)朱珪序,序中称:“公之孙隽甲,为余丙午典试江南所得士,偕其弟贵甲来京师,持公所纂《春秋正辞》一书问序于余。”[15]4由朱珪序我们可以推测,嘉庆六年庄隽甲兄弟持书稿向朱珪求序,应该是计划将《春秋正辞》与《周官记》放在一批,于嘉庆八年左右刊刻,但索序之后却耽搁了下来,一放又是26年。
既然早有书稿,《春秋正辞》为什么一直不刊刻呢?为何又一推再推,乃至令人对其在清代公羊学的开山地位产生怀疑?
笔者以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正如阮元所说,是庄存与感到“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13]。庄存与主要生活在乾隆时代,在推崇“训诂明,六经乃可以明”[31]801的乾嘉时期,庄存与实堪称异类。梁启超称其“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32]74-75。《清儒学案》亦称其“在乾隆诸儒中,实别为一派”[33]2793。庄存与的《尚书既见》即使到了同治年间仍被李慈铭斥为“皆泛论大义,多主枚书,绝无考证发明之学”,“附会纠缠,浮辞妨要,乾隆间诸儒经说,斯最下矣”[30]109。另一方面,应该与《春秋正辞》始终未能完成修订有关。庄存与沉浮宦海四十余年,历任翰林院编修、詹士府少詹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前后为同考者二,主乡试者四,为会试总裁者一,为学政者三,为香差者一,知贡举者一,天文、算法总裁官及乐部大臣”[14]122,更罕见地长期兼值南书房及上书房,一直无暇对书稿进行系统的整理,一些缺失的部分始终未能补齐。
庄存与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致仕之后,即准备对书稿进行整理修订。鲁九皋《祭庄座主文》称:“前年尚奉手书,谓平生于诸经疑义皆有训释,今得归田,将订正成书,命九皋进与校字之役。顾九皋以老母多疾,未克遄趋函丈朝夕请业。”[34]1只是这项工作未及展开,庄存与就于乾隆五十三年病逝了。鲁九皋所转述的“平生于诸经疑义皆有训释”之言也进一步验证了《春秋正辞》早有成稿的结论。
今天我们见到的《春秋正辞》,虽经庄氏后人整理,但仍缺失严重。如卷一《奉天辞》叙目中列有十例,文中有二例未见。卷二《天子辞》叙目列有二十五例,文中有十二例未见。卷三《内辞上》叙目列有十六例,文中有六例未见。其余诸卷大致仿此。不过,虽然文有缺失,但例目皆在,且主旨也都已经在叙目中交代清楚,全书整体框架亦已完具。而且这些例目,是庄存与经过对《春秋》经文的属辞比事而归纳出来,并分列于各辞之下的。能提出这些例目,说明庄存与其实已经分配好了目下的内容,只是无暇完成而已。
当然有些残阙也可能是年月长久而造成的散失。按庄绶甲《周官记跋》,庄存与《周官记》五卷及《周官说》前二卷皆庄存与手定,《周官说》后三卷,则由庄绶甲“于遗稿中检得零章断句及批注简端者,并录而编之成三卷”[35]。《春秋正辞》可能也与《周官说》的书稿类似,或本有缺,或年久散失,子孙只能就遗稿进行辑录。
四 学术渊源的梳理
如果说撰著时间很难精准断定,那么从学术渊源上进行梳理的话,《春秋正辞》为清代公羊学开山之作则是可以确定的。
首先,孔广森研习公羊学实质上是受了庄存与的影响。阮元曾明确指出二者的这种关系:“通其(庄存与)学者,门人邵学士晋涵、孔检讨广森及子孙数人而已。”[13]《清儒学案》亦将孔广森列入“方耕弟子”[33]2868-2869。
孔广森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恩科进士,当年会试的副主考官正是庄存与,因此孔广森称庄存与为座主。孔广森选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正逢庄存与“受命教习庶吉士”[14]30,于是又跟随庄存与问学。孔广森提及这段从学经历时,说:“某等曾趋鱼亶座,窃附龙门,白虎观前,伏受《汉书》之义;绛纱幔侧,与传《周礼》之经。”[36]14与孔广森同科的进士鲁九皋,在《祭庄座主文》中亦称“始以文字见知,继而以传经相属”[34],可见庄存与和不少门生有着实质上的学术授受关系。而孔广森与庄存与之间更是非一般的门生与座师或者庶吉士与教习的关系,学术上确实存在师承关系。《春秋公羊通义》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条下孔广森自述说:
座主庄侍郎为广森说此经曰:“屈貉之役,《左氏》以为陈侯、郑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后至,圈子逃归。《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蔡,同姓之长,而世役于楚,自绝诸夏。商臣弑父,罪大恶极,犬彘将不食其余。盖窃位以来,诸侯尚未有与盟会者,蔡庄侯首道以搂上国,独与同恶相济,同气相求,不再传而蔡亦有弑父之祸,遂使通《春秋》唯商臣与般相望于数十年之间。若蔡庄侯者,所谓用夷变夏者也。”广森三复斯言,诚《春秋》之微旨。[37]494-495
这条材料,说明庄存与确曾为孔广森讲授《春秋》,而且孔广森认为庄存与所言确实讲明了《春秋》微旨,对其经说表示信服。陈祖武先生《关于常州庄氏学渊源之探讨——兼论〈春秋正辞〉之撰著年代》、黄开国先生《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皆曾引过此条,但未展开分析,我们这里不妨对比一下《春秋正辞》“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条的相关内容。孔广森所述之语,如“《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春秋正辞》说:“削诸侯而独著蔡侯,以为天下诸侯之国,未尝有如蔡者也。”如蔡“世役于楚,自绝诸夏”“用夷变夏者”,《春秋正辞》说:“蔡为楚之徒也……夫楚之为楚,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蔡实亲而习焉,久而不知,与之化矣。……欲其子孙之仁且孝,必以中国之法为其家法。蔡惟楚是亲,则惟楚是师。”如“不再传而蔡亦有弑父之祸”,《春秋正辞》说:“祸卒见于固与般之世。……其家果与楚同祸。”如“通《春秋》唯商臣与般相望于数十年之间”,《春秋正辞》说:“《春秋》有世子弑君,楚商臣、蔡般相望于八十四年之策书,若接迹然。”[15]164
可见,孔广森所述之语,《春秋正辞》中大义俱在,有些语句甚至极为相似。也就是说,庄存与为孔广森讲授的正是《春秋正辞》之经义,这也可从侧面证明,庄存与为孔广森讲《春秋》之时,《春秋正辞》已有成稿了。
其次,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影响清代公羊学后来发展走向的,是庄存与而不是孔广森。刘逢禄作《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绪的是庄存与,而非孔广森。
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与庄存与《春秋正辞》在体例上就非常相似,皆是总结《春秋》义例,以“例”统摄经传注文,又以经传注文举证“例”。刘书自序称该书旨在“寻其条贯,正其统纪”[38]2,与庄书自序“櫽括其条,正列其义”之旨,若合符节。而且二书之例,皆宗何休。朱珪为庄书作序称该书“义例一宗《公羊》,起应寔述何氏”[15]4。翻开庄书,卷一《奉天辞》之下,何休公羊学的核心“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6)“张三世”只见于叙目。皆赫然在列。刘书既以“何氏释例”命名,更以发明何例为己任,梁启超说刘书“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32]75,全书之首即是“张三世例”“通三统例”。此外庄书有“内辞”“外辞”,刘书则有“内外例”;庄书有“建五始”“正月日”“察五行祥异”,刘书则有“建始例”“时日月例”“灾异例”,亦可显现某种承袭关系。
而孔广森虽然也主张《春秋》有例,但对何休之例却并不太认同,其称“何邵公自设例,与经诡戾”“传所不信,邵公反张大之,目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37]730。其又说:“何氏之例,大国篡例月,小国时,又纳亦为篡,皆误也。”[37]351孔书中“大一统”“通三统”只见于对传注的引用,正文中“大一统”未见,“通三统”用“存三统”代替;“张三世”一词全然不见,其讲“三世”之义也只限于“三世异辞者,见恩有深浅,义有隆杀”[37]253,完全没有何休“三世进化”之义。我们看庄存与说“张三世”:“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大平以成。”[15]8刘逢禄说“张三世”:“《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38]4庄、刘所说分明都是何休“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
在对何休的态度上,也能突显孔广森和庄存与、刘逢禄的区别。庄存与称赞何休说:“公羊子之义,纳、入、立皆篡也,何休氏传之矣,允哉!允哉!”[15]232庄书通篇未见一字责备何休。刘逢禄对何休更是推崇备至,说何休“于圣人微言奥旨推阐至密”[38]193,“余宝持笃信,谓晋唐以来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门,不升其堂者也”[2]62。孔广森虽说“《解诂》体大思精,词义奥衍”,但却指出何休有两大“不通”,一是“承讹率臆,未能醇会传意”,二是“不肯援《穀梁》”“不取证《左传》”,并表示《春秋公羊通义》就是要“袪此二惑,归于大通”,对何休《公羊解诂》进行“存其精粹,删其支离,破其拘窒,增其隐漏”[37]730的工作。孔书中,屡屡称何说“误矣”“谬解”“甚谬”“殊非师说”[37]706,310,633,474,表示“所不敢信”“支离之说,今悉无取”,更说何休“不善读传矣”[37]329,398,579。以上用辞堪称严厉。
最后,庄存与、刘逢禄对公羊学大胆突破文本束缚的诠释方式持肯定态度。庄存与说“大一统”:“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义,莫大焉。”[15]10刘逢禄说《春秋》:“详略之以理嫌疑,偏反之以制新义,……圣人议而勿辨,其言弥微,其旨弥显。”[38]44-45而孔广森坚持严格以经、传文本为据,指责何休:“都无传文,横生枝说。”[37]302孔广森也因此完全否定何休“王鲁”等说,以为“圣人应符,为汉制作,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云云之说,皆绝不见本传”[37]722,何休是“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矣”,并引晋儒王接之语讥其“往往还为《公羊》疾病者也”[37]241,549。庄存与虽然也不认同“王鲁”,却并未加以指责,而是提出“《春秋》应天受命作制,孟子舆有言天子之事。以托王法,鲁无愒焉;以治万世,汉曷觊焉”[15]8。虽排除了托王于鲁、为汉制作,但却肯定了《春秋》受命作制、以托王法的内涵。刘逢禄则不光全盘肯定“王鲁”,更引《诗》之三颂,作为“新周、故宋、以《鲁颂》当夏而为新王之明征”[38]8。刘逢禄还做了一个解释:“《春秋》之托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且鲁无可觊也。……《春秋》者,火也。鲁与天王、诸侯皆薪蒸之属,可以宣火之明,而无与于火之德也。”[38]110其强调鲁只是燃亮《春秋》之火的薪柴,“王鲁”只是借以示义的一种工具而已,这样刘逢禄关于“王鲁”的表达就与庄存与有了一定的契合,尤其是“鲁无可觊”分明就是接着庄存与说的。如此看来,刘逢禄作书之前必曾接触过庄书此语。
我们知道,三世、三统、王鲁等说是公羊学的重要内容,这正是何休解诂《公羊传》的贡献所在,而孔广森皆予以否定或抽离其核心内涵。孔广森还把公羊学“三科九旨”的内容进行了抽换,从而招致了刘逢禄的严厉批评:“如是,则《公羊》与《穀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尚奚微言之与有?”[2]57-58正如《清儒学案》所说,孔广森“其于公羊,别立三科,自成一家之言,与武进庄氏、刘氏诸家墨守何氏之说者,宗旨故殊也”[33]4293。孔广森虽然也强调“《春秋》重义不重事”[37]725,其实他并没有走出乾嘉考据之学的治学路径。因此梁启超说:“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32]74也正因为如此,“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39]517的张之洞独对孔广森表示赞赏:“《春秋公羊传》,只读孔广森《公羊通义》”“国朝人讲《公羊》者,惟此书立言矜慎,尚无流弊”[39]170。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刘逢禄所说的“孔先生广森始以《公羊春秋》为家法”呢?此语出自《春秋论》下篇。该论上篇专攻钱大昕否定《春秋》褒贬书法之说,以立公羊家法;下篇专攻孔广森别立“三科九旨”,以正公羊家法。否定褒贬书法之人史上多矣,而上篇独举钱大昕。下篇的孔广森,一如上篇的钱大昕,也是刘逢禄立的一个靶子。彼时《春秋正辞》尚未刊刻,公羊学久束高阁,孔书以接绪公羊之名面世,却又否定公羊学的核心思想。当此“大义微言千钧一发”之际,深谙公羊托事明义传统的刘逢禄不得不“托始”于孔广森,奋起“钩幽起坠,干城御侮”[2]211。
也有学者提出,从刘承宽《先府君行述》所说的“府君……至《春秋》则独抱遗经,自发神悟”来看,“刘逢禄未承认庄存与对其公羊学的影响”[40]。拙文《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曾对刘逢禄的学术渊源有一个简单的叙述,认为刘逢禄公羊学固然属于自学,但是绝不可否认外家庄氏的学统对他的影响。[41]这里我们不妨对刘逢禄与庄存与的学术关系再作细致一点的梳理。
刘逢禄童年时,经常从母亲那里获闻庄存与的经说,其中就有庄存与“素精”[2]184的董仲舒之文。乾隆五十一年(1786),刘逢禄11岁时,庄存与致仕归里,考察刘逢禄功课,对其能熟读董仲舒文章非常高兴,说:“此外孙必能传吾学!”[2]209庄存与给予刘逢禄以“传学”的期许,而刘逢禄也恰在此之后开始了对公羊学的探索。“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继读《公羊》及董子书,乃恍然于《春秋》非记事之书,不必待《左氏》而明。”[42]2“十三岁,……尝读《汉书·董江都传》而慕之,乃求得《春秋繁露》,益知为七十子微言大义,遂发愤研《公羊传何氏解诂》,不数月,尽通其条例。”[2]209“年十有五,治《公羊春秋》条例之学。”[2]36
只是庄存与回乡不满两年便辞世,刘逢禄得庄存与亲炙的机会不多,庄存与给予他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方向的引领。李兆洛说:“申受(刘逢禄)所著《公羊》,多本宗伯(庄存与)。”[43]董士锡说:“嘉庆间,其弥孙刘逢禄作《公羊释例》,精密无耦,以为其源自先生(庄存与)。”[7]二人皆为刘逢禄好友,相交甚笃,其言刘逢禄公羊学渊源于庄存与,必不诬也。刘承宽在《先府君行述》中特意记下庄存与“传学”之语,其实也是意在表彰刘逢禄的传学之功。所谓传学,并非亦步亦趋全盘接受,而重在推进与发扬。刘逢禄也确实做到了将庄存与春秋学向前推进,发扬光大。
皮锡瑞《经学通论》说:“庄存与作《春秋正辞》,传之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诸人。”[44]618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是从传学的角度,叙述刘逢禄与庄存与的学术关系,并将庄存与列为以公羊学为标志的清代思潮“蜕分期”的开创者:“庄存与,始治《春秋公羊传》有心得,而刘逢禄、龚自珍最能传其学。”[32]5-6学术史的源流,往往是当时人不甚明了,而后人反而看得越来越清楚。
我们说,清代公羊学正是沿着庄存与《春秋正辞》开出的方向发展的,其复兴的路径是由庄存与发其端,再经刘逢禄全面发明公羊大义,至道光年间刘逢禄弟子龚自珍、魏源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至晚清康有为以公羊学说作为变法改制的理论基础,使公羊学在历史上再度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而孔广森公羊学虽另走一途,其源头实亦出自庄存与。因此,无论是从撰著时间,还是从学术渊源上来讲,清代公羊学的开山之作,庄存与《春秋正辞》都可当之无愧。